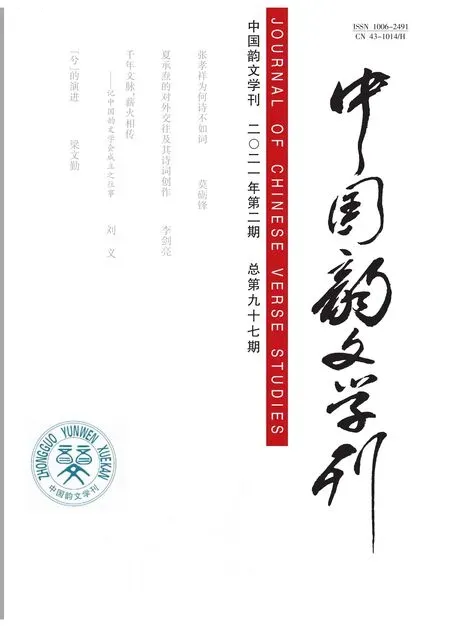夏承焘的对外交往及其诗词创作
李剑亮
(浙江树人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5;浙江工业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5)
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词学研究与诗词创作兼长。他的诗词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专为外国友人而作,如《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即分别收录了《谢日本林谦三教授书》(七绝)、《捷克女诗人译陶诗成,北京友人介其来杭相访两首》(七绝),以及《菩萨蛮》(谢神田喜一郎教授寄赠《日本填词史话》)和《清平乐》(再为艾德林教授题卷)等。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教师,夏承焘一生未曾走出国门,却创作了上述以对外交流为题材的作品,颇具特色。究其原因,与他当时所参与的对外交往活动有关。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教授受邀参与各级各类外事活动的历史,同时彰显与提升了传统诗词在现代外交领域的实用功能与文化价值。
一 参与官方的对外交往活动:从1951年至1965年
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所记,他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是在1951年1月,接待对象是捷克文化代表团。自此,直到“文革”之前的1965年5月,夏承焘先后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工作期间,受邀参加了30余场次的外事接待活动。
这些活动,有的是由学校安排的。如1960年10月7日,“夕顾祖康来,邀集会于其寝室,谓明早有捷克友人学中国古典文学者来访,中文系古典教研组拟开一座谈会”。又如,1965年5月3日,“晨八时,校长办公室来电话,谓日本友人八时半即来,应往会议室待之”,来访的日本学者为笕文生教授等。
还有一些是浙江省或杭州市相关部门安排的。如1955年8月4日,“午后院长室张君来,谓杭州交际处邀予今晚往迎日本和平代表团”。又如,1964年11月3日,“浙江科委及科研所来邀,明晨迎日本学术代表团”。
有时,甚至是来自省领导的邀请。如1957年4月25日,“夕接沙文汉省长请帖,往杭州饭店参加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宴会”。面对各方邀请,夏承焘都会欣然接受,参与接待。接待的方式丰富多样,包括游览文化名胜、走访各界名人、与外宾共进晚餐、参加座谈会以及观摩外国文艺团队艺术表演。
其中,游览文化名胜最为普遍。如1955年11月7日,夏承焘陪同罗马尼亚格劳乌尔院士游览西湖景点。“八时,往大华饭店晤格劳乌尔院士,同车往游孤山、岳坟。同车有外宾招待所丁君、法文翻译李君及管燮初君。格拉乌尔留学法国,以马列主义治语言学。”又如,1959年1月10日,陪苏联科学家艾德林游灵隐寺,访问盖叫天。“晨九时,浙江科学院曾衍堃以车来,同赴城站迓艾德林与余冠英。与艾君别二年,与余君别三年,几不复识矣。十时同在杭州饭店午膳。十一时同游灵隐,见大悲方丈。过玉泉,在岳坟同摄一影。艾君甚欲一晤盖叫天,午后二时同往访于金沙港。一家老小俟于门口。盖老七十三矣,脱长袍在庭院中为客演武松打店及赶美国人出台湾等剧,并令其四孙演水浒戏,一女孙五六龄亦能演梅兰芳身段。盖老边演边解释,历久不倦,五时方辞出。”
与外宾共进晚餐是一种比较正式的接待方式。如上所述,1957年4月25日,夏承焘在杭州饭店参加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欢迎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而举行的宴会。这应该是他参加的规格最高的宴会。“少顷,伏老进厅,周恩来、贺龙、彭真在门口延之入,此翁身材不高大,貌如六十许人,红润壮健,频频挥手点头。……与宴会者共二百人左右。”又如,1957年6月17日,应邀参加杭州市文化局交际处在大华饭店为招待法国汉学家考古团而举行的晚宴。“予与团长埃地安布尔谈甚多,谓法国一作家住中国五十年,顷与巴黎李君(中国人)合译《红楼梦》,甚谨严,已成三分之一(德国有译本不及此)。巴黎大学汉学家有一团体,研究宋代文学(戏曲),与世界各国治此学者联系,同席之叶理父等三四人,即其团员(共五六十人)。……予与南扬赠埃地安以《词人年谱》及《宋元戏剧辑佚》。九时半席散辞归。”
此外,参加座谈会和观摩文艺演出,也是接待活动中经常安排的议程。前者,如1952年10月5日与捷克客人的座谈,“午后有捷克大使馆商务专员莫利斯来校参观。文学院各系主任往陪,座谈一小时余。予问中国文学在捷克流行情形,答谓剧院演《白毛女》,鲁迅、丁玲小说有译本”;后者,如1952年11月23日观看中苏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主办的苏联著名艺术家表演会,会上,“乌兰诺娃与康德拉托夫表演之芭蕾舞(华尔兹及夜曲),米哈依洛夫独唱《船夫曲》《磨坊主》,纳赛罗娃高音独唱《和平摇篮曲》等,皆极动人”。
当接待的外宾是一位学者的话,夏承焘还会以书相赠。如1957年2月27日,夏承焘在参与接待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艾德林时,艾德林“以六年前所译《白居易诗》一册见示,予以《唐宋词论丛》为赠”。这一方式有时也是主办方所希望的。1956年6月3日,越南教育代表团来访,夏承焘与同事“送越南教育代表团离杭。校长嘱予与亮夫各送著作,予赠《词人年谱》一册”。
接待活动中最有仪式感的一项则是迎来送往。夏承焘也常常受邀参加。如1955年11月底12月初,西德历史学专家马尔悌斯教授来访。11月28日,夏承焘“午后接交际处电话,属予四时余往城站接外宾。同车者有文联秘书长郑伯永、华东美专分院院长莫朴”。12月2日,夏承焘“早五时四十分往城站送德国马尔悌斯离杭”。又如,1964年7月23日晚上,夏承焘与同事赴城站火车站送越南南珍等人离开杭州。“十一时二十分,南(珍)、阮(文环)暨范宁上沪粤快车。返舍已十一时四十分矣。”
这样的迎来送往,对年近花甲的夏承焘来说实属不易。对此,他也曾犹豫过。如1955年11月8日,“外宾招待所来电话,明早五时邀予往城站送罗马尼亚外宾。初畏冷欲不往,步奎谓此代表国家之任务,不可不往”。在深秋的早晨去车站送客,夏承焘起初有点惧怕天寒,后经同事劝导才克服困难,“晨四时半起,往车站送格劳乌尔院士,出门时天尚未亮,坐三轮车甚冷”。
正如同事徐步奎所说,夏承焘参与的上述对外交往活动是“代表国家之任务”,是官方活动。此外,夏承焘还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与国外学者联络交往。
二 与外国学者基于书信往来的学术交流
夏承焘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往的国外学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未曾谋面的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这与其研究领域有关,因为,对方大都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如林谦三、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清水茂等。在与这些学者的通信来往中,主要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等。如1960年12月19日,夏承焘接到了林谦三新近出版的《尺八新考》《博雅笛谱考》《伎乐曲の研究》三部学术著作。其中的《博雅笛谱考》一文,引用了夏承焘《唐宋词论丛》《论白石词谱》中的材料与观点。夏承焘只是“惜不能读其日文著作”。
夏承焘与清水茂的交往源自龙榆生的中介。1957年2月16日,夏承焘接到龙榆生寄来的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1956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文学报》第五册。该《学报》刊有清水茂评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文。夏承焘因此请了一位通晓日文的朋友给自己讲解。听完讲解,夏承焘感叹道:“清水君读予书甚仔细,并以《词学季刊》所登予《谱》校阅。所论皆甚中肯,赞美亦无溢辞。日人治学谨严可见。”自那以后,夏承焘便与清水茂开启了通信往来的历程。同年3月16日,夏承焘致函清水茂,并寄去《唐宋词论丛》。4月22日,接到清水茂复函,表示愿意将日本收藏的《又玄集》照相后,赠送给夏承焘。夏承焘接到清水茂寄来的《又玄集》后,第一时间联系出版社,并最终促成该书成功出版。1957年6月6日,“得古典文学出版社函,愿印《又玄集》,影印线装,第四季度出书”。至此,两位学者间的交流上升为两国学术资源的共享。
夏承焘通信交往的另一类学者便是他参加外事接待时认识的国外学者。当这些学者结束访问回国后,夏承焘与他们中的一部分因相近的研究领域或创作爱好,继续通信往来。如1964年7月,夏承焘参与接待了越南南珍等人。在南珍回国后的次月,夏承焘便致函南珍。时隔一年,又为南珍创作并寄赠两首七言绝句。不久,夏承焘收到了南珍来信以及“和诗”。
夏承焘与这一类学者的通信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其此前参加的外事接待活动的一种延续与深化。
三 为交往对象赋诗填词
通过考察夏承焘对外交流活动的经历,我们发现,夏承焘在其对外交流过程中,常常为交往对象作诗填词,包括外事接待的对象和书信交往的对象。
(1)为书信交往对象而作
如上所述,夏承焘与一些未曾谋面的外国友人的交往方式主要是书信往来、互赠著作。每当接到寄赠的著作后,夏承焘便以作诗填词的方式致谢对方。本文开头提到的七绝《谢日本林谦三教授赠书》,便是夏承焘接到林谦三寄来的三册新著后所作。诗曰:“灵峰芝坞冷香间,何日扶筇共往还。传语东风齐着力,万梅花底看湖山。”同样,《菩萨蛮》(谢神田喜一郎教授寄赠《日本填词史话》),也是因获赠书而作。词曰:“偏师一战归成霸,朗吟人亦从天下。槐竹各干云,后身应是君。 词流携屐地,回首今何世。万帜展东风,蓬莱怒海中。”词中“槐竹”是指森槐南与高野竹隐这两位明治时期的词人。夏承焘将神田喜一郎视作森槐楠、高野竹隐之后身。如此相提并论,当缘于神田喜一郎对这两位词人的评价有关。神田喜一郎在其《日本填词史话》中对这两人评价甚高。此次致函夏承焘,再次赞誉这两位词人,曰:“日本填词一道作者寥寥,江户时代末期,野村篁园、日下部梦香辈风气渐开,途径始通,大抵宪章竹垞,祖述樊榭,学步虽陋,稍觉形似,或可以发一粲;厥后迨明治时代,森槐楠、高野竹隐高据坛坫,相竞角技,自谓一时瑜亮,天下无敌也。”
(2)为外事接待对象而作
为外事接待对象创作诗词,是夏承焘以对外交流活动为背景而创作的主要体现,贯穿其参与的对外交流活动始末。作品数量较多,流传至今者,诗歌(均为七绝)有:《赠民主德国文学史家康托洛威茨教授》(1955年1月)、《日本和平代表松井岩男教授》(1955年8月)、《日本和平代表团团长高桑纯夫》(1955年8月)、《赠罗马尼亚格劳乌尔院士》(1955年11月)、《欢迎伏老》(1957年4月)、《捷克女诗人译陶诗成,北京友人介其来杭相访两首》(1960年10月)、《去年越南文学院南珍教授偕作家阮文环同志过访于杭州大学,闻将归赴南方国难,心壮其行。别后叠得南越抗战捷报,感奋无已,作此寄怀。南君才五十余,予已逾六十矣》(1964年7月);词有:《醉花阴》(艾德林教授嘱同译李清照词,作《醉花阴》,题其卷子)、《风入松》(苏联艾德林译香山诗成,顷复来北京研习陶诗,寄小词,邀其重游杭州)、《清平乐》(再为艾德林教授题卷)(均作于1957年2月)。
从创作形态看,这些作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活动当下应他人之要求而创作。如1957年4月25日,夏承焘在参加了沙文汉省长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而举行的宴会后,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江工人日报等报社纷纷要求他写作欢迎伏罗希洛夫的诗歌以便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宣传。于是,夏承焘就给这几家报社分别作诗。给浙江日报的一首为:“此日儿童识姓名,当年草木凛威声。好招泰岳坚盟誓,共挽黄河洗甲兵。”给杭州日报的一首是:“苍颜英概世无双,来缔同心漆与胶。他日与翁共照影,黄河如镜练如江。”给浙江工人报的有两首,一曰:“千雷动地万人呼,一朵彩云来绛都。四海明朝传盛事,老人星下看西湖。”二曰:“和平柱石海之东,欧亚如今峙两雄。试上湖楼携手看,高高南北有双峰。”其中,写给杭州日报的诗歌中,前两句“苍颜英概世无双,来缔同心漆与胶”,正面赞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功绩与盛名,以及他本次访问的使命和意义。
还有一类则是在活动结束后所作。如1960年10月8日,夏承焘参加学校接待捷克诗人李诗玛的活动。次日,夏承焘“晓枕作二诗送捷克李诗玛”。而写给越南诗人南珍的两首七绝《去年越南文学院南珍教授偕作家阮文环同志过访于杭州大学,闻将归赴南方国难,心壮其行。别后叠得南越抗战捷报,感奋无已,作此寄怀。南君才五十余,予已逾六十矣》,则是在南珍结束访问回国后的第二年创作的。
四 对外交流背景下的诗词创作
如果我们对夏承焘上述诗词作品的创作形态进一步比较与分析的话,就会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交往对象,其创作的过程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为外事接待对象创作诗词,更像是在完成“命题作文”。举例来说,他在参加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活动后,曾创作多首表达欢迎伏罗希洛夫主题的诗歌。他之所以创作这些作品,据夏承焘《日记》记载,是因为受浙江日报等多家报社之请。那么,这些报社为何要向夏承焘提出这样的请求?夏承焘为何在接到这样的请求后便立即响应而创作?这就需要从夏承焘受邀参加这些外事活动的原因去探究。
夏承焘受邀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的时间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间,新中国对外交流呈现出新气象、新格局,高校对外交流活动也因此日益活跃。各级宣传部门和宣传媒体在宣传报道这些活动时,除了采用记者撰写的新闻稿件外,也希望刊发学者们以文学手段创作的诗词作品,从而增强宣传报道的艺术性。于是,高校中擅长诗词创作且学术造诣高的学者,往往受邀参加外事接待活动。夏承焘之所以多次被邀参加此类外事接待活动,也当缘于此情。因此他既要参加上述对外交流活动,还要创作诗词来艺术地反映这些活动。
在此背景下创作的作品,在立意和措辞等方面难免存有令人不甚满意之处。仍以夏承焘为欢迎苏联领导人来访而创作并在杭州日报发表那首为例,诗曰:“苍颜英概世无双,来缔同心漆与胶。他日与翁共照影,黄河如镜练如江。”该诗发表后就引起读者的质疑,于是夏承焘又“发杭州日报一稿,答某君问迎伏老诗三疑”。三天后,杭州日报刊发了夏承焘的这篇释疑的文章,“杭州日报今日载予答洪祖经一短文,论迎伏老诗”。
又如,夏承焘曾经为艾德林作《清平乐》(再题艾德林教授卷)词,其中以“烂熟白家长庆集”一句,来称赞这位苏联学者对白居易诗集的熟稔程度,似有过誉之嫌。这大概也是这类“命题作文”难免的问题。对此,夏承焘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晚年编录诗集、词集时,对这类作品的选录颇为严格。
但这些现象并不影响上述作品的创作意义和传播价值。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之关系,一直是诗人们十分关注的命题。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这既是对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阐述,也是对作家历史使命的一种自觉追求。“为时而著”,对诗人而言,意味着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承焘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之外,屡屡参与对外交流活动并以诗词加以表现,也是对“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一宝贵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他的这些作品,在当时,为配合相关部门宣传、报道对外交流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文学的实用功能。在今天,这些作品又让人们得以重新领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教授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的情景与风采,体现了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从夏承焘诗词创作历程看,这些作品又丰富了他的创作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