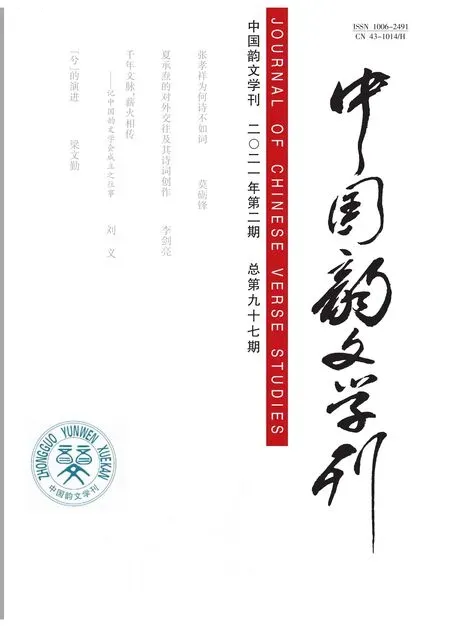学政顾莼与嘉道云南士风
李 超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清代乾嘉道三朝,云南人才辈出,风雅大盛,这与清政府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治理分不开,更是内地文化对边疆影响的结果。内地文化对边疆发挥的影响,一是通过内地官员仕宦云南,主衡云南,推行文教,作育人材实现;一是由云南士子科举仕宦,走出云南,与内地文人交往中耳濡目染习得。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对云南文学的意义尤其重要。因此,仕宦云南的官员,尤其总督、学政对云南士子的影响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本文以嘉庆十七年云南学政顾莼为对象,以期为研究云南文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顾莼其人
顾莼生平,《清史》有传,另外朱士彦《顾南雅传》、程恩泽《皇清诰授中宪大夫通政司副使顾公墓志铭》、戴纟冋孙《顾南雅师行状》所记甚详,可知:公名莼,字希翰,一字吴羹,号南雅,晚号息庐。先世自江宁迁吴县。曾祖渐,为州同知;祖阶升,考应昌,皆为国学生,俱赠中议大夫。莼自少能为文章,工书画,尚气节,以诡随险诐为耻,为诸生见赏于掌教钱少詹、吴进士霁、学使胡文恪、钱少宰。嘉庆七年中进士,官编修。十三年,充会试同考官。十七年,御试翰詹,名列第一,擢翰林院侍读,是年放云南学政。二十五年,授日讲官,擢侍讲学士。上疏不称旨,降编修。道光九年,擢右中允,擢侍读。十年,擢侍讲。十一年,擢通政司副使。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
顾氏是吴中著姓。其祖父顾阶升,字步岩,“唯以图籍、法书、名画自娱”,精于赏鉴。其父顾应昌,字殿舍,号桐井,行第五,又自号五痴。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称:“《会稽三赋》,余所见三本,一得诸顾八愚家,一见诸顾五痴家。八愚、五痴为昆仲。”可知其叔父号八愚。祖、父、叔三人皆以藏书著称。顾莼《先考桐井府君行述》记载:“东庄先生遗书极富,皆善本,有借读者,绝不吝,曰:‘吾父尝言,我有书不能读,得他人读之,我书庶不徒具。’”藏书而不吝书,颇有世家子弟风范,为顾莼所秉承。顾莼有弟名顾蘩,字薲洲。
顾莼师长辈,诸生时的钱少詹即钱大昕,号辛楣,竹汀居士;吴霁字倬云,号竹堂;胡文恪即胡高望;钱少宰即钱樾。皆一时名流。顾莼嘉庆七年参加会试,考官为纪文达晓岚、铅山熊谦山、满洲玉研农、大庾戴可亭。师长辈还有翁方纲,号覃溪,历官至内阁学士。此外,资料所见,顾莼与名流孙星衍、钮树玉、陈鸿寿、张问陶、黄丕烈、吴锡麒、韩崶多有往还。
顾莼生平中重要的交往是进士同年。今存《嘉庆壬戌同年雅集图》,图中除去顾莼,其余14人:谢学崇,字仲南,山阴人;朱鸿,字云陆,秀水人;沈维鐈,字子彝、鼎甫,嘉兴人;吴廷琛,字震南,号棣华,元和人;梁章钜,字茝中,又字芷邻,号茝邻,晚号退庵,长乐人;陶澍,字子霖,号云汀,安化人;朱珔,字玉存、兰坡,号兰友,泾县人;吴椿,字荫华,号退旃,歙县人;申启贤,字子敬,号镜汀,延津人;龚守正,号季思,仁和人;孙世昌,字少峰,号少兰,桐城人;李宗昉,字芝龄,山阳人;卓秉恬,字静远,号海帆,华阳人;朱士彦,号咏斋,宝应人。此外,同年中还有吴县(现已撤销)潘世恩、宜黄洪介亭与顾莼交往密切。这些人在朝为官或历任地方官,活跃于嘉道诗坛,所存诗集中多有赠顾莼诗作。
顾莼人品学识俱佳。其《黄定轩同年传》中批评当时不良风气,谓:“余尝怪今之人,一入仕途,亲虽老,置不顾,必及于丧而始归,虑人议其后也,则曰:吾亲故矍铄,勉我以专心事君,勿得顾私情。人果有不顾其亲而能忠于君者耶?其亲纵有是言,亦逆知其子之必不归,姑为饰词以掩子之过,不知其饮泣于无人处也。”坚持孝亲才能忠君,颇能反映他读书人忠孝的观念。顾莼在官场尤为人称道的是尚气节。《清朝艺苑》卷十《顾莼奏疏之敢言》,记其听闻逆匪林清之变后,上疏朝廷要严密中禁,尤其圆明园要严防敌人乘虚而入;其擢学士也,适值道光初登极位,上疏君王要崇君德、正人心、饬官吏;其再迁学士时,上疏请于喀什噶尔添重兵控制安集延边,宜牧民屯田以备西域滋扰;其迁通政司时,适两湖三江皆大水,上疏称饥民与盐枭纠合,易生事,建言变通盐法,听民挟赀趋产盐地收买。由此称赞顾莼即使“论事左迁,冷署回翔”仍然“侃侃敢言,忠爱惓挚”的品格。朱士彦为其作传道:“呜呼!翰林以记载文诰为职。苟少知文之模范,行己无大过失,委蛇栖迟,率可致尊显。君独勤勤恳恳貌,以建言为务,虽遭摈斥不少悔,忠爱之性,实有过于寻常者。”顾莼道义风骨得到朝臣公认,程恩泽《通政司副使顾公墓志铭》云:“自公卒后,天子以畿辅久不雨,诏求直言,朝野追思公者,谓使顾公少留,必有格言谠论,裨益国家,而公不及待矣。”综观顾莼言行,个性耿介戆直。蒋宝龄将顾莼的行实追溯到苏东坡,谓“先生少日最重苏文忠之为人,曾画《从游赤壁图》以志向慕,故其言事获咎,屡进屡蹶,亦略似云”。顾莼年少所作《秋树》中“孤干贞心迥出尘,不随凡本共沉沦”两句,正是一生襟抱写照。
顾莼兼工诗书画,“书工楷法,师欧阳率更,下笔英挺”,“行草、分隶亦沉郁入古”,“画梅宗杨补之,水仙学赵子固,写兰不专一家,或肆为披纷,或敛为简淡,皆天真自然,不求妍妙而别饶风格”。《新世说·巧艺》将其视为乾嘉风雅大盛十六画人之一。顾莼著述现存《思无邪室遗集》4卷、《顾南雅先生制艺》1卷、《顾莼致黄丕烈书札》10通、《顾南雅尺牍》1卷等。
二 顾莼实学思想与云南士习丕变
顾莼生活的嘉庆道光年间,是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之时。学者指出,时人对顾炎武的态度正是此种思潮的一道风向标。顾莼在国史馆编纂《顾亭林先生传》,可见其学术倾向。在传记中他引述顾炎武“窃叹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名与仁,夫子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者,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厥中’”一段。此段顾炎武自然是批判宋明理学,重新高扬传统儒学。接下来引述顾炎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之语,有鲜明的天下家国实学色彩。近人楚金《道光学术》指出“亭林所犹重者,在于敦砺品节,以成致用之才。所谓经世之学,所以阐宋儒未尽之蕴者。”顾莼原文引述,正说明他对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体认。后来《国史儒林传》以顾亭林传为首,是否始于顾莼,难以确考,但顾莼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顾莼的姻亲朱珔《顾亭林先生像赞》序称“受先生族裔之请”题识,这族裔很可能就是顾莼,序中有“硕学开昭代之始,舍先生其谁与归”的认识,很可能受顾莼的影响。顾莼还有《惠砚溪先生传》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人作传,文中引钱大昕语:“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虚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乾隆五十四年,钱大昕入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以精严古学、实事求是作育一方俊彦。从顾炎武、惠栋到钱大昕,延续了复兴古学的道路,贯穿了学古以致用的思想。而顾莼正是钱大昕紫阳书院弟子,他对顾炎武、惠栋的体认,或许正得于乃师。顾莼立于经世致用的潮头,强调以传统儒学敦砺品行,成就致用之才,并实践经世之学。
顾莼于嘉庆十七年任云南学政。陶澍《送顾南雅侍读督学云南序》称:“陛辞之日,天子雍容召见,语以云南虽边徼,其名惇且文,一切培养之法宜立。盖天子所以徯顾子厚矣。顾子亦可借是以报特达之知,而造士于云南。”赴任之际,得嘉庆帝亲自召见,并多有勉励之语,因此顾莼云南学政之行,黾勉努力。到任不久,他接连上了几通奏折。在《授云南学政谢恩折》云:“臣现饬各学校教官集文武生员,谕以我皇上嘉惠士林、崇尚实学之至意。臣仍于接见之时严加训导,俾知致用端在乎通经,储才必资于扶质。庶先器识而后文艺,笃修为臣为子之经,正士习以式民风。”“崇实尚学”“致用”等字眼,充分反映了顾莼的经世思想,也反映了顾莼牢记圣上嘱托,为改变云南士风勤勉努力的意愿。他有如下举措:
首先重视场屋考试公正严肃性。《慎重武试以端士习疏》中,他称云南武生考试中“内场默写《武经》字迹模糊十有七八”,而且挟带之弊、代倩之病往往不免,因此在云南广西、曲靖两棚他亲自监考,以期杜绝作弊行为。并上疏君王,建议武考除默写《武经》百余字外,复令默写《孝经》《四书》各百余字,“字数较多,则无暇兼顾他人,书本较厚则挟带难而搜捡易出”。他还严惩马光庭与包玉桂换卷舞弊案件。又“其童生覆卷,远逊正场者又斥去数人”,收获“诸生童俱能恪守场规,绝无枪冒传递之弊”的成效。
其次重视书院教育,作兴人才。顾莼今存“养成心性方能静,实用人才即至公”一联,足见他对人才实用的期许。他“自书朱子《白鹿洞规》镌之石,嵌二书院壁间,又于节署西偏颜其轩曰‘树木择士之才,而贫者留读其中’”,反映他对人才尤其贫寒子弟的爱护。他又担心学政与诸生势分太疏,必无以收教益,所以闲暇之时,“谕令生员逐日进署,与之论束身砥行之道,庶异日或有品学兼优足以效用国家者”,亲自教导,诲人不倦。
再次编纂选集,以示轨辙。他认为“文者,心之声,文不趋正轨,行必入邪僻”,因此‘“日进诸生,教之以修身敦行,至于作文,务使黜华崇实,根柢经史”。他先后编撰《试牍扶质集》《试贴必以集》《思无邪室制义》《选八家文》,还有《律赋必以集》,该选本序称:“见生童于作赋之法多所未谙,因择其稍有思绪者重试之,日讲手画,诸生童颇有开悟,唯念不能遍喻,特选唐律赋一卷,附宋赋数首于后,以观其备;继念唐人之法盖有所受,复选汉以来古赋俳赋以溯其源。”可谓用心良苦。现存赵辉璧《古香书屋文钞》,其制义稿后多保留有顾莼的评语,反映了顾莼对士子作文的悉心指导。
顾莼曾有《映雪校文图》以记其为国选才之剪影。在他努力下,云南士习丕变,“诸生咸知自好,力洗从前肤浮之习,文风遂骎骎日上”。李于阳称:“习尚返淳朴,声华黜浮伪。”朱雘称“遂令彩云地,人与云相郁。”顾莼“使滇四年,凡所甄拔,俱有本末可观,滇士翘颖者多出其门”。这些翘颖的滇士,可考者有:范仕义,字质为,号廉泉,嘉庆十九年进士;李煌,字栯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池生春,字钥庭,道光三年进士;黄琮,字象坤,号矩卿,道光六年进士;赵辉璧,字蔺完,一字子谷,号苍岩居士,道光六年进士;朱雘,字丹木,道光九年进士;窦垿,号兰泉,道光九年进士;戴纟冋孙,字袭孟,号筠帆,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戴家政,子子政,嘉庆二十一年举人,等等。像范仕义,“为人宽平仁恕,于民不扰,民德之,呼为‘佛子’,及再任如皋,百姓撰联,有‘士民皆望慰,父母喜来归’之颂”;像池生春视学广西,“课士先行谊而后文艺,其大旨曰立志、曰修身、曰穷经、曰讲学”;像黄琮,告养回籍,掌教五华书院,咸丰兵乱,自经家庙中,赐谥文洁;像戴家政,“训士以礼,士贫不能应省试、礼部试者,多资送之”,“风范端严,加意作育,接见士人必以礼法相绳”。这些弟子品行多有顾莼的影子。赵辉璧《读南雅师遗集感念示诸门人》云:“师门报德今无地,好借传衣惠士林。”弟子们以这样的方式感念践行顾莼的教诲。难怪林则徐《跋顾南雅手泽》称:“滇中人士于南雅无不尸而祝之者。”
三 顾莼文艺观念与云南风雅之教
顾莼提倡作文文道合一,文章与政事同源。他就文与质关系立论,认为:“三代以来,制作日夥,上者以文明道,下者因文求道。道者,文章之质,不可离而二也。”在《思无邪室制义序》称:“自来论诗古文者,皆薄制义,谓其摹口气而无我在也,然制义代圣贤立言,人孰不当以圣贤之心为心,则圣贤之言者仍是言我心。”《祭熊谦山夫子文》:“呜呼,文章政事,从古同原,不悟其原,其途判然。猎词华者,名义灿陈,茧丝保障,无长可观;谈经济者,才足处艰,不学无术,贻诮遗编。”这些观点可以说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散见于他为别人文集所写序言中。
于诗歌,他主张从性情学问出,强调性情之正。在为明人屠隆《园居杂咏五十首》所作跋中称:“诗本性情,要轨于正。而不必尽同老杜,得风雅宗主。而太白近于仙,摩诘近于佛,一并以诗称。如李邺之学仙,富文忠之学佛,皆不失为名臣,特以性情正也……何必强同于退之、放翁,而始为诗耶?”他认为只要创作主体性情正,无论学佛学禅学仙,诗歌皆有可观。《借秋亭诗草序》,他又提出性情之真,称:“诗贵得真,凡入廊庙山林之异,其遇穷通顺逆之异,其境喜怒哀乐之动于中,好恶攻取之感于外,凡所见山水草木鸟兽虫鱼之有以触于怀,皆必有所不能自已者。因是一寓于诗,故见其诗,可见其人。”在为总督伯麟《退思斋吟草》作序中对近世诗风批评道:“余尝论,自世之能诗者多而诗之道衰,古之人本不欲以诗名,惟蕴其学问之所积,感于性情之所触,动于闻见之所历,发于不能自已。故见之于诗,虽千万世尤可想见其为人而因之兴起。自后世以声调格律相尚,于是取工于字句之间,势不至有明七子之弊不止。近今五六十年来,知惩其弊矣。而以抒性灵为主,夫诗主性灵是也,顾本其庸妄之志以逞其淫靡之词,使古人以诗闲邪之旨荡然无存,不更谬乎?余昔有句云:‘譬诸桀纣性,庸愈五伯假。’非为明七子解嘲,深痛若辈挟其藩耳。”顾莼对当世斤斤于格律、独抒性灵的诗风表示不满,可以看出他反对淫靡,认为性情之真是从蕴积学问出,从而肯定伯麟的纯臣之心、忠良之性。《味经书屋诗稿序》云:“窃怪世之称诗者,或章摹句仿,界宋分唐,其流也常失之伪,矫其弊者,专主性灵,似矣而或侧艳淫哇,或纤佻浅俗,其流也,又失之荡,入主出奴,互相诋诮。”仍然不满的是俗情滥情之性灵,反对斤斤模拟,反对壁垒。从其诗论,可见顾莼的诗学功力。其诗作留存很少,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说顾莼“诗集罕觏”,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顾莼《云在轩遗集序》所说:“余于诗古文本无所得,刚曾十二三岁,见辄为收贮,及其死,余悉取焚之,自是不复作。”因此其创作倾向也难以看出。但顾莼活跃于嘉庆后期诗坛,参与翁方纲寿苏会,他与同年一道成立消寒诗会(即后来的宣南诗社)。翁方纲评价其诗与字“皆有骨,能用功,当传世”。吴嵩梁《石溪舫诗话》称顾莼“诗不多作,而格高音雅,如王、谢子弟,自有大家风韵”。
顾莼虽不大留意于诗歌,但以自己的亲身力行带动了云南诗坛的风雅。他在校文时注重对弟子诗学的指导。顾莼《行次禄丰夜雨不寐成古诗五章聊示诸生》云:“文章虽小道,言实心之声。如木蟠根柢,当春自扬英。雕虫逞奇技,窜雉矜飞鸣。弋获趋所尚,矢音表其贞。安得昌黎伯,一挽狂澜倾。”勉励云南学子诗文要有根柢。戴家政《观野烧》诗跋称:“此吾师顾南雅先生前科试考古题也,时得首拔,亟蒙奖誉,此诗实受知吾师之始。先生归省,晤五华山长刘寄庵师,曾诵及之,且云,将来各体都可成就。”也反映顾莼对云南士子诗事的注重。在为弟子严廷中诗集作序中称“文章一道,关乎性情学问”,勉励严廷中“当以读书明理为要,一切经济政事俱当趁此时”,并谓“实不欲以诗人名足下,即如老杜之许身稷契,韩子以卫道自任,若使其得志,岂欲以诗名?唯其不欲以诗名,此诗所以绝顶耳”。这些都是在向弟子传授诗学自得。
顾莼任学政期间正是昆明诗坛雅集盛行之时。从现有记载看,顾莼与时任云贵总督伯麟关系融洽,与刘大绅关系相得。顾莼任云南学政是嘉庆十七年,而刘大绅入主五华书院也是此年,两人私交非常好。刘大绅《送顾南雅先生述职入觐》其三云:“先生一相见,谓此真吾徒。车马日过从,吹嘘忘朽枯。珍馐助朝膳,堂北增欢愉。”又有《梦伯玉亭先生赋寄顾南雅先生》称:“百年数知己,曾未一二得。”他把顾莼视为真正知交,他们一道促成了嘉道云南的风雅之盛。如顾莼《丙子乡试放榜前二日选拔诸君携酒进署雅集》、池生春《丙子十二月陪顾南雅先生圆通寺赏雪分韵得暮字》、赵辉璧《试竣将归呈顾南雅师督学》《顾南雅师招至湖心亭赏雪即席赋诗分得双》等诗,以及戴纟冋孙《奉怀顾南雅师》其五自注:“丙子十一月十一日,师以及代将还, 招诸同人集翠海莲花寺赋诗。”这些都可以说明顾莼与弟子们诗学活动的频繁。顾莼还以翰墨为云南风雅助兴,这不能不提黑龙潭唐梅的品题。顾莼有数幅唐梅之作在士林流传,而刘大绅与弟子常于唐梅下雅集,当时戴纟冋孙、马之龙、倪绣、杨载彤、侯锡珵、马骏、杨松麓、牛焘等五华子弟都有唐梅之作,甚至一些相同的诗题如《问讯龙泉观唐梅》,很难说不是受到顾莼的影响。吴嵩梁《顾南雅学士滇南纪胜图》其实指出了这一点,称:“知君选胜即抡才。”又称:“老梅艳发唐朝树,蟠根下有双龙护。门生载酒及花时,应念醉翁行乐处。教泽如今被百蛮,云泉常在卧游间。”说明顾莼与云南士子唐梅下的诗画风雅是常态。顾莼还常以书画题咏砥砺士子品行。戴纟冋孙《何子贞编修以先顾南雅师画梅属题即倒用图中先师元韵》结句称:“炼骨冰霜总未能,我愧苏门老晁子。”自注:“先生尝三为纟冋孙画梅,其题词皆以用世勉之。犹记丙戌下第后,出画梅纨扇相赠,有‘且向空山炼骨来’之句。”顾莼还画梅赠“五华五子”之一的戴淳,题诗:“羡君诗思清于水,我写梅花清似君。”皆是此类。陶澍《送顾南雅侍读乞假还吴》诗注:“南雅督学云南,士服其教,去后闻于省城黑龙潭两侧为建生祠,与汪云壑同祀。”于黑龙潭立生祠,显然是别有纪念意义。顾莼在任期间,云南诗坛不仅出现了著名的“五华五子”,昆明诗坛还有“五才子”之谢琼、王长卿、尹尚廉、杨文源、王毓麟,以及五华学生诗人群体,诗学彬彬大盛。
小结
总之,在四年的云南学政期间,顾莼以实学思想砥砺人才,端正士风,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有为进士,又以自己的诗学功力和艺术修养,促成了滇南的风雅大观。离开云南之际,他作《滇南山水画册》12幅,以不忘旧游。云南士子洒泪送别,并有送行诗作。刘大绅《顾南雅先生还京送行诗册序》,联想《诗经·甘棠》篇,将顾莼于滇南的教化媲美召伯布文王之化巡行南国之功。顾莼逝去后,朱士彦挽联云:“魏阙鉴诚衷,建议词臣追汲黯;滇池施善教,酬恩祀典泣侯芭。”林则徐《挽顾莼》云:“风节树朝端,鸣凤声高,为感恩慈酬再造;文章惊海内,登龙望峻,更余书画重千秋。”顾莼遗集,黄琮等门人为之收集刊刻。清代岭南著名诗人宋湘《题顾南雅先生映雪校文图》云:“吾道宗风要主持,臣心冰雪路人知。苍山洱海英灵在,记起昌黎解学时。”洵可作顾莼滇南教士的风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