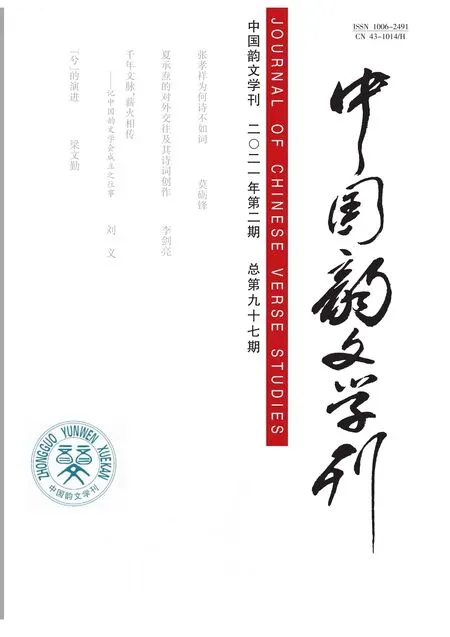论唐宋词三大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王靖懿,张仲谋
(1.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其后,王昌龄首倡“意境”,殷璠拈出“兴象”,以及司空图“象外之象”说,严羽“兴趣”说,王士祯“神韵”说,王国维“境界”说,诸此种种,彼此勾连,相互生发,构成中国文学个性卓荦的理论系统。
关于意象,我们的理解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当某种自然物象与特定的人文内涵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这种艺术形象就被视为意象。这种界说一是强调意象应该具有形象性,二是强调意象应该具有人文内涵,从而避免对意象的泛化理解。有些论著把诗词中的各种动物、植物等等一概称为意象,其实是不妥当的。意象又不同于典故。典故是基于历史人物故事而形成的,其内涵比较稳定而单纯;而意象是经过长期创作实践与欣赏经验积淀而成的,其内涵更丰富也更灵动,比典故更能引发丰富的联想,也更富于诗意。叶嘉莹先生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把那些能够揭示词人创作旨趣、引发丰富联想的语辞称为“语码”,而她所说的语码,大部分是由意象构成的。
唐宋词的意象系统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梅、柳、蘋、絮等植物意象,雁、燕、蝉、萤等动物意象,帘、屏、扇、镜等器物意象,以及檀郎、谢娘等人物意象。然而在林林总总的唐宋词意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残阳和落花两种意象。残阳就是夕阳,是黄昏或薄暮的标志,是一日之末与人生暮年的象征物;落花是暮春的标志,是花事凋零、青春将逝的象征物。和残阳对应的是流连光景的生命意识,和落花对应的是美人迟暮的伤春意识。残阳和落花两种意象是绮怨词的标配。另外一种值得关注的意象是春草。因为伤春伤别是唐宋词的基本主题,词中的春草意象出现频率也很高,所以本文主要分析残阳、落花和春草三种基本意象。
一 残阳与生命意识
残阳或黄昏使人感伤,是建立在类比思维上的自然反应。人们总是在不自觉间把人从少至老的一生比作太阳的东升西落,所以青少年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老年就是暮年,故李密《陈情表》曰:“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在汉唐间的诗文中,以白日西沉比况人生之衰老,早已内化为一种思维模式。如曹植《箜篌引》:“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刘琨《重赠卢谌》:“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谢灵运《豫章行》:“短生旅长世,恒觉白日欹。览镜睨颓容,华颜岂久期。”李白《古风》:“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姚合《哭贾岛》:“白日西边没,沧波东去流。名虽千古在,身已一生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才会说“愁因薄暮起”,皇甫冉《归渡洛水》才能得出“暝色起春愁”这样的大判断来。
所谓“残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意象,而是一个可以变化衍生的意象群。意象群是由三个以上共同指向特定人文内涵或情感意蕴的意象复合而成,它跟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所提出的“意象串”内涵相似,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和纵深性等特征。“意象的组接,生成意象群;意象群的连缀,构成意象系统。”试以《全宋词》为检索文本,检索可得“黄昏”567条,“斜阳”452条,“夕阳”259条,“暮云”192条,“日暮”142条,“斜日”118条。其他还有斜晖(47条)、残阳(44条)、日落(34条)、薄暮(33条)、日斜(30条)、残日(27条)、夕照(21条)等等。因为汉字具有超强的单字组配能力,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变化呈现方式。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谈唐宋词中的黄昏和斜阳意象。
斜阳与黄昏属于同一个意象群,但不是同一个意象的别称。这两个意象之间的微妙区别是,斜阳虽然已是残阳,但它还没有落山,而黄昏则比之稍后,是太阳落山而天尚未黑的一段光景。也正是因为这种相邻相生的关系,赵令畤才会说“恼乱层波横一寸,斜阳只与黄昏近”(《蝶恋花》),李莱老亦云“斜阳苦与黄昏近”(《杏花天》)。把两种易于生愁的意象叠加起来,就是古人所谓“加一倍”写法。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既曰“斜阳”又曰“暮”,和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中的“青山万里一孤舟”一样,也有递进强化意味。有人说秦观“斜阳暮”伤于重复,不仅拘泥,亦少见多怪。秦观之前有柳永《夜半乐》“空望极,回首斜阳暮”;秦观之后有赵彦端《点绛唇》“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张震《蓦山溪》“情脉脉,酒厌厌,回首斜阳暮”;而秦观自己也另有《点绛唇》“烟水茫茫,回首斜阳暮”。“回首斜阳暮”五字三重四复,不知是何原因,但至少在宋代词人们看来,这“斜阳暮”连用是没毛病的。
黄昏生愁,宋词比唐诗有更突出的表现。柳永《诉衷情》:“思心欲碎,愁泪难收,又是黄昏。”苏轼《虞美人》:“日长帘幕望黄昏。及至黄昏时候、转销魂。”晏几道《两同心》:“好意思曾同明月,恶滋味最是黄昏。”李之仪《踏莎行》:“王孙一去杳无音,断肠最是黄昏后。”赵令畤《清平乐》:“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赵长卿《水龙吟》:“最消魂,苦是黄昏前后,冷清清地。”陈亮《眼儿媚》:“愁人最是,黄昏前后、烟雨楼台。”石孝友《摊破浣溪沙》:“正是悲伤愁绝处,更黄昏。”张炎《梅子黄时雨》:“最愁人是黄昏近。”吴礼之《雨中花慢》:“酿造一生清瘦,能消几个黄昏。”诸此种种,几乎是同样的意思,两宋词人如此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唐宋词中的斜阳,在画面布局和意境营造方面,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最常见的是与草相配。有些与春草、芳草相配,那是渊源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用于烘托伤别念远的主题。如张元干《踏莎行》:“芳草平沙,斜阳远树,无情桃叶江头渡。”韩淲《风入松》:“望中一片斜阳静,更萋萋、芳草还生。”吴文英《诉衷情》:“忍教芳草,狼藉斜阳,人未归家。”有些与衰草相配,那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悲凉的情调。如辛弃疾《踏莎行》:“西风林外有啼鸦,斜阳山下多衰草。”周密《献仙音》:“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僧宝月《洞仙歌》:“水亭山驿,衰草斜阳。”基本手法是压低视线,使衰草与斜阳叠映,既有情调,也有很强的画面感。
还有的与飞鸟相配。如赵师侠《清平乐》:“苦恨无情杜宇,声声叫断斜阳。”吴文英《浪淘沙》:“秋色雁声愁几许,都在斜阳。”这是以声为用,是为了有声有色。更多的是动静相配。如贺铸《想娉婷》:“鸦背夕阳山映断,绿杨风扫津亭。”周邦彦《玉楼春》:“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吴文英《夜行船》:“鸦带斜阳归远树。无人听、数声钟暮。”仇远《蝶恋花》:“秋又欲归天又暮,斜阳红影随鸦去。”这些词句均有意营造斜阳与鸿雁或乌鸦齐飞的动感效果。观此乃知臧克家的新诗《难民》中的警句“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虽然是中国新诗史上推敲修辞的著名范例,臧克家亦自言是殚精竭虑,数易其稿,其实好言语早已被前人道过。
因为斜阳在组构景物、制造情调方面有比较强的整合晕化功能,唐宋词中常用于歇拍处。在这方面,李白《忆秦娥》已为宋人提供了典范。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李白词的沉郁气象,当然和洒在那荒陵断碑上的一抹斜阳有关。宋人深悟此法,往往把斜阳系于词末,既有返虚入浑之效,又平添一种悲凉况味。如晏殊《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李邴《清平乐》:“又是危阑独倚,一川烟草斜阳。”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李曾伯《八声甘州》:“斜阳外、梦回芳草,人老萧关。”这不仅是以景结情,尤贵在意境含浑,有苍茫沉郁气象。
因为斜阳本身自带悲凉情调,历来登临怀古之作,总喜欢以斜阳为点缀,以助成兴亡之感。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当然是经典之作,后来杨慎《临江仙》写白发渔樵在江边笑谈今古,也是因为在夕阳返照下显得更有韵味。宋代登临怀古之词,总喜欢以夕阳余晖为点缀。如柳永《双声子》: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唯闻麋鹿呦呦。 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在柳永《乐章集》中,这是为数不多的登临怀古之作,见得柳永在刻红剪翠之余,还有这样一种怀古情怀。词的构思一般,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为常见模式。但值得肯定的是结尾二句,“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把吴越争霸的历史遗迹,范蠡、西施的风流韵事,一笔抹去,眼前只见得斜阳下暮草茫茫,氤氲成一派愁情。柳永的词因为好写男欢女爱而不免俗气,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但凡写到斜阳处,总能平添一份深沉。比如他的《玉蝴蝶》:“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木兰花慢》:“纵凝望处,但斜阳暮霭满平芜。”《临江仙引》:“凝情望断泪眼,尽日独立斜阳。”叶嘉莹先生曾发现,柳永那些萎靡俗气的词多写暮春,而他写清秋雨后的词大多清新近雅。实际上,柳永写到斜阳的词亦多为雅词,或因为斜阳的忧郁色彩会冲淡一些俗气,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
宋词中写斜阳的名句,是周邦彦《兰陵王》中的“斜阳冉冉春无极”。前代词家,赞不容口。谭献《复堂词话》说:“斜阳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入三昧、出三昧是禅宗术语,这里借指出神入化的境界。梁启超评曰:“斜阳七字,绮丽中带悲壮,全首精神提起。”程千帆先生专门著文《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对该句的好处及各家评语有精彩的分析,可以参看。
二 落花与美人迟暮
“落花”是另一组意象群,在唐宋词中也有多种变化组合方式。检索《全宋词》,可得落花300例、落红96例、落英29例;残红122例、残花64例、残英34例;花飞235例、花落170例、花谢67例、花残56例。这些词例虽然不宜简单相加,但去掉交叉重复,也不考虑其他变化形式,至少也在千首以上。这就难怪我们在唐宋词中经常会看到花谢花飞、落红成阵的暮春光景了。
唐宋词多写春天,但很少是歌唱春天的生机活泼,而是喜欢徘徊在暮春光景里独自伤感。像朱自清的散文《春》中所写:“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这一看就是“五四”之后的青年文人,而绝不是千年之前的宋代士大夫。唐宋词中的风景,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美人,在暮春时节,黄昏时分,独自看夕阳芳草,流水落花。暮春、黄昏、芳草、落花,每一个都是渊源有自的传统意象,每一个都是触动或催生绮怨的语码。四者居一,已足令人伤感,何况四者并集于一时乎?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包含“落花”意象的词中,选取一些典型的佳作,来做分析鉴赏。先来看张先《青门引》: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这首词,有的版本会加上一个词题“春思”,其实这样的词题,加不加都一样,因为《张子野词》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的主题。词中说:“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残花,是眼前光景,中酒,“中”字当读去声,是指饮酒过量而造成的身体不适。“又是去年病”,是说去年如此,今又如此,甚至放长远一点说,是年年如此。温庭筠《更漏子》“虚阁上,倚阑望,还似去年惆怅”,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也是这个意思。晏几道《玉楼春》上片:“碧楼帘影不遮愁,还似去年今日意。”周端臣《春归怨》:“流水落花,夕阳芳草,此恨年年相触。”施岳《兰陵王》:“伤心事,还似去年,中酒恹恹度寒食。”都是岁岁如此、春来依旧的意思。
值得分说的是,宋词中的“中酒”,不是出现在个别词人身上的偶然现象。用宋人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风流病”,而且还是宋代词人中的常见病、高发病,在宋词中可谓屡见不鲜。中酒后的感觉,宋人描述甚为传神。秦观《促拍满路花》:“春思如中酒,恨无力。”吕本中《浣溪沙》:“中酒心情浑似梦,探花时候不曾闲。”陆游《隔浦莲近拍》:“才醒又困,厌厌中酒滋味。”张孝祥《虞美人》:“无聊情绪如中酒。”浑身无力,才醒又困,恍惚如梦,百无聊赖,写尽中酒情状。
但中酒实际不是身体的原因,而是因为心情。不难发现,虽然有少数人中酒是在秋天或是别的季节,而绝大部分词人是在春天,准确地讲,是在暮春,在寒食、清明前后,在落花时节。如此说来这又是季节病。少数词人中酒是因为离别相思,如柳永《甘草子》“中酒残妆慵整顿。聚两眉离恨”,这是因为伤别念远;吴文英《风入松》“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是因为伊人消逝,双鸳不到。然而就绝大部分词人来说,中酒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闲愁,因为伤春与惜花,而潜在因素是流连光景、惆怅自怜。如贺铸《浣溪沙》:“临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范成大《菩萨蛮》:“愁病送春归。恰如中酒时。”赵长卿《临江仙》:“怀家寒食夜,中酒落花天。”刘过《浣溪沙》:“残春中酒落花前。”詹玉《渡江云》:“伤春滋味,中酒心情。”张炎《踏莎行》:“可曾中酒似当时,如今却是看花病。”可知中酒诱因虽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与落花之间的连带关系。
再来看晏殊《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既然习惯以花比女性,所以预想中唐宋词的落花意象,应该主要是借众芳芜秽来表达美人迟暮的意思;而实际情况是,在这上千首悼惜花落春残的词中,更多的是男性词人的流连光景,惆怅自怜。晏殊此词,因为有“酒筵歌席莫辞频”这样出于男性口吻的句子,应该不是女性视角的代言体。“一向”,即一晌,言年光迅疾飘忽,转瞬即逝。人之一生,实为有限。所以接下来便自排自解,言不要伤春复伤别,既不因亲旧离别而痛苦,也不为落花风雨而感伤。所谓不辞酒筵歌席,亦即及时行乐之意。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是化用唐人成句。元稹《莺莺传》结尾处写莺莺赠张生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这里的“眼前人”,当指张生后来的爱人或妻子。也许晏殊对此句比较满意,所以在《木兰花》中也说:“不如怜取眼前人,免更劳魂兼役梦。”但以“眼前人”指眼下的爱人,出于莺莺口则可,出于男性当事人之口,则不免有苟且世故之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写莺莺赖简之后,张生对红娘说:“不如咱两个权作妻夫。”退而求其次,全无爱情忠贞之意,是张生形象塑造的一大败笔。而在晏殊词中,假如以好好爱怜眼前的歌女为不负韶光,亦不免有逢场作戏的意味。这是有损《珠玉词》格调的。窃以为,王国维《浣溪沙》:“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这个“眼中人”即是词人自己。晏殊词中的“眼前人”,或亦可解为当下现在之人,即词人自己,故“怜取眼前人”即含自爱自重之意,也就是楚辞中“惆怅兮私自怜”的意思。
再来看周邦彦《浣溪沙》:
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 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听林表杜鹃啼。
这首词是写伤春伤别。上片伤别念远,写得比较含蓄。因为晴空万里,故登楼一望,唯见芳草接天。而“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见芳草即不免思念远人,所谓“劝君莫上最高梯”,即不忍登高临远也。下片写韶华流逝,匆匆春又归去。“新笋”“落花”二句,是说春天不是将归未归,而是已经彻底消逝了。“落花都上燕巢泥”,是怜惜落花之诗意延伸,比起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也算是一种好的归宿了。秦观《画堂春》“杏花零落燕泥香”,曾觌《阮郎归》“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俱是同一思致。末句“忍听”,其实是不忍听的意思;“杜鹃啼”,不是化用思归的典故,而是暮春时节花事凋零的标志。宋词中写春归鸟鸣,有时说是杜宇,如张先《山亭宴慢》:“落花荡漾愁空树。晓山静、数声杜宇。”有时用鶗夬鸟,如张先《千秋岁》:“数声鶗夬鸟。又报芳菲歇。”苏轼《蝶恋花》:“小院黄昏人忆别。落红处处闻啼夬鸟。”有的用杜鹃,除周邦彦此词外,又如秦观《画堂春》:“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辛弃疾《婆罗门引》:“落花时节,杜鹃声里送君归。”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同一种鸟,所谓鶗夬鸟、杜宇、杜鹃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
三 春草与别离母题
春草意象有两个原生性出处。一是《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东汉王逸编集《楚辞》时收录的这篇汉代楚辞体作品,也是《楚辞》集中的压卷之作。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时,题名刘安,所以后来诗词中亦有“淮南春草”之类的说法。如姜夔《江梅引》:“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另一个出处是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是咏草名句,但它在抒情方面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所以只是在后来咏草诗词中节取字面以为点缀,并不具有意象或语码功能。而《楚辞·招隐士》既把王孙远游与春草萋萋的景象联系起来,又有“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这样富有情韵的句子,从而使春草成为写远游或送别几乎不可或缺的意象。从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一直到唐诗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罗邺《咏草》“不似萋萋南浦见,晚来风雨正相和”,一方面在沿袭《楚辞·招隐士》的抒情传统,同时也巩固和确立了春草之离别意象功能。
当然,还有另一种和草相关的意象,即黍离麦秀。《诗经·黍离》首段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据说东周大夫行役,过其故宫,见宗庙宫室旧地,尽为禾黍,乃作此诗。所谓“麦秀”,出于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殷民闻之,皆为流涕。”这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与《诗经·黍离》之章相似;“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则沿用赋诗言志的传统,以近似《诗经》的辞句,表示事情乖违、愿望破灭的痛惜心情。清代沈德潜将此题为《麦秀歌》,收入《古诗源》卷一。后来人们以“黍离”与“麦秀”合并,用以表达故国之思。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仍在暗用《诗经·黍离》意象。但这是另一支脉,与《楚辞·招隐士》的春草离别之思没有关系。
诗词中与离别关系最为密切的物事有两种:一是柳,也称杨柳,其源出于汉代以来形成的折柳赠别的习俗;二是草,也称春草,起于《楚辞·招隐士》中的名句。相比之下,唐诗写离别,多用折柳典故,名句如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劳劳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白居易《青门柳》:“为近都门多离别,长条折尽减春风。”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而在唐宋词中,春草取代了杨柳,成为表现离别主题的主要意象。唐五代词中的名句如冯延巳《南乡子》“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王国维《人间词话》叹为“能摄春草之魂者”);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以有形之春草摹状无形之离恨,离恨与春草合而为一,秦观“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似从此夺胎。
“春草”意象亦有多种衍生性表现。使用最多的是“芳草”,检索《全宋词》,可得551例,远超“春草”的79例。但是因为宋词中的“芳草”,不尽与离别主题相关,所以没有选用它作为意象之主名。旨趣相通之例,如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张先《菩萨蛮》:“忆郎还上层楼曲,楼前芳草年年绿。”晏殊《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晏几道《浣溪沙》:“梦云归去不留痕。几年芳草忆王孙。”这里的芳草,都是伤别意象。
当然有时就叫草,或是春草。如徐俯《卜算子》:“绿叶阴阴占得春,草满莺啼处。”周紫芝《阮郎归》:“烟漠漠,草萋萋。江南春尽时。可怜踪迹尚东西。故园何日归。”吴文英《浪淘沙》:“离亭春草又秋烟。”韩玉《减字木兰花》“客路茫茫,几度东风春草长。”
或曰“平芜”。如柳永《木兰花慢》:“纵凝望处,但斜阳暮霭满平芜。”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张舜民《卖花声》:“又看暝色满平芜。”
周邦彦《点绛唇》:“极目平芜,应是春归处。”曹组《点绛唇》:“十里平芜,花远重重树。”陈允平《齐天乐》:“旧柳犹青,平芜自碧,几度朝昏烟雨。”
总之,无论是草、芳草、平芜,都是春草意象之别名。它们总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在那些伤别念远的词中,构成解读离别词的“语码”,一看到这些,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一望无际的萋萋春草,而心中涌起的则是离愁别绪。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提到的三阕“咏春草绝调”。第一首为林逋《点绛唇》: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 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
这首词有的版本加上词题《草》或《春草》,其实无论加不加词题,事实上都是以草为中心来生发建构的。明卓人月《古今词统》评曰:“终篇不出‘草’字,古今咏草,唯此压卷。”“压卷”之说或不免夸张,说名篇佳作则毫无问题。
第二首是梅尧臣的《苏幕遮》:
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其诗以高老生硬为特色,就词而言则与林逋一样,也是非专业词人,但这首咏春草的词也写得很出色。“庾郎”一句,是借用李商隐诗句,庾郎指南朝庾杲之。据《南齐书·庾杲之传》载:杲之美容仪,风范和润,为尚书别驾郎,人称庾郎。李商隐《春游》诗云:“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因为词中下句是“窣地春袍”,所以可断定这里庾郎是指庾杲之,有的注本说是指庾信,不确。末句“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是写景,也是抒情,或者说是借景抒情法,最具有表现力。梅尧臣论诗名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或可移用于评其词。其好友欧阳修见长于词,读到该作也大加叹赏,并且自己动手另外写了一首咏草词,这就是与林逋、梅尧臣二词并列为“咏春草三绝调”的《少年游》:
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欧阳修此词,足以媲美林、梅二家咏草词而无愧色。其特色是语辞多有出处,写来却自然清新,如同己出。王国维《人间词话》讲“隔与不隔”,就认为欧阳修此词“语语如在目前”。其中“栏干十二”,出自南朝乐府《西洲曲》,写女子登楼远望,伤别念远,有“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之语。“千里万里”,用《花间集》中张泌《河传》:“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分别指谢灵运《登池上楼》诗和江淹《别赋》。至于楚辞《招隐士》中的咏草名句“春草生兮萋萋”,因为林、梅二词都用了“萋萋”,所以这里就回避了。但篇末“更特地、忆王孙”,还是又找补了一下。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以植物比喻艺术:“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唐宋词意象的生成亦不例外。唐宋词以残阳、落花、春草为代表的意象系统是唐宋文化“气候”氤氲渲染的产物,既富时代特征,又区别于唐宋诗歌的经典意象,体现出词体自身的特色。这三大意象及其衍生出的意象群,构筑起唐宋词的基本主题类型,凝固并深化了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取向。唐宋词作为词体的源头与“黄金时代”,其意象系统一旦生成,就逐渐定型,且具有了“原点”意义。此后,尽管时代“气候”风云变幻,但唐宋词相对稳定的意象系统业已形成思维的惯性,持续影响着后世词的创作,并推动着词体“上不类诗,下不类曲”个性塑造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