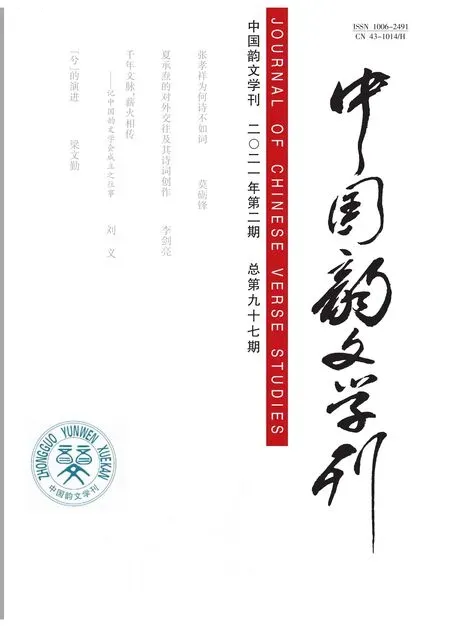文学与人生的融通
——读《刘禹锡诗传》
袁 韵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肖瑞峰先生积三十年之功潜心撰著的《刘禹锡诗研究》由上编“诗论”与下编“诗传”两部分构成,如果说“诗论”属于规范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范畴,因其宏通视野与理论深度而在刘禹锡研究领域“成一家之言”的话,那么“诗传”则以诗歌评析与人物传记相结合的形式,体现了作者在文体形式上的创新意识。“诗传”者,以诗为传也,即以刘禹锡不同时期的诗歌为线索,串联起传主一生的生平事迹、仕宦履历与交游行状。这种别出心裁的文学体式,将深厚的学术底蕴与浓郁的文学色彩融为一体,体现了“学术与文学的融通”,也将文学与人生联系得更为紧密,彰显了文学与人生的融通。
一
“诗”与“传”的融合,究其实,也就是文学与人生的融通。中国传统诗歌评析向来强调的“知人论世”,其中蕴含的正是将文学与人生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诗传”之所以予人以文学与人生融合无间的阅读感受,具体而言,与作者几个方面的努力密不可分:
其一,将传主的人生置于中晚唐宏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中,揭示造就其政治命运沉浮的社会历史动因,展现时代潮汐下士人命运的变迁与沉浮。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封建官员政治命运的升沉往往是朝政变化尤其是皇权嬗替的直接效应。刘禹锡一生先后经历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等七位帝王,其跌宕沉浮的政治命运正是中晚唐复杂动荡的政局的折射,如远贬沅湘是永贞革新失败后受宦官势力残酷打压的必然命运;量移夔州是敌视永贞党人的唐宪宗被弑、唐穆宗即位带来的际遇改善;奉调和州,则是唐敬宗登基后政局调整的连锁反应……至于刘禹锡晚年政治热情的冷却与明哲保身思想的潜滋暗长,则反映出甘露之变后晚唐政治生态的日趋衰败与恶化。
其二,将传主置于中晚唐政坛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在其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中凸显其人格与个性。如叙刘禹锡与王叔文的交往,彰显其政治抱负与淑世情怀;叙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往,或调侃戏谑,或劝勉激励,于披肝沥胆中凸显其忠厚无私、笃于友情;与武元衡的关系,表面上虚与委蛇,却在不动声色中对其“鹰隼仪形蝼蚁心”予以辛辣讽刺;与牛僧孺的交往,在甘于处下的避让姿态中隐匿着圆熟练达的官场智慧;与白居易的唱和,则在心息相通的嘤鸣之情中尽显“诗豪”本色……
其三,注重心理描写,力求细致入微地探寻和呈现传主深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诗传”不仅是记载刘禹锡一生行迹与交游的生平史,更是展现传主复杂深曲的内心世界的心灵史。作者堪称与传主灵犀相通的异代知音,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传主所处的时势、处境和氛围之下,细致入微地揣摩和体味其时其地其境之下传主的心灵世界。如对刘禹锡于开成元年(836)秋回东都洛阳任太子宾客时的心态剖析:“这是他第二次回到东都洛阳赋闲了。和十年前的那一次相比,同是赋闲,心态却截然不同;那时,是把赋闲洛阳当作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期待着略事休整后便向着新的目标进发,内心充满对未来的渴望;现在,则把赋闲洛阳视为曲折多变的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港湾,决心将生命之舟永远停泊在这里,不再启程远航,内心已失去任何现实诉求。”又如第八章中对刘禹锡听闻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后心理波澜的呈现,第九章中刘禹锡踯躅于宫墙之外与京城做最后诀别时心态的描摹等等,都堪称切理餍心、剖肌析理。在全书每一章节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对刘禹锡心理心态的细致揣摩和准确把握。要之,作者不仅是刘禹锡生平的载录者和诗歌的解读者,更是刘禹锡心声的代言者;不是以他者的身份遥踞于历史之外记人叙事、指陈是非,而是穿透重重历史迷障而直抵传主心灵深处,发覆洞幽,抉隐探微,乃至与自己的主人公心契神合、浑融为一。这种走进传主心灵世界“同情”与“体贴”的功夫,实乃人物传记殊难臻至的艺术境界,彰显了作者令人叹服的艺术功力。
其四,注重对人生况味的表述与对复杂人性的把握,在传记中融入深沉的个人情怀与生命感喟。“诗传”不仅将刘禹锡诗歌与其跌宕坎坷的人生绾合为一,完整地呈现了刘禹锡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体现了传主之文学与人生的融通,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说,也体现了文学创作与作者人生体验及人生智慧的融通。文学是人学,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离不开作者自身丰厚的生活积淀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人生的历练、世事的洞明,同样也是一种学术积累。所谓“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刘禹锡《和仆射牛相公寓言二首》),“诗传”中那些闪烁着人生睿智的精辟笔墨,都是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为根底的,熔铸着作者对世态人心的深切体味与深刻洞察。譬如作者对刘禹锡与武元衡之间微妙关系的论述、对刘禹锡离京出牧苏州时为其送别的四类人群不同心态的剖析等,无不基于作者对于纷繁世事及人情人性的深刻洞悉。
陈平原先生说:“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诗传”就是这样一部融注着作者个人情怀与生命体验的传记文学作品。虽是为千年之前的古人作传,读者却时时能够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的作者自身的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作为一部融学术与文学为一体的著作,“诗传”之厚重不仅是学术积淀的博大丰厚,更彰显了一种生命的厚度和人性的深度。
二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而言,这种以诗、传融合的方式对诗人一生进行历时性、全方位解读的文体形式,在我们当下的阅读环境下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为抵制网络环境带来的碎片化、肤浅化的阅读倾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整体性阅读”“整本书阅读”的呼声。其实,整体性阅读与其说是产生于21世纪网络环境下的时髦理念,不如说它是一种关于阅读的早已有之且行之有效的阅读策略,是古今读书人具有的普遍性经验之谈。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可以说就是整体阅读理念的积极倡导者。《红楼梦》中林黛玉谈到学诗的方法,认为应将王摩诘、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每家读一两百首,以此来打底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将这几位大家诗作每人选读一百、两百首,已经算是比较完整和体系化了,但在钱穆先生看来,这还很不够。他说:“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但我主张读全集。又要深入分年读。一定要照清朝几个大家下过工夫所注释的来读。陶、李、杜、韩、苏诸家,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比如读《全唐诗》,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是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至于读全集的好处,钱穆先生这样说:“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这番话,恰可作为对“诗传”之特色与长处的最好说明。所谓“一家一家读”“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其所蕴含的不正是当下倡导的整体阅读理念吗?对于见惯了碎锦集萃式的“作品选”的现代读者来说,这样一部将诗人生平与诗作进行整体性观照的“诗传”,自然有裨于引导读者告别碎片化,进入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整体性阅读”。以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为例,此诗是刘禹锡怀古咏史题材的名作,几乎在任何一部唐诗选集中都可见到对该诗的收录,诸多学者都曾对此诗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做过详尽深入的解读,但诗人是在何种处境、何种心境之下完成的这首诗?这首名作与诗人的个人生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从诗人的创作生命史来看,它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倘不是对刘禹锡一生行迹与心迹有详尽的了解,恐怕就不得而知了。而“诗传”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孤零零地对某首诗作进行分析解读,而是将诗人的所有诗作都有机地嵌入到诗人的生命历程中去,在诗作与诗人生命历程的交汇处,映现其与诗人个人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进而凸显其在诗人创作生命史和政治生命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再以刘禹锡的《九华山歌并引》为例,此诗最为人所激赏的是其豪迈的风格、壮阔的境界以及雄奇的想象,但此诗究竟作于何时何地?作于诗人的哪个生命时段?一般并不为人关注,似乎也没有关注的必要。在“诗论”第七章“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中,作者曾以此诗为例分析刘禹锡诗歌豪健雄奇的风格特征:“腾跃于诗人笔下的九华山的形象显然是其情志的一种物化,而诗人写作这首诗的目的正在于托物寄意。诗中那雄奇的想象,说到底,缘于诗人磊落不平的情怀。”那么,诗人磊落不平的情怀究竟缘何而起?是怎样的偃蹇际遇导致其发此不平之鸣?这些问题在以专题性探究为特色的“诗论”中不便深入展开,但读者如若细读“诗传”,上述疑问自会迎刃而解。在“诗传”中,作者将该诗的解析置于“传”亦即刘禹锡的人生脉络中,置于其由夔州调任和州途中这一具体的人生旅程之中。读者经由前面六章已详尽了解了此前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近二十年的坎壈人生:朗州十年、连州五年、夔州三年……自然不难理解刘禹锡这种郁积于心的磊落不平的情怀。而就在五年之前,他的挚友柳宗元就在难以解脱的抑郁苦闷中死于柳州贬所,年仅47岁。“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贬谪生涯之后,那种郁闷不平之气在他心中可谓蕴蓄已久,只是在面对九华山时,遽然找到了最好的抒情载体,遂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了!“结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长在无人境”,“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这些诗句也很容易令人联系到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所写的《钴鉧潭西小丘记》:“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可见,这种悲士不遇的愤懑情怀不只是属于刘禹锡自己的,也是与他一起远贬遐荒的所有永贞革新志士所共有的。总之,作者采用“诗传”的形式,使“诗”不只是可供单独品鉴的艺术作品,而是将其与传主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传中之诗”,从而将文学与人生浑融为一。读者在为刘禹锡诗作兴发感动的同时,自然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和深化着自己关于人生的思考。
三
钱穆先生所言“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对于提高阅读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无疑大有裨益,但对于大多数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要么受限于对古典文献的阅读解析能力,要么拘囿于对古代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的了解认知水平,对诗作的理解仍会有诸多隔膜之处。而“诗传”的意义正在于此:作者以其深厚精湛的学术研究为根底,采用生动形象的文学化手法,将诗歌讲析与人物传记融为一体,犹如为读者搭建了一座桥梁,使读者得以更便捷、更通畅地进入诗人宏深寥远的精神世界。
为使刘禹锡的一生更为鲜活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赋予这部诗传以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文学色彩在“诗传”的前四章中尤为突出。譬如第一章“风华少年”,作者摒弃了通常人物传记从传主的家世、出身、籍贯等入手的套路,将镜头聚焦于刘禹锡少年时期在嘉兴的一个生活场景:在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曼妙春光中,以少年刘禹锡与其同伴裴昌禹南湖垂钓的情节展开全书,这一独具匠心的“入题”方式显然体现了作者对“诗传”之文学旨趣的追求。而这一情节却绝非作者向壁虚构,它是据刘禹锡《送裴处士应制举》诗中的“垂钩钓得王馀鱼,踏芳共登苏小墓”一句生发而来,经由作者丰富的想象编织为一幅有声有色而又趣味盎然的生活画面。又如,对于唐代以诗取士的科举文化背景的介绍和交代,作者也没有像纯粹的学术著作那样做“知人论世”的平实叙述,而是巧妙地采用了情节化、故事化的处理方式,以居住在嘉禾驿的少年刘禹锡与驿吏之间对话的形式展开,并适时嵌入元稹与李贺关于进士出身的一则逸闻轶事,使读者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了解唐代进士考试的相关历史背景。
如果说前面四章是以传为主、传中有诗的话,后面五章则是以诗为主,诗中有传。就诗之于传的关系而言,一则诗为传之线索,起到贯穿人物传记的连缀作用;二则诗为传之灵魂,对传主的思想人格起到画龙点睛的揭示作用。譬如刘禹锡的《观棋歌》,作者就未对其进行平面化的泛泛解读,而是巧妙地将此诗缀入人物生平的珠线之中,通过刘禹锡应试前在京城旅馆中观棋—对弈—赋诗等一系列饶有情致的故事情节,展现出青年刘禹锡博通众艺、胸有丘壑而又谦谨持重的卓异质素,同时也见微知著地呈现了李唐诗歌王国“郁郁乎文哉”的文明盛象。诚如作者所言:“诗歌是全书的贯珠之线,是流遍周身的血脉,是使传主的生命焕发出光彩的精气神。”对读者而言,因对传主人生历程的系统了解而更易理解诗作本身的内涵,也因作者对诗作的细致解析而得以更深刻地了解传主的思想和人格,诗与传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不以学术研究为旨归而以增益人生为目的的广大读者来说,这种诗传融合的方式自然更能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深刻的人生启迪。譬如,从《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中,我们读到的是刘禹锡傲视权贵、疾恶如仇的耿介性情与豪爽本色;而在大和元年(827)途径扬州时的宴席上,面对牛僧孺睚眦必报的小人嘴脸、酒后轻狂的出言不逊,他的表现则是“无意反唇相讥,逞一时发泄之快,而贻日后寻仇之患”。从畅言无忌、快意恩仇到包羞忍辱、卑身求和乃至以德报怨,从中可见世事沧桑的磨砺之下诗人性格的成熟和思想的嬗变,同时也丰富和深化着读者对于人性与人情世态的认知。纯粹的学术著作,无论是文学评论还是文献考证、年谱汇编,其意义更多体现在对学术研究本身的推进,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难免或因其艰深的学理性望而生畏,或因其枯燥乏味而无意翻阅。“诗传”这种将诗歌与传记结合为一体的文体,则将文学性与学术性融为一体,在淡化学究气息、强化文学色彩的同时,自然也拉近了它与普通读者的距离,扩大了读者的受众群,从而赋予其更广泛的文学普及的意义。在这部以刘禹锡为主人公的“活的电影或戏剧”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刘禹锡这位主角一生的悲欢荣辱,还可以看到活跃于中晚唐政坛上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裴度等配角的身影;不仅可以尽览中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的政治生态之复杂,亦可感受唐王朝“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文化景观之繁盛;既能体验到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又能在作者的深入剖析之下体会“诗家三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部“诗传”当然要比那些艰深的纯学术著作更受欢迎了。
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之下,古代文学何为?古代文学何用?程千帆先生早就说过:“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针对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边缘化的现象,詹福瑞先生更明确地指出:“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自不例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理会人民大众,淡化现实人生,古代文学研究变成了研究者个人为学问而学问,为研究而研究的学科,也势必会失去一般读者的关心与支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照此发展下去,真的只剩下研究者孤家寡人了,而这恐怕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真正想看到的结局。”重视基于文献整理之上的理论阐释,在对研究对象思想意义的揭示和价值评判中体现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是肖瑞峰先生治学的固有特色,其《刘禹锡诗传》更以独出机杼的文体形式,实现了作者融通文学与人生、以文学启示现实人生的创作旨归。令我们钦敬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杰出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关心社会人生、改造现实的责任和使命。从叶嘉莹先生的诗词评讲系列著作,莫砺锋先生的《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到戴建业先生的《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等,这些既具学术内核又具普及意义的著作,使得古代最优秀的作家作品走进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引领普通民众精神成长的良师挚友。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仅推动学术自身的进步,还能走出象牙塔,成为惠及普通民众的精神飨宴,发挥情操陶冶和人格塑造的积极作用,岂不正是古代文学最大的功德与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