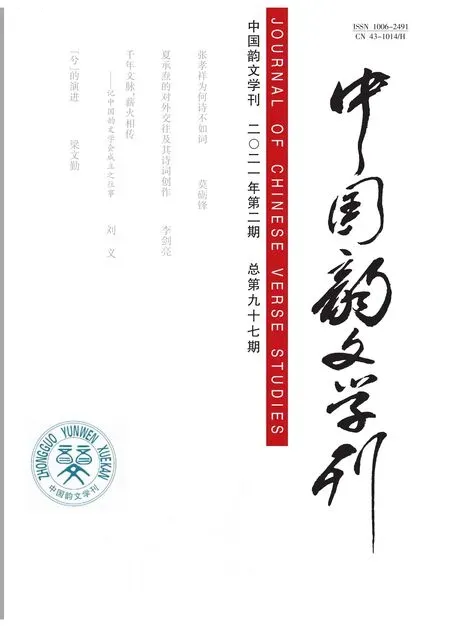俸禄考量与归去之思:论宋人的仕宦谋生方式对怀归题材宋诗之影响
叶 烨,杨 丹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怀归于宋代文学而言实为一种重要题材类型。在词体方面,研究者曾将全宋词按题材类型分为36类,其中第8类为羁旅词,指“表现旅居异乡孤寂情绪的词作。内容涉及对功名仕途的厌倦、对往昔繁华热闹生活的怀念、对他乡荒凉环境的怨苦、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等”。又第9类为隐逸词,指“表现隐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或表达对隐士生活的向往、以隐士的高洁情操品格自勉的词作”。两类题材总数在全宋词中占10.66%。就内容而言,这两类题材大致与通常意义上的怀归题材重合,由此可见出怀归题材在词体中所占之比重。在诗方面,虽然由于宋诗总量超过20万首,因此尚不易对全宋诗中怀归题材之具体数量做出统计,但今人仍可以由一些个案窥见怀归题材在全宋诗中所占之分量。例如,以“思归”“怀归”等38个关键词对全宋诗的标题进行检索,可得到结果1100项,可想而知,内容涉及怀归而未以诗题揭示的作品当远远超过此数。
然则宋人何以对怀归题材如此热衷?文学终究是现实遭遇和相关情绪的投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怀归题材盛行是宋人生活方式决定的结果。传统时代的士人之所以怀归,无非缘于暌违乡关、久别亲人,由此生出思念、无奈、不甘等种种情绪。而就宋代文士而言,与怀归题材有关的一项前提,是已知宋代文士绝大多数曾有仕宦之经历,仕宦对于宋代文人而言实为最重要的谋生方式,这样一来,仕宦求俸便成为文士离家在外的最主要原因,奔走四方也成为宋代文人(主要是入仕文人)的生活常态。事实上,检点宋人笔下的怀归作品,绝大多数正是作于仕宦期间,这一状况直到南宋后期才出现明显变化,江湖文人漂泊求食,笔下也多见怀归之作,但这对应的正是由于冗官问题加剧、入仕艰难,以致宋人以仕为生的生活方式出现明显动摇的新形势。就此而言,仕宦作为一种主流生存方式构成了宋代怀归诗大量出现的基本背景。
不过,仕宦求俸的生活方式对于宋诗怀归题材的影响还不仅限于对于离家状态的促成。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士人对于这一生活方式的态度,也或隐或显地在怀归诗的情绪生成及表达中发挥作用,以下本文试分别予以阐释。
一 以仕谋生与欲归情绪之生成
怀归情绪的具体生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宋人以仕谋生生活方式的结果。
就怀归情绪的通常触发点而言,大抵出于宦游士人对处境以及遭遇有所不满,因不满而思归,故乡于是具有了映照当下不堪的彼岸意义。所谓不满,虽然可能出自各种原因,但如果当事人是抱有谋生目的出仕,则自然会将种种不堪视为谋生选择的结果,感慨仕途艰辛之余,归去的愿望便也顺势而生。这种谋生选择与不满现状之间的矛盾,适如徽宗朝赵鼎臣在《过武强渡》诗中感叹的那样,“心欲求田耳,身如作吏何。荒凉三径晚,归计日蹉跎”。而这种两难与无奈在宋人笔下实为常见,如宁宗朝黄干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言及:
幹本但为贫,循常调,窃升斗耳,岂敢为寸进计。诸公推挽,朝廷误以为可用,擢贰淮州,又不得展布。而受命于庸人,其势必不合,不合则当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听命。然未能决去者,试邑之后作倅,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故山之梦甚切,来春当力恳庙堂,求为归计也。
(《复杨志仁书》之二)
据黄干所言,治绩出色而获擢用,又与上官不合而改任,职守渐重而事体愈繁,心欲归去又不忍弃职守于不顾,其间经历虽无特别之处,然而本来为生计出仕,一入宦海则身不由己,看来又是势所必然,黄干于此呈现的也正是入仕文人的普遍感受。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仕途坎坷、功业难遂似乎是士人意欲归去的最重要原因,但由于以仕谋生在宋代已成为士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对于经济收益的考虑事实上也在宋人的归去意愿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常常与对于功业的考虑共同发生影响。关于宋代官员的仕宦收入,目前学界大多认为,虽然中高层官员收入较为丰厚,但下层官员的俸禄收入则非常有限,与中高层官员差距极大,而下层官员实为宋代官员的主体,约占官员总数的80%。又由于宋代官员支出多端、家庭家族负累较重以及守选待阙时间漫长,短暂或长期的入不敷出对于宋代官员来说乃是常态,可以说大多数宋代官员在日常生活中都不能避免拮据之感。因此对于宋代士人的实际处境而言,常常可能是由于功业与谋生俱不理想,使得居官在外的意义丧失殆尽,返归田庐也就成为自然的诉求,即如黄干所言:“进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家,以是思之,不若放归山林之为乐也。”(《与林公度》之十二)又或如陆游之谓“功名富贵两茫茫,唯有躬耕策最长”(《书怀》)。而由这类表述之中,也正可见出宋人谋生方式对于其日常心态乃至其怀归情绪的影响。
宋人可能出于对谋生方式之不满而心生归意,这种情绪的抒发自然会成为怀归诗中的常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于士人而言其出仕本有谋生目的,那么这种不满乃至反思中往往会带有一种权衡利弊得失、计算仕宦谋生代价的意味,即并非直接表达对于具体收入的不满,而是以收入与付出相比较后生出不甘之感,这也成为宋人怀归诗中一种相当重要的表现类型。就此而言,类似的情绪似以陆游《思归引》一诗表现得最为透辟。此诗结尾云:
……
莼丝老尽归不得,但坐长饥须俸钱。
此身不堪阿堵役,宁待秋风始投檄。
山林聊复取熊掌,仕宦真当弃鸡肋。
锦城小憩不淹迟,即是轻舠下硖时。
那用更为麟阁梦,从今正有鹿门期。
诗中所流露出的思归情绪相当浓烈,对于谋生与归去取舍之艰难的描述也可说淋漓尽致,尤其“山林聊复取熊掌,仕宦真当弃鸡肋”两句更为微妙,正写出了归去与谋生对比而生成的价值。仕宦适如鸡肋,而山林则于相形之下俨然成为熊掌,并最终使得诗人舍弃功业之心,而坚定了归去之想。
陆游此诗中并未提及究竟是怎样的遭遇使得诗人作如此之想,而在更多情况下,诗人会在诗中袒露引发归意的具体缘由。有时可能出于涉身政治的创伤,如苏轼的《过高邮寄孙君孚》一诗即是典型:
过淮风气清,一洗尘埃容。
水木渐幽茂,菰蒲杂游龙。
可怜夜合花,青枝散红茸。
美人游不归,一笑谁当供。
故园在何处,已偃手种松。
我行忽失路,归梦山千重。
闻君有负郭,二顷收横从。
卷野毕秋获,殷床闻夜舂。
乐哉何所忧,社酒粥面醲。
宦游岂不好,毋令到千钟。
此诗的后半篇所谈到的便是宦游与归乡的选择:如果乡居能有田亩若干,得以保障生计无忧,则足堪为乐;而宦游虽然有其收益,然而考虑到其中的风险,尤其是作为高阶文官卷入政治风波的风险,相对于乡居便不再具有优势。苏轼此诗作于绍圣元年(1094)南谪途中,所表达的当然是深受政争之苦的伤痛,但这种利害得失的计算又绝不仅限于政争的受难者,对于普通文官而言,日常的公务同样可能催生出得不偿失之感。如范成大《公退书怀》一诗云:
昨者腾章奏发仓,今兹飞檄议驱蝗。
四无告者仅一饱,七不堪中仍百忙。
皦日自能临俯仰,浮云宁解制行藏?
求田问舍亦何有,岁晚倦游思故乡。
此诗作于孝宗淳熙十年(1183)知建康府任上。时逢蝗灾,范成大作为守官奔走不暇,既不堪于奔波劳苦,又自咎于不能稍解民众之急难,愧烦交攻,则以为生计之事较之于此种忧患亦不再具有吸引力,归心也因此油然而起。
相形之下,陆游在《岳池农家》中的类似感想则表现得更加直白:“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宦游所得真几何,我已三年废东作。”奔走于职守的辛劳、市朝争夺的风险,都使得农耕在特定情境下俨然较以仕谋生更具优势。而沿着这一思路推导下去,则士人很容易生出以仕谋生并非理想生存方式、甚至仕不如耕的感想。张耒即曾因为不堪宦海飘零而慨叹:“闲于万事常难得,仕以为生最拙谋。”(《题洪泽亭》)陆游也不无夸张地声称:“人生觅饭元多术,最下方为禄代耕。”(《春日杂赋》其五)类似的表白当然都只是情绪不宁时的极端之言,但由其中也不难看出,仕宦谋生的生存方式对于宋人“欲归”情绪之生成所发挥的作用。
要言之,宋人对于现状的不满往往混杂有多种情绪,而对于收入和谋生方式的失望则在这种复杂情绪中占有相当比重,在功业之想已经无望的形势下,对于收入和谋生方式的失望会对归去的意愿产生“叠加”效果,最终使得对于现状的厌倦和对于故园的向往成为明确的意愿。
二 俸禄考量与归而不得之困境
不过,对于怀归题材的构成而言,不满于当下而欲归只是情绪的一个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果真如此不堪,挂冠径去便是,又何须呶呶多言?问题在于现实中的文士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断然抽身,苏轼诗中的“渊明赋归去,谈笑便解官。今我何为者,索身良独难”(《送曹辅赴闽漕》),正是宋代文士两难处境的写照。如此一来,归心郁结又不得宣泄,遂成为怀归题材流行的又一方面原因。
然则缘何不能归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据宋人在诗文中自陈,不外乎出于两种理由,或是声称君恩未报,如王安石《寄张先郎中》所谓“投老主恩聊欲报,每瞻高躅恨归迟”,或表示出于经济考虑,而后者尤其能见出以仕为生对于怀归题材的影响。虽然,正如“君恩未报”的理由只可姑妄听之一样,以经济原因作为解释也未必代表当事人的真实想法(正如前文所引黄干的感受,受知于人或出于士人的使命感都使当事人不能率尔去职),但这种解释作为可被普遍接受的理由而出现,至少可以表明,经济原因确实能对宋人的归田选择造成切实影响。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即便大多数人的仕宦收入并不优厚,入仕仍然是在农耕时代文士的谋生首选,因为舍此之外并无更为理想的出路,而且就社会整体而言,入仕在收益方面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某些研究者之所以否认宋代官员俸禄微薄,也正是着眼于这种比较优势而非具体俸禄数量。根据研究者的测算,“不论是官员俸禄水平相对较低的北宋初年,还是物价高涨的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即使是九品小官,也能维持高于广大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及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的实际收支水平一倍以上,收支平衡或收略大于支的相对优适生活。至于那些品第在九品之上,尤其是五品以上的各级官员,其俸禄多是九品官的几倍,甚至十多倍,其收入明显地大于支出更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测算因为忽略了具体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及当事人的经济感受而显得过于简单,但仍有助于今人感知宋代文官的客观经济处境,并理解宋人之所以不能率尔归去的尴尬。
由此可知,宋人倾向于以仕宦为生其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弃官归田,便意味着收入消减,可能更难以维持生活,这是入仕文人在起怀乡之思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黄庭坚《和答孙不愚见赠》一诗所述便颇为坦率:“……簿领侵寻台相笔,风埃蓬勃使星鞍。小臣才力堪为掾,敢学前人便挂冠。”自知谋生乏术,因此即便心怀不甘或愧疚,也只能隐忍而已。类似的表达在当时绝非少见,其中有的文士陈述更为明确:之所以羁留不去,无非是某些具体的经济目标如儿女婚嫁之计尚未实现,仕宦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的意味于此尤为明显。如王禹偁于太宗至道元年(995)因言事而罢职出知滁州,其间作《高闲》诗云:“谪官滁上欲何为,唯把高闲度岁时。费尽俸钱因合药,忙于公事是吟诗。京中吏去慵传信,江外僧来与撰碑。更待吾家婚嫁了,解龟休致未全迟。”梅尧臣则在送友人致仕的诗中不无向往地写道:“久无归田人,今喜子去禄。……我心虽有羡,未遂平生欲。更期毕婚嫁,方可事岩麓。”(《寄光化退居李晋卿》)而在张元干的人生规划中,也唯有儿女婚嫁已毕,方有弃官而去的现实可能:“簪绂久已弃,行装今甚疲。买山如略办,毕娶更奚为。小筑开三径,躬耕趁一犁。赖公霖雨手,忍赋语离诗。”(《上张丞相十首》其十)这些具体的描画无疑都能使人感受到仕宦生计之于怀归之意的切实影响。
而对于入仕文人而言,仕宦收入不仅承担着维持日常生活和应付重大开支的功能,还具有为晚年生活进行储蓄的意义,因此对于储蓄不足的忧虑便成为宋人在面对怀乡愿望时不得不考虑的另一问题,这种忧虑不仅直接作用于文士自身,甚至可能成为家庭成员的潜在压力转而作用于文士,辛弃疾词作《最高楼》(吾衰矣,须富贵何时?)之小序曰:“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正可见出其中消息。如此则对于田园的渴望、对归计不足的无奈以及以此作为不能归去之解释等,也就成为宋人怀归题材中的常见表达。其中较为典型之表述又如:
久厌尘氛乐静缘,俸微独乏买山钱。
(周敦颐《宿山房》)
几时能致买山钱,便好山中醉暮天。
(黄裳《秋日有感》其二)
安得五亩园,旁营二空庵。心游万物表,旷若巨海涵。恨无买山具,抚境思髯参。
(程俱《同叶内翰游南峰,窃观壬辰旧题诗,谨次严韵》)
我生饱识田家趣,只坐无田归计迟。
(赵蕃《晚行田间书事三首》其三)
挥毫拟就归田赋,检点山资苦未丰。
(李正民《再领宫祠》)
买田如有路,誓欲老吾邦。
(周紫芝《挂席》)
不过在这种表达中最为著名者,无过如苏轼《游金山寺》中之发愿:“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无田可归成为不能去职的最重要理由,而这两句喃喃自语也仿佛一声戛然之响,骤然将读者的意绪从绚烂热烈的奇景中拉回到以生存为目标的现实中来,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正可视为经济生活渗入文学表达的例证。
三 仕宦谋生方式对怀归宋诗审美特征之影响
以仕宦谋生的生存方式首先可能给宋代怀归诗带来的影响,是有助于诗中的情绪保持一种理性与平静的情感基调。
在论及宋诗中的理性情绪时,研究者有时将之归因于宋人所面临的思想文化背景,但以这一宏观判断来对应众多具体作品可能不免失之简单。事实上,在与宋人经济生活有关的作品中,理性与平静情绪也往往与作者的经济生活状况有关,稳定的经济生活状况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作者由于生计而产生的烦恼,这不妨被视为宋人所享有的有利条件。就宋人的怀归诗而言,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条件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笔下的怀归之作虽然为数众多,且常涉及欲归不能之困窘,但其间态度往往并不激烈,情绪更多表现为懊恼、伤感或无奈而已。如果将经济收入问题视为欲归不能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一现象也可以因此部分得到解释:这仍可以视为入仕这一谋生方式的特性所带来的结果。既然选择以入仕作为谋生方式,则只要俸禄收入能够解决生计,现实中的种种不堪便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令人无从过分抱怨;更何况无论现实处境何等难以令人忍受,“归去”始终是一个可以执行的选择,如果是出于经济考虑不能离去,那么这一问题的解决虽然可能遥远,却也无疑是可以预期的结果,假以时日,愿望终究可以实现,既然有这样一种明确预期的存在,诗人自然也无须为当下的欲归不能感到过分焦虑。
就此而言,陆游的经历与感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陆游自孝宗乾道五年(1169)赴任夔州通判,至孝宗淳熙五年(1178)春间奉诏东归,在蜀地长达八年。在蜀地任职期间,陆游屡屡在诗中流露出飘零万里的怅然,从中也可以看到经济状况对于这种客愁的影响。一方面,诗中为就食而仕宦远方的不甘可谓连篇累牍,诸如:
万里西来为一饥,坐曹日日汗沾衣。
(《假日书事》)
书生迫饥寒,一饱轻三巴。
(《鼓楼铺醉歌》)
我生胡为忽在此?正坐一饥忘百虑。
(《木瓜铺短歌》)
北风岁晚号松楸,哀哉万里为食谋。
(《宿彭山县通津驿大风邻园多乔木终夜有声》)
万里驱驰坐一饥,自怜无计脱尘革几。
(《书怀》)
但另一方面,陆游诗中也常常写到因为积蓄不足而不能归去的不得已,诸如:
巾褐已成归有约,箪瓢未足去无缘。包羞强索侏儒米,豪举何人记少年。
(《晓出城东》)
亦知归去好,无地着蜗庐。
(《夙兴出谒》)
暮年作吏宁长策,薄禄縻人尚小留。
(《晨起》)
家弊须微禄,年衰尚远游。
(《自讼》)
贪禄忘归只自羞,一窗且复送悠悠。镜明不为人藏老,酒薄难供客散愁。
(《自嘲》)
不过,在蜀地期间虽有种种不如人意,陆游很少抱怨过经济的困窘,反而不时流露出对于收入的满足,有时甚至有尸位素餐之愧叹,如:
责轻仍饱食,三叹愧无功。
(《午兴》)
低回惭禄米,官事少于诗。
(《晨至湖上》其二)
似闲有俸钱,似仕无簿书。
(《醉书》)
终恨无劳糜廪粟,夜窗聊策读书勋。
(《夜分读书有感》)
如若俸入微薄,当不会再三做此感想。诚然,乾道八年(1172)陆游向时宰虞允文上书乞求祠禄时曾自述贫苦:“峡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穷人。伏惟少赐动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上虞丞相书》)但此类请求有夸张之处,而且在这种夸张之下依然可以看到,陆游所关心者是俸禄不足以为东归、婚嫁等大事进行储蓄,而非日常生计有急,更何况陆游提出的解决办法乃是请求祠禄,仍然是通过俸禄收入来获得积蓄而已。事实上,陆游在蜀地为官并非没有俸禄节余,无非可能不如人意,如其《客思》即有“还家谁道无余俸,倒槖犹堪买钓舟”之表述,正显示出仕宦收入与预备晚年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从陆游晚年诗歌来看,经济生活尚能维持必要的水准,大致在小康以上水平,这些足以表明早年的仕宦生涯绝非无济于事。
由陆游的这一系列述怀之诗当可以看到,稳定而足以维持温饱(乃至能提供一定节余)的俸禄成为诗人入仕期间以及晚年生活的重要依赖,这种生活水平使当事人能够以较为平和的心态来处理诗歌中的怀归主题,这种心态在陆游作于乾道六年(1170)初至夔州时的《雪晴》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诗中有“腊近春生白帝城,俸钱虽薄胜躬耕。眼前但恨亲朋少,身外元知得丧轻。”一面是远离亲朋的遗憾,另一面则是对于俸禄收入的满足,这正可以使人窥见中下层文官怀归时的复杂心态,进而理解其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情绪。
除此之外,仕宦谋生方式还使得怀归题材宋诗呈现出真切与写实的风貌。若将宋人怀归诗与唐人怀归诗对比,这一特点便显现得更为清楚。
显而易见,由于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入仕机会,宋人得以对仕宦生活有较为完整和切实的感受,对于仕宦造成的缺憾也有更为直接的体验,这才使借助怀归诗来展示有关情感成为可能。前述宋人因俸禄考虑而感受到的无奈和困窘正是如此。在这样的怀归之作中,诗人并非简单地描述归去意愿如何强烈,往往也兼及这种意愿的来源和背景,这就使得诗中的情感获得了现实情境的支撑,具有某种写实的意味。
而若检点唐人怀归诗,则可以感受到其中对于归去意绪的处理具有明显的抽象化与空泛化倾向。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为其中往往不指示怀归的具体原因,而更为着意于表达诗人一时的情绪感受。诗中的思念固然可以令人感受,却又使人无从清晰地捉摸把握。这一特点或可被理解为特定技法的自然结果,盖唐人惯于以画面来传递情绪,自然会导致情绪表达显得空泛。但与此同时,唐人的怀归诗在内容上又常常呈现出“意不在此”的效果,虽曰怀归,其中的归意归心并不浓厚,诗人往往另有怀抱,这也就构成了唐人怀归诗空泛化的另一个方面。从总体上看,唐人对于归去并不热衷。唐人笔下即便对于归去田园的实际行动表示肯定,也多是从不慕名利、操志雅洁等俗滥的价值标准着眼,而较少涉及当事人的具体遭遇或生活趣味,这种虚应故事的做法表明归去行为并未引起诗人共鸣。这一点在唐人送人归去之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盖唐人送人归田之际,诗中重点往往落在挥手自兹去的难依难舍,对于对方归去之后生活,却少见切实的欣羡或祝愿。如赵嘏《送李给事》诗:
眼前轩冕是鸿毛,天上人间漫自劳。
脱却朝衣独归去,青云不及白云高。
虽是送人归去,却并不涉及对于对方选择的祝福和评价,泛泛说归去之好,以为是不苟且于名利的高尚之志,但这样的表述不仅由于了无新意而缺乏诚意,也由于是用抽象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具体的生活选择而显得不切实际。事实上,在唐人的观念中,归去虽有高尚之名誉,在价值序列中却是明显后于功业的,因此归去只有在功业完成后才可能成为恰当的选择,即如陆龟蒙《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之六:
水影沉鱼器,邻声动纬车。
燕轻捎坠叶,蜂懒卧燋花。
说史评诸例,论兵到百家。
明时如不用,归去种桑麻。
其间固然不否认归去田园之乐趣,然而所谓“明时如不用”,又分明有着某种怨望,所谓的田园之想,更近于对功业无望的排遣,而非真心实意的生活理想。要之,唐人的怀归之作往往看似怀归,实则言不由衷,对于归心的陈述更近于对现状不满的牢骚,就此而言,骆宾王《寒夜独坐游子多怀简知己》堪称唐人此种心曲的典型:
故乡眇千里,离忧积万端。
鹑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
富钩徒有想,贫铗为谁弹?
柳秋风叶脆,荷晓露文团。
晚金丛岸菊,馀佩下幽兰。
伐木伤心易,维桑归去难。
独有孤明月,时照客庭寒。
开篇直抒离乡千里之忧,“万端”亦可见离忧之深厚,但其后的“鹑服”“富钩”“贫铗”等语又分明显示出,不安于贫贱、渴求出人头地又不得的处境才是痛苦的真正来由以及全诗的重心所在,只是这种痛苦借助于离忧的外壳予以引出而已,所谓“伐木伤心易,维桑归去难”,其间的两难似乎正可以被视为唐人对于归去之态度的缩影。
总之,唐人笔下虽绝不少见怀归之作,但唐人的怀归诗多言归而意不在归,使得所谓归意呈现某种程度的空泛之感。之所以如此,或与唐人处境有关,正如今人所知,唐人的功业之路远非顺畅,有限的晋身之路使得多数唐代文人被拒于仕途之外,在其功业之愿未能实现之前,自然无暇也无心绪来实现对于家山田园的拥抱。而相形之下,宋人的怀归之想则多是直接来自仕宦中的客居羁旅,乃是功业与经济生活的需求在基本得到满足之后所出现的对于自由生活和回归亲情的向往,如果借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理论,或许可以认为,相对于功业理想尚未实现的唐人,宋人所追求的实为更高层级的生存需要,这正是宋人的怀归之作不同于前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