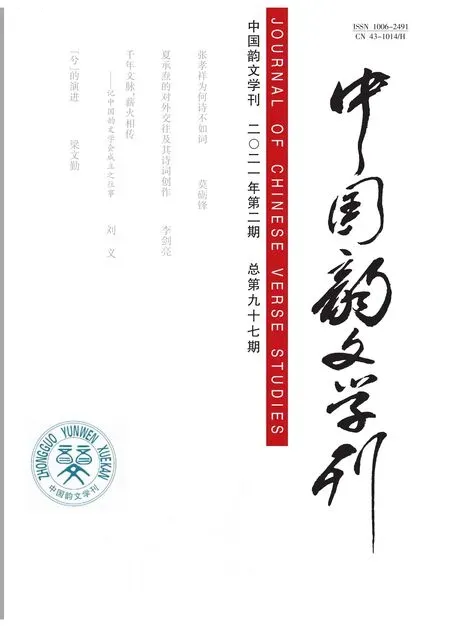宋词中的杜鹃与鹈夬鸟
刘泽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词开篇便传来鹈夬鸟的鸣叫,“绿树听鹈夬鸟,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茂嘉为辛弃疾族弟,稼轩自注云:“鹈夬鸟、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洪兴祖《〈离骚〉补注》:“李善云:《临海物志》:‘鹈夬鸟,一名杜鹃,至三月鸣,昼夜不止。’……然则子规、鹈夬鸟二物也。”鹈夬鸟是唐宋诗以及宋词中常常使用的意象,辛弃疾此注说明杜鹃与鹈夬鸟在其之前常常被当作同一意象混用,为何他要专门对二者加以区别呢?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一 杜鹃与鹈夬鸟的意蕴之别
《汉语大辞典》释鹈夬鸟:“鸟名。即杜鹃。”然而杜鹃与鹈夬鸟实则是有区别的,本文无意对二者做名物训诂角度的区分,仅谈其作为诗词意象的区别。杜鹃,又称杜宇、子规。《禽经》:“鸐、嶲周,子规也,啼必北向。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杜鹃作为意象为文人墨客所征引时,往往源于蜀帝的传说,《说文解字》:“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规啼,皆云望帝。”鲍照《拟行路难》其七:“中有一鸟名杜鹃,言使古时蜀帝魂。”杜甫《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皆言望帝之传说。蜀君失德而去位亡国的故事使杜鹃的意象带有了黍离之悲、亡国之思,此在宋词中亦可见,如向子諲《秦楼月》(芳菲歇):“眼中泪尽空啼血。空啼血。子规声外,晓风残月。”向子諲此词作于靖康之变后,国土沦丧,其借杜鹃之鸣发江山异色之叹。
蜀帝失国后化为杜鹃哀鸣,本就凄恻悲凉,后世又为其添加了鸣至泣血的掌故,《尔雅翼·释鸟》:“子嶲出蜀中,今所在有之,其大如鸠。以春分先鸣,至夏尤甚,日夜号深林中,口为流血,至章陆子熟乃止。”这让杜鹃意象更添悲凉,文人们于是常常以之状凄切之音,发悲慨之叹。如《琵琶行》中白居易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鸣就常常唤起古人心底的郁结,南北朝民歌道:“猿鸣三声泪沾裳。”而白居易被贬,感慨生平蹉跎,以杜鹃和猿鸣并列,足见其悲。又如刘攽《竹鸡》:“惯听巴山杜鹃哭,饱闻湘岸鹧鸪啼。”因杜鹃啼叫自春分开始,故又为其添加了暮春伤逝的春愁,如谢逸《春词》:“豆蔻梢头春事休,风飘万点只供愁。杜鹃啼破三更月,梦绕云间百尺楼。”
杜鹃的凄恻鸣叫总能唤起游子离人内心的柔软,甚至对其叫声有了“不如归去”的拟音,《禽经》云:“春夏有鸟,若云不如归去,乃子规也。”杜鹃的声音似乎在呼唤着背井离乡的人早些归去,于是它又承担了去乡之人的惆怅,如顾况《忆故园》:“惆怅多山人复稀,杜鹃啼处泪沾衣。”范仲淹《诸暨道中作》:“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曾巩《杜鹃》:“杜鹃花上杜鹃啼,自有归心似见机。”杨万里《晓行道旁杜鹃花》:“杜鹃口血能多少,不是征人泪滴成。”乡愁离思又总伴随着送别,在杜鹃催下征人羁旅他乡的眼泪后,在送别时又听到了它的声音,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如果说李白这首诗只是遥闻友人离去而作诗送别,那之后的诗歌便是在执手相顾时有杜鹃鸣啼相伴了,如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释智圆《春日别同志》:“忍向离亭折杨柳,晚花零落杜鹃啼。”
综上所述,作为诗词常用的意象,杜鹃自蜀帝失国的传说引申开去,又有着抒发黍离之悲、状凄切之音、伤春将去、离人送别、游子乡愁等意蕴。
鹈夬鸟在文学作品中的首次出现是在《离骚》中:“恐鹈夬鸟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屈原将鹈夬鸟安放在此处表面上也是发出了暮春时众芳将谢、韶华不再的感慨,这里似乎与杜鹃伤春之情一致,但《离骚》全文借芳草美人以抒己怀抱,鹈夬鸟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内蕴。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按《诗·卫风·氓·小序》“华落色衰”,正此二句之表喻;王逸注所谓“年老而功不成”,则其里意也。下文又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贻”;“恐鹈夬鸟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言之不足,故重言之。不及壮盛,田光兴感;复生髀肉,刘备下涕;生不成名而身已老,杜甫所为哀歌。后时之怅,志士有同心焉。
此节周振甫先生以“美人迟暮”名之,钱先生认为屈子借美人迟暮以言“年老而功不成”,“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恐鹈夬鸟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等都是“重言之”,如“不及壮盛,田光兴感;复生髀肉,刘备下涕;生不成名而身已老,杜甫所为哀歌”,感慨壮志未酬而年岁已长,将此种感情投射到“美人迟暮”上,含蓄委婉发出,这也是在诗词中鹈夬鸟意象与杜鹃意象之不同。
二 北宋词中的鹈夬鸟
辛弃疾在自注中区分杜鹃鹈夬鸟实为二鸟,言外之意是此前词中多将两意象通用,《全宋词》所收词作辛弃疾之前以鹈夬鸟入词者共四首,下面逐一分析。
苏轼《蝶恋花·离别》:
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小院黄昏人忆别。落红处处闻啼夬鸟。 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断魂销,应是音尘绝。梦破五更心欲折。角声吹落梅花月。
此词作于元祐六年(1091),在杭州任上二月召还,三月离杭,时为暮春,故首句云“春事阑珊芳草歇”。行旅途中,正值清明时节,落红纷纷,鹈夬鸟鸣叫,让苏轼忆起别时情景。东坡心系杭州,却无奈奉召离去,渡江后即楚越两分,回首望余杭“应是音尘绝”。五更梦醒,心中戚戚,远处传来角声呜咽。鹈夬鸟在东坡词中既是暮春时节的标志,又抒发其离别之情。
舒亶《临江仙·送鄞令李易初》:
折柳门前鹦鹉绿,河梁小驻归船。不堪花发对离筵。孤村啼夬鸟日,深院落花天。 文采弟兄真叠玉,赤霄去路谁先。明朝便恐各风烟。江山如有恨,桃李自无言。
舒亶此词显是送别之作,折柳相赠,岸边驻船,鹈夬鸟的鸣叫成为分别的注脚。王之道《风流子》援引鹈夬鸟也是岸浦送别、临行清涕:
扁舟南浦岸,分携处、鸣佩忆珊珊。见十里长堤,数声啼夬鸟,至今清泪,襟袖斓斑。谁信道,沈腰成瘦减,潘鬓就衰残。漫把酒临风,看花对月,不言拄笏,无绪凭栏。 相逢复相感,但凝情秋水,送恨春山。应念马催行色,泥溅征衫。况芳菲将过,红英婉娩,追随正乐,黄鸟间关。争得此心无著,浑似云闲。
李清照《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夬鸟。
徐培均先生将这首词系于绍兴三年(1133)定居杭州前后,暮春花落,唤起作者南渡前在北方的回忆,所谓“海棠开后”,或许是指前作《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晚间酒醉歌罢,灯火闪烁,鹈夬鸟正鸣。此词中鹈夬鸟有伤春意,亦有怀乡之意。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与诸多男性词人不同,她的词中感时伤怀本就有美人迟暮的意蕴,但她的抒怀是切身而发,与男性词人借香草美人自喻不同,更没有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意思。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辛弃疾以前的宋词中鹈夬鸟亦是思乡、离别、伤春,与杜鹃在诗词中所承担的情绪并没有区别,可见这一时期在词中鹈夬鸟与杜鹃完全等同。
三 南宋词对鹈夬鸟意象的改造
前文所述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稼轩自注以区分杜鹃与鹈夬鸟,现存辛词中出现鹈夬鸟意象者有二,另一首即《满江红·饯郑衡州厚卿席上再赋》,邓广铭将其系于淳熙十五年(1188),创作时间早于《贺新郎》。我们先来看此词:
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还记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对花浑醉梦,而今醒眼看风月。恨牡丹笑我倚东风,头如雪。 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算怎禁风雨,怎禁鹈夬鸟!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
首句作者唤道“莫折荼蘼”,妄图以此来“留取一分春色”,但显然无济于事,在这时光飞逝的无奈里过往与现在交错,似乎牡丹都在“笑我头如雪”。在年华一去不返的悲戚中作者感叹“怎禁风雨,怎禁鹈夬鸟”。自题目看此词是送别之作,但直到歇拍处才明言离别。此处的鹈夬鸟虽与离别相关,但显然更是辛弃疾对时光不复的喟叹,是化用《离骚》中鹈夬鸟的内涵。如果此时尚未体会分明,那当下一句“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出现时就可谓明白无误了。“老冉冉兮花共柳”典出《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是屈原对壮志未抒、时光不再的感慨。“是栖栖者蜂和蝶”典出《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孔子为复礼而奔走忙碌,让微生亩十分不解,故发出了“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的疑问。词中“是栖栖者蜂和蝶”更像是辛弃疾的自嘲。
辛弃疾力主抗金,但他关于抗金的建议和措施一直得不到采纳,淳熙八年(1181)他罢官闲居带湖,这首词正是闲居时做,其壮志未酬而英雄已老的情绪注入词中,屈原的遭遇在此时似乎感同身受,于是鹈夬鸟的内蕴不再与杜鹃相同,它的鸣叫成为稼轩急切想抗金复国的呼喊。
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辛弃疾自注杜鹃与鹈夬鸟的不同,似是提醒读者自己词中出现的鹈夬鸟是有独特内蕴的。
绿树听鹈夬鸟。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开篇鹈夬鸟与杜鹃此起彼伏地鸣叫,芳菲皆歇,但作者却说如此凄恻的声音也抵不上离别的痛苦,显然这首词虽然同时出现了鹈夬鸟与杜鹃,但它们的内蕴似乎却是一样的。辛弃疾宣称鹈夬鸟与杜鹃二者不同,但在创作实践中对它们进行区别运用却是在之前所作的《满江红·饯郑衡州厚卿席上再赋》中。关于这首词的系年诸家观点不一。吴企明将该词系于庆元六年(1200),其引郑骞注“刘词盗起民散,谓金国事。金之衰乱,始于宋庆元、嘉泰间,即稼轩六十岁左右,赋茂嘉,当在此时”,“刘词”即指刘过同时之作《沁园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吴先生认为:“四印斋本列本词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和前韵》《又和》之后,又列本词于《题傅君用山园》《用韵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余谓当筑陂于其前》《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三词之前,前三词作于绍熙三年,后三词作于庆元六年。据此亦可见本词必作于庆元六年。”邓广铭云此词具体作年无考,但亦根据刘过之词,引岳珂《桯史》刘过于嘉泰三年(1203)被辛弃疾延入幕府,所以送嘉茂之桂林不当早于嘉泰三年,“词中有‘筹边如北’语,知茂嘉之‘如北’必在稼轩起废之前,其赴调或即在由北边归来之后,是则二词均当作于稼轩移居瓢泉期内”。两种系年都是在辛弃疾的暮年,或许词中的鹈夬鸟有英雄迟暮、功业未竟的意味,但是这也只是猜测罢了。
无论哪种系年正确,张镃《木兰花慢》(清明初过后)都在辛弃疾《满江红》之后,《贺新郎》之前。
甲寅(1194)三月中瀚,邀楼大防、陈君举中书两舍人,黄文叔待制、彭子寿右使、黄子由匠监、沈应先大著过桂隐即席作 。
清明初过后,正空翠、霭晴鲜。念水际楼台,城隅花柳,春意无边。清时自多暇日,看连镳、飞盖拥群贤。朱邸横经满坐,紫微渊思如泉。 高情那更属云天。语笑杂歌弦。向啼夬鸟声中,落红影里,忍负芳年。浮生转头是梦,恐他时、高会却难全。快意淋浪醉墨,要令海内喧传。
词序中言创作时间为甲寅三月,张镃生卒年中只有绍熙五年(1194)为甲寅年,此词当作于此时。这首词是桂隐与友人宴享时即席之作,上片写清明过后“春意无边”,与友人出行,高朋满座的盛况。欢声笑语的欢快总易引起人盛况难久的哀思,下片一声鹈夬鸟的鸣叫让作者感叹浮生如梦,“恐他时、高会却难全”。南宋内忧外患,偏安一隅,士人心态也转向与东晋相似的内向超越型文化心态,对自身意义价值的思考成为士人常谈的话题。生命流逝、朝不保夕的情绪占据了南宋文人的案头,张镃就常发出“白发欺人早,多似清霜”“算到底、空争是非”的感慨。《木兰花慢》这首词中的鹈夬鸟是美人迟暮的叹息,但与辛弃疾相比少了英雄壮志,多了忧生的哀伤。此词的鹈夬鸟是应时而生的鹈夬鸟,是时代赋予士人普遍情绪的表达,《全宋词》中南宋词对鹈夬鸟意象的使用远远多于北宋,张镃式的感伤占据了多数,如吴文英《六丑·壬寅岁(1242)吴门元夕风雨》:
渐新鹅映柳,茂苑锁、东风初掣。馆娃旧游,罗襦香未灭。玉夜花节。记向留连处,看街临晚,放小帘低揭。星河潋滟春云热。笑靥敧梅,仙衣舞缬。澄澄素娥宫阙。醉西楼十二,铜漏催彻。 红消翠歇。叹霜簪练发。过眼年光,旧情尽别。泥深厌听啼夬鸟。恨愁霏润沁,陌头尘袜。青鸾杳、细车音绝。却因甚、不把欢期,付与少年华月。残梅瘦、飞趁风雪。向夜永,更说长安梦,灯花正结。
此词写于上元节时,上片回忆昔日元夕佳节盛景,过片处“红消翠歇”笔锋一转,写今日元夕之风雨凄切。光阴流转,白发斑斑,旧交不再,此时传来的鹈夬鸟声让作者更是心情郁结。此时尚在初春,正是新绿待发之时,不当有鹈夬鸟声,显然此处非实写,乃是借之表现自己少年不再,状今夕之异。
援引《离骚》对北宋词鹈夬鸟意象加以改造,辛弃疾壮志未酬的呼喊与张镃美人迟暮的感叹成为两种不同的声音,一出以壮语,道英雄老矣,一出以哀声,喟年华不永。词起于配乐而歌,随着文人士大夫对词创作的介入,词开始了徒诗化的进程,即逐渐摆脱音乐赋予它的特点。由代歌者言趋向作者与抒情主人公的同一,由即席演唱变为案头文学,无论创作者是否自觉,这都是词体的发展规律。苏轼的以诗为词是自觉的改造,李清照反对东坡,提倡别是一家,但她的词作也表现诗化的趋势,婉约和豪放是词体徒诗化进程中展现出的两种风格,苏轼不过是略显激进的一派。鹈夬鸟与杜鹃同为伤春,但因《离骚》的源起,使鹈夬鸟带有强烈个人意识的介入,南宋对北宋这一意象的改造是援《骚》入词的雅化,也是自我意识凸显的表现。而辛弃疾以豪壮语抒发和张镃以哀伤语抒发则是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在词体徒诗化进程中的呈现。
明白了鹈夬鸟意象在南宋时的变化,我们对一些词便可进行深入的解读,如戴复古《浣溪沙》:
病起无聊倚绣床,玉容清瘦懒梳妆。水沉烟冷橘花香。 说个话儿方有味,吃些酒子又何妨。一声鹈夬鸟断人肠。
戴复古词追慕稼轩,现存词作46首,大多都以豪放语出之,即“歌词渐有稼轩风”。诸葛忆兵先生将其中5首视作别调,认为都属于艳情词,其中《清平乐·嘲人》偏离艳情话题,真正意义上的艳情便只有4首,《浣溪沙》(病起无聊倚绣床)当列其中。戴复古一生布衣行走江湖,但他对仕途是怀有热情的,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抒发爱国情怀和收复江山的愿望,其《思归》曰:“不能待诏金銮殿,尝欲献诗光范门。身在草茅忧社稷,恨无毫发补乾坤。”显然他力图进入仕途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未果,并非甘心载酒江湖的生活。清楚了戴复古的诗词旨趣和身世,再联系鹈夬鸟的内蕴变化,对于这首《浣溪沙》我们便可视为戴复古是借描写女子病起无聊、韶华消逝而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情绪。由此可见,词在经历了由作者代女子言而发展为自抒胸臆后,以女子代作者言的诗歌比兴传统逐渐进入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