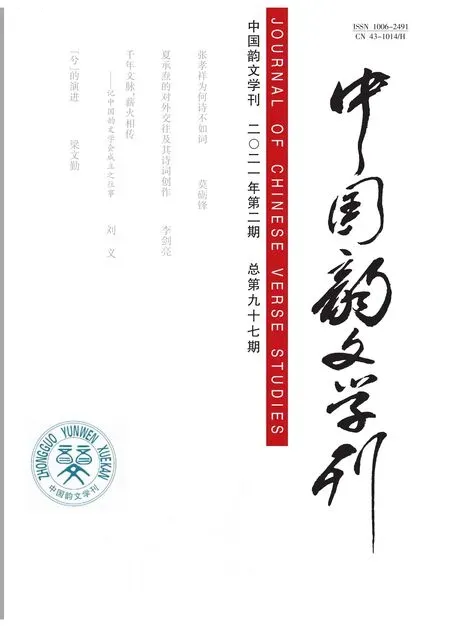略论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型塑
杜松梅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视人品与诗品的关系,所谓“文如其人”,认为作家的人品关乎诗品,严苛的理学家甚至将道德修养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人品包括作家的人格、操守、思想、品行等多方面要素,光明正大、磊落洞达、忠君爱国是人品高尚的表现,而狂狷、诡激、恃才倨傲、薄行寡义则是相反的品性,为儒家伦理所不容。尽管人们也承认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创造,追求创作自由的观念常常使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打破传统道德习惯的约束,用道德判断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就有失偏颇,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因人品导致对作家作品不能全面接受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李商隐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因背负着“背恩无行”的骂名,李商隐诗歌在唐宋元明四朝始终走不出接受低谷,尽管人们也注意到他在艺术方面的种种突出成就,但这些肯定的声音或被淹没,或仅有一时反响,总之,得不到主流诗坛的普遍认可。分析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塑造过程,可以让我们了解李商隐接受早期形态,理解读者对作家作品接受的影响,以及文学史上人品与诗品合一的接受现象,探究接受史的一般规律。
一 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始作俑者——《旧唐书》
对李商隐人品的贬抑性评价由来已久。追溯所及,可至于唐五代。唐五代李商隐接受资料不多,除去选本选录外,大约有17条笔记文献,外加8首赠诗,其中就有4条明确涉及李商隐人品问题。这4条文献分别是王定保《唐摭言》、刘昫《旧唐书》、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了两条)。长期以来李商隐“背恩无行”的形象就由这几种文献共同塑造。其中《旧唐书》对李商隐的生平遭遇及其与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交往始末有详细交代,并直接记载了李商隐“背恩”“无行”的说法,成为对其人品贬抑的源头。不妨就以这条文献入手展开分析。为便论述,现将相关文献附下: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祕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雠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
这则文献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的始作俑者。根据其记载,李商隐早年受知于令狐楚,入过其幕府,跟随其入京,还与其诸子交游,受到很多优待,关系非同寻常,但在会昌、大中年间却又入了王茂元、郑亚幕府——本来文人去就在唐代非常普遍,不幸的是,令狐楚是“牛党”,即李宗闵一党,而王、郑则属于“李党”,即李德裕一党,两党政见不同,势同水火,故李商隐入王、郑之幕就被认为是“背恩”“无行”,遭到“牛党”鄙薄。
这段记载看起来相当客观纪实,但从叙述线索中我们仍可以分析史官的评判立场。从事实来看,李商隐并非有意背弃“牛党”——他在令狐楚幕主要是学习骈文写作,与令狐绹的交往也仅是诗文唱和,且此时方当年少,未有功名,于党派之争自无机会参与;此外,入“李党”诸人幕府如果是出于有心的选择,接连两次转投还有何颜面再向当年背弃的“牛党”陈情告哀?就像纪昀所说:“义山盖自行其志,而于朝廷党友无所容心于其间。感王茂元一时知己,故依而从之,不幸值绹之溪刻,遂成莫解之怨,固迫于势之不得不然耳。倘以为有意去就,则后之屡启陈情,又何说以处之?”但史官似乎无意分辨于此,而是武断地做出了“背恩”“无行”“无持操”“恃才诡激”的结论,并将李商隐仕途不顺的原因归结为此。“无行”指向李商隐的人品问题,由于其“背恩”并不仅仅是背弃令狐楚师恩这么简单,它还加入了党争的因素,引发的后果是被整个李宗闵党鄙薄,性质是很严重的,所以“无行”之评是非常严厉的斥责。有这样一个“背恩”“无行”的名声在先,李商隐的整个品行真可以用“无持操”“恃才诡激”来评价了。如果说前面“背恩”“无行”之评可能出于史实,出于“牛党”的说法,但后文的“无持操”“恃才诡激”则实在是史官的判断,是他对如何定义李商隐“背恩”之举的态度——翻检整个唐五代文献,除《旧唐书》之外也没有类似记载。“无持操”,是指没有操守,这里用来指李商隐首鼠两端、依违于两党之间。“恃才诡激”,指仗着有些才华就行为放纵偏激、不加检点,做出一些有违伦理道德为文士阶层所不容的事,其实质还是指李商隐“背牛就李”的行为。这便是史官的立场。
史官虽然批评了李商隐“背恩无行”,但也记载了其仕宦坎坷的原因在于令狐绹一党的打击。据此记载,会昌年间李商隐第一次背弃令狐楚转靠王茂元,令狐绹即对其心生怨恨,故施以打击,“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史书虽未对李商隐官职不升的原因细说,但根据上下文,这件事发生在令狐绹已对李商隐“背恩”行为有了成见之后,因此它很显然的意味是:导致李商隐“久之不调”的原因就是令狐绹从中作梗。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中说自己应博学宏辞科时“尔后两应科目者,又以应举时与一裴生者善,复与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似乎是已经入选,又因一“中书长者”的诋毁被除掉了名字。冯浩《玉谿生年谱》说此“中书长者”是令狐绹相厚之人:“义山以娶王氏,见薄于令狐,坐致坎壈终身,是为事迹之最要者。……宏词不中选,已因娶王氏而为人所斥也。《与陶进士书》既叙绹助之成进士,复曰:‘此时实于文章懈退,乃命合为夏口门人之一数耳。’其感之也浅矣。又曰:‘前年为吏部上之中书,归自惊笑,复懊恨周李二学士以大法加我。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乐。’此饰辞也。中书长者,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很可能就是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做出的推断。冯浩认为李商隐在应博学宏辞科时已经与令狐绹有了嫌隙,所以在写作《与陶进士书》时就很隐晦地用了曲笔。该书还说:“时令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资绹力,而遽依其分门别户之人,此‘诡薄无行’之讥断难解免,而绹恶其背恩者也。”显然与《旧唐书》的观点一致,认为李商隐就是一个“背恩无行”之人。冯浩是清中期李商隐研究大家,此时已有很多学者为义山人品做过辩护,但冯浩仍对此颇著微词,可见《旧唐书》“背恩无行”的评价影响之大。尽管《旧唐书》未对令狐绹打击李商隐的行为加以回护,表面看一个“背恩无行”,一个“无情”,双方都有责任,但对二者的批评程度是不同的:“无行”是人格、道德上的大缺陷,这对最重人格出处的古代士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为儒家伦理所不容;而“无情”则更多属于个人行为,类似“冷漠”“薄情”,与“无行”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故《旧唐书》以“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作为结论性的评语收束,贬抑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顺便提及,“无行”之评具贬抑色彩,带有历史积淀意味的价值评判性质,一旦被烙上“无行”的印记,似乎文章作得再好也无甚可观。这就可以解释《旧唐书》对李商隐诗文造诣的评价了:“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仅仅说他通古文、骈文,而于其诗歌未置一词,其言外的不屑意味是可以想见的。
《旧唐书》“背恩”“无行”“无持操”“恃才诡激”之评等于正式宣告了李商隐“背恩无行”的文人形象。作为官修史书和李商隐人品记载的最早来源,该书以其权威性和“想当然”可靠性,成为对其人品贬抑的源头,此后史书、笔记诗话凡关涉义山人品者皆首先以此为据或作为重要考量,如《新唐书》和《唐才子传》。《唐才子传》还涉及李商隐《九日》诗的笺释问题,拟待下文讨论,此处不妨以《新唐书》的相关记载与《旧唐书》做一比较,以见其流衍变化。为便讨论,亦将此文附下: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或言英国公世绩之裔孙。令狐楚帅河阳,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岁具资装使随计。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调弘农尉,……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茂元死,来游京师,久不调,更依桂管观察使郑亚府为判官。亚谪循州,商隐从之,凡三年乃归。亚亦德裕所善,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京兆尹卢弘止表为府参军,典笺奏。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弘止镇徐州,表为掌书记。久之,还朝,复干绹,乃补太学博士。
仔细对比《旧唐书》所记,可以发现《新唐书》除了对李商隐生平有所补充、修正外,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对其人品的记载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该文突出了李商隐与令狐绹的交谊:“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
,故擢进士第。”这为下文二人的交恶埋下了伏笔。二、在对李商隐“背恩”之举的态度上,《新唐书》更鲜明,其立场一共出现三次:“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在《旧唐书》中,李商隐只是被李宗闵党即“牛党”鄙薄,而到了《新唐书》中,李商隐成了一个被两党都看不起的人:“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三、对李商隐“背恩”行为的谴责,二书用词也不同。《旧唐书》说“背恩”“无行”“无持操”“恃才诡激”,《新唐书》则是“诡薄无行”“忘家恩”“放利偷合”,如果说“恃才诡激”还有点恃才傲物、行为不大拘检的意味,那么“放利偷合”则实在是夤缘攀附、苟且狡诈、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两相比较,《新唐书》对李商隐“背恩”行为的谴责更甚。这些变化说明:《新唐书》接受了《旧唐书》所塑造的李商隐人品形象,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衍化,其结果就是李商隐在这种几乎具有“历史定论”的官修史书中“背恩无行”的形象进一步定型。二 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加固者——《唐摭言》《北梦琐言》
上文述及,唐五代文献共有4条涉及李商隐人品问题,除《旧唐书》之外,另外3条出自《唐摭言》和《北梦琐言》。后二书都涉及李商隐《九日》诗的笺释问题,其实质都是以一首诗歌的本事考证隐含对李商隐人品的批评。先来看《唐摭言》的记载,该书卷十一“怨怒”条记云: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
这则文献中提到的诗就是《九日》。“令狐文公”指令狐楚,“赵公”即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大中中”,表明故事发生在大中年间。若联系《旧唐书》的记载,此时正是李商隐与令狐绹交恶之后,这是此则诗话所记情事发生的背景,虽然文中没有明确提到,但我们应当理解为隐含在其中,这只要看条目“怨怒”二字即可知。只是“怨怒”二字是指谁?是令狐绹怨怒李商隐所以不接见,还是李商隐不获见因此怨怒?抑或指双方都有怨言或怒气?这则诗话于李商隐着墨较多,于令狐绹只说“义山谒不见”,并没有流露更多态度,而说李商隐不获见就题了一首诗在人家屏风上,如此看来“怨怒”指李商隐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这样,那么《九日》诗就是一首李商隐表达怨望的诗了。顺着这个思路,《九日》诗的内容也就可以这样解:“山公”指令狐楚,“郎君”指令狐绹。前四句指李商隐回忆当年与令狐楚把酒言欢度过的一段畅快时光,后四句寓意令狐绹:郎君如今显贵腾达就忘了当日相交之谊,空让“我”如放逐之楚客咏《离骚》而已。如此,李商隐的确容易给人诡激、无行的印象:拜谒不获见就毫无顾忌地在人家屏风上题了一首寓意这么明显的诗,其怒意、其讽刺意溢于言表,这不是反向证明了李商隐确实做了“背恩无行”的事吗?
《唐摭言》的这条记载便是李商隐《九日》诗“本事”的来源。我们以上的分析结合其出现的背景及前后语境做了一定阐解,但严格说来,除在条目中标明“怨怒”外,作者并没有对李商隐或令狐绹表达谴责或同情等主观态度。稍后于此的孙光宪《北梦琐言》所记也是此事,但却有了进一步发挥。且看其原文: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已。……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卷二“宰相怙权”)
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卷七“李商隐草进剑表”)
与《唐摭言》比较可见,在后书中,事件的叙述还很简略,只于条目前标为“怨怒”,并记载李商隐往谒令狐绹未获见,于是在屏风上题了一首《九日》诗,没有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且它看起来只是在记录一个事实,并不表明作者立场;但到了《北梦琐言》中,“屏风”被换成了“厅阁”“厅事”,还补充了令狐绹见到此诗的反应——“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笔者以为这与夹在二书之间的《旧唐书》的记载有关。也就是说,《北梦琐言》关于《九日》诗的记载是在《旧唐书》李商隐“背恩无行”的背景之后,很可能受到其影响。按《旧唐书》所记,李商隐初依牛党令狐楚,后投靠了为李党的王茂元,茂元死后又转向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企求援引,但令狐绹不予理睬,所谓“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这些记载便是《北梦琐言》“(令狐绹)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的依据——两种文献意思非常相近,文字也大同小异,可证《北梦琐言》的确是接受了《旧唐书》的说法。
同样是关于一首诗歌的“本事考证”,《北梦琐言》没有完全承袭《唐摭言》,而是添加了一些元素,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使它看上去更像一则班班可考的名人逸事——说明从《唐摭言》到《北梦琐言》,由于《旧唐书》的关系,《九日》诗的内涵在流传过程中被进一步发挥了。
再回到李商隐的人品上来。《唐摭言》《北梦琐言》和《旧唐书》相较,前者表面看仅记《九日》诗“本事”,对李商隐人品并未直接评价,但其出自故事的形式,以其具体生动的情节为这则诗话增添了可信度,从而可以让我们深刻地感受李商隐与令狐绹交恶的程度和后果。总之,二者进一步坐实了李商隐“背恩无行”的人品形象。
三 《九日》诗本事衍化中的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
《唐摭言》《北梦琐言》之后,《九日》诗本事基本定型,后此关于该诗的解读基本分成两种:沿袭和辨析,两者努力方向虽相反,但就对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塑造上则无根本不同,都推动了这一形象的加固。
从《唐摭言》到《北梦琐言》,《九日》诗的本事有了初步衍化,但二书的成书年代相去不远,后人遂将其并为《九日》诗本事的起源,从北宋李颀,南宋计有功、葛立方,元代辛文房,一直到清代笺注李商隐诗的几位大家钱龙惕、朱鹤龄、吴乔、胡以梅、陆鸣皋、陆昆曾、姚培谦、程梦星等,后人解此诗者基本都援引此说,有的还“添油加醋”,遂使《九日》诗的内涵进一步衍化和丰富。其中,李颀和计有功仅引原说,未加评论(前者引《北梦琐言》,后者引《唐摭言》),他说则做了意味丰厚的引申和发挥,而这背后又无不关涉着李商隐的人品问题。如较早对李商隐提出严厉批评的北宋理学家葛立方在其《韵语阳秋》卷十一中记载道:
李商隐《九日》诗云:“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盖令狐楚与商隐素厚,楚卒,子绹位致通显,略不收顾,故商隐怨而有作。然实商隐自取之也。且商隐妻父王茂元与所依郑亚皆李德裕党也。商隐与二人昵甚,故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绹恶其异己也。后绹当国,商隐亦归穷自解,绹虽与一太学博士,然商隐亦厚颜矣。唐之朋党,延及缙绅四十年,而二李为之首,至绹而滋炽。绹之忘商隐,是不能念亲;商隐之望绹,是不能揆己也。”
在唐宋官修史书新、旧《唐书》中并没有将李商隐的“背恩无行”形象与《九日》诗的解读联系起来,到《北梦琐言》才有所关联,而到了《韵语阳秋》中则明确将二者结合记录。所谓“自取之”“厚颜”,贬抑色彩非常浓厚。与《北梦琐言》比较,后者所谓“宰相怙权”“惭怅”等语,显然是站在同情李商隐的立场上,对令狐绹持讥讽态度;而在葛立方的笔下情况则完全相反,语语直指李商隐,并上升到对其人品的斥责。再从用语来看,很显然是综合了《唐摭言》《北梦琐言》与新、旧《唐书》多种文献,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加工。
与葛立方一致,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谈到李商隐与令狐楚父子的一段交往,并引《九日》诗本事为证:
楚出,王茂元镇兴元,素爱其(李商隐)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除侍御史。茂元为牛李党,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来京都,久不调。更依桂林总管郑亚府为判官,后随亚谪循州,三年始回。归穷于宰相绹,绹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谢绝殊不展分。重阳日,因诣厅事,留题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绹见之恻然,乃补大学博士。
这条记载显然也与《韵语阳秋》同一脉络,不过,将其与此前的相关记载加以比较仍可看出变化。其一,李商隐的“背恩”行为在《旧唐书》中仅说遭到牛党鄙薄(“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新唐书》又说同时遭到牛、李两党轻视(“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唐才子传》则将受鄙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士流(“茂元为牛李党,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可见这种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也说明辛文房对李商隐人品的定位。其二,对牛、李两党的态度有所变化。“绹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小人”二字在此前的相关记载中还未出现过,也就是说,之前的所有记录者们在这场“牛李党争”中都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即究竟“李党”是正义的,还是“牛党”对国家、人民更有益,从记录者的态度中看不出,但在《唐才子传》中却出现了这样的字眼,这虽然不能完全看作辛文房的态度,但还是容易引导读者:“小人”之谓说明令狐绹是代表正义的一方,他对李商隐的鄙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是代表整个政治上坚守正义一方的,这样,李商隐的去取行为性质就变了,由一个有违道德的文人变成了政治上投机取巧、不辨忠奸的小人(同谋)。
《九日》诗的所谓“本事”自《唐摭言》《北梦琐言》定型以来,再经宋元人的引申加工,内涵已相当丰富,清人的笺注则使其进一步衍化。如吴乔云:“故犯家讳,令不得削去耳。”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云:“或以此触其忌讳,故益憾之欤?”都完全在前说的基础上作解。一直到张采田,其《玉谿生年谱会笺》尚且云:“王定保、孙光宪皆五代人,于唐耳目相接,所载似可信从。”
对史书与笔记小说未加分辨的抄录和发挥,表面看是一种信实的态度,但在客观上却助长了《九日》诗就是为怨怒令狐绹而作的可信性。人品既已不忠不义,还将不满发泄在诗作中,这样,李商隐就不但是一个人品有问题,还是一个喜欢在作品中不知羞耻地流露怨怒之态的人。从《唐摭言》到《北梦琐言》,对《九日》诗的解读已不难看出在《旧唐书》影响基础上的演绎变化,再到《韵语阳秋》、《唐才子传》、清人笺注,更是在评价诗人或详述其人履历时援引笔记家言以为《九日》诗作解,于是,随着《九日》诗“本事”的衍化,一个“背恩无行”的文人形象就这样牢不可破了。
作为李商隐接受早期文献,《唐摭言》《北梦琐言》似乎以不可撼动的“可靠性”为《九日》诗提供了阐释的依据,不过,也不是所有批评者都同意这种解读,只是初期辩解的声音在“无行文人”形象已牢固树立的情况下太过微弱,或某些质疑基本是在细枝末节上修正,不足以撼动人品缺陷的根本。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南宋胡仔,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四云: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满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裁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人得再窥。”《古今诗话》云:李商隐依令狐楚,以笺奏受知,后其子绹有韦平之拜,寖疏商隐。其后重阳日,商隐造其厅事,题此诗,绹睹之,惭恨,扃锁此厅,终身不处。又《唐史本传》云:“令狐楚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后从王茂元之辟,其子绹以为忘家之恩,放利偷合,谢不通。绹当国,商隐归穷,绹憾不置。”则商隐此诗必此时作也。若《古今诗话》以谓“绹有韦平之拜,寖疏商隐。”其言殊无所据。余故以本传证之,但绹父名楚,商隐又受知于楚,诗中有“楚客”之语,题于厅事,更不避其家讳,何邪?
胡仔首先考证了李商隐《九日》诗的作年,认为《古今诗话》(记载与《北梦琐言》一致)系于令狐绹“有韦、平之拜”时有误。其次,胡仔认为李商隐既受知于令狐楚,不应在诗中直呼其名讳,这一点《古今诗话》记载也不确。胡仔从这两方面辨析了《唐摭言》等笔记小说记载的不可靠,但他说得比较含混,后来冯浩在笺注该诗时明确指出:
义山于子直,既怨之,犹不能无望之,敢于其宅发狂犯讳哉?诸家之辨已明。余更定为此时途次(笔者按,指大中二年自桂管赴巴蜀途中)所作。……及三年入京,内实暌离,外犹联络,屡曾留宿,备见诗篇,何至不得窥东阁哉?本传所云绹谢不与通,亦误也。后人妄撰一宗公案,皆不足信。
不但分辨《九日》诗不可能题于令狐家厅壁,并进一步表明《唐摭言》等所记皆为“妄撰”。的确,李商隐再任诞偏激也不至于在人家厅堂上题诗讥讽,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令狐绹肯定会对他更厌恶,两个人的关系会更糟,令狐绹后来也不会再对他施以援手。从《九日》诗的字面如“山公”“十年”“汉臣”“楚客”“郎君”等,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寓意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联想,这大概是《唐摭言》根据这样一首“叙事”诗虚构出一个故事的原因。
从胡仔、冯浩的辨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虽然驳斥了《九日》并非一首题壁诗,但却未从实质上推翻《唐摭言》的解读,其中缘由可以程梦星的言论说明。程氏《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在笺注该诗时说:
旧人说此诗者以为题令狐之厅壁。驳之者以为“楚客”字不避绹之家讳,必非题壁,此论得之。况明言贵施行马,东阁难窥,又何从题壁耶?然要为怨绹而作无疑也。
道出了大多数笺释者的心声:尽管《九日》诗的题壁之事或出于妄撰,但其寓意令狐绹则一定没有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对《九日》诗本事的辨析于义山人品的驳正其实并无本质上的突破——它仍在巩固着李商隐作诗以表达怨望之情这个说法。
唐五代从一首《九日》诗发展而来的对李商隐人品的塑造,又借助史书的记载加固了这种形象。虽然解读方法受到过质疑,但仔细对照李商隐自己的作品,我们大概也会产生一种“怨怒”“希求援引”的文人形象。在其他诗篇中,如《酬别令狐补阙》一诗,他还表达了“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的渴求,诗语虽不至“志卑”“惕惧”,其急于剖白之意却也不可断然否认。确实,这也是为什么李商隐作为一个“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的文人形象被长期普遍接受的原因。
孙康宜先生在《陶潜的经典化与读者反应》一文中分析史书对陶潜嗜酒一事的记载时这样说:“这些逸事只是谣传而已,编造出来也许只是要强调陶潜作为一个隐士的任诞的性格。然而正是这些不很可靠的来源才成为了最重要的背景,被后代的批评家拿来解读陶潜作品。”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唐摭言》《北梦琐言》对李商隐“无行文人”形象的塑造手段如出一辙。这些诗话逸事被创造出来也许只是为了突出史书中的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或为其增添生动的细节,作为一个与昔日恩师以及恩师之子交怨的形象,一个不太懂得收敛、行为诡激的文士代表——毕竟一首字面上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诗歌的确可以构造出一个生动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些不太可靠的记载成为解读《九日》诗的最重要依据,这样,从一则诗话逸事发展而来的对李商隐人品的塑造,又借助笺释的“正当性”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形象,两者互相成就,遂使《九日》诗的所谓“本事”面貌定型下来。
《唐摭言》《北梦琐言》《旧唐书》,三者作为李商隐早期接受文献,前两种因为真伪难考,也就具有一种想当然的可靠性,《旧唐书》则因其官修史书具有一种历史定论的权威性,成为对李商隐人品贬抑的源头。恰好分别以《唐摭言》和《旧唐书》为界,发展出两条主线:《旧唐书》的记载直接塑造了李商隐陷入“牛李党争”的“背恩无行”的形象;《唐摭言》则借助“虚构”《九日》诗的本事,塑造了一个在诗歌中表达怨怒、陈情告哀的文人形象,其深层意涵则是揭示李商隐与令狐绹交恶,李商隐“背恩无行”在先的实质。这两条线索互相借镜:《唐摭言》对《九日》诗的解读成为《旧唐书》所记人品之污的具体实证,而《旧唐书》对李商隐人品的贬抑则进一步加大了后世对《唐摭言》所记的可信度,这便是唐五代对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塑造过程。
比较而言,《旧唐书》关于李商隐“背恩”“无行”“无持操”“恃才诡激”的记载是其“背恩无行”形象的最早文献,亦可说是这一人品形象的正式塑造者。相比于《唐摭言》《北梦琐言》,它的言辞更激烈,“背恩”“无行”“无持操”,这些对看重人生出处问题的古代文士来说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从官修史书的立场来看,显然道德人格及政治角色是其关注焦点,它被记录下来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不重人生出处问题的反面典型起到警示作用。而后两书借助《九日》诗本事的创造和衍化,侧面突显了李商隐行为无拘检、诡激放纵的人品形象,长期以来成为其“背恩无行”形象的补充。其弊端是作为诗人的一面在人品的压力之下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当然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