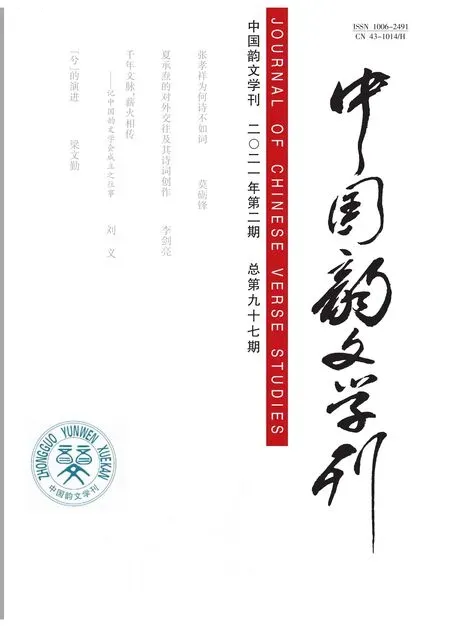赋与明朝的对外信息传递
——以《朝鲜赋》《交南赋》为中心
尧育飞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明朝翰林院侍讲董越(1431—1502)奉使朝鲜,五月归国,旋即撰成《朝鲜赋》。两年后,《朝鲜赋》刊成,董越将书寄赠朝鲜,朝鲜成宗(1457—1495)下令“其速印进”。此赋日后还传播到日本,成为东亚外交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名赋。在明代赋作中,类似《朝鲜赋》这样的外交赋作还有不少。它们的诞生受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左右。
赋与外交关系密切,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古代之诗,虽不别标赋体,然凡作诗者,皆谓之赋诗,诵诗者亦谓之赋诗。”行人作赋起源甚早,主旨及题材也丰富多样。汉代以后,行人赋作甚少。明代的《朝鲜赋》及《交南赋》是存世行人赋作的典型,业已成为研究热点。曹虹较早揭示董越《朝鲜赋》与明、鲜外交的关系,并探讨儒家“周览咨询”与《朝鲜赋》创作的关系。叶晔将《交南赋》与《朝鲜赋》并列为“明代域外赋的双璧”。不过,与明朝外交关系密切的赋作并不止于《朝鲜赋》与《交南赋》,赋与明朝的外交关系尚待深入拓展。在明朝的外交活动中,赋居于何种地位?《朝鲜赋》《交南赋》何以成为赋史上典范性的行人赋?明代出使赋作与明代外交信息传递机制关系如何?明朝如何利用这些赋作传递外交信息?此外,就创作的内容和体制而言,外交活动在赋作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凡此,是本文着意探讨的。
一 《朝鲜赋》《交南赋》的诞生与外交
赋与外交活动紧密相连。汉赋中的《甘泉赋》《羽猎赋》《大雀赋》《荔枝赋》等均有外交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并非外交活动的直接产物。汉代以后的赋史流变中,与外交有关的赋作约分两类:一类是与国家典礼相关的赋,如宋祁《王畿千里赋》、孔仲武《四海以职来祭赋》、司马光《交趾献奇赋》、李光地《眼镜赋》等;另一类则是“外交使臣采风异邦所作之赋”,这一部分赋作集中出现于明代。以出使朝鲜为例,收录在《皇华集》中明朝使臣赋作共计13篇,分别为:倪谦《雪霁登楼赋》、陈鉴《喜晴赋》、祁顺《太平馆登楼赋》《凤山赋》、董越《朝鲜赋》、龚用卿《登大平楼赋》、吴希孟《游翠屏山赋》、华察《登大平楼赋》《游翠屏山赋》、薛廷宠《宴庆会楼赋》、许国《吊箕子墓辞》、王敬民《谒箕庙赋》、姜曰广《吊箕子赋》。明朝使臣出使琉球也有赋作2篇,即萧崇业《航海赋》、谢杰《海月赋》。出使安南的赋作则有湛若水《交南赋》。
明代诞生数量不菲的出使赋,外交背景是明朝与周边国家关系较为和谐。朱元璋颁行《皇明祖训》,将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列为“不征之国”。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朝外交呈内敛态势。“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大大受损,为对抗鞑靼势力,明朝对朝鲜政策更为柔和。安南方面,永乐四年(1406),朱棣发兵讨伐,改安南为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但此举招致安南民众抵抗,明朝于是在宣德五年(1430)撤销交趾郡县,安南仍为藩属国。与朝鲜类似,安南在与明朝的交往中也获得优待。凡此,使明朝的外交活动得以正常开展。而明代活跃的外交事务也为出使文学提供丰硕土壤。朝鲜李朝开国前59年(1392—1450),明廷派往朝鲜的使团达95次,而朝鲜派往明朝的使团更高达418次,可见两国交往之密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朝使臣中文学人才的比重日益提升。景泰元年(1450),明朝遣翰林院侍讲倪谦出使朝鲜,取得良好反响。此后,明廷在选派使臣时更注重文学才能与德行名望,有名的使臣董越、湛若水都出自翰林院。而朝鲜方面,在倪谦出使后,则开始编撰大明使臣和朝鲜文人酬唱的《皇华集》,为中朝“诗赋外交”谱写新篇章。
弘治、正德年间,文学复古思潮逐步成形,而赋学的复古更早于此。明初文坛已衍绪祝尧“祖骚宗汉”说,利用赋作宣达王命、歌颂盛世。建文元年(1399)刘三吾创《敕下御制大明一统赋》,此后明人作赋歌颂大明一统、王朝盛世不绝如缕。明成祖迁都北京,诞生《南都赋》《北都赋》。莫旦(1429—?)成化年间作《大明一统赋》,第四卷专写外夷,显示利用外邦王化来歌颂盛世的创作意图。此外,“朝贡”“典礼”类赋作时有继作。永乐十二年(1414)秋,外邦进贡,夏原吉作《麒麟赋》,并率领群臣上表恭贺。可见,外交文化影响赋作在明初也较普遍。部分原因是外邦风物容量极大,在古代文章中,赋是较为适宜的载体。
与此同时,赋在周边国家也日渐兴盛。受中国科举东传影响,朝鲜在新罗末期即有零星赋作问世。到李朝成宗时期(1469—1494),朝鲜辞赋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与朝鲜类似,越南辞赋创作也因科举制度引入而兴起。越南黎朝(1428—1789)的“应制考试、试东阁科、士望科乃至武举考试均有诗赋题目……由此促成了越南辞赋的自立”。明代周边国家辞赋创作的兴起,使明朝“诗赋外交”的渠道变得更为通畅。
具体而言,董越与湛若水是弘治、正德年间有名的赋家。李东阳在《董文僖公文集序》云:“公初举乡荐游国学时,已能古文歌诗。暨及第入翰林,奉诏与庶吉士肄业,学益博,制作日益工,四方造请酬应,无虚旬月。”湛若水虽为道学先生,亦有《瑞应白鹊赋》《瑞鹿赋》《铁柯赋》等赋作多篇。两人分别出使朝鲜和安南,直接促成《朝鲜赋》与《交南赋》的诞生。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董越奉命出使朝鲜,通报上年弘治帝登基消息,当年五月回到北京,在朝鲜境内逗留约四十天。回京途经辽东时,董越已撰成《朝鲜赋》。《朝鲜赋》开篇云:“竣事道辽,息肩公署者凡七日,乃获参订于同事黄门王君汉英。所纪凡无关使事者悉去之,犹未能底于简约。”董越门生欧阳鹏在《朝鲜赋引》中云:“凡宣布王命,延见君臣之暇,询事察言,将无遗善。余若往来在道有得于周爰咨访者尤多,于是遂罄其所得,参诸平日所闻,据实敷陈,为《使朝鲜赋》一通,万有千言,其所以献纳于上前者率皆此意。”由其回京复命文书“率皆此意”,可推断此赋为董越出使朝鲜的直接产物。董越出使朝鲜后24年,湛若水于正德七年(1512)年二月从北京启程往安南,次年正月抵达,在安南逗留近一个月后回国。《交南赋》开篇云:“予奉命往封安南国王睭。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年正月十七日始达其国,睹民物风俗,黠陋无足异者,怪往时相传过实,托三神参订,而卒归之于常,作《交南赋》。”《交南赋》创作时间当在湛若水回国后不久,或亦是其回京奏复的文学副本。
二 赋作所见明朝外交信息传递
明朝使臣出使海外,诗文创作颇多,但诗文多为吟咏性情,据实记录外交信息不如赋作详细。外国对待明朝使臣的宾礼如何?明朝使臣如何在他国宾礼中获取外交信息?亚洲国家如何利用明朝的外交信息渠道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些信息在使臣的诗文中甚为罕见,《朝鲜赋》和《交南赋》则集中予以揭示。
《朝鲜赋》和《交南赋》如实记载朝鲜和安南的宾礼。《朝鲜赋》为纪实之作,内容大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记录朝鲜的地理形胜和风俗礼制;第二部分重在描绘朝鲜的山川气象及城郭建筑;第三部分叙写朝鲜国王礼遇明朝使臣,实际上是朝鲜王国狭义上的宾礼。从广义的宾礼而言,则《朝鲜赋》全篇都围绕这一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赋》记载朝鲜形胜和风俗礼制的文献材料,多由朝鲜官员提供,而这种文献交流活动处于礼制范围内。总体而言,《朝鲜赋》状物写景完全跟随董越出使的脚步。董越从辽东渡过鸭绿江,赋中则云“眷彼东国”,至义顺馆,便叙述“凡为城郭,皆枕高山”。此后的山川气象及城郭建筑,都随董越的步伐而移形换影。董越一行抵达王京慕华馆之后,国王出迎,则是“诏至也,王则衮冕郊迎,臣则簪裾鹄侍”。此后则叙述在王京颁弘治皇帝诏书,及朝鲜官方的礼遇。可以说,《朝鲜赋》是朝鲜成宗时期宾礼的实录。湛若水《交南赋》同样是外交活动的纪录,是安南宾礼的如实反映。不过,由于明朝与安南关系不佳,湛若水描叙越南山川风物等方面似乎颇受限制,如“悬崖崔兮渊际,设鸟道兮侧旋。或深入兮厚土,又上登兮高天。郁乎山林之险隘,川屈诣而缠绵”。湛若水自注云:“交人尚诈,不欲使由城邑为间。于乱道山中屈曲示远次数,自盘桅度水数十次,大抵皆此一水也。”在两国关系紧张时,安南的戒备无可厚非,毕竟湛若水也利用这次外交活动,进行情报搜集。如:“系木星以节行兮,披鹤氅而荷戈;兵衔枚以无言兮,挟矢弧而谁何?伏万矢于林中兮,一夫呼而众呀。”尽管受安南官员限制,湛若水还是尽可能根据耳闻目见记载安南的地理和军事信息。
《朝鲜赋》初步揭示明朝外交信息的获取渠道和加工手法。曹虹根据董越的自注,系统分析董越所做的资料准备工作为:“参考图书资料”“亲见目睹”“询问当地知情者”。这三项工作是使臣的本职工作,初意或并非为了作赋。明朝使臣能否顺利搜集资料,与国际关系变化息息相关。由于明朝域外文献储量有限,董越在搜集有关朝鲜资料时不得不倚仗朝鲜官员。而缺乏安南官方的帮助,湛若水依据中国古代一些笔记所写的《交南赋》不免荒诞。如“何海上之居人兮,头宵飞而海食。晨则返而完归兮,又追随于往夕”,湛若水自注云:“旧传安南海峒,有人头飞海中求食,晨返,头中有缝如线。”这一文献源自费信的《星槎胜览》及马欢的《瀛洲胜览》,尽管费信和马欢曾随郑和下西洋,但两书的记载可能出自《搜神记》。湛若水出使安南,两国不无猜疑,故湛若水文中云:“慨有职乎咨询兮,虽草木鸟兽而莫予馈。或申申而问俗兮,恐邦人之汝绐。”湛氏自注云:“其俗多诈,问之不以实告。”由于安南官员故弄玄虚,湛若水的情报工作基本失败。他所能借助的外交信息管道只剩下中国古老的典籍,而这些文献显然不足以应对彼时的外交需求。相形而较,董越咨询朝鲜士民则顺利得多。弘治元年(1488)正月十九日,出使前一个月,董越在北京着手咨访朝鲜燕行使。朝鲜贺登极使右议政卢思慎等人奏告云:
臣等在北京,正月十九日,通事朴孝顺到礼部,适见翰林院外郎马泰,曰:“我是侍讲董越陪吏。今以颁诏正使差往汝国,欲见汝国人,审问道路远近。汝宜往见。”翌日臣等令孝顺往见,语之曰:“本国宰相以贺登极入朝,明日当还。闻大人奉诏使本国,敢问起程日时。”董越答曰:“闰正月十一日、十九日中发程。但辽塞寒甚,欲待天气向缓发行。”仍问殿下春秋几何,孝顺答曰:“吾是微臣,未敢知道。”且问道路远近,答曰:“自辽东至义州,八站;自义州至王城,二十八站。”且问:“汝国站马良否?轿子有无?”答曰:“本国站路一如中朝,乘马、乘轿,唯大人所便。”董越曰:“我是今皇帝在东宫时侍讲。前此你国使臣皆以行人司员差之,未有堂上员差往者。今朝廷以你国事大至诚,特以如吾年老之人充使。此意传说宰相。”有称编修官者在坐,曰:“主人以东宫旧侍升为堂上,汝国当尊敬之。”
当然,朝鲜方面也迅速掌握董越一行的基本信息,并传回国内。《成宗实录》记载:“人言董越等皆能文者”,“闻今日上使长于诗,副使精于经学”,“见中朝待外国甚严,而待我国则甚亲厚”。为此,朝鲜做了相应准备。以往朝鲜接待大明的奉使者多为宦寺,此次董越出访,朝鲜方面仍循旧例,使董越颇为不快。朝鲜方面获知后,在董越一行抵达义州时,即派文臣许琮接待。许琮“长身玉立,衣冠伟然,两使瞿然相目曰:‘堂堂哉若人。’自是严棱渐消。左右虽或迕意,皆不问。每见公必留语,从容相与讨论经史,或至夜分而罢”。随后,董越和副使王敞方接受朝鲜奉使者馈赠,营造出良好的交往氛围。
上述内容亦可见明朝搜集外交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且为周边国家所熟知。安南与明朝关系紧张,故通过阻塞外交信息传递渠道表达对明朝的不满。而朝鲜则积极利用这一渠道表达本国的利益诉求。关于这一点,朝鲜《成宗实录》中远接使许琮的奏闻及成宗的诏复有详细记载:
臣在路上与天使言本国风俗。天使云,修先帝实录时当载之矣。此虽不可信,使本国美俗传播中朝亦幸矣。如丧制、职田、再嫁女子孙禁锢事,令该曹尽录,送付于臣,则臣与天使闲话时欲以此嘱之。(三月十八日)
天使到临津,舟中设小酌,从容谈话。天使语臣曰:前者诣成均馆时,请书学令以来。今来否?臣答曰:已书来矣。两使即令取来看了,谓臣曰:尽好。此本国大段美事也。两使又移坐相近,同看学令,密语良久。大抵皆称叹之语。副使语臣曰:本国若有美风俗书付老董先生事,曾已说与,何至今不书来。董先生还朝修先帝实录时,本国风俗当奏皇帝,书于史策。先生性直,平生不二言。吏曹还归,须将此意启于殿下。(三月十九日)
下书于伴送使许琮曰:“我朝良法美俗,今录去。如卿所启,其以是嘱天使。”(三月二十日)
从中可见,朝鲜官方有计划地授权许琮为董越提供大量参考文献,其中包括《风俗帖》。朝鲜官方希望通过董越去改变明朝对朝鲜风俗鄙陋的刻板印象。最终,他们的利益诉求取得显著成效。董越《朝鲜赋》云:“若夫所谓川浴同男,邮役皆孀。始则甚骇于传闻,今则乃知已经更张。岂亦以圣化之所沾濡,有如汉广之不可方也欤?”董越自注云:“予未使其国时,皆传其俗以孀妇供事馆驿,予甚恶其渎。比至,则见凡来供事者皆州县官吏,妇人则执爨于驿外之别室。相传此俗自景泰中其国王瑈袭封以后变之,辽东韩副总兵斌所谈也。川浴事出旧志,今亦变。”董越的论述与朝鲜方面的期待完全一致,不过他将信息来源转移到辽东总兵身上。此外,《朝鲜赋》还提及朝鲜“婚媾谨乎媒妁”,也扭转了以往中国典籍记载朝鲜不婚而娶的蛮俗印象。《朝鲜赋》最终呈现的文本表明,董越基本满足了朝鲜方面的利益诉求——朝鲜方面的外交取得初步成功。
《朝鲜赋》和《交南赋》还涉及明朝外交活动中的口头信息传递。“以文字记录、传递信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用口头传递信息方便、快捷,因而是历代君主对内对外沟通的主要方式。”董越出使朝鲜,尽管携带弘治帝诏书,但在颁诏等活动中,口头信息传递仍相当重要。《朝鲜赋》云:
“阍译则俯伏于周遭。”自注云:“阍者皆为乌纱帽、黑角带,俯伏捧王坐椅之足。通事、承旨则左右俯伏,以伺传言。予二人坐后通事亦伏俯,但无阍者。”
又云:……译者乃误以“天渊”为“天远”,予二人解其语音而为之申说。……译者又误传“远别”为“永诀”,盖张有诚善华语而少读书,李承旨读书而不熟华语。每观其传言至汗发而犹未达,殊可笑。
从中可见,明朝使臣拜谒朝鲜国王,译者由朝鲜方面提供,而明朝使团似并不配备翻译官。董越出使中,朝鲜方面派出的译者水平不足,导致大明使臣和朝鲜国王信息沟通不畅,幸而两人及时更正译者的误译,外加两国关系此时处于“蜜月期”,否则恐酿成外交风波。
三 如何利用赋作释放外交讯息
明朝善于利用赋作传递帝国政教讯息。“明代帝王时有特命文臣作赋的情况。……献赋一事,在明代历久不衰。”内政如此,外交也不例外。《朝鲜赋》和《交南赋》也作为明朝“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成为明朝释放外交讯息的途径。
明朝使臣回国后,多撰写文章记载出使经历,所选文章体裁各有不同。董越选择以赋作呈现此次出使活动,除本人文学造诣突出外,还与明朝官员意识到赋在东亚外交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关。桑悦(1447—1513)《两都赋后序》云:“臣成童时许国,为邑庠生。年十有九领成化乙西乡荐,屡举进士。之京,每见安南、朝鲜进贡陪臣寻买本朝《两都赋》,市无以应。臣私念我朝圣圣相承,治隆唐虞,则反无班孟坚、张平子等颂德之臣,非缺典邪?是心日往来胸中,奔走南北,觚临仲尼。去年春,蒙恩除授本职,训课之暇,颇有长晷,因忆旧阅,衍成二篇,总若干言。自起草至脱稿,凡三阅月而成。盖臣之此赋,经真纬实,不敢耕奇猎异,故不待十年之久也;虽以职卑不敢上进,然传示四方以及万世,两都制度亦可考见一二云。”桑悦这篇写于成化十五年(1479)的《后序》表明,朝鲜与安南使臣出使北京搜集外交信息时,目光触及赋作。赋的体国经野作用在外交视域下被放大了。桑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讯息,迅速撰成《两都赋》进献。桑悦这篇颂德之作有助于“传示四方”,显示天朝“治隆唐虞”的盛世气象。尽管桑悦并未因这篇颂世的赋作而超迁,但《明史》记载桑悦此文,足见这篇赋作在当日的影响,以及朝鲜使臣在中国搜集赋作的活动的频繁。朝鲜使臣的活动,当对明朝官员和士子造成一定的触动。
董越选择赋作呈现出使活动,获得极大成功。赋作流传海外,直接促成外交信息的二次传递。《朝鲜赋》弘治三年(1490)刊行,朝鲜使者很快在北京和广宁的书市注意到此书。朝鲜使臣卢公弼在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六月将书上献朝廷,成宗敕命:“此赋详载我国之事,其速印进。”可见,朝鲜方面非常重视这本书。而因为书中一些不利朝鲜的记载,此书在1503年还险些被禁:
大司谏李自坚曰:“前此天使之来,士族妇女成群观光,不合妇道。况我国女笠,中朝所无,华人见之必笑。向者董越、王敞之来,有一妇女乘轿过行。头目辈见之,不觉绝倒。董越著《朝鲜赋》,摭其事以讥之,请一切禁之。”王曰:“华使之来,观光似无妨。”
幸而朝鲜国王燕山君(李隆,1476—1506)宽宏大量,不以为意。此后,《朝鲜赋》广为流传。此书在朝鲜还有古活字本、嘉靖辛卯太斗南刻本等。另外,该书还被朝鲜编撰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收录,流传到日本。日本有《朝鲜赋》的覆刻嘉靖辛卯太斗南刻本、星文堂刻本、昭和十二年刻本等。在中国境内,有好事者把《朝鲜赋》中董越的自注抄撮而出,汇为《朝鲜国志》而单独刊行。《朝鲜赋》在明代还有抄本、《董文僖公文集》本、国朝典故丛书本、格致丛书本。由此可见此书在整个东亚的风靡程度。
《朝鲜赋》作为明朝外交“软实力”的一部分,在东亚广泛流传,这种现象引起明朝使臣的关注。此前,明朝使臣出使朝鲜和安南,多作诗文或图经等,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赋体上。嘉靖十六年(1537),翰林院修撰官龚用卿(1501—1563)奉使朝鲜,朝鲜重臣金安老(1481—1537)在谈论接待来使时云:
其日于江上,天使好打投壶,江山亦不观赏也。且前于祈顺天使来时,开城府分送妓女于闾阎,乱作丝竹之声,天使闻而乐之,《朝鲜赋》,亦有‘春风酒旆,夜月管弦’之语,以此或为故事。
看来,朝鲜官方已把《朝鲜赋》作为前代“故事”,去指引外交活动。而龚用卿也踌躇满志,希图续作《朝鲜赋》,以记朝鲜之盛:
上使告曰:“本国江山、州郡、风俗、官爵制度及举子名字书给事,已蒙允诺矣。因此可以不忘国王矣。”上曰:“时方撰集而未毕,当随后送之。”两使曰:“多谢多谢。董翰林《朝鲜赋》,意未备,故欲赋而敢请。”上曰:“今闻作赋之教,非徒一国之大幸。山川草木,皆赖大人,得以流芳名于百世。岂非美事?”上以《汉江游览图》呈之,两使曰:“此乃无价之宝。”(三月十七日)
上使曰:“俺依董先生越《朝鲜赋 》而作《续朝鲜赋》,于辽东入京师印送。”(四月三十日)
龚用卿希望补董越《朝鲜赋》之未备而作《续朝鲜赋》的愿望最终落空,其记出使朝鲜的文章仅有《登大平楼赋》传世。但受《朝鲜赋》成功的影响,明朝使臣借由赋作释放外交讯息的意图已公开化。而朝鲜国王也认为此类赋作描绘本国山川、风俗、官爵制度等乃“一国之幸”,是流芳百世的“美事”。
在安南,明朝使臣也逐步意识到利用赋作去宣扬威德。正德五年(1510),翰林院编修鲁铎(1461—1527)出使安南,回国途中作诗《丁卯元旦仍用前韵》云:“春回异域已无边,痛饮谁论酒圣贤。仗节来因颁紫诏,看花归拟及琼筵。旧传王会夸千载,新为《交南赋》一篇。却想履端同日庆,圣恩洪阔正如天。”从中可见,鲁铎很可能已经完成一篇《交南赋》,可惜这篇《交南赋》并未流传至今。直到两年之后,正德七年(1512),湛若水出使安南,方才创作出赫赫有名的《交南赋》。
董越《朝鲜赋》在东亚文化圈的广泛影响,激发使臣作赋的兴趣,其篇章结构也一并影响后来的赋作。仔细研究两篇赋作,不难发现,《交南赋》在诸多方面都有模仿《朝鲜赋》的痕迹。《朝鲜赋》开篇小序的结构为:“余使朝鲜经行其地者浃月有奇。凡山川风物……皆以片楮记之……参订于同事……赋曰。”《交南赋》则为:“予奉命往封安南国王啁,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年正月十七日始达其国。睹民物风俗黠陋,无足异者,怪往时相传过实。托三神参订而卒归之于常,作《交南赋》。”《朝鲜赋》选取自注的形式,《交南赋》也沿袭这一结构。不过,也许心存竞争意识,《交南赋》采用有别于《朝鲜赋》的骚体形式。
与《朝鲜赋》的轰动效应相比,《交南赋》的反响十分平淡。背后原因,颇为复杂。首先,《朝鲜赋》纠正对朝鲜的诸多偏见,颂赞朝鲜的礼俗,且朝鲜的一些外交诉求借此赋得以实现,故朝鲜乐于传播这一文本。再加上《朝鲜赋》资料翔实,不亚于国史方志,故东亚诸国对这一文本也有需求。《交南赋》则不同,赋中过于强调大明天威。湛若水铺陈交南历史,历数马援平南“立铜柱”、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功绩,“观其作赋主旨,仍是传统朝贡之武力统疆、礼德御宇的思想”。且赋作信息来源又仅为中国古老典籍,无从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史料价值也大打折扣,外加交南与明朝交恶,凡此,注定《交南赋》在安南无法流行。迄今也未见《交南赋》在越南地区的传播痕迹。
从《朝鲜赋》与《交南赋》作为外交“文化软实力”的效果看,《朝鲜赋》无疑取得成功。它既点明明朝乐见的域外王化,也照顾到朝鲜利益,还增进了大明子民对朝鲜的客观认识。而罔顾外国利益诉求,盲目宣称天朝威德的《交南赋》则纯粹变为明朝使臣的自我吹嘘。尽管假以辞色,实际外交效果却适得其反。嘉靖以后,随着明朝外交的收缩,出使作赋的创作条件进一步萎缩。万历以后,除去天启六年(1626)年翰林院编修姜曰广(1584—1649)出使朝鲜作《吊箕子赋》外,明朝使臣不再作赋,也无由利用赋作传递外交信息。
四 外交对明代赋作的影响
赋是明朝传递外交信息的重要文本。它既具有赋本身的文体特征,也随外交活动的变化而调适。明代出使赋开辟新的特点,周边国家也随之诞生形式谨严的唱和赋。由于明朝外交重在彰显国威,故使臣甚而利用赋作篡改外交活动内容,借以夸饰出使功劳。随着外交形势的变化,明代出使赋在颂美和讽谏之外,具备宣谕的新功能。
明代外交活动使赋的写作范围大大开阔。“赋史上首先出现了写外国的《朝鲜赋》和《交南赋》。”关于这一点,孙康宜写道:“以地域为描写对象的另一创新形式就是用赋描写海外之行。湛若水的赋……表达了明代中叶人们发现新世界的愿望。这些赋作所反映的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相互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外交须忠实记录出访经历,故明人评价出使赋也以纪实、征信为重要标准。《朝鲜赋引》所言“凿凿乎可信,郁郁乎有文”,可看作明人对出使赋的最高要求。《交南赋》评价稍低,征实不足即是原因之一。然而,又因明代外交往往意在扬我国威,为彰显外交成果,使臣不免着意夸耀出使功劳。董越在《朝鲜赋》中就经常露骨地凸显外交成绩,不厌其烦加以叙述,如“乃序东西,乃分宾主”。(自注:宣诏毕,引礼引天使降自中阶,东至幕次,俟王易服,乃引天使由中阶东升殿,引王由中阶西升殿。天使居东,西向;王居西,东向,再拜序坐。王之位对副使,稍下半席。)对颁诏时使臣和朝鲜王国如何行礼,董越不厌其烦予以渲染,以维护大明皇帝的威严。董越的意见,为朝鲜接纳,故其赋注中详细加以披露。
对出使中争礼失败的行为,《朝鲜赋》则存在有意裁剪乃至篡改外交信息的痕迹。《成宗实录》记载:
传曰:“我国事大至诚,故朝廷亦敬待我国。开国以来,国王无乘马迎诏之礼。今来使臣虽据《大明集礼》而言,岂可遽从其言而乘马迎诏乎?……”(三月十日)
权瑸将许琮之言启曰:“臣对天使夕饭后,因便语之曰:‘诸王则迎诏于门外,而今使殿下徒步于郊外,一国臣民莫不痛愤。’言之切至,两使相顾言曰:‘若然,则迎诏时乘辇,迎敕时乘马,颇近事体。’”(三月十二日)
针对朝鲜国王迎诏时乘辇还是骑马的问题,董越认为天子方能乘辇,藩王迎诏应当乘马,否则有僭越嫌疑。然而朝鲜方面表示反对,最终董越做出让步。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朝鲜国王迎诏时乘辇,奉敕时乘马。而《朝鲜赋》中则云:“诏至也王则衮冕郊迎,臣则簪裾鹄侍。巷陌尽为耄倪所拥塞,楼台尽为文绣所衣被。乐声也若缓以啴,虚设也亦华以丽。沉檀喷晓日之烟雾,桃李艳东风之罗绮。骈阗动车马之音,曼衍出鱼龙之戏。”在赋作中,董越有意规避朝鲜国王乘马还是乘辇这一外交礼仪环节,从而掩饰自己在争礼环节做出让步的尴尬。
因为征实,且须记载陌生的域外景象,故出使赋多师法谢灵运《山居赋》的自注体例,以避免因辞藻堆砌造成阅读障碍。其他体例上,则继承都邑赋传统。诚如明人王文禄所言,“甘泉《安南赋》效孟坚《两都赋》”。又因出使赋多传至域外,周边国家的文臣或起景仰之心,或不甘示弱,起而和之,形成独具特色的唱和赋。如倪谦《雪霁登楼赋》一出,朝鲜大臣申叔舟便有次韵之作,其序云“不揆孤陋,敢踵二苏和归来之辞,掇拾荒芜,强续高韵。非敢为赋,聊表景仰不能自已云尔”。朝鲜文臣的和赋并非率尔之作,其所作往往较中国唱和赋要求更为严格。朝鲜文臣悉数步和明使臣赋作原韵,难度极大,却为唱和赋提供了严格范例。唱和赋之外,异域同调的王粲“登楼赋”体,也经由明朝使臣的赋作,得以在朝鲜发扬光大。明使臣登楼赋作有倪谦《雪霁登楼赋》、祁顺《太平馆登楼赋》、龚用卿《登大平楼赋》等。这些赋作促进了王粲《登楼赋》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也激发朝鲜文士创作更多的“登楼赋”体作品。
此外,明代赋作的感情基调也受外交形势的影响。在《朝鲜赋》中,是颂美为主。而在《交南赋》中,感情基调既非颂美,也非讽谏,而是挟持天朝威严,斥责交南。赋中云:“曰国君之称富兮,又曷数以为对?”这是在责备安南国王为何与明王朝做对。“累杯盘之狼藉兮,瓜亦先期以为献。奏夷乐于殿上兮,鼓噪杂进而零乱。列雄虺以为阵兮,又沐猴而加冠。曰而重黎其苗裔兮,实乃祖之司礼也。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发而脱屣也。……倾都人以杂观兮,士女不分而塞途。悉鞠躬而加额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大指而跣趺。”这是强烈谴责安南的野蛮与落后。湛若水的道学家身份,或促成他斤斤于申斥安南应当被德治而王化。这与传统讽谏赋作不同,形成别具一格的“宣谕体”。
需要指出的是,出使赋尽管是外交活动一部分,创作时所受限制较多,但作者个人的文学色彩和艺术特点仍时有流露。董越搜集作赋材料,可找副使参订,而湛若水羞恼于无材料可找,乃云“托三神参订”,这种戏谑和荒诞是湛若水的特色。要之,湛若水生活时代晚于董越,此期明代文学思想中个人意识开始觉醒。董越不会把自陈记载在《朝鲜赋》中,湛若水却在《交南赋》中记载回答安南国王的询问:“曰中华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湛若水表明自己是增城人,此信息与出使活动关涉甚少,但湛若水却着意书写,从中可见其活泼泼的自我,也可窥见明代文学在正德年间的转变之一端。
五 结语
赋在明朝外交活动中扮演特殊角色。一方面,从中可见明朝外交信息传递机制;另一方面,出使赋作为明朝文化软实力一部分,扮演着传递外交讯息的角色。《朝鲜赋》和《交南赋》作为明代两篇重要的出使赋,在中国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扩充了都邑赋的题材,促成唱和赋的成熟;在讽颂之外,为赋作的功能开辟了宣谕和申斥的另类感情基调。《朝鲜赋》自问世以来,不仅在国内广受关注,在东亚也广泛传播。其中海东人士对此尤为关注。朝鲜人赵曮在《海槎日记》中记载他1763年1月24日在日本大阪“得见《朝鲜赋》三十余张,即皇明人学士董越以天使往来我国后所撰,而流入日本刊行”。咸丰十一年(1861),朝鲜使者赵云周在《答研秋(董文焕)》诗中云:“安知无后会,奉使重问津。好续《朝鲜赋》,青眼更相亲。”《朝鲜赋》已成为中朝友好外交的一个文化符号。
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教分离,外交收缩,使臣甚少作赋。外交信息传递的模式越来越以奏议、日录、图经等形式表现,虽不影响外事活动,但文学色彩大大降低,而辞赋作为“文化软实力”影响域外的功能也逐步丧失。赋在明代外交活动中的隐退,也是明代外交气象萎弱的一个写照。文学既可觇“世运”之端倪,则研究世变就不能不善加利用文学材料。“文运”与“世运”息息相关在赋作中表现尤深,则利用赋作以研究“世运”兴替,不妨作为开辟赋史研究的一条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