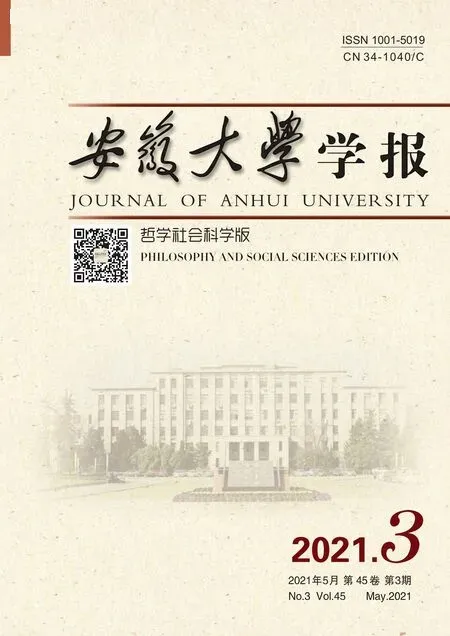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陈 光
明代台阁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概念,离不开四库馆臣的建构。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四库馆臣视吴伯宗为明代台阁体的滥觞和萌芽,而且这一观点接受度比较广泛。且不论大量学位论文谈及台阁体之渊源则必论吴伯宗,一些学术专著亦承此说。但是四库馆臣这一判断到底有没有问题,实际上已有学者尝试考辨。何宗美认为,“四库馆臣在衡量吴伯宗文学地位和影响时实有主观夸大之嫌”,至于主观夸大的原因,却未做进一步深究。应该指出,何宗美对吴伯宗的相关问题做出了一番十分有益的探索,如驳斥四库馆臣对吴伯宗《荣进集》的判断。四库馆臣认为《荣进集》为诗文残编,谓:“后人掇拾残剩,合为此编。”何宗美则认为,《荣进集》乃是极力突出吴伯宗状元身份的诗文选本,其主题是“荣进”。可见,四库馆臣将一本刻意突出作者政治身份的诗文选本,误认为可以全面反映创作状况的诗文合编,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吴伯宗为明代台阁体之滥觞。这一从立论前提便出现问题的判断,其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当然,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四库馆臣的真实意思并非简单地将吴伯宗视为明代台阁体的开创者。但问题在于,四库馆臣分别用“胚胎”和“滥觞”二词肯定吴伯宗对明代台阁体的重要意义。这种判断的真实内涵到底是什么?为何会做出这种判断?这种判断所反映的四库馆臣对明代台阁文学的文学史建构有没有问题?以上几点都使重估四库馆臣这一判断变得十分必要。
一、四库馆臣提出判断的具体语境及真实内涵
四库馆臣评吴伯宗《荣进集》曰:“(吴伯宗)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诗文皆典雅雍容,明一代台阁之体,于是滥觞”。对此,我们需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四库馆臣的这一判断以诗文风格为出发点。他们认为,《荣进集》反映出吴伯宗诗文的主体风格为雍容典雅,而“明代台阁之体”的风格亦为雍容典雅。因此盛行于明代的台阁体,以明初之吴伯宗为“滥觞”。其逻辑以诗文风格的相似性为基础。
第二,四库馆臣看重吴伯宗“有明首位开科状元”的政治身份,这可从两方面加以佐证。其一,明初文人中诗文写得雍容典雅的不止吴伯宗一人,汪广洋、蒋有立等人的诗文创作皆舂容雅正,陈谟、梁兰亦被四库馆臣视为诗文写得雍容典雅的文人。如果单从诗文风格上立论,这些人亦担得起明代台阁体“滥觞”“萌芽”的评价。但四库馆臣之所以只将吴伯宗视为滥觞,正是因为吴伯宗有明首位开科状元的政治身份。这就涉及第二点,即“有开国之规模”的两层含义:“开国之规模”首先指的是吴伯宗的诗文风格,意象宏大、气势豪迈;其次隐含对吴首位登科状元身份的看重。开科取士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运行以及相应的文官的政治、文学活动,意义不可谓不重大。而明廷通过科举考试遴选出的首位状元,可谓官方选拔、认定的新朝文人的最理想代表。四库馆臣正是看中吴伯宗新朝文人的代表性身份,站在风格论的角度,在吴氏与“有明台阁之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联系——明代文官的文学品味,在首位登科状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绝非历史的偶然。这亦是四库馆臣没有将诗文同样雍容典雅的汪广洋等人视为明代台阁体滥觞的原因。
第三,“明一代台阁之体”有其特定内涵,其所指并非四库馆臣通常意义上的“台阁体”,即以“三杨”为代表的馆阁文学。这牵涉到四库馆臣在不同语境下使用“台阁体”这一概念时的不同内涵。从整体上来说,四库馆臣所谓“台阁体”有广狭两种内涵。狭义的“台阁体”主要指以“三杨”为代表的馆阁文风,如所谓“三杨之体”“三杨台阁之习”“三杨倡台阁之体”等等。广义的“台阁体”不限于“三杨”,甚至不限于明代,指的是一种美学类型。如四库馆臣评价清人李霨:“其写一时交泰之盛,盖遭际盛时,故其诗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谓台阁文章者,盖若是也。”评王泽宏诗:“所作类皆和平安雅,不失台阁气象。”这种广义的“台阁体”,指的是以朝廷文官为主要创作主体的政治文学或曰庙堂文学。本文的观点是,四库馆臣在评价吴伯宗的文学地位与影响时,其所谓“明一代台阁之体”,指的正是宏观意义上的政治文学。但是四库馆臣为此添加了限定语——“明一代”,因此其所指应为明代的政治文学,它包括“三杨体”却不限于此。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四库馆臣做出“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吴伯宗)”的论断。之所以将“明一代台阁之体”做此种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如果将“明一代台阁之体”的具体内涵理解为狭义的以“三杨”为代表的馆阁体,则很难找到吴伯宗与“三杨”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内部的风格论、创作论还是文学外部的人格与心态,吴伯宗对“三杨”并不存在学理化的影响,其源流关系难以成立。其次,吴伯宗开科状元代表的文官身份,与“雍容典雅”的风格特征,二者共同构成了明代政治文学的两翼。由此可以推断四库馆臣提出这一判断的着眼点是有明一代的政治文学。关于四库馆臣看重吴伯宗“有明首位开科状元”身份这一点,前文已有详述。而“雍容典雅”足以代表明代的政治文学。在四库馆臣建构的明代政治文学的美学框架中,“雍容典雅”虽不能完全概括明代政治文学的风格特征,但它始终是最核心的关键词——明前期诗文以“雍容典雅”为优长,明中后期诗文以缺乏“雍容典雅”为弊病。因此,“雍容典雅”的美学风格论,和“文官为作者”的创作主体论,共同构成明代政治文学的两翼。四库馆臣认为,吴伯宗的状元身份,和“雍容典雅”的诗文风格,恰好与明代政治文学“文官创作”“雍容典雅”的两翼相契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吴为明一代台阁之体之滥觞的判断。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真实内涵:以翰林文官为创作主体,以雍容典雅为主要风格的明代政治文学,早在明初第一位状元吴伯宗身上初现端倪,因此可将吴伯宗视为明代台阁体的萌芽和滥觞。对于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真实内涵,已有学者予以指出。郑礼炬认为:“所谓‘明一代之台阁体,胚胎于此’,其真实内涵指的是明朝开国以后通过科举培养的翰林院作家及其创作的馆阁文学作品,以吴伯宗及其作品为肇始者。”郑礼炬抓住语境中的两点要素,其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对吴伯宗开科状元身份的把握,应该说符合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真实内涵。更重要的是,郑礼炬对“明一代台阁之体”具体内涵的理解,已经超越狭义的“台阁体”,将之拓展为“明朝通过科举培养的翰林院作家及其创作的馆阁文学作品”。此种解释,强调的是“明朝本朝培养的翰林院作家”这一创作主体的身份。这种理解与本文所谓“以明代文官为主要创作主体的政治文学”有一定相似性。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即使“明一代台阁之体”的真实内涵指的是明代的政治文学,吴伯宗是否担得起“滥觞”“萌芽”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四库馆臣在断代史视野下的文学史建构是否存在问题?欲解决以上问题,有必要考察明初科举的具体状况,尤其是吴伯宗所参与的洪武四年的科考。另外,吴伯宗本人所受教育的来源以及内容、特点,吴伯宗在明代的职官履历状况,亦需详加审辨。而以上两个问题皆须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考察。
二、易代之际视野下的吴伯宗与明初科举
(一)洪武文臣皆元材
吴伯宗,名祐,元统二年(1334?)生于江西金溪,洪武四年(1371)状元及第,官授礼部员外郎,洪武十七年(1384)死于任上。吴伯宗50年的生命历程有34年在元代度过,而只有16年在明代度过,是典型的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一般来说,文史学家将其归入明代,主要是因为吴伯宗在明代由科举入仕,其政治、文学活动亦主要发生在入明为官以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吴伯宗是一位典型的新朝文人,恰恰相反,他所接受的是典型的元代教育,其文学活动的积累期在元代。影响其文学才华、文学品味的诸多要素皆与元代关系密切。简而言之,他是一位典型的“元材”,只是政治与文学活动主要发生在明代而已。
这要从洪武四年的首次开科说起。此虽明初科举,但却与前元科举有诸多联系,其考试方针、取士标准等内容既承袭元制又具己之特色。从明太祖对历代科举制度的评价便可看出端倪。“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士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在朱元璋看来,汉、唐及宋代科举之弊在于过分看重士子的词章之学;元代科举依循古制,但弊端在于取士流程不规范,常有豪权势要干涉取士,使真正的贤者隐而不出。相较于对汉、唐及宋代科考内容的否定,朱元璋对元代科举采取了相对肯定的态度,因此其主导的科举制度部分承袭元制便实属正常。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明初科举部分承袭元制亦不失为一种“妥协”。毕竟此时参加科考的士子皆为前朝旧民,其文化人格的形成受元代的影响更重,其知识系统的建立更与元代举业密不可分。如果明初的科举完全弃元制不顾的话,从现实层面来看,将为科考士子带来巨大困难。
实际上,作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纂官的纪昀,已经注意到吴伯宗的科举试文,恰好能反映出明初科举承袭元制的特点。“元延祐中定科举法,经义与经疑并用。其传于今者,经疑有《四书疑节》,经义有《书义卓越》,可以略见其大凡。明沿元制,小为变通。吴伯宗《荣进集》中,尚全载其洪武辛亥会试卷,大抵皆阐明义理,未尝以矜才炫博相高。”既然纪昀认为吴伯宗《荣进集》所收之文,是证明明初科举承袭元制的证据,那么他也应当明白吴伯宗应为“元材”而非典型的新朝文人。但是四库馆臣依然将吴伯宗视为明代台阁之体的滥觞,对于这个矛盾之处的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判断并非纪昀本人的观点。因为四库馆臣对吴伯宗的观点,不止一处与纪昀之观点相龃龉。例如,四库馆臣谓:“其(吴伯宗)乡试、会试诸篇,可以考见当时取士之制,与文字之式……而集中所载试卷,乃经义而非经疑,殊不可解。”他们认为吴氏科场所作之文,属经义而非经疑,这恰恰与纪昀之观点相矛盾。纪昀早已认识到明承元制,“经义与经疑并用”,即使吴伯宗所作之文为经义,也实属正常,并无“殊不可解”之处。更何况,吴伯宗科场之文,确为经疑而非经义,只是四库馆臣没有辨清而已。清人《钦定续通典》亦载:“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七年开科,十八年会试,循元旧例,作经疑。至二十一年,始定三场之制。”作者将明初科举循元旧例的范围扩大到十七年开科、十八年会试,准确与否仍需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洪武四年的开科取士,大体上承袭了元朝旧例。而吴伯宗正是在这一年状元及第,开始了其在明代的政治、文学活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吴伯宗并非典型的新朝文人,而是依前元旧例、按前元标准所选拔的士人。无怪乎崔铣曾指出:“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乐而后乃可得而称数云。”
考察吴伯宗个人求学与成长经历,亦可看出他确为“元材”。吴伯宗生于书香之家,具有一定的家学传统。其曾祖父吴可与兄弟热衷科举,且“兄弟并以文鸣”。其父吴仪为元至正丙申乡贡进士。“(吴仪)自幼以缵承家学为事,鸡初号辄起,秉火挟册而读之。时建昌江公存礼、谢公升孙皆前进士,先生负笈从之游,继登乡先达虞文靖公集之门,于是博极群书,其学绝出于四方。”元季社会动荡,吴仪坚持在家讲学授徒,“遐迩学徒争奔走其门。先生随其资器,孳孳训迪,必使优柔厌饫而后已”。在文学功能观上,吴仪倡导文应有补世教:“作文不原于圣经,不关于世教,虽工无益也。”
吴伯宗受其家族,尤其是其父吴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热衷参加科举,具有积极入仕的精神。吴伯宗在诗文中屡次谈及君子应积极入仕的价值取向:“夫天之生贤所以为当世用也,明君在上,正群贤效用之时也……且既学矣,文矣,可以仕矣”;“是故幼而学,壮而仕,老而休,天下之通义也”。其次,在文学功能观上,吴伯宗与其父亲一样,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功能:“宜深究圣经贤传之旨而明其体,适其用,正其心,修其身……其大要在乎言忠信,行笃敬而毋自暴弃焉。……故夫学之术亦多矣,必欲体用之兼该,言行之两尽,然后可进于圣贤之域,可应乎国家之用,舍是虽有过人之才,朝夕孜孜犹恐学非有用之学”;“夫贤者之生世,或以忠贞奋,或以节行著,或以文章政事显,皆足以宏济于当时而垂范于后世,亦犹台莱之生,材美而有用也。夫岂夸耀荣显而已哉”。总而言之,家学对吴伯宗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说道:“共喜韦家经训在,惠连才大亦传芳。”吴伯宗对家学肯定、自豪的态度,亦可看出其所受家学影响之深,而其家学则多具元代特质。
梳理完家学对吴伯宗的影响,再联系吴伯宗的生平,我们便可得出结论:吴伯宗在家庭,尤其是其父吴仪的影响下,接受的皆为元代的教育。“(吴伯宗)生而颖悟,十岁通举子业”,吴伯宗十岁时(1344)为元至正四年,他所通晓的举子业毫无疑问应为元代举业。因此,他所接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与明朝都没有丝毫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典型的“元材”,而非新朝文人的代表。
(二)官大学士而非入阁:吴伯宗的职官履历
一般来说,明代的状元大多供职于翰林院,是典型的翰林文官,优者入阁为相,在政治、文学领域产生相当的影响。因而,明代的状元大多被视为准翰林文人,他们的仕途是一条由翰林院开始的文官之路,其文学创作亦可归入明代馆阁文学的范畴。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情况却并不适用于吴伯宗。在吴伯宗登科的洪武四年,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尚处于调整与准备期,具体来说,登第举子的授官制度尚未正式建立,朝廷没有明文规定状元要供职于翰林院。“洪武四年初开科,状元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第二、第三人郭翀、吴公达俱吏部主事。而会元俞友仁中三甲,为县丞。盖官制未定也。”可以说此时的科举制度在各个方面尚处于调整阶段,而登科士子授官非翰林只是一个细节而已。陆荣感慨“国初制度简略如此”,指的就是明初的科举制度。而洪武十八年,登科举子授官翰林院始成明文规定。“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初,翰林院官皆由荐举,未有以进士入者,故四年开科,状元吴伯宗止授员外郎,榜眼、探花授主事而已。至是诏更定翰林品员……而翰林遂为科目进士清要之阶云”。而“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则是天顺以后的政治惯例。从明代科举制度的完善过程来看,作为明代首位状元的吴伯宗,的确“无缘”由状元而直接官授翰林而成为翰林文官。而从吴伯宗状元及第后的职官履历来看,他亦未做过几年翰林文官,并无机会履行太多翰林文官的文化职责。
我们不妨将吴伯宗的职官履历与其参与的主要文化活动简列于下:洪武四年(1371),状元及第,授礼部员外郎,与宋讷同修《日历》;洪武六年(1373),与宋濂等同修《皇明宝训》;洪武八年(1375),谪居凤阳;洪武十年(1377),出使安南,归,任国子助教;洪武十二年(1379),进讲东宫,陈诚意正心之学;洪武十三年(1380),改翰林典籍,上制十题,命典籍吴伯宗赋之,援笔立就,上称“才子”;洪武十四年(1381),与编修吴沉、典籍刘仲质共进《千家姓》;以为太常寺丞,不拜;洪武十五年(1382)授国子司业,不拜,贬为金县教谕,未至,召回,授翰林检讨,不久授武英殿大学士,译《回回历》《经纬录》等天文诸书;洪武十六年(1383),坐弟吴仲宴谬荐案,降为翰林检讨;洪武十七年(1384)卒。可以看出,在吴伯宗的政治生涯中,担任翰林文官的时间比较短暂:洪武十三年至十六年,期间还有一段时间赶赴谪所金县,如果将东宫讲学的经历计算在内,吴伯宗的翰林文官经历不过五年而已。再看他的主要文化活动:参与编修《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进《千家姓》;译《回回历》《经纬录》等天文诸书;应制十题获明太祖嘉奖。其中,《大明日历》的编修,吴伯宗以礼部员外郎的职官身份兼职参与,可见这并不属于其主要的职责范围。而进《千家姓》与译外文书籍,亦非翰林文官的主要职责。唯一值得圈点的是应制十题为朱元璋所嘉奖。需要注意的是,吴伯宗曾任武英殿大学士,这一职官履历似乎与后来所谓“三杨”内阁重臣的身份有相似性,但实则不然。吴伯宗之武英殿大学士,与后来杨士奇所任大学士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具“顾问”的功能,并不具参与内阁机务的权力。因此王世贞曾指出:“官大学士而非入阁者,吴公伯宗也。”焦竑亦将吴伯宗划入“状元官学士”而非“入阁办事者”的行列。因此,吴伯宗借阁臣身份以发挥文学影响力的论断便难以成立。总体而言,吴伯宗担任翰林文官的时间比较短暂,因此并不是一位典型的明代翰林文官;他参与的文化活动亦难言丰富,在此基础上而产生的文学层面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三、易代之际视野下的明代台阁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吴伯宗并非明初新朝文人的典型代表,仅以吴氏与明台阁体诗文风格的相似性为基础,将其视为后者之滥觞的学术判断,不过是对文学表象的归纳总结,缺乏立足史实的学理性辨析。四库馆臣对吴伯宗的受教育情况与职官履历、文学活动缺乏具体入微的了解,且未考察明初科制与前元之关系,都导致其对吴伯宗文学地位与影响的夸大。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深层原因在于,四库馆臣对明代台阁体的文学史构建具有方法上的缺陷。如何宗美曾指出的,《总目》对明代文学史的建构具有明显的官学意识。通过对吴伯宗的考察可发现,四库馆臣过分看重文人的政治身份。吴氏开科状元所代表的新朝文人这一政治身份,影响了四库馆臣对其文学地位的认定。此处不妨考察四库馆臣以文人个案为节点构建起的明代台阁体的文学史脉络,管窥其构建的断代文学史所隐含的问题。
杨士奇是明代台阁体的代表人物,四库馆臣评价其地位:“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肯定杨士奇诗文创作对明代台阁之体的主导作用。再如评倪谦:“谦当有明盛时,去前辈典型未远。故其文步骤谨严,朴而不俚,简而不陋,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俨然将倪谦视为明代台阁体由雍容典雅走向肤廓冗沓之前的最后一位“经典”台阁体作家。四库馆臣对台阁文人与明代台阁体之关系的判断比比皆是,此处不再一一举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明代文人与台阁体关系的建构上。除了四库馆臣看重的“三杨”以外,涉及的文人主要有刘崧、吴伯宗、袁华、陈谟、梁兰、金幼孜、周叙等人。不妨将四库馆臣对这些文人的评价摘录于下。
(刘崧)大抵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然崧诗平正典雅,实不失为正声。固不能以末流放失,并咎创始之人矣。
今观其(袁华)诗,大都典雅有法,一扫元季纤秾之习,而开明初舂容之派。
(陈谟)至于文体简洁,诗格舂容,则东里渊源实出于是。其在明初,固沨沨乎雅音也。
(梁兰)于杨士奇为姻家,士奇尝从之学诗……而于繁音曼调之中,独翛然存陶、韦之致,抑亦不愧于作者矣。
其(金幼孜)文章边幅稍狭,不及士奇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颇亦肩随。
今观(周叙)所作,虽有舂容宏敞之气,而不免失之肤廓。盖台阁一派,至是渐成矣。
四库馆臣通过对这些明代文人与台阁体之关系的界定,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明代台阁体发展脉络,但详加审视便可发现,这些判断仍具有很大的言说空间。从整体上来说,四库馆臣的这些判断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历史材料作为支撑的相对客观的判断;第二类则是缺乏史料支撑的模糊性言说。视陈谟、梁兰为杨士奇的学诗“渊源”,这些判断属于第一类,有相当的史料作为支撑。前者曾教授杨士奇,后者于诗文方面亦对东里有颇多教诲。因此,肯定陈谟、梁兰对杨士奇的影响,甚至对整个明代台阁体的影响皆言之成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类判断,这些判断既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其内涵亦具有模糊性与多义性。不妨举例视之。四库馆臣称袁华开启明初“舂容之派”,其依据是袁诗“典雅有法”,不具元季“纤秾”之弊。这一简洁的判断,实已隐含诸多问题。“舂容之派”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它和四库馆臣笔下的“台阁体”是什么关系?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舂容之派”指的应为明代的台阁体,它是四库馆臣对台阁体的另外一种表述。由此来看,四库馆臣认为袁华开启明初“舂容之派”的判断,本意并非像判断陈谟与梁兰对杨士奇的影响那样,做一严密的学术判断,而是强调袁华在元明之际,其诗文既无前朝旧弊又具新朝风气的风格特征。但无论如何,“开明初舂容之派”的评价的确存在夸大袁华文学地位与影响的嫌疑。同样的还有四库馆臣对周叙与明台阁体关系的判断,称“盖台阁一派至是渐成”,大有将周叙视为明代台阁派形成的标志性人物的意味。实则不然。四库馆臣主要强调的是,周叙的诗文创作既有台阁体前期舂容典雅的优长,又具台阁后期冗沓肤廓的弊病,“恰好”完整地体现了明代台阁体的风格特征,故言“台阁一派至是渐成”。回到四库馆臣对吴伯宗的判断上来。他们视吴伯宗明一代台阁之体之滥觞与萌芽的判断,同于其对袁华、周叙的判断,并非具有详实的史料加以支撑的学理性判断,而只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对文学表象的归纳总结。
以吴伯宗为明代台阁之体的滥觞,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明代台阁体的历时性发展过程。要言之,明代台阁体绝非是随着明代的建立而新产生的一种独具明代特色的文学现象,而是历经了元季与明初的转换。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台阁体所代表的政治文学,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便一直存在,区别在于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明代台阁体绝非生成于明代政治与文化土壤的“特产”。这种以断代史为基础所构建的文学史,忽视了元明易代之际诸多历史要素的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台阁体生成的历史性。明代台阁体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文化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与范畴。就明代台阁体做断代史研究,固然有其理论建构的明晰性和系统性等优点,但缺点则在于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如果不关注明初科举与元代科举之关系,不关注吴伯宗易代之际文人的身份,而只将其作为明代新朝文人的代表,并以之为节点建构明代台阁体的学术史,这样的学术结论看似系统周密,但最大的问题是失之于简单与机械。而如果将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在断代史的基础上,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非止四库馆臣所谓吴伯宗为明台阁体之滥觞这一判断值得商榷,关乎明代台阁体的很多问题尚需继续言说。但同时亦应看到,在易代之际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文献的缺失。就本文所涉研究对象吴伯宗来看,除《荣进集》之外,其《玉堂集》《成均集》《使交集》等诗文集全部散佚,这便严重影响我们对其诗文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尤其缺乏对其元季三十四年间的诗文创作的考察。如果这些文献能够再现,或有助于我们从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把握吴氏与明代台阁体的合与离。但即便如此,通过对四库馆臣视吴伯宗为明代台阁体滥觞这一观点的反思,仍可得出独具价值的学术结论。其中,最大的价值便在于对研究范式的省察——在现有的断代史考察的基础上,继续在易代之际的研究视野加以考察,或能更加全面细致地把握明代台阁体的真实状况与历史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