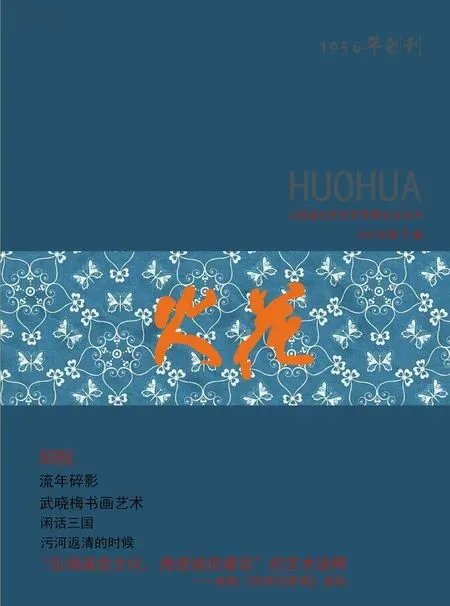流年碎影
谢飞鹏
屋场、村庄、铺里,还有我那儿时的小伙伴……流年似水,逝者如斯。回首往事,那些日渐遥远的记忆碎片,犹如一组组电影镜头,由远而近,渐渐清晰起来……
屋场
我住的地方珠子笼,那里只有我们一家人,珠子笼也就成了我家的代称。我到村里玩,经常不记得回家,要吃饭了,母亲便在屋角头扯着嗓子呼喊我。边上的大人听了,这样提醒我:“双,珠子笼在叫你吃饭哩……”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叫珠子笼。我家后面是大山,前面是开阔的田垅,中间有个圆圆的小土墩,像是一颗珠子。两道低矮平缓的山丘一左一右逶迤而来,好像把那个小土墩都关在笼子之中,这应该就是珠子笼得名的由来吧。
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母亲却总是说,我们珠子笼是个好屋场。她是这样解释的:当年做屋打地基时,挖到了旗杆石。她特别强调,从前只有出了举人或进士,大门口才能竖大旗的。这样说来,我们珠子笼确实是个好屋场。
虽然母亲总说珠子笼是个好屋场,但那时我家却很穷,和我想象中好屋场该有的光景有着很大差距。我们每餐吃的都是薯丝饭,揭开炉罐盖子,上面尽是薯丝。每次吃饭,母亲都用饭勺把薯丝扒开,尽量从里面挑白米多的饭盛给我。
因为生活很苦,父亲和母亲非常勤快,他们忘我地劳作,希望把日子过好点。而对我来说,除了玩之外,几乎就没有其它的事了。不过有时母亲也差我做点小事。我在坪里打陀螺,鞭子“叭叭”地抽着,陀螺“呼呼”地转着。“双,去拔两茎大蒜来。”忙着炒菜的母亲叫我。我正玩得起劲呢,听到母亲呼叫后不敢怠慢,赶忙向屋背头的菜园跑去。大蒜、韭菜和葱杂种在一起,我找到那块地畲,挑上几茎硕壮的大蒜,抠着根须拔起来,然后飞快地跑到屋西头的水潭边上,洗干净后送到厨房的灶台上。灶膛里不时冒出青烟,母亲眯着眼睛一边切菜,一边用锅铲翻动锅里。我正要接着去打陀螺,母亲又说:“菜炒好了,去叫你爸来吃饭。”父亲去犁田了,我又赶紧跑到坪外沿,双手拢在嘴上对着前面的田垅大喊:“爸——吃饭喽——”父亲正呼斥着牛:“转——角——”于是我放大声音再呼:“爸——爸——吃饭啦——”父亲提着犁从田角转过来了,他瓮着声音应道:“听到了,犁完这圈就来。”
父亲母亲的辛勤劳作,也只是让我们免受饥寒而已。稍大些后,当母亲经常说起我们珠子笼是一个好屋场时,有一次我忍不住说:“伊(我们对母亲的称呼),我家这么穷,这里还算好屋场呀?”母亲却说:“当初做这房子时,位置往里偏了点,这样发起来就慢了。风水先生说过,到了你手上我家会发达的。”说罢母亲摸着我的头又说:“蠢崽,我们现在算是好的,你不知道,当初和你爷爷分家时,日子有多么苦。我和你爸只分到一只破炉罐,两只半碗(其中一只破的),三升半米。”
如此说来,现在我家日子确实算好的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爷爷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当初为什么这么抠门?母亲告诉我,其实爷爷那时也穷呀。爷爷有四兄弟,只有爷爷娶到了老婆。爷爷能娶到老婆纯属运气好。我的奶奶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儿,因为不愿给一个做官的当小妾,她父亲一气之下,就将她撂给了当时他家的长工——我的爷爷。为此,我的奶奶一直非常忧郁。爷爷虽然穷,但脾气却很坏,经常打老婆。生下父亲三个月后,奶奶就服毒身亡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她的坟,就在我家珠子笼的后山。她特意嘱咐我:“你要记得,这是你爸的娘的坟。她是个苦命的女人,以后我们老了,每年都要来给她上坟。”这话我牢牢记在心中。
爷爷脾气很坏,对我却很好。母亲说,要是她去菜园里做事,听到我在摇篮里哭,爷爷就赶紧过来摇我。他一边摇一边说:“这孩子长得大气,睡觉都撒手撒脚的。看他的骨架,不到十六岁就是个梢长大汉了。”
爷爷过世时我还不到两岁,对他没有一点印象。我所记得的除了母亲说的那句话外,就是在父亲母亲的辛勤劳作下,日子终于好些了,当然也只是煮饭不用再拌薯丝,有了纯纯的白米饭吃而已。
母亲经常说,屋场到我手里会发达起来的,使我对未来不由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多年以后,我长大成家了,可是并没有发达。母亲还是这样说,我们珠子笼是个好屋场,到了我手上是会发达的。有一次妻子也忍不住了:“伊,现在我们都当家了,也没怎么发达呀?”
母亲说:“你们还不算发达呀?你老公考上了师范,是村里第一个吃到公家饭的。你也教书有工作,村里都羡慕我们家呢!”
哦,在母亲看来,这就是发达呀!
母亲见我们有些不在乎,便指着房屋四周给我们解释:后面高高的大山是来龙,前面远远的山尖是案山,左面那道延绵的小山丘是青龙,右边的则是白虎。屋背来龙高,前面案山远,还有青龙白虎护卫,这样的屋场还不好吗?你们后头的日子会更加发达的……
母亲说得有板有眼,好像看到了我们日后的飞黄腾达似的。虽然我对风水不懂,但觉得能在这样好的地方安居,确实不错。以后只要看到那些傍山而建的农家小屋,我就会想到,有那么一座大山,下面有个好屋场,那里有我的家——珠子笼……
村庄
我们的村庄叫胡家塅。据老人讲,从前这里住的都是胡姓人,村庄边上很多坟茔墓碑上刻的就是胡姓名字。不知是搬走了还是其它原因,现在一家姓胡的都没有了,住的都是杂七杂八的姓。
因为住的杂姓,村庄似乎没有什么凝聚力。用村里人的话说:我们胡家塅是呼拢的班子,都是“黄牛角(方言音gè),水牛角,各顾各”。因而虽然村庄不大,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百余口人,但经常有人会因一点小事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吵得很厉害。特别是那些妇女,吵嘴时叉着腰、挺起肚,站在不近不远的两对门,呼爷骂娘,发誓赌咒,互不相让,直吵得天昏地黑,吓得狗都不敢乱叫,那些鸡鸭更是逃得远远的,整个村子只有她们吵嘴的声音。不过毕竟同在一个村,低头不见抬头见,过几天也就好了。要是哪家老人病了,照样会提点东西去看;要是哪家做红白喜事,照样会请他帮忙。要不村里人会说闲话,说他不懂礼数。
其实,胡家塅是我们村庄的大地名,村里还有很多小地名,比如我住的地方叫珠子笼,过去一点叫岗上,从岗上下一道小坡,再经过一段田垅,就是胡家塅了。因为村里大部分人都集中在那里,所以胡家塅成了我们村庄的名字,我们简称为塅里。就是塅里,也分许多小地名,可以说一家就有一个小地名。比如,住在磡上的叫上屋,住在磡下的叫下屋;房子很老的叫老屋里,房子建的年头不多的叫新屋里;靠近水井的叫井头,住在山弯的叫弯里……一个一个地名很有意思。
这些地名当中,我们最喜欢的是村庄正前方的槠树下。那里长着一棵大槠树,巨大的躯干三四个大男人都合抱不过来,像是村庄的守护神。槠树那么大,不知有了几百年。村里老人讲:小时候看到槠树就是这样的,如今他们都老了,槠树还是这个样子。槠树长得很特别,躯干横斜的,中间横长着一支大树桠。孩子们喜欢爬到上面玩耍,可以这样说,村里孩子没有一个不是在上面爬大的。劳作之余,大人喜欢到槠树下坐坐,东家长,西家短,谈论着生活中的琐碎。谈着谈着,槠树下人越来越多,嬉笑喧闹声充盈在整个村庄。村里人就是这样过了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
在大槠树周围,分布着许多农田,它们也有名字。面积很大的叫大口,面积很小的叫细口;形状长的叫长坵,形状圆的叫圆坵;用来过水的叫过水田,用来育秧的叫秧田……除了农田,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小菜园,分布屋前或屋后。和农田不同,菜园都用主人的名字来称呼,说是某某家的菜园。
八十年代初,村里开始分田到户,实行承包责任制,每人都有户口田。因为种的是稻谷,我们叫谷田。我们衡量谷田不用亩,而是用担。这块田可以割到多少担稻谷,就叫几担谷田,听上去亲切。每个户口大概分到八担谷田。村里好的谷田都集中在塅里,我家在塅里也有一块。那是一块大谷田,可以割八担谷,我们叫它大口,刚好一个户口的田。
田地的名字很少变动,变动的是它们的主人。近些年来,村里的年轻人不断到外面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孩子。村里忽然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嬉笑,甚至妇女吵架的声音都很少听到,让人感到有些不习惯。有人打工挣了钱后便在城里买房,把乡下的房子卖掉,干脆到城里安家了。连同房子一同卖掉的,还有他的户口田和菜园地。
他们虽然卖了房子和田地,但卖得并不彻底。他们卖的往往只是大人的户口田,孩子的户口田是不卖的。菜园也只是暂且借给新来的人种,还归自己所有。尽管他自己没有了户口田,但户口还在村里,还是村里的人。那些田还是叫那些名字,就是连卖掉的菜园,我们还是习惯称作某某的菜园,而不是用新主人的名字称呼。这样,即使他们走了,还和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村里的红白喜事,他们一样到场。他们做红白喜事,一样会请村里的人。
不过,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就是像我这样考出去的人。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师范,由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要退出户口田。那个大口刚刚八担,父亲很不舍得地拿出去了。
让我感到感动的是,虽然我的户口不在村里了,但大家一样把我当村里人,不管谁家做红白喜事,都会请我。回到家里,每次经过那个大口,村里人见了便说:“回来啦!喏,这个大口原来是你的户口田呢!”真没想到,我的户口虽然不在村里,但那块大口却像一根无形的纽带,始终把我和这个村庄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是那些随着他们父母到城里安家的孩子,虽然他们的户口还在村里,虽然他们还有户口田,但是若干年后他们还会回来吗?他们还记得那些田地的名字吗?
时光在悄悄流逝,村里人走的走、来的来,生的生、老的老,回到村里,经常发现一些陌生的面孔。只有那棵大槠树依然撑着它横斜的身躯,默默守护着村庄。看到它周围那些名字依旧的田地,想起村里过去的那些琐屑,在恍如隔世中感受那份日益模糊的亲切,心底不由默然一声叹息……
伙伴
我们的村庄不是很大,人家不是太多,但玩的小伙伴倒是不少。小伙伴们的名字大都是随意取的,男孩便叫什么狗,春天生的叫春狗,秋天生的叫秋狗,家里太穷的甚至叫贱狗。女孩就叫什么姑娌,大女儿是大姑娌,二女儿是二姑娌,小女儿是细姑娌。姑娌多了分不清,住在上屋的叫上屋细姑娌,住在下屋的叫下屋细姑娌。也有些另类的名字,有一个出生时很细小,叫虾人。隔壁女孩生出来时也很细小,便叫虾婆。当然也有个别好听一点的名字,如劲松、华生、朝阳、润阳或是什么花的,那他父母肯定多少读了点书。我的名字叫双喜,算是这类。
伙伴多了便好玩,玩得最多的是捉迷藏。这么多伙伴,谁来寻人呢?用点指头来决定。大家蹲下,把无名指伸出来放到一处,由一个人依次点着。他口中念道:“点指点指,乌云茂密;新官上位,老官请出。”出字落在谁手上,谁就去藏好。点到剩下最后一个,便由他去寻人。寻人是很难,有的藏得紧,半天都寻不到。大家都愿意藏,而不愿寻。我有点小心眼,口诀十六字,知道如何不让开最后一个字落在我的无名指上,因此很少点到我寻人。大家为此感到有些诧异,直到现在,这个秘诀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还玩一种剥蛋壳的游戏。捉迷藏是寻人,剥蛋壳则是找物。大家先把一个人的眼睛蒙上,将一个东西(例如小石头)随意藏在一个人的手心。大家都把手掌握紧,蒙着眼睛的小伙伴把手巾解开,依次掰开大家的手掌来找。大家一边唱着:
种莲子,开莲花,种到谁人手里佳不佳。
家家种大蒜,大蒜接木耳。
木耳九月九,拧紧拳头张开手。
黄牛角,水牛角,放牛崽娌出来剥蛋壳。
这个游戏不太好玩,但那首童谣却非常美,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那些伙伴当中,和我玩得最好的是虾人。他兄弟多,家里很穷,五六岁便开始放牛。我家条件相对好一些,不用干什么活,便经常跟他去放牛。
放牛很轻快,牛吃饱了便把它赶到栏里。这时我们没有什么事了,便到牛栏边上的地里偷蔗秆吃。我们个子很小,匍匐着身子,从菜畦中间爬过去。挑一个粗壮的蔗秆,齐兜掰下。没有刀,张开牙齿用力去咬。腮帮上甚至嘴巴里都是土,吐掉后接着再咬,我们年纪很小,牙齿却十分厉害。刀柄那么粗的蔗秆蔸,几口便咬断了。把蔗秆拖到牛栏后面,叶子给牛吃,我们吃茎干。
伙伴之间大多时候都玩得很融洽,但也会闹别扭。为了一点很小的事情,甚至打起架来,做爷娘的自然心疼。特别是做娘的,本来是小孩子闹,弄不好变成了两家大人吵,并且吵得很凶。不过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两家大人吵得正起劲,孩子们早玩到一起去了。大人看后哑然失笑,也就不再吵了。
这些伙伴当中,有一个很特殊,便是和我青梅竹马的毛姑娌。我们两家隔得不远,经常在一起玩。那时我们只有三四岁,她母亲问我:“双喜,把毛姑娌给你做老婆怎样?”我高兴地说:“好呀!好呀!”她母亲又说:“你拿什么作聘礼哟?”我不知聘礼是什么,便傻乎乎地说:“我家养了条大白猪,用它来兑吧。”这在村里成了笑谈,一见到我们俩便说:用大白猪把毛姑娌兑给做老婆吧。开始我很乐意,长大后知道这是羞人的,再也不说了。不过毛姑娌待我还是不同,我们去打猪草,男孩手脚慢,她经常偷偷帮我。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她虽然没有成为我的媳妇,却认了我母亲作干娘,成了我的干妹子。
我们渐渐长大,男女之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大家知道了男女有别,并且相互取笑。比如虾人和虾婆,他们出生时都很细小,因为从小给家里干活,十三四岁便长得如大人一般。我们便说他们是一对,还编出了歌谣来唱:“虾人虾婆两公婆,提起铜鼓打破锣……”羞得他们脸红红的。不过,他们也没有成为两公婆,虾人家里条件不好,到别村招亲了,虾婆则嫁到了很远的地方。
虽然如此,我们男孩子还傻乎乎的,但女孩子们早已春心暗动。这时,村里发生了一起悲剧,下屋细姑娌突然吃农药死了。原因很简单,她和几个同伴去山上打了些尖栗,被她老弟偷吃了。她和老弟吵了几句,便去吃了农药。下屋细姑娌经常和老弟争吵,没想到这次竟然吃农药了。我们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但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解释。有的说她在山上遭了邪气,有的说她家那屋场不好。多年后我听人说,当时外面的混混经常到我们村玩,他们开放大胆,穿着时髦,村里女孩没见过什么世面,很容易被俘虏。下屋细姑娌便和其中一个好上了,但不敢和家里人说,她的死极有可能和那有关。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亲眼目睹一个共同成长的生命凋零后,生活中便多了一份沉重,我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天真无邪。
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不知不觉我们长大成人了,男的结婚生子,女的嫁到别村,大都重复着父辈们的生活。也有不同的,比如我考上师范走出了农村。还有一个也出去了,就是上屋细姑娌。小时候大家一起玩耍,一起打猪草,偶尔也吵吵,没觉得她有什么不同。后来她父亲做生意发了大财,她也跟着父亲到县城做起生意来。不过,她看到大家依然一样亲切。
虽然我考上师范成了老师,回到村里大家还是直呼我的乳名,我也一样呼着他们的乳名。有一次参加朋友宴请,竟然和上屋细姑娌碰到一起了。她大大咧咧地叫了一声:“双喜,是你呀?好多年没见了。”我也大咧咧地说:“是呀,上屋细姑娌,好多年没看过你了。”这时,边上有人特意纠正我:“哎!这是我们公司叶总。”
铺里
那时,村里只有一家国营商店,设在大队部边上。我们习惯把商店叫做店铺,因此称那里为铺里。
铺里是我童年到过的最大地方。说最大,其实也不怎么大,就是大队部周围聚居着二三十户人家而已。一条铺着乱石的便道从中穿过,旁边有商店、药铺。虽然不过百十来米长,那里的人却把它叫做街。现在看来,叫街确实有些勉强。但在童年的我的眼中,那里不但很大,而且很不简单。
第一个让我感到不简单的是那家商店。因为是我们整个村子唯一的店铺,自然显得特别不同。我很少有零花钱,每次经过商店时,总是忍不住看看里面。我人还没有柜台高,柜台前面搁着一块踏板,我便站在上面,努力把头伸出来。里面有糖果、麻饼,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呀!卖货的人很神气,见我伸出头在看,冷硬地呵斥:不买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于是,我赶紧从踏板下来,向学校走去。我想,当卖货的人真好,商店那么多东西,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怪不得他那么神气了。
另一个让我感到不简单的是药铺。药铺和商店隔得不远,主人养了条咬人的狗,去上学时,我最怕经过那里。不过我觉得,很多人不仅仅是怕狗,更多的是对药铺主人的敬畏,因为他是大队支书的女婿。在我们眼中,支书是当地最大的官,看上去很威严,他的女婿自然应该敬畏,由此延伸到了狗身上。不过,我是真的怕狗。到了那里先远远看好,狗不在门口我才过去。要是在的话,我就停下,等着熟人给我赶狗。有时看见狗不在门口,等你过去时,它冷不丁窜出来,吓你半死。不过还好的是,只要你站着不动,它在你身上嗅几下便走开了,不会咬人。还有,凡是给过它饭吃的人,不管过了多久,都不咬他。我觉得那狗挺讲义气的,总想弄点饭给它吃,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不过,我也从未被它咬过。
真正让我感到不简单的是大队的礼堂。礼堂在商店和药铺中间,大队部就设在里面,可以说是全村的中心。礼堂的大厅很大,可容纳几百人,是全村开大会的地方。里面设有主席台,威严的支书就是端坐在上面讲话的,当然最不简单了。
不过礼堂更多的是用来放电影,因而我很喜欢它。放映机也是支书的女婿买的,去看电影要买票。小孩没钱,于是我们便想着逃票。主席台下面是空的,我们早早地藏到里面,电影放映以后再出来。开始这招挺灵,被发现后,每次放电影前,支书的女婿都要把我们从里面清出来。这样不成,我们便另想办法。买了票的大人可以带一个孩子进去,我们便在门外守着,看到认识的大人,便叫他带我进去。万一没有熟人,看到大人没带孩子,便大摇大摆跟在后面,居然多次成功混进去了。
电影好看,但也经常出事。我们村放电影,周边几个村的人也赶来看。虽然是邻村,但有时好像国与国之间那样,一不小心便弄得紧张兮兮的。特别那些小青年,为了争座位,或是争某一个姑娘,经常大打出手。铺里有个叫老黑的,据说练过醉八仙,特别能打。老黑很仗义,只要是跟我们村里人打架,他都会出手相助。而只要他出手了,打架总是赢得多。有一次打架不知因何而起,但对喜欢打架的人来说,那不重要。用他们的话说“不怕打不赢,就怕打不成”,打不赢下次接着来。当时我在边上,对方有个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铁锹,朝老黑当胸铲去,我顿时吓傻了。好家伙,老黑一脚踢开,铁锹铲在他的脚板上,崭新的解放鞋底断作两截。好在没有伤到他的脚。对方吓得一愣,老黑抢过铁锹,那边人吓得一哄而散。我不由觉得,原来老黑也是不简单的哪!看到他那么厉害,我竟然产生了去学功夫的念头。
进入中学后,回家还要经过铺里。时光在悄悄流逝,铺里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当了很多年的支书,终于退下去了。药铺自然换了主人,支书的女婿也不放电影了。商店也换了人。原来那位卖货的人进了牢房,据说是盘点对不上账。我这才知道,商店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拿的。最让我想不到的,为了防身,家里真的送我学了点功夫,老黑竟然成了我的好朋友。
再后来,大队变成了行政村,由于礼堂日渐破旧,在另一地方新建了村部。新村部比原来的礼堂气派多了,那里自然成了全村的中心,药铺、商店都移到它边上了,不过都是私人承包的。虽然大队成了行政村,但支书还叫支书。支书换了好几任,但不论是谁,和原来的支书差不多,看上去都很威严,可能到镇上见了点世面吧。我觉得铺里不但不怎么大,那些原来在我眼中很不简单的东西、人物,也渐渐变得寻常起来,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支书。
没有了商店、药铺和礼堂,铺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但我们依然把那里称为铺里。如今,走过那条铺着乱石的街道,我便想起铺里当年的点点滴滴,特别是那条狗。其实,那条狗虽然可怕,但直到老死,从未咬过一个人。现在想来,倒觉得它有几分亲切。
许多年后,我离开农村进了城。每次回家,经过铺里,来到村庄,再走几步,眼前便是我的屋场珠子笼。此时,我的目光会不停逡巡,看看哪些地方还留有我童年的痕迹。地方还是这些地方,地名还是这些地名,但多了很多新房子。还有就是,当年的那些小伙伴,都已在流年里浸饱了岁月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