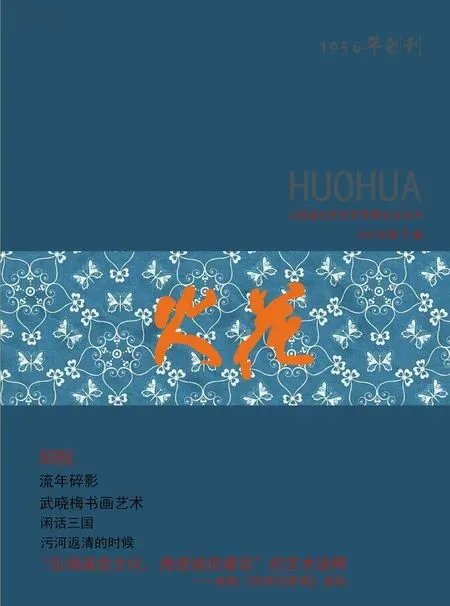奶奶
苏斌
时间恰似溪水般向前轻柔流淌,越来越接近我心中的一个特殊日子。我没露声色,一个行动在心底酝酿几个月,大家也毫不察觉。到这一天,我突然通知爸妈,和我一道去发起一场发自心底深处的纪念。
埋藏心中永不泯灭的深深怀念
小时候,住在平房的我,充分享受着四季分明的季节特点。
夏天的午后,门前大家自砌的砖台上,各种盆栽——无花果、串串红、仙人掌,林林总总,仿佛花展一般,盆里的土被无奈地晒得干裂,只有君子兰,这类“名贵”植物,才被端进家里;后排梧桐树上的知了懒懒地叫着;铜钱空悬,竹帘垂下,除了上班在外的,排房里住着的老人和孩子们摇着扇子渐已睡着。忽然一阵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顷刻打破了安逸。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慌忙中,把挂在门前铁丝上洗过晾晒的衣服迅速收起。雨点打在瓦房顶上,顺着房檐滴落的水珠,或被我看作潺潺瀑布,或让我联想成断线的珍珠。即便是打在石棉瓦上,滴到搪瓷脸盆里,流入水桶中,各路水流声,也都是那么欢快。人们刻意利用大自然赏赐的这“无根之水”,或浇花或清洗污水桶。生活是何等惬意和幸福。
秋天放学后,凉风瑟瑟,月圆风高。坪西小学对面蔬菜站的磅房周围,拖拉机和马车混杂排列的长长队伍,川流不息。丰收的农民拉着一车车西红柿、黄瓜等着过磅称重。偶有个别同学放下手中正在拍的烟盒,尾随在拖拉机后面,有人揪萝卜,有人“拿”西红柿,尽显各路人马身手“敏捷”。眼疾手快的,拿上一个就撒丫子一溜烟儿跑掉了,也有同学被扭送老师或家长。我作为一个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的后代,不敢做“短跑飞人”,也没有尝鲜的想法。秋天到了,我更喜欢捡来变得有韧性且坚实的杨树叶叶柄和同学一拼。
冬天的早晨,上学以前,常常顺道进了厨房,揭开水缸上面沉重的木头盖子,拿起挂在瓮子壁上的大铜瓢轻轻铲起水缸上部结成的一层薄冰,勇敢地咬食着这大自然赐予的魔术般的“产品”。厨房里,冬天堆得比较满,储存的大白菜、土豆和大葱往往占据了这里很多空间。上学路上,千里冰封,亦有别致风景!各家门前污水桶已经冻成了冰坨,下水篦子慢慢被积雪和脏水共同封冻,有人不时拿火柱捣开那凝固的浑浊结晶体,继而又被冻结。瞧,这不太勤快的人家的烟筒头上冰溜子又是老长!滴到地上夹杂着焦油和水的褐色冰凌,像一个装饰用的假山一样,不时还被我们搬走,做一个琥珀对待。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过了年,就是春天了。
春天,在众人期盼中到来!对我们小孩儿来说,不仅仅是对穿新衣、吃好吃的、压岁钱不断袭来的春节的遥远期盼,而且衣物逐渐变薄,活动变得轻快,最有盼头的是这个季节意味着我们又可以更多地户外活动了。气温回升,杨絮挂枝头,槐花分外香。大家又开始分头组织起捉迷藏、跳皮筋、丢沙包,“团队”之间相互交错,玩累了,新鲜感降低了,大家还进行互访,开始进入另一个组织活动。每天下午放学后,家属院里面顿时“活”了起来,小朋友们叽叽喳喳,显得生机盎然,给白天较为安静的院落带来活力。依我看,这温度并不是季节变化,或日照点北移后催暖的,而是我们这群欢呼雀跃的小不点儿们呼唤回来的。
十岁的我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该有的欣喜被一种自发的、隐隐的、挥不去的伤感所压制。我并没有小伙伴那种爬墙、爬树的本领,但还是设法摘了一捧捧槐花,我挑出那些圆嫩的、还没有绽放的槐花骨朵儿,找来了针线,一朵、两朵、三朵……不歇气地把七十二朵白花串起来,做成一个小的花环。我把花环围绕在奶奶的一张大约两三寸黑白免冠照的周围,摆在正屋对面的厨房窗户边上。窗户下,是一个不到两尺高、用砖砌成、抹了水泥的窄窄台子,那正是奶奶喜欢拄着拐棍坐的地方。如今,奶奶的照片上还是那温热慈祥的面庞,然而,她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虽然年龄小,我已经懂得了亲人离去的悲痛;虽然没有任何人会刻意观察一个十岁孩子的喜怒哀乐,但我极力控制住心中的伤感,用那每一个花朵代表她走过的人生的每个春秋。
印象
奶奶,生于1913年,属牛,离开我们的时间是1984年4月14日。
奶奶的一生,多数时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她心地善良,和蔼慈祥,是街邻们公认的好人。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再提起我的奶奶,大家仍是唏嘘不已,怀念至今。
伴随我出生和成长,奶奶退休了,似乎该顺理成章安享晚年。但就在我八岁时,她因病住院,来年春天,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奶奶一辈子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到老来,她一身疾病。
奶奶一生拍过的照片也只有那么两三张。现在想起奶奶,除了照片上的样子,印象深刻的还是她中等身高、身材偏瘦,常常在排房间的小路上拄着她那支唯一简单的“丁”字型黑漆拐棍。她走路时并不快,驻足时,身体略向前倾,右手拄着拐棍,左手轻轻扶在右手手背上。她总是和蔼可亲地和人交谈,诉说着过去,期盼着儿孙美好的未来,但她从不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别人。走累了,她就在自家砌起的砖台上坐一会儿。在她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对于痛苦的过去,她并不多说。
每次看到奶奶的照片,我都会陷入痛苦的追思当中。奶奶五官清秀,皮肤白皙,晚年的她,额头上有了几道比较明显的皱纹,花白偏黑的头发,发型是当时传统的老年人的剪发头。她眼睛细长,鼻子和嘴都比较秀气,给人的印象首先就是“慈祥”。可是奶奶慈祥面庞的背后,埋藏着多少曾经的痛苦,谁也难以说清楚。
悲苦的前半生
老人们回忆说,奶奶十岁出头,便失去了父母双亲。之后,她在出嫁前几乎就跟着逝去丈夫的婶婶艰难度日。奶奶后来嫁给了她的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里的“丈夫”,并不是我的爷爷。一切都平静地发生在河南老家。也许奶奶认为正常生活就会这么开始,会在男耕女织中平静度过。然而,大旱和蝗虫的光顾后,重新开启的是这么一家三口的漫漫逃荒路。
我奶奶当时和丈夫,带着孩子,面对严酷现实,为了生存下去,向着希望,从河南一路逃荒过来。他们经晋南进入山西,和河南老乡结伴讨饭,过着游走、乞讨的生活。据说,逃荒路上,走到一个山洞,按照丈夫的“兴许恁俩还能活下去”的想法,把剩下的东西给了我奶奶和他们当时大概十岁大的女儿,把生的机会给了他认为世上最亲的两个人,丈夫竟然活活饿死了。我问过很多人,人要饿死是一种什么状况?现在的人,恐怕对“饿”都没有概念,况且是饿死!
切身设想,在一种穷困极致的状态,拼命找寻食物或者可以果腹的东西,在困难到丧失所有希望之后,很有可能继而再出现一丝生的可能,然后又是无奈,或许与希望的一丝光亮反反复复,但最后一天天没有进食,一阵阵昏昏沉沉,一刻刻昏醒交错,最后,历经几天的煎熬,痛苦地死去。这不是那种果断的,而是极其残忍的折磨!
想到慷慨地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让人怎能不联想我们所熟悉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也曾经怀疑过世上有如此舍生的真爱,谁知道,我的至亲就是从这种凄美故事里走出来的,走出了艰难困苦,逃过了死神魔爪。我奶奶带着女儿,最终游走到太原一带。后经人介绍,带着孩子嫁给了我的爷爷。此前,我爷爷在老家的原配妻子也因嫌弃贫寒,早已跟着别人跑了多年。彼时,爷爷是一个来到异乡短短几年的、一个没有自己孩子的、三十几岁的青年人。
老人们从来不提起这些,他们在那个婚姻观念相对传统守旧的年代,总觉得说起不是原配,会不光彩。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丢人的事,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前半段恰是各自无奈的悲楚“历史”。不愿意说,也可能因为痛苦而不堪回首?
痛!谁愿意没事在伤疤上抹盐?苦,远远还没有结束。
爷爷奶奶后来生过几个孩子,多数夭折了。原因凄惨:有因家里生火煤烟太重呛死的,还有不慎让被子捂住窒息夭折的。并不是命运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人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当时生存环境就是这样。最终,爷爷奶奶的孩子中,只有姑姑和我爸长大成人。
那个我爸都没有见过的、受尽颠沛流离的我的异姓姑姑,在1949年,随着十八岁的到来渐渐长大成人。谁知道她命运中恐怖的阴云也随着那个晚春悄然而来。1949年4月23日,正是在太原市解放的前一天,太原的晋安兵工厂内的一场事故引发了为解放太原而“祭城”的一次巨大爆炸。爆炸中,多人丧生!飞来横祸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苦难的这个姑姑匆匆离开了这个即将“红了天”的世界。我奶奶再不能提起此事,每当她回忆起这次灾难,都会泪流满面。
解放了,天亮了。爷爷奶奶和刚刚两岁的我姑姑从太原带着种种不愿回想的痛楚回到了老家河南。在老家,仍止不住他们心头伤痕隐隐发出的痛。两年后,他们再次回到太原。
生活初好
1953年6月,我爸出生。
1958年,单位的新宿舍交付使用,爷爷奶奶一家四口搬到了排房里。
我曾经见过那张发黄的五十年代的住房证,上面写明了作为单位宿舍配置的家庭的几大件——木床一张、火炉一个、火柱一个、火钩一把、凳子二个。共产党给了一家人希望,给了一家人温暖,新瓦房里,住着历经颠沛流离的一家四口人,生活开始平稳、安定。此时,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四十五岁,姑姑十一岁,我爸五岁。
后来,奶奶的职业从铁道边拾矿渣废铁到在聋哑木器厂分拣木料,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退休。
奶奶因为多年的苦难,身体不好,其中,最直观的就是因为风湿病造成骨头变形。人们都清楚记得,她瘦弱的身躯,为了支撑起这个家,曾经经常扛起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这就是坚强的我的奶奶!
奶奶身体确实不好。的确,她不能照看我,但这不代表她不亲我。老人亲小孩儿,好像天经地义。经历生生死死、坎坎坷坷的多半生,看着儿孙成长,老人内心该是多么高兴!
我是1975年出生的,妹妹比我小两岁。奶奶对我们兄妹都很好。现在记忆里有很多片段,经常还自觉不自觉地记起,有时候就像演电影一样,一件件小事也总让人感觉心头震撼,眼睛发酸。“电影”里总是放映着奶奶挽着印有北京火车站图案的黑色的“高级”人造革提包,拄着那条熟悉的黑漆拐棍慢慢走来,慈祥的老人微笑着说:“给孩子们买了两毛钱的樱桃,吃个稀罕吧。”看着刚刚铺了一层提包底子的樱桃,回想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这已是非常的奢侈。
老人一定都有重男轻女的情结。我至今经常回忆起奶奶带我去我家附近“自由市场”的情景:奶奶拉着我的手,走出副食商场,走到门口高耸的柱子旁,她用手剥去松花蛋上包裹的泥土,磕开蛋皮,让我赶快吃掉她从不舍得吃的松花蛋。是呀,这个贵,她不舍得吃。也没有那么多钱,不能够买给其他人吃。我总是这么被“自然”地带出去,然后似乎毫无异样地被领回家。每想到这些事,我总是想念奶奶,这种感情,现在的人大概不会有,但在我心里,一辈子不会褪去。
悄然离去
1983年,我八岁了。这一年,在我生活里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慈爱的奶奶因为肝腹水住院了,就住在我们街上的这家医院;二是这一年暑假,爸爸出差时,带我去了北京,因为没有拿单位介绍信而没有进到毛主席纪念堂,但我还是幸福地看到了天安门,喝到了“北冰洋”冰镇汽水;三是在邻居的带动下,我开始集邮,这是何等奢侈的事情。
此时的病房里,奶奶很坚强。那时候我还小,并没有感觉奶奶是和“死神”搏斗,与时间赛跑。
家里众多亲戚经常来看奶奶,我只感觉到了奶奶好像是在会客一般,病房里总是奶奶和亲人们娓娓道来,轻松交谈。在和亲戚们的对话中,奶奶似乎感觉到时日不多。那时候我还小,有时候也听到亲戚们劝奶奶不要多想,要安心治病。我也偶尔会动动小脑筋,装模作样地拿起扑克牌给奶奶“算卦”:“开卦了,这个牌的意思就是你能活到100岁。”奶奶笑着看着我,或许她的心里却在哭泣。记忆中,虽然久经病痛,加上有着痛苦的过去,奶奶却从来没有流过泪,也没有因为病痛喊过一声,她绝非一般坚强的人。
生活在一天一天地变好,她并不奢求过上什么衣食无忧的生活,她是多么希望看着我们兄妹长大呀!
还原1984年的生活。现在经常在网上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照片,心中颇有感受,那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也是我从小认识世界的最初期。奶奶却在这个好生活即将到来的起点走了。她没有看上彩色电视机,没有用过电话机,也从来没有见过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更不会知道后来的手机、微波炉……
大家回忆起奶奶,说她爱吃肉饺子和猪蹄。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当时的这种生活,她已经感到非常富庶。在她住院期间,父母尽量给她买一些好吃的,医院对面新开的小卖部里卖着两种稀罕玩意儿——鹌鹑蛋和方便面。奶奶对方便面这种新食品,赞赏有加。她看到,社会开始变得美好了。
就是在那个初春的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妈妈告诉我说奶奶要出院了。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奶奶好了吗?”“奶奶再也不去医院了吗?”我高兴地跟着大人们去了医院。我跟着肃穆的抬着奶奶担架的人群,前呼后拥下,回到了家。
这时候,大人们好像顾不上管我。我照常去上学。不一会儿,有人又把我从学校接了回来。这时候,奶奶已经躺在长凳支起的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张白纸。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作“死”。
奶奶就这么默默地走了。
我并不知道奶奶去世以后,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妈妈让我去找了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向厂里求助一些家里急需的物品。我借用电话的时候,人家问我打电话缘由。我绝不愿意说我奶奶“死”了,我只是低声地说了一声“我奶奶”,然后从裤兜里掏出我的“孝帽”。是呀,不愿意呀,不愿意说奶奶“死”,也不相信她就这么离去。回到家,我看着静静躺在那里的奶奶,偶尔轻轻掀起白纸,再多看奶奶一眼。我不愿走远,在奶奶遗体旁守着,一会儿拨一拨大碗里的油灯的灯头,一会儿点着香插入香炉,深深鞠躬,重重磕头。
一个老人对儿孙的好,一点一滴,慢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地消失在记忆深处,留下的仅仅是众多“仁爱”中的九牛一毛。那些散去的记忆哪里去了?真的随着脑细胞的死亡和新陈代谢消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了吗?不!记忆已经转化成感性的爱的温度,始终成为一辈子的温存,进而又转化成对那些记忆找寻的长路。
六年后,还是一个春天。我们家即将搬入平房旁新建的单元楼房,也即将告别旧排房。这里留下了我许多纯真的记忆。在家里搬空后,我悄悄躲过家人的视线,又回到当年停放奶奶遗体的地方,对着那里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默默地离开。
在我心里,奶奶似乎没有死去,她一直“活着”,只不过好像搬到了另外不为我知的地方。我默默祈祷着,她在那个世界里能够收到我们的祝愿,安享幸福和快乐。
特殊的这一天,我带着爸妈上了山。阳光洒在奶奶坟头,蓝天映衬下,一切都显得格外明媚。坟前,我摆上了她最爱吃的猪蹄,拿来了她从来没有吃过的“高级”水果蛋糕,献上鲜花花篮,挽联由我写下,上联“故人仙逝三十载慈祥和善犹如昨日”,下联“凡人在世百十年感受恩德会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