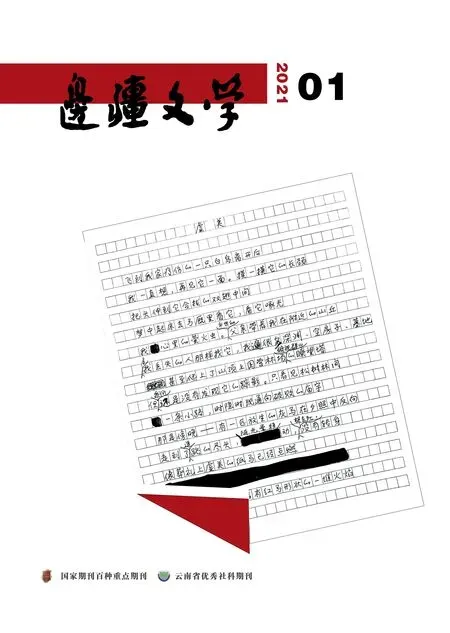驴和狒狒 短篇小说
郑阳
2014 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天气晴朗,我正在刚租下的房间里收拾东西。我在想,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措置那些东西,那些书籍和暂时不会用但肯定用得上的杂物,比如一对哑铃、一副拖把、几只打火机……这仅是其中之一,问题不在它们,问题是它们现在不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它们全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包括我本人。这情形有点像某种囚禁,几十个犯人被关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抑或这本来就是囚禁。
我总奢望有一间比较宽敞的空房,摆放这些东西,以便有地方支画架,却又从不去为这事操心。
我从纸箱里提出一个纸袋,掀开罩在上面挡灰尘的报纸,准备把里面的东西规整到其他地方去。我看见了那个拉链文件袋,我的心一下子就回到了过去。那里面装着几个笔记本、一些早年的素描、一本集邮册。让我回到过去的,不是素描,不是笔记本里的诗歌,不是从少年时就开始收集的邮票,是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封信。似乎过了几百年我都知道那里面夹着一封信,尽管收到时看过一回,之后再没看过。
何泉:
见到这封信,你一定感到突然,但我想,你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关于我们的未来,我觉得,你也知道。我没有理由不考虑现实问题,实在抱歉,只能就这样跟你不告而别,我想,你能懂我的意思。
马小染
2003年7月22日
我知道,从这封信开始,我就不再是她的泉泉了,从这封信开始,我回到我自己,叫何泉。一想起这点,我就会心寒。一种陌生,一种被抛弃的冷落,一股久违的伤感袭上心来。我好像又回到了刚跟她分手的时候。
恋人主动选择离开你,你会觉得费解,你往往会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其实不是。这在不同的时代都发生过,原因大同小异。
记得当时,朋友们都喜欢称我和马小染为“河马”,是一个整体。
不知是哪个混球,曾经把女人归结为感情动物,还引起了普遍的共识。说实话,一个女人在生活中的选择,往往会割舍掉感情。
马小染,当时我还真是不懂你的意思,那时我怒发冲冠,气急败坏。现在才真的懂了。但是爱,没变。
我盯着那些字迹,钢笔写的,她的名字,那个日期,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好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忧伤却仍旧新鲜,像刚出锅的青豆荚,飘着热气。
汪汪来了电话,她的电话阻止了我的忧伤。她约我出去吃饭。我说搬家了。在一年前,她经常这样来约我。有时候还觉得城里乏味,跑到城外去吃。
汪汪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情人,在幼儿园当老师。十年前好朋友带我认识的,那时他们各自都有人了,为了把神秘的约会变得很自然,像一般的朋友相处,就需要一个外人作挡箭牌。我就是那个外人。我们,也就是我们三人,经常在一处吃喝玩乐,轮流做东,但多数是汪汪把一切搞定。她有钱。在他俩那里,我是挡箭牌;在我这里,我只是在跟朋友一起玩。我只是刚刚跟马小染分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在马小染离开后,我发现自己不会再爱上谁了,不会再有女朋友了……所以我无所谓跟他俩混在一起。后来,果然如他们所料的那样,不妙的情况出现了,好朋友的未婚妻突然出现,好朋友跟他的未婚妻介绍说,汪汪是我的情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哈哈……这口黑锅,一直背到现在。虽然后来我跟汪汪时常在一起,但我始终没有跟她从情人的方向发展,我跟她,只是一般交往,吃饭、泡吧、聊天,如此而已。
三年前,我匆匆结婚,两年前,我带着离婚证搬了出来,并不是我心里始终住着马小染,是其他原因。一年前,我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做事情,刚回来没几天,房东说要装修房子,之后肯定就是涨价。我不得不搬家,好在就搬到附近。这个城市拆毁和建设的速度相当,汪汪已经忘记我在那棋格子般的哪条巷子里了,我叫她就地等着,我去找她。
一出门来,我就想起前天见过面的那个女人,是一个月前在网上认得的,还有些耐人寻味,模样也不算差,带着个小孩,有一套需要还贷二十五年的房子。但是她的要求有很多项,比如:有九十平米以上的房,没房的话至少要有车,爱她,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懂幽默,如果买花送她,要买红掌,不要玫瑰,也不要康乃馨,要有时间经常陪她……
我觉得能够商量的,只有抽烟喝酒和赌博。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的要求像是产品配件,那么多的配件,集中起来,就像是在出售一套组合音响。有钱的话,可以买下来,使用其中一部分功能,烦了,就甩到一边不管,或者索性再倒出去。这不是使用的人决定的,是音响本身决定的。如果谁能满足这些要求,那他一定是个功能很正常的白痴。她有要求,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她没问我的要求,那情形,等于告诉我,我就是买家,她就是货,货就是这些,要么买,要么不买。我说考虑考虑,其实是托辞。都已经两天了,现在,好歹得给人家一个答复。
汪汪坐在车里打着电话,那车已不是以前那辆,应该是第四辆了,如果在此前的一年里,她没有换车的话。
你咋又搬家了?她挂了电话,两眼无光地望着我。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是在流浪。
那我这是算哪样?汪汪低头看着方向盘。我也在流浪。
你这不叫流浪。我坐进车里,她看着我,我说,叫流窜。
她呵呵一笑,说,跟你在一起,就是好玩。这是实话,我常会有些类似的话出口,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她又说,真不知该吃点哪样。我说随便。她朝楼天相接处看看,然后说,干脆去吃素菜?
怎么想起吃素食了?
清心寡欲嘛,怎么样?
可以的,但吃了不一定清心寡欲。我说着,拿出烟来点了一支。
她无声地笑笑,把车转出巷子,一边问我的近况。她总这样问我。
老样子。我总这样回答她。
我所谓的老样子,就是包括她通常问的:女朋友呢?(还没有眉目)。不想再结婚了?(也不是,得看情况)。你妈还好吧?(好的)。今年有几岁了?(八十多了)。你这样整天写写画画的,不会寂寞?(基本不会)。你平常去哪里玩?(基本不玩,除了麻将)……她总像审贼一样问我这样那样,我总是如实回答,就像交代罪行一样。
若不是老相熟,我会被这些问题弄得很尴尬,现在我对答如流。什么叫老脸厚皮,这就是。她说,你可真是太素了。
我说我是素面朝天,心怀鬼胎。她哈哈一笑,脸上似乎生动了一些。
我那老朋友,最近给跟你联系了?
没有,她淡淡地说道,不知道他在干啥,好久没联系了。其实我知道,他们已经互相厌倦了,很难再有以前那种情人关系。
转过弯,迎着阳光,她拉下遮阳板,并转转头,看了看自己。
我摸出手机,想回复那个女人。微信上内容丰富,不乏动人之辞,也常有些貌似真理的语录,宣称删除昨天,不想未来,只活在当下。那些佯作洒脱的语词,我有些不屑。所谓“忘掉过去”那种信誓旦旦的论调,是不足采信的,我从来不信,相应地,“活在当下”也是值得商榷的,不可细究。无论我在做何种事情,总会想起马小染,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如风拂过,然后是其他事情,不经意间,又几秒钟,然后再几分钟……她的身影或者话语,在生活事件和意识中穿行,如此伴随我度过一天,一周,一月,一年。年复一年。
素食店在新城区,那是富人区。这种素食店,仅有健康二字还不够,如果不搞得足够体面,那就会让人怀疑进餐的人是吃不起大菜;如果不卖得贵一点,那就会降低进餐者的身份。这家素食店,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所以来者都显得仪态大方,举止矜持,和某些中国人享用西餐相当,基本上不会出现在路边小店进食的贼眉鼠眼之态。我之前来过两次,这次来,忽然想起《大腕》里面那句台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她选择坐到窗户边,盘子里只有一只荞麦馒头、两片儿西瓜。我坐下后,她翘着三个指头捏起一只馒头,很不满意地咬了一口,就开始说她纠结的事情。她说,她介绍一个叫青圆的闺蜜给老冬瓜(老冬瓜的头型像冬瓜,练过西洋拳,人挺粗壮,给一个老板做保镖,我知道的),但老冬瓜后来把青圆甩了,甩了就甩了,可他却……把她扯进去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汪汪说出这句,样子就像挑着一担大粪的农村妇女。
老冬瓜跟汪汪的关系,我认为是暧昧的。我早看出来了。谁叫她那样干呢?现在反倒抱怨对方。我不知说点什么,所以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我从不想陷入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中,就像我跟她,我完全可以把她变成我的情人,但我从没那样去做,即便有好几次在包房里,她半醉着把我的大腿当枕头。
她把我的大腿当枕头,我也没有把手放在她的任何地方,尽管我们之间常会开些黄色玩笑。我肯定不是柳下惠,我还可以肯定的是,我只愿意接受一种相对单纯的关系。我有时候很讨厌她那种生活,但由于她避免让我知道她跟其他男人的暧昧关系,我也就只好装糊涂了。她说了一大通,说曾经她对老冬瓜如何如何好,像倾诉血海深仇一般。最后她问,你平常跟他联系吗?她好像担心老冬瓜会跟我说什么。
我说,没有联系过,好长时间没见了。的确是这样,我跟老冬瓜只不过在K 歌的时候喝过一次啤酒,貌似很要好的朋友,平素其实并无私交。关于她和老冬瓜以及青圆之间的关系,她没具体说,我也没问。我已渐渐失去了追问别人的那份好奇心。
我想她一定伤得不轻。她垮着脸,耷拉着嘴。失意,只能叫失意。
不行,我得再打个电话,问问他安的什么心,至少再嘲他几句。汪汪拉开坤包,掏出电话。在她拨号码的时候,我伸手按住她的手臂。我说,他既然已经做成那样了,还会告诉你安的什么心?嘲他几百句,也不起作用。
汪汪泄气似的垂下手来,接着把电话放入包里。她吃了西瓜,问我,你平常不会孤独吗?
基本不会,我解释说,可能是习惯了吧。在有点艺术追求的人那里,寂寞和孤独,往往是另一种创作的能量。完全感觉不到寂寞和孤独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它。汪汪显然还不会处理。在很多人那里,孤独和寂寞是垃圾,那么,处理它就需要讲究方式了。
我尽量把她的问话,小声地回答过去,但还是引来了左近的人颇有些惊讶的眼光。我不喜欢那种毫无艺术追求的眼光——他们除了惊讶,就是疑惑。艺术跟许多人的生活无关。许多人只跟艺术成品的经济价值有关。
你就只吃那点东西?我问她。我刚吃下两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准备再弄点儿其他的。我起身,有一半原因是想终止跟她继续谈论孤独寂寞这类话题。
我自己来,她说,等我看看,再点几个其他的,说着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菜单。
这是一家将自助和点菜合而为一的素食店,有各式各样看上去像肉食的素食。我觉得自助的部分已经比较丰富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我干涉不了别人的欲求。我想,素食确乎跟清心寡欲有些关系。修佛念佛之人吃素,除了戒之于不杀生,也确实能在戒定的修持上获得一些清心之力;一般人吃素,多是为了所谓的健康,至于能不能清心,并且寡欲,要看吃素之人的心念。日常里要是怀着一颗素心,可就大大地有益身心了,犯不着专程来吃素,不然,就是喝白开水也等于零。素食店环境很好,但跟汪汪没有关系,她吃的时候,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另外带回来一杯豆浆,示意给她,她摇摇头说,她点了几个菜,她把菜单递给我,叫我也点几个。我说够了。
真想像你一样,不上班,自由自在。她竟然羡慕我。
我说,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没钱没车没房,甚至……我冲着她笑笑。她苦笑了一下,叹了一声,慢条斯理地吃着,像大病初愈的人。
我真想辞掉工作。她望着我,疲倦而无奈的样子。实在不想上班了,她说,可是有老公孩子在,这行不通。
那就出去走走。我建议道。她即便辞掉工作,也照样不愁花销,她老公有的是钱。
走走,还不是要回来。
你是想壮士一去不复回啊?我笑道。我知道她是想抛开现有的生活,但这对于她来说,根本不可能。如果她病了的话,这不是病因。
我就是太贪,她自我谴责,站起来,两肘向后拉了拉,下了只有三级台阶的拱台,朝那边去了。一年前,她有一头垂到肩上的卷发,现在剪短了,肯定还染过,边缘部分是黄的,衣着很随便,是那种懈怠慵懒的随便,尽管都是名牌。我一旦跟她在一起,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在一起。当然,这没人知道。我们之间本来毫无故事,因为那口黑锅,竟然经常坐在一起吃饭了。
我就是她的反面,如果她认识到这点,想必不会那么愁眉不展。我估计,她的家庭没有出现严重问题,顶多是被冷淡而已。她老公经常在外弄生意,遭受冷淡是肯定的。
我不知她会弄些什么东西回来。我在猜。
吃素食的人不少,几乎满座。这年头,这是潮流,就像早些年家家户户挤着去抢买肥膘猪肉那样。如今,吃素食好像会让人更健康,似乎因此能更长久地活下去。至于活下去干什么?活那么久又要干什么?可能谁也不愿多去想。我看看周围的人,想起尼采,尼采曾说过:“活得太久,是不体面的。”
怎么突然会想起尼采来?我感到莫名。
我莫名的还有一桩事情。汪汪端着一碗汤回来后,她点的菜也陆续端上来了,它们的名字仍然沿用所模仿的东西,比如“牛排”“狮子头”“鱼香肉丝”“宫保肉丁”……做得确实像肉,吃起来也像。汪汪又问我最近给找着合适的伴儿了?难道真不愿再结了?我索性给她讲了那件莫名的事。
是这样,就在前几天,有个朋友给我物色了一个女朋友,有三十老几,朋友说,已给她看过我的照片,对方基本认可,朋友给我一个号码,叫我加她的微信。你知道现在流行这个,就像早些年家家户户挤着去抢买肥膘猪肉那样。汪汪听我这样比喻,忍不住笑起来。我说,如果再用短信联系,就显得落伍了。微信我已弄了一年多,但加她,得等她认证,这其实是多此一举,一个短信就可以解决了,没必要非要微信,但好像不用微信,人就会掉价,就不会说话了,就显得土了,就……这个你是知道的。汪汪咬着下嘴唇,点了点头。第二天,她通过了认证,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说,就说,听说你是红河州那边的?二十分钟后,她回复了两个字:是的。如果她问我点哪样,我会很好说话,但她没问。乏善可陈了。现在不是三月吗?到处都见得到樱花,有的开得很好,就在道边上,我总是忍不住过去拍几张,我就挑了一张樱花,发过去,但半晌没动静。
我看着汪汪,表示对此感到茫然。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回来这几天,是跟网上认识的女人见面、搬家,交叉进行的。
她至少应该表达一下对那些樱花的看法,好看,还是不好看,如此而已,但她毫无反应,哈哈。我说起来,仍不免有些忿然。
后来呢?汪汪盯着包子,毫无心情地咀嚼着。她总喜欢刨根问底。
后来,也就是第二天,为了不辜负朋友的一番好意,我就在微信上问她:给在上班?你上班忙不忙?有空来玩?她回复说:在,不忙,好的。我说,咋有点像坦白从宽的样子,我又不是看守所的刑警。这句话后面加了个大笑的表情,我想,如果对方有意,这个玩笑和那个表情,应该会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效果,结果不是,没反应了。一下没反应,可以理解成对方忙着,如果一天过后还没反应,那就是真正的反应了。
我望着汪汪,表示说完了。她说,你也真不会说话。
这可能不是说话的问题,我说,这年头……是很实际的,这你是知道的,要有实际的东西握在手上,看得见,摸得着,否则谁有工夫跟你空谈?还一张樱花照呢,一堆樱花也没用。
哈哈,也是,她说,最近画点哪样?
我说,在搬家,收拾东西,没工夫弄油画了,只在手机上写了几句诗,觉得言不由衷,就画了一张速写:一头驴,站在屋顶上,你知道,那种地方,周围都没有草,那头驴茫然地看着前方,前方是鳞次栉比的楼房,灰茫茫的城市。这时我注意到,此前那只馒头,汪汪只吃了一半就扔下了。现在她喝了几口汤,拿起一只小包子咬了一口,眼盯着包子里面的豆沙。
你就是那头驴。汪汪笑起来,拿起餐巾纸,擦擦嘴。
我说,那可不一定。
旁边有人又转过头来看看我们。我没再说话。
窗外边还有一道像阳台样的方寸之地,也坐下了人。再外面,就是马路,马路边有树,皮像白桦树,叶子嫩绿。下午的阳光照在天空上,以及从对面高楼的窗玻璃上反射回来,把叶子映得通透,绿叶中散发着黄晕,像黄金龙。这种嫩绿的叶子,看着就想去吃,如果神思飞扬,就会有种自己是长颈鹿的感觉,但是她没有看。单行道上不时有车过往,如果加点儿想象力,坐在这窗边的人,在被阳光映衬的嫩绿树叶之下,会有一种正坐在开往天空的列车上一般的奇妙感觉。这是很感性的东西,没人会去想,因为它太不实际,虚无缥缈。很多人都热衷于身体的旅游,但却不懂神思的旅行。如果在媒体引导者那里,掺入一点这种看似虚幻的东西,可能他们集中了上流精英的关于幸福的谈话节目会更加有的放矢。
她没看这些,她放下没吃完的包子,拿起另一只包子,咬了一口,看看里面的馅,又放下,端起汤喝了一口,瞅瞅前面、也就是我后面的人,慢条斯理地吃那些像肉的菜,不时眨眨眼,像在寻思什么,然后她说,真不知该去哪里玩?
是的,在这个城市里,她哪里没有玩过?全都被她玩完了。
我说,现在可能老了,不想玩了,被人叫去KTV,跟受罪差不多。
我也不常去了。她说着,又喝了口汤,随手放下,像是丢到一边,然后扫视着大厅里的吃客,两眼茫然。
我看向窗外,道边上,她的车停在那里,很新。是的,她啥也换不了,就只有换车了。
我们回到车里。一般情形是,车主人会放一张CD,但她连这也没做。她嘘了一声,也可以说是叹了口气,然后说,我就是太贪。
你们女人样样都想要,有车有房,不够,要有爱自己的,还不够,要有自己爱的,这也不够,还要在节日有鲜花奉上,这也还不够,要有好吃的好玩的,还要有陪玩的,心情不佳时,要有人哄,啥都有了,某个无聊的时候,还要有几个陪聊的……不求高端大气有品位,也要低调沉稳上档次。当然,这些话我没说。她让我想起狒狒,把爪子伸进树洞抓坚果不肯放手的狒狒。
太贪,没看出来。我故意这样说,以便让她相信,我对她跟老冬瓜的事一无所知。
太不可思议了!汪汪将头仰在靠背上,瞪着前面。嗨!那种人都会有,他跟青圆上过床后,竟然说,是我为了抛开他,才把他介绍给青圆的,你说,给牛逼?
他可能是想甩开青圆,故意在找借口。我帮她分析。
汪汪说,青圆后来原话问她,她感到窒息。那以后,青圆已经好久不联系她了。青圆相当于她的闺蜜,青圆淡出,她的生活里就会出现一块空白。真正让她窒息的,是这块空白。
这就叫故事。我说,人来到这世间,也许就是为了完成一些故事,其实你还不如把老冬瓜留给自己,亲自把他消化掉,省得生出这些事来。
她迟疑了一下,眨眨眼睛,似乎在分析我的话有无弦外之音,接着就笑起来。
这个主意倒不错,早知道给他黄焖掉,省得他这样不识好歹。
呵呵,呵呵。她望着车窗外,接着说,我们去哪里转转吧?
我说,不知道该去哪里。
今天吃素食,要不就再来个素的?
什么?
不去打牌,不去唱歌,去散步?
于是我们就去了广场。我看看微信,考虑说句什么话,回复前天见过面那个女人,还没想好,已经到了广场。我们沿着湖边走。我把手机揣了起来。傍晚散步的人不少。楼房上的霓虹灯、路灯和湖滨路上的行道灯,都亮起来了,点了一个城市的光荣。至于黯淡的那些,谁知道呢。沉默着走了一段路,天色全黑了。
不知道该干点啥,就来散步。她让过一个东张西望的散步者,在我前面说。
我想也是,我打趣道,两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想法。
她仰起头,眨眨眼,建议去喝啤酒,但接着又说,算了算了,一喝就多。从湖对岸照过来的灯光,把她的脸衬得像个煤矿工人。
我说,不如向西北方向走走,到兰溪桥上,去喝西北风。
她呵呵地笑了一下,接了个电话,说了很长一段路,还没说得清楚。
继续走。她在后面打电话,我在前面东张西望,学大鹅走路。一路还有些花香,这些微弱的东西,可以使人愉悦,但这对于陷入尘世纠葛中的人来说,无足轻重。到了更暗的地方。更暗的地方,似有情侣依偎。我跟汪汪最近的时候,也有一米或五十公分的距离。如果有人在黑暗中看见我们的话,这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很多关系,其实只有天,才知道。
她老公是个生意人,阅人无数,我们在一起吃过饭,他一眼就看出我对他老婆没有心思,要不然,我才不会跟她转到这种黑灯瞎火的地方来。
还是不要动真心的好。她挂了电话,在昏暗中说。
那可不好控制。我仰头看着星星,是轩辕十四,在东南边,很亮。
你真的不会感到孤独?她又问道,我咋个总感到寂寞。
也不是……完全不会,我有些不好措辞,还是坚决地说,但孤独算得了什么,比起麻烦来。话音未落,只听一声不知是什么管子发出的声音,从某个黑暗的地方窜出来,不像笛子,是黑管还是箫,搞不清楚,吹得不成调,但感觉得出那个人很有兴致。第一声劲头很足,之后的音节很想弄出点抑扬顿挫,可是,实在是难听。
我跟她说,这个人比我更素。哈哈,她笑着说,走吧。
湖那边的灯光更加灿烂了,和城市里的灯光连成一片,高楼和连片的房屋上,都有霓虹,流光溢彩。我相信这对汪汪没有任何意思,说不定她会因此更烦。我想找句什么话安慰她一下,实在找不出来。
后来我说,今天吃素,有什么感想?我知道她每顿饭都是必吃肉的。其实我也差不多。
她反问,吃素还要什么感想?
那你得想想。
你们搞艺术的,就是喜欢胡思乱想。
我又说,你比他们,比那些吃素食的人要丰富。
为什么?她盯着前方,把车转上了高架桥。为什么?她又问。显然,她不明白我的意思。
他们,连寂寞都不会。
呵呵呵呵。这话让她开心了一下。她瞟了我一眼,将右手甩在方向盘上,伸直了掌着,脸上似有一些释然。我又想起马小染的信,心口一紧。那种只属于个人的忧伤,在狭小的胸口里剧烈地翻腾了一下,足够凄凉。我忽然夸张地大笑了几声,她吃惊地看看我,我说,你就不可以笑笑吗?强烈地欢笑!
哈哈、哈哈……我似乎是在教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她把头俯向方向盘,又仰起来。
这些放肆的笑声,穿过光影交错的车道,尽管很快,我还是看见马路上的一些人,转过头来朝我们看。
强烈地欢笑,这句话好。她带着脸上的笑,看着前方。这天,她终于笑得自然了一点。
到了我的住处外面,我下车后,朝她挥挥手,在车屁股上一拍,像驱一匹马。她一溜烟驱车而去,在我眼中,骤然缩小,变成一条线,一个点,然后消失。
我回到局促的房间里,一派拥塞,周遭的各种物件重新向我逼来,每一样东西都似乎在质问我:
我应该摆在哪里?
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似乎有些愠色,我将它优先考虑,放到电脑后面的书架顶上立着。我考虑着,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措置那些书籍和暂时用不上但肯定用得上的东西。只要能够从哪里挪出一小块空档,我会因之感受欣慰;那些东西可能也会。
我调整了一下,画架暂时是没地方摆了,提起来,插到几箱书和电脑机箱的后面,靠墙立着。我就手拿起铅笔,在那头驴的旁边勾画了一只狒狒。狒狒仰头看着天空。我在上面点了几点,那就是星星,像轩辕十四。
在荒凉的屋顶上,它俩也算是有伴了。
驴看着苍茫的城市,狒狒看着星星,就这样。
然后,我将堆满杂物的桌子靠墙,索性把茶几竖起来,靠到桌子旁边,堵在门口的靠椅终于移了进去,背靠在桌子的抽屉上,对着一台摆在单桶洗衣机上的电脑。
——总算有坐的地方了。我与电脑之间,是几箱书,键盘和鼠标就放在上面。我想,暂时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
我从椅子下面的空当里伸手进去,在椅子后面的书桌下面抓出一瓶啤酒来,咬开盖子,放在地下,开了电脑,同时想起那个女人,遂掏出手机,发现两小时前她已来过短信。她说,她可以放弃一些条件。我回复说,我们三个,可能将会是四个,在一起的话,以后恐怕就只有吃素了,这是现实,你知道的。
其实情况不会这么糟,但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搜出要看的电视剧,正要坐下,她回复过来了,像一直等在边上一样。她说,好吧,我再考虑一下。
我想,她是不会吃素的。
我坐下来,往后一靠,从旁边的空档里跷起二郎腿,舒了口气。汪汪的笑声还在我耳边,包括我自己的——强烈的欢笑。
那是两只动物的笑。我这样想着,慢慢喝了口啤酒,脑海里忽然闪出马小染无比清丽的形象,是那次,初相识的时候,十月的天气,有些微凉,我邀她到酒吧里喝酒,我喝啤酒,她喝爽口山葡萄。橘红色的灯光,落在墙壁上,从左边喷绘的英格玛蓝色十字飞船上映衬过来,从我背后橙黄的吧台柜面上映衬过来,从她背后的大朵红色玫瑰布画上映衬过来。她脱了黑风衣,露出里面的黑色细条纹的淡咖啡色毛衣。她把左手横放在桌上,右手握住酒杯,抵在桌上轻轻晃着。她的头发在高领和肩上滑动。她歪着头,抿着嘴,有些羞涩,好像是看着酒杯里的酒,其实是在等我说话。
我一下抓起酒瓶,接连灌下去几大口啤酒,然后点燃一支烟,接着看那部还没有看完的《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