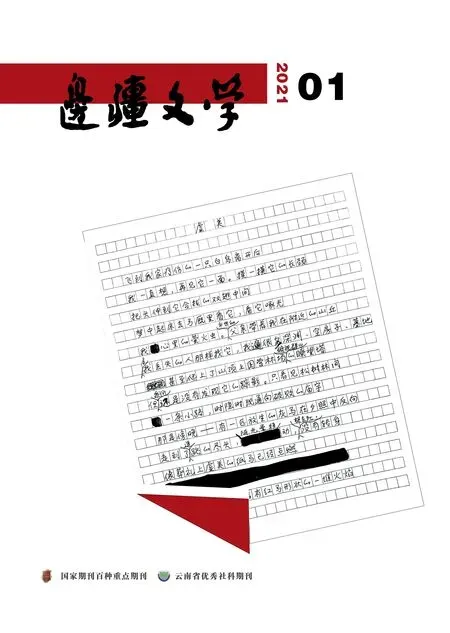夜行 短篇小说
林东林
1
我妻子跟她前夫在客厅说话。
我在厨房里忙活着,把早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那只乌鸡剁成小块,焯水,又用砂锅炖上,把米饭也蒸上,又用榨汁机榨了大半桶橙汁,倒了一杯。现在,我正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一边从窗户里望着楼下街头上那些陆陆续续停下来等着红灯转绿的车辆,以及正从马路两边行色匆匆地走向对面的人群,同时也等着他们俩把要说的话说完。现在是下午五点,他们俩已经说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还要说多久,以及他是不是会留下来吃晚饭。
李斌心里难道没一点儿×数吗?这个点儿了还不走?我给妻子发微信说。不过她没有回。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回事儿,是因为没看见不回,还是明明看见了却不回。
又过了会儿,街头上又有一些车辆陆续停下来,又有两队人马从马路两边急匆匆地走向对面,妻子还是没回。这让我不得不做起最坏的打算,就是李斌将留下来,他、我妻子、他们的儿子晨晨,还有我,我们四个将不得不围坐在那张餐桌之前享用我精心烹制的这顿晚餐。虽然那会让我觉得自己(而不是李斌)反倒成了到他们家里(我们家里)来蹭吃蹭喝的人,但是我也没办法,我又不能提着擀面杖或者菜刀把这个厚脸皮的家伙撵出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那也太不符合我的形象了,不是吗?
半个小时后,我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大门开了一下,接着又砰地一声关上了,再接着客厅里就彻底安静了下来。等从厨房里走出来时,我看见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了,李斌不在,我妻子也不在,客厅里到处都漂浮着一股不小的烟味儿。我注意到沙发旁边的那张小茶几一角上放着一只纸杯,里面丢了好几只烟蒂,把那小半杯水都浸黄了。我从来不抽烟,我妻子也是,不用说,那肯定就是李斌抽的了。我把几扇窗户都打开,把风扇也打开,好把他带进来的和他造出来的那些气味儿都吹散掉。
然后,我就在沙发一角坐下来,准备给妻子打电话问她去哪了。坐下来,我才注意到那只正卧在沙发另一角的穿着一件黄色马甲的小泰迪。见我坐下来,它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抖了抖身子,然后就支着两只前腿开始冲我狂叫起来。叫的时候,它脖子下面那只粉红色的小铃铛也在叮当作响。我冲着它笑了一下,招招手,又拍了拍手,不过它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摇着尾巴亲热地跑过来,而是继续冲着我狂叫个不停。
就在这时候,妻子从外面打开门走了进来。见到妻子走进来,那只小泰迪就叫得更凶了,甚至要朝我冲过来。冬瓜!冬瓜!她喊了它两声,然后它就不叫了,哼唧了一下,又在原地卧下来,不过那双聚着两个光点儿的小眼睛还是在一直盯着我。
谁家的狗?我看了一眼狗,又看了一眼妻子说。哦,李斌送过来的,明天他要回老家一趟,冬瓜就没人遛了,她说,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来。她一坐下来,冬瓜也叮叮当当地跑过来,在她屁股左边卧下来,不过还是狗视眈眈地盯着我这边。妻子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它,直到它把头低了下去,不盯着我这边了。怎么,那么多宠物店不能送,非要送到我们这儿来?他什么意思?我没好气地说。哦,他老娘快不行了,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病危通知书已经下来了,妻子解释说,临走之前他老娘想再见孙子最后一面,他是来接晨晨跟他一起回去的,就把冬瓜顺便带过来了。
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晨晨并不在客厅里。四点半的时候,妻子去学校把他接了回来,回来后他一直待在家里。现在,他的小书包还在椅子上挂着,他摊开的作业本和文具盒还摆在他每天总是爬在那儿写作业的那张桌子上,我给他买的那只威尔逊足球也还在那张桌子底下,但是他不在,他刚刚被他亲爹李斌接走了。这给我带来的一种错觉:李斌用那只小泰迪把晨晨换走了——虽然儿子本来就是他的,狗也是。
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他的,至少曾经是。在这个屋檐下,他和我妻子(当时是他妻子)一起住了七年。本来他们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的,幸福或貌似幸福地住下去——就像我们每天在电梯里或楼道口见到的那些年轻夫妻一样,直到他们的脸上布满皱纹,头发也一天天变白——就像我们每天在电梯里或楼道口见到的那些颤巍巍的老两口一样。但是前年年底李斌出轨了,最重要的是她发现他出轨了,就在这套房子里,就在他们一起睡了七年的那张大床上,出差提前回来的她抓了他和那个婊子的现形。一个月后她就和他离了婚,房子和儿子归她,只留了那辆福特翼虎给他。
我和妻子是半年前走到一起的,在她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她三十二岁,本地人,在一家地方银行做信贷员。我比她大三岁,也是本地人,是一个所谓的作家。见了几次,相处了一段,她觉得我还算靠谱,年貌和她差不多,情况也和她类似,是个她当时遇到的可以和她将就着把日子过下去的人。而我对她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感觉。于是我们就领了证,摆了几桌酒,请了双方的一些亲友参加,也就算婚礼了。是的,这并不复杂,对两个都结过婚又都离了婚的人来说,我们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挑剔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对方了——而事实证明,千挑万选走到一起的好像也不顶什么用。
结婚之后,本来我是想要她和晨晨搬到我那里去住的,毕竟那边的房子大一些,位置也更好一些,但她嫌那边到她上班的地方太远了,往返一趟要两个多小时,就让我搬到了这里。我住过来已经半年多了,也已经渐渐适应了在这里重新展开的家庭生活——和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尽管这里的一切基本上都还保留着他们一家三口在这里住着时的样子,只除了墙上的那副结婚照由他们俩的换成了我们俩的之外。
我是一年半前离的婚,准确说,是被离的婚。表面上是情感破裂,实际上是前妻认定了我不可能给她带来她想要过上的那种生活——而她周围那些在她看来完全比不上她的那些女的却早已经过上了那样的生活。她已经忍受八年了,再也忍不下去了。
她比我小四岁,在我女儿读书的那个小学当英语老师。在我们相识、恋爱的那段日子里,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她对我——作家——这个身份还抱有某种浪漫的想象,但是后来,尤其是在女儿出生之后,她就再也不那么想了。和我离婚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她就和分管她们学校的一个教育局领导好上了,后者比她大十几岁,好了还不到三个月他们就结了婚。至于她嫁给他之后过得怎么样,是不是靠她拥有的那些东西换到了她一直没能拥有的那种生活,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她的朋友圈早在她跟我离婚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经屏蔽了我,而离婚之后,如果不是必要的联系——按时索取女儿的抚养费和安排她每个月跟我见一次面,她也从来不主动联系我。
虽然对前妻还有一些不甘心,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她再嫁了,我也再娶了,不联系那就不联系吧,不联系正好,对双方都好!是的,如果我老婆现在还跟她前夫李斌经常联系些有的没的,那同样也是我不想看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实是这个理儿。但就这一点来说,妻子——正坐在我身边的妻子——做得还不错,离婚之后,尤其是跟我在一起之后,我暂时也没发现她和李斌还有什么出格的藕断丝连。
2
把我面前的那小半杯橙汁喝完之后,妻子端起杯子去了厨房一趟,出来后,她又端出来两杯橙汁,她一杯,我一杯。她起身时,冬瓜也叮叮当当地跳了下去,跟着她一直跑到厨房;而等她出来、坐下时,它又跟着她叮叮当当地跑了出来、爬上沙发在她身边卧了下来。——那意思就好像是对我说,我跟你老婆才是一家人,跟你不是。
来接儿子就接儿子吧,李斌怎么还说起来没完没了了?我问妻子。哦,他老娘不是快不行了嘛,我就安慰安慰他,怎么,你不高兴了?妻子说。我看你们一直聊,还以为他要留下来吃饭呢,还想着要不要加两个菜,给他整点儿酒什么的!都什么时候了,他哪还有心情喝酒?!我有!我说。她瞪了我一眼,拿起遥控板儿打开了电视。
来来回回调了一圈台,也没找到什么节目,有个频道正在放《武林外传》,她就定在了那里。播的是第四十集,一个中秋之夜,众人思乡心切,聚在一起回忆人生。郭芙蓉说,如果当初她没有来客栈,而是继续闯荡江湖下去,没准儿现在就已经是一代女侠了;李大嘴说,如果他当初一直当捕头,没准儿现在已经是四大神捕;而白展堂则认为,如果他当初学的是医术,现在已经是一代神医了……那么脑残的片子,那么无聊的剧情,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她却被逗得笑个不停。我不明白她的笑点在哪里,这可能也正像她完全不明白我——有那么好看的片子我为什么还要玩手机。
我,妻子,还有那只小泰迪,现在我们三个并排坐在沙发上,妻子靠着我,冬瓜靠着她。我在看手机上的新闻,冬瓜在看着我,只有妻子在盯着条几上的电视屏幕。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快递员,一个水电工,或者一个催缴物业费的什么人,当他看到我和妻子紧靠在沙发上,看到她不时发出的大笑,看到挂在我们头顶上方的那幅结婚照,看到看上去很乖巧地卧在妻子旁边的花花,闻到正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鸡汤的香气……他会想到什么?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他认为这是一对幸福的两口之家,这种幸福会感染着他,让他羡慕这样的生活并进而努力追求这样的生活,而他完全不知道我们背后的所有导致了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那些事。
是的,仅仅在一年半之前,我现在的妻子还是李斌的妻子,我现在坐的位置还是李斌坐的位置,他和那个婊子的奸情还没浮出水面,他们一家三口还在这里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而仅仅在一年之前,我还是我前妻的丈夫,我前妻还没对我没能给她带来她想要的那种生活感到绝望,我们还住在江对岸的那套大三居里,我们的女儿也还没叫那个完全可以给她当爷爷的教育局领导叫继父。但是现在,我、妻子,我们这两个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认识的人竟然睡在了同一张大床上。而这些,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是的,如果现在真有这么个人走进来,我一定会挪挪屁股让他在我旁边坐下来,好好跟他讲一讲我和妻子背后的这些鸟事,让他知道他的眼睛刚才是被两团巨大的眼屎给糊住了,让他明白所谓的幸福只不过是别人眼睛里的一种幻象。是的,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这么做,而且只有我——或者是另一个谁——向他无私奉献出了这一人生真谛,他才不会被自己欺骗,才能距离真正的幸福更近一步!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此时此刻他并没走进来,所以我只能把这一套收起来留给自己用。
现在鸡汤已经炖好了,我把上午没吃完的那条鱼热了热,又炒了个蒜蓉空心菜,就可以吃晚饭了。我、妻子,就我们两个,我坐在餐桌一边,她坐在我对面那一边。
不,不是的,她给我夹一筷子,我再给她夹一筷子,她给我舀一碗汤,我再给她舀一碗汤,在有说有笑的温馨气氛之中我们俩幸福地享用着这顿晚餐,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完全不是。事实是,她一边吃喝着还一边盯着屏幕,现在《武林外传》已经放完了,她又换了一个台,看起了那个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
一个叫蒲光勋的男的,28 岁,身高170,是四川广安华蓥市洋河镇政府事业编制人员。他说如果出生在两百年前,自己就是统一欧洲的拿破仑,他有英俊的容貌、傲人的才华以及远大的理想 ;他又炫耀起自己辉煌的考试经历,说他参加过三十多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后来终于考上了,觉得自己无人能敌。而他的择偶标准是,女方必须要像他一样没谈过恋爱,一张白纸,身高要在165 以上,双眼皮、大眼睛,最重要的是工作要稳定,最好是空姐,如果不是就必须是公务员或有事业单位编制,如果都没有,就必须在成都三环以内或重庆渝中区有一套200 平的房子作嫁妆……
果然,当其貌不扬、傻不拉几却自信心爆棚的蒲光勋恬不知耻地说完他的那番话之后,他不但收获了主持人孟非的揶揄,台上二十四位女嘉宾的灭灯,以及其中一位女嘉宾把他称为“男版凤姐”的嘲笑,还收获了我妻子的一双翻到天上去的白眼儿。
妻子把汤碗往桌子上用力一顿说,奇葩,什么人啊这是,节目组是傻了还是找不到人了?怎么会让这种脑残上节目呢?我喝着鸡汤冷笑了一声,心里说,节目组才不傻呢,是你们这些观众傻,本来就是策划出来的节目效果,你们还当真了!但我并没有跟妻子说这些,因为我还在想着之前担心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李斌留下来吃饭该怎么办,他坐在哪里?我又在坐哪里?是他、我妻子和晨晨坐在一家人的位置,还是我、我妻子和晨晨坐在一家人的位置?或者他和晨晨坐在一边、我和我妻子坐在另一边,还是怎样?看着餐桌边的另外两把椅子,我为没发生的这一幕设想了种种可能。
3
想什么呢你在?“非诚勿扰”播完之后,妻子用筷子敲了敲碗沿儿冲我说。没想什么啊,我回过神来望了望她说,没想什么!我为李斌没留下来吃饭感到一阵庆幸。
嗯,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她说,不过你别多想啊。什么?我停下筷子说。哦,李斌的事儿,他老娘不是快不行了嘛,他想让我跟他回去一趟,说。回哪?跟他回老家?我说。嗯,他老娘还不知道我们离婚,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就一直没跟她说。你答应了?我说。还没有,我说要跟你商量一下。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婚都离了,你还要去给他冒充老婆?你是不是想跟他回去?我说。不是我想,是回去能让他老娘走得安心些!我说,那你就去!她说,那你呢?我说,我怎么了?难道要我也一起去?给你们当电灯泡?她说,我是说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跟他又不会再怎么样了!
说完,她起身把桌子一角的骨头和盘子里的剩菜都刮到报纸上,把垃圾桶里所有的垃圾都倒进一个塑料袋,然后又把盘子和碗摞在一起端进了厨房。接下来,我就听见水龙头里哗啦哗啦的声音,以及她在洗碗槽里洗涮那些锅碗瓢盆时所弄出来的清脆撞击声。我从餐桌边走到沙发上坐下来,听着厨房里的那些声音。过了十几分钟,她洗刷完出来了,穿上羽绒服,把狗绳套进冬瓜的脖子里,又提上刚才倒出来的那袋垃圾,然后冲我说,遛狗你去不去?去!我一边说,一边把那袋垃圾从她手里接过来。
下楼之后,电梯门刚刚打开一条缝儿,冬瓜就急不可耐地拖着绳子猛窜了出去。它把我妻子扯出电梯,扯出单元门,一直扯到小区花圃周围的那条路上,看上去就好像它要遛我妻子而不是我妻子要遛它一样。它跑在前面,妻子夹在中间,我跟在最后。现在,跟在最后面的我,不由得站在它的角度上替它想了一想。是的,时隔一年半之久,现在它再一次回到了曾经无比熟悉的小区,再一次走上了曾经走过无数遍的小区花坛旁边的那条路,再一次路过无数次抬起后腿朝那儿撒尿的那些树和那些角落,也再一次碰见了它熟悉的那些母狗、公狗以及它们的主人,它怎么会不兴奋呢?
这个点儿,很多人都吃完饭了,都陆续下楼来了。一圈又一圈来回遛弯的老头儿老太,耳朵里塞着耳机跑步的年轻人,踩着闪烁着五颜六色灯光的平衡车的小孩儿,当然也有不少像我们一样遛狗的夫、妻或者夫妻,他们都走在花圃周围那条落满了一层枯叶的小路上。而接下来,我们也就成了他们之中的两员。我们走得不快不慢,不时超越过去比我们走得更慢的人、狗,也不时被比我们走得更快的人、狗超越过去。
有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的也在遛狗,她走在我们前面,牵着一只个头儿高大的全身雪白的哈士奇。在我们要从她旁边经过时,她的哈士奇和冬瓜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又停下来嗅了几鼻子,最后它们可能终于认出了彼此,认出了彼此原来是自己的老相好。而接下来,冬瓜就扒着两只前腿儿对准那只哈士奇的屁股凑了上去。这时妻子连忙用力扯了一把绳子,把它拉了回来。那个女的看了我妻子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妻子一眼,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是抱怨我们怎么不把自己的狗牵好吗,还是好奇经常跟妻子一起遛狗的男人本来一直都是他,现在怎么换成了我之类的吗?
以前你们俩是不是经常一起在这儿遛狗?等牵着冬瓜走远了一点,我问妻子。我们俩?我和谁?她愣了一下说。还有谁?我说。哦,你说李斌啊,她好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没有,谁有时间谁遛,主要是他遛!我笑了一席说,那怪不得呢!什么怪不得?她看了我一眼。我说,有什么样的主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狗啊!她说,什么意思?我说,能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她说,对了,我跟他说一下明天一起回去的事。
她把手里的狗绳递给我,掏出手机走到离我三四米远的地方给李斌打电话。我站在原地,用力扯着绳子拽住一直要往她那边跑去的冬瓜。她声音不大,所以我听不清楚她和他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走到离我三四米远的地方去给他打电话。
几分钟之后,她挂了电话走过来,又从我手里把狗绳接了过去。打完了?我问。嗯,她点点头说,明天早上六点半,他开车到楼下来接我。我说,怎么,你还真要去?她说,是啊,你不是也答应了吗?我说,都有谁一起回去?李斌,晨晨,你,就你们一家三口?她说,是啊,不然呢?我说,李斌……李斌就没有再找个女朋友什么的?她愣了一下说,这我哪儿知道,可能有吧,也可能没有。我笑了一下说,怎么,作为前妻,你也没有表示一下关心?她说,神经,我关心他这个干什么,愿找不找!
上楼后,妻子去洗澡了,我在客厅里坐着,——冬瓜被我拴到了阳台上,但它并没有钻进那个由纸箱子做成的临时狗窝,而是蹲在玻璃推拉门后面望着我,时不时地叫唤上几声——不过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到,因为那就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一样。
听着浴室里的花花的水声,我想到了花洒下面那具小巧玲珑的裸体,想起了妻子那并不那么高耸的胸部,并不那么纤细的腰肢,以及并不那么高翘的屁股,也想起了与并不那么高耸的胸部、并不那么纤细的腰肢、并不那么高翘的屁股很不相称的她在床上横冲直撞的那股劲头和声嘶力竭的那些呐喊。尽管每天晚上都睡在一起,但我们最近一次做爱却是在一个月之前了,或许还更久,事实上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次做爱的任何细节了。我不知道这一个多月来我们为什么没再做,是因为她的欲望降低了,我的欲望降低了,还是我们的欲望同时都降低了?或者是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别的原因?
半个小时后,她穿着那条淡蓝色的睡衣出来了,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在我旁边坐下来说,你不去洗?我说,你们明天六点半就走?她说,是啊,到他老家那儿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呢。我说,那怎么不坐高铁或者飞机?她说,我也想,但是得有才行啊!我说,那你去多久?她说,那我哪儿知道!我说,那我跟你一起去!你也去?她吃了一惊说,你去干嘛?我说,陪你啊,还能跟李斌轮换着开开车,怎么,不行?她说,你不是还要在家写东西?我说,是要写,不过也不急这几天了。她说,那冬瓜怎么办,谁喂?谁遛?我说,带着一起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先跟李斌说一声。
4
第二天,当我和妻子一起出现在李斌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尴尬的样子,还把手伸过来,跟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我握了一握。你好,他说。你好,我说。
他还是穿着昨天来我们家时穿的那身衣服,黑色羽绒服——敞着怀,牛仔裤,围了一条本来是白色的但是现在看上去像是灰色的围巾。在他驾驶座旁边挂挡的那个位置的凹槽里,放着一包黄鹤楼、一只打火机和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盒;而车棚顶上靠近挡风玻璃的位置,还挂着一个随着车的前进可以一圈圈来回转动的黑檀木转运珠。我笑了一下,就把头扭向了窗外,跟李斌、跟跟李斌一样的很多人不一样的是,我从来不在自己车里挂这些,完全没那个必要,再说了,挂上了转运珠就能真正转运吗?
这是我和李斌的第四次见面了。第一次——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对方,是他把晨晨送到我们那儿,当时妻子在卫生间,是我开的门,开门之后我和他都愣了一下,不过很快也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第二次是妻子出差那天,她要我把晨晨送到他那边去,他就在租住的那个小区门口等着我们,到了,我就让晨晨自己下车走了过去,我看到了他,我估计他也看到了出租车后座上的我。第三次,也就是昨天下午,妻子说他要来一趟,他上楼后,和他打了个照面我就到厨房忙活去了。而现在这次也就是第四次了,我们不得不一路开车回他家,对我来说,也就是我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妻子在名义上成为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出现在他家人面前,而我却不得不识相地跟在一边。
我和李斌坐在前面,妻子和晨晨坐在后排——妻子坐在我的后面,晨晨坐在他的后面,冬瓜则卧在妻子和晨晨之间。如果在车子中间前后画一条线的话,那么我和妻子恰好落在左边,而李斌和晨晨则正好落在右边,这跟我昨天晚上想到的那个吃饭的座位安排之中的一种是一样的。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昨天晚上没有上演的画面现在竟然在这里上演了,而且还将一直上演下去——起码在回去和回来的路上将会是这样。
走二环出城,出城上了高速之后,李斌把车子开得飞快。窗外掠过一座接一座低矮而光秃秃的山包,在山包和山包之间,是一片片纵横交错的田块,有些是什么都没种的白地,而有些则种植着我并不认识的什么庄稼。开了半个小时后,一轮绯红色的太阳就从远处升起来了,在冒出地平线并照射进紧挨着我的那扇车窗的那一刻,我看见它就像一块被烧得通红的圆铁片儿一样。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天的日出,那是我一生之中所见过的最美的日出,这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之后也再没见到过。但是李斌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它,而是专心致志地开他的车,当然他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它。
妻子和晨晨在睡觉,上车没多久他们俩就睡着了。妻子仰躺着,脸上盖着一顶红色的绒线帽,那是几天前逛商场时她买给自己的;晨晨也仰躺着,头枕在妻子的左腿上,两只脚正好蹬在车门的位置,是的,这很舒服,他的身高和身份决定了他可以这么舒服和不管不顾地睡觉。冬瓜趴在晨晨座位下面放脚的位置,看上去也像睡着了。
是的,妻子肯定困了,昨天晚上睡那么晚,今天早上又起那么早,别说她了,就连我也有些困了。昨天晚上,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妻子已经躺到床上去了。她侧躺着,露出两截光滑洁白的小腿,在淡黄色台灯的照耀下,她显露出一种久违的女性魅力。我凑上去,一只手搂住她,另一只手就不老实地游走了起来。她捉住我那只到处游走的手,把它攥在手里,但几秒钟后我又抽了出来,又开始到处游走起来。她没有再捉我的手,因为她身上开始紧了起来。于是,接下来,在那张我们一个多月都没让它发出来吱吱呀呀声的大床上,我和她又轰轰烈烈地做了一次。我很卖力,她也是,我们又像回到了刚在一起时的那种感觉,——这跟我们那么久没做有关系,也跟不用担心隔壁的晨晨听到有关系,或许还跟我说不出来是什么的那点儿东西有关系。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抬头看了她一眼——在后视镜里,她还在睡着,那顶红色的绒线帽还是盖在她脸上。又想到昨天晚上她在我身上的那一幕,我不能自禁地笑了出来。我想,李斌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的笑,或者即使是注意到了,他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我因为什么而笑——虽然我在妻子身上所体验到的那些内容他也都曾经体验过。
这一路上,李斌一直都没说话。我也一样,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山包、原野和那些叶子半黄半绿的树木,并想象着接下来几天可能遇到的事情。
车子里很安静,连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也没有,只有林志玲偶尔跳出来说一句——前方有违章拍照、您已超速、您已超速……又开了一会儿,李斌把他那边的车玻璃摇了下来,点上一根烟。你抽你拿啊,他抽了一口说,把那盒黄鹤楼和打火机丢给我。谢谢,我不抽烟,我说,把烟和打火机又放了回去。哦,还有不抽烟的作家?他看了我一眼说,我还以为作家都抽烟呢!我说,是有很多作家都抽烟,不过我受不了,抽一根就头晕,一直也没学会。嗨,抽烟还有什么好学的,抽多了自然也就会了,他笑了笑说。他一笑,让我也放松了下来,把上车之后保持很久的那个姿势调整了一下。
还是你们作家好啊,他感慨地说,自由自在,在家里写写字就有钱拿,不像我们这些上班的,天天忙得脚不连地儿不说,关键是还挣不到什么钱!我说,有班上还不好么?你们文体局的收入应该还不错吧?政府单位!他笑了一下说,是苏静跟你说的吧?我点了点头。不错个鬼!就这还叫不错呢?以前多少还能有点额外收入,现在连毛儿都没有了,就是请个假也难得跟什么似的,科长批完要副局长批,副局长批完还要局长批,至于么?他又说。我说,那确实太严了,也没必要,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就是!他又点上一根烟说,天天在单位里耗着有什么用呢,还不都是面子工程!
5
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车里抽烟,不要在车里抽烟,怎么就是不听呢你?这车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过了会儿,妻子的声音从后面响起来。她已经醒了,我回头时看见她手里抓着刚才盖在脸上的那只绒线帽,正在生气地望着李斌。好了好了,李斌说,然后他就把那根抽了小半截的烟弹了出去,把窗玻璃又摇上来。别摇玻璃啊,车里都是烟味儿,妻子说。于是李斌只好又把车窗玻璃摇了下来。我注意到妻子和李斌说话的时候,俨然还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命令式口气,而他好像也很乐于接受这一点。
这时候,晨晨也醒了,他揉着眼睛问妻子,妈妈,是不是很快就到奶奶家了?妻子说,哪有那么快啊,还早着呢,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晨晨摇了摇头,他一骨碌翻下来,把冬瓜抱了上去,用两只手握住它的两只前爪来回逗弄不停。他穿着一件蓝色卫衣,上面绣着一头黄色的小象,小象下面又绣着一排英文字母——LOVE ME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那几个字母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十分醒目。在我的记忆中,晨晨好像从来没穿过这件卫衣,我不知道那是李斌昨天晚上给他新买的还是怎么样。
晨晨,你是不是想奶奶了?李斌说。是啊,我都好多好多天没见过奶奶了,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他扭过头来,奶声奶气地嘟囔了这么一句。李斌说,奶奶怎么会不要你了呢,奶奶要的,奶奶要的……我能听得出来,他的声音中已经有了一丝异样。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下,九点二十七分,我们已经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在高德地图上,我看见一个我们坐在其中的带箭头的蓝点儿正在京港澳高速上向前方缓缓蠕动着,这个蓝点儿正处于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地带,准确地说是一个叫灵山镇的地方。再把地图缩小,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点儿处于它所离开的武汉和将要到达的最终的目的地——也就是李斌的老家淄博——之间大概三分之一距离的位置。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窗外的景色也已经从之前的丘陵变成了现在一望无际的平原,绝大部分田块里种植的都是冬小麦,一粒粒坟头和一棵棵光秃秃的树木就好像浮游在那些麦苗之中。
到前面找个服务区停一下啊,妻子在后面说,我要上个厕所。李斌,你都开了那么久了,也让陈栋开一会儿,她又说!李斌说,没事,我没事!我看了看他说,还是换一下,你也休息休息。然后他就没再吭声了,把车子缓缓地开进了灵山镇服务区。
下车之后,妻子带着晨晨去了卫生间。李斌没有去,他下了车,靠在车门前点上了一根烟。本来,我想的是如果李斌去卫生间我就不去的——我很难想象妻子的前后两任丈夫肩并着肩地掏出东西冲尿池里撒尿的情形,现在既然他不去了,那么没有多少尿意的我也就只好去了——我也很难想象和李斌单独待在一起时那种没话找话的尴尬。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撒完尿回到停车的地方时妻子和晨晨还没回来,所以我还是不得不和李斌单独待在一起一小会儿。他冲我笑了笑,我也冲他笑了笑。
他又点上一根烟说,这一次真是感谢你啊!是的,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说,没事,这不也是应该的嘛!不过,与此同时又在心里骂道,他妈的,你以为我想让苏静跟你跑出来这么一趟啊?你以为我想跟你们跑出来这么一趟啊?如果不是不放心她跟你死灰复燃,我怎么会放着已经构思好了的小说不写,非来跟你们受这份窝囊气?
等妻子和晨晨上完厕所回来,我就主动换到了驾驶座,李斌就坐到了我刚才坐的副驾驶座上。开了一会儿,妻子又睡着了,那顶红色的绒线帽又重新回到了她脸上。
晨晨没有睡,不过他的兴趣现在从冬瓜身上转移到了妻子的手机上——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玩那款经常玩的“鸭嘴兽泰瑞在哪里”。之前他已经闯过了17 关,但是他怎么也过不去第18 关了,我跟他一起玩过几次,不过我完全玩不转,连第10 关都闯不过去。如果你也有一个孩子,碰巧他或者她也喜欢玩这个游戏,那么你也可以试试,我可以肯定你十有八九也玩不转,因为越到后面的关卡情况越复杂,各种激光发射器会扰乱你的思路,而错综复杂的管道出口也总是会把水流带向错误的位置。
晨晨,玩一会儿就行了啊,不要玩太久,不然你的眼镜度数又得加深了!李斌扭过头去冲晨晨说。哦,晨晨说,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手机里还是发出滴滴答答的游戏声。现在的小孩子说起来也怪可怜的,什么都玩不了,也只剩下电子游戏了好像,李斌感慨道。我们小时候哪里玩过电子游戏啊,好像连动画片都没怎么看过,那时候只有弹玻璃珠、呼纸牌、跳房子、打陀螺,或者到河里塘里抓鱼摸虾什么的,他又冲我说道。李斌说的这些,让我眼前立时浮现出来一个小男孩的形象,他很瘦,很黑,肚皮和小腿上经常布满了一道道血痕,这并不是小时候的李斌,而是我的农村表哥。
是这样的,在我小学四年级毕业的那个暑假,父母把我送到了河南驻马店农村的舅舅家里。李斌刚才所说的那些游戏,我就是在舅舅家住的那一个多月里跟着大我一岁的表哥学会的。他很调皮,经常带着我在他们村旁边那片树林里爬高上低的,他肚皮和小腿上的那一道道血痕,就是在爬树时挂上去的,当然我的肚皮和小腿上也好不到哪里去。表哥还会做一种火柴枪,用一节节的自行车链条做枪膛,为了做枪,他甚至把我舅舅那辆除了铃不响别的地方都响的凤凰牌自行车也拆卸了。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把枪的样子,钢条捏的枪架,车胎箍的枪栓,枪膛上面还带着一个并不能用来瞄准的准星。我之所以清晰地记得它的样子,是因为表哥在用它打鸟时一不小心走火打到了我的右胳膊上,并为我留下了一小块一直跟随我到今天的淡粉色疤痕。
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位表哥了,前年他到武汉找过我一次,想让我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他弄些便宜点儿的猪饲料,不过我能有什么关系帮他这个忙呢?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我读大学那一年他结了婚,在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一家一直生活在驻马店下面的农村老家。虽然我们现在正在从驻马店城区的边儿上穿过去,不过这一次我也没时间拐过去看他了,而即使我有时间去看他,恐怕他也没时间接待我了。他忙得很,承包了一百亩地,养了700 多头种猪,已经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每天拉着一车车母猪到他的养殖场里配种的人络绎不绝。
6
你没在农村生活过吧?李斌又说。我说,没有,只是读小学时去待过一个暑假!他说,怎么样,好玩不?我说,比城里好玩。他说,我也这么觉得,不过当时还是觉得城里好玩,城里有电影院,有游戏厅,还有游乐园什么的,我们老家那儿太穷了,96年才通上电,才看上电视,他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说,你能想象得出来不?我读初中时教室里还没有电灯,我们上早自习点的都是煤油灯,连蜡烛都点不起……他还在吧啦吧啦地跟我说着这些,就像是跟他的一个多年未见的发小在缅怀昔日时光一样。
我不知道李斌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是排遣这一路上的无聊时光,是从晨晨玩的游戏话赶话地说到了这些,还是想让我对他产生一点儿同情,进而陪着他、妻子和晨晨一起把这出戏演下去——而不是搞砸了?我不知道。作为回应,作为妻子现在的丈夫对她前夫的回应,我只能不咸不淡地附和那么一两句,嗯,哦,是的,确实如此。
后视镜里,晨晨还在继续玩他的游戏,妻子还在继续睡她的觉。我不知道妻子刚才是不是也听到了李斌说的那些,她那顶绒线帽下面是不是睁开着眼睛我也不知道。
这时候,李斌把他那边的车玻璃又摇下来,又点上一根烟。他吸了一口,朝外面喷了一口烟气,然后就把夹在手指里的烟留在了车窗外面。我们家兄弟三个,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是老幺,他们都没怎么读过书,早早就辍学出去打工了,到浙江,到广东,兄弟姊妹四个里面,就我自己离开了农村,到武汉读书、工作,后来又跟苏静结了婚、有了晨晨,可以说,我就是一家人眼里的骄傲,李斌说,我父母都是那种极其传统老实的农民,他们接受不了我离婚这个事儿,我哥我姐他们都知道了,只有我老头儿老娘不知道,一直在瞒着他们。我看了他一眼说,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过了一会儿,李斌又说,也不瞒你说,离婚之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老婆老婆没了,儿子儿子不跟我,工作工作也调了岗。我安慰他说,也别多想,总会好起来的。他说,苏静没有跟你说过吧,我现在不在文体局了,到下面一个公司挂职去了,从管理岗调到了生产岗,收入降了三分之一,交完房租之后也就没剩多少了,将将能顾住温饱……他摇了摇头,对着车窗外面叹息了一声。他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来了,之前每个月月底妻子跟他催要晨晨的抚养费时,他总是要拖到下个月月初才转过来。
已经离婚了这么久,你也没再找一个?我试探着问他。找一个?说得容易,李斌说,找谁?我连自己都顾不了了,还能找谁?!我说,那你……那你原来那个……女的呢?他说,哪个啊?我小声说,就是那个啊,让你和苏静离婚的那个!他脸色变了一下,朝自己背后指了指,然后小声说,等方便的时候我再跟你说这个。接下来,他看了一眼手机,又提高音量说,这都快两点了,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吃饭吧!他扭过头去问晨晨,晨晨,饿了没有?晨晨还在玩游戏,嘟囔了一句我没听清楚的什么话。
我在前面一个服务区停了车。停好后,妻子还在睡觉。我轻轻摇醒她说,该吃饭了!她把绒线帽拿下来说,吃什么?我说,你想吃什么,快餐还是桌餐?她眯着眼睛摆了摆手说,你们去吃吧,我再睡会儿!我说,你怎么了,下车吃点儿嘛,到李斌老家还要四五个小时呢。妻子说,算了,你们去吃吧,我来事儿了,身上不舒服。晨晨也说不去吃了,他还在一门心思地打着游戏,已经过了第18关,正在过第19关。
于是,接下来就只有我和李斌去吃饭。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点了两盒快餐,他要了一份烧茄子盖饭,而我要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李斌饿了,狼吞虎咽的,我才吃到一半他就已经吃完了。吃完一抹嘴儿,他又摸出来一根烟。你慢慢吃,他说,然后点上烟,眯着眼睛一脸满足地吐了个烟圈儿。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他笑笑说。
我又想起来他和那个婊子的事,就问他,你原来那个女……朋友呢,没有在一起了?他说,早分了,哪是什么女朋友,炮友!我说,那就怪你了,有老婆了还在外面乱找什么炮友!他说,当然怪我了,我也没说不怪我嘛!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找炮友啊?我说,怎么,找炮友还有理由了?他说,苏静不让我碰她啊,半年都不让我碰一次,我不知道她在外面有人了还是怎么着——他或许以为我就是那个“人”,你说,夫妻生活都不跟我过了,我怎么就不能找炮友了?我看了看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其实我知道,离婚是早晚的事儿,即使不出轨我们也走不下去,李斌又说,苏静一直都看不上我,她觉得我跟她不是一路人,她喜欢那种能让她仰望的男人,有才华的男人,能征服她的男人,可能,哦不,也就是你这样的男人,你说,这跟我出不出轨有什么关系?她不过是找个跟我离婚的借口而已!我不知道李斌说的是不是真的,以及有多大的成分是真的,就我对苏静的感觉来说,她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们俩真正的症结是什么——我想一定存在,我也没问过苏静这个问题,也没必要。
等我吃完,李斌还在说着他所以为的他和苏静之间的问题,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对我来说,听妻子的前夫谈论他和妻子从前的种种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而实际上,我也没必要去理解他,进而去理解他们之间的问题——那已经不重要了,李斌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回来,以及为什么和他面对面地坐在这儿一起吃盒饭。是的,他说这些什么都不能改变,连屁用都没用,或许他只是需要说出来,只是需要一双耳朵听他说出来而已。我为他感到难过,并尽量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去同情他。
7
重新上路,李斌说他来开车,于是我又重新坐回了副驾驶座上。还没开多久,妻子又把那顶绒线帽盖在了脸上,我给她买回来的那盒饼干她也没吃几块。我给她发微信说,你是不是还很难受?要不要去买点儿止疼片什么的?不过,她一直没回我。晨晨也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但是手里还捏着手机,手机屏幕上还显示着游戏界面。
现在,车子已经进入了山东省境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已经放晴了,太阳也露了出来,车窗外面蓝天白云的,一路上的阴霾终于被我们甩在了身后。午后的阳光透明澄澈,撒在那些平缓起伏的山坡上,一块块绿油油的麦田上,也透过车窗撒在我身上,在我衣服下面生出来一寸寸的暖意。同时可能也因为刚刚吃饱的缘故,后来我也就渐渐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很长,我记得虽然中间朦朦胧胧地醒过来几次,但是泛上来的睡意很快又让我继续睡了过去,同时我也不想再听李斌唠叨些什么有的没的。
等我醒过来时,车子已经下了高速。我问李斌,快到了?他说,快了,还有五十多公里。我说,那换我开吧,你歇会儿。他说,算了算了,很快就到了,这一段路不太好走,还是我开吧!既然他这么说,我也就没再争了。这是一段坑坑洼洼的乡道,确实不太好走,路上车很少,路两旁有两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白杨树。因为掉光了叶子,所以树杈子上面那些大大小小的鸟窝就显得特别醒目。晨晨指着它们问李斌,爸爸,树上那些黑乎乎的是什么?李斌说,那是鸟窝,爸爸小时候还经常爬到树上去掏鸟窝呢。晨晨说,我也要去树上掏鸟窝!李斌说,等你会爬树了,爸爸就带你……
后面的几个字他还没说完,我就听见嘭的一声,然后就感觉到车子的一角歪了下去。妈的,不会爆胎了吧?李斌说,然后他就停了车,拉开车门到后面去查看怎么回事,我也下了车。果然是爆胎了,左后方的那只轮胎已经泄了气,一根上面钉了好几根钉子的木板被它死死压在下面。妈的,哪个狗日的扔的,李斌气呼呼地扯了扯那块木板,又向四周望了望,好像要把扔木板的那个家伙从空气中揪出来暴揍一顿一样。
这时候,妻子和晨晨也从车上下来了。看了看瘪下来的轮胎,妻子指着李斌说,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换备胎啊!李斌看了她一眼说,哪还有备胎了,这个就是备胎!妻子瞪着他说,什么,车上的备胎呢?李斌说,上周拿到修理厂去了,还没取回来。妻子又冲李斌说道,你怎么老是这么不着调儿?猪脑子?李斌被骂得耷拉着脑袋,不再吭声了,我看见一团接一团白气从他鼻子下面呼出来。接下来,李斌从裤袋里摸出来一根烟,点上。妻子摊着两只手冲他说,那现在要怎么搞啊,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连忙走过去打圆场说,别急,我先搜一下,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方。
地图上显示,最近的一家汽修店在附近的清河镇上,距离我们这儿有三公里。我对李斌说,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开到清河镇上去,不过,等开过去你这个轮胎差不多就得报废了。李斌说,那没关系,能修好车就行!于是我们就又上车,按照导航提示往清河镇的方向开去。上了车,妻子还在不停地数落李斌,说他不应该绕近路,如果走大路根本就不会爆胎,又说他出门连备胎都不带,吧啦吧啦的,李斌也不吭声。
等到了清河镇,找到那家汽修店时,夕阳已经全部落下去了,整个天色都暗了下来。车一停,李斌就着急忙慌地下车,冲进那家卷帘门拉下来一半的汽修店里找人。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说,怎么没人啊?我说,门还开着,肯定有人,估计是去旁边了,我指了指卷帘门上的那个电话号码说,那儿不是有电话么,打打看!李斌打完电话几分钟,一个小伙子就从路对面的棋牌室里走了过来,他看了看车,又看看李斌和我们说,修车?李斌连忙点点头,抽出来一根烟递过去,然后又打着火凑到他嘴边。
打牌呢正,那个小伙子捂住火抽了一口,冲李斌说,爆胎了?李斌说是是是,爆胎了。接下来那个小伙子就叼着烟走进店里,不太情愿地把千斤顶什么的家伙什都搬了出来,然后忙活起来,李斌也跟他一起忙活着。直到这时候,我才算舒了一口气。
汽修店旁边有一个卖烟花爆竹的店面,两个跟晨晨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正在铺子前面放鞭炮。他们把一只鞭炮用一个铁盒子压住,露出捻子,其中的一个小孩就用一根香去点,点着后他们俩就笑着跑开,捂着耳朵躲到一棵大树后面,盯着那个冒出一缕缕白烟的铁盒子,接下来,嘭的一声,那个铁盒子就被打到了半空中,又叮铃咣铛地落下来。晨晨觉得新鲜,蹲在路边一直盯着那边看。我说,想不想玩这个?他点了点头。我说,这个你玩不了,被铁盒子砸到头那就麻烦了,叔叔去给你买燃鞭放。
我在店里买了一盒燃鞭,抽出一根,点着,递给晨晨,然后他就噼里啪啦地甩起来。四处溅落的火星把他那张小脸都照亮了,空气中散出一股好闻的硫磺味儿。一根燃完他又抽出来一根,我又点着,他就挥舞着跑动起来,身后拖着一条火星带。晨晨一直跑到李斌背后,对着半蹲在车前的他挥舞起来,接着李斌就把头扭了过来,耀眼的火花就照亮了他脸上的汗珠和他周围暗下来的夜色。我停下来,我看见妻子也停下来,我们就这么从不同方向看着这一幕,直到那根燃鞭一点点燃完,那些溅落的火星也一颗颗消失,直到最后一颗在地面上啪地亮了一下,又熄灭了。我想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幕,我、妻子、晨晨、那个司机,还有李斌,我们都看了这一幕,尤其是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