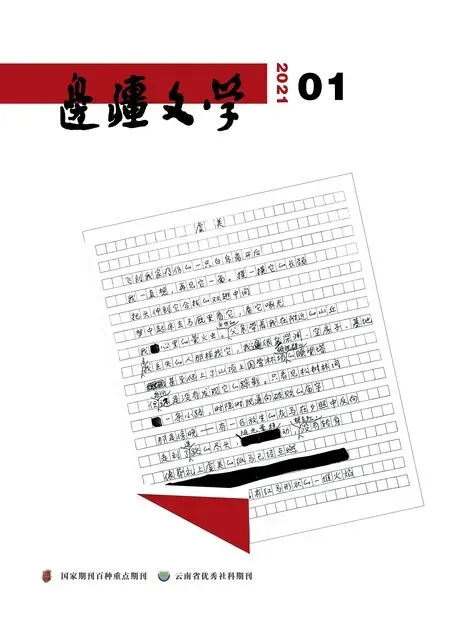少年与草命 组诗
芒原
逝去者
撞破秋风,得要多大的心力
而钟声落于江心,抱有沙粒终身之憾
白鹭腾空,溃散于纸上
电话里,传来逝去者的消息
雨滴便滂沱于虎口,乱风渐入我怀
弃我去者,皆弹奏一曲:那如风般逝去的
或正在逝去的,亦将要逝去的,以及
还未逝去的……
在逝与不逝间,统统都入土为安
统统是扰我、乱我之心者,皆如白驹之隙
她已驾鹤西去,云游极乐,却听不见
一丝活人的悲恸
一生守寡,曾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世替人看命,又看不出吞象的人心
天地阔远,空空的薄纸里
小小的安息
化古海子
远去的云,还在天边
这是时间的搬运术,也是人心的幻象
灵魂出窍时,已带出借尸还魂
化古海子,一个小山村,被乌蒙群山
围得水泄不通;一个生与死挤压的交接地
一片高原之上的小汪洋
像水晶的制造者,被苍老的戏揭穿
一万年,十万年
甚至是上亿年。它的身体里,曾无数次
填满图书馆的残页,捍卫着
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
侏罗纪,白垩纪……
同时,也落入土地、草木、牛羊
和炊烟的繁衍中
一心想化掉虎腹里的乱象
在秋风里
抚一次流水的古琴
杂咏
日光透过寺庙的窗格,花朵在塔尖
僧人的口里,舌如莲花
在大金塔下
一对未来的新人在拍婚纱照
粉脂如雪,胭脂香腮
塔下的早课,正经声四起
像花间的菩萨
而我此刻恰巧路过,仿若莲台下的童子
满心欢喜,它们的慈悲
用弱小的声音
托梦——
泛舟记
登上竹筏,不知是流水
接纳了我,还是竹筏顺从了流水
一种命运与共,瞬间
抱成了一团。立于筏头,胸中之酒力
正在延宕,而漓江上,冷风扑面,巉岩高耸
让我思接千载——
忽而,有噫吁嚱,危乎之高哉
忽而,有清泉于石上之幽秘
忽而,又有城春草木之深的忧愤悲叹
而脚下,却是水推送着竹筏,竹筏推送着水
恍惚中,听见船家唱:“唱山歌来,山歌
好比春江水嗳,嗳,嗳……”
歌声飞渡,在这刘三姐的故乡
我们一群人,又做了一回
流水的虎衣
少年与草命
在江湖仅存于内心时,自己
就是自己的江湖,自己就是自己的
刀客。但少年不同
不知他从哪本书籍里习得江湖
每次回老家,总要在他祖父的果园里
挥刀。他把整个果园的荒草都预设为江湖
他要行侠仗义,他要斩妖除魔
把每一棵草都当作一个横征暴敛的
盟主,必须取它首级;把每一棵草都当作
奸佞小人,必须取它项上人头
把每一棵草
都当作一个诛心的华山论剑,必须
一一铲除;把每一棵草都当做吸星大法
九阴白骨爪,葵花宝典,玉女心经
必须给它一扫而光……
我看着那么多草倒在他的刀下
成了他臆想中的冤魂、刀下鬼和替罪羊
我告诉他,割草是“割”,不是砍草
杀草、宰草、捅草、切草
灭草、挖草、屠草。少年听了
不得要义,略显得
有些忧伤
铁轨与豹子
在乌蒙山巅眺望,每一列火车
都像一枚子弹,从山的身体里一穿而过
从每个如白纸的清晨开始
到疲软得像一片滩涂的夜晚
生铁与速度碰撞的火花,轰鸣交织
可在事物的内部——
对立的统一,辩证的悖论,都已形同虚设
在平面滑行的铁轨上,呼啸
是埋伏在歌颂者冷血下羞耻的澎湃
而豹子,是汉字
勾勒出,一块力学下摧枯拉朽的弹头
每个人都在列车上
突然,朋友发来微信
他在看南边的残荷、云影和天光
我却在北边躲避刺骨的寒风
我回复他:
南在南,北在北
望天吼
在乐马厂旧址,我们都落入
时间的圈套,一块残损多年的碑帖
只剩下石头的骨架,以及它身边的荒草
——而望天吼,这石头的神格
它是一只不死不灭,望着天空
怒吼的猴子。见到它,我想送给豢养老虎的人
吼一吼;送给那废墟上盛开的冷兵器
吼一吼;送给骨头与骨头相撞时
吼一吼;当日落压在
黄昏的舌头上,也代喉咙
吼一吼
哭声
天空是闪电的故乡,梦是人的故乡
清晨的水龙头,听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
流水之声,被围追堵截
妻子在催促,儿子也在催促
——“要迟到了!”
可我还在低着头,用清水一遍遍
清洗脸上的哭声
像个求救的人,把一盆肮脏的铁屑
泼在时间的
墙上
还俗
一个久居山林
还俗的人,他最终活成一个
在内心博弈的僧人
他从女人的火焰上看到青灯,又从盐里
看到了海水,从橱窗里的仿真花朵
看不到春风吹拂,却依然盛开
所有的不平凡——都是平凡的极致,所有的修行
都是内心的执念
他曾视万物为亲人,视行善为功德
殊不知,生活是另一座深山
得重修庙宇,金身重塑
把黑夜里穿云而过的闪电抛下
等风起,等胸中的月光
逼出明亮的
业障
撞响
是不是日有所思,才导致
夜有所梦,是不是自己欺骗自己
太久了,才导致梦中是非颠倒。或者说
这根本就不是梦,但我宁愿相信:就是一个梦
“生活如此陡峭,那么多囚徒
紧紧抱在梦中。”
古人在现实中饮酒,我却在大梦中初醒
喝五柳先生的菊花酒,杜甫的草堂酒
苏轼的大江酒,李商隐的蓝田酒,易安的
梧桐酒,还有庭钧、纳兰……
这些孤独的灵魂,酒是他们血性中的
第二重火焰,心中搓洗的黄沙
我曾答应去看多依河
可事实上,我只是枕着一条河水
坐在油菜花盛开之地,痛饮
那金黄的浪涛
代我撞响天空的蜂巢
万古愁——兼致滇中诸友
暮色残留湖面,月亮落在水中
兰隐、翔武、小缺和我
以及眼前的岩石、崖洞、亭台
庙宇、草木……
在此刻,都成了孤山的仆从
我们对着湖水喊,对着苍茫的天空喊
它们无声无息,又无动于衷,惟有那一面月影
像块波浪中闪烁的白玉璧,令我动容
令我思绪万千,突然像个
等待救援的人,那胸中的万古愁
又怎能敌得过
古墓上那句“四面碧涛
惊梦客”。
写在纸上的春天
歌咏,或纵酒
给花朵一个安抚悲伤的理由
把这个庚子的春天,统统写在纸上
让灰色、凋敝,都擦洗一遍
相信:“恐惧的伤口会开出明亮的花朵。”
也相信无助、焦虑、煎熬、疼痛
都会烟消云散
妻说,“樱桃花开过后
就会轮到梨花、桃花、杏花
迎春、夹竹桃……”
是啊!在彼此无法预测花期的身份里
就做个穷途末路的
葬花人
晚安
又一次
与那个油菜花自由盛开的地方
失之交臂
它呼唤我,可我拒绝了它
我像一个不配拥有花香和金黄的囚徒
而那些金黄的波涛,是大地上镶在天边的彩云
会让我想到文字中的抱团取暖
酒中的惺惺相惜
可又不能。我相信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
坤哥是懂我的,琼姐也是懂我的
唯独这无边的黑夜
——像张又爱又恨的巨大渔网
仿佛是它故意在骨髓里点灯,在电网下监视
故意在狼狈不堪的身体种植流水
但事已至此,那就随它吧
那就默念:晚安!
默念从凌晨办公室走出的每一个人
空荡荡的大街上,那些被释放的身体
被放生的自由,是那么的冷清
和无所适从
菩萨
在摄影师身上,我看见
一个浮世中的菩萨:自己给自己开示
自己丈量自己,自己用照片
留住菩萨的金身,也留住工匠的锤痕
还有时间的穿肠与莫名的弹痕
看一眼,就不能忘,就触目惊心!而那些把菩
萨
当作靶子的人,或许仍活在我们中间
一个个都慈眉善目,平静而安详
像极了另一尊世相中的菩萨
他们仍在大快朵颐地谈论因果,和慈悲
谈论信奉,虔诚,以及忍耐之心
花开和花落,沙中法身……
某一刻,在摄影师的照片里,我怀疑
这些人已越过菩萨的边界
企图
活在每个人的心中
删除
每一刻世界都在朴素流血……
如此清澈的事,可能无需思,无需感伤
——哑石
第一滴雨落在额头上
让我认出一滴透明的心脏
接着是第二滴心脏
山雨欲来。我的身体上,也有
羞于袒露心迹
随后是:第三滴、第四滴
雨与雨滴之间,被裹在越来越多的雨蔓里
它们不断地重复、吞噬
甚至毫不手软地删除前面的雨滴
在雨中,我手里的卷宗,也渗进了雨
那些红色的手印沾满了雨滴,指纹在垮塌
所有的口供,所有的陈述,都在
退让。这令我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挽救谁?谁先谁后
更担心这雨滴,它巨大的删除能力
会不会把不同的身份
混为一谈
在警史馆
陈列着那么多刑具
脚镣,手铐,警绳……
移步往前,我明明听到:“刑不上大夫。”
可为什么
我的身体里又叮当作响
甚至,在靠近肋骨地方,突生尖刺
离开警史馆,都舒了一口气
心又重新回到了身体
其实,在观摩中,很多人和我一样
都听到一把冰雕的锥子,在时间的对抗中博弈
在肉身、文字、人伦、教化、荒诞
甚至是,宗教、政治、哲学
或经书里
被一次次地逼退疼痛
但谁也不愿轻易
喊出来
来人了
庙里的八哥会说话了
至于它是谁教的,何时教的
人们也说不清——只要一有响动,它就憋着嗓子
喊
“来人了,来人了……”那份高兴劲
那份永不厌倦的热情,迸发出
它乐此不疲的哲学,有时可能是一阵大风
有时可能是另一种鸟叫,有时
是一片月光。但不论何时,它都是
一副报喜不报忧的腔调
更多的时候,是它在笼子里
上蹿下跳,自娱自足
练习“来人了
来人了……”
黑色幽默
百米开外的弹坑
密密麻麻的轮胎,堆砌成一座
橡胶的监狱,或者说一片黑色的泥沼
在时间的废墟上,每一个练习者都在瞄准
都在对准虚拟的敌人射击,都想
弹无虚发。事实上,谁都不是天生的神射手
谁都有成为一名神射手的潜质
这并非罪过,是生而为人的卑贱
当很多的误解叠加一起,就是一场战争
灾难中,很多无辜的生命
失去家园和亲人,饱尝那担惊受怕的枪林弹雨
煎熬、困顿的炮火烽烟……
射击结束,我还停留在刺耳的枪声里
想着那些迅速飞向轮胎的弹头
有的整个落在地上,有的却是半遮半掩
更多的,肉眼已经看不见了
有时,正是这样一个橡胶的缓冲
安抚了
多少子弹的亡魂
夜饮——夜访朱零
在哪里不重要
不论是北京,或是云南
河与山,并无两样。可以忽略
吃什么不重要
不论是滇菜,或是川菜
都是菜,一样穿肠而过。可以忽略
喝什么不重要
不论是杜康,或是明月
呼儿的轻,万古的愁。也可以忽略
唯有大理:月下排排坐,在本园里读诗
十个人,十条小船
在那夜的洱海潮声里荡漾
至今,被磨成一把
月光匕首
己亥冬夜,与雁超兄弟饮茶
茶壶里的水,是滚烫的
对面三楼,入喉的酒,也是
滚烫的;楼下面嘻嘻哈哈的少年
他们的心,也是滚烫的
可两个人的世界,沉默得像入世的石头
我们心照不宣,却往窗外的黑夜
凝望一下——瞬间,寒冷就被拦在窗外
昔归茶气足,回甘生津,喉韵中含有甜度
我说出一片叶子对沸水的解构与消融
也包括置之死地的孤绝
最后,他说起瓶子具有的普遍性
我知道,那个瓶子的历史与自己有关
取下,或者敲碎瓶颈
与滚烫无关
于是,我又往更深的暗夜
看了一眼,他却不去在意了,把杯子
轻轻放回桌上
午后浇地所见
很多人从水源地回来
每年都找到相同的那一部分,欢喜又悲观
仿佛春天的泥土是咸的
惟独苹果树一直沉默,活在它的尘世
不卑,不亢;开枝,散叶
看着忙碌的人们
像一群正在集结赶路的蚂蚁,把午后的影子
背对日落的方向,拉长
再拉长,又慢慢
消亡
离别咏——兼致杨碧薇
“人生是无趣的
若不喝酒,那就更无趣了。”
是的,一个无趣的人,我听到
他身体的仓库正被搬空,开始堆积灰尘
昔日,他也在酒里埋伏,无酒不欢
酒就是兄弟,酒就是情敌
酒就是酒的桃园结义,酒就是柳暗花明下
又一重火焰
可以喝得天塌地陷,气吞山河
可以借酒明心,抽刀断水
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以
酒逢知己……
今夜,饯别是掉在酒里的月亮
所有的美意,在这一刻,都是明晃晃的月光
都是一架轰炸机,穿过远方的地平线
而今夜,也请允许一位痛风患者
说一声:抱歉!
窗外,星空辽阔,夜色冒着酒气
愿顺利,愿皆安!
想起老博尔赫斯
葡萄是从露水醒来的,每一颗
都是翡翠的泪珠
在看守所我又看见了葡萄
它们正在集结生长
而我却像一名拾慧光阴的扫地僧
一瞬间,就想起了遥远的老博尔赫斯
他的雨里,那么多黑葡萄
在葡萄架下私语
谈论着暴雨之夜,北半球的另一端
更多的葡萄平静地腐烂
或被晾干。此时,铁闸将要合拢
我赶紧闪身出来,忍不住
又看了一眼
那些翡翠般的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