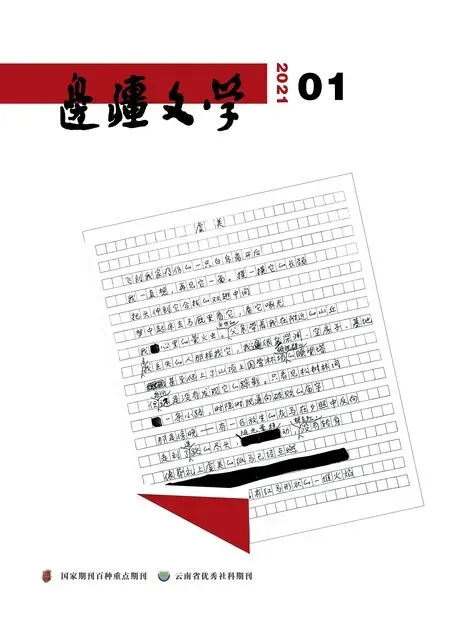怀念伯父杨明 散文
清凉(白族)
1946年前后的昆明,一首题为《死在战场外的中国兵》的长诗,被闻一多先生多次在争自由、反内战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朗诵。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我的伯父杨明。在闻先生被枪杀以后,他没有辜负先生的慧眼擢拔,继续奋斗,成长为卓越的戏剧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人物。
一
大约1935年前后,许多个月末周日的中午,都会从喜洲古镇的南寨门走出一个骑马的长者和两个徒步疾行的少年。两个少年是我的伯父杨明和父亲杨昭,骑马的长者是他们的舅舅,清末举人、教育家,曾任大理中学校长的赵甲南。得到舅舅的资助,兄弟二人得以在大理中学读书,每月回家一次。他们将母亲缝补浆洗过的制服鞋袜打在包袱里,挂在马鞍上,要跟着舅舅走四十里到大理城去。
我的祖母送两个儿子跟着她的哥哥走出富春里时,倚着祖屋的大门心怀惆怅。两个儿子穿的是她亲手打的山茅草和旧布条混编的草鞋,耐穿、柔软,足以走到大理城而不磨破脚。祖母嫁进“杨八郎”大家族时,喜洲人都称道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杨家六世祖杨士云,明朝正德年进士,钦点翰林,至今喜洲还有关于他的“让解桥”“七尺书楼”的传说和遗迹。而我祖母赵家也是喜洲以“父子举人”著称的书香门第。
听着舅舅的马蹄声,伯父和我父亲顶着丽日蓝天往大理城走着,但对苍山洱海巍峨秀丽的风景熟视无睹。他们还从来没有领略过书本上那些遥远的平原、海洋和沙漠,无从与家乡做比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只是一心想靠读书改变自己的生活,憧憬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杨士云后裔中富春里一支,清末民初在18世孙杨公毓桂(字香庭)的带领下,八个儿子勤奋创业,节俭经营,出现过几十年殷实富裕的好时光。但由于经商的能力和运气都有所欠缺,在集中大部分资本进行的一次贸易中,货物和马帮遭土匪劫掠,损失惨重,家道中落。
伯父生来瘦弱,好静不好动,小伙伴捞鱼摸虾放风筝他不参加,以后上中学大学,同学们打球赛跑他只负责看衣服。但他天资聪慧,尤喜读书绘画,深得祖父、父亲喜爱。他小小年纪就已经不满足于熟读四书五经,研习传统书法绘画,开始找旧小说和各种野史传奇看,而丰富生动的白族民间传说和民歌、戏曲也耳濡目染,时时在熏陶着他。
当伯父甜蜜地沉浸在民间的和书本的文学艺术世界中时,杨八郎家的财务状况已渐渐变得困顿起来,孩子们也得要经常面对严峻的生存现实了。我父亲砍柴割草,在喜洲及周边的集市卖过凉水、火柴、香烟;伯父则到下关的商铺当学徒。伯父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
“下关是滇西水陆交通码头,商业中心,风气比较开通。在这里,我不仅学会说汉话,还有机会接触到报纸杂志,也接触了新文艺,知道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谢冰心、巴金等作家。最热爱的是蒋光慈的作品。读到《鸭绿江上》中的一篇描写学徒生活的短篇小说《福寿》时,因身世类似,引起极大共鸣,晚上蒙着被子流泪。从此,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明确的不满情绪,开始不满于屈辱的命运,于是开始模仿着写一点诅咒社会人生的文章,向省城和上海的杂志、报刊投稿。有时刊登出来,兴奋得睡不着觉,好像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伯父这一段学徒生活,终结于1936年的阳历年:“我一大早起来放鞭炮,烫伤了来抢鞭炮的邻家孩子,惹起一场吵闹。这可是触犯了做生意人最大的禁忌。祸闯大了,只好出走。步行十五天,一路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跑到了省城昆明。在昆明,尝尽了人世的酸苦。”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过“有谁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人世的真面目。”伯父后来也曾多次回忆这段学徒经历:起初连一匹绸缎布料、一块铺板都搬不动,但还是什么杂活都要做;劳累一天,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能借着老板房间板壁缝透出的灯光看书。
二
渐行渐近,晚饭时分,远看如一条青灰的横线的大理古城墙,现出了它庄严宏伟的轮廓。在北门口的溪水边——这应该是苍山十九峰十八溪中的桃溪吧,从终年积雪的山顶流下的溪水清澈寒凉,两兄弟掬水洗脸洗脚,丢弃草鞋,换上制服和布鞋。舅父赵甲南在一旁饮马、抽烟。看着自己资助的两个外甥不惧劳苦,英气勃勃,甚是欢喜。不过他未必想到,六十多年后,在他125 周年诞辰的时候,他传世的文集《龙湖文录》会由眼前这个外甥杨明作序,生色不少。
看到小妹妹生活艰辛,两个外甥有辍学之忧,赵甲南自当伸出援手。他安排、资助两个外甥到大理中学就读。在大理读初中的几年,是伯父直接受教于舅父赵甲南最多的时期。伯父在《龙湖文录》序中说:“忆余自幼及长,时从先生就读。先生于余,关爱甚深,教诲尤多,期许殊殷;而余于先生,夙所敬仰,知之甚悉。”
夕阳西下,休整完毕,两个少年虽然饥肠辘辘但精神焕发,踏着舅父的马蹄声。他们一起走进了大理城。
我记得看过伯父那时的一张照片,明丽的阳光,他和一个同学斜倚在谁家的屋顶上,后边的大理古城的房屋鳞次栉比。照片背后题字记得是:你看我们爬得有多高呀!书生意气,风华正茂,跃然眼前。
伯父博闻强记,读书的速度和记忆力令人吃惊:“由于白族语言大量的保留了古汉语的语法、词汇和发音,所以我小时候读古文不觉吃力,比其他许多汉族同学还要轻松自如。因此进了中学以后,我不用像别的同学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背诵古诗文,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中外新文学的阅读上,放在编演新戏、活报剧等等活动上。同时抗日战争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责任感,都成为了自己读书的强大的动力,那些文学名著有时借到第二天早上就要还,我经常是一夜读完,而且铭记久久。而创作的冲动也压抑不住地涌动起来。我的散文、白话诗歌、小剧本已经小有名气了。”
做学徒闯了祸,初中行将毕业,伯父为未来的生计和学费发愁。好在这时他的三伯父杨化中将军决定资助伯父到昆明读高中。
三
伯父和我父亲是得力于杨、赵两个家族的支持,才读完大学的。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李贽的身世时谈到:“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义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简约,积铢累寸……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
1938年滇缅公路还没有修通,肩负家族期望的伯父是跟随马帮从大理走到昆明的。十几天风餐露宿,睡在马驮下看守货物,听赶马人前呼后应的行话,唱山歌,锣锅焖饭,小鹅卵石在油盐锅里滚一下,吮一吮下酒!这些底层生活体验,为他未来的诗歌戏剧创作,积淀了丰富鲜活的细节和语言营养。
随着“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一大批文化精英随一些著名的大学迁至云南,在各个中学里兼职任教的都有不少,这让在读高中的伯父受益不少。他写作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已经开始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并且小有名气。
早在小学、初中时期,伯父就在喜洲和同学杨锡羡、杨朂文等编演新戏,宣传抗日救国和新文明。杨锡羡曾步行十多天到昆明试图参加奔赴抗日前线的滇军六十军。但当他走到昆明时,六十军已经开拔了。1939年初,伯父与杨锡羡、杨朂文三人相约,准备经重庆、西安到延安投奔革命。没想到了重庆,伯父却被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的杨化中将军严厉劝阻。另外两人辗转到了西安,也被抓进集中营。后来杨朂文九死一生逃回昆明,只有杨锡羡一人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三爷爷杨化中将军劝阻伯父奔赴延安,其中一条理由是:你作为才华卓越的一介书生,完全可以在昆明,在文学文化领域大有作为。可以想见在重庆停留到最终折返昆明这段时间,伯父的思想,一定如浩浩长江起伏激荡。
从重庆返回昆明以后,伯父考入中法大学文学院,继续投身于旺盛的文学创作和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中,受到在中法大学兼课的闻一多先生的喜爱和培养。以后几年,他的诗、杂文和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在昆明已影响甚广,他已成为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骨干之一。在轰动全国,惨烈悲壮的“李·闻”案中,闻先生参加“7.15”大会前,伯父亲自安排也是民盟成员的我父亲到闻宅护送闻先生参会。闻先生牺牲后,伯父冒着生命危险,将闻先生最后一次演讲以《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为题,编入《民主周刊》最后一期,直到散发完毕,才转入地下隐蔽状态。
以伯父在古典文学领域研究的天赋,他完全可以成为文史研究大家。他对楚辞研究颇有新意,相关论文得到闻一多、吴晗、游国恩、罗庸等大家的赞许。他早年收集的有关目录学、音韵学、文字学和考古方面的资料、卡片成箱成柜。他晚年重启云南民间戏曲的考察研究,几篇论文再次展现了他的学术功力。他也可以做一个不过多介入政治的诗人,或者出国游学,享受宁静安逸的生活。
但伯父选择的是将身家性命置之于脑后的革命道路。他的笔友、战友唐登岷、张子斋等都是云南地下党的老同志,民主运动中的笔杆子,个个才华超群。在那几年四处奔走、躲藏的日子里,他经常在昆明的背街小巷里与盯梢的特务捉迷藏,在滇缅公路时而搭车,时而步行,曾经翻车时被从货箱上甩了下来,只受皮肉伤,而驾驶室里的师傅和徒弟则滚下了悬崖峭壁,尸骨难寻。
四
云南1950年和平解放,已是云南民盟领导的伯父,感觉自己身为文人应该回归本行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多想,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已经颁发,任命他为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当年体制各省司局一级的任命书竟然还是国务院总理签发),在省文化局,除其他几位党政老领导外,伯父是文化人管文化了。
后来的几十年,既是分工,也是喜爱,伯父一心扑在云南戏曲的改革和创新上。他没有再写新诗,研究过楚辞,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两个他学生时代卓有见地,深得闻一多等前辈赞许,寄予厚望的领域。他整理、创作了几十个剧本,写就了几十篇戏曲论文,许多剧目还是他亲自担任导演,其中一部分获得了国家级的褒奖或拍成电影。后人的若干回忆文章,记述了他写戏、改戏、排戏、改革、创新、提携培养后人的事迹。云南剧协主席、文联主席、“云南文学艺术卓越贡献奖”,他当之无愧。
爱戏、写戏,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伯父最深沉的情愫。伯父在《谈白族大本曲唱腔的艺术特点》中写道:大本曲“只有一人坐唱,一人以三弦伴奏。如此简单的演出形式,听众却那么多,无论男女老幼都聚精会神、鸦雀无声地听着。我那时是六七岁的顽童,看庙戏总是跟同伴追逐打闹,可是听曲的时候,却从不扰乱,总是依在母亲膝上,睁大眼睛,安定地听着。当唱到陈世美不认前妻,场子里就会发出低声的唏嘘,还有人啜泣;唱到梁山伯不辨雌雄,祝英台巧言暗示,机智含蓄的语言,引得年轻妇女低头吃吃发笑,还互相碰碰肘子,扯扯衣角。……唱到祝英台洗手下厨房,做出一道道白族农村传统名菜时,全场活跃,‘坶坶’‘啧啧’之声,不绝于耳。情景历历在目,思之神往。”
1972年暑假,伯父已从蒙自插队落户“解放”回来,领导改编《黛诺》为《景颇姑娘》。他召集李鉴尧、杜桂甲等几位编导者天天来家里“磨戏”,台词、情节和舞台调度,翻来覆去讨论,我在旁边听热闹。他们对戏的痴迷让我知道了什么叫作“戏比天大”。他们有时争吵,有时大笑,茶水一壶又一壶,房间里烟雾弥漫,烟头成堆,揉碎的废纸一篓篓。
伯父迷戏。要继承发展滇戏、白剧、花灯这些当年处于编、演、唱混合一体的草根艺术,既要深谙一般艺术规律,又需要熟悉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及其沿革。伯父身体力行,如痴如醉的钻研、揣摩这些流传民间自生自灭的戏剧形式的特点,强调要真正了解代表性艺人,掌握各剧种不同的音乐传统,熟悉其声腔和表演程式,总之要真正懂得舞台。这些成功的作品和《戏曲艺术丛谈》中的若干篇文章,至今让新老艺术家惊叹、服膺,认为最具艺术和理论价值,是奠定了建国后云南戏剧创新发展的基石。
伯父在云南戏剧文艺界深孚众望,还基于他超强的组织能力和从不把个人名利放在心上,甘为人梯的人格魅力。剧目编创,他总是不辞劳苦深入排练场和大家共同研讨;对同行后进他总是悉心培养,帮助解决的困难;演出、获奖时,他又总是真诚谦让,尽量把其他人推到前台。就连过了许多年后出版《戏曲艺术丛谈》,他还要把收入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充分肯定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贡献。
伯父能团结云南戏剧同仁长期合作奋斗,还在于他有坚韧正直的气节和政治智慧。在六十年代关于历史剧新编,人民性与阶级性的讨论中,他把握原则,和风细雨,鞭辟入里地组织和参与讨论,保护了参与争论各方的积极性,又理清了受或左或右的思想干扰。这对于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繁荣营造了很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文革刚结束不久,依然两个“凡是”,一些“禁戏”重排上演后,又受到上边的打压指责,要伯父“制止”和“批判”,但他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了软拖的策略,没有怪罪下边同志,没有把压力传导给大家。在拨乱反正条件逐步成熟以后,在中央召开的全国戏剧工作会议上,伯父顶着压力,慷慨陈词,两次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讲,并及时在《光明日报》发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戏剧界的思想解放和创作繁荣。瘦弱文静的伯父是有他铁骨铮铮的一面的。
伯父有深厚的国学修养,驾驭文言和白话文字都有匠心独运的能力。他晚年为赵甲南《龙湖文录》所作序言就是一篇情辞隽永,音韵和美的文言文。他用白话文写诗、叙事时,又晓畅明白。他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他舅父赵甲南的思想,其主张“意贵求其真切,辞无事乎雕琢”“我虽雅好古文,但非食古不化者。我之参与提倡语体,重乎内容而不拘形式。要之有思想感情,均不失文学之价值。” 所以在早年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创作中,伯父都极力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1959年他参加了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说看着毛主席抽着香烟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走来走去,用辩证法讲社会主义文艺方针,谈天说地,纵横捭阖。那种渊博的知识,那种严密的逻辑,那种挥斥方遒的气势,使他心悦诚服,决心要竭力践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二为”方针。
在戏曲改革创新中,他认定既要让草根民众喜闻乐见,又要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水平。他在《杨明戏曲集》后记中写道:“在处理传统剧目的思想内容上,我也做过把古人按今天的政治标准拔高之类的蠢事,但在艺术上,记得我是被同志们目为偏于保守的。我自己心中明白,我不喜欢把话剧、歌剧、甚至电影的编剧手法硬搬到戏曲中来。我希望让戏曲还是戏曲,中国戏曲始终要不同于外国戏剧。这也许真是保守的偏见,我的本子都打上了这种偏见的烙印,看起来颇不入时。例如唱词,我也力避‘水词’,但我不喜欢追求‘典雅’,更不喜欢把新文艺词藻往古人嘴里装。因为题材的需要,应该写得更多一些文采,我也宁肯向民歌靠拢,不愿过多堆砌辞藻,有害通俗。因此没有写出一句‘闪亮’的语言,很不入时......戏曲作者至今不为士林所重,我想,这恐怕是原因之一吧。”
正当伯父事业如日中天,那场运动开始了。
五
伯父作为云南文艺界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双栖型领导,自然也会受到运动的冲击。他藏书不少,经过几次抄家,尚余不少内容古奥的文史古籍。去干校的说法渐起。伯父苦笑中一本本挑来挑去,痛如割肉,留下两大木箱珍贵善本,铺上台布充作茶几,其余安排我和多姐搬运到废品站处理。
伯父先是去了“干校”,后来又被下放到大落就公社当了农民。而且他还要带着七十多岁的奶奶,去艰苦的环境中艰难度日。但在简陋的土屋、昏暗的油灯下,他也心态平和地坚持下来,还和当地一些农民交上朋友,真诚的友谊永久保持着。
林彪事件后,政策有所调整,一批老干部被解放,伯父重新回到了省文化局副局长的位子上。但真正的否极泰来是四人帮被粉碎,运动结束。三十年没有写诗的伯父写了几首咏物诗发表在《边疆文艺》,很快又完成了白剧《望夫云》的创作编排,在全国汇演获奖。伯父为了去北京参加会议,他理发吹风刮了胡子,换上了大妈为他新做的中山装,全家都夸他焕然一新,年轻十岁。他也只是呵呵一笑,“你们说少了,局里同志说我年轻了二十岁,像新郎官!”
六
细细想来,伯父一生最推崇的品行就是仁爱谦和,最鄙夷的就是张狂霸道。但他不是单纯朴素的善良和无原则的好脾气,而是基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厚修养。他的座右铭“小曲直长存恕道,大是非不苟和同”,超越了封建士大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经世处事哲理。但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虽然是学者、长者、领导,但却是难得地善良、正直、谦和。和他相处,或长或短,都会让你温暖轻松,如沐春风。
伯父是得闻一多先生扶持才扬名诗坛的,所以他也一贯仁心扶持奖掖后人。
大约1980年前后,为装饰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伯父坚持要用云南画家姚仲华的一幅油画,大气磅礴的玉龙雪山和金沙江,与有关方面产生较大分歧。从云南一直扯到北京,他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主管部门和专家们的认同和支持。这件事,可能伯父回到云南都不会多说,但当时他对我说,这个抉择,对这幅画这个画家还是对云南厅都非常重要,我看准了,不怕得罪人,就是要坚持。
知青作家严婷婷刚刚出道时难免有一些不顺。伯父看到她的作品纯真自然和对生活的感觉敏锐新鲜,觉得是一个有前途的作家的宝贵天赋,于是给予她许多鼓励和支持,帮助她解决了一些工作和创作中碰到的困难。后来严婷婷去美国定居了,伯父还几次说,遗憾遗憾,如果留在国内,写云南写昆明,她应该是最好的。
大理赵勤先生少年就离家当兵卫国,复员后回到家乡喜洲工作,为了促成《喜洲镇志》的编纂,他“冒昧”给伯父写信求助。伯父热情回信,赞扬了赵勤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奉献精神,充分肯定了编纂《喜洲镇志》的重要意义,并且为志稿写了序言。赵勤说,伯父的复信和序言,鼓励着他和同仁们坚持再坚持,终于圆满出书。
七
看着伯父、大妈虽已年迈,依然风仪翩翩,老照片中俨然一对才子佳人,儿孙亲友不禁喝彩:二老当年要是像聂耳一样去上海滩从影,肯定不亚于赵丹白杨。我们当然也会好奇伯父大妈当年的因缘际会。
1942年一个平常的工作日,耀龙电灯公司的材料课长刘剑华,把伯父带到办公室,向已经是骨干会计的大妈韩国珍介绍,“这是中法大学的学生杨明,来勤工俭学,以后就听你安排,帮助你们抄抄写写。”
不知道两人相识,是否会有宝黛初见,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那种戏剧性,但都心生亲切是一定的。伯父当时虽然靠三爷爷杨化中资助了学费,但生活还是拮据,借住在亲戚刘剑华家里,也帮助他看顾房子。大妈聪颖秀丽,刻苦读书,不仅生活完全自立,还在抚育几个弟弟读书。大妈喜爱书法绘画,对戏剧电影,诗歌小说,也都有很高鉴赏水平。一笔恭整挺秀的小楷,据说就是当年考进待遇优渥的耀龙的敲门砖。一个清俊才子小有名气,尽管衣履寒碜,但人穷骨头硬,周围崇拜者中不乏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一个是当年在昆明还很少见的女子高级白领,身边追求者也多是出身豪门的“高富帅”。他们在愉快的相处中越来越被对方吸引,在深思熟虑中越来越明确对方就是自己最合适的人生伴侣。
在小舅(大妈的小弟弟)的回忆中有这么精彩一段:“记得那是1944年,我还在读小学4年级。大姐正在谈恋爱,常带杨明到家里来,我就记得他是个瘦瘦的高个,白皙的面孔,常带笑容,穿一身旧西装,说话很有趣。那时我父亲已过世,在议论大姐的婚事时,有两个从贵州来的亲戚说三道四,说什么杨明长得瘦,他家又不富有,不同意这门婚事。我母亲几经考虑,斩钉截铁地说:‘瘦,怕什么,他瘦得有骨气,国珍嫁给他我同意。’就这样一锤定音确定了大姐的婚事。从此我就叫杨明作瘦哥哥。
再就是1945年初在大姐的婚礼上,闻一多先生是证婚人,在简短的祝贺中,一多先生讲了一句话,杨明突然抱起大姐来转圈,于是来宾们齐声喝彩,婚礼进行得十分热烈和喜气洋洋。”
想象一下,如果这一段拍成电影慢镜头,配上音乐,一定会很美。
八
伯父对精神文化营养,可谓一息尚存,孜孜以求。文革中不被批斗的日子,伯父从收缴剩下的书里,挑着读一些在我看来古怪无趣的书,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巴普洛夫的《生理学》《黄帝内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等。他说写戏要写各种人物各种事情,他在找一些一直在找的答案,有的书几十年前就想读但苦于没有时间。
看书时间长了他就练书法。一只笔一碗清水,就在写字台的桌面上写,写完抹布一擦,造反派来了也看不到。伯父大字承颜体,但有自己风格,云南民族村,腾冲,大理,楚雄,留下的匾联很多,远远一看就是他的字不会认错。
七十年代末,伯父到京开会,常带我去看内部资料片。记得第一次看到《太阳浴血记》《出水芙蓉》,伯父对好莱坞非常熟悉,导演、编剧、明星如数家珍。他看我诧异,说你以为我只会写滇戏、白剧啊,四十年代在昆明,有好莱坞的电影我是必看的。
到了晚年伯父更是懒看山水,总是窝在宾馆里看书。每次他来京开会我都会带一些书供他挑选。最开心的休闲,就是到一辈子爱书如命的我岳父家吃饺子聊天。饺子就酒,两位书生纵论古今,兴味无穷。
伯父善饮,但从不闹酒。碰上豪放张狂的敬酒人,他都从俗照饮。有朋友说,“想不到杨主任文文弱弱,酒量却这么大,回敬我们,不喝失礼,但真喝可就要现场直播了。好在你伯父大人大量,见我们认输了,呵呵一笑就饶我们了。老人家的酒量酒德让我们甘拜下风!”
九
伯父虽住院日久,但最后的辞世还是十分突然。医生说,杨老其实没有什么大病,就是长期瘦弱。如果能多吃一些,健康长寿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他吃口永远那么秀气,到老就更加少食,而且格外怀念奶奶做的喜洲白族家常菜。“自从你奶奶去世后,我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伯父去世前一天深夜,我的一个同学还电话告诉我,刚刚和多姐去看望了伯父,和他聊天,多姐还给他洗脚剪了指甲,情况平稳。然而第二天一早就接到三妹电话,伯父病危正在抢救中。极其衰弱的伯父,生命之火已如残烛,经不起一丝微风了。在最后这段时间,他没有什么具体的交代,一切都顺其自然。他顺从地配合医生,默默忍受各种检查和治疗的痛苦,不愿给任何人多添一点儿麻烦。体力尚可时,他依然看书,平和愉快的聊天说笑,一如既往。
在等待伯父火化的时候,我再次低声诵读伯父的成名作《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几十年前我就看到过这首诗的原版,一本印制粗劣的发黄小册子,还配有版画插图,由西南联大新诗社出版。我当时觉得写的不是上战场的八路军而是国民党的壮丁,还都是大白话,既没有唐诗宋词的韵律,也没有普希金的童话和徐志摩的浪漫,实在不以为然。而此刻我真正懂了,那直白的文字如一块块山间巨石磅礴翻滚,那沉郁愤懑的节奏是一声声农夫悲壮的呼号,伯父把自己的才华和生命,和人民的血肉融合在一起,为他们发出了要生存要民主要自由的最强音。在诵读声里,我又看到了伯父,那个清俊瘦高的白族少年,穿着母亲编制的布草鞋,踏着舅父的马蹄声,走过七尺书楼和让解桥,走出喜洲,走向大理,走向昆明......他的脚步艰难而坚定,他一生心中都充溢着喜悦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