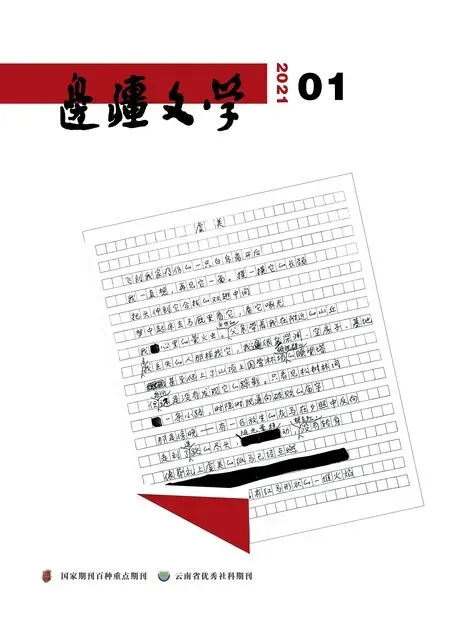酒话 散文
叶芳(土家族)
总之,我爱酒,酒也爱我。
一
小时候,我和弟弟最爱看父亲喝酒。
父亲年轻时酒量大,加之身形高大俊朗,五官深邃,留两撇八字胡,喝酒的样子尤其豪气潇洒。家里来了客,母亲麻利地搜罗出几个菜,无非就是炒腊肉、炸干洋芋片、摊个泡蛋等。那时候家里哪有什么菜,多半是洋芋换着花样吃。反正不管吃什么,总有一个炉子锅儿在桌子上煨着。
父亲的朋友多半都能喝酒。比如我的班主任——我父亲的亲表弟谢叔、我家的邻居冯叔、再旁边的邻居长友叔叔,还有开酒楼同时又当了好多年医院院长的张伯伯,以及他的哥哥另一个张伯伯等等。时隔多年了,我依然可以想起来好多好多和父亲喝酒的人。也难怪,父亲喝酒的日子数不胜数,可以说,我就是在父亲的酒桌子边长大的。父亲喝酒的时候,和他的朋友高谈阔论,大多数时候以吹牛为主,反正很少有提及现实的话题,总是从某一点小事开始,喝着喝着,话题就扯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了。
有一次,他们说自己喝酒之后的糗事。向叔叔讲在沙道街上喝完酒,趁着月色回十多公里之外的××中学,在枪毙人的杨仕桥头上转了一整夜没找到回去的路。我听得背后一阵阵发麻,连忙把凳子往大人身边挪了又挪,生怕背后的黑暗处有鬼。我父亲说:“有一回我从龙潭骑自行车带着娃儿回沙道,中午喝的酒,下午到屋就睡,晚上小明(父亲对母亲的称呼)回来问娃在哪里去了,我吓得半醒,但是大半夜又到哪里去找呢?干脆继续睡。第二天早上,我和小明去找,我芳儿在老百姓屋里一点事都没得!”我母亲边给锅里打鸡蛋添菜边说,“你睡得么子都不晓得,我哭一夜,你看你骑的么子车,娃儿掉下车了你都不晓得,你还晓得把车骑回家?不晓得你醉成哪号的了……”母亲是舍不得用脏话骂父亲的。那一年我6 岁,被父亲从任教的××中学载着,天擦黑的时候,在离镇上3 公里的杨仕桥,把我颠掉在石子路上,毫发未损,那地方传说鬼都打得死人。
父亲的故事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我们也从前一个故事的恐惧中一下子就跳跃到欢乐中。父亲就是那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地方,在他的眼里,可能是另外一种色彩。多数时候我把它理解成豁达,成年后多了一些别的理解,比如避世、高傲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父亲说到兴头上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凑到了他身边,好像别人吓得破胆的杨仕桥,我和父亲都不怕一样,甚至有一点当了一回小英雄的得意。父亲见我仰着头看他,就用筷子头蘸了一点白酒喂给我。好辣呀!但是我没喊出来。父亲又蘸了更大的一滴酒喂我,我强忍着火烧一样的痛苦笑着将酒就吞了进去。这娃儿可以啊,有点酒量哟!宾客们一阵胡夸,我便飘飘然了。那一夜父亲他们喝完酒又通宵打牌,直到第二天家里恢复寂静的时候,家里的酒肉味和烟味还久久未散,父亲在书房沉睡,母亲去鞋厂上班了,只有我和弟弟,孤零零的在家待着。那,便是我对于父亲喝酒最早的记忆。
二
我大伯在医院边开了镇上最大的一家酒厂。
他的性格极其孤僻。我们老家说一个人不好打交道,叫“隔”,大伯的外号叫“叶隔老儿”,一街的人都晓得。
大伯怎样子从非常偏僻的渔泉河里到街上去安家的,我无从知晓。而且大伯娘是街上出了名的能干人,不晓得木讷的大伯是怎样认识和善、外向的大伯娘的,又哪里来了娶她的福气。他的酒厂开在临大路的一面,用圆石块垒砌了一堵弧形的围墙,围墙上爬满刺槐。那条路,是通往沙道中心小学的必经之路,刺槐开花的季节,孩子们总要忍着被扎手的危险,以及被叶隔老儿发现后更大的危险,悄悄摘几串雪白的刺槐花。他们猫着腰悄悄摘花的时候,我和弟弟就大摇大摆地拣开得最浓密的摘几串——然后在他们诧异的眼神中扬长而去。大伯的名声在外,小孩子们都怕他。那时候传说医院的公厕里丢了很多私生子,我们只要在那里上厕所总忍不住偷偷对粪池看,要是谁看见了鼓鼓包包的不明物,一定会添油加醋地说真的看见了被丢弃的婴儿。但是相对于厕所的鬼故事,对大伯的害怕却是更加众所周知的,毕竟谁也没有在粪坑里见过有鼻子有眼的婴儿,可是那个又黑又胖从来不笑的叶老头,几乎要天天见面。
酒厂门口铺满煤渣子。厂外原是一条泥泞路,若是雨天,我们上学路过那里,鞋子袜子打湿是小事,倒霉的是在密布的水坑里摔跤,裤裆都是稀泥巴糊糊,才叫丑。后来,大伯用煤渣填了路,那条路变成了一条“黑路”,却因煤渣滤水,下雨天晴走起来都利索。煮酒的年头越来越长,煤渣子就越铺越厚,越铺越宽,就像有人用手蘸着墨水围绕酒厂画圈,里面是黄色的酒厂,中间是白色和绿色的槐花,外面就是一圈一圈的黑色,笔画很粗,有点国画的味道。有一年学校填操场,老师叫我们从家里带土,我和弟弟怯生生地向大伯讨煤渣子,大伯爽快地叫我们班上的人都去撮。那天,酒厂的大门敞开,孩子们像蝴蝶一样飞进向往已久的禁地,然后欢快地飞进飞出。我和弟弟的班级很快完成了任务,老师表扬了我俩,那件事后来让我和弟弟骄傲了好一阵子。
酒厂地势低于路面。推开两扇大木门,进去右边,有一口方形水池,刺槐枝条在池子一角撑开了一架天然的绿棚子。池子里喂着大鲤鱼和大金鱼,黑色的居多,白色和黄色的几尾尤其漂亮。左边有一撮圆形的木房子,形状有点像鄂温克族的撮罗子。木屋里面除开一口椭圆形的大木缸,再无他物。煮酒的时候,大量的蒸汽凝成热水,一条花线粗细的水流通过水管引入木缸,正好用来泡澡。冬天在家里洗澡往往冻得够呛,我们乐得去酒厂洗澡。特别是半大孩子的时候,家里的木盆小了坐不下,站着洗又冷,蹲在盆外面又舍不得那热水,着实尴尬。在酒厂洗澡,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时辰几个时辰,也没有人催你,每次泡到全身发软、肚子饿瘪了才起来,全身舒爽。那个年头,我好多同学耳朵根子、膝盖弯子都是黑的,我猜多少和洗澡有些关联。
酒厂的房子是人字形房脊,又高又敞亮,里面十分空旷。房子一头,有一尊巨大的甑子。地下是一排发酵酒糟的方形深坑。每个坑里面的酒糟都不一样,有的盖着薄膜纸,薄膜纸上挂满水珠;有的敞开着冒着热气;有的已经凉透了。每一口酒糟池都插着一支温度计。刚出酒的糟子闻着喷香,黄澄澄的,一粒一粒鼓胀着,有时候我忍不住剥一粒吃,味道很酸很淡,并不好吃。
酒快出酢的时候,整个厂房里弥漫一种奇特的香味,那种味道介于酒糟的酸腐和白酒的辛辣之间,一会儿清淡,一会儿刺鼻。味道越来越浓,逐渐就有粮食的味道出来,那是一种经过发酵、烤制、蒸腾,熟透了的味道。焦香味、软糯味,还有从玉米芯儿出来的拔着丝的甜味,以及土地长出粮食的甘苦,山地农民扒着石头缝刨食的辛劳和委屈,似乎全都在里面,简直妙不可言!
大伯和二伯接头酒的时候,我最爱蹲在地下死死盯住出酒的口子,和他们一起期盼着,常常看得入了神。很久很久之后,终于有一滴晶莹的酒珠子沁了出来,逐渐变大,变亮,变重,终于挂不住了,晃悠悠地滴落进酒缸中,发出瓮声瓮气的响声。而后,滴滴答答的密了,后来就牵成细丝,再后来,就像泉水汩汩地往外冒。大酒缸接满后会用厚实的裹着布的盖子封好后窖藏起来。后来在初中历史课堂上,我常常将那一排一排的酒缸同秦始皇兵马俑作比较,试图体验相似的肃静和庄重。
偷吃酒糟和酒是我的老把戏。有一回快出酒的时候,二伯正在将酒糟装车了送到猪场去,手头忙得很,他便交待我和弟弟守在甑子前等着。这样的好事我们好久盼不到一回。出酒的时间无法预测,我俩时不时将手伸到龙头下探几下,指头并得紧紧的,生怕酒猛地出来了自己没接住。后来,手酸了,我们干脆一屁股坐在龙头下,仰着头候着。蒸馏酿酒法,头锅酒一开始度数低,尔后逐渐增高,所以接酒的时候要边尝边接,度数合适了才能要。我心里想着,到底要接多少了才用酒桶装呢?正在犯疑的时候,酒出来了,我连忙张开嘴接了一口,啊!好大一股煳味子,我“噗”地一口吐在地上。弟弟连忙也接了一口,也“噗”地一口吐了出来。酒还在冒,手边没得工具的我们,只能用嘴接一口,用手抔一捧,你一口我一口,每一次都要尝一下,忙得一团糟。我清晰地记得酒下喉的感觉,仿佛一条火龙向里面钻,酒往下走的时候,我顺着它走的方向用手在身体上抚摸拍打,只想将它按住。等到一点煳味子都没有的时候,上好的苞谷老烧终于出来了。二伯回来的时候,一坛酒刚好快要接满,而我和弟弟靠在酒坛子上,酣睡如泥。
三
“喝酒从来不醉的人,不能做朋友。”这句话,被我奉为信条。
大约十六年前,我喝了最多的一回酒,和我的两个闺蜜。那时候宣恩城里流行喝饭泡酒——把白酒用白米饭浸泡一会儿了再喝,说是口感更好。我和两个闺蜜的关系,是铁三角,铁到什么程度呢?她俩曾经帮我抡着扫帚一起当街打架。那时候,我已从前夫家的豪宅搬出来,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她俩比我小,都生得如花似玉。之前我宽裕的时候,吃啥喝啥我们仨总是在一起。我落魄后她俩想帮衬我却又力量不足。过了一段时间,华在恩施谈朋友了,到恩施工作去了。艳和我依然留在县城,靠代课混日子讨生活。
七月我生日,华从恩施赶了回来。下午我们仨走到大桥头上,一屁股在青石板上就地坐下,然后开始发呆。向晚的太阳还有几分毒辣,双龙湖水库被紫红的晚霞笼罩,像皇后头顶的华盖和皇冠,很是奢靡。行人不多,要是有美女过路,我便像流氓一样吹口哨撩几下。美女一般都会骂一句“妈×,有病!”然后我们便神经质地放肆大笑。华是一个假装腼腆的人,躲在我和艳的身后小声说:“你两个莫搞咯,别个以为我们是癫子!”我和艳于是又一阵大笑。
在街上逗留一阵后,我们决定去林业局对面的地下夜市吃东西。华说她同学经常去那里吃,她同学经营文具店,比我们的社会经验丰富得多,不像我们,完全是涉世不深的菜鸟。从五金店门口一个被栏杆围起来的进口往下走十几步梯子,就到了店内。大瓦数的白炽灯泡明晃晃的,刺得人睁不开眼。夜市里面有大约五六张桌子,挤挤挨挨的,中间有简易的隔断。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后,老板咋呼着走过来要我们点菜,于是点了几样小菜。老板问:“喝不喝酒?”华和艳一起望着我。“不喝不喝!”“喝!”“喝一点吧!”我们给出三个不一样的答案。最后,还是由我拍板。“有么子酒?”“饭泡酒,好喝得很!”“怎么卖?”“20块钱一盆。”“好,来一盆。”我们三个从学校出来就在教书,没有接触过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周围桌上的那些男男女女见我们点酒喝,都停下筷子,将胳膊杵在桌上,斜眼乜着我们。我仿佛听见他们心里的疑问:耶?有点意思哈!这三个小姑娘是么子来头?同时又感觉我们就像落入土匪窝的三个小娘子,有一种即将被抢去做压寨夫人的危险。显然我们与这环境格格不入。
那天的一盆酒,分配不均,我喝了五杯半,艳喝了三杯,华喝了大半杯。虽然是闺蜜,性格各自不同,喝酒也不深劝。然后,我醉了三天,呕出了血水。艳和华醉没醉,我不知道,也没问。倒是她俩给我送的生日祝福,我至今记得:“自己开心就行了,别的不要想那么多。”
十年前的春节,我发癫,一个人开着车去椿木营玩。
我以为椿木营像城里,餐馆和酒店大年三十都营业。到了才发现,完了。各家各户关门闭户,大雪封山,天色已晚。我掏出手机,用最后的一点电联系一个老家在这儿的同事小玲,希望她能找个开店的熟人,让我去打个尖。她说,你真的是,三十两夜,哪个还开门啊!要不你去我姑姑家吧。我婉言拒绝,毕竟是过年,我宁可在车里箍一夜,也是万万不会给别人找麻烦的。几番推脱,小玲突然想起来我侄女弦子的夫家就在镇上,刚好今年他们在老家过年。
弦子是我大伯叶隔老儿的孙女。去她家,虽然更加不好意思,但是自然是无法拒绝。弦子的公公婆婆,按照辈分就是我的亲家,不到六十岁,十分能干。家里还有奶奶,八十高龄。高山人家,一个回风炉子烧着,一家四代老老小小围坐在一起,暖和又热闹。一会儿工夫,亲家母烧了四个锅儿,一锅野味、一锅土鸡子、一锅猪肚,一锅牛肉丝,还有若干小菜,菜的周围摆满了糖食果饼,很是排场。陪我喝酒的是亲家公和女婿。椿木营的人礼节很大。我一个人吃,他们一家人都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堆成小山一样,稍微吃几口下去,立马又给你夹,生怕怠慢了。奶奶抽的是旱烟,女婿给我装的是中华烟。那一晚,我们吃喝闲谈至深夜,外面风大雪急。第二天拂晓我悄悄离开了。院子里我给弦子的儿子——我的外孙子,堆了一个雪人,那是我送给他的新年礼物。
下面要说的就是小玲了,她留给我的是一个终生难忘的跨年夜。
2013年元旦,晚9 点我约小玲陪我宵夜,她欣然前来。从她做决定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注定要江湖留名,虽然她至今都拒不承认其中的某一些情节。
我们宵夜的地方是宣恩县最著名的定发市场大排档。一排排胶棚子,夜夜灯火通明,人声喧嚣。毕竟是在县城混迹多年的中年妇女了,轻车熟路地点了一堆招牌菜——烤猪尾巴、烤鸭头、糊汤豆皮、臭豆腐等等。隐约记得那天我们喝的是衡水老白干。我问老板要玻璃杯,老板说没有,要喝就是一次性塑料杯。小玲说,哎呀,不需要那样讲究的。于是就开喝。第一杯喝完,小玲想上洗手间。老板用手一指,二楼有个网吧,你们去吧,给网管说是在我这里宵夜的客人就行了。我看小玲脸蛋绯红,之前听说她很少饮酒,于是决定陪着她去。网吧很大。进去七弯八折才找到吧台。台子后面一枚小鲜肉,身高八尺,肤白貌美。小玲朦胧的眼神一下子就变清亮了,她笑吟吟地问:“帅哥,请问一哈你们洗手间在哪里啊?”帅哥用韩剧中男主角的语气回答:“呶,那边就是!”我一看,就在大门边。小玲好矜持地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向洗手间。完事后,无视近在咫尺的大门,绕了一大圈回到吧台,气质优雅地说:“谢谢哈!”此后的几个小时,这样的情节重复上演,不超过半个小时,美少妇的屁股就坐不住了,非要去洗手间。去了以后先打招呼,再跑到洗手间门口捂着嘴偷笑,然后洗手出来去感谢网管,搞到后面,干脆连洗手的戏份都删除了,搞得我这个作陪的人都害臊。
大约到凌晨一点吧,天气凉了一些,周围只剩两桌人了,棚子里安静了很多。喝到3 杯的时候,我俩又加了几个菜,爽性吃闹。突然,小玲猛地把桌子一拍,一声断喝:“嘘!我俩声音小一点!”我望着她不敢出声。“日妈你看我两个都戴着眼镜,认识的人就还好,要是不认识的人肯定会骂。妈×,这两个货只怕是小姐,半夜还在外面浪,现在也是拐了,当小姐的还戴眼镜装×!”天啦!此话一出,我瞬间感受到周围人的眼光像箭一样射过来,我的脸唰地一下全红了。
5 杯酒以后,已是凌晨2 点半左右,小摊的老板明显有收摊的意思了。另外两桌客本来早就要结账走的,但是又希望看我们的表演,也死撑着眼皮下蛮捱时间。老板很大声地问我们:“今儿我们做活动,生蚝烤一打送一打,你们这几桌客要不要啊?”“要!我给我公公老汉儿和婆子妈带点!”美少妇第一个举手答应。我说要得,还加点么子别的一起嘛!然后掏钱准备补差价。这时候——“咚!”小玲又把桌子猛地扇了一巴掌,“不行,生蚝不行,吃了我婆子妈今天要吃死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旁边几桌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爆笑,其中有一个嘟囔着:“还没醉嘛,晓得生蚝是好东西!”
酒品见人品。酒这个好东西,带给我无数次的温暖回忆。这么多年,我喝酒认识的朋友甚众,成为挚交的不过几人,以上所记均在其中。总之,喝酒从来不醉的人不行,总是醉的人,那也不行。
四
“明家梁的酒,我从来就没喝够!”夸下这个海口的是我父亲。女婿走丈母娘屋,从来没有人敢说这个大话,嘎嘎(外婆)和舅舅却由着他说了几十年。
父亲和母亲很早就订婚了,大约只有几岁吧,反正舅舅说,我父亲开始给嘎嘎拜年的时候,腰杆还没有火坑火塘深。嘎嘎把父亲当儿子,宠了几十年。母亲在家里被唤作“八妹”,那是她的排行。嘎嘎一共生养了十几个孩子,只活下来两个,母亲曾告诉我,有一次一天之内死掉两个,早上饿死一个,下午病死一个,嘎嘎整天整夜地哭,眼泪就没干过,后来就没有眼泪了。
父亲考起学后没资格去读,成分不好,于是就在大队当老师。大队学堂开在我大嘎公外公屋,和嘎嘎屋共一条阳沟,两支屋一正一横,中间是个很大的院坝。那时候父亲和母亲是朝夕相见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美人,皮肤很白,梳着两条大辫子,脸颊有一片淡淡的雀斑,深眼窝,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有点像高加索人,那时候叫长得乖,现在叫异域风情。母亲嗓子清脆,搞“三治”的时候,是文艺小分队的积极分子。唯一不足的是,母亲左下巴靠近脖子的地方,有一枚硬币大小的黑痣,母亲为此很是介怀,但是我认为那丝毫不影响母亲的美貌。父亲自不必说,身架子高大,浓眉大眼,总爱手捧一本书,谈吐举止有别于一乡青壮男丁,很是儒雅俊逸。我曾经在看电影《1980年的爱情》的时候幻想过父母亲的故事——17 岁的教书先生和18 岁村花的爱情,实际上那种爱情在我父母之间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候的母亲肯定是很爱慕父亲的,她早早知道那个让多少姐妹眼红的人,按照媒妁之约便是她未来的夫君。可是父亲从心里只是把她当姐姐的——父亲曾经说过,他很多年一直以为母亲就是他亲姐姐,关于身世,他知晓得很晚。
1978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也是巧,一般去拜年的时候都落大雪,去的时候全程下坡路,从父亲的家陶家崖出发,经过亲山里、苕洞边、山外、张家坡、奚家屋后头,几脚路就到了嘎嘎屋。父亲走最后面,我和弟弟在中间,前面是背着背篓的母亲——农村话说的是,“鬼打前,狗咬后”——山路荫蔽,土狗凶恶,白天父亲总是拿着一根打狗棍在后面压阵,走夜路的话,父亲则是在前面挡着。父亲是从来不会背背篓的,他觉得做家务的男人是最没有出息的。当然,如果换成一满背篓的土豆和红苕,父亲还是会背的,他觉得那是做农活,不一样。拜年货通常就是那几样,一块巴掌宽的信(腊肉)、一把面条、不超过十沓糍粑、两包白砂糖、一瓶梨子罐头,还有一盒饼干。大雪足足没到了我们的膝盖。咔嚓咔嚓,父亲用脚趟出一条道来。他走过的地方,会留下一枚枚整齐的脚印,胶鞋或者皮鞋底子上的花纹清晰地拓在了雪地上。我会努力将每一步都印在父亲的脚印上走,这样子省力,而且在小女孩子看来,就像一个游戏一样有趣。弟弟就不同了,他是满山钻。看到巴茅草在雪下面鼓出来一个包,他要踢一脚,看到哪里水凼结了冰,他要跺几脚,不把冰踩碎他是不得放过手的。有的冰很厚,他就用脚跟拼命地跺,冰破碎的时候,稀泥巴浆子溅得一身,少不了讨母亲几句骂。骂归骂,即使父亲走出好远了,母亲也会插着手站在那里等弟弟玩尽兴了再接着走。大人说外坎有时候是泡雪,下面是空的,走不得,弟弟偏不听,遇到缺口扑通就踩空下去了。父亲这时候会眉头紧皱着看他爬起来,一言不发。母亲边给他拍满身的雪沫沫边说:“幺儿,幸好是旱田,要是冬水田你今天就拐了,你爸爸要打死你!”
到嘎嘎屋之后的晚饭,舅舅和父亲一定会喝酒,气氛热烈。父亲一般会讲时事、镇上的新闻,还会安排两家人5 个娃读书的事。舅舅说的,全部是他的业余生活,比如上山赶仗围堵两火枪才打死一头野猪,差点被野猪咬伤;下河捞鱼抓到的娃娃鱼十几斤重嫌它不好吃直接丢掉;套竹鸡的时候怎样模仿竹鸡的叫声。至于农活,他不屑于讲,别人种土豆的时候他栽黄连,别人栽黄连的时候他种百合,别人撵着他的屁股跑,他玩玩哒哒都比别人的收成好一大截。舅舅比父亲年长13 岁,两人经常是说得对方哈哈大笑。舅舅对父亲的宠一般看不出来,看菜你就晓得。桌上有野鸡肉、野猪肉、猪脑壳肉、海带炖耙肉、老母鸡炖黄豆、猪脚杆炖豆腐等等。父亲爱吃发臭的猪脑壳,据说炕肉的时候,猪脑壳上有一块臭骨,要是不抠就会臭,别人家都会抠掉臭骨,嘎嘎屋年年都把猪头肉炕臭了等着父亲。那时候野物多,一般人却难吃到,而舅舅是方圆几十里最厉害的猎人。其实舅舅岂止是打猎厉害,他还会木匠、篾匠、铁匠,他做哪样像哪样,无师自通,简直是聪明绝顶的一个人。
父亲对哥嫂的敬重那也是心里有数。舅娘出身于大户人家,一手好茶饭、一手针线活、一手农活,手艺盖几个村。舅娘身高一米五左右,背重东西百把斤不在话下,和高大的舅舅一起做农活,一起出门一起放工,从没见过她有半点吃力。舅舅家擦脚的毛巾,比好多人家洗脸的还要白净。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在农村看见过比我舅娘更能干的女性。以至于姑嫂之间要是有半点嫌隙,父亲一定是会压着母亲的。
父亲最引以为傲的是舅舅三个孩子的名字全是他取的,大哥清文、二哥清乐、姐姐娉妤,而且他还亲自教过他们,所以他们既要称呼他为老师又要喊他“姑爷”。大哥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年,因为感情受挫,一下子跑到内蒙边境被边境公安扣押了。那是八十年代初,二哥和姐姐分别在高中和初中读书,舅舅把家里最值钱的大黄牛卖了,由父亲带着他去接大哥。那时候的绿皮火车很慢很慢,他俩买的硬座,父亲说经过山西的时候忘记关窗户了,打个盹醒来,桌上的茶缸子被煤灰埋成了一个锥形的小丘。把保释人的钱和路费扣除后,再没多余的钱,为了驱寒,父亲和舅舅一路买高度散酒喝,没钱买别的。父亲说同车厢有个蒙古大汉,袍子里似乎藏着吃不完的羊肉,蒙古大汉用匕首片羊肉吃,吃一片喝几口酒,火车走了几天他就吃了几天,硬是把舅舅和父亲的眼睛都欠直了。舅舅家出事后日子一落千丈,可是酒还得照喝。他俩将找大哥的故事在酒席上摆的时候,几桌人听得耳朵都竖了起来,而我们在舅舅和父亲脸上竟然看不到半点的伤心和难过。
嘎嘎、舅舅和舅娘像待上大人一样,待了父亲25年。按照我舅娘的话说,姑爷在他家喝了25年酒,虽然酒没喝好,但是硬是没格外他。
后来再过了些年。去舅舅家拜年的时候,换作我和弟弟陪舅舅喝酒。舅舅照例只喝大半杯。酒到深处,舅舅只说一句:“你爸爸呀,这辈子离开你们,是他做过的最大的错事!”父亲离家17年来,我从未在父亲和舅舅口中听见他们说对方半个错字。舅舅和母亲早年丧父,吃过千般苦受过万般罪。舅舅比母亲年长12 岁,兄妹俩与外婆相依为命,走过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艰难岁月。以舅舅的眼光和父亲的人品,舅舅原本指望将妹妹托付给这个姑爷,肯定是稳妥的。后来我父母之间的变故,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嗯,舅舅喝酒!”我闷声应着,弟弟抿着嘴,将酒杯子举起来给舅舅敬了一下,一饮而尽。
五
恐怕我真是得了爷爷真传,除他之外,家族内,就我喜欢打冷疙瘩了。冷疙瘩——就是有酒无菜,不论时间,想喝就喝。
酒和菜,本该是密不可分的。
大约是二月底的一天,我在社区参加门岗防疫执勤。帐篷外走来一位老爷子,要出小区去购物。门卫问他,“您的通行证呢?”“掉了。”“那您需要买么子啊?您没有通行证不能出小区,要不,我们去帮您买可以不?”“我啊,别的我不买,就是想打2 斤酒。”老爷子说话一口东乡腔,语气颤巍巍的,听起来很有一把年纪了。正是疫情暴发期,小区五百多户人家的采购几乎全是超市配送,这位大爷竟然冒险出来买酒,真是奇人。正在登记的我听闻此言,一下来了兴趣,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出帐篷细瞅。老爷子穿着长短几件夹袄,须发全白,看起来像是在儿女家过春节的农村人。“爷爷您好大年纪啊?”“七十八。”“您一天喜欢喝酒啊?”“嗯,喝了一辈子。”“一天喝好多呢?”“一餐二两,早餐减半,一天半斤。”“您喜欢喝么子酒?本地酒还是瓶子酒?”“就是散装酒,那个叫三个么子的啊,蛮好。”“‘三峡’是不是?那个酒不贵,口感是还可以。”老爷子见我问话越来越到点子上,眯缝着一双浑浊的眼睛问我:“这个妹妹,您戴着口罩我也不晓得你的年纪,未必您也喝酒啊?”我赧颜一笑,没做回答。在保安去给老爷子买酒的空当,我给老爷子搬来一把凳子坐着等,两老少一直聊些喝酒的闲话,很是投机。我说假设超市没有您儿要的酒,我就回家取点自己泡的酒送给您喝,不料老爷子却断然拒绝,然后掏出一沓钱来,吐了点口水在手指上开始点,大约有几十张红版版,然后是五十的,十块的,压得平平整整,不晓得在荷包里揣多久了。边点钱他嘴里还边说着:“给我分个2 斤那是可以。红土的酒我晓得,那是好酒,就打20 一斤,2 斤40 元。送给我喝,那我不得要!”我心里打算着,虽然我也不富裕,但是几斤酒还是送得起的!正说话,保安回来,买了3 斤酒,20 元找回2 元,老爷子欢喜地提了酒走,2 元打赏给保安做路费。他走远后,物业经理悄悄问我,“你不认识他啊?他就是我们小区开发商吴总的父亲!他家里不晓得好多茅台五粮液,老爷子不爱喝,他说散酒喝惯了。”额!我一下子噎住了。那个开发商,曾经因为我参加小区的车位维权在前年的正月初一将我家断水断电,我是恨不得吃完这个“资本家”的肉,哪晓得今天,我这个房奴还要去给他的父亲送酒。我觉得自己的脸分明被扇了两耳巴子,觉得自己真是好不识相。老爷子批评我的话声犹在耳:“我和你不同,第一我一辈子不喝冷疙瘩,没菜也要喝,伤身体,酒没得命重要;第二不要钱的酒我从来不喝,不好喝。”这老爷子果然是道行深,我猛地想起某一刻他那鹰一样的眼神来,当真是老辣得很。呃,活该我穷。
我的爷爷一辈子爱喝冷疙瘩。爷爷的胞兄当兵去了台湾,爷爷多受牵连,曾被打成“走资派”。爷爷娶过三位奶奶。第一位奶奶生了我父亲难产逝去。第二位奶奶体弱多病,生养儿女四个。第三位陪伴他的晚年。爷爷从小学老师退休后,看书写字抄经书,自得其乐。爷爷的鹰钩鼻遗传给儿孙三代,想必他年轻的时候很是英俊。我常与爷爷说笑,他说我的脸盘子和奶奶一个样子,就是身架子没得奶奶高坯。爷爷临终前几天的一个中午,父亲那辈和我们这辈在医院旁边的餐馆吃饭,大家破例喝了一些酒。到病房后我逗爷爷:“爷爷,您看我们屋里哪个喝酒狠些?”爷爷抬起重重的双眼:“我的儿孙,没得一个孬的。”随后说:“我这个病,几黄缸药也是治不好的。你们还不如让我喝口酒呢。”父亲他们商议后,让爷爷喝了几口冷酒,爷爷喝酒之后窝在枕头里,一反常态的平静安详得很。自始至终,我都记得爷爷打冷疙瘩时,那满足的神情,仿佛生活,从来没有亏待他半分。
“我的身体里面肯定住着一个酒鬼,是这个背时的酒鬼要喝酒,不是我想喝酒。”我在微信上和朋友戏言。庚子年春,封城封路封小区。几个好酒之徒建了一个微信群,有时间的时候便视频喝酒。群内7 位网友,清一色的美女帅哥,有在一线直接参与抗疫的,有在单位值守的,有困在家的。群内公约,每次喝酒的量是白酒半斤以上,啤酒6 罐以上,必须用透明的带刻度的杯子喝,不扯酒皮,不谈工作。群内唯一一位老板是军哥,喝酒扯酒皮是他的老习惯,曾经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参加朋友聚会,清点酒瓶子的时候我的6 个瓶子被他偷了4 个。他每次开视频的第一句话就是:“给你们报告一下哈,我没等你们,我已经走一个了哈……”最热闹的是阿登,他吃饭的时候,身边依次坐着3 岁的大儿子、1 岁的小儿子和他妻子,每次视频一开,他两个儿子比他还要先喊我:“姨,干杯!”然后阿登“咯嗤”一下吃一口葱,递过去,大儿子吃一口,辣得眉头一皱,再递过去,小儿子也吃一口,辣得揉半天小鼻子。三爷子吃着闹着,一顿酒几个小时,弟媳妇在镜头边边上不说半句,贤惠体恤,羡煞一帮兄弟。其余阿超、阿荣、小玲、日成便不赘述,反正都是耿直人。一众伙计拉扯着喝了小一个月后,有一天,不晓得是谁刷存在感,突然提议说大家晒晒菜晒晒菜。这一晒,军哥家吃的卤鸭脖子卤猪尾巴;阿登家吃火锅,小黄鱼羊肉卷火腿肠金针菇土豆香菇等,荤素12 个菜;小玲的老公是大厨,况且公公婆婆在县城有小半条街的祖传房产,吃的牛灿皮炖白萝卜、土鸡炖山药、半汤甲鱼等等,很显然,家底子厚,一家7 口人吃喝几十天之后的菜依然是那样的扎人眼睛;阿荣吃的腊肉烧豆腐;我吃的酸辣草鱼。我们一番显摆之后,日成和阿超就是不切换镜头,嘴里说:“没得看场,没得看场。”他俩越是抗拒我们越是不依不饶。好嘛!他俩被迫秀了出来。阿超的桌上,一盒泡面、一包花生米、一罐豆豉鱼罐头。日成的桌上,一袋饼干、一袋兰花豆。群内的气氛瞬间变化。阿超在县城工作,疫情发生以后40 多天一直没有回州城的家。日成在乡村卡点执勤,本来他刚结束一轮值守可以回家轮休一天,但是考虑到家人安全,他没回家。我们之前笑称这个群叫“酒群”,过几天又改成“睡衣群”“酒窝群”“荷尔蒙群”等等,我们一天插诨打科,笑傲江湖,谁也没想到,摄像头翻转的那一刻,生活似乎一下就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来,喝!”不知谁在群里邀请了一句,大家一饮而尽。当“岁月静好”与“负重前行”真真切切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默契地选择了绝口不提。
大约一周以后,疫情到达爆发期,我家的菜又一次微微末末的了。下午6 点半,兄弟们在群里喊喝酒,我也懒得进厨房,切了一盆地瓜就和他们猛喝了一顿。趁着酒劲,胡写了一首诗,他们嘲笑我,说我想我男人了,竟然搞起冷疙瘩了,我说:“下酒菜下酒菜,么子菜下酒,那是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法,姐姐我就爱搞几口冷疙瘩,怎么,你们羡慕嫉妒恨啊?”酒话照录如下:
好酒的女人
木瓜泡酒
枸杞泡酒
拐枣儿泡酒
刺梨泡酒
老蜜蜂泡酒
杨梅泡酒
家里酒多、书多,腊肉多
男人被隔离在另一个小区
我和他之间
隔着一条江
一座桥
无数楼房
每天下午喝酒之前我在酒坛子前逡巡
如同威严的老皇帝开始翻牌子
这段时间独宠刺梨儿
每天半斤
不醉也不清醒
昨天刺梨儿被喝干了
一代美人就此香消玉殒
我要留着这个坛子
泡什么呢?
对了
把这段时日泡着吧
庚子年
正月初一到二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