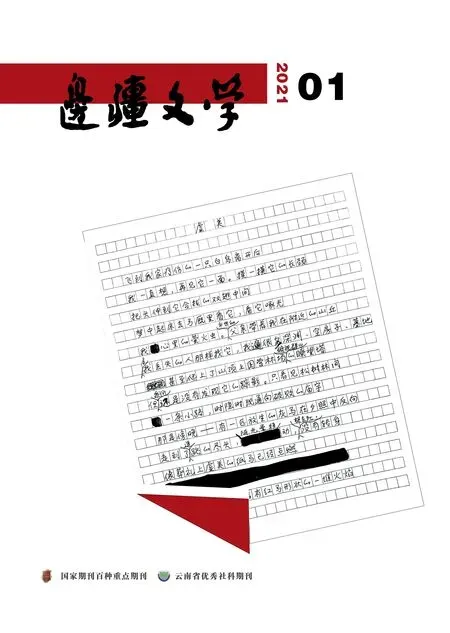读与被读 随笔
刘文飞
十多年前,我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在耶鲁大学访学,一次偶然在耶鲁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上看到一句醒目的短语:“Read or be read !”翻译成汉语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被大家阅读!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这其实就是我们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我们存在方式的全部!
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即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即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如果有,那他也只能是上帝了,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的开头一句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英文版《圣经》中,此句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在俄文版《圣经》中,此句为:“В начале было Слово,и Слово было у Бога, и Слово было Бог.”英、俄文版本中的“道”字皆为“词”,而且是大写的“词”,于是,《圣经》中的这句话又可以翻译:“太初有词,词与上帝同在,词就是上帝。”
不读却能被读的人,只有上帝。
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即知识分子。“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即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即文人时带有的敬意。当然,在中国社会某些特定语境下,读书人及其称谓也可能遭遇麻烦,比如十年动乱时的“臭老九”,比如战乱时的“秀才遇见兵”,但特殊时代或特殊场景下文化人的窘境,其实又恰好凸显了文化人的特殊性,即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野。西方也早有“书人”之称谓,如英文中的bookman 和俄语中的книжник。《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提及的“文士”,俄文版《圣经》中用的就是“книжник”,直译就是“书人”,而英文版中用的却是“scribe”,直译就是“抄书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即“书虫”(bookworm,книгоед):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吞噬书页,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谓。这一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
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自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莎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却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一切后果。
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所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
一个读不读书的人,一个喜欢不喜欢阅读的人,是可以从他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读小说的人,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肌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被读就是他的外衣,读就是他的内衣。
读与被读都是一种对话方式,一种交流手段,同时又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是一种独处。工作学习时大家围坐在一起读报纸,这不是阅读,至少不是有效的阅读;儿童会聚在一起看小人书,但这种方式很少持续到他成年之后;钢琴演奏时会出现两人四手联奏,但两位读者脑袋贴着脑袋始终同步地把一本大部头书从头读到尾,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即便这两位读者是夫妻或情人;现在的学术论文有多人合作,有的论文甚至会署上长长一串十几个姓氏,但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却鲜有多人合写的,除了《诗经》这样的合集。
读要自己去读,一个人独自地读,写也要自己去写,一个人独自地写,读与被读于是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就像寺庙中的修行,教堂密室里的祈祷。与此同时,读与被读又是一种最渴望交流的举动,都充满对各种可能的奇遇之期待,都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远握。世界上不存在对作者一无所求的读者,恐怕也很少对读者无动于衷的作者。苏联时期曾有“抽屉文学”之说,指一些作家深知自己的作品内容有“异端”倾向,一时难以发表,但他们依然继续写作,为抽屉而写作,但激励、支撑他们写下去的动力又恰恰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的作品有朝一日终将面世。后来,在20世纪下半期苏联社会的宽松时期,如解冻时期、改革时期,这些作品果然纷纷浮出水面,有些还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中的杰作,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将写作行为等同于向茫茫大海投掷漂流瓶,因为,“理想的读者只存在于后代”。读者和作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非共时性关系,构成了读与被读之间一种强大的张力。
多年前,一本翻译过来的理论书籍很走红,书名叫《语言的牢笼》,作者是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詹姆逊先后就读于哈佛和耶鲁,后在杜克大学任教。1985年,他应邀来北大做系列讲座,在北大校园内外引起轰动,相当于在中国“科普”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十几年后他再度来华,在华东师大讲学,所受到的关注已无法与当年相比,似乎,他传播到中国的后现代解构意识已在中国得到了心领神会的接受。不过,詹姆逊毕竟是一位在中国很有影响的西方文论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由王逢振先生主编的洋洋十四卷的《詹姆逊文集》。詹姆逊是一位很会写书的理论家,至少很会为他的理论著作取名,他几本著作的书名都很别致,如《时间的种子》《政治无意识》《黑格尔的变奏》《侵略的寓言》等,但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还是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这其实是一本研究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相当枯燥的理论著作,但题目本身,即“A Prison-House of Language”,却构成一个绝佳的隐喻,这让我们意识到:语言是牢笼,你所掌握的语言原本是你与世界交往的工具,可是在你掌握了一门语言之后,这门语言却反过来构成一种限制和束缚,把你死死地关在里面。读与被读都是语言行为,因此都与语言的牢笼不无干系,如果说,阅读是在主动地为自己营造一座舒适的牢笼,那么写作就是一种试图打破这座自我牢笼的不懈尝试。所谓“阅读圈”,是读者的画地为牢,但也是读者为自己构建的一片自由思想的天地;所谓“影响力”,是作者的自我放大,但也是作者为自己构建的一座自我重复的透明宫殿。读与被读,都既是自我空间的营造,也是对这一空间的突破,与这一空间的抗争。读与被读,因此也就成了世界上最为自由的行为,至少是最富有自由精神的行为。
20世纪40年代,纳博科夫先后在美国的卫斯理学院和康奈尔大学为学生开设文学名著选读课,他的一次导论课讲稿后以《好的读者和好的作者》(Good Readers and Good Writers)为题发表。在这堂课上,他向他的学生们传授了这样三个阅读秘籍:
首先,在阅读时要留意并把玩细节。纳博科夫所用的“把玩”(fondle)一词在英语中还有“抚养”“爱抚”“抚摸”“抚弄”等意,常用来表示人的一种“爱不释手”状态,比如抚摸情人、摩搓古玩、把玩宠物等。读书就是读书中的细节,而不应带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不该抱有了解世界的愿望。纳博科夫还提及他在一所偏远的学院讲座时给听众们出的一道测试题,他列出一份“好的读者”必须具备的十个选项,让学生们从中任选四项。这十个选项是:
1、参加一家读书俱乐部。
2、认同作品的主人公。
3、关注某一社会经济角度。
4、推崇有情节、有对话的故事。
5、观看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
6、做一位初学写作者。
7、有想象力。
8、有记忆力。
9、有一本字典。
10、有一定的艺术感。
纳博科夫给学生们揭晓的答案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最后四项,其他都无关紧要。同时具备这四个选项的读者,就是纳博科夫心目中的“好的读者”。这个标准其实是很高的,一本字典不难拥有,但同时具有“想象力”“记忆力”和“一定的艺术感”的读者可能就不太多了。
其次,他认为阅读必然是重读,必须是反复阅读:“一位好的读者,一位大读者,一位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读者,就是一位重读者。”所谓“重读者”(rereader),就是一遍又一遍阅读的人。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读一本书,也不可能一生只读一次书,因此,重读必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纳博科夫此处所言的重读,却可能既指读者对某一本书的反复阅读,也可能指读者阅读行为的一次次重复,更可能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创造性,即一次又一次地回味阅读体验。读书不似看画,无法一览无余,需要读者自身的想象建构,“在我们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阅读的时候,我们对一本书的态度就近似看画了”。在这个时候,读者就很接近作者了,读与被读的距离就开始缩小了。
最后,“一位读者应该具有、或发展的最佳气质,就是艺术气质和科学气质的结合”。过于冲动的艺术气质会使读者在对待一本书时过于主观,只能用科学的冷静判断来冲淡火热的直觉,如果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激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享受伟大的文学的。也就是说,好的读者既要冲动,又要冷静,既要天马行空,又要明察秋毫。
说到好的作家,纳博科夫认为他就是那个大喊“狼来了”而身后并没有跟着一只狼的男孩。文学就是发明。文学就是虚构。文学就是那个骗人男孩的幻觉。一位大作家是集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人,即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教师(teacher)和魔法师(enchanter):讲故事的人带来娱乐和精神上的兴奋,教师给那些未必高明的读者带来道德教育和直接知识,而“伟大的作家永远是伟大的魔法师”。
纳博科夫这堂课是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的:
一位大作家的这三个方面,即魔力、故事和教育,往往会合成为一种统一、独特的华彩印象,因为艺术的魔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中,思想的精髓里。有些杰作具有风格平实、条理清晰的思想,但它们在我们身上激起的强烈的艺术冲动并不亚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或狄更斯富有感性意象的任何一道丰沛水流。我认为,就长远来看,衡量一部小说之质量的最好公式,即诗的精确和科学的直觉之合成。为了能沐浴魔力,一位聪明的读者在阅读一部天才之作时,不是用他的心在读,也不完全是用他的大脑在读,而是用他的脊椎去读。
1988年5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布罗茨基在意大利都灵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怎样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他一开始就抱怨,书比作者更长寿,“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它们的作者活得更久”,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比作者占据着更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一把尘土之后,他的书还常常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不好的书,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需的标准。(俄罗斯作家巴别尔也说过相近的话:“人一生其实并不需要读太多的书,读上七八本好书就足够了,但在读到、读懂这七八本好书之前,你又不得不阅读成千上万的书。”)一位读者要想读到一本好书,则必须培养起良好的阅读趣味,而这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那片海洋上,四面八方都有书页在沙沙作响,你紧紧抓住一只你对其浮力并不太信赖的木筏。因此,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去发展你自己的趣味,去构造你自己的罗盘,去让你自己熟悉那些特定的星星和星座,它们无论暗淡还是明亮,却总是遥远的。然而这需要大量时间,你会轻易地发现自己年岁已老,头发花白,腋下夹着一本糟糕的书正向出口走去。
于是,布罗茨基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他还为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读者两手都捧着翻开的书,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小说,他会首先放下哪一本书呢?十有八九是小说,因为他左手上的书比右手上的书更轻。
像纳博科夫一样,布罗茨基后来也离开祖国俄罗斯来到美国,在美国的大学里讲授文学课;像纳博科夫一样,他也不懈地向学生灌输个性化阅读的重要性,把读与被读视为确立个人存在意义的唯一方式。他的朋友、美国达特默斯学院教授列夫·洛谢夫在其所著《布罗茨基传》中写到布罗茨基当年的授课场景,并归纳道:“诗人在向学生们解释这些东西时,首先获益的却是他自己。”布罗茨基当年的一位学生后来也回忆说:“布罗茨基把我们这些学生领进战场,可是他却不打算代替我们作战。”
读与被读,说到底还是自己个人的事情。
阅读是功利性的,中国人对此有许多露骨的表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当然,这里的“读书”主要指的是接受教育,为仕途之路做好准备。当然还有另一种功利,即所谓修身养性,更注重于自我的精神需求,如果说“黄金屋”是一种物质欲望的象征,那么,阅读的精神功利性则表现为试图在自己内心构筑“象牙塔”或“乌托邦”的隐秘愿望。与阅读相比,被读的功利性显然更强,或为了物质利益,如畅销书作者,或意在青史留名,如发愤著书的司马迁,或试图教谕世人,如晚年的托尔斯泰,完全没有任何目的的写作行为是不多见的。就行为的目的性而言,写作远胜过阅读,因此,阅读可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写作反而成了一种被迫,就这一意义而言,被读较之于阅读,作者较之于读者,也未必具有多少天然的优势或优越。
广义的阅读无处不在,一切能被眼睛看到的东西,包括文字在内的任何符号,都是阅读对象,阅读甚至超出目光所及,比如盲文,比如黑暗中的歌声,比如梦中的场景。如此看来,阅读其实就是身体的所有感觉器官对一切信息源的接受。另一方面,我们通常所言的阅读又是十分具体的,多指对文字的阅读,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对经典的阅读,读《成功学》《炒股大全》《减肥秘诀》《操作指南》等似乎都算不得阅读。如此看来,读与被读,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具有文学性文字的读与被读,指文学作品的读与被读,尤其指文学名著的读与被读。每一民族文学中的名著都是该民族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积淀,是该民族的文学想象力和艺术智慧之结晶,往往代表着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准和审美传统,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学名著的价值和历史地位是绝对的;与此同时,文学名著又往往是后天的,是追认的,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和作者沙里淘金的结果,因此它又是相对的。一个没有文学名著的民族就难以被称为高度文明的民族,一个没有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的民族就难以引起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尊重。对于本民族的后代读者而言,名著具有巨大的文化塑造意义,一代又一代后人的世界观、生活观和美学观,往往就是在阅读本民族文学名著的过程中形成的,发展的。文学名著的地位可能是有起伏的,有些名著的地位可能会随着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焚书坑儒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相反的例子也有,即那些被埋没的名著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重新浮出水面,成为新的经典。
名著的历史命运取决于特定的时代,也取决于它的每一个读者,每一位接受者,在接受美学理论兴起之后,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名著的这一属性,即它也是某种民主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学者尧斯在他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1969)一文中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即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只能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而实现的过程就是作品获得生命力的过程,就是作品功能的最后实现。读者是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主动角色,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性质的制约,也受读者素质的制约。也就是说,作者完成一本书,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创作过程的结束,只有当它被读者阅读之后,这部作品才完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从作者到文本,再从文本到读者,这才是一部作品完整的接受过程。读与被读,从此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读者的地位空前提高,几乎与作者平起平坐了。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莎士比亚的读者都可以成为部分的莎士比亚!读者也是作者,是部分的作者,是作者的延续和补充,是作者之后的作者。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读与被读之间的区别由此变得模糊起来,甚或合二为一了。
很多大作家都曾言及阅读的温馨和温暖。托尔斯泰说:“一本好书,就像与智者的一次交谈。读者可以从书中获得关于现实的知识和概括,以及理解生活的能力。”笛卡尔说:“阅读一本好书就像是与过去年代最智慧的人物交谈。”然而,读与被读也是一场场残酷的竞赛。这是读者与作者的竞争,阅读一本书,就是在与它的作者进行智慧的较量,读者读了一半就扔下了书,表明这场竞争有了输赢,或是读者主动认输,即读不懂,无力继续与作者对话,或是读者看穿了作者的老底,不屑于再与他为伍;读者在读了之后一遍遍重读,则表明读者和作者的较量是一场马拉松,读者试图在某一次长跑中接近作者,甚至超越作者。阅读,也是读者与读者的竞争,大家阅读同一本书,却总有不同的收获,这就是阅读竞争分出的胜负,更何况,对不同的阅读对象的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阅读,不同读者之间的高下也会立马显现出来,因为阅读作为一个从“编码”(encode)到“解码”(decode)的过程,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是猜谜,是博弈,是智者与智者的对话。而作者和作者之间的竞争更是你死我活的,既生瑜何生亮,一个天才的出现就意味着其他众多潜在天才的夭折。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写过一本书,题目叫《汉堡排名》,他借用一个传说,说汉堡的拳击手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内部比赛,在放下窗帘的密室里通过比武排好座次,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大家都会遵循这个结果,他认为,作家们之间的竞争也是这种行业竞争之结果,是内行之间的比试。为了被读,被更多地阅读,作者们是需要使出浑身解数的。
有这样一句拉丁语谚语:“要提防那只读一本书的人。”只读一本书的人可怕,可能因为他读得少,没有知识,因而粗鲁蛮横;也可能因为他读得专心,读得执着,因而令人生畏。
阅读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犹太人家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会在孩子稍微懂事的时候在经书上滴几滴蜂蜜,然后让孩子去舔一舔。这种仪式的含义不言而喻:书是甜的。当然,书也可能不甜,也可能是苦涩的,可能是五味俱全的,更有像鸦片一样诱人的书,像酒一样醉人的书,像药一样苦口的书,世上有多少种滋味,就有多少种味道的书;有多少种味道的书,也就有多少种读书的人,也就有多少种写书的人。
然而,读与被读又毕竟是一种向善的事业。布罗茨基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指出:“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阅读可以使人成为有感情的人,成为善良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断言: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读与被读,都是人类最广义的善举。
读与被读都是一个自我塑造过程。对一本书的阅读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读者爱上的每一本书,往往就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座路标。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反之亦然,写什么样的书,就会暴露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文如其然,书如其人,你写出了一本书,你也就完整地把自己展示给了所有人。读与被读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即两者都是在寻求自我,形成自我。
阅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俄国作家罗扎诺夫在他的《落叶集》中写道:“书应该是昂贵的。”相比物质食粮,我们的精神食粮无疑是便宜的,一个人一生买书的钱肯定少于他用于维持一生物质生活的开销。索尔仁尼琴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很多人都会在清晨花上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健身,却很少人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健脑,也就是阅读和思考。读与被读都是时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消耗,生命的消耗,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人们用于读与被读的时间则差异更大,读与被读在人的生命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往往就决定着一个人生命的品质,至少决定着他精神生活的品质。
语言能力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曾被作为区分人类和动物的主要依据,可是生物学家后来发现,许多灵长类动物都有使用,甚至制造工具的能力,也有它们独特的语言,如此一来,读与被读,至少是文学意义上的读与被读,可能就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了。
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在上世纪80年代访华,他在听说了一个个关于中国翻译家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坚持翻译的故事后十分感动,写下《中国翻译家》一诗,他在诗的结尾写道:“要为无名的翻译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
一个读者身后墓碑的高度,应该就是他读过的书摞起来所形成的高度;一位作者身后墓碑的高度,应该就是他写出的书摞起来所形成的高度;一个文人身后墓碑的高度,应该就是他读过的、写出的书加在一起所垒成的高度。我们经常称赞某人“著作等身”,却很少称赞某人“读过的书等身”,“读万卷书”似乎才是一件可以夸耀的事情。需要读多少书才能写出被读的书来呢?读过的书和被读的书之间会构成怎样的比例呢?这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但这两摞书之间的高低差异也肯定是巨大的,这两者间的比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位文人的读写习惯和存在方式。
读与被读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一件相伴终生的事业,你吸入的最后一口气就是读,你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就是被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