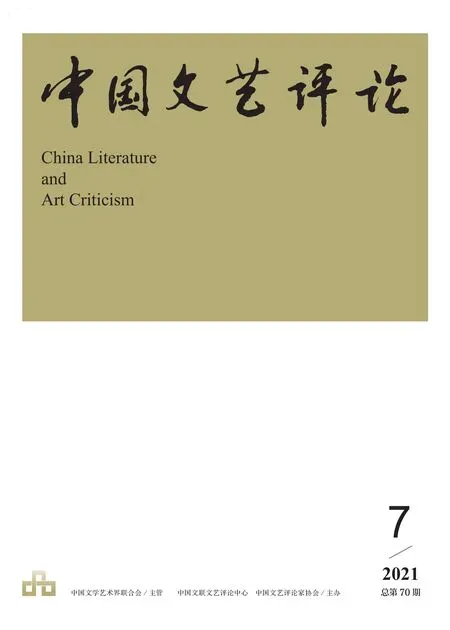中国古代艺术的意象之美
毛宣国
意象美学是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意象作为一个美和艺术本体的范畴其内涵如何界定上,以及意象如何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进入到现代美学体系中。实际上,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经验的总结。要理解意象美学的魅力,让意象美学进入到现代人审美视野中并发扬光大,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各种艺术类型的意象审美特征的把握,离不开对传统艺术意象之美的魅力的感悟。基于此,本文主要选择书法和水墨山水画这两种充分体现中国艺术韵味和精神的艺术类型,探讨中国古代艺术的意象之美,并兼及论述中国古代其他艺术类型如诗歌、音乐、戏曲等的意象美创造,目的不止于让人们感悟到审美意象的创造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共同特点,更重要的是把握不同艺术类型审美意象创造的独特意味及其对于中国美学的意义。
一、中国书法艺术的意象之美
书法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常被视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熊秉明将书法称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林语堂亦认为“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书法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中心,与汉字的书写方式分不开。汉字的特点是象形表意,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人那种主客一体、亲近自然、注意整体关系、意在言外的思维特征,同时也使汉字发展成为一门特殊艺术,即书法艺术。
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再加上书写工具的原因,中国书法艺术本质上亦成为一门意象创造的艺术。从甲骨文开始,中国文字就具有了象形写意的特征,它构成了中国书法意象美的文字基础,这种象形写意来自于自然。中国古人对此有深刻的悟解。汉代书论大家蔡邕在《九势》中有“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之说,即指出了中国文字的意象之美来源于自然,体现了自然界中阴阳两种力量的变化与协调。在《笔论》中,蔡邕又提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自然界的水火云雾、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都是文字取法的对象,与自然界真实的物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南朝书画家袁昂非常善于以自然物象来比喻书家的艺术风格,如云“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等等。唐代李阳冰、蔡希综、韩愈等人论书法,都非常重视书法的意象之美与自然物象之间的联系。如李阳冰的“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即把自然物象作为书法意象之美创造的基础。
将物象作为书法意象之美创造的基础,并不是要求书法单纯地摹仿和仿效自然,而是要求书法家以物象、具象的形式表现出书法家的精神情感与生命气韵。宗白华谈到元代大书法家赵子昂的创作时,说他写“子”字,先习画鸟飞之形,使子字有着鸟飞形象的暗示;写“为”字时,习画鼠形数种,穷极它的变化。不过在赵子昂的笔下,“子”字和“为”字都不仅仅是对自然界形象的摹仿,“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中国书法对物象的书写在本质上是超越物象的,不是“象”而是“意”,构成了其灵魂所在。
中国书艺历程的演变也说明了这一点,它经历了一个由尚象向重意的转变过程。早期的汉字,无论是甲骨文、金文,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是“尚象”的,重视对生活中具体事物进行摹写。商周时代书法的群体风格倾向即是尚象,如金学智所说:“商周时代书法美的尚象倾向,最典型地反映在金文作品里,其中一个个字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奇古粗野的姿态,光怪陆离的形象。”“商周书法不但结体取物尚象,而且其整体的章法风格,在形式上也各随字形大小,使人顿生‘百物之状’、‘各各自足’(米芾《海岳名言》)之想,‘各尽物态,奇古生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之感。”这种状况到了汉代,随着小篆和隶书文字的兴起并走向高峰有了改变。裘锡圭认为:“从商代文字到小篆,汉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断降低,但是象形的原则始终没有真正抛弃”,而到了隶书,则“不再顾及汉字象形原则”。这里说的“不再顾及”,笔者的理解是隶变之后的文字的象形意味大大减少,并不是根本抛弃“象形”的原则。这种转变,改变了汉字与事物直接对应的象形关系,在表意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于是,汉代也成为创立字体最多的时代,如飞白、草书、行书等,它们都指向“意”的表达自由。
中国书论中有“晋人取韵,唐人取法,宋人取意”之说,其实都是指向“意”之表达的。王羲之论书法极其重视“意”。“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意”在王羲之那里,成为论书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其评价书法作品最重要的标准,书法艺术正是因为有了蕴含于点画之间的意的表达,才具有了非言语能够表达的书写自由。唐代书论大家张怀瓘亦将书法艺术引向“意”的层面。他言“意”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书法意象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如《文字论》中提出书法艺术“可以心契,非可言宣”,《书议》中提出“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二是突出书法意象之美的精神气韵,如其所说的“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于飞动”,即是如此。“尚意”是宋代书家普遍的追求,无论是黄庭坚的“书画当观韵”、米芾的“真趣”和“意足我自足”说、董逌的“笔意”论,还是李之仪的“凡书精神为上”、晁补之的“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等,都将“意”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对“意”的推重,最典型的代表是苏轼。苏轼的诗论、画论都很重视“意”,于书论则更为突出,如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称赞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无点画处而意态自足”等。宋代书家对“意”的普遍重视,标志着中国古代书法意象美的创造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不再是点画形态的形似摹仿,而是以书家的心性情趣与精神气韵成为中国书法意象创造最核心的内涵。孙过庭曰:“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法是“本乎天地之心”的艺术,它的字势结构和点画形态,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生命的存在。它的存在,也不在于再现客观事物的美,而是“同自然之妙有”(孙过庭语),以大千世界为观照对象,遗其形迹,取其神质,从根本上表现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中国书论家重视“意”,但“意”不可能脱离“象”,必须以“象”为载体,对此,中国艺术家有明确的认识,于是锻造出“意象”范畴。“意象”观念表现在书法理论中,早在东汉蔡邕那里就开始了。他提出的“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的观点,此中“象”是取法自然物象的意思,也可以看成是“意象”的雏形。后来传为卫夫人《笔阵图》的“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张怀瓘《六体书论》中说的“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等,都发展了蔡邕的观点,将“意象”看成是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元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杜本首先将“意象”一词引入书论,其《论书》曰:“夫兵无常势,字无常体: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倘悟其机,则纵横皆成意象矣。”对“意象”本体特征作出最全面阐释的是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他提出“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的观点,辩证地阐释了书法意象创造中“意”与“象”的关系。“意”是指书法家主体创作的情意,它是根本,是第一位的;“象”则是主体情意落实到方寸之间的笔墨表达,它是“意”的载体,是第二位的。“先天”和“后天”原是易学的术语,刘熙载将其引进到书论中,认为书艺创造也有先天后天之分,即“意”在先,“象”在后,这与传统的“意在笔先”的书论观点是一致的,强调“意”对于“象”的优先性,强调落笔成象之前主观情意的重要性,这是符合中国书法艺术特点的,也是由重象转向重意的中国书艺美历程的真实写照。
谈到书法艺术的意象之美时,还必须注意到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的不同特点。中国古代有“书画同源”说,如何良俊所言“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是也”,即它们都是从“象形”这一起点发端的,都具有图画性的特点(特别是早期汉字甲骨文、金文、篆书等)。“同源”即强调书法与绘画的相通,对此,晚清书论家周星莲有高度的总结概括:“字画本自同工,字贵写,画亦贵写。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故曰:善书者必善画;善画者必善书。”不过,书与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此,郑樵《通志•六书略》中有很好的论述:“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郑樵指出了书与画之间存在的差异,即画的“象形”是取形,比较实,书的“象形”是取象,比较虚,所以书法艺术较之绘画艺术更多变化。虽然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有“以形写神”“神似”“意似”之说,但“形似”在唐代以前的绘画理论中一直都是受到人们重视的,郑樵的“画取形”之说也是对这一观点的一种概括。而他强调“书取象”,则将书法艺术看成是一种超越形似,在本质上追求意似神似的艺术,这是符合书法艺术特点的。他用“画取多,书取少”来区别二者,意在强调书法艺术较之绘画艺术,是更加简约、更加追求意似神似、更加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意味的艺术。
追求写意神似这一特点又决定了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重视线的艺术表现力,其在本质上可以看成是线的艺术。金学智说:“中国书法是最典型的线的艺术,它一不靠色彩,二不靠光影,三不靠团块。它的一切,纯粹由线条组成,是一个线的王国。”中国古代有“八法”之说。“八法”即书法之“用笔”,宗白华认为它构成了书法艺术的笔画之“势”。他说:“中国人用笔写象世界。从一笔入手,但一笔画不能摄万象,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之‘势’。”中国书法艺术是重视“势”的艺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张怀瓘曰;‘作书必先识势,则务迟涩,迟涩分矣’。”康有为可以说是从宏观视角揭示了中国书法艺术重视“势”的传统,从微观上看,“永字八法”的每一笔都是一种“势”,“势”亦是线条不同的表现方式,其长短粗细、轻重徐疾,点画撇捺的流转变化,都构成了书法意象表现的“势”。中国书法意象的“势”和线条之美,不仅通过用笔,而且通过结体与章法表现出来。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每个字的结体优美,收放相宜,而且章法布白更是讲究,前后相管领,相接应,有主题,有变化,全篇中有18个“之”字,每一个结体不同,“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暗示着变化,流淌着线的韵律。可以说,书法艺术是用线条表现出来的笔画与结构。章法布白的“笔势”和“体势”构成了书法意象的美,这种美用宗白华的话就是“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中国书法艺术的美即是人心之美与万象之美的统一。
二、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意象之美
中国绘画也是高度重视意象美创造的艺术。中国古代意象美学的许多重要命题都来自绘画理论。中国古代绘画主要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型,无论哪一种画,笔墨、线条都是基本要素。这决定了追求“意似”,重视审美意象创造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东晋的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以形写神”的命题,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气韵生动”的命题,都代表着对绘画艺术的审美意象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南朝绘画理论随着山水画创作的兴起,亦出现了像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这样的作品,提出了在自然山水之间何以实现“澄怀味象”“澄怀观道”,如何通过山水“畅神”,得山水之趣灵的问题,强调山水画与实用性地形图的区分,强调山水画的创作与欣赏不再是服务道德、伦理的实用性需要,而是“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以山川形胜感动人的心灵,创造出生动有致、富于审美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这些看法可以说都深化了人们对于绘画审美功能的认识,促成了中国绘画审美意象理论的系统形成。
水墨山水画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美学意味的艺术。水墨山水画是纯用笔墨不用设色的山水画体,是以最自然、最本色的东西创造出一个以形求神、抒情写意的世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人那种与天地相始终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中国古人那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维语)的宇宙意识和人生情怀。它的意象之美突出指向了意境审美的层次,水墨山水画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艺术最具有意境美学意味的艺术类型之一。
水墨山水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山水画和文人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隋唐是山水画发展的重要时期。吴道子是人物画大师,张彦远对其评价时曾说:“吴生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所”,“这种重线条而不重色彩的基本倾向扩展到山水领域,对后世起了重要影响”。另一位人物则是王维。王维山水画以“破墨”为主要画法,《历代名画记》评王维画的特点是“破墨山水,笔迹劲爽”,“破墨”即用比较浓的墨(水墨)来渲染画面。中国画唐代之前重视设色,画山水用勾线,王维开水墨之风气,“一变勾斫之法为水墨渲染”,并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观点,对后世水墨山水画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另外,王维山水画多平远构图,富有诗意,这也对文人山水画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五代也是山水画发展的重要时期,荆浩、关同、范宽等人的画多是大山大树的全景式的水墨山水画。董源、巨然等在山水画上追求平淡天真的笔墨趣味——“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趣”,“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更是为文人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可以说,水墨(文人)山水画的基本理念和规范在隋唐五代就基本形成,文人画的兴盛与高峰却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代表着文人画的高峰,也代表着水墨山水画的高峰与艺术成就。
李泽厚用“宋元山水意境”一语来概括宋元山水画的美,笔者认为非常到位。不过,他特别推崇元代绘画,认为其中包含着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文学趣味的异常突出,二是对笔墨的突出强调,三是水墨画压倒青绿山水,这一判断则不太准确。应该说这三个要素宋元山水画都具备,只是到了元代绘画中达到高峰。早在唐代,王维的水墨山水画体现了诗画兼通的审美情趣,而这一点到了宋代为人们普遍推崇。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都将绘画与诗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有着精神的一致性。欧阳修认为画应具有“萧条淡泊”之意,画家应有“闲和严静,趣远之心”,这既是对中国绘画也是对山水画提出的最高要求,正是来自他的诗学主张。苏轼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的观点,亦是将绘画提升到与诗一样的崇高地位。正是对绘画的诗意和文学性的要求,使得宋元山水画摆脱了以前的山水绘画那种形似与写实的风格,转向对笔墨趣味和神似写意风格的追求。李泽厚说:“对笔墨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它说明“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亦即笔墨本身”。为什么中国山水画以水墨山水为代表,用徐复观的话说,“这是和山水画得以成立的玄学思想背景,及由此种背景所形成的性格,密切关连在一起”。并不是说设色山水画(如青绿山水)不美,但与水墨山水相比,设色山水舍去了中国绘画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艺术家与自然的接近。水墨是最朴素的颜色,它可以超越于各种颜色之上,作为各种颜色的母色,所以也是最自然、最能表现艺术家精神意趣的颜色。也可以说,水墨山水画最典型地体现了老庄之学的山水悟道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亲近自然的精神,所以它以最纯净的姿态呈现出中国画的笔墨趣味与意境美。
中国水墨山水画的笔墨趣味与意境美表现,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淡”的意境。董其昌论及文人画和南宗北宗之分时,特别提出了“淡”的标准。他提出,“质任自然,是之谓淡”,“淡”就是一任自然,就是天真、不用意,不饰雕琢。可以说,它构成了水墨山水画意境表现的基础。这一标准最早见于宋代诗论,梅尧臣作为宋代诗风的开拓者,提出的标准就是平淡——“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而后成为诗论、画论、书论的普遍标准。山水画审美,自然更是以“淡”为宗。董源、巨然等在山水画上追求平淡天真的笔墨趣味,沈括称其为“淡墨轻岚为一体”,“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淡”就是用疏淡自然的笔墨表现出令人悠然神往的艺术意境,如沈括所评价董源、巨然的画那样:“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近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所以它为文人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规范。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亦是“淡”的意境美的典范。它表现的是画家最熟悉的景色,即杭州以西富春一带的山水:坡岸水色、峰峦冈阜、飞瀑清泉、山村小桥、渔舟人影以及散落着林居亭台的河岸,在一幅长达七米的山水长卷中自然呈现,看不见画家的精心构撰,只有其自由兴趣徜徉其间,却又是那样令人神往和意趣悠然。中国山水画家“以水墨为上”,追求“淡”的意境风格表现,亦包含着中国山水画家对宇宙人生的最朴素理解,“平淡而山高水深”(黄庭坚),“至平至淡至无意,而实有所不能不尽者”(恽向),“淡”不仅表现了画家与宇宙天地的生命相通,更传达出艺术家的主观情绪与心境。正是在简淡水墨世界中大道之美得到了观照,所以“淡”与“简”相联系,代表着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就像我们从倪云林山水画中所见到的那样:“几棵小树,一个茅亭,远抹平坡,半枝风竹,这里没有人物,没有动态,然而在这些极其普遍常见的简单景色中,通过精炼的笔墨,却传达出闲适无奈,淡淡哀愁和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沉默。”
其次是“逸”。“逸”也是水墨山水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逸”本来是指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逸”由人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转向书画领域,最早见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有“高逸” “横逸”一类品评书画的话语。不过,真正将“逸”作为品评书画的最高标准则是从北宋黄休复开始的。他在《益州名画录》中将画分为“逸”“神”“妙”“能”四品,“逸”则处于最高品级。他所谓“逸”即是“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之意,亦可以看成一种师法自然、不拘一格的艺术创造。它不为笔墨所限,又不露笔墨之痕,所以水墨山水画成为最好的表现形式,如清代恽格所言:“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逸”的意境风格亦是画家主观心境、气度人格最完美的表现,它在倪云林的画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比如,他的代表作《幽涧寒松》《容藤斋图》等,画面上常常只有几株枯树或寒松当风而立,另外就是一个茅亭,或几个土丘,远处是平缓并不显眼的山坡,树枝的枝叶稀疏,但是很有性格,在一片空寂、荒寒的境界中显示出孤傲与不屈。这些画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即是倪云林自己说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它是中国古代士子文人精神气节和胸襟人格的写照。
再次是“远”。它也是中国水墨山水画着力表现的一种意境。早在魏晋时期,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就有“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宗炳《画山水序》就有“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迴”之说,皆是论“远”。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则有“山水咫尺万里”,“咫尺间山水寥廓”,“工画山水,平远极目”之说,亦是以“远”为宗。正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北宋山水理论大家郭熙明确提出“三远”的概念,认为“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
“三远”说即是对水墨山水画意境表现的很好概括。对此,徐复观说:“郭熙所提出的三远,乃山水画发展成熟后所作的总结。因为作者对于山水,是以远势得之,见之于作品时,主要是把握此种远的意境。而远势中山水的颜色,都是各种颜色浑同在一起的玄色;这种玄色,正与山水画得以成立的玄学相冥合,于是以水墨为山水画的正色由此而得以成立了。我们可以说,山水画中能表现出远的意境,是山水画得以出现,及它逐渐能成为中国绘画中的主干的原因。”山水画审美重“远”,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远”与“玄”同义,亦通向道。“远”,在中国山水画家那里,亦是一个可以表现无限宇宙的空间视象。唯有“远”,才能突破有限画面空间的限制,进入一个无限深邃的宇宙世界。宗白华先生说,中国山水画言“远”,是以“动的节奏引起我们跃入空间感觉”,“引起吾人游于一个‘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的宇宙”,表现为一种类似音乐审美的境界。这种山水、音乐、宇宙感同在的“远”的空间画面展现,从根本上体现了山水画内在的生命节奏,呈现出一个韵味深远的艺术境界。
山水画言“远”,又指“平远”之境。“平远”不同于高远,自山下而仰山巅;也不同于深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而是一种平视,自近前向渺远层层推去,所谓“极人目之旷望也”。所以,郭熙强调“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韩拙在郭熙的“平远”之说基础上提出“阔远、迷远、幽远”三远法:“有山根边岸水波亘望而遥,谓之阔远。有野霞暝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而这种“冲融”“冲淡”,“旷阔遥山”“烟雾暝漠”“微茫缥缈”的平远之妙,按徐复观先生的说法,“正是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脱时的状态,正是庄子、魏晋玄学所追求的人生状态”。“平远”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画家那种与天地相终始的生命安顿意识,因此它较之高远深远,“更适合于艺术家的心灵的要求”,“更能表现山水画得以成立的精神性格”,因此成为中国水墨山水画意境美的典型体现。
三、意象美创造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共同特征
总体而言,远不止于书法和水墨山水画,中国古代各种艺术类型可以说都是以意象美的创造为目的的。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通过诗歌艺术的创作实践总结出“诗”的本体既不等于“志”(意)也不等于“史”,而是情景融合的意象这一观点。这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情景、虚实、兴象、意象、气象、兴趣、神韵、意境等,都指向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更具有想象性、心灵性的特征,更加追求含蓄空灵的审美意味和象外之象的艺术体验。对此,中国古代诗论家亦有着深刻的认识,如王廷相云“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着,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叶燮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原诗》),强调的即是诗歌意象所具有的含蓄空灵、意在言外的审美特征。中国诗歌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与汉语言文字有着密切关系。费诺罗萨认为,中国文字可以唤起自然事物的意象,因此作为诗歌媒介,中国文字比西方抽象的字母文字要优越得多。也正因为这一特点,中国古代诗歌多“兴象”的诗,它是心与物、情与景的偶然相遭、适然相合,没有什么主体思虑和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一类诗,如叶维廉所说,是以“以物观物”的方式,“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观读者目前”。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陶渊明的《饮酒诗》之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都属于这一类诗。鲁迅谈到汉字构造时,认为它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形、音、义是汉字之美所在,三者的高度统一所生成的意象世界,亦是中国古代诗歌审美意象的独特美感和韵味之所在。
中国音乐在本质上也是意象创造的艺术。早在《乐记》中就有“乐象”的概念,明确以“象”为音乐本体,将音乐之象看成是宇宙天地自然的模拟与反映。《乐记》强调音乐意象与人心、与人的情感的统一,将“情”作为音乐的本体,从心物关系来理解音乐意象的创构,认为有什么样的情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意象,并意识到声律形式对于音乐意象创构的意义。这些看法可以说奠定了中国音乐意象创构理论的基础。音乐是一种时间性意象,具有起伏、流动、变化不定的特点。对此,中国音乐理论有明确的认识。如汉代马融的《长笛赋》云:“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汜滥溥漠,浩浩洋洋。长矕远引,玄复回皇”,强调可视性的形象必须通过音乐性的时间性意象(听声)来体现,让人们产生遐想,领略到音乐的美妙与无限。中国古代音乐理论有著名的“律历融通”说,亦是将音乐看成一种时间艺术,从时空一体的音律节奏变化中来体悟音乐意象创造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意义。中国音乐是一种以“心”为本体,表现人的心灵律动的艺术。嵇康提出“音声无常”和“和声无象”的观点,并不是为了否定音乐中的象,而是要指出音乐意象的特殊性,它是一种“心象”。“心象”的世界是变化无常、流动不居的,它所体现的是音乐与天地造化的相互感应和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家只有进入到这个心象世界中,才能创造出完美伟大的音乐作品。明代音乐家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曰:“纡回曲折,疏而实密,抑扬起伏,断而复联,此皆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也。其有得之弦外者,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中国古人所创造的就是这样一个“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不可言传,有着弦外之音的音乐意象世界,它看重的不是眼前可视可听的这个“象”,而是“象”后面所隐含的深远无限的“意”,是体现了艺术家情感、心灵、人格精神的意象世界。
戏曲这一戏剧类型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它在本质上也是一门意象创造的艺术。戏曲具有中西戏剧艺术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必须有“故事”,戏曲意象可以看作是一种“事象”。故事性和文字表现等文学性因素对于戏曲艺术的审美意象生成很重要,比如,《西厢记》《牡丹亭》一类戏曲,不仅有好的故事,而且有非常美的唱词。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出场唱的第一支曲子《赏花时》就写得非常美,整个剧情就是在这样美的意境中展开的,直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唱词,将这样的意境美推向顶点。但是,中国戏曲又不同于西方戏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绎故事,创造意象,而是以舞台形象塑造的美和所达到的艺术品位和艺术境界为中心,以程式化、虚拟化的舞台表演来展现丰富的审美意象创造。中国戏曲欣赏有“听戏”“看角”之说,它说明中国观众能清楚意识到戏曲审美意象生成的特殊性,戏曲的“戏”(舞台意象)是演出来的。“听戏”与戏曲的“曲”的品性,即歌舞化表演分不开,中国古代戏曲表演讲究“声情并茂”,演员的唱腔、吐字、念白、身段、舞姿都很讲究,听众必须对此有深刻了解,否则就谈不上戏曲欣赏。“看角”即是如此,主要不是看演员所饰演的人物和事件,而是看他如何表演,每一个表演大师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京剧才有那么多的流派,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如提起“梅派”,人们自然会想起《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天女散花》《洛神》一类作品;提起“程派”,人们自然会想起《文姬归汉》《荒山泪》《窦娥冤》一类作品。戏剧表演大师的表演往往形成为观众所认同的规范性审美意象,形成最强烈的审美效应。
另如,中国的舞蹈、中国的建筑等,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摹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虚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即使像《红楼梦》《西游记》那样的长篇叙事作品,也充满了喻象寓意和情景交融的诗意描写,体现了以意象为特征的中国美学精神。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美的创造中,有的艺术还突出指向意象美中的意境创造层次,比如中国园林艺术。中国园林是一种集建筑、山水草木、诗、画、书法、雕刻等因素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也是通过“声、色、香、味、触”等多种感官交融将人们引向一个可以唤起无限联想、想象的诗意空间,体现了中国艺术意境创造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境生于象外”,以有限的空间来表现无限的宇宙人生意蕴。宗白华说,园林是处理空间的艺术,但这种空间绝不是园林中人们可见可感可游可望的实体性空间,而是一个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由有限通向无限,可以给人们带来丰富的人生意蕴与体验的大空间。这种空间美感和意境美的创造,在别的艺术形式中都有体现,但在园林艺术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张宣),“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苏轼),“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即是。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园林艺术的本质就是“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或隐或现,或曲或直,于亭台楼阁、山水花木、诗书乐画的有机组合中创造出一个具有无穷意味的空间美的意象世界。
结语
本文主要结合不同艺术类型的特点讨论了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范畴存在,反映了各门艺术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意与象的交融、情与景的融合、形与神的统一,是化景物为情思,以象显意,以形写神。意象世界重视的不是表层的、感性可见的、形式技巧之类的东西,而是隐含在表层的、感性可见的、形式技巧背后的,深层次的、更具有精神意味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谈论得很多。但是不同艺术类型的意象创造又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与不同艺术类型所依赖的媒介手段、形式特征密切相关的,反映了不同艺术类型所蕴含的哲学美学观念的差异,对此,学界显然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选择书法和水墨山水画两种类型予以探讨,并概略谈到诗歌、音乐、戏曲、园林等艺术类型的意象创造,意在体现不同艺术类型在审美意象创造方面所体现出的个性特点。宗白华提出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而结合不同艺术类型的特点来把握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意象创造,即是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它不仅有助于人们把握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共同价值,而且通过不同艺术类型美感经验的阐释,可以更好地揭示和丰富意象美学的内涵,使人们意识到意象美学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的重要性,使意象美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