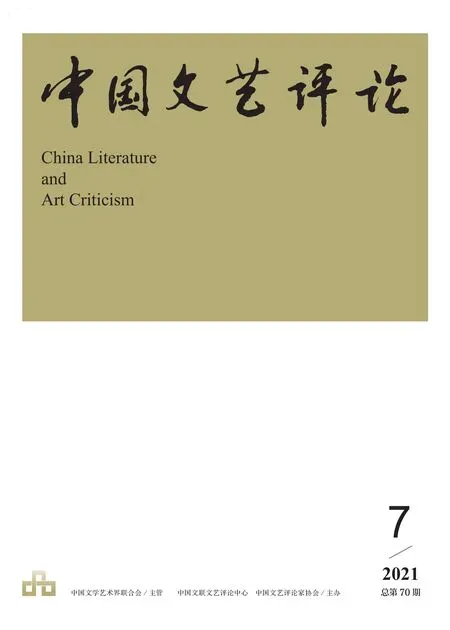“典型”与“形神”
——中西文艺理论、美学关于艺术形象认识的差异性解析
李 健
在中西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史上,艺术形象都居于核心的理论地位。任何文学艺术都必须创造艺术形象,文学艺术审美也以艺术形象为中心。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的艺术形式,艺术形象的呈现各不相同——可能是完整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也可能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也就是说,艺术形象包含人、事、物,那是具有深刻的情感和意义蕴涵的人、事、物。不管何种艺术门类,也不管何种艺术形式,艺术形象都是灵魂。离开艺术形象,文学艺术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在各自文化中孕育的文学艺术形式不同,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自然也不可能一样,这就导致了中西艺术形象观念的根本性差异,不仅使用的概念不同,而且概念的内涵也不相同。中国对艺术形象的称谓比较复杂,秦汉称象、意象、形神等,唐代又出现了境、兴象、意境等,此后,这些概念相互混杂,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到了20世纪,随着叙事文学的兴起,引进西方、苏俄的典型理论,用典型指称理想的艺术形象,随之,典型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美学最重要的话语之一。中国古代的艺术形象概念都有各自的生成背景,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每个概念都具有独特的意义结构,意涵极其丰富。而西方对艺术形象的称谓大致统一,除了“形象”这一笼统的概念之外,还有类型、典型、性格等——这涉及文学艺术的人物形象创造理念,既追求个性(特殊性),又追求共性(普遍性、一般性),最终实现个性(特殊性)与共性(普遍性、一般性)的统一,这就是理想性格或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古代的诸多艺术形象概念与西方的典型、性格等讨论的虽然都是形象问题,但是,理论的基点不一样,认识的途径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不好把中国古代所有的艺术形象的概念拿过来与西方的典型、性格相比较,因为很多内容缺乏可比性。鉴于形神、典型都关乎具体而微的艺术形象创造,都指涉人物形象,故而,我们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观照,以期对中西艺术形象认识的差异性作出力所能及的解析,从而彰显中西文艺理论、美学各自的价值。
典型:西方对艺术形象特征的美学规定
典型是西方对艺术形象的最高规范。作为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典型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其对艺术形象特征的认识及美学规定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逐渐完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和必然原则的论说,达•芬奇“人物形象显示了表达内心激情的动作”(《论画》)的观点,歌德掌握和描绘人的个别特殊与普遍性的看法,黑格尔的理想性格是普遍性和个性统一的论述,别林斯基“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的说法,乃至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阐发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充实了典型的内涵。典型作为艺术形象的特征逐渐清晰,其美学规定也趋于完整。这对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完善艺术形象的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学界通常认为,典型理论肇始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的模仿说,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人物性格刻画问题,学界将之视为典型理论的发端。亚里士多德说:
刻画性格,就像组合事件一样,必须始终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这样,才能使某一类人按必然或可然的原则说某一类话或做某一类事,才能使事件的承继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
这涉及人物形象塑造的美学问题。塑造人物,刻画性格,就好比作品中组合事件,在现实中,事件并不一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发生在多个人身上,但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情感的需要,必须按照必然和可然的原则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反复讨论如何描写一个好人或者坏人,认为只要抓住只属于这种人的品格就能够达到目的。在他看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之所以做得好,就是因为它们描写的好人比一般人好,描写的坏人比一般人坏。这里的好与坏并不是指程度,而是指艺术表现。同时,好与坏也不纯粹指作品描写的人物形象品德,而主要指文学艺术家运用的艺术手段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审美意识。由此看来,对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连同艺术与美学的评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标准。这实质上开启了典型理论,开启了西方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追求。“必然”和“可然”是亚里士多德讨论人物性格所使用的两个独特的概念,同时也是他区分文学(诗)与历史的概念。他曾经这样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历史家记述的是真实的事,而文学家(诗人)描写的是虚构的事,然而,这种虚构并非无厘头,而是按照必然或可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文学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也是虚构的产物。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得出的结论。正是因为艺术形象是虚构的产物,才生发出关于典型的众多认识,赋予典型以丰富的意涵。
必然的原则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必然导致的结果,那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可然的原则就是事物发展可能会导致的结果,那是一种偶然性、不确定性。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和运行规律,人也一样。人的个性、气质、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思想意识、审美趣味等都是左右人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就囊括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必然和可然原则。人的个性、气质是恒定的,这种个性、气质决定他(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人的生活经历充满变数,这是偶然性的生长点。如何处理必然和可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物形象成败的关键。可以说,必然与可然之于人物性格是亚里士多德布下的一个迷魂阵,后来,艺术形象的讨论都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艺术形象仿佛蒙娜丽莎的微笑,永远让人无法参透。
歌德、黑格尔、别林斯基对艺术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延续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歌德要求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要满足于一般,而要写出个别特殊。描写一般,任何一个作者都能做到,而写出个别特殊,却不是任何作者能够做到的,只有具有创造力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完成。要写出个性鲜明的个别特殊,就必须在个别特殊性中注入普遍性,这极其艰难。歌德说:“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歌德谈话录》1823年10月29日)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身上都聚集了很多人物的性格、品质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普遍性,个别特殊的人物形象要在展示个别特殊的同时展现普遍性,这才是典型形象。然而,个别特殊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它是作家、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因此,歌德非常重视个人体验的重要性,主张作家、艺术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见,歌德的所谓个别特殊就是独创,艺术形象只有突出个别特殊才具有生命活力。如何通过个别特殊展现普遍,创造典型?歌德讨论的并不多,他只是说,世间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话虽不错,仿佛只要写出了个别特殊就展示了普遍性,其实很多个别特殊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如此一来,歌德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通过艺术作品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在展示个别特殊的同时,又能表现出普遍性,这并不是容易的事。
黑格尔则从整体与个体切入讨论人物的性格,其入思方式与亚里士多德、歌德大体一致。实际上,黑格尔是用“情致”(这是翻译并改造了的希腊语概念)一词而非“这一个”来统摄人的行动、统摄整体与个体的,把它看作“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的意蕴的价值与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力量。”由此,黑格尔讨论人物性格时说:
我们原来的出发点是引起动作的普遍的有实体性的力量。这些力量需要人物的个性来达到它们的活动和实现,在人物的个性里这些力量显现为感动人的情致。但是这些力量所含的普遍性必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融会成为整体和个体。这种整体就是具有具体的心灵及其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神们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情致”是主宰整体与个体的力量,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充当着灵魂的角色。“情致”使整体成为一个具有具体心灵和主体性的人,也就是说,它首先使个体具有鲜活的个体性;其次,它蕴含的价值与理性使个体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在黑格尔的理念中,人物性格的整体和个体就是一体化的,它们被“情致”所统摄,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就是典型。这典型就是整体与个体相融合统一的人物性格。在20世纪中国学界开展的典型大讨论中,学人们经常搬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用来认识感性确定性的概念——“这一个”来说明典型的特征。其实,“这一个”太抽象、笼统,将之和“情致”、整体、个体对读,对从认识论上解析黑格尔典型理论的丰富意涵会有很大的帮助,从而能更深入地发掘出他典型理论的独特之处。
俄国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是从极度民族性的立场认识典型的。他赞美果戈理小说所表现的极度民族性,这种极度民族性由于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因而具有独创性。在别林斯基看来,果戈理身为俄罗斯人,不仅能写活俄罗斯人,而且能写活德国人,这得益于他对俄罗斯生活的了解,得益于他的创作天才。大凡创作天才是不会把民族性当作一回事的。在这方面,果戈理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这种独创性就是典型性。他说:
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
典型只有具有真正创作才能的人才能写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天才才能写出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天才”,是康德意义上的天才,是为艺术立法的人。只有这种才能的人才能创造出典型形象。这种典型形象对于读者来说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所谓“似曾相识”是普遍的、一般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管是同一民族还是不同民族;所谓“不相识”就是个体性、特殊性,只有某个人身上才有。“相识而又不相识”,说明典型是源自现实生活的、真实的、普遍的,同时,又是虚构的、个体的、一般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别林斯基的典型观与亚里士多德、歌德、黑格尔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然而,西方对典型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另一种观念的类型说,也不是哲学的立场,而是指立足于典型的艺术表现。意大利著名画家、美学家达•芬奇从绘画的角度讨论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虽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等人一样将问题上升到偶然与必然、普遍与个别、一般与特殊这类哲学的高度,但是,却关注到外在与内在问题,要求人物形象应通过人的外在行为来展现内在心灵。因此,他非常强调动作的刻画。他说:“绘画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动作都应当表现它的精神状态,例如欲望、嘲笑、愤怒、怜悯等。”“一个优秀的画家应描画两件主要的东西——人和他的思想意图。第一件容易,第二件难,因为他必须借助体态和四肢的动作来表现它。”“在绘画里人物的动作在种种情形下都应当表现它们内心的意图。”(《画论》)通过人物的动作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似乎格局小一些,但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却至关重要。在表现出共性与个性的同时,又能做到以形写心,通过人的动作、行为表现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这种形象才更具有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将西方的典型理论拿来谈论艺术形象的创造,使得典型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美学的核心话语,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之与阶级性、党性等意识形态密切交织在一起。在阐释典型的特征时,基本延续的是西方的普遍性和个别性(共性与个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统一的认识,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突破。乃至于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发展时只是集中讨论所谓的“统一说”,即共性与个性统一,或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直到刘再复提出性格组合论,将典型形象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不同的侧面观照性格的创造,典型的研究才算推进一步。西方对典型的艺术形象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美学规定,总体来说是抽象的。典型的创造如何实现必然与可然、普遍与个别、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依然是一个难以说尽的话题,需要结合时代和具体的文学艺术创作发展来认识。因此,典型创造是一个进行时,典型理论同样是一个进行时。
形神:以形写神,传神写照
中国古代对艺术形象的认识是形神。作为一种艺术形象理论,形神并不像典型,仅仅从概念的字面上就能够得出评价性的意见,它的字面本身是不包含任何评价成分的,只有深入到具体的言说,才能看到评价性的态度。形就是外形、外貌,神则是精神、气质。中国古人对艺术形象创造的要求是既要写形又要写神。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易写;而神是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难写。这就给形神理论带来很大的言说空间。如何写形?如何写神?形与神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形神对艺术形象的创造存在怎样的美学规定?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解说,如“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神本无端,栖形感类”“取形不如取神”,等等,这些说法就是评价性的言论了。中国古代对艺术形象的追求是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传神是艺术形象创造的最高追求,当然,也是对艺术形象特征的美学规定。
中国古代的形神理论受老庄的影响最大。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提出了“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的观念,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形神理论。所谓“大象”就是最美妙的形象,蕴含的道最为丰富,表达的思想情感最为深邃。这与西方典型确实有点类似,但是,不是必然、可然,也不是普遍与个别。这种“大象”是“无形”的。何以如此?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形能承载意义无限丰富的道,每个形内在的蕴含都只能是道之一极,不可能是全部。这其中的哲理非常丰富、深奥,丝毫不逊色于亚里士多德的必然与可然原则。同时,老子还说过:“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老子》第六十章)这里的“神”有神秘的意思,也有自然的意思,神秘与自然是可以发生关联的。也就是说,当道莅临天下的时候,鬼就不是那么神秘了,就成为自然了。老子的思想给后世的形神理论确定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追求自然。
庄子描绘了很多形神严重错位的人物,借此宣示他的形神观念。他写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写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写哀骀它:卫之恶(丑)人,以恶骇天下;写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等等。这些外形极度美妙和丑陋的形象,都成为道德典范。这说明,形并非不重要,离开形,神不会存在,只不过,形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是可以多元的。形神的错位给人带来的审美震撼往往更加巨大,那是通过正常的表现无法实现的。到了汉代,形象的创造则追求“君形者”。《淮南子》将生命整体区分为三个要素:形、气、神。它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原道训》)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形、气、神三者缺一不可。艺术形象的创造不仅要写好神,而且要写好形,写好气。因为形是生命的房舍,它的存在就是家的存在。神主导着形,是形的主人,因此,《淮南子》称之为“君形者”,主张艺术形象的创造要展现“君形者”。“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说山训》)所谓“不可说”“不可畏”就是失去了形象的内在生气,没有画出西施和孟贲的精神气质。气是存在于形之中的,是神的表现中介。《淮南子》之所以将神冠以“君形者”之名,就是因为注重形神的一体化。可见,画家之所以没有画出一个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还是因为没画好形,没能在外在的形体上注入生气。这是画家的思想和审美出了问题,不单纯是技法问题。
形神理论的发展深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都相当繁荣,文学家、画家、书法家等广泛地将形神观念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创造之中,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命题。山水画家宗炳曾经遍游庐、衡、荆、巫,他在陈述自己的绘画体验时说,“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但是,人的视界是有限的,以山水之大、人的眼力之小,如何才能把“昆阆之形”“围于方寸之内”?只能“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就是画形。如此画出来的形,并不会影响形的整体表现,观者自然会“不以制小而累其似”。可见,画家在画形的过程中需要精心布局,把具有特征性的要素进行加工,或删减、或改造、或浓缩。这就是说,单单画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需要发挥神思。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画出形象的神和理。宗炳说: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画山水序》)
“应目会心”是指通过对画面的观赏,激发内心的情感,引发内在的联想,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很亲切,都能使人的心灵产生回应。这是因为绘画表现出形象之神韵,从这种神韵中,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理——道理、哲理、智慧等。这种“神”是虚幻的、无端的,是通过“形”捕捉到的,足见宗炳的形神理论蕴含着美学的大智慧,以形写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宗炳的形神理论虽然言说的对象是山水画,但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适用,对文学塑造人物形象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宗炳的形神观体现了整个时代的风尚。南朝时期,无论画家还是文学家都非常推崇形似。南齐谢赫著有《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其中有三法涉及对形的描写,即“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六传移模写”。他赞美一品卫协的画是“形妙”,二品顾骏之的画是“赋彩制形,皆创新意”,在此基础上才强调“气韵生动”。也就是说,“气韵生动”的形成得益于形的描写,那就是“形似”。故而,沈约评司马相如“工为形似之言”(《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评魏晋以来的文学“文贵形似”(《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评王粲“巧构形似之言”(《诗品•晋黄门郎张协》);颜之推评何逊“多形似之言”(《颜氏家训•文章》)。这些言论大都是肯定性评价。南朝理论家们之所以如此注重形似,是因为形似紧密关联着现实真实。现实真实是参照,是人的一切认识的基础,离开现实真实,文学艺术家是不可能创作出惊天地、动鬼神的作品的。然而,形似所包含的真实又必须是融合本质真实的艺术真实,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的虚构与想象。实际上,魏晋南北朝的形似是包含神似的。我们从《世说新语》关于顾恺之(长康)作画的一些经典记载中可以窥测一二。请看《世说新语•巧艺》: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这些例子说的都是顾恺之画人。顾恺之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大画家,他的创新意识强,艺术手法高妙。他画的人大都非常传神,就是因为他善于抓住人的神明,所以画出了人的个性。传神写照是他的艺术追求,是强调他在画人的时候善于根据人的实际情况,抓住人的外形特征,并突出这种外形特征。他画裴楷,在他的脸上平添了三根毛发,这是着意强化裴楷的外形特征,并以这种外形特征来表现他俊朗的精神气质。“三毛”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同样,他画殷仲堪,巧妙地运用他一只眼瞎的外形特征,明点瞳仁,用飞白的线条轻轻掠过那只瞎眼,就仿佛轻云蔽日。如此一来,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就呈现出来了。在顾恺之看来,人的眼睛最能传达人的精神气质,这就是所谓的“传神写照”,是写形与写神的有机统一。
中国古代对写形与写神的讨论关乎艺术形象的创造。唐以前,以形神理论谈论绘画、书法;唐以后,随着小说的兴起,便将形神理论用来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李贽曾经评点《水浒传》的人物形象,他说:
描写鲁智深,千古若活,正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点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三回回评)
人物形象的描写要真正地实现传神写照,必须抓住同和不同的地方,善于在同中辨别出不同。这就要求抓准人物的个性化的特征——可能是外形的,也可能是行为的、言语的,也可能是性格的——进行分毫不差的描绘。李贽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来塑造人物形象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做到的。因为作家的个人经历有限,不可能遍览所有精彩的现实生活;同时,现实生活的精彩度也有限,完全照搬不可能长久吸引人的眼球。因此,他强调写假,就是强调虚构。“《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第一回回评)假事也可以表达真情;倘若假事表达了真情,也是真实,是可以永恒的。“《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便可与天地相始终。”(第十回回评)李贽关于人物形象创造的认识显然是受南朝“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思想启发,已经蕴含了比较深刻的关于艺术真实的思考。这说明,传统形神理论对人物形象的创造意义重大,随着古典小说的繁荣自觉地介入人物形象的创造,其丰富的理论意蕴,值得深入探讨。
“典型”与“形神”的差异性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大体上把握了西方典型和中国古代形神的主要内容,对它们关于艺术形象特性的美学规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概括地说,典型追求的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个别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典型的艺术形象是追求鲜明的个性的,同时,又要展现普遍的人性。就像别林斯基说的,不要单纯写一个挑水的人,而要能借写一个挑水的人写出所有挑水的人。这其中包含着作家、艺术家概括、综合等艺术加工能力。如何进行概括、综合?涉及很多的细节。对此,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以及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多有论述,这些论述几乎囊括了典型的方方面面。而形神追求的是“以形写神”“传神写照”,无论写形还是写神都要求表现个性特征与精神气质。这与典型追求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人虽然把形象区分为形与神,实际上是把形神看成一个一体化的存在,它们绝对是不可能分开的,故而,写形与写神也是一个一体化的行为,写形是为了更好地写神,更好地展现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气质。因此,中西关于艺术形象的观念,从典型与形神这两个概念、两种理论的内容实质可以看出,差异性非常明显。这表明,中西对艺术形象的美学追求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完全悖离的。
典型与形神的差异性之一是,它们内在蕴含的哲学理路不同。这不同的哲学理路导致对艺术形象的认识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似乎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特别指出来,意在提醒人们在讨论中西文学与艺术的相关问题时,千万不要漠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典型的哲学理路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哲学。古希腊就非常注重理念,在追逐事物的理念和理想的过程中运用的是辩证法,追求抽象,讲究逻辑的推理、分析、演绎,自然而然将这种方法带入对文学艺术包括艺术形象的认识之中。柏拉图认为,理念才是真实的,现实不真实,而文艺只能模仿现实,不能模仿理念。因此,在他看来,诗人都是说谎的人,应该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看法,他认为,诗人是按照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来进行描写的,诗同样可以表现真实,表达真理,那么,艺术形象当然也应该遵循可然或必然的原则,表现真实,表达真理。理性主义强调理性高于感性,把理性看作知识来源的基础,主张通过逻辑的推理与论证来获得结论。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西方将典型看作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和个别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通过个别表现普遍则成为必然。中国古代的形神理论是在道家的哲学背景下产生的,经过两汉黄老之学和魏晋玄学的充实,形成了极其丰厚的内涵。道家的思想核心是自然,形神的表现当然以自然为标准、典范。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和之以天倪”,都是形神的思想资源。关于人的形象,在《庄子•德充符》里有具体而丰富的言说。在谈及人的德与形时,庄子说,“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而在谈及人的情与形时,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对于“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们大都能理解,而对于“有人之形,无人之情”,人们大都不能理解。在庄子看来,“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其身”,也就是说,倘若在人的身上没有了是非,就实现了自然。因此,他说:“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而自伤其身。”正是在老庄的影响下,才有汉代以黄老之学为主导的形神论,才有魏晋南北朝以玄学为主导的“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理论。这些理论对后来艺术形象的美学追求意义重大。
典型与形神的差异性之二是,对艺术形象的认识方式不同。艺术形象的特性是艺术形象之所以成为艺术形象的性质。典型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个别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统一的认识,要求艺术形象既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这里的个性是包括人的外部形象特征和内部形象特征的,外部形象特征指人的外貌、行为、语言等,内部形象特征指人的性格、心理、情感、气质、精神状态等,典型就是要把这些生动、细腻地展示出来。不仅如此,典型还要具有共性,或者称为普遍性、一般性,这种共性就是指人性共有的东西,或者一类人共有的东西,例如,哈姆雷特、阿Q等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古今中外关于艺术形象共性的讨论中,我们体悟到,共性是对艺术形象特性的高度抽象,要求典型表现理念、真理,或者带有普遍性的人性,或者某种规律,即从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身上能够看到一类人或所有人身上都有的东西,比如性格、思想、情感等方面的优点或缺点,做到以小见大、以少总多。这足见典型的要求之高,典型塑造的难度之大。林兴宅在分析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阿Q的影子不仅在统治阶级的人物中普遍存在,而且在被压迫阶级的人群中也可以找到;不仅过去的时代,而且今天也仍然存在阿Q一类人物,不仅中国有阿Q,外国也有阿Q。”这就是所谓的共性。正是因为阿Q身上有这么多共性,他才是典型。这样的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但是,这种对共性的追求很可能会导致典型的泛化、机械化,由此也产生了很多争论,在概念上兜圈子。这是典型理论存在的问题。如何处理共性和个性,依然是艺术形象塑造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形神理论则弘扬个性,凸显独特性,无论写形还是写神都要求凸显个性,这是显著地不同于典型的地方。所以,顾恺之在画人时,喜欢突出人的外貌个性,他画裴楷,在他脸上添加了三根毛发,并认为这是“识具”;画人“多年不点目睛”,是为了寻找一个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眼睛是传神的,给不同形体的人物画上一双不同神采的眼睛,能够突出一个人的个性气质。人的形体的美与丑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传神。“传神写照”传达出来的一定是个性之神。即便写共性,也要求突出个性。《水浒传》写了这么多急性子,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但都是“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点不混”,就是因为写活了个性。因此,形神理论中没有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问题,只有传神。传神是艺术形象创造的最高要求。
典型与形神的差异性之三是,对艺术形象的美学追求不同。典型追求的是真实、规律、真理,形神追求的是气韵生动、趣味。典型要求从个性中发现共性,试图从一个艺术形象身上发现现实中众多人身上都有的一些东西,或思想,或气质,或品德,其目的是净化,净化人的思想、灵魂。恩格斯在写给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赞美她的《城市姑娘》写出了典型人物,但是却批评她没有写出典型环境,由此提出了著名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观点。他所谓的典型环境是“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致玛•哈克奈斯》)。这就把典型的意义放大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确实不能抛开社会历史背景的设置,这是突出典型真实性的前提。因此,典型的美学追求是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呈现出规律和真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和个别性,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都体现了对规律、真理的追求。形神主张以形写神、传神写照,那是为了追求气韵、趣味,在写形的基础上做到“气韵生动”。宗白华解释道:“艺术家要进一步表达出形象内部的生命。这就是‘气韵生动’的要求。”也就是说,气韵的艺术形象呈现出来的是个性、气质、精神、风貌。而这些是不能游离于对人的外貌、语言、行为的描写的。与此同时,古人还追求形神的趣味。趣味有不同的种类,如高濂就将趣味分为天趣、人趣、物趣三种。他说:“天趣者神是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夫神在形似之外,而形在神气之中。形不生动,其失则板;生外形似,其失则疏。故求神似于形似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燕闲清赏笺论画》)当然,中西这些美学追求的不同应该归因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这是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审美差异。这正体现了人类审美追求的多元、自然,对艺术形象的要求也是多元的。
上文我们只是简单地讨论典型与形神理论关于艺术形象认识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在现代随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外转已经差不多被抹平了,到了20世纪,中国也已经开始崇尚典型了。因此,中国20世纪开展的典型问题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西方原创的典型理论。而中国传统的形神理论并没有被充分纳入艺术形象的考量之中。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缺憾,对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美学无益。因此,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意在重估典型与形神之于艺术形象的理论价值,以便完善艺术形象理论,提高人类的文艺创作与审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