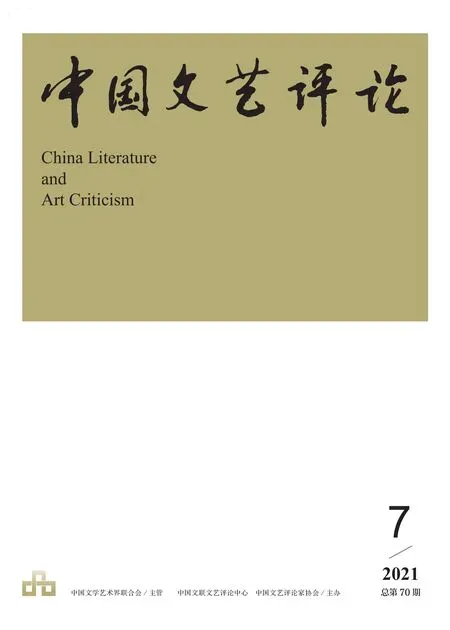布莱希特对1950年代英法戏剧的影响比较
——以阿达莫夫和阿登的创作为例
宫宝荣
布莱希特叙事戏剧(或叙述戏剧)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创立,并在其流亡期间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但直到二战结束、布氏回国创立“柏林剧团”之后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成为完整的戏剧体系。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布氏叙事戏剧在欧洲的知晓度十分有限。1954年以来,随着布莱希特及其柏林剧团几次巡演欧洲,叙事戏剧才逐渐在欧美戏剧界传播开来,并因为契合战后戏剧界及百姓求变求新的愿望而影响日广。无论是1954年在法国还是1956年在英国,柏林剧团的巡演都吸引了许多观众,戏剧界的反响尤其热烈。正是在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的推动下,英法两国戏剧发生了重大转折。
距离二战结束不久的1950年代,英法两国戏剧原本走的是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在法国,以尤奈斯库、阿达莫夫等人为代表的“荒诞戏剧”开启了戏剧革新即“新戏剧”(le Nouveau Théâtre)之路;而在英国,以奥斯本为代表的“愤怒的戏剧”(the Theater of Anger)更多表达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并预示了这一时代英国戏剧的政治化倾向。然而,当柏林剧团前往巴黎、伦敦巡演之后,两国戏剧无不深受启迪并发生重大变化。布莱希特醍醐灌顶般地唤醒了法国戏剧家的政治觉悟,以阿达莫夫为代表的戏剧家们开始反省,不再视戏剧为表达荒诞主题的手段,而将其作为表达社会现实和民众诉求的工具。“愤怒的一代”剧作家们则更加强化了其左翼政治倾向,同时开始吸收布氏“叙事戏剧”的精华。以阿登为代表的左翼剧作家们,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叙事手段,使得英国剧场面貌灿然一新,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总之,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1950年代英法戏剧各自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变革之道,左翼化、政治化和叙事化俨然成为两国戏剧变革的主流,或者说叙事化的“政治戏剧”变成了这一时期英法两国最为重要的戏剧思潮,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60年代以来的欧美戏剧的发展趋势。本文将围绕1950年代布莱希特对英法戏剧的影响所引起的变化进行比较,结合代表性剧作家的具体作品,论述两国戏剧通过对叙事戏剧的接受所产生的殊途同归的结果。
一
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法国戏剧很快得到了恢复。以阿努依等人为代表的新型林荫道戏剧让巴黎各家剧院恢复了生机,让•维拉尔通过创办阿维尼翁戏剧节和领导国立大众剧院(T.N.P.)在努力实践着先人们的“大众戏剧”理想,而以尤奈斯库、阿达莫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戏剧家则开创了以“荒诞”为主题的先锋戏剧。谁又曾料想到,1954年布莱希特率其剧团首次访法,竟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布氏“旋风”,令法国戏剧界和理论界深受震动。文艺理论家罗朗•巴特、贝尔纳•道特及其《大众戏剧》杂志同仁开始不遗余力地在法国传播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理论与实践。多股力量作用之下,叙事戏剧逐渐深入人心,法国戏剧家们的观念和创作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而其在1950年代最为明显的标志便是戏剧的政治化。
虽然早在1945年,就有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大力鼓吹“介入文学”,前者甚至还通过自己的戏剧创作来身体力行,但是1950年代上半期的法国戏剧总体而言其政治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其时戏剧家们努力的重点并不在此。一方面,以维拉尔、吉努为代表的主流戏剧家们将精力集中于推动戏剧外省化运动和创建“大众戏剧”这一凝聚了几代人心愿的宏大事业,旨在使普通百姓都能和巴黎“贵人们”一样欣赏高雅的戏剧艺术。另一方面,“新戏剧”作家则致力于打破传统戏剧的桎梏,在罗歇•布兰、尼古拉•巴塔耶等不乏创新精神的新一代导演的帮助下致力于实验戏剧。也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当时的法国剧作家中过问政治、利用戏剧表达观点者并不多见,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麻木不仁的。正是在布莱希特及其柏林剧团的演出感召下,尤其是在罗朗•巴特、贝尔纳•道特等一众布氏拥趸的大力鼓吹之下,阿达莫夫改弦易辙,不再坚持荒诞戏剧的道路,开始关注具体的现实生活,甚至将巴黎公社的历史事件搬上了舞台。而年轻剧作家维纳威尔则受此影响,一开始提笔写下的就是不乏政治意涵的直指当下现实的戏剧。如此,他们已经为1960年代的法国戏剧进一步政治化和叙事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达莫夫(Arthur Adamov,1908-1970)作为荒诞戏剧“三驾马车”中的一员,由于早年坎坷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身心创伤,早期剧作具有明显的荒诞特征。无论是《滑稽模仿》《侵犯》,还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塔兰纳教授》等剧作,其主题都围绕着“人生是痛苦的、命运是荒诞的”展开,而在表现手法上则有着其独特的标记。《滑稽模仿》剧中的“职员”无名无姓,为了追寻所谓的“爱情”来到某个城市中心的广场,而市政厅墙上的时钟竟然没有指针,好不容易遇到了“莉莉”,女人却不承认与之相识,且追求者如云。“职员”最后的命运更是令人感慨,横尸街头之后竟被清运工当作垃圾一般对待。《塔兰纳教授》中的主人公塔兰纳教授看似是一位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却因为一直被错认为别人而烦恼,甚至还有人当面指控他剽窃。为了证明清白,他最后不得不将所有裹在身上的衣服从上到下脱得精光……直喻性的荒诞手法在当时无疑极具震撼力。然而,时间久了,这种过于封闭在痛苦之中的自我宣泄性戏剧不仅观众接受有限,连阿达莫夫本人也有进入死胡同的感觉。因此,布莱希特戏剧的出现无疑为其寻找突破指引了一条道路。
果然,阿达莫夫很快就否认了此前的“荒诞”主题的戏剧创作,并在《乒乓》(Le
Ping Pong
,1955)中开始蜕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许多东西都随着《乒乓》一剧改变了。”剧作家在其中开始试水表现与法国社会现实相关的主题,通过维克托和阿尔图尔两个大学生朋友因为迷恋上弹子机而丢失自我、一事无成的故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此剧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它在法国当代戏剧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戏剧理论家贝尔纳•道特指出:《乒乓》超越了一切形而上学意义的企图,乃是法国第一部在观众面前向其展现我们的生存困境、揭示我们所拥有或战而胜之或为之所败的方式、我们日常中的异化以及自我神化的作品。
与《乒乓》相比,阿达莫夫在创作《帕奥罗•帕奥利》(Paolo
Paoli
,1955)时转变得更为彻底。让-伊夫•盖汗认为:“阿尔图尔•阿达莫夫通过《帕奥罗•帕奥利》一剧,完成了双重决裂,即政治决裂和美学决裂。”剧作家直接以19世纪法国殖民地上发生的蝴蝶标本交易为主题,通过揭露资本家剥削底层人民的事实,引导观众思考自身所处的社会处境,从而正式进入了其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即现实主义的政治戏剧阶段。与《滑稽模仿》相比,该剧不再是一部行动抽象、人物模糊、思想悲观的荒诞戏。《帕奥罗•帕奥利》有着明确的人物、事件和时空。剧情发生在1900年至1914年之间,恰是法国历史上所谓的“美好时期”。然而,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阿达莫夫并不是要歌颂这段在法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稳定、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的历史,而是要揭露在其“美好”表面之下的“丑恶”和“肮脏”。换言之,对底层百姓来说,这是一段被剥削、受压迫、充满辛酸与痛苦的经历。剧情描写的是,一战即将爆发前夕,资本家帕奥利和于如-瓦瑟尔在法属殖民地圭亚那分别从事“美丽的”蝴蝶交易和羽毛加工。在唯利是图之心的驱使下,帕奥利为了获得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不惜雇用流放犯人马尔浦在委内瑞拉丛林里为其卖命捕捉,而于如-瓦瑟尔则无情地让女工们为其加班加点。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虚伪的本质,剧作家还设置了索尔尼耶神父这一角色来充当掮客。马尔浦最终被帕奥利榨干血汗,甚至连妻子露丝也成为其囊中之物。须知,阿达莫夫是一位已经有着七年创作经验、发表和上演了至少七部剧作的荒诞戏剧家,却在不到两年之内就如此脱胎换骨,成为一位几乎与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无异的戏剧家,可见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当然,如果阿达莫夫只是在剧本的内容设置和主题表达上转向社会现实的话,那么充其量也只是回归到19世纪末易卜生时代的戏剧罢了。事实上,这位剧作家受布莱希特叙事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布氏一样,他在《帕奥罗•帕奥利》中采取了与传统的分幕分场不同的结构手法,12个场景被分成两个部分,且每个场景均如电影一样在帕奥利的蝴蝶收藏室、于如-瓦瑟尔的办公室、神父的房间、马尔浦的房间和斯泰拉的帽店等之间不断切换。为了强化时代感,他在每个场景之前都选取了“美好时期”的报刊文字摘录,用幻灯形式打出,以便让观众了解剧情发生的历史背景。这些报刊摘录来源广泛,既有法国的,也有世界各地的,甚至还有中国的,从而大大增强了历史纵深感。除此之外,阿达莫夫还和布莱希特一样,在剧中采用了音乐、歌曲等手段,以增强演出的娱乐性。如在第一场景之前,他选取了七段来自当时的《小报》、政治家演说、羽毛制作行会以及一位捕蝶人的语录等,从而将剧情发生的时代、尤其是与之相关的行业背景交代给了观众。尤其是最后两段(“羽毛工业新产品在法国出口单子上名列第四”“为了满足我的买家,我需要大量的捕手”)与主题密切相关,手法与深受叙事戏剧影响的文献剧如出一辙。此外,阿达莫夫还在《前言》中告诉我们:
观众在阅读这些句子的同时,还将听到戏剧行动发生时期的乐曲和歌曲。有些歌曲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调调(如《来吧,宝贝儿》),其他的则受启发于当前时事。
所有这些叙事手段,在布莱希特那里可谓司空见惯,但在阿达莫夫这儿却是初试牛刀,它们不仅阻碍观众沉浸到人物的个人命运之中,而且还引导观众透过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来思考资本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毁,从而达到让观众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国向联合国递交的NDC,是中国为实现《公约》第二条所确定目标做出的,反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最大努力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国向世界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13]。中国更是为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共识、生效与持续落实,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自《帕奥罗•帕奥利》之后至1965年左右,阿达莫夫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一直坚持创作兼具政治性和叙事性的剧本,甚至还以巴黎公社事件为题材写下了《71年春天》(Le Printemps
71
,1961)这样一部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剧作。虽然他在晚期重新拾起了荒诞主题,但也不再是抽象虚无的“人生是痛苦的”呻吟,而是结合了具体社会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痛苦,并且与剧作家自身的遭遇不可分离。1950年代中期,法国戏剧家中除了像阿达莫夫这样业有所成的戏剧家也发生了重大的创作转向之外,布莱希特对当代法国戏剧的影响还体现在普朗雄、维纳威尔等这样的青年戏剧家身上。普朗雄(Roger Planchon,1931—2009)原本在里昂从事戏剧导演工作,虽然小有成就,但却一直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当他在巴黎观看了柏林剧团的演出、尤其是与布莱希特交谈之后,心底豁然开朗,从此在舞台上大施拳脚,并发明了“舞台写作论”来为自己的导演创作提供理论依据,渐渐成为法国当代戏剧导演界的领军人物,其影响持续了整个20世纪下半期。而剧作家维纳威尔(Michel Vinaver,1927—)则从一开始便涉足当代社会现实,写下了诸如《今天或朝鲜人》(1956)等这样反映当下的代表作。而所有这一切,都对1960年代以姆努什金及其“太阳剧社”等为代表的法国戏剧政治化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
英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特而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国,其自身的戏剧传统十分强大。这种传统,先是有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戏剧,后来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萧伯纳、高尔斯华绥、巴克为代表的“思想剧”,20世纪上半期则有以毛姆、叶芝、艾略特为代表的诗剧等。而英国戏剧传统的精髓,乃是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相比法国戏剧自19世纪中叶以来便革新不断且高潮迭起,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使英国的戏剧与其文学一样,对实验性的戏剧有着天然的“免疫功能”。《20世纪英国文学史》作者在分析英国非现实主义小说为何晚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原因时如此写道:
它(指英国文学,笔者按)有着一种非常不同于法国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国际上新一波实验主义浪潮冲击英国时,不可能不被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大大缓冲。长期以来形成的经验主义的民族禀性造就了一种实证、质朴、重社会、重道德、散文性的、相对说来不那么看重形式的文学气质。
文学方面如此,戏剧方面也同样如此。
不妨略微回顾一下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诸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戏剧流派对英国的影响似乎都远逊于法、德等国,难以撼动其传统戏剧的地位。而在二战结束之后,英国特殊的国情和氛围使得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艺术也具有与法国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战后以克莱门特•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选举中打败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使得整个英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党政府施行了与保守党不同的治国方针,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政策、新税收政策和经济国有化政策使得底层人民产生了不小的获得感。与此同时,工会势力乘势而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凡此种种,使得当时的英国社会整体氛围向左倾斜,也使得受到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具有“反省的、焦虑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但并未丧失对时代进行道德批判的能力”等特点。而就戏剧而言,这一切也正是以奥斯本为代表的“新浪潮”剧作家们的特点。
有意思的是,约翰•奥斯本第一部独立完成即被誉为“现代英国戏剧的里程碑”的剧本《愤怒的回顾》首演(1956年5月8日于宫廷剧院the Royal Court Theater)之年正值柏林剧团首次在伦敦驻演,而这要比布莱希特剧团在法国首演晚了两年。1956年8月至9月,布莱希特刚去世不久,柏林剧团便前往伦敦宫殿剧院(the Palace Theater)驻演了三周,演出了《高加索灰阑记》《大胆妈妈》等剧,给英国戏剧界和观众带去了极大的震撼,即使像威廉•加斯基尔(William Gaskill,1930—2016)这样的大牌导演都表示“1956年为柏林剧团来访伦敦并改变了我的生活之年”。柏林剧团回德之后,加斯基尔在伦敦举办了以布莱希特叙事戏剧为主题的戏剧训练班,包括约翰•阿登(John Arden,1930—2012)、阿诺德•威斯克(Arnold Wesker,1932—)、爱德华•邦德(Edouard Bond,1934—)等日后在英国剧坛上大显身手的剧作家都名列其中。奥斯本也改变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先后于1957年和1961年写出了具有叙事风格的《卖艺人》(The
Entertainer
)和《路德》(Luther
)等剧作。如果说前者还只是简单地通过将歌舞、杂耍等元素融入剧情以实现叙事剧的形式的话,那么后者简直就是布氏《伽利略传》的拷贝,一样的历史人物题材(路德22年的成长过程),一样的人物内心挣扎主题,甚至一样的串线方式,即每一幕演出之前都安排了一个骑士来交代时间与地点等。《路德》上演十分成功,不仅赢得了观众和剧评家们的一致赞誉,而且还获得了美国百老汇的托尼奖。奥斯本之外,阿登、威斯克、邦德等人的戏剧创作同样打上了明显的叙事戏剧的烙印,其中阿登追随布莱希特的步伐无疑最为坚定,其剧作的政治化和叙事化的倾向最为突出,也因此有人称之为“英国的布莱希特”。阿登主要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创作素材,他的剧作关注社会、政治和个人。他不仅在取材方面与布莱希特相似,而且在风格上是当代英国剧作家中最为布莱希特式的剧作家。
这段话出现在其所翻译的《穆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以下简称《中士的舞蹈》)的导语里,不妨让我们对这部戏略作一番分析。
从创作目的来看,剧作家和布莱希特一样,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讲故事和写性格,而是要通过展示不同阶级的不同境遇以及人物之间的冲突来唤醒观众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为此,阿登将《中士的舞蹈》的剧情设置在19世纪末期,背景是塞浦路斯人民反殖民统治战争期间,以穆斯格雷夫中士为首的四名逃兵来到英国北方一个煤矿小镇,为的是告诉人们不能轻易施行暴力。因此,跟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假借“30年战争”来影射二战一样,阿登表面上写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实际上针对的是其所处时代的英国社会。总之,《中士的舞蹈》与传统的戏剧不同,既不是为了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也不是为了构建令人窒息的剧情和塑造人物性格,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剧作家反对殖民统治及其战争,具有明确的政治特征。
为了达到其教育民众的目的,阿登在剧中大量运用了布莱希特的常用手法,如穿插民谣、合唱和舞蹈等,一方面旨在增强演出的娱乐性,另一方面则在避免让观众陷入剧情、失去清醒,而要他们透过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来思考自己的处境和社会的状况。全剧总共三幕,每一幕都有丰富的歌舞穿插来活跃气氛,散文化的情节不时被诗化的歌谣所打断。这些歌谣往往是对人物进行介绍或评论,与布莱希特叙事剧中的文字或歌曲具有相同的功能。而人物的设置也反映了剧作家的上述用心,除了以穆斯格雷夫为首的士兵们和客栈太太等有名字或姓氏之外,其余人物均以其社会阶层和地位的职务来称呼。有意思的是,为了产生对比的滑稽效果,阿登还故意设置了“一个迟钝的矿工”和“一个好斗的矿工”,甚至还有“一个诚实的矿工”。而在第三幕镇长发表演讲时,阿登的处理是典型的布莱希特式的:
因为没有群众,演说是直接对着群众发表的,船夫扮演一个示范者来制造群众反应。对话中指明的舞台外的喧闹声是相当非现实主义的——仿佛仅仅是闹声的象征。
此外,阿登在剧中还安排了大量颇具布氏“社会性动作”(gestus)意味的人物动作与姿势,以此来启发当代观众,让他们透过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件和人物来了解和认识英国社会以及自身的处境。
然而,由于英国戏剧固有的强大现实主义传统,再加上包括阿登在内的“第一次浪潮”剧作家们在创作上尚未成熟,还不能够像布莱希特那样信手拈来地将叙事手段与政治主张、教育目的嫁接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叙事化政治剧作往往显得僵化和生硬,叙事手段反而成为了一种模式化的创作方法。有英国学者如此描述道:
写作和舞台呈现上的一种文本模式(如片断式结构以及直接的揭露),以及左翼的政治姿态。与之相随的是,作者往往选取一个可能成为戏剧事件的主题并且由此将人物和事件堆砌在一起,借以表达这种政治态度,而英国观众往往对这种自我鼓吹姿态表示反感。
《穆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之外,阿登的其他作品如《巴比伦矿泉》《济贫院的驴子》等,也都具有布氏戏剧的叙事特征和辩证色彩。然而,由于这些剧本往往概念先行,剧情枯燥,辩论多于行动,采取的又是街景式结构,再加上英国观众普遍保守,所以哪怕不乏歌舞也不能真正地打动他们。同样,1960年代初,无论是威斯克的三部曲(《大麦鸡汤》《根》《我在谈论耶路撒冷》),还是邦德的《教皇的婚礼》《拯救》,作品中存在着明显揭露社会问题的政治戏剧特点,但是因为不符合英国戏剧传统而不受欢迎。《拯救》更因惊世骇俗的场景与语言遭到了禁演,只是意外地导致了长达200年的剧本审查制度的取消。
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叙事剧在1950年代的英国戏剧界虽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兴起了第一波改革浪潮,出现了以加斯基尔为代表的导演、以肯尼思•泰南为首的戏剧评论家,以及以阿登等人为代表的布莱希特拥趸,并且创作出一批叙事型剧作,然而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模式戏剧的英国观众来说难以立刻接受。值得强调的是,泰南这位有着独特灵感的剧评家和理论家,不仅在奥斯本及其“愤怒的一代”正式登上英国舞台时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是叙事戏剧在英国的有力推广者,甚至对英国剧坛上的巨人劳伦斯•奥立弗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奥立弗曾经是奥斯本的第一部叙事剧作《卖艺人》中骑士的扮演者,1963年担任国家剧院艺术总监后立即任命泰南为戏剧顾问(dramaturg)这一极有德国和布莱希特意味的职务,从而为其大力传播叙事戏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由于泰南等人的这些努力,以及1960年代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使得英国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其戏剧观念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因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之后,英国剧坛上便水到渠成地出现了以叙事戏剧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浪潮”。
余论
由上可见,1950年代无论对法国戏剧还是英国戏剧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法国,二战结束之后的戏剧舞台相当活跃,无论是“大众戏剧”还是“戏剧外省化”运动,都在维拉尔的主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以贝克特、尤奈斯库、阿达莫夫等人为代表的荒诞戏剧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而英国虽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之一,也是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国之一,但其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盛世不再令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感到失落、失望和不满,体现在戏剧方面便是出现了以奥斯本为代表的“愤怒的一代”剧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莱希特及其柏林剧团的巡演如一股新风,在两国剧坛上兴起了一股新潮。以阿达莫夫为代表的戏剧家开始反思,不再坚持“世界是荒诞”的观点,转而关注现实,并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和底层人民的不幸,从而进入了“政治戏剧”的新阶段。与此不同,英国剧作家原本就对政治充满热情,但在创作手法上仍然偏于保守,柏林剧团的演出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启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大胆地运用歌曲、舞蹈、诗歌等手段来“间离”剧情、引发思考,从而开启了“第一次浪潮”。可惜的是,这次浪潮并没有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没能掀起大浪。直到1965年柏林剧团二访伦敦,英国观众终于更好地理解了叙事戏剧。这次巡演再次对英国剧坛形成冲击,引发了“第二次浪潮”,甚至出现了类似法国的“大众戏剧”运动,诞生了所谓“替换戏剧”(alternative theater,又译“轮换戏剧”),使得叙事戏剧在英国重新焕发了生机。而在法国,随着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戏剧的政治化和叙事化倾向在1960年代越发明显,至“太阳剧社”上演《1789年》《黄金时代》时达到了高峰。
英法戏剧对布莱希特戏剧的接受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叙事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及其影响的过程。由于本文的主题以及篇幅所限,我们在此只能简略提及。众所周知,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有着一定的了解,与梅兰芳又曾有过交往,还写过关于戏曲表演的文章,甚至其核心理论“间离效果”也明显地受到戏曲表演的启发。也因此,不少国人在理解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时难免先入为主,将有着不同审美标准和目的的两种戏剧样式混为一谈,其集中体现便在于对“间离效果”的理解与运用之上。抛开布莱希特本人对中国戏曲中所谓“间离”的“误读”不谈,布氏运用“陌生化”手段实际上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即让观众通过“陌生化”手段与剧情以及表现对象拉开距离,换一种新的目光去审视,从而对以往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有所醒悟,进而行动起来。然而,对经历了长期封闭、国门刚刚打开不久的中国戏剧家而言,布莱希特叙事戏剧及其“间离效果”则成为了突破禁锢的不二法宝。须知新中国前期的十七年期间,特殊的国情一度使得我们独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以至于1960年黄佐临先生第一次将布氏《大胆妈妈》搬上舞台时,尽管是亦步亦趋地依照东德方面提供的资料“描红”,还是把观众们吓出了剧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布氏《伽利略传》成为第一部被搬上新时期中国舞台的外国剧作,黄佐临先生再次执导时吸取了十多年前的教训,将叙事戏剧技巧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方法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手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终于让布莱希特的这部代表作赢得了观众,并就此为叙事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必须承认的是,叙事戏剧的引进对新时期的中国戏剧突破其时发展的僵局、尤其是对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戏剧的片面理解而造成的思维固化起到了极好的消除作用,直接推动了1980年代上半期那场意义深远的“戏剧观大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戏剧的面貌。从此,中国戏剧舞台上不再是现实主义一枝独秀,而是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争奇斗艳,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极大程度地满足了人民的审美需求。不必讳言的是,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多重因素,中国戏剧人对布莱希特及其叙事戏剧的理解不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当局限,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欠完整、甚至是充满“误读”的。不过,正如笔者上述提及的1960年代英法戏剧对布莱希特的接受一样,这些话题已经超越了本论文的范围,有待于今后另外行文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