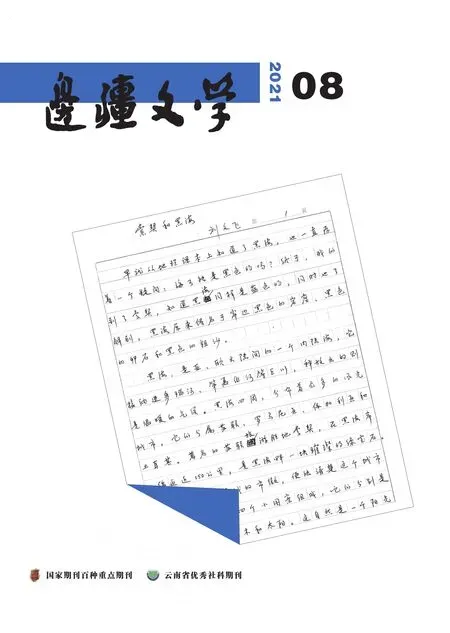出书记 短篇小说
季风
1
那时我还在我们县文联负责。有一天,年近七旬被不少人戏称为老作家的苏应丰来文联办公室找我,说是要出一本书。苏应丰在我办公室坐下,用一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这种眼神只要他来我办公室就是这样,以前是巴不得能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作品,哪怕就是一篇千字文也行。尽管他写的文章不少,可我却很少满足他这个愿望。在我看来,确实还不够发表水平。当然,为鼓励他写作,偶尔也发表一两篇,他就会非常高兴,兴奋得直搓手,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莫非这次又是来投稿的?想到这里我就头大。我看见苏应丰头上的白发好像又多了一些,很像我窗户外面小河边绽放的芦花,好像在无意之间,又开出来了不少。
我站起来给苏应丰倒了一杯开水。我说:“苏老师,最近都写啥了,是不是又来投稿了?我跟你说过,不用亲自跑的,投到我们邮箱里就可以了。我知道你不会用电脑,可你儿子会用啊,你女儿会用啊,你让他们投进我们刊物邮箱,这不就行了?”尽管我知道苏应丰并没有和他儿子、女儿住在一起,可我还是这样说。至于为什么他老婆不在了,还要自己一个人住,这我就不清楚了。
苏应丰喝了一口开水,把杯子放回茶几上,这才说:“庹主席,你是不是很怕我来你这里投稿啊?我这回可不是来投稿的,真不是来投稿的。最近我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又哪里有稿子来投啊!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这件事只有跟你打听才会清楚。”
原来不是来投稿的。我心里稍稍松下来一口气,对苏应丰说:“苏老师,哪里的话?我们不是办着一本刊物嘛,办刊物就需要有稿子,怎么会怕你来投稿呢?我们对所有投稿作者都是欢迎的。你说吧,有什么事需要跟我打听,这你尽管说。但凡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苏应丰又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水,脸有些红,很害羞似的。好一会儿,他才说:“是这样的,庹主席,我想出一本书。我想把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文章都收集起来,然后出一本书。”
苏应丰的话让我有些吃惊。要把几十年写的文章收集起来,还要出一本书,这事容易吗?我写文章这么多年,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比苏应丰多很多好很多,但对出书我也只是想过,并没有去办理。现在出书不比以往,只要达到了出版水平,出版社就会给你出,还会给你一笔不菲的版税。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家都奔着市场去,出版社也不例外。你的书写得再好,如果市场不认同,出版社断然不会给你出的。如果硬要出也可以,那就得自己掏腰包。我曾经把自己这些年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整理好,也想出一本书,但一想到自己要出不少的钱,然后出一堆书摆放在家里,或者拉着板车出去销售,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苏应丰却动起了这根花花肠子。
我看着苏应丰,苏应丰还是那种很期待的眼神。我本来想给他泼一瓢冷水,把他浇清醒,可又有些不忍心。我说:“苏老师,你知道不,现在出书不仅没有稿费,还要自己出钱?当然,要是莫言、贾平凹出书,就会不一样了,这些名家的书,出版社会争着出。”
苏应丰说:“这些我都打听过了,可我还是想出一本书。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如何跟出版社联系出书的事。出钱就出钱吧,据说现在出版社的日子也不好过。人家出版社给你出了书,又哪有不给钱的道理。”
我有点哭笑不得,感觉有些悲凉。自费出版,既实现了作者出书的愿望,满足了一回虚荣心,出版社还能获得一点收入,虽不能说多,但总还不至于出现亏损。这些年,我就收到不少这种自费出版的图书,这些书大都印刷精美,有些书内容还很好,可还是没有逃脱自费出版的命运。我说过,我虽然也有出书的想法,可一想到发表作品稿酬没挣几个,却要为出书掏出上万的钱,这出书的想法,便像雨点儿在地上砸出来的水泡,很快就破碎了。我记得给我们印刊物的印刷厂,会经常给一些自费出书的作者印书,他们肯定知道怎么跟出版社打交道。
我对苏应丰说:“出一本书,这你是真的想好了?出书需要很多钱,你可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这样吧,下周我要去印刷厂送我们这期刊物的稿子,我就顺便帮你问一下。因为在他们那里印书的也不少,我想他们跟出版社联系会很紧密,一定会知道这书怎么出版。”
苏应丰听了我的话,又拿过杯子来喝了一口水,然后站起身来对我说:“庹主席,谢谢你!那你先忙,等你去了印刷厂回来,我再来找你。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啊!”
苏应丰说完,就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了。我本来要出门送送他,可他却对我说:“庹主席,你请留步,你忙你的。”我目送着苏应丰从我办公室走出去,他的整个身形很快就融进小河边这大片的芦花里了。我看见芦花开得越来越放肆,知道这秋天来得越来越深重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都在渴望有所获得,可这可能吗?尤其是这个跟我说要出书的苏应丰。
2
我是什么时候认识苏应丰的?好像还真有些记不太清了。
因为自己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县里要成立文联,就把我选去当文联主席了。我是知道的,当文联主席,就是要多做一些文艺工作方面的事,否则怎么能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呢?加上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因此最初去文联任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到文联,第一件事就是要摸清家底,都有些什么文艺人才。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文学创作座谈会,大概来了十多个人,这其中就有苏应丰。我还记得,在这些文学创作者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苏应丰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本人,苏应丰,天晟小学教师,不过很快就要退休了。苏联的苏,当然也是苏修的苏,应该做什么的应,丰收在望的丰。”在座的十几号人听了苏应丰的介绍,禁不住全都笑了。我认真看了一眼这个名叫苏应丰的人,觉得他这样介绍自己还真有些意思。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苏联,知道苏修呢?更多的只是知道俄罗斯,知道普京。
苏应丰最初是谁介绍来的,我同样有些记不太清了。依稀记得是他的校长介绍来的。苏应丰平时爱写些东西,偶尔也在一些报刊的不当紧处,发出来一篇把千字文。可苏应丰教书是真的不行。据说有一次,校长听了苏应丰的课,很不满意,就对苏应丰说,你教书要像你写文章那样就好了,听说县里要成立文联,还有文学协会,你干脆去他们那里算了。苏应丰后来知道文学协会,只是一个松散性的社团组织,大失所望。他知道校长只是在说气话,这书还得继续教下去,尽管教不好。有趣的是,自从有了文联,有了文学协会,他写的东西更多了,时不时就要跑来文联找我。烦人是烦人,但你也不得不佩服他有这样一种精神。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现在要出一本书,出一本他自己写的书。
苏应丰加入我们文学协会以后,对文学协会的各种活动倒是很热心,都积极参加,差不多凡是有活动都到。我一直以为,在文艺工作上要做出成绩,当然离不开书法、绘画、音乐和戏剧,但我觉得在我们这里,更容易出成绩的却是文学。我一直在思考,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没准就会有作者冲出去了,就可以把作品发在外面的文学刊物上。因此,在重视其他艺术门类的同时,我更重视这支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那段时间,我们经常都会组织文学协会活动,不是采风座谈,就是组织征文评奖,要不就是请一些著名作家、资深编辑来做文学讲座。这些活动确实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得到了上级文联的好评。这些活动,苏应丰没有一个落下的,而且表现得非常积极。他的文章也写得比以往要好一点。
我利用去印刷厂送稿件的机会,帮苏应丰打听这有关出书的事宜。印刷厂老板还以为是我要出书,就说:“庹主席,你确实应该出一本书了。你没见很多像你这样当文联主席的,也都出书了。”我说:“应物兄,你想多了,哪里是我要出书,是我一位朋友要出书。当然,你也可以把我这位朋友出书当作我要出书来对待,该优惠的你还是要优惠。”老板名叫苏应物,跟我很熟,我平时就叫他应物兄,他也乐于接受。我对苏老板说:“应物兄,这个想出书的朋友跟你一个姓,是你的本家,而且字辈还和你相同,应该就是你的兄长了,莫非这你还不想帮他一把。”苏应物告诉我,出书其实就是一个书号的问题,只要在出版社弄来书号,我们这里就可以排版印刷了。你回去跟你那位朋友说,先抓紧把书稿编好,书号我们会去出版社帮他弄。书号有独立书号和丛书号,一个独立书号只能出一本书,丛书号可以出十本八本的不等。独立书号一般在一万五至两万之间,丛书号要贵一些,因为一个丛书号可以出很多本书嘛。不过你那朋友只出一本书,自然是独立书号好了。
我回到文联以后,没有忙着跟苏应丰联系。又过了两天,苏应丰来了。他在茶几旁坐下,我找来纸杯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苏应丰问:“庹主席,我请你帮我办的事怎样了,打听清楚了吗?”我说打听清楚了,于是把我知道的全部讲给他听了。苏应丰认真听完,好一会不说话,喝了一口水才说:“书我肯定是要出的,不过你能不能再跟那位和我一个姓的老板说说,能不能够再优惠一点。一万五、两万,太贵了。还有,印刷费能不能再优惠一点。书号费和印刷费在一万五左右,我就出。书我肯定是要出的,都写大半辈子了,不出一本书,这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呀!”我看见苏应丰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果决,当然也透露出丝丝可怜。也许他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他却要为这书号费和印刷费犯难了。
我对苏应丰说:“那我就再跟他谈谈吧,我想办法给你争取到最大的优惠。这段时间,你可以抓紧把书稿先整理出来,你等我和苏老板的消息。”
苏应丰听到这里,站起身来握住我的手。我感觉到这手明显松弛无力,尽管这双手原本是要握紧我的。苏应丰说:“谢谢庹主席,你这个人太好了。县里选你做文联主席,算是选对人了。这些年,你为我们县的文学艺术事业,做了多少好事和实事啊!”我说:“苏老师,就别给我戴高帽了,回去抓紧整理书稿。既然要出书,就一定要出一本上点档次的书才好。”
3
去参加县里的一个座谈会,是有关文化强县方面的。会议在政府小会议室举行,到会的人大概也就这么二十来个。这二十多个人,据说都是县里的文化名人,所以请这些文化名人来谈文化强县,应该说是找对人了。我找了一个靠墙角的座位坐下,被分管文化的县领导看见了,直呼坐到前面来。县领导说:“你是我们县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怎么可以坐到后面去呢?”听了县领导的话,我感觉很尴尬,甚至都有些无地自容,不过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到前面去了。我听了不少人的发言,并没有记住多少,但县领导在总结发言中说准备出一本书,我倒是听清楚了,因为县领导要求出这本书要由我们县文联来具体抓落实。
座谈会后,我认真想了一下这本书应该怎么出。我知道,这些年,我们县不少作者也确实写了一些作品,还在外面发表了一些。但真正涉及要出书就有困难了,出谁的?是出个人专辑,还是文学爱好者的合集?是单本的,还是丛书?还有,经费从哪里来?这些年,说到文化,大家都会说很重要,但真正要用钱,又总是说没钱。我们出版刊物的经费就常常难以为继。要出的这本书,县领导的意思是要找企业赞助,可近年来县里的企业,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效益并不是很好。我真的不好意思去向企业要钱,即使去,也未必要得到。这件事想起来就让我脑壳痛,好在时间要求还不是太紧,我可以暂时不用去想它。
倒是苏应丰要出书这件事,一直让我心有挂碍。记得有一次,我曾组织一个文学采风活动,活动开展完以后,从他家门前经过,他请我们到他家坐坐。于是我们十几个人便往他家里挤。苏应丰说:“家里太乱了,真不好意思。随便坐,请随便坐。”我们谁都没有坐。这里是老城区,大都是一些五六层的楼房,看上去有些陈旧,就让苏应丰这样的老住户住了。苏应丰家里之所以很乱,是因为到处都摆放着书,很杂很乱。我们十几个人在他家里只是站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苏应丰在送我们出门的时候,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苏应丰说:“实在对不起,家里确实太乱了。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回去吧,以后有活动我会通知你参加的。”苏应丰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谢谢庹主席!”
坐在办公室里,我又想起了苏应丰出书的事。我记得,我问过他,不出书就不行吗?用这些出书的钱来改善一下生活,这不是更好嘛!我看你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几件。苏应丰听了我的话,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不过,苏应丰说:“这物质贫困我已经无法改变了,莫非精神还要跟着贫困?”听了苏应丰的话,我有些吃惊,莫非出一本书,精神就不贫困啦?我看了看他的一张老脸,还是一脸平静,没有半点犯病的样子。我说:“那好吧,你既然要出,那就出吧。我能帮你的,一定会帮到。”
我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通了苏应物的手机。我说:“应物兄,我上次给你说你那个家门出书的事,我回来跟他说了。你家门说,书他一定要出,只是要你多给他点优惠,具体说就是在一万五千块以内。多了,他拿不出这么多钱。”苏应物在电话中说:“庹老师,你开什么玩笑?一万五千块,买一个书号都不够。你就这样跟他说,没有钱就不要出嘛!”我说:“应物兄,你就不能通融一下?你跟出版社很熟,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还有你可以少收点印刷费,这事就可以办妥了。”苏应物说:“庹老师,我的庹主席,你还以为我是慈善家啊!少收印刷费?你知不知道,我这里养着好几十号工人,少收印刷费,你这是要让他们吃空气啊!”苏应物称我为主席,这就是要公事公办了。我说:“你就不能像帮我一样,就收点成本费和人工工资,这样总可以吧?”苏应物说:“我就知道你会说这种话,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再想想。”苏应物沉吟了好一会儿,才在电话里说:“这样吧,在我这里,有一个县文联才在出版社弄了一个丛书号,准备出版一套丛书,估计他们不会有那么多本书要出。你找他们商量一下,把苏应丰的书也作为丛书之一出版,至于他们要收你多少书号费,这个我不管,但肯定比你去买独立书号便宜。我这里印一千册书,收一万块钱。印量小,成本会很高,估计连成本费都收不回来。但是遇着你,我只有认命了。”
苏应物说的要出丛书这个县的文联,跟我们县文联关系非常好。我和这个县文联的主席是好朋友,铁哥们儿。我当即给他打电话,说我这里有一个文学爱好者想出一本书,听说你那里正在出一套丛书,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位作者进来插个队,也混在里面出一本。朋友听了,对我说:“这样不合适吧?还有,这样做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向县里交账。”我说:“也不是白出。我可以让这位作者分摊一部分书号费。他就是因为经费有困难,买不起一个独立书号,才想到在你那里插队的。”朋友说:“说钱我就不跟你说了。这样吧,我再核实一下,看我们县要出多少本书,如果还有多余的,我就让你这位朋友出。弄来一个丛书号也不容易,不能够把它浪费掉,一定要想办法出够。”我在电话里说:“那我先谢谢你!”朋友说:“先不忙言谢,还不知道得不得行呢!”
挂断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发了好一会儿呆。依我朋友的性格,我知道这事应该能成。我不知道,我这会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告诉苏应丰。真要告诉他,还不知道他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4
也不知道为什么,县里分管文化的领导知道苏应丰正在出一本书,而且还知道我正在为他跑关系,为他联系有关出版事宜。
这天早上,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我忽然接到这位县领导秘书打来的电话,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说是有工作要跟我谈。走进领导办公室,领导早到了。办公室有点乱,这让我想起苏应丰的家。不过苏应丰家里摆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书籍,领导的办公桌上却摆满了各种文件。领导见我进来,指了一下办公桌对面的沙发,让我先坐下。我刚坐下,秘书进门给我送来了一杯开水。我坐了几分钟,领导签了几个文件,这才走过来,坐在了我的对面。领导说:“庹主席,让你到我这里来,是想请你谈一下出书的事情。听说最近你在帮一个名叫苏应丰的人出书,以前也没有听你说起过嘛!不过这很好,我们县不是要出一本书吗?年初定下来要搞的‘六个一’活动,其中就包括要出这一本书。”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可能不能够做好,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还有,把它作为县里要出的这本书合适吗?”领导说:“怎么说一点把握都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把出这本书的事情抓好。还有,我觉得合适,你觉得呢?”
其实,来领导办公室的路上,我就在想苏应丰出这本书的事。以前领导就说过要出一本书,可是没有经费,我又找不到企业赞助,没有办法出县里要求的这本书。我就想,苏应丰出这本书是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应丰要出一本书,这是无意中把我给救了。
当然,苏应丰出书也给我增添了烦恼,给他联系出版社和印刷厂,为他出书跟朋友谈书号、谈优惠印刷费,这些都让我很为难。现在书号落实了,印刷费也谈妥了,书稿也送印刷厂了,出书只是时间问题了。可是在领导面前,我能这样说吗?我只能谈正在做,对能不能够做好没有把握。我想,在苏应丰的书没有出来之前,我这样说是对的。谁也说不好会不会出问题。
领导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庹主席,这件事你不要有什么畏难情绪。既然我们把苏应丰出的书作为县里出的书,我们肯定会给苏应丰帮助的,县里虽然财政有困难,但我们会考虑补助他一些费用的。还有,等书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他搞一个首发式,或者分享会,这些,要没有政府出面,能搞得起来吗?你放心,既然县里有这样的打算,苏应丰出书,就不再是苏应丰一个人的事情了,而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个你懂吗?”
关于书号的事,我那朋友太给我面子了。本来,他们购一个丛书号,是要为他们县的文学爱好者出书的。朋友说,这其中就有他的一本,听了我的介绍以后,朋友说他不打算出了,把名额让给苏应丰。他以后还会有机会出,像苏应丰这样的老同志,说不定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书号费的事不要再提。我们县的文学爱好者也都是不出书号费的,苏应丰也就不用出了”。我很感动。我把这件事给苏应丰说了,他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我那时想,为苏应丰这个老家伙出书,犯得着这样认真吗?又是找印刷厂老板又是找文联主席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是不是很犯傻。
坐在领导的办公室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我这人最近感觉总是不好。领导说:“年底能出来吗?要拖到明年就不好了。我们是把它作为‘六个一’活动的一项活动来完成的。明年还不知道又会提出一个什么活动来呢!我在想,到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首发式或者分享会搞好,一定要弄出一点大的响动来。”领导说到这里,我大致想了一下,离年底还有两个月时间,这个时间应该说不是太紧张,书号是现成的,书稿已经送印刷厂,跟印刷厂催紧点,应该能够完成。我说:“领导,我努力吧,我尽量争取吧。”领导说:“不是努力的问题,也不是争取的问题,是必须要按时把书出版出来。”
从领导那里出来,我要苏应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想把领导给我讲的,也让苏应丰了解一下,让他心中好有个数。苏应丰接到我的电话,很快就过来了。可能是因为出书的事情很顺利,他的脸色看上去很不错。以前对苏应丰忙着要出书,我有些不理解。现在或许应该轮到这个苏应丰,在我对他出书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不理解了。又不是我要出书,用得着这么火急火燎吗?也可能是我想多了,人家苏应丰说不定对我还是心存感激的呢!
我让苏应丰先坐下,要他歇一口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放松一下,关于苏应丰出书,我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过了一会儿,我对苏应丰说:“你准备一下,我两个明天去一趟印刷厂,让印刷厂抓紧给你排版,加紧把书印出来。”苏应丰看了我一眼,说:“不急的,慢慢出,只要能出出来就行了。让人家优惠了那么多印刷费,又怎么好意思去催人家呢!”我说:“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你跟我一道去,这话我去跟苏老板说。你去主要是看还有没有内容需要增删。”
5
所有困难都解决了,苏应丰的书出版很顺利。还没到两个月时间,清样就出来了。分管文化的领导让秘书打电话来,说是要让我送两本过去。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知道苏应丰刚收到印刷厂给他寄来的清样。现在领导需要,我只有让他先送过来,好给领导送去过目。我把电话打给苏应丰,说明情况,苏应丰很快就过来了,手里拿着两本清样,看上去很开心,也可能还有一些小得意。我对苏应丰说:“领导要看看你的书,我只好打电话向你要。看你手里拿着这两本清样,我就知道这书很快就可以出版了。”
自从我把苏应丰介绍给苏应物老板认识以后,我就很少过问此事了。我在忙一个书画展和一个文学讲座。我是搞写作的,联系著名作家、评论家来做讲座并不难,但我对书法这一块就相对陌生,不过你必须得做,否则搞书法的同志就会说你偏心,不关心他们。因为要忙这些事情,我就很少过问苏应丰出书的事了,任由他跟印刷厂联系。
苏应丰把两本清样递到我手里,看上去都有些喜形于色,活生生就是一个老顽童。苏应丰说:“庹主席,你找我?我把印刷厂快递来的这两本清样都拿来了。等印刷厂印出来以后,我再给你送几十本来。我知道,我出这本书,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我说:“倒不是我急着要,是县里分管文化的领导等着要。你可能不知道,县里今年有一个‘六个一’活动,其中就有要出版一本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县里知道你正在出这本书,就把你这本书作为‘六个一’之一来落实了。要求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出来,这不是快到年底了么,这领导自然会很急。”
苏应丰说:“县里就是多事。我想出一本书,这跟县里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用他们的钱。他们要弄‘六个一’,只管弄去就是。我一个退休老头儿,不关心这些事的。”
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嘛!你这就跟我一起去,最近你跟印刷厂怎么联系的,我一点都不清楚,你去了,领导要是问起来,你也好回答。”
苏应丰说:“我不去。我还在上班时就怕见领导,现在你却要我去见县领导,我就更不敢了。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见他们做什么?”
我对苏应丰说:“今天你必须得去,你要不去,你出书这件事,我以后就再不管了。你不要以为现在出书已经差不多了,就可以对我这样使性子了。我告诉你,我要跟苏老板说,就能够把你的书停下来;你相信不相信,这只是分分钟的事情。我说到做到。”
苏应丰说:“我当然相信,我知道你有这个能耐,但我更相信你不会这么做。要不然,你也不会这样跑上跑下的帮我了。好吧,我跟你去就是了。我倒要看看,县领导对我出这本书,到底怎么想的。”
我和苏应丰来到县领导的办公室,领导看到苏应丰,先是一愣,然后就走过来握住苏应丰的手。县领导说:“我猜,你就是苏应丰苏老师吧?文联庹主席在我这里早就谈起过你了。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能出一本书,这为我们县文化领域可是做了一件大事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不错,这个确实不错。”
领导翻看了苏应丰拿来的清样,好久没有说话。我和苏应丰站在一旁,头微微低着,有点像两个等着法庭宣判的囚犯。又过了一会儿,领导才说:“你们坐吧,站着干什么?”我和苏应丰这才像得到特赦令的囚徒,忙在沙发上坐下来。就在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秘书端来了两杯水,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出去了。出去的时候,还不忘把门关上。
领导把清样放到书桌上,回过头来对我和苏应丰说:“关于出书,这个我不太懂。庹主席是行家,就由你来说说。”我说:“其实我也不太懂。主要是苏应丰苏老师在做这件事,最近他一直在和印刷厂联系,苏老师才会说得更清楚。”苏应丰说:“是我在联系,但主要是庹主席在帮我,帮我跑书号、跑印刷厂,都是他在做,要不我出这本书肯定会非常困难。”领导说:“不过这些都已过去了。我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你出了这本书,才有了我们‘六个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位退休老同志,你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老有所为。我们其他的老同志要都能像你,我们县的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不少老同志动不动就跑到县委政府来说事,烦心啦!”领导说到这里,我和苏应丰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领导还说:“等书正式出版出来,我们可以搞一个首发式,还可以开一个作品分享会,庹主席,是这个说法吧?”我点点头,我对领导说:“对,就是首发式和分享会。”领导又说:“出一本书不容易,非常有必要把首发式和分享会搞得隆重一些。”我趁着领导高兴,抓紧对领导说:“苏老师出书不容易,如今又被纳入了县的‘六个一’活动,看能不能够在资金上给予苏老师一些支持?”领导听了我的话,看了看苏应丰,说:“完全应该,出好一本书,这已经不是苏老师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县的事情……”说到这里,领导面露难色,说:“只是我的二次签批资金已经安排完了,手里已经没有钱可以安排了。这样吧,我再想点办法,等有消息了,我再跟庹主席联系。”
6
年底了,苏应丰的书正式出版了。只是没有搞首发式,也没有开分享会。这我和苏应丰都没有想到。好在当初苏应物给我和苏应丰提建议,要在扉页上印上“××县‘六个一’活动作品”字样时,我没有赞成,尽管苏应丰很动心。现在看来,我当初还真有些先见之明。
苏应丰这本书没有以官方的名义搞首发式和分享会,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本书的内容,我一看就觉得不好。除了有几篇小说、散文之类的作品,还有言论,甚至本报讯之类的豆腐块文章,他都收进书里去了。早年,苏应丰热衷于给报纸写文章,尽管写的多发的少,可还是乐此不疲。可能是看他勤奋,市报社给他发了通讯员证,这让苏应丰兴奋了好久。把发在报纸上的一些质量并不高的文章也收入文集,我一向有异议,可苏应丰不为所动。可能是觉得自己老了,写不动了,收进文集,就可以盖棺定论了。还有就是如果不收入这些文章,要出一本书,文字量就不够。我之所以反对在扉页上印上“××县‘六个一’活动作品”字样,就是觉得这本书质量不高,怕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毕竟我是文联主席,苏应丰出这本书我又一直都在参与,这方面的觉悟我还是有的。现在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可苏应丰还在等。自从苏应丰和我去见了县领导回来,他就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不仅要出书,而且县里还要为这本书搞首发式和分享会,这是多么大的荣耀。现在书已经从印刷厂拉回来,整整一千册,在他已经很零乱的屋子里码成了小山。时不时,苏应丰会看着面前的一大堆书,眼光迷离而温润,还会拿起来一本,在手里不停地翻动摩挲,那神情充满专注和慈祥。
一个早晨,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苏应丰来了。他手里提着还散发着油墨味儿的书,应该有十多本,提书的手被强行往下拉,看上去有些吃力。苏应丰把书放在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庹主席,我给你送来了十多本,你看够不够?”我说:“有一两本就够了,要不了这么多的。”苏应丰说:“我知道你要不了这么多,可你们办公室不是还有其他人么?还有,你这里来的人多,你还可以送人啊!对了,我还准备再给你送百把本过来,你好送你那些朋友。”我说:“不用,你自己留着吧,我这里有这十几本足够了。”苏应丰说:“县里说要给我的书搞首发式和分享会,肯定需要书吧?不知什么时候要,还有要多少,可不能要得太多,我总要留下一些来做个纪念吧。”我说:“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说。”
“六个一”活动总结表彰会如期召开。“六个一”活动中的“一本书”,用一本画册来代替了。我想,等总结表彰会结束,我去看看苏应丰,看他是不是还在看着他的一堆宝贝书籍发呆。苏应丰原本要出一本书,或许真是出于他对写作的热爱,虽然文章写得并不好,但毕竟是他这些年来写作的结晶,也算是对自己人生有一个交代。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的写作其实也并不好。
“六个一”活动总结表彰会散了以后,我去了苏应丰家。苏应丰见我来了,说:“庹主席,你请坐。”我坐下,不知道怎么跟苏应丰说。苏应丰给我端来一杯茶。苏应丰说:“庹主席,你们的总结表彰会散啦?”我说:“散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苏应丰说:“今早我去你办公室了,你们同事说,你去开总结表彰会了。这样,我很快就回来了。你散会后会来我这里,是你同事告诉你我去过你那里了,是不是?”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是我自己要来的。”
自从那次组织采风活动来过苏应丰家,我再没有来过。现在苏应丰的家还是乱,但已经好了很多。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个大书橱,这个大书橱里摆满了他出的书,在我面前形成了一面书墙。近千册书,摆开来,还真有点气势。苏应丰退休前教书,退休后蜗居在家,几乎没有朋友,后来加入文学协会,除了参加一些活动,平时还是很少走动,因此朋友并不多。苏应丰送书,大概就送出去了几十本,余下的就砌了这面书墙。我看了这面墙,心里好一通感慨。我原来想借着县里搞首发式和分享会,还想借此为他搞一个签名售书活动,能够帮助卖出去一些最好。虽然,苏应丰出这本书整体质量不高,但我相信也还是有可取的地方,不能说一无是处。
我本来要安慰一下苏应丰,还没等我说上话,苏应丰先说话了。苏应丰说:“县里不打算为我的书搞首发式和分享会,就算了。只是苦了你庹主席了。”我说:“哪里的话?是我人微言轻,帮不上你什么忙,真是对不起了。”苏应丰说:“庹主席要这样说,我就会难过了。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还说没有帮上忙,这你让我如何是好。”苏应丰的脸色不大好,有点像印书用的80 克轻型纸一样,看上去有些泛黄,不过当他望着那一面书墙的时候,他的脸色很快就好了。看得出,他对能够出这本书还是很满意的。
7
我没当文联主席了。没有任何征兆。
我从文联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还在文联上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段时间,我更多的是在为退休热身,免得真正退休了把自己弄得无所适从。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我忽然想去看看苏应丰。没当文联主席以后,刊物差不多我也没有参加编辑了,但依然有人向我投稿,都是些熟悉的名字。只有苏应丰再没有来送过稿,电子邮箱里也看不见有苏应丰的稿子。以前他写稿投稿总是很积极,这总让我心烦;现在他不来投稿了,我又很希望他来。不投稿,来我这里坐坐也是很好的。
苏应丰家没什么变化。苏应丰见了我,有点吃惊,也有点喜出望外。苏应丰说:“庹主席,我不知道你要来,快请坐。”我说:“我已经不是主席了,跟你一样,很快就会成为一位退休老人。”苏应丰说:“庹主席,我听说你不当主席了。是不是我出书给你造成了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很吃惊,说:“谁说的,没有这回事。你出一本书还会影响到我,不可能的。”苏应丰说:“这就好,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真怕是因为我出书影响了你。”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年龄大了,不当文联主席很正常。我问你,自从你出书以后,怎么就不来投稿了?”苏应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还投什么稿?我都已经不写了。”我问为什么,苏应丰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写了。”苏应丰在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眼那面书墙,那上面已经蒙着很厚的一层灰尘。苏应丰看着这面书墙,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脸红一阵白一阵。
又过了半年,我又鬼使神差来到了苏应丰居住的小区。可远远地,我怎么也看不见那个小区。走近后才发现,这里早已经是一片废墟。一位在废墟上捡废旧钢筋的老人,初看很有点像苏应丰,细看发现不是。我问老人:“怎么,这里的人家都搬走了?”老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里不是要搞棚户区改造么?这里的住户早都搬走了。”我问他:“你知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名叫苏应丰的老人?”老人说:“你是说那个书呆子?死了,早死了。”我大吃一惊,说:“苏应丰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呢?”老人说:“这书呆子是被他出的书砸死的。”
我忽然想起那个大书橱,上面摆满了苏应丰出的书,形成一面很有气势的书墙。
大书墙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