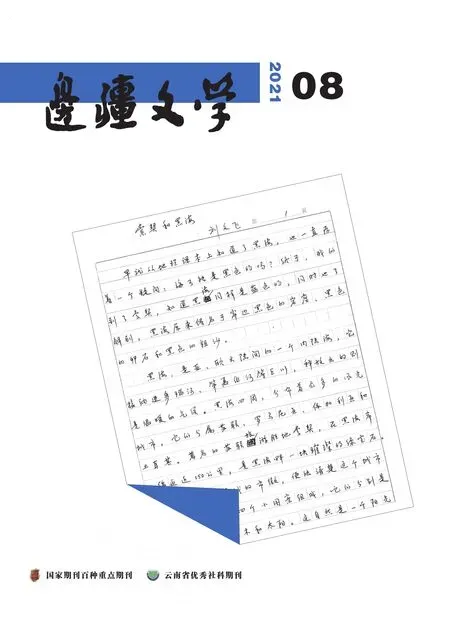响卜 短篇小说
于小耕
一
我看冯二还在往屋里抱柴,就让他把北炕也烧一烧,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慌里慌张地把半捆柴送进灶坑。不一会儿,我的屁股底下暖和了许多。
冯二家南北两铺炕,南面的烧得勤,直烫屁股,北面的不住人,烧得少。烫屁股的南炕要腾出来给周先生,一会儿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有事求他。
八点刚过,南炕上就挤满了人。邻里乡亲、三叔四舅、七大姑八大姨得到信儿都聚到这里,甭管有事没事,总要让周先生给看一看、算一算、找一找、破一破,迷信不迷信暂且不说,就是大家往一起凑合这股热乎劲儿,也是着实让人喜欢的。
周先生年轻时做泥瓦匠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后来跟一位算命师傅学了这门手艺,没想到这行饭碗端起来就没放下。近几年,周先生走路有些吃力,经人引荐我成了他的助理。
还没到晌午,已经有九个人从周先生这里“满载而归”了,有的人拿着一道符信誓旦旦地往家赶,有的人默念一首打油诗将路人的招呼声当作耳旁风,还有人既激动又亢奋一时按捺不住就像喜鹊一样抽身飞走了。
徐大海来得有点晚,他递给周先生一张纸条,那是他儿子的命运代码。周先生扫了一眼,掐指一算脱口而出:“此命推来有官星,庶民之子做公卿。经天纬地人中凤,朗朗乾坤任尔行。”
徐大海听完直拍大腿,跟打了鸡血一样,掏出一百元钱“啪”一声拍在炕上,霸气外漏。周先生捡起纸币,抚平边角的褶皱,塞进棉袄内侧衣兜里,嘴角微微上扬。徐大海说要把孩子不平凡的命运告诉他爹,于是得意忘形地跑向屋外。
小巴黎一个侧身挤进人群,撩起大衣襟坐到了炕沿上。“老周,给我也算算,算我这辈子还能吃上几家井水?”小巴黎话一出口,就把大伙逗乐了,她有过八次离婚经历,村里人就封了她这么一个洋气的外号。
围观的人群中不乏单身汉,“俺家那口井水旺,来不来?”“不嫌弃的话,我耕地来你浇园,你呀嘛你是我滴责任田……”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小巴黎顾不上和这些男人闹,剜了他们一眼,转回身瞅着周先生,这边才是正经事。
或许是累了,或许是不习惯“老周”这个称呼,周先生摆摆手,屁股在炕上挪了挪,“今天不算喽,今天就这样,大家先回去吧。”周先生说着要起身,围拢过来的人放不过他,“这还没到晌午,再给我算算。”“别走哇,俺这媳妇娶了二十多年,算算啥时能结个果子……”
“不行,今天算的太多,容我缓缓,等明天。”周先生撂下这句话,大伙才让他穿鞋。我扶着周先生走向屋外,正好碰上马聪明开着拖拉机停在大门口,“咋的,我一来你就走,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不给大家好好算算?”马聪明嗓门大,说话跟吵架差不多。
作为助理,我紧忙上前解释,“周先生有规矩,每天只算十个人,一个都不能多,不好意思啊。”
马聪明早上听说周先生回来,他火急火燎地往这边赶,嫌走路太慢,就开起了拖拉机。“规矩都是给旁人定的,”马聪明见周先生没开口,一把将他抱起上了拖拉机,周先生又瘦又小,在马聪明怀中像个孩子,耷拉着肩膀不说话。
马聪明一脚油门踩到了自己家,进屋就把周先生放在炕上,面前摆了一张炕桌,临走前沏好的茉莉花茶端了过来,还冒着热气。
我跑得飞快,在拖拉机后边撵了好半天,紧跟着马聪明他俩前后脚进屋。因为没能保护好自己的老板,我脸上、嘴上全是歉意,周先生摆摆手,提示我没啥事,别大惊小怪。他双手贴在茶杯上,跟马聪明强调,不能破了规矩,改天再算也不碍事。
周先生是靠山屯走出去的奇才,这个小学都没念完的人,凭着一张嘴闯世界,这些年赚得盆满钵满,光是三亚、厦门和西双版纳的房子数都数不完,别人嫉妒也没用,祖师爷偏偏赏他这碗饭吃。
有了名气,周先生这些年总也不在家,他带着我天南海北地走,朋友圈里三天两头就换一个位置信息,什么大庆、大同、大理啊,什么锦州、沧州、亳州啊,什么青岛、秦皇岛、济州岛啊……别看他走路一瘸一拐,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刚才马聪明的行为简单粗暴,有些失礼,周先生并没有生气,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什么世面没见过呀。他把刚才这一幕,当成家乡人们对他的爱,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如今是有身份的人,香饽饽被大家争着抢着,再正常不过了。
二
马聪明没念过几天书,斗大的字识不上两筐。就是这么个人,在周先生刚入行不久,就给他抖了个包袱。
说起来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周先生只身一人走街串巷,累了就在马聪明岳父家停下歇脚,见院子宽敞,将桌子一摆,人群就围拢过来。
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无论九零后还是六零后,大家对他人的隐私总是不乏窥视欲,尤其是身边熟人的命运走向甚至比明星八卦更耐人寻味。
周先生不到四十岁的年龄,胡子拉碴,衣着打扮有些老气,不过这丝毫没有降低他的职业身份,就像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中医,越是年老越容易被人信服。年岁不仅是增添阅历的筹码,还是施展才能的外衣。
多数人让周先生算了之后都说准。给岳父家送大米的马聪明在人群中看热闹,他从小就认为这是迷信,今天非要在周先生身上验验真假。看大伙算的差不多了,马聪明挪一下板凳,坐到桌子前,“给我也算个人。”
周先生问他给谁算,马聪明不说,“让你算就算!”
“那好,把生日时辰报一下。”周先生觉得这人有些鲁莽。
“庚午年,九月初七,嗯……对,晌午。”马聪明犹豫一下,很确定地说。
周先生掐算半天,思考再三问了一句:“这时辰没错吧?”
“没错,你算完了?”马聪明有些催促的意思。
“别着急,”周先生又掐算了一遍,眉头一皱,自言自语:“不能啊。”
聚拢过来的人比刚才厚实了许多,里三层外三层,没人说话,都伸着脖子往里瞅,从天空俯瞰,人群围成的圈就像一个巨大的钟表盘,周先生和马聪明坐在表盘中央的原点两侧,像停止的时针和分针,没人开口说话,现场鸦雀无声,时间好似凝固。
过了好久,马聪明打了一个喷嚏,圈中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犹如上了发条的钟表,秒针开始有节律地移动。周先生貌似比刚才老了一些,那副疲惫的样子像刚干完农活。周先生终于开口说话,“这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他在征得马聪明的同意。
“有啥说啥,咱不怕外人听,说就完了。”马聪明说话倒是爽快。
周先生咬着嘴唇,有点为难,但还是想说道说道,“我先不说这人,我先说这人父母,你看咋样?”
“你磨蹭啥,说!”马聪明有些不耐烦。
“好,我说这人母亲身材魁梧,善于奔跑,脊背有力,可担重物。”周先生说完眼睛盯着马聪明。
这勾起了马聪明的兴趣,他示意周先生继续。
“我再说这人父亲,耳朵奇长,性情暴躁,声音迥异,耐力不凡。”周先生紧盯着马聪明眼睛,仿佛那眯起来的一道缝能泄露秘密。
“哎呀,对!接着说。”马聪明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算的这个人不简单,体质结实,兼具父母特长,但……”周先生停顿一下,马聪明瞪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但是,这人不可能有子嗣,必定孤独终老。”周先生说完,和马聪明的目光撞到了一起。
“哈哈,你他妈的成仙了,哈哈,成仙了。”马聪明腾一下站起身,甩袖走出人群,从岳父家的马棚里牵出一匹骡子,在众人的注视下套上马车,他坐上去挥了一下鞭子,骡子踩起轻快的节奏上了大道,转眼间跑远了。
小巴黎在人群中,当时的她还没这外号,还没“八离”这样的资历,但嘴快是天生的,“你这缺德玩意儿,哪有给牲口算的理儿,亏你也想得出来!”她说完朝马聪明远去的方向啐了一口吐沫。
周先生给骡子算命的事传遍了十里八乡,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被普及了生物学知识——骡子是马和驴两种动物结的果子,他们都知道。
给骡子算命这件事,对周先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好还是坏,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大家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说周先生真乃神人也,名不虚传;也有人说他被一个乡野莽夫给愚弄了,还不自知。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们都知道靠山屯有个周先生,这个周先生不仅能给人算,还能给牲口算。
给骡子算命的事对马聪明影响不小,这件事彻底颠覆了他固有的思想和观念,他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姓周的瘸子,甚至赶车回去的路上还有一点愧疚和自责。
好长一段时间里,靠山屯的人们将周先生的话语奉为圭臬,大家觉得周先生深不可测,给牲口算命只是冰山一角,那只不过是骡子身上的一根毫毛罢了。
至于周先生还有哪些过人之处,那些因好奇而产生的联想,充斥在靠山屯人们的现实中和梦境里,就像一个个尚未打开的盲盒,层层包裹的外衣因神秘而引人遐思。
三
见周先生上了马聪明的拖拉机,大家也一路跟着凑到了马家,那些未能如愿的人们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嫉妒,都以为周先生会给马聪明“开小灶”。大家陆陆续续进了屋,周先生正坐在炕上喝茶水,没有继续工作的意思。
看大伙都围拢过来,马聪明吩咐儿子马溪给邻里乡亲倒茶水。别看马聪明平时有些鲁莽,种地可是一把好手。每年春播前,村里的人都向他取经,比如山坡地用什么种子多产粮,洼地选什么品种抗倒伏,土地深耕好还是免耕好,他都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心服口服。
马聪明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接受新鲜事物一点不比年轻人差,他在农耕劳作中不断寻求技术革新,在村里最早实现了农业全程机械化。这几年,粮食增产,腰包鼓了,儿子上了高中。马聪明闲下来时就不满足,看着村里谁把家搬到了省城,谁跟着子女去了大城市,他的心就变得不安分起来。
马家上溯三代都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收入不少也不多,毕竟是靠天吃饭,收成由天不由己。此时自家炕上的周先生成了马聪明的榜样,周先生这份工作,没什么劳动强度,掐掐算算就来钱,你说让人眼馋不眼馋。
借着这次周先生回靠山屯的机会,马聪明想和周先生唠扯唠扯,交流交流,想让这位见过世面的奇人给他支个招儿、出个道儿,如果可以,再帮他看看身上还有哪些潜能可以挖掘,还有哪些潜力有待开发。
趁着周先生解手的空档,马聪明扶着他进了自家仓房。仓房紧挨着正房,平时停放着一些农机具和米面杂粮,马聪明在里面搭了一个火炕,一进门热气扑脸。周先生竖起大拇指,说马聪明不单种地是把好手,过家在靠山屯也找不出第二个。
周先生越是这样说,马聪明就越是觉得不好意思,在农村这样的家庭属实过得不错,但是怎么能和城里人比呢。远的不说,就是眼前这个姓周的瘸子,手中的房子就有几十套,人家摸过的钱,马聪明见都没见过。
马聪明说话直,开门见山,他想跟着周先生干一番事业。周先生笑得面若桃花,问马聪明想干啥,马聪明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子丑卯酉。周先生夸他,如今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守家在地,自在安然,那就是福中之福了。马聪明连连点头,但好像并没听进去,突然问了一句:“现在跟你学这个晚不晚?”
这句话让周先生猝不及防,竟然有人对自己吃饭的家伙感兴趣,周先生一时半会不知道如何回答。马聪明看出了这句话自带笑料,“晚是晚了点儿,我也是马上奔五十的人了。那你看,什么看相、摸骨啥的,我……我学学咋样?”
周先生摇摇头,一言不发。他心想,眼前这个膀大腰圆行为鲁莽的马聪明,竟然也有憨厚可爱的一面。任何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周先生思考再三,打算教给马聪明一个小技能,“教你一招也无妨,平时有事可以预测,没事就图个乐子。”
此话一出,把马聪明高兴坏了,他竖起两只耳朵,立在周先生面前,原本高过周先生一头的人如今矮了半截,等着周先生发话。
周先生示意他行有行规,这个东西不能明说,他在马聪明耳朵边窃窃私语。马聪明好像明白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他不住点头的样子像个奴仆。
看到周先生手指比画着,马聪明眼前闪过一道灵光,“挣了钱,咱俩三七分?”他惊讶地问。
“额……我是说,这个东西三分真相,七分想象。”周先生差点笑出声来,眼前这个兄弟竟是个求财心切的家伙。
两个人神神秘秘,嘀嘀咕咕,好半天才从仓房出来。马聪明推开仓房门,一脸得意,满面红光。
周先生在他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进屋,马溪提着暖壶过来给他续杯,周先生夸这孩子长得有福气。
刚才围拢过来的人耐不住寂寞,打麻将的打麻将,推牌九的推牌九,马聪明的媳妇二英赶集回来,买了不少菜,说中午预备了饭,让大家都别走。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饭菜就上了桌,有小鸡炖蘑菇、鲶鱼炖豆腐、干煸蚕蛹和锅包肉,外加四个凉菜,荤素搭配,有模有样。
动筷子前,周先生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还配了一行字“无论走多远,心一直在围绕家做圆周运动,回来真好。”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几十个赞,有小巴黎、徐大海、冯二,还有蹦爆米花的老胡头、卖糖葫芦的老贾头等等。小巴黎还在下面留言,说周先生有诗人气质。
午饭一直吃到下午四点,直到男人们在酒精的作用下耷拉着头昏昏沉沉地睡去,女人们才开始收拾桌子,洗盘子刷碗。
我和周先生一觉睡到了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靠山屯,到机场坐四个小时的飞机去重庆。
听说,我们走那天的晚上,马聪明就病了,浑身绵软无力,低烧断断续续,整个人精神恍惚,总是疑神疑鬼。这个虎背熊腰的男人活了四十多岁几乎没吃过药没打过针,他在家炕上躺了三天才好。
不知怎么回事,自从马聪明和周先生在仓房窃窃私语之后,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尤其是他那两只耳朵变得敏感起来,对声音有着超乎寻常的洁癖。
四
“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不为俗尘洒一物,只为美酒动心弦。”马聪明哼哼着下了炕,二英见他病好了就紧忙端来早饭,说他气色好多了,心情也不错嘛。还问他哼哼的什么曲子,马聪明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扒拉几口饭就走出屋外溜达去了。
二英怔怔地看着,不知自家男人得了啥病,话少了,像是心里藏着东西。
马聪明大老远就看见了徐大海,徐大海刚要打招呼,马聪明紧忙抄起手机假装接电话,徐大海不便打扰,点个头与他擦肩而过。见徐大海走远,马聪明自言自语:有啥可聊的,无非就是问我吃了么。
路过小巴黎家门口,马聪明快走了几步,这个嘴碎的女人话多,他今天格外不喜欢听她讲话。小巴黎拎着泔水桶出门,见马聪明就想上前唠扯几句,问问那天周先生在仓房里跟他嘀咕了啥。刚要张口,马聪明戴上两只耳机,径直往前走,看都不看小巴黎一眼,那根耳机线在屁股后面甩来甩去。小巴黎盯着他的背影看老半天,有些莫名其妙。
马聪明转悠到村西头的小卖店,隐隐约约听见门口有说话声,“芝麻酱不要了,大酱来点,”冯二正在电话里说自家小卖店进货的事情,刚好这句被马聪明听到了。马聪明停下脚步,问冯二要新进大酱?冯二点点头,说县城黄家豆瓣酱做得不错,等货到了让他尝尝。马聪明愣了一下,像是咂摸“酱”的咸味儿,突然乐呵呵地说,太好了。说着顺路继续往西走。冯二心想,这个马聪明平时很少光顾小卖店,怎么听说要新进大酱就这么兴奋,冯二摸着后脑勺,搞不明白。
马聪明还在咂摸这个“酱”,刚才冯二所说的大酱,也就是豆瓣酱。严格来说,冯二的那句话是马聪明走出家门听到的第一句话。这让他格外上心,他像咀嚼炒熟的花生米一样,认真咀嚼起冯二说的每一个字。“芝麻酱不要了,大酱来点,”马聪明跟丢了东西一样,急忙往家跑,一路上他迎着向他打招呼的老人和孩子,偶尔举手回应,不说话,闭着嘴,就像嘴巴张开会跑掉好运气一样。
到了家,马聪明发动拖拉机,一口气开到镇上的彩票站,买了二百块钱的彩票,像藏私房钱一样将一张张纸片塞到鞋垫下方,然后得意地将拖拉机开回家。运气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他鞋垫底下那些小纸片第二天就变成了一摞钞票,总共有八千多块钱。
马聪明后来的解释是,冯二的那句话提醒了他,芝麻酱不要,也就是像芝麻一样的小奖不要,大酱来点,就是大奖来点。
中奖的钱,马聪明原封不动交给二英,二英乐得合不拢嘴,原来在家炕上躺三天,就是为了寻思中奖啊。不管怎么说,二英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着实是憨厚可爱,那名字里的“聪明”二字就像幸运之神一样,降临在他家,看来父母当初给取这个名字没浪费笔墨。
有了中奖的经历,多数人都喜欢再来一次,可这件事并不像“再来一瓶”一样那么容易得到。接连几天,马聪明每天早上都要在冯二的小卖店门口路过几次,他还想听听大酱的声音。可是左等右等,冯二也不说。冯二以为马聪明老在门口转悠,可能有事,就问是不是家里缺啥要买,马聪明没听到要听的话,爱搭不理地回了一句,啥都不缺。冯二热脸贴在冷屁股上,自找没趣,也就不再问他,自顾自地摆放商品。
这天一早,马聪明吃完饭就出门遛弯,小巴黎家是必须要经过的,他今天故意放慢脚步,想听听这个单身女人能说出来啥花样。小巴黎虽然单身一人,但一日三餐绝不糊弄,每顿饭都做得十分精细。见马聪明在门口慢悠悠地踱步,小巴黎藏不住话,就问马聪明那天为啥急匆匆地路过她家门口。
马聪明心情不错,说是自己做了一个好梦,中途被媳妇吵醒,为了续上剩余的片段就在马路上寻找梦中的一草一木,看看能不能勾起自己的回忆,以便睡午觉的时候还能接上那一段暂停的美好。小巴黎撇着嘴,说马聪明啥时候也这么能编瞎话了,还有鼻子有眼的。
第二天早上,马聪明还要路过小巴黎家,赶巧小巴黎在门口倒泔水,她问马聪明早上吃的啥,马聪明让她先说。小巴黎咂摸下嘴说,“枣、丸子和鸡蛋,就着稀粥。”马聪明听完皱了皱眉,脸色变得阴沉下来,没等小巴黎说话,他就原路返回了自己家。刚到门口,二英就哭丧着脸说,马聪明的舅舅快不行了,刚刚舅母打来电话,让大家都过去。
还没从小巴黎的早餐中抽离出来,就听到有人给舅舅报丧,着实让马聪明感到意外。二英打了车,载着一家三口往市里的医院赶。车开到半路,马聪明像是突然开了窍,小巴黎的早餐“枣、丸子和鸡蛋,就着稀粥。”连起来不就是“早完蛋,舅西走”嘛!马聪明竟然恨起自己来,不该在小巴黎家门前停留,应该快走几步,或许能帮舅舅躲过这一劫。
五
舅舅去世后,马聪明愈加笃信周先生传授给他的技能,整个人变得谨慎而多疑。他恨透了小巴黎,要不是小巴黎告诉他早餐吃了啥,他的舅舅也许不会那么早完蛋。
人总是要出门的,小巴黎家位于屯子中间,是进出村屯的必经之路。每次路过小巴黎家,马聪明都会戴上耳机,把手机上的音乐放到最大声,以此抵消那些听起来“不吉利”的声音。
可是,马聪明发现,音乐里唱的也不都是大吉大利的歌曲,比如有的歌名里带有“死”字,在他看来就不能听,带有“痛哭”“伤心”的会被他从手机上删掉,删来删去,只剩下一首《恭喜发财》,被他设置了单曲循环,音量开到最大。有的人是眼里容不得沙子,马聪明是耳朵里容不下“不吉利”。
整天戴着耳机也不是个事儿,人毕竟是社会化动物,不像城市关起门来互不往来,在农村母鸡下几个蛋都不是秘密,何况一个大活人呢。这些天,马聪明的怪异行为引起了靠山屯人们的注意,大家觉得这个跟周先生在自家仓房窃窃私语的马聪明瞧不起人了。
这天清晨,刚吃过早饭,马聪明戴着耳机走出家门,寻思往冯二的小卖店方向走一走,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听到“大酱来点”,他不紧不慢地走着,耳机里无比熟悉的歌声既喜庆又悦耳。马聪明刚走过小巴黎家,就被身后一只大手吓了一跳,原来,徐大海通知他去村里开会,喊了三声马聪明都没听见,徐大海就从后面撵上来拍他。
马聪明一扭头,拽掉右侧的耳机,那个耳膜瞬间暴露在空气中,无处遁形。
“该死的老马,我叫你三声都不答应。”徐大海嗔怪马聪明。
这句话不要紧,马聪明原本红扑扑的脸蛋立刻阴沉下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徐大海也觉得不妙,马聪明这是怎么了,正愣神儿。马聪明撇下耳机,抡起拳头朝着徐大海打去。徐大海只觉得腮帮子发酸,瞬间栽倒在地。
“你他娘的,我就寻思着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马聪明很气愤,一大清早就听见这么不吉利的话,这是他这些天听到的最不吉利的话。撇下徐大海,马聪明像个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
这事完得了吗,不一会儿徐家四兄弟找上门来,徐大海招谁惹谁了。二英就出面解释,该道歉的道歉,该掏钱的掏钱,徐家这才就此罢休。马聪明刚才还气汹汹的,这会儿成了霜打的茄子,蔫躺在炕上,半天憋不出个屁来。
二英和马溪都奇怪,这周先生走后,马聪明究竟是犯的什么浑,怎么竟干些出人意料的事情。难道是上山拾柴被野鬼吓到了?二英让马溪找几张邮票,最好是从关里邮寄过来的(东北人习惯把山海关以南的地方叫关里)。
马溪翻箱倒柜,真找到几个盖着外地邮戳的信封,那是他中学时和笔友们往来的信件,没想到它们会在父亲这里派上用场。马溪小心翼翼地揭下三枚邮票,他们分别来自聊城、邯郸和连云港。
当天晚上,趁着马聪明熟睡之际,二英起身将三枚邮票掐在手上,在丈夫头顶对着的炕沿儿将其点燃,火焰燃烧之际还念了三声丈夫的名字。见马聪明一直呼呼大睡,二英吐了一口气,就像丈夫的魂儿真被她叫了回来,悄悄钻进被窝。
二英刚把眼睛闭上,马聪明就翻身起来去屋外撒了一泡尿。二英寻思,这个该死的男人,原来刚才一直在装睡。好吧,在鬼神面前,只要把戏份演足就好,管他是真睡还是假睡。
第二天醒来,二英给马聪明做了他爱吃的韭菜炒鸡蛋和溜肉段。马聪明吃完美滋滋地剔着牙,问儿子马溪能不能把那个能包住耳朵的耳麦借给他。难得父亲有兴致,马溪立马从抽屉里拿了出来,特意强调这个耳麦有降噪功能,还给父亲演示了一遍。马聪明惊讶于高科技带来的便利性,如获至宝。
马溪没想到,这个耳麦从此以后就长在了父亲耳朵上,除了洗澡不戴,就连睡觉都戴着。有了这个玩意儿,马聪明觉得自己彻彻底底与那些不愿听、不想听和不吉利的东西隔离了,这个世界只有他想听的。
自从马聪明耳朵上长上了耳麦,大家也就不跟他说话了,说了也听不见,说了等于白说,那说他干嘛。不过,人怎么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呢,总免不了与人交流。二英和马溪那是自家人不必多说,哪怕一个眼神,马聪明都知道啥意思。和外人嘛,马聪明就跟他们对口型,用手比画。
屯子里的人都奇怪,好好的一个人大病一场怎么就成了聋哑人。村里人不知道的,就为他惋惜,说他因为一场大病烧聋了耳朵,从此遗失了世界最美妙的声音。
六
对口型也好,用手比画也罢,总之还是没有说话方便,难免会出错。
这天,小巴黎刚从冯二家小卖店出来就撞见了马聪明,她是个好事的人,喜欢问东问西,有时候还会揪住一个事情刨根问底。最近马聪明行为诡异,神神叨叨,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正好,平常躲着,今天撞见了。
小巴黎听说如今跟马聪明说话要对口型,还得比画。她想问那句使用率最高的打招呼用语“吃了么”,可这嘴发音容易,用手比画还不熟练。她就把嘴张得大大的,两只手像两把扫帚往嘴里做清扫状。马聪明瞪了她一眼,掀开门帘进了小卖店。
小巴黎觉得被羞辱了,转回身掀起门帘也跟了进来,从身后一把摘掉马聪明的耳麦,“你聋啦,和你说话听不见。”小巴黎恶狠狠地瞅着马聪明,就像心中积怨已久,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好多天没听过外面的声音了,马聪明觉得这些声音是那么陌生,那么刺耳。没想到第一句先听到小巴黎说自己聋,马聪明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因为小巴黎的早餐,让舅舅提前去送死,这回,这回新账老账一起算!马聪明一个巴掌拍在她的太阳穴上,小巴黎被扇出去好几米,挺了下身子趴在地上。
冯二吓坏了,他紧忙上前抱起小巴黎,大拇指掐着人中,往脸上喷了口凉水,小巴黎这才缓上一口气,“多悬啊,多悬啊,这是咋的了。”冯二说着,眼泪不知道何时流了下来。
马聪明这回没走,在一旁看着,他那只耳麦掉在地上,还循环播放着同一首歌曲“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Oh,礼多人不怪……”冯二的两个孩子捡起耳麦,不敢交给马聪明,他们不知道他下一刻会有什么惊人举动,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冯二接过来递给马聪明,转回身问小巴黎要不要去医院,小巴黎摆摆手,捂着头,在那两个孩子陪同下走回自己家。
小巴黎一个人,没儿没女,挨了马聪明这么一巴掌,让她拾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她的第四任丈夫是个酒鬼,喝完酒也是这么打她的,每次喝完酒都要打她一顿,在农村这样的家暴是没人关心的,两口子吵架,床头吵完床尾和,所以小巴黎当年挨打,没有一个人过问,也没有一个人关心,挨打的次数多了,她就变得耐打了,知道怎么着不疼,知道疼过了就麻木了。马聪明这一巴掌,对小巴黎来说,只是勾起了她的陈年哀怨,由此产生的悲伤大于疼痛。
二英知道事情后,不知如何是好。要说女人最了解女人,一个单身女人被她丈夫扇了一巴掌,二英的心里五味杂陈,又是送老母鸡汤,又是送鹿胎膏,反正家里有的,自己能下手做的,全都送去了,如果马聪明的胯下之物能送出去,二英也绝不反对,她恨不得把那玩意割了给小巴黎做个汤。
二英纳闷,马聪明这是得了什么病,听不得不吉利的话,听不得别人说他不好,这哪行啊,天底下哪能所有的事情都依着他呢。难道是上次叫魂不管用?二英心里七上八下的,寻思着晚上跟马溪合计一下,要不要带着马聪明去一趟精神病院。
有了徐大海和小巴黎被打的事情,村里人都开始警惕起来,路上遇到马聪明就远远地绕开了,实在躲不过去就背着身子装作打电话,或弯腰把鞋带解开再系上一个蝴蝶扣。赶上集体活动,大家就不怕了,反正那么多人,不怕马聪明搞突然袭击。
人多的场合大家也很少见马聪明,他们躲着马聪明,马聪明也躲着他们。只有村里开大会的时候,大家才会看到马聪明,有谨小慎微的人逼不得已跟他交流,就用一只手遮掩嘴巴跟他说,生怕因口型不对引起误会。
年轻的女人还好,用手捂着嘴略带几分矜持与羞涩。上了年纪的男人捂着嘴就显得有些滑稽了,但也并非一点好处没有,至少马聪明看不见他们因牙齿缺失而带来的自卑与胆怯。
马聪明的耳麦掉在地上后,降噪效果不如以前,紧贴耳朵的海绵也因为频繁佩戴破损了。马聪明就把耳麦的声音调到最大,以此抵消这个随身之物在硬件层面的不足。
七
谁也没想到,马聪明会死在驴蹄之下。
那天早晨,太阳还没露头,马聪明被岳父发现躺在他家的马棚里,口吐鲜血,面色紫红,双手紧捂肚子。警方判断马聪明是被驴踢踏致死,确定“它杀”,排除了“他杀”。
马聪明岳父搞不明白,自己的女婿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蹊跷的是他怎么会跟一头驴结下仇呢。
其实,马聪明距离岳父家也就四公里的路,他自幼熟悉牛马驴骡这些东西,还干过劁猪骟马的活计。前些天,马聪明因为扇了小巴黎一巴掌,二英就不跟他同一铺炕睡了,二英说想把马聪明裤裆里的东西割了炖汤给小巴黎补补身子,没想到她随口说的气话,马聪明却当真了。自己那东西这三年五载还用得上,岳父家那头叫驴的阳具倒是闲得寂寞,马聪明思来想去,觉得不如骟了它。
那天一早,天还没亮,马聪明趁着二英和马溪熟睡,悄悄来到岳父家,翻身跳进院墙,那头叫驴正在酣睡,梦见自己身子掉进一条小溪里,怎么跳都上不去,叫唤主人也无济于事,眼看溪水就要淹没鼻腔了,突然听见远处有同伴奔跑的声音,它终于见到了希望,垂死挣扎,最后一搏,后腿突然踏到硬物,一下子跳上了河岸。
见主人的女婿被自己踢翻在地,原来是梦。驴子懊悔之情难以言表,只听见马聪明临死前说了一句,“哼点儿好听的吧,我就要走了……”马聪明没等说完,驴子接连叫了三声“啊呃……啊呃……啊呃……”不知道马聪明是否满意,驴子看见他眼角淌下几滴泪,闻上去有点咸,不知道是幸福的,还是悲伤的。
腊月二十八,我和周先生回靠山屯过年,司机从机场接上我们就往靠山屯赶。冯二在电话里说家里下雪了,落雪后宰大鹅吃着不腥,和酸菜一起炖最好。别克商务车开得不快,农村的路上还零星地分布着被压实的积雪。
快到靠山屯了,进村口的北山坡上立着一座新坟,隔着车窗看不清墓碑上的字,我问司机是谁走了?司机说是马聪明,没想到吧。我和周先生大吃一惊,刚入冬的时候,我们还在一个桌上吃饭喝酒呢。那么壮实的体格,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当天晚上,我和周先生在冯二家吃饭,铁锅炖大鹅,喝着东辽河水酿造的小烧。我们说着、唠着,话题就扯到了马聪明身上。冯二问周先生前一阵来的时候,在马聪明家仓房里教了他什么招?周先生说就是古时候人们用的一种占卜方法,叫镜听,也叫响卜,根据声音预测吉凶。
周先生举例,明末清初浙江钱塘有个叫黄机的人,考中秀才后就用镜听的方法预测官运。早上出门,他听到一家婆媳俩对话,儿媳问婆婆“明日客人来,是宰白鸡好呢,还是宰黄鸡?”婆婆说:“宰黄鸡。”黄机听了十分得意,因为鸡与机发音相同,宰又是宰相的宰,后来黄机果然前程似锦,官至宰相。
冯二恍然大悟,他把前段时间马聪明的怪异行为讲给我们听。
周先生不住地感叹,说可惜马聪明这个人了,当初在仓房真不该告诉他那些东西。
冯二说,这个怨不得别人,命由己造,相由心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周先生点点头,抿了口酒,沉默好长时间,说明天一早要去看看马聪明。
马聪明坟前,有一些没有燃尽的纸钱,还有一个被烧的变了形的耳麦。几盒颜色鲜艳的磁带和光碟,被摆放在马聪明的墓碑前,我仔细看了一下,上面都是一些喜庆的歌曲。
不知谁给选的地方,周先生说这块墓地风水不错,周围有一些粗壮的树木,偶尔有几只鸟飞过,马聪明应该不会寂寞。
下山的路不好走,我背着周先生,他怎么吃都不胖,也就七十多斤,趴在我背上跟个孩子差不多。
路上,我们遇到一只喜鹊,冯二盯着它,说它朝着马聪明的坟飞去了,喜鹊的叫声总是讨人喜欢的。冯二问周先生,这只喜鹊是不是给马聪明报喜去。
周先生嘴角翕动了一下,没开口说话。冯二和我都以为他睡着了。不一会儿,周先生放了一个屁,有气无力的,我和冯二都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