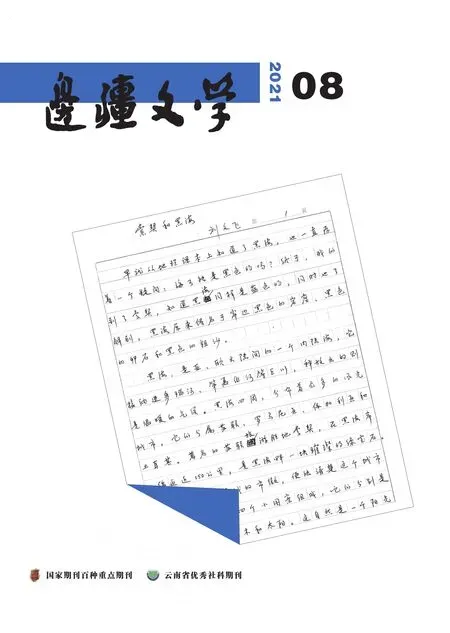流逝 短篇小说
赵雨
流
母亲很多年没出门了,家里唯一一件计量时间的工具是放在床头柜的三五牌座钟。棕黄色的木质钟架在她每天擦拭下油漆闪亮,玻璃钟罩光可鉴人,白色钟面的两根黑色指针犹如两把匕首。上足发条,几十年来,它从未走快或走慢过一次,在这么一面圆盘上,时间被不断刻制、重复,指针划出一块独立天地,和外面的世界全然无关。母亲几乎每天长时间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盯视座钟,在整点报时声中兀自发呆。
随后,外地人来了,他们无处不在,深更半夜还围坐在围墙外聊大天,操着听不懂的方言,有时摆开桌椅,打牌、搓麻将。母亲在房内听着嘈杂的声音,胸口闷气越积越深,以致彻夜失眠,神经处在崩溃边缘,终有一天,她倚门而立,在风中,在夕阳下,揣着一口袋瓜子,一粒粒磕着、剥着、吐着。外地青年们正在举哑铃,练习手臂肌肉,外地青年的外地父母们烧晚饭,满街飘荡着辣椒的气味、豆瓣酱的气味,还有分不清什么材质的拌料,这些食物在她眼里都不是体面人吃的。
街面不时走过提着热水瓶去小店冲水的人,他们谁都没和她打招呼,仿佛她是一尊立在门口的石像。她站了一阵子,直到夕阳沉落地平线,返身关上了门。
她叫来一名装修经理,向他阐明将对房子做出的改变,经理听明白她的要求,叫来几位小工,动工。
他们用铁皮把庭院封了顶,小工们站在外墙,从东往西一层层铺上那种一触碰就会像雷声般唰唰作响的铁皮,铁皮在太阳的反光下照得人睁不开眼,她叉着双手站在底下,仰头望着院外的天空被铁皮一块块遮没。封顶那一刻,庭院变得黑暗,隔绝了外面的声响,她心头仿佛拧上了一个安全阀。
她下厨烧了一桌菜,犒劳装修经理,席间,她为装修经理倒了酒,这是多年来她第一次和一位男士单独吃饭,脸庞在吊灯下显得拘谨闪烁。经理用足了酒饭,临走前对她说,其实你没必要做这些。她问,为什么?经理说,这一带马上就要拆迁,什么东西都会拆掉。
她对拆迁一无所知,她深信自己的房子不经她同意没人能随意拆除——她还有大把时光在此度过余生。
一个人。
但她的神经质不可救药地往畸形的方向发展。
她翻出所有旧物,一件件排列在地:儿子满月时的围兜,泛黄的材质脆弱易碎;她结婚时的褪色胸花,像一枚危险的暗器;她父亲去世前穿的内衣,忘记丢进火堆烧化。
午夜的电视节目,空旷的客厅,无边的沙发,电视上的鬼尖声厉叫。
第二天一早,她打电话给装修经理,要他来一趟。
装修经理来了,她说,有些地方还想改动下。带着他从一楼走到二楼,又说不出想改动哪里。她接二连三给装修经理打电话,经理接二连三上门,她发觉自己不对劲,意识到打电话的原因只是想见见这个男人,这个从外部世界唯一延伸到她的世界的男人。自第一天见到他,她就想着他们之间或许能蔓延出什么,那桌饭菜还留在她脑海,吊灯下,他的喝酒姿势以及不多的言语挥之不去。她终于鼓足勇气对他说,你如果能常来坐坐就好了。
他们开始来往,他每次进门前都会看一看周边,是否有人关注他的举动,她每次开门前,都把身子藏在墙后。他们的行为像是秘密幽会,无数双外地人的眼睛盯着,背地里说这对男女时常坐在阳台聊天,面前摆着一张木藤桌,桌上放着两杯明亮的绿茶。男人跷着腿吸烟,女人为他斟茶倒水,脸上带着羞涩的表情,像极了电视上优雅的贵妇人。
一天,她出门了,人们议论纷纷,她竟主动跨出了那座房子的大门。
她穿了一件长及膝盖的淡绿色外衣,衬着一件白色毛线衫,脖子下挂着一条透明的水晶项链,紧贴毛线衫熠熠生辉,底下一双黑色圆头黑皮鞋。没有人见过她这身装扮,有些外地租户连她的面都没见过。她的身后跟着装修经理,大家认为,正是他说服她出的门,他在她身后谦恭的样子让人想到古时贵族家的奴仆。
这次出行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大家热切的谈资,连她黑皮鞋踩在石板路上的声音都被无限放大,简直成了一个时代的回音。她从家门前的小巷经过机耕路,来到大马路,眼前所见早已不是她熟悉的事物:高耸入云的庞大建筑,外墙蓝色玻璃构成一面屏幕,播放着广告和影讯;横跨半空的轻轨线蜿蜒躺卧在一排排硕大的立柱上,动车飞速而过;大马路上的汽车没有一刻停歇,十字路口排成长长几列,等待信号灯的转换。她的世界只有那只座钟,在家里安静地等着她。她的内心起了些震动,和装修经理沿着人行道走进马路一侧的一家连锁早餐店,吃了一顿内容丰富的早餐,对放进嘴里咀嚼的汉堡和鸡腿报以怀疑态度,摸了摸肚皮,起身离开。
他们踏上一辆公交车,选定两个靠窗位置,在车上暗暗牵住了手。六站过后,公交车驶出小镇中心地带,在育王公墓站停了车,他们下车,走上通往公墓的甬道。
育王公墓寂静一片,上山的坡道略为陡峭,她的黑皮鞋走得异常艰难,他不时搀一下她的手。她抬头望巍峨的山峦,树间传来清脆的鸟鸣,他们拐上一条狭窄的墓道,两排都是不同年代建造的坟墓,有些气派整洁、有些孤立无援,样式千奇百怪,他们在其中一座墓碑前停下脚步。
她说这是她丈夫的墓室,她带着她的新伴侣来祭拜去世的丈夫。装修经理取出随身带来的蜡烛和一支香烟,点燃,插在耸起的土包上。墓碑正中刻着她丈夫的名字,她伸出手摩挲了一遍,对他说,她的丈夫死于一场意外。他问,怎样的意外?
她说,她丈夫生前是一名出海捕鱼的船员,一年有大半时间漂泊在海上,她不喜欢他的工作,长期不在身边让她倍感孤独。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他喜欢大海,他一次次出海捕鱼日晒雨淋下网捞网的目的是攒够钱,购买一条属于自己的船,带着妻子和儿子出海航行。一个人干着不喜欢的事,为了换取另一件他喜欢的事,这是个奇怪的道理,她说,他最后没有实现理想,钱即将攒到足够购买自己的船时,一次在海面上,遇大风暴,海浪拍过船板,把他卷走了。所有船员都在,只卷走了他一个人,所以这是个衣冠冢,她说,里面没有遗体,他的遗体沉到了大海深处,早已被大鱼吃进了肚子。
装修经理听完,沉默不语。一位老汉提着毛笔和漆桶过来问,是否要添漆?她挥手粗暴地回绝了他。正欲离开,装修经理发现坟墓后方,还有一口墓,长方形建制,深一米,豁然敞开,墓碑紧挨着前方的墓尾,相隔不到十公分。装修经理说,这口墓奇怪。她说,是我的寿穴,同时做的。装修经理说,为什么不做在一处?她说,我死后可不想和一堆烂衣服躺在一起。她带他绕过丈夫的衣冠冢,站在自己的寿穴旁,黄色土壤干板结实,其中有一张脏手帕、两只易拉罐,跳下去,一一捡起,丢在一旁别人的坟墓边,站在敞开的墓穴中央,伸开两臂,抬头望着天空,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说,以后我就要很久很久躺在这里了。
这是她第一次和装修经理外出,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天下午晚些时候,装修经理坐在床沿看电视,那是她和船员丈夫曾睡过的床,她在阳台收衣,不经意一瞥,一位农妇打扮的女人朝这边走来,一边沿巷向人们打听什么。她不认识她,没放心上。送装修经理出门时,那个陌生女人正站在门外,装修经理如见瘟疫,双目睁得铜铃大。她还没反应过来,陌生女人走上前,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番。
装修经理说,你怎么找到这里的?话音刚落,陌生女人一把推开装修经理,扬手给了她一记耳光。她只觉牙齿在口腔内壁摩过,尝到一股甜甜的味道,头一歪,手一摸,手背粘下一条血丝。
她问陌生女人,怎么了?陌生女人不给她喘息之机,抓住她头发,一串穷凶猛打,打得她眼冒金星,不辨东西。围观的人里外皆是,有人捧着饭碗看热闹,有人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她挣不脱那只老鹰般的大手,那是一只被农事和家事弄得粗糙不堪的劳动妇女的手,这只手提着她的头往铁门上撞,大有赶尽杀绝之势,围观者这才上前干涉,将她解救出来,一大片头发掉落。
她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双目茫然,装修经理拽住陌生女人的手离开,她这才知道陌生女人是装修经理的合法妻子。
她无话可说,无理可申,一场闹剧揭示了面目可憎的一切,她还盼着装修经理给她一个解释,结果她再没见着他的面。
她又回到一个人的世界。
拉上窗帘,屋内像个大地洞,拉开窗帘,外面的太阳令她无所适从。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四周静得可怕,唯一的声响来自那只三五牌座钟,变成震耳欲聋的循环嘀嗒。
嘀嗒……嘀嗒……嘀嗒,每一记打在她的胸口,漫漶成一种嘲笑,嘀嗒……呵呵……嘀嗒……哈哈。
她猛坐起,打开台灯,天花板上鬼影憧憧。翻下床,趴在地上,慢慢爬过去,爬到座钟前,仰头看,钟面和指针构成一张人脸的轮廓,上发条的两只圆孔深不见底,如两颗黑眼珠,居高临下看着她。她在深夜和一座钟对视,突然钟体响起一记“当”,午夜一点,仿佛从地洞深处传来,形成波纹状,荡开去,余音萦绕,将她的魂魄震了震。她捧起钟,高高举着,在头顶停留十秒,钟给她记着时,一秒、两秒、三秒……她铆足劲,使劲往地上砸,棕黄色钟架崩裂,钟罩变成六块大小不一的碎玻璃,吕制钟面在地上咣咣滚了几转,指针落地的位置正好尖头指向她,她闭上眼,犹如被判了刑。
她回到的世界没有声音,没有光亮。
她摆弄一件人形雕塑,向左挪四十五度,向右挪四十五度,往中间摆正,侧过来,翻过去,不管哪个角度都不能满意。
摆不好一件人形雕塑,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事。
折磨一只落地未死的飞蛾,掰掉翅膀,扯去头,撕裂腹部,沾了一手绿色黏液。
冰箱背后陈年的污垢,沙发下一圈圈毛绒尘埃。
女人的手,男人的眼睛。
她拿起电话,拨通我的号码,用气若游丝的声音说了句:
你回来吧。
逝
很多年前,我就和她背道而驰了。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和别人不同,她几乎和所有外人都不往来,家里从未招待过她的朋友,父亲的朋友偶有上门,事后总会被她嫌弃、数落,因为要花时间打扫、整理、招呼,慢慢就没人来往了。
她对外地青年严阵以待,我多数时光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他们斜叼香烟,穿着白背心,在各大工地、车间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我和他们打成一片,瞒着她去外面玩,买了辆二手摩托,风驰电掣满大街跑,小卖部买一罐可乐,手肘靠着柜台“咕噜噜”灌一气,开到海边,迎着海风大吼大叫,像一群神经病。夜幕降临,我们去溜冰场、舞厅,摩托车往门口一停,走进霓虹闪烁的舞池,鬼影闪烁、烟味弥漫,对面的人脸看不清,感觉筋骨舒展,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愤怒随着旋律摆动发泄出去。
而在家的时光,我终于无法忍受她日复一日变得几近病态的神经质,和她住在一起就像和鬼魂相伴。父亲去世后,她尤其阴气袭人,即便知道她在房子的哪个角落,那里也嗅不到一丝活物的气息。她走路没有声音,呼吸没有声音,却会冷不防朝着虚空大吼一声,仿佛内心窝着多大的委屈和不满。家里任何摆设都不能挪动半寸,一旦弄乱了什么就会遭到一通莫名其妙的指责甚至谩骂,这时她中气十足,嗓门洪亮,表现出一副绝不饶人的咄咄相。这世界能和她相安无事的,我想大概只有那只放在床头的三五牌闹钟了。
随后,我就搬了出去,她的消息只有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听说她对房子进行了改变,将居住空间重新布局。我在市区租了一间房,找了一份半空擦玻璃的工作,简单培训几天就上手。我喜欢悬荡在高楼外的感觉,透明的玻璃能窥见楼内办公员的动静,累了,休息一会,抓着绳索,眺望远方,大半个城市尽收眼底。
我从没这样吊在半空观望过这座城市,它很漂亮,楼房一直排列到地平线那端,护城河一线,河水像丝带。遇到有晚霞的傍晚,整片大地笼罩在迷人的霞光中,蓝色楼面玻璃反射着光线。但并非一律如此,有些地段不那么雅观,多是西部的老城区,袒露出一块建筑被夷平的地面,光溜溜,黑色和黄色的泥,东一堆西一堆砖石废墟,犹如剖肚挖肠被屠戮的尸体,横陈歪倒,与周边格格不入。那是被拆迁的区域,那些日子,到处都在拆。
她打我电话时,正是我家所在区域坐实拆迁之际,从拆迁办发布公告到实施,历时小半年。工作人员进了村,测量住房面积、核实补偿资金、签合同,住户都比较配合,村委会唯独拿我家的房子束手无策,体形矮胖的刘主任无数次敲响那扇双合大铁门,从未得到过回应,他一度以为主人独居太久,猝死家中。
集体合同签订的期限即将到来,她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刘主任向我求助,让我做她的思想工作。
儿子的话她肯定听,刘主任说。
我回了趟家。
下了地铁,是城区边界,沿着柏油马路走,汽车三三两两行驶而过,村子入口连接着国道,闻到一股久违的农作物气息。
拐进一条弄堂,到了赵氏家族居的地界,以前我们整个大家族,叔伯姑嬷,以及几户迁来的外姓,全住在一起。这些年,陆续搬出,房子租给了外地打工者。
刘主任已等候在我家门口,拉住我的手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说服你妈,再晚就来不及了。旁边站着几位我不认识的人,应该是村委会的职员。我点点头,敲起了门,一记记慢慢地敲,敲了十来下,没效果,加重力度,手指的每一次叩响都如小石子投入水面。
刘主任急了,我也急了,改用手掌拍门,啪啪啪重重地拍打,门还是没有开。刘主任说,你没有自家钥匙吗?我说没有。他说,那怎么办,难不成把门撞开?这时有人指着上方说,看,那里有人。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我家阁楼面向大门的窗户,窗后站着一个幽暗的身影,乍看还以为是鬼,大好的太阳,黑色倒影整个贴在玻璃上,上半身嵌入窗框,脑袋低下,目光直射底下,摆出一副睥睨的居高临下的样子。
她在阁楼上,背后顶着悬于屋顶的太阳,瘦小的身形被阳光和阴影包围在不足两平米的窗玻璃间。她的大半生就困宥在这样局促的地方,如一只蝴蝶标本。
我向她招招手,她离开窗户,没多久就把门打开了。
除我之外,她没有放任何一个外人进去,我示意刘主任在外等。
穿过庭院,我差点认不出这是自己住了三十年的家,东墙下花坛外围半米高的砌墙残破不全,泥土溢出地面,那棵父亲当年亲手种下的金桂拦腰折断,斜挂于墙体。西墙半壁白漆大片剥落,露出黑色砖石,地上东一块西一块粘结的毛发、碎纸、果壳,一把扫帚和簸箕倒在一边,一股若有若无的馊味弥漫在空气中,透入我的鼻子。走进客厅,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八样菜肴,四边桌沿是几只小酒杯,倒满黄酒。
这是一场祭奠的排场,父亲的黑框遗照搁在桌子上位,靠着椅背,多年未见他的模样,有些陌生。母亲从楼梯背后出来,穿着一身素净的衣服,脸上挂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她说,今天正好是你爸五十岁阴寿,坐下吃个饭吧。
她给我拿来一只碗和一双筷,倒了一杯酒,自己在对面坐下,也倒了一点酒,这倒让我尴尬起来,我们太久没坐在一起吃饭了,本来见了面就打算说的拆迁一事咽了回去,喝起酒,一面打量相框中的父亲。
父亲在我十五岁就去世了,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喝过酒,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双眼通红,掀翻菜桌、踢翻板凳是常有的事。母亲也毫不示弱,面对他的暴烈,予以回击的是刀剑般刻毒的言语,任何一个女人无法说出口的话她都肆意卷舌吐出,配以夸张的舞台剧般的动作,使父亲的怒火窜得更高,揪住她的头发,掴她耳光。她仍旧骂,不还手,言语是她唯一的利器,要刺穿攻击她的这个男人的身躯,挑起他体内潜伏的更凶残的秉性,直到两人筋疲力尽,偃旗息鼓,仿佛经过一场仪式的洗礼,得到身心的升华。
一天,父亲在翻阅报纸,看到一条招工启事,招聘船员,出海随船作业,捕捉海鲜渔获,两个月回一趟家。他的眼神射出一道光芒,决定前去一试,母亲反对,两个月回家一趟,等于家里没了男人。父亲说,此项工作薪酬高,是他现在的三倍,机不可失。他没有捕鱼经验,可以学,只要肯吃苦,捕鱼船欢迎任何一位身强体壮的男人。
他很快就被录取,从那以后,家里就不再能见到他的身影,偶尔回来,一改之前的模样,态度温和,告诉母亲和我关于大海的一切,他说,他要挣够钱,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带一家人去远航。
他说这话时,母亲看着他,全然没了昔日挨揍的哀怨,幻想那片大海和从未生活过的世界。只有我知道,父亲这些话是无法相信的,他从干船员的第一天起,就扮演一名逃离者的角色,因在家和母亲拉扯、捆绑、黏稠,每次出门,满怀轻松自由。购买一条自己的船、出海航行,这些是真的,但他的计划中没有我和母亲的份,他未来可能会拥有的那艘船上除了他自己和自己的理想,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是他出事后,我从船员交给我的他生前的航海本中得知的。
我瞒着母亲把本子藏起来,深夜翻阅那一条条记录,被他冷漠的文字震撼,他在无数个海上星夜细数母亲的种种罪状和不通人情处,把母亲形容为神经失常的疯女人,是他急于甩脱的一个包袱,对这个家庭,他早已没了牵挂,可惜那个巨大的海浪把他卷入海底,将他的满腹计划全部托付海水东流。带给我航海本的船员说,你父亲像一条滑溜的鱼,包裹在海浪之中,从船舷一侧滑过甲板,在另一侧腾空而起,消失在两三丈高的白沫间,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他是个几乎不跟别人讲话的人,船员说,他把一半时间用来写那个本子,另一半时间坐在甲板,望着海面和天空,长久出神。他的遗物中还有一只航海罗盘,普通船员不会有这东西。
此时父亲的遗像稳坐在桌子上首,留着板寸头,目光聚焦前方,菜盘冒出的蒸汽氤氲着相框玻璃。
母亲至今还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一心以为,如果没出意外,父亲将会带着她和我驶向大海,我至今没告诉她真相,对她来说,这没有好处。
我和她聊了一阵,她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脑海浮现高空眺望城市的一幕,不能说,她不会接受我在干这么一份活,编了个谎,她没说什么。我趁机说,拆迁的事,你把合同签了吧,这地方迟早是别人的。她说,这事我会做好的。
喝了不少酒,没吃饭,坐了一阵,打算走。
出门前,她上楼拿了个包裹给我,一条大布帕包着,沉甸甸的。
是什么?我问。
一个坏了的钟,她说,你找个地方修一修。
我打开布帕看了一眼,钟的散落的骨架和零件奇怪地堆在一起,破碎的玻璃钟面的一角闪烁着水晶般剔透的光泽。我想起幼年时经常趴在这架座钟前,嫌指针走得太慢,眼盯酸了,才走一小格区间,用手指抵住长针,顺时针(或逆时针)快速拨动几圈,钟声接二连三响起,我很开心。逃不过被母亲发现,那时她的精神还没那么糟,会带着一种柔和的语气和明媚的微笑和我说话。那时的阳光也很柔和,后来再也没有那么柔和的阳光了,她在阳光中调整指针,一边说,钟是不能乱碰的,那是时间在走。我说,时间怎么会走?时间看不见。
时间当然会走,她说,拿起我的手指,放在指针前进方向的下方,一动不动放着。指间有规律的一下下“咔咔咔”,进逼而来,无法阻挡,仿佛时间有了形状,能感知,能被触摸到。
坏成这样还能修好吗?我包起布帕,像包住一具残破不全的尸骸。
修得好,母亲说,当然修得好。嗓音在刺透庭院上方铁皮蓬的阳光中显得异常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