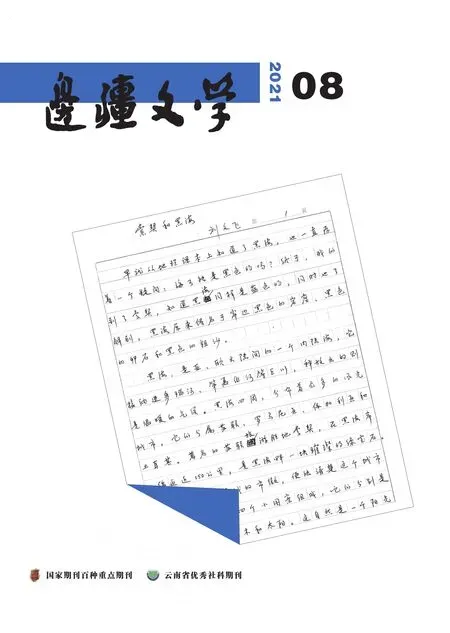幸福苑286号 短篇小说
谭成举(土家族)
1
我早出门,并不是要公干。我有什么公干?我一富商家的唯一的少爷需要什么公干?我一天玩得舒服了,就是公干!可是偏偏这罕见的连续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一波接一波的寒潮让我极不舒服。我天天宅居室内,腻透了,憋透了,烦透了,我得出门去透透气。尽管我按二十八星宿娶了二十八房可以说是美若天仙的妻妾,以护佑我,而这二十八房妻妾也整天或与我琴棋书画、歌舞诗赋,或与我吃喝玩乐、犬马声色,她们换着花样尽心尽力伺候着我,博取我开心,可时间久了,我厌了,我开心不起来了!有时,我那些狐朋狗友也找我吟诗填词、写字作画、饮酒骑射,名义上他们是来相助我长进技艺、愉悦心情、康健身体,实际上他们是来打秋风、愉悦他们自己的,我有时就懒得见他们,我厌烦他们,我也小瞧他们,这样,我的心情就好不了。所以,当大地刚一解冻,我便急不可耐地要突破宅院的圉圄,奔向广阔的天地去。
我是在二十八房妻妾和众仆从的簇拥下走出辉煌而威武的大门的。要在往日,我是威风而自豪的,飘飘然,幸福感满满的。可现今,我却找不到那种感觉了。我被仆人搀扶着走进了豪华马车。坐定后,我掀开帘门,见众妻妾及一干随从都各自上了自己的马车,守门人也将厚重的、布满铜钉的、霸气十足的朱漆大木门缓缓地闭合了起来,而门楣上突然怪异出现的“幸福苑286 号”的门牌号却闪着寒意的光,强劲地不由我有丝毫抗拒地向我飞奔而来,强势地钻入了我的脑中,让我心中无来由地猛地一颤。
可我不管这些,却是急着催喊车夫扬鞭策马。
车夫问我何往。我不耐烦地斥责道,何须多问?只要让本少爷尽兴,哪里皆可!
车夫还是不知所往地、缺少脑子地望我一眼,见我木着脸,便迟疑着扬起了鞭。
我见了,不由火起。飞身过去,夺过马鞭,将车夫掀下马去,又三下五除二将马车上那些缚住马儿的羁绊粗野地去掉,便跃上马背,两腿一夹,让马鞭甩出一声爆响,我再放肆地暴喝一声“驾”,将一干妻妾和仆从远远地甩了,独自扬长而去!
只有“幸福苑286 号”的门牌号狡黠地闪着绿光,在后面叮咬着我,紧随不弃。
2
你他妈发什么神经?还让老娘睡不睡觉?
我被她一脚踢下床来,额头“咚”地一声硬硬地磕在地板上。
她是我的妻子。曾经的妻子。当然,现在名义上仍然还是我的妻子。我估计,凭了我的懦弱和一味的忍让,她会永远是我的“妻子”的。除非她当我的妻子当厌了,或者说,她不再需要我当她的遮挡物了。是的,自从她当上了几千员工的国企老总,自从风闻她与某些要员不干不净,自从她将我的尊严扼杀得一无所有,我就只叫“她”而不叫“妻子”了,她也实质上不再是我的妻子了。
我一边揉着麻木继而转向肿痛的额头,一边不得不对她喃喃地说,做了一个梦,梦见骑马……不小心将你吵醒了,对不起……
做梦?骑马?做梦娶媳妇吧?胯下的马是我吧?看你兴奋的……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能控制我的人,你还能控制我的梦么?做梦娶媳妇怎么了?我愿意!我梦中把你当马骑又怎么了?我高兴!
在黑暗中,我弱弱地冷笑一声。不再向她解释,不屑再理会她,我用无声做着抗争。我愤然地、而又轻脚轻手地离开卧室,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我摸来一支烟点燃,让那黯然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她和我是大学同学,在大学时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偷吃了禁果。毕业后,我俩一同进入了一家国企,只是我搞技术,她搞行政。由于我的问题,我俩没有孩子。也正因为没有孩子,我俩便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她则在仕途上风生水起,一年一小步两年一大步,不上十年就高居老总位置。对于她的快速“进步”,我开始是没有怀疑的,我知道她有从政的特质和能力;对于她的经常夜不归宿,我开始也是没有怀疑的,毕竟搞行政千头万绪,忙,不像我们搞技术那么单一。可是,随着某要员被“双规”,传说出他自己交代出了与众多女性有染,据说其中就有她,这便让我回想起了她的快速进步的不正常、经常夜不归宿的不正常,这便证实了有关她的传闻的真实性。我便找她吵,找她闹,找她离婚。可是她对我的吵闹不解释,不争执,不搭理,也不离婚,只是一味地讥讽和蔑视,并拿我的饭碗来敲打我。我知道,她要敲碎我的饭碗很容易。我知道,我那下岗的父母需要我的饭碗来养活。我知道,我的能够维持我与父母生计的一技之长只有在这家企业能有生存的空间。这是我的命脉,这是我的死穴,这是我的“七寸”。而她恰好点住了我的死穴,掐住了我的七寸,而且很轻松,很拿捏到位。我只得屈服,只得无时不说服自己,忍!忍!无论如何都得忍!不为别人,为含辛茹苦养育我的父母。而屈辱感、压抑感无时不在,无声的抗争在内心也无时不在。这我没有法,我控制不了自己。
抽完一支烟,我站起来走到窗前,任凌晨的风带着寒意地吹拂着我。
我便开始回想那梦。其实那样的差不多的梦境不是第一次出现,尤其是那“幸福苑286 号”的怪异的门牌号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出现的场景不同而已。
难道我与“幸福苑286 号”有什么关联?难道我的后半生能被“幸福苑286 号”所逆转?
我想,我是时候得抽空去找人解解密了。
3
我来到算命一条街。
这条街不长,也就200 来米吧,背街,位于城乡结合部,一般外来人找不到,按常理本地人一般也走不到那里去,但事实是这条街人来人往,生意异常地红火。做算命生意的人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瞎的不瞎的有能耐的浑水摸鱼的。来算命的也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本地的外地的官场的贫民的。所以,这条街与这座城市的主街像媲美地繁荣,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条街的生意曾被取缔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据说是某要员暗访后发了话,说这条街的生意人,是凭本事在吃饭,不要社会救济,又不影响社会治安,背街小巷也不影响整座城市的市容市貌,况且这些生意人能从心灵深处安慰那些需要心灵慰藉的人,何必对他们强加干涉反而引发不安定因素呢?凡存在的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嘛!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是那位要员还在不是要员时曾暗中接这条街的某位大师去他府上为其指点过迷津,该要员才从此发迹了的。这一说法无人考证,也无从考证。不过,考不考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说法又不影响生意的红火,反倒是增强了生意的强势繁荣。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从街这头从到街那头,又从街那头走向街这头,并且借助天上飘着的毛毛细雨,撑着一把很不起眼的黑色雨伞,将伞檐降得低低的,若不是刻意,没有人会认出我来的。
走的走,来的来,每个摊位前都围了不少的人,他们有的求问着婚姻、家庭、亲人的未来境况的如何,有的毫不隐瞒地诉说着自己的困扰,虔诚地肯求着大师指点迷津。
我不想在人多时去凑热闹,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还是公职人员,毕竟这座城市还有一些人认得我,毕竟我还不想让外人知道我目前的尴尬处境。我便继续在街上若无其事地慢慢游走,只不过是有时走街左边,有时走街右边。当然,我也不会走到街这头就即刻转身走向街那头的。我总会走出街头,在其他地方溜达一些时间再重新踏入这条街,让别人看来,我就一刚入这条街的人。
我不知道我在这条街溜达了多少趟,我只知道差不多到中午了,我才瞧见一个摊位空闲了出来。我慢吞吞地走过去,不让那位算命者或是相面者看出我的破绽获取我的信息。我要其显示出真本事,我要他真实地为我指点迷津,帮我走出窘境。
我装着平静地面含微笑,向那位先生点点头。我正待用言语向其问好,那位先生却先开了口,叫我坐。我镇静地随意拉把椅子坐下。尽管天气寒凉,屁股却有热气仍在散发,看来亲密接触过它的男男女女不在少数。
先生在这条街来回都走了八趟了,看来先生是有大事要做,却又犹豫不决啊!
我一惊,我的行踪早被他瞧得一清二楚了!能一边算着他人的现在未来、旦夕祸福,一边却将另一个人的行踪、心思了然于心,这样的人能不叫我心惊么?我这才正眼瞧那位先生。这一瞧,更是让我大吃一惊,而且是深深地心惧了。那先生面色红润,长髯飘飘,明显的仙风道骨,双眼却是明显地睁不开,即便睁开,而眼珠也是朝上翻着的,除了眼白,看不见晶体。标准的瞎子一个。一个瞎子,却能远远地将我的一切尽收“眼”底,这能不让我惊惧么?其后,我又生出无际的欣喜,眼前这位定是高人了!遇见高人,我的谜团就能被一清二楚地解开,我的未来就有了解救的希望。
见识了他给我的“见面礼”,我原打算不先向他透漏我的信息,而是让他给我算算我眼前的境况看看其准确度再做打算的想法便立马改变了。还是直接说出我的梦、我的窘迫吧。我正欲开口,他却先说开了。他说,先生此来定是问未来,求疑解的吧?
我说是,求先生指条明路。
他说,你将手给我。
我将右手伸去。
他说,左手,男左女右。
我伸去左手。他将我的左手用他的左手垫了,托于掌心,弯曲着右手中指在我的掌心各纹路处游走。他的手指很温暖,也很柔软,摸在我的手掌上极舒坦。我一阵战栗。我有了麻酥酥的感觉。我又找回了谈恋爱时她抚摸我手掌时的快感。
这时,他的中指突地一跳。他“咦”了一声,脸色也有了明显变化。
他的中指在我手掌心的纹路上再游走了一遍。这次他没有发出“咦”声,只是脸色更加地阴郁了。
他便改变方式,不再摸手纹,而是叫我报来生辰八字。一番推算后,他说,先生,恕老夫妄言,先生流年不利啊!
我正要诉说我的处境,他又说,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先生却是相反,你不仅得不到大树的荫庇,反倒是大树遮住了你的阳光,让你在阴暗中求生存。久不见阳光,日子过得蹇劣啊!可你又是大树下的一棵小树,你们根根相连,根本无法割裂开来啊……
我正要说说她,尚未出口,先生就扼杀了我的话。他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似的,说,无须多说,老夫的话,姑妄说之,先生姑妄听之罢了。
我只得作罢。我改说我的梦和“幸福苑286 号”。他脸上明显一怔。
他久久不语,似在沉思,寻求答案,又似闭目养神,以便精神充沛后给我解答。
我就耐心地等待。许久以后,我终于忍不住了,说,先生,请你指点。
他这才眨几下眼睛,长叹一声,说,那是先生的未来,是先生的理想之地啊!只有到了那里,先生才能……
我静等下文,等了许久,却再没有下文。我请求先生对前文进行详解,他说,天机不可泄露,老夫只能说这么多了。
这时,又有前来求解的人,先生便给我下了逐客令。
我只得怏怏地准备离去。我问他酬劳多少,他不说,只怜悯地“看”我一眼,叫我离去便是。我摸出一张百元大钞放置他的桌案上,他立马抓了塞给了我,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守规矩的,有几种钱不能收,否则有违师训,那是要遭天谴的……
我有一瞬的郁闷。只一瞬。不一会儿我又恢复如常了。接着便是高兴,我终于知道了“幸福苑”是我的未来、是我的理想之地。不管是福还是祸。
4
我开始去寻找我的“理想之地”了。我是个并不算愚笨的人,我知道关于大树与小树的事已成定局,无法逆转,纠结在这上面毫无意义,只徒增烦闷罢了,我转而去找寻幸福苑286 号,破解我的未来之谜,这才是正途。我想,我只要找到幸福苑268 号,我还在乎什么大树与小树么?
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也有二十余年了,这里的大街小巷旮旮角角哪里我不知晓?哪里我没到过?可我从没听说过有幸福苑这个地方呀。当然,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尤其是为了发展的需要,当地几个土专家撺掇当地民政部门,将很多老地名都改了,如,将“三光路”(取“日、月、星”三光之意)改成了“三观路”(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之意),“庆凤山”(取“庆贺凤凰莅临”之意)改成“凤鸣山”(取“凤凰鸣叫”之意),而且更换频繁,让我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幸福苑”也许是以前的哪一个老居民点更名过来的,也许是新划定组建的一个新区。
要快捷地找到幸福苑,我得理定思路,找到捷径。我知道,地名、路名、区域名之类当属民政部门管辖。我自然得去民政局。
雨下得很大,路上行人不多,却是车流不断。我原本打算走着去的,可终究一来雨大,尽管有雨伞遮蔽,下身也是不能幸免的;二来我的家离民政局有十里之遥,凭我这瘦弱的身子在这大雨天走着去委实艰难。我便向一公交站台走去,准备坐公交。刚跨上站台,一的士“唰”地一下飞奔而至,在我身边停住,卷起的风雨及地上的积水直向我猛扑过来,让我临车的一边浇了个透彻,使我瞬间变成了一个“阴阳人”。我正要骂娘,却又忍住了,我一落魄之人,多受一次欺侮也无所谓。我将尚还积存在我身上的雨水抖了抖。这时那的士司机将车窗玻璃摇了大概五厘米宽的缝,将头略微伸向了我。我以为他是要向我道歉的,正准备大度地说,没事的,你走吧。不想他却叫我上车。那语气好似我必须坐他的的士似的。我一皱眉,厌恶地盯视那司机一眼,向后退走一步,再懒得理他,而将目光伸向远方,寻找公交车的身影。那司机不满地骂一句“傻逼!这么大的雨有的士不坐,淋死你!”便又问站台上有打的的没有,见没人搭理他,他骂骂咧咧“唰”地一声将车开走了,去拉不是傻逼的客人去了。
我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公交车终于来了。这座城市的公交车才运行不久,车少,线路长,而愿坐公交车的人又多,因而每辆车上都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挤上了车,却引来一片骂声。我知道,这骂声是因为我的上车让拥挤的车上更拥挤,这一拥挤就让有的人踩痛了别人、挤痛了别人,还有我这湿漉漉的身子也让临近我的人要湿漉漉的了。我让他们骂,反正我这个人习惯了忍辱负重,不在乎被再骂这一次。
公交车前行才百余米,不得不停下了。前面出了交通事故,一辆的士和一辆摩的在不准转弯掉头的地方转弯掉头,这就撞上了。的士车前面陷进去了一大块,司机伏在方向盘上;摩的司机和乘客倒在雨水中,有血和着雨水往低缓处游走。不知死人了没有。
120 来得倒是很快,据说是被承包了的,时间就是金钱,不快不行,不快就是傻逼。交警却是迟迟不见到位。这时,车上就有人开始骂起娘来,有骂那俩肇事者不守交通规则找死活该的,有骂交警拿着比别人优厚的俸禄却不履职尽责的。骂着骂着,就开始议论起这座城市交警的怪现象来。说正式交警不上路,只是坐在家里指挥,上路的是协警,协警嫌工资开得少,又没正式交警带,便出警磨蹭,到达现场后,也只管记录,又没执法权,不好处置事故,就等正式交警来,这一等,又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又说,这些协警也是,外面的高工资他没本事拿,本地工资少,又嫌弃,一天就混日子……我推断此路暂时是不能通行了,得等,这一等,没有几个小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正准备请求司机开门让我下车,司机却好似习惯性地自觉地将车门打开了,让乘客蜂拥着下车,他却抽出一支烟点燃尽情地闭目享受去了。
我不得不绕过事故现场去前面打的,尽管我对这座城市的的士十二分的厌恶。的士很好打,我不用招手,就有一辆的士抢着去投胎似的“唰”地射到我身边,让我湿漉漉的半边身子再湿一次。
我坐上车去,尚未关上车门,的士就箭一般地朝前窜去。我好不容易将那已经难以关上的门勉强算是关上了,那司机才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民政局。他说三十。我说打表呀。他说不打表,就三十。我说打表也就十来块,怎么就不打表呢?怎么就要三十呢?他说都不打表的,就三十。我说三十我不坐。他说都上车了岂能不坐。我说三十就不坐。我拉开了本来就要开不开的车门,的士就被迫停了下来。他说不坐可以,但“上车十块”的规矩得遵守。我懒得理会他,给他车上扔下十块钱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背后又传来一串骂声。我心里说,骂吧骂吧,你就尽情地骂吧,更大的屈辱我都忍了,我还在乎你的骂?
刚在路边站定无目的地张望,就见对面有两辆摩的从车流的缝隙间比赛似地往我这里窜来,引来车流中一片喇叭声兼具怒骂声的齐齐响起。
先到的摩的叫我赶快上车。我问去民政局多少钱。他说你快上车再说。我说你说了多少钱我再上车。眼看紧跟而来的那辆摩的已经要在我身边停下了,他才说,便宜你,就给二十吧。我说,二十?你当我是冤大头呀?紧跟来的摩的已经在我身边停稳,并向我喊话,说,我只要十五。我心中正不快,像有意做给先到的那位摩的师傅看似的,赌气地说,十五就十五。我就上了后到的这辆摩的。我刚将屁股挪上车,双脚尚未找到踩踏的位置,那摩的“䀚”的一声大叫就窜了出去。只听先到的那位摩的师傅大声开骂了,你给老子等着,下次让老子见到了捶不死你!不知是骂我还是骂这位摩的师傅。不管骂谁,我反正是无所谓的,即便你真的要捶我,我也并不在乎。
到达民政局的时候,我接了个电话。单位小周打来的。小周是才招聘到我们单位的,他做我的助手。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也很讨人喜欢的一个小伙子。他问我今天怎么没来上班,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他过来陪我上医院看看。他知道我身体一直不好,不是万不得已,我都坚持带病工作的。小周一打来电话,我才想起我今天应该去上班而不是来找寻“幸福苑”的。我现在怎么如此糊涂了呢。我说没事,我就是在外有点急事需要办。他说,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说,帮我告个假吧。他说,早上没见你来,我就给你请病假了的。只是刚才吴总路过我们科室门口,没见到你,便问起了你。她有些不悦。吴总就是她,我曾经的妻子,我现在的挂名妻子。我说,你管她呢!我又说,我下午也可能不来上班,这要看事办得怎么样。他说,没事的,你只管去办事好了,科室有我顶着。听了小周的话,我一时很是感动。
我与外单位接触少,不知道其内部机构设置,像民政局,我要打听的事该找哪个科室呢。我正想着,无意间来到了局办公室门口。我就径直走了进去。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女孩子。正在打电话。见我进来,眉头皱了一下,明显的有些不悦。这个我看得出。她将左手握着的电话换到右手,这才用左手连指两下门外,不知是叫我出去,还是把我当成要救济的了,说是要救济得找外面哪个科室。一路来的经历绞得我也是累了,身累心更累,我需要歇息一下,缓缓气。我不出去,我得在这里歇歇。但我很知趣,安静地找了张椅子坐下来。我怕站着有催她之嫌,也怕妨碍她打电话。我历来怕给别人找不痛快。她若认为我站着妨碍了她,或者是在催她赶快结束电话,她肯定不痛快。她见我坐下了,也懒得再理会我了,就继续她的电话。当然,其实她的电话也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间断过。她这就旁若无人了,该大声的大声,该笑的笑,该打情骂俏的打情骂俏。她毫不约束,极其随意。我很羡慕她。羡慕她的不约束,羡慕她的随意。我就不能。我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看别人的脸色说话,不敢重手重脚,不敢粗声大气,要尽量地压抑再压抑,小心再小心。
在女孩子煲电话粥的过程中,我少有的触景生情起来,想到了我的过去,又想到了我的现在,甚至把思绪牵引到了未来。想到过去很平淡,想到现在很哀叹,想到将来很迷茫却又充满希望。
正在想到未来时,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响了起来,我条件反射地一瞧,十二点了。听到钟响,那女孩也停止了电话。这就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我急忙堆满笑脸走向那女孩。那女孩说,下班了,有事下午来。我说,就一句话的事情,很简单,耽误不了你。她又皱了下眉头,说,快说。我说,想咨询一下“幸福苑”这个地方,不知该找哪个科室。她说,你怎么不早说?这时都下班了,你找谁问去?我说,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吗?她冷冷地说,我只管办公室的业务,哪管别个科室的事?说到这,她的一只脚已迈出了办公室大门,她也半推半赶着将我撵出了办公室大门。接着便听她“嘭”地一声将门关了起来。
我很沮丧。我蔫蔫地,脑子一团糨糊地毫无目的地往前走。这就撞上了一个人。一个男人。大概五十几岁的男人。我忙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他见状,先一怔,接着便笑了。说,不用这样。我仍满脸赔笑地说,对不起。他不笑了,以为我神经有问题。他便不再理会我,继续往前走。他大概是把我当着痴、呆、傻、残、神之属的人了。当然,也难怪他要这么认为,来民政局的么,大多是这类人来要救济的。我自然不放过这个咨询的机会。我想他八成是这民政局的。我就快走几步,赶上他,当然不能与他平行,更不能超过他走到他前面去。得略微拉后一点。这个规矩我懂得的。我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我都是这么做的。习惯成自然。我说,我向您老打听个地方,您知道“幸福苑”在哪里吗?他说,幸福苑?没听说过,可能是哪个福利院的名称吧,你去各个福利院找找。
5
我这几年身子一年比一年弱。上午淋了雨,下午便开始发起烧来。浑身无力,走路轻飘飘的,似踩在云端上,怎么走也走不直,怎么踩也踩不实。好在我家里有凤头生姜,我找一块洗洗,切细了,用开水冲服,发发汗,又睡了一下午,起来便好了。久病成良医,这句话有道理,也有用,关键时刻我能自救。当然,我也养成了凡是依靠自己的习惯。
晚上她没回来。这对她是家常便饭,她经常夜不归宿。我也眼不见心不烦。尽管上午查找“幸福苑”有些不顺,但我今天心情却好于以往,毕竟我知道了“幸福苑”与我有些关联,它是我的未来、我的理想之地。我胡乱应付一餐晚饭。饭后,脑袋突然灵光一现,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现实中有“幸福苑”,网络上也会有的。对了,这几天我脑子有时有些短路,我也不知是怎么的了。我就急切地坐在电脑桌前,将“幸福苑”这个名称,满怀希望地输入百度,希望万能的电脑能给我解惑答疑。网上这个名称很多,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我又打开高德地图,在我所在地的区域内仔仔细细地找。也没有。我不死心,又进入我们这个县民政局的局域网,我想无论是地名、街道名还是福利院名,在民政局的局域网上都是应该查得到的。可是,网站的旮旮角角都找遍了,连一个字都不漏掉,我花费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结果连“幸福苑”的影子都没看到。
我摸出一支烟点燃,深吸一口后,来到阳台上站立。华灯早亮,亮得有些妖冶,让这座城市处于五彩斑斓之中,我这时突然觉得灯光和这座城市搅和在一起,很暧昧,很招摇。就觉得这座城市和灯光教坏了许多人也暧昧也招摇。你想,整天生活在暧昧和招摇之中的人能不暧昧、能不招摇吗?我深深地叹息一声。
我的目光透过暧昧和招摇,投向机器轰鸣、塔吊昼夜不停的雨后春笋般遍地往上冒的楼房,耶?我何不去住建局网站查一查有无叫“幸福苑”的楼盘呢?看我这脑子怎么又短路了?据说,这座城市现在变成土地财政了,这座城市的财力,已被上届领导提前透支了二十年。上届领导潇洒够了,屁股一拍走了人,这届领导却生存不下去了,就只得打土地的主意,就敞开口子卖地,房地产生意就欣欣向荣、一派形势大好。我立马返回电脑前,深吸一口烟,后将其灭掉,就埋头进入我的工作状态。在正式查找前,我增加了点技术含量,从不信教信佛的我,破天方地双掌合十,闭目凝念,无比虔诚地默念一遍“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让我顺利查到幸福苑!”然而,也许菩萨要保佑的人太多了,并未让我进入他的法眼,或者是我“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让菩萨不满,他便不屑理睬我。他没有让我查到一个与“幸福苑”沾边的楼盘。
我沮丧至极。
但我有耐心。我锲而不舍。
我换了一种方式。
我开始思索,哪些人还与我有联系。我断断续续地逐一开始打电话了。十点钟之前打的,除了已关机的几个,其余都给我回了话。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不知道有这家楼盘,不知道有这么个福利院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地还问,你找“幸福苑”有什么事?十点钟以后打的,就没多少人接了,好多在铃声才响起一两声时就给掐断了。但我不气馁。我要坚持,我必须坚持。在十二点以后打的,接我电话的就更少了。有几个尽管接了,听了是我的声音,却只说了句“都这半夜三更的了,有事明天再说吧!”就无情地关了机。还有几个接是接了,却根本不问我是什么事,就劈头盖脸一声断喝,你神经病呀,这半夜三更的,你打什么电话?接着自然是关机,我还明显地感觉出他们关机时是那么狠狠地用了力的,好像搅扰他们美梦的不是我而是手机,他们都把火发泄到手机上了。但我不厌其烦,我不燥不恼。
我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小周的,那时已经凌晨五点多了。我无意间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了的。小周接到我的电话,电话那头尽管他呵欠连天,听语气他却相当的着急。他以为我病得厉害。他说你不要着急,我马上过来送你上医院。听了他的话,我有一时很苦涩,但接着我很感动,我分明感到他话语的温度在这雨夜里是多么的暖人。我几乎要哭了。真的!这么多年,我还没遇到有人这么关怀我。我说我没事,我昨天的感冒已经好了,我就是想问问“幸福苑”在哪里。电话那头的他明显地松了口气。他说,他不知道“幸福苑”在哪里。他说这个时候了别打电话了,好好休息一下吧,注意休息,注意身体,这事他上班后会来帮我认真打听的……
后面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了。我脑袋一沉,眼睛一闭,手一松,电话掉在了地上。
我睡着了。
6
我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对面墙上的挂钟,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五十八分。咦!不对呀,我们家不曾挂有这个样式的挂钟呀!我这是在哪里?我又往四周看看,这才看到我是躺在病床上的,我左右两边各有一架病床,上面也躺有病人。他们都睡着了。陪护他们的人也睡着了。我是在医院?我病了?
我来到走廊上,朝走廊两头一望,入口的门楣上和尽头的墙壁上都写有“精神医学中心”几个大字。看来我是真的病了,但我明显感到我是好端端的呀!我怎么会病了呢?莫不是有人要将我当作病人囹圄于医院里了却我的残生了?想到后者,我一激愣,浑身打了一个寒战。我十分害怕。我还要找我的幸福苑呢,我怎能被羁绊于医院呢?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我前脚刚跨出“精神医学中心”的大门,背后就被揪住了,让我不能再前行一步。我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一白大褂。他高大威猛,在我面前绝对是一孔武有力的巨人。我没有任何抗拒的余地。我只得老老实实地任他将我提进大门内。他板着脸,盯着我,冷冰冰地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不干什么呀,就溜达溜达。他说,病人没有亲人陪伴不得跨出这个大门一步。我说,我不是病人呀。他说,你不是病人?你自己看看。他指着我的衣服裤子说。我一看,这才发现自己穿了一身病号服。我说,我真没病,我不知道这身病号服是谁给我穿在身上的。他看了看我衣服上的号码,说,咦?你不是昨天凌晨被一小伙子送来的那个啥吗?你病得不轻呢!你还在狡辩……看护你的家属呢?哪去了,怎么就让你走出病房了呢?明明我昨天就交代他了的,暂时不能让你走出病房一步……我忙打断他的话,说,我真的一点病都没有……他说,别啰嗦了,赶快回到你的房间去。他这就如拧一只小鸡似的,将我拧着直接摔在病床上。
这时我左右两床陪护的人被吵醒了,他们直愣愣地望着我。那白大褂对两陪护说,他的陪护呢?哪去了?怎么就让他乱跑呢?你们得帮忙盯着点,别再让他跑出去了!
看来是有人真的要将我圉于医院了。莫不是她么?小伙子送我来的?是小周?小周成了她的帮凶?小周也被她俘虏了?她现在在开始老牛吃嫩草了?她俩要合谋我?……我再次打了个寒战,我更加地害怕了。
我还得逃出去!
我得动动脑子。我得想想计谋。
我开始假寐。我开始假装打呼噜。我等待那俩陪护放松警惕后的再次睡去。我要偷偷地溜走。我要潜逃!
7
我终于逃了出来。这要得益于我脑子不短路了。我聪明起来了。也得益于小周的笨拙。他没有将我的衣服收走,而是折叠得好好地放于我的床头柜中。我笑了。我很舒心。我换下病号服,穿上我自己的一身行头,还趁病人和他们的陪护都睡着了,顺手将左床病人的一副眼镜轻轻顺下来,戴在我这一点五视力的眼睛上。我踉踉跄跄快速地走出病房。这眼镜真他妈不是个东西,也是个势利的家伙。别人戴着都说能更清晰地看清东西,而我戴着它却让我头昏眼花,让我视物模糊,让我头重脚轻,让我走不直路。管它呢,尽快逃出去要紧。后来我一逃出医院大门,我就将它狠狠地扔在地上,还踏上两脚,最后又飞起一脚将它踢得不见了踪影,这才解了我的心头之恨。
走廊上尽管有人来来往往,他们却丝毫没在意我,甚至连看我一眼都不。只是冤家路窄,我遇见了白大褂。这时他好像比先前拧我时更加高大威猛了。我自然地浑身一颤。我忙将头扭向一边,装着看房号找人的样子,心理却默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别让他看见我别让他看见我”。这次菩萨开了恩,真的保佑了我,让白大褂好像只瞟我一眼就走开了。
阿弥陀佛,待我找到幸福苑后我一定多给你烧几炷香。
也许是我的虔诚感动了菩萨吧,我的运气好起来了。我一跑出医院大门,喜事就与我碰了个正着。
我遇见了一个人。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他是我的福星。他见我就唱“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而且是反复地唱,并且就只唱这两句。边唱还边瞅我。莫不是菩萨显灵,化着这么个人唱着这两句歌来暗示我的么?
我就紧跟了他。只是他不让我接近他,我疾走几步他也疾走几步,我放慢脚步他也放慢脚步。他还嘻嘻朝我笑,仍旧唱着“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我就喊,菩萨,你是要告诉我幸福苑在哪里么?他看我一眼,不正面回答我,仍朝我嘻嘻笑,仍唱“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这时我脑子不再短路了,突然灵光一闪。我知道这时菩萨点化我了,他这是要我跟他走呢!他是在带我去“幸福苑”呢!
我就不离不弃地跟他走。
菩萨路过一垃圾桶时,往里看了一眼,就迅速伸手捡起一个什么东西往嘴里塞,东西吞进肚里后,他又朝我嘻嘻一笑,继续一边朝前走一边唱“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菩萨这是在暗示我应该要买上东西向他表示心意么?
路过一家包子店,我赶紧买了一屉小笼包。
菩萨不知是踩到了什么还是有意要考验我,他滑倒了。我赶紧走向前扶起了他,而且将那袋包子伸向他,虔诚地说,菩萨,这是我敬献给你的,求你带我找到“幸福苑”!
菩萨抢过包子,朝前跑了。他边跑边吃。直到包子吃完了,这才回过头来看我,又是嘻嘻一笑,继续边走边唱“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
城市走完后,菩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难道“幸福苑”在郊区?管它呢,就是在天边我也要跟着去找到它。
8
当我在一座牌坊式的门楼前站定时,看着门楣上的几个朱漆大字,便疑云丛生起来。难道菩萨在忽悠我?
我来到了这个城市的公墓了。哦,应该说是菩萨将我引到公墓来了。
今天也怪,从小就害怕死人、害怕坟墓的我,现在我一点也不害怕,相反,倒有种说不出道不清的亲近之感。
难道“幸福苑”就是公墓?公墓就是“幸福苑”?
我将疑虑的目光投向菩萨时,菩萨又向我嘻嘻一笑,一闪,就不见了。
这时,夕阳从西山顶上的树枝间投射下来,让我一时眼花缭乱。
先生,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来祭拜呀?我正在轻揉被阳光照花了的双眼时,一个阴恻恻的声响从我前面几米远处缓缓传来。我逆了光望去,一高长大汉模模糊糊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与我对着话。
我说,我不是来祭拜的,我是来找“幸福苑”的,不想却来到了这里。我又说,你知道“幸福苑”在哪里吗?
他说,哦!知道了。其实你来对了,这里就“幸福苑”。你想,人一当死了,来到了这公墓里,什么忧呀愁呀,什么恩呀怨呀,什么穷呀富呀,什么官呀民呀,都不存在了,大家都一律平等地居住在这里,大家都相安无事地居住在这里,大家都无忧无虑地居住在这里,不都很幸福么?这公墓不就是“幸福苑”么?
这时,我脑子又短路起来,反应迟缓起来。我想了一会儿,才点点头,说,嗯,你讲得有道理,来到这里后都很幸福,这里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幸福苑”。
我脑子又恢复了正常。我很兴奋,我终于找到“幸福苑”了!我的未解之谜终于要解开了!
他说,那么,你要去哪里看看呢?
我说,要去286 号。
他似乎显得很惊讶,说,286 号?你是说286 号?
我说,是的,286 号。
他说,286 号不简单呀!它有两百多年历史了,是这里最豪华最气派的一座墓。据说,墓主人在世时,那可是名人呢!一辈子风光得很哟,家大业大不说,光妻妾就有二十八位,而且个个貌若天仙……
他还在絮叨个不停,我本想还听听他说些什么的,可是我的心思却瞬间变成了一个矛盾体,却又早已等不及了,让我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牵扯着,懵懵懂懂走进墓园,直接朝286 号奔去。
这时夕阳已经彻底地隐下西山了,不知是雾罩还是炊烟,早已笼罩了整个墓园,让遍地的坟墓若隐若现。暮归的鸟儿不时从身边、从头顶掠过,扇起冰凉凉的风。一只夜猫子在这边叫了又飞到那边叫,其声瘆人。还有一种鸟,孤独地叫着“狗饿狗饿”的,甚是悲切。
我看着、听着这一切,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一点也不觉得怪异,我倒是觉得这种氛围太好了!很适合我!我很激动很激动!我知道这是为我准备的,这是一种奇特的迎宾仪式,不,是欢迎我归来的盛大典礼!
找到286 号很容易。我不需费脑子,也不需劳动眼睛,那脚很自觉地往前走,轻轻松松就将我的整个身子带到了286 号。
这时,朦胧中,我似乎听到了墓园外有救护车、警车的鸣叫,似乎还听到了呼唤我的声音,其声焦急。管它呢,快快进入286 号要紧。
286 号是墓园中的墓园,其规模与豪华比皇家陵园毫不逊色。墓园的大门口有一口几十亩大的被正方形地块包裹起来的圆形水塘,我猜测这是取“天圆地方”之说,意为圆满吧。当然,墓地讲风水,这里没有河,自然得让其有水。我记得有次旅游时,导游介绍某皇家陵园时是这么给我们讲过风水的。进入园门,便是石板铺就的长长的六米左右宽的甬道了。甬道是逐级而上的,这让人要不自觉地向前抬头仰视。我想这是要前来观赏或祭拜的人对墓主人充满敬意吧。甬道两边,里侧是三十六组形态各异的石人石马,好似墓主人的仆从,又似护卫墓主人的兵卒,恭立于前,随时听候主人的差遣。外侧则是苍松翠柏相拥,将整个墓园拱卫了起来,让墓主人在其间恬适地享受。甬道尽头的两侧,是两块供祭奠的平台,奇怪的是这时尚还有香烛没有燃尽,发出时明时灭的惨淡的光。不过在我看来,那是为我指路的灯。中间后退一点是一座宫殿式的城楼,城楼巍峨耸立,让人仰望,很是肃穆。这时,厚重的朱漆楼门在沉闷的“吱嘎”声中自然地打开了,我穿过门道,便看见了城楼后面小山似的让人震撼的坟墓。
我兴奋地疾疾地奔向墓前,不自觉地围绕坟墓转起圈来,左三圈,右三圈。最后在墓门处停止,那双脚很自然地朝地上跪去。
我借着微弱的天光,开始阅读起墓碑上的文字来。越读我越兴奋,读着读着,我好像渐渐进入到二百多年前的时光了。这时,便有仙乐骤然响起,不一会儿,但闻一群马蹄声“嘚嘚”而来,须臾间,我骑着高头大马,在浑身遍插繁花的二十八位妻妾和众仆从兴奋地前呼后拥下威风而至。远远地,那门楣上“幸福苑286 号”的门牌号闪着清冷却很亲切的光,似在召唤着我的快快归来。守门人尚来不及打开大门,早已等不及了的我跳下马车,伸手用拳头“咚咚”地擂了几下门。门才被守门人拉开一条缝,我便头朝前,霸气地向门里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