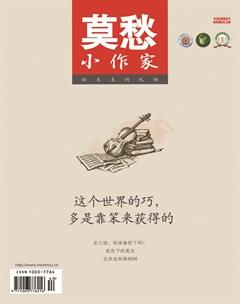十八子
拧开绿药膏的盖子,淡淡的药香扑鼻而来,云菱抠了一块,膏体像果冻似的,晶亮亮,绿莹莹,颤巍巍。云菱细细打量一番,偷偷将药盒装进衣兜。
正自偷笑,厨房传来呼喊,夹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云菱回以同样高亢的嗓音,“老妈,十八子有事喊你!”
“没大没小!要懂礼貌,十八子不是你喊的,晓得啵。听话,喊李舅爷,妈给你买最爱喝的冰可乐。”说话间,老妈已闪进后厨间,顶着陆石河畔秋老虎的暑气,去遭遇另一场人为制造的高温。
书上管这叫人间烟火,云菱不懂,她小脑瓜左摇右摆,麻花辫一甩一甩,正是如风般自在的年纪。
里厨,锅已烧至温热,将鸡腿去骨,切块,放在砧板上按压松软,至水中浸泡抽出血腥,佐以料酒,冰糖、酱油、盐巴搅拌均匀,倾盆倒入滚烫已久的热锅,鸡肉炖开的间隙,备好去壳板栗,压回锅中。十八子正埋头做他拿手的板栗炖鸡。
云菱坐在堂屋,看见墙角日光照射处,现出簌簌剥落的墙衣,她觉得十八子脸上的皱纹,比墙衣斑驳。
“老妈,能不能别带我去蹭饭,丑行。”丑行,陆石河方言中寓意丢脸。云菱不喜欢十八子,也不喜欢去十八子的家,十八子拿手的那道板栗炖鸡,自己也早已吃腻。在十八子家唯一感到快乐的事,莫过于那些花花绿绿的药瓶,果盘中她最爱的永不见底的果丹皮,以及电视机里按上许久都摇不到末尾的电视频道。云菱最爱看额外付费的点播频道,趁老妈帮厨的工夫,抄起电话一通乱拨,可以连续看上好几集《百变小樱》。
待到日暮西斜,迷迷糊糊梦醒从沙发爬起,方桌上已摆放起三副碗筷,火锅夹在当季时蔬中间,板栗打底的鸡汤冒出咕咕热气,过去坐下,鸡腿早专门拣出挑到自己碗里,不消问,十八子的手笔。
十八子,龅牙齿。龅牙齿的十八子每每端起碗便打趣道:“吃饱不想家,多吃点,吃饱不想妈,把你可乐分一半给舅爷喝好啵。”
“我不!”
日久年深,云菱对于十八子的厌恶有增无减。更深月色半人家,时逢月圆他总要饮到大醉酩酊才罢休,孤家寡老没人管,记忆深处,每回皆是自己同老妈推着自行车,自陆石河畔棉地里将他拽至后座拖回家中醒酒,一副赖皮样。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怎么还有越活越转回去的。云菱抱怨:“少管他,老妈,远亲罢了。”
“小孩乱嚼舌头,远亲就不是亲了?你可没少吃舅爷的果丹皮,宗亲孤老一个,能搭把手的就帮衬下。”
时光飞逝,宛如簌簌剥落的墙衣。云菱不再是拿药膏当橡皮泥玩的孩子,也不再拿豌豆黄盒子当口哨吹,教会她吹哨的十八子舅爷早就离世。
三伏天,云菱给蚊子叮得身上全是大包小包,遍寻各种驱蚊水毫无功效后,治好身上叮咬伤口的,居然是老妈带來的绿药膏。还是小小一盒,装着果冻样的膏体,这么多年都没变过。云菱想起一个久违的人。
那个在三伏天的人间烟火里,满头大汗做板栗炖鸡的人,那个在果盘里填满果丹皮的人,那个把鸡腿留给她的人。
十八子,龅牙齿,这回我把可乐全分你喝,好啵?
刘博文: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作品集《至尊荣耀》,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编辑 沈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