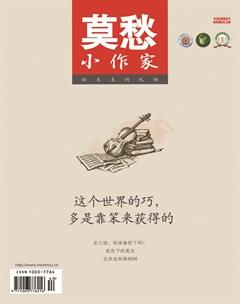晴蓝
丽晴
多数时候人们对于阅读是有偏爱的。有一向,我爱看老电影,黑白片,有些还是默片。没有声音。语言隐匿之后,神情和肢体的表现就显出某种特别的张力,比如卓别林的表演,看第一遍时为他夸张的肢体语言而笑,看很多遍后,才渐渐懂得,那些亦丑亦怪亦搞笑的表情、动作之下,是一种儿童式的天真无邪。那段时间还爱读旧书,南京的仓巷没拆之前,常去,晚秋的午后,低矮的屋檐下那张破旧的藤椅上,半依着一个枯瘦的中年人,渔夫帽遮住他半个脸,只要门前有自行车的脚撑子一落地,听声音便知有逛店的人到了,立即睁眼。那种迅捷,猫一样的敏捷和灵动,全然没有先前假寐时的中年式的颓唐。
还老惦念着去上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火車,与现在相比是慢的,慢车才可将人带往真正的远方,如同好诗从来不必堆砌在枝头闹春意,最远的远方是在自己心里,人迹罕至,从不狂欢。每次到上海,思南路和山阴路必然要去,正午时分,阳光安静,路人贴着墙边走,偶尔有几朵玉兰从围墙高处伸出来,红玉兰红得像三月春花,白玉兰白得如早餐桌上兑了黄油的牛奶。山阴路附近有家旧书店,在那里淘得不少的宝贝,其中有本《恩格斯传》,三联书店出版,1975年第1版。书的版权页和封底上标明是内部发行。定价1.65元,我花15元买来。封面上盖着蓝色的长方形印章,上海市延安中学图书室。蓝色印章中间,盖了三个红色的字,注销章。这家二手书店的店名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一间旧旧的地下室里,店员的衣服和脸上的神情干净、洁净,有着全然不同于仓巷旧书店的晶莹澄澈。
这些默片、旧书、老街,影像受损,纸张发黄,包括街边那种实木包边的玻璃门,都有着沧桑过后的宁静,也都透着时光过滤后的从容,带给我一种陌生的新奇。我却一直没找到一个词能精准地说出这种心境,词穷。
有一天,读加缪的日记。很短,写那天的天气。他写道:“8月的雷雨天。热风和乌云。但东方却透出一抹晴蓝,轻盈而剔透。教人无法直视。”我迅速停下,慢慢合上书,生怕刚刚看到的那个词,那个晴蓝,会从纸页间漏走。连续几天,心里都有着隐隐的小小的欢愉,为一个词语的出现。晴蓝,两个简单的汉字,一旦重新排列组合,便打破了原先各自约定俗成的意思。晴蓝,是我之前所有的关于默片、旧书、老街的答案。每一个词,当放到生活的具体场景里,都有着比词典上所给出的更丰富的含义,比如晴蓝,两个字,字字认识,但真正读懂一个词如同读懂一个人,靠的是阅历和积淀。比如汉语中的“西”字,无言独上西楼,古道西风瘦马,西塞山前白鹭飞,门前流水尚能西。此处的西,换成东北南任意一字都不适合,东西南北对应着春秋夏冬,西风就是秋风,是人在精神上的淡远、清幽和疏离。晴蓝,空与灵、虚与实相结合,照应现实而不照搬现实,遵循着现实的逻辑但又有着艺术的浪漫,这就是晴蓝的美妙,它与默片、旧书、老街有着类似于春草碧色、春水绿波般的契合。
还是加缪说得对,“套话,我们要小心,它有时像打雷,很惊人,却不照亮。”他在1935年写下的词语,晴蓝,故纸堆里冷艳无声,但依旧是高树朗月,照亮幽微,捎来东风消息。
转头望向窗外,洁净豁朗。晴蓝,一个词就是一个答案,就是一种境界。山高水阔,长亭短亭却未必再相逢。纵然人情再美,桃花潭水深千尺也只能冷暖自知。岁月尽管漫长,但世事难料,唯星汉照耀文明,唯词语让人心里能瞬间漾起美意,甜意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