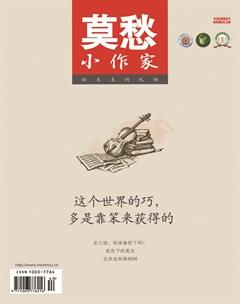老楼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城有一处热闹非凡之地,叫“北招”,全称应为“海安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因为招待所位于通扬河北侧,人们就称之为“河北招待所”,简称“北招”。后来,县政府又在通扬河南岸盖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海安宾馆,海安人却坚决不买账,偏偏不称它“宾馆”,只叫它“南招”。
北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面看呈“凸”字形,从高空俯视,则是“凹”字形,里面布满了低矮的平房,一栋主楼则是典型的筒子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府机关办公楼,乃至政府招待所,其建筑大多是苏联建筑风格的筒子楼:一条长长的走廊,串起两旁众多的单间,每个房间只有十来平方米,每个楼层都建有公用的盥洗间、热水供应炉和卫生间。
北招这栋筒子楼的第三层和第四层,住着几十户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家庭,以及陆陆续续分配过来的大学毕业生。楼里每天都演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每天都回荡着孩子们的笑语欢歌,每天都发生着令人捧腹的成长故事。而推开窗户,向楼外望去,又是另一番阳光灿烂的景象,楼下人流的喧嚣清晰可闻,热气腾腾的市井气息拂面而来。1990年4月,我从县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调进县政府办公室后,我们一家三口就从县歌舞团宿舍区搬进来,在这栋老楼里住了整整五年。
老楼像一座巨大的蜂巢。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进出最频繁的一定是女人们。大清早,我还在睡梦中,楼梯上一阵一阵咔嗒咔嗒的脚步声,家庭主妇们去招待所大门西侧的新华菜市场买菜、买早茶(早点),买回来就到盥洗室择菜洗菜,簇拥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着中午的菜谱:慈姑烧肉、扁豆饭、炖鸡蛋、丝瓜炒毛豆米、青菜手擀面……你怎么买到手擀面的呀……在菜场对过西北角落儿的刘大麻子面店……哦,原来不在菜场里面……我家才从墩头镇搬过来,对县城里头还不熟,你下次买面条要带上我一起去呦……你是才到街上的?你家男将从墩头镇调到哪个单位啊?……哦,县计委,管计划的,吃香!……啊,不是计委,是专门查人的纪委哎……哦,我对上号了,张书记是你家男将,嘿嘿嘿……
洗完菜,再打发孩子吃过早饭去上学,女人们才有空闲解下围裙坐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打扮一下。男人在政府机关上班,女人不能穿着打扮太随意,又不能过于花枝招展引人注目,必须大方得体,否则招人耻笑,自个儿的男将也跟着被人看不起。
盥洗间每天的第二次高潮则是在晚饭后,主妇们洗碗刷锅的时候,像一群倒了窝的喜鹊,叽叽喳喳传递着一天内自己工作单位的各种信息:我俫单位的陈二小,活像个武大郎,还是个斜眼儿,这个怂形还找了个海北乡下的一个漂亮姑娘。多漂亮啊?活像电影演员李秀明!那么漂亮的姑娘,圖他什么呢?还不是图他城市定量户口吃的计划粮?另一个女人接过话茬:哎,肯定是。我俫单位的王五儿,人倒长得不丑,可天生哑巴,城里的姑娘哪个嫁给他?也只好找了个乡下姑娘,哑巴宝贝得不得了,恨不得把细马马儿当个菩萨供起来呢……
住在大楼西侧的是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隔了不久就当上副县长的王夫人。她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了,儿子正在念大学,等大家碗洗好了,她开始召集女邻居,组织当晚的娱乐活动——打牌。活动场所就是她家的小厨房。我老婆把锅子碗筷朝门口过道的电磁炉上一丢,说一声“我去耍子了”,就丢下我和还没上幼儿园的儿子看动画片《猫和老鼠》。老楼的夜晚属于无忧无虑的女人们。
老楼很像一座儿童乐园。以我家为界,东半部七八户人家的孩子都在上小学,西半部的七八户人家,除了王县长家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其他家的孩子都还没上幼儿园。最小的细伢儿还鼻涕拉多长,小手抓着脆饼坐在瓷马儿(海安的城里人喜欢用痰盂做尿盆)上咧着嘴哇哇大哭。那时的工作日,大人们把门钥匙往孩子脖子上一挂,各自上班去了,孩子就托付给家里有老人的照应。老楼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邻里之间相互帮衬着,过着悠悠的日子。
让大人发笑的事情接二连三:东边那个叫小立的男孩,找不到年龄相近的男孩做玩伴,就低三下四地放低身段,想和隔壁两家的女孩子打成一片。那两个小丫头的性别意识实在太强烈,要么让他吃闭门羹,“应怜阿立小男孩,小扣柴扉久不开”;要么一个前拉一个后踹,将他扫地出门。就在小立发扬钉子精神坚决赖着,企图在脂粉堆扎根之际,姓唐的小丫头顿生一计,模仿起头天晚上在招待所大会堂看到的香港电影片段:只见她用小手捂着胸口平平坦坦的娃娃衫,细嫩的童声发出波涛汹涌的尖厉咆哮,“非礼啦!非礼啦!”愤怒的女高音响彻楼道。小立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惶惶然逃回家。回过神后,他气得满脸通红,又羞恼又不甘,委屈的模样痛苦不堪。其实,小立原先是有玩伴的,那孩子叫丁一。丁一的父亲在县公安局工作,成天忙着抓坏人保安定,顾不上孩子。丁一的妈妈是饲料厂的供销员。海安是养鸡大县,饲料市场生意火爆,平时丁一妈妈也忙得四脚朝天。孩子没人管可怎么办呢?这个女将经常跑大城市,见多识广,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或启发,想到让儿子丁一去学二胡。丁一从此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小立也由此失去了最好的玩伴。每到星期天,全楼的孩子像野鸭似的,到处乱奔乱跑乱叫着撒欢时,丁一背着乐器盒子,一步三回头地望着小伙伴们,依依不舍,眼眶里噙着泪水。晚上回到家,丁一还要回课,拉二胡给父母听。于是,整个三楼的长廊里就回响着悲悲戚戚断断续续的二胡声,让我总感觉有个乞丐站在门前乞讨似的。
老楼也像是男人们的港湾。忙忙碌碌工作一天之后,男人们一回到家就变得慵懒倦怠,仿佛刚在机关干成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又好像才从挑河工地回来似的,成了油瓶倒了也不扶的甩手掌柜。女人们则满怀着灼热的母爱,毫无怨言工蜂似的忙碌着。她们从不幻想修到一个理想来世,她们满怀着对生活的耐心,脚踏着此生的坚实大地,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操心着丈夫,操心着孩子,操心着稀松平常的柴米油盐酱醋。
女人们把家人照顾妥当,扎堆耍子去了之后,在县里身居高位的男人三扒两咽吃过晚饭还要赶去开会,研究秋收秋种和给特困企业解困。我则和住在我家对门的两个大学生开始谈闲沰寡。他俩刚从北京、南京的名牌大学分配回家乡,对眼下的小日子十分知足,没有牢骚,没有怨言,看淡了人世间浮华,在老楼的小房间里,摸着肚皮,享受着安安稳稳的幸福。偶尔开夜车加班,为县领导起草讲话稿,也算不上辛苦。他俩刚刚分配到政府机关时,正好有一个财校的女大学生也分配在县商业局当会计。这个楚楚动人的姑娘经常约两个小伙子打扑克。我有孩子缠着,就站在一边围观,发现那个女生把牌局弄得风情满满,她的意图,在我这已结婚生子的过来人眼里昭然若揭。然而,此景不长,随后会计名花有主,我家对门的两个小伙子下班后就开始踢足球,从楼上带球到楼下,一路踢到招待所后面的海安中学操场。我儿子跟着他们一路当铁杆球迷,陪着血气方刚的他们挥洒无处发泄的青春。
自从我在县政府办公室见习期结束,跟着县长当秘书之后,工作就开始忙,有时竟然忙到十分迷茫。带着对人生的各种思考,带着各种疑虑和不安,我心神不宁。我经常深夜里一个人蹑手蹑脚走上四楼的顶层,望着浩渺静谧而又美好的夜空,内心涌动着大海般的孤独和惶惑。此时,唯有老楼在默默陪伴着我。
老楼里驻扎着我们的过往岁月。回望这些岁月时,才会猛然发觉老楼里的人们老了。当年慈眉善目的王县长早已退休,儿子已是省级机关某部门的厅级干部。那个当年手拿着脆饼坐在瓷马儿上放声大哭的小女孩,如今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那个带着哀怨眼神去学二胡的丁一,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民乐团工作。那个根本不懂何为“非礼”却叫着“非礼”吓走小立的小姑娘,她的孩子都进中学了。那个被小姑娘吓得狼狈逃窜的小立,而今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那两个住我家对门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早就离开了家乡,在外面发展得风生水起。
老楼依旧矗立,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样子。只是,老楼里再也没有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笑声。他们已经长大。他们正和他们曾经年轻过的父母亲一起,优雅地慢慢变老。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肖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