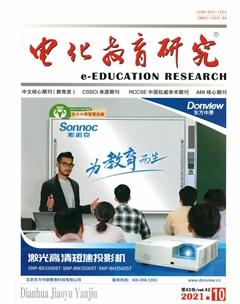连接式建构:知识建构研究的新取向
万海鹏 余胜泉 王琦
[摘 要] 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对学习和认知的革新,学习的关键除了要构建知识并促进学习者的认知行为,在此过程中建立一个能够联通各个知识节点的社会知识网络也变得日益重要。不同于以往知识建构所秉持的行为交互层次、个体知识内化与外化水平以及社区整体知识增长的角度,研究从后现代知识观和联通主义学习观的视角出发,设计了以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为双核驱动的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该模型强调知识建构过程中知识具有的情境性、进化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以社会知识网络为建构载体,关注知识建构活动中建立的知识与知识、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的可视化连接。随后,基于学习元知识社区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探索,以期为知识建构领域的研究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关键词] 连接式知识建构; 知识网络; 社会网络; 社会知识网络; 学习元知识社区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万海鹏(1988—),男,江西宜丰人。讲师,主要从事在线学习认知地图、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研究。E-mail:dnvhp@163.com。
一、引 言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信息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传统工业时代,“以教为中心”的被动接受式学习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知识更新换代迅速、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共建共享的知识型社会。而知识建构则试图从理论、教学与技术多视角进行创新,立足于21世纪社会所需要的合作式知识创造能力,尝试以最直接的方式重塑学习,即将学习者置身于真实的问题情境中,让学习者积极主动、有目的、持续性地参与以观点改进为目的的社区知识建构活动,从而获得知识创造能力,扮演协同知识创造的贡献者角色[1]。
近年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习以及知识观的改变,打破了当前知识建构贡献的局限性及封闭性,增加了知识建构体验的选择性、自由性及社会性,促进了知识建构过程的数据化和可解释性,推动了网络时代知识建构模式的变革。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在线学习中的知识建构过程,探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展示的新特性,寻求知识建构的新方向,形成可操作的知识建构模型或方法。
二、知识建构相关研究回顾
知识建构(Knowledge Building)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现代科学萌发时期,当时只是被看作一种问题探索或解决的科学方法[2]。随后许多研究者纷纷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开始了将学校重塑为智能型社区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理念和模型,如学习者和思考者社区[3]、探究社区[4]和知识建构社区[5]。为更好厘清当前知识建构研究的关注焦点,本研究选取三类典型的知识建构模型进行介绍。
(一)基于交互层次的社会性协同知识建构
为了深入理解知识建构的过程,Gunawardena等人从交互层次的视角提出了知识建构交互层次分析模型[6],将社会性协同知识建构过程划分为共享和比较信息、发现和分析观点间的差异、通过提出新建议共同建构知识、测试和修改协同建构的知识、成员间达成共识并应用新知识五个基本阶段,见表 1。
表 1 社会性协同知识建构交互层次分析模型
(二)个体与群体协同的社会性知识建构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认为学习是一个协同建构知识的过程[7]。为了揭示这种协同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群体协作和个体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Stahl基于社会建构主义对学习的理解视角,提出了包括个体理解和社会性知识建构的双循环知识建构过程模型[8]。双循环知识建构过程模型中的箭头表示知识转换过程的方向,矩形表示知识转换过程的产物,即不同形式的知识。模型中的左循环表示个体获得知识理解的过程,涉及缄默的预先理解、产生问题冲突、个人的信念、内涵解释、个体的解释、接受并成为个体的认知六个阶段;右循環表示社会性知识建构的过程,涉及用语言表达问题、个体公开陈述的观点、群体中他人公开陈述的观点、解决方案探讨、具有争论的证据和理论解释、意义协商、可共享的理解、达成共识、协同知识、对协同知识的形式化或物化表征、文化制品、将文化制品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12个阶段,如图 1所示。该模型背后所依据的学习理论是社会认识论,个人基于其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知识、共同的语言和外部表征环境,将自己的观点发展成为个人的信念,而这些个人信念又通过沟通、讨论、澄清和协商等社会性交互最终发展成公共知识。该模型为设计、应用和评估协同知识建构环境提供了可借鉴的概念框架。
图1 双循环知识建构过程模型
(三)基于原则的知识建构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Scardamalia和Bereiter将知识视作一种公共产品,认为建构意味着班级作为一个社区整体进行知识的生产,建构的产出即公共知识,这些公共知识是集体贡献的产物。具体说来,其概念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
(1)知识陈述和知识转换阶段(1977—1983年),研究处理知识的不同策略对学生写作的影响,随着这些处理方式与Wiki之类技术的出现变得越来越相关,研究的重点从尝试改善学生写作转向利用设计技术为写作中积极的知识加工过程提供支持。
(2)有目的的学习与认知阶段(1983—1988年),强调认知目标、高水平能动性在学习中的重要性,研究专家和像专家一样的学习者获得专门知识的过程,注意到了社会性支持在有目的的学习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开发了计算机支持的有目的的学习环境CSILE(Computer Supported Inten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并成为下一阶段知识建构支撑环境的雏形。
(3)知识建构阶段(1988—至今),肇始于“知识建构环境设计”的项目。项目初期并没有对知识建构与学习做区分,但却生成了诸如具有生成能力的知识加工环境、管理社区知识等知识建构的基本要素。直到1994年,Scardamalia和Bereiter才將知识建构与有目的的学习做了严格区分,将其定义为对社区有价值的想法的生产和持续改进过程[9]。同时,在技术环境方面,第二代CSILE知识论坛也在这一阶段诞生。随后,Scardamalia提出了基于原则的知识建构教学法,细化了知识建构的十二条原则[10],如图 2所示,并从社会—认知动力学和技术动力学的视角对知识建构原则及其在知识论坛中的技术支持功能之间的不同进行了深入阐释,成为设计知识建构教学法及技术支撑环境和评估知识建构实践的基本准则。
图2 知识建构原则与概念框架[11]
(四)知识建构发展新思路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多是从学习者个体的知识内化和外化水平、社区整体知识的增长、社区成员之间行为交互的层次和深度等视角探讨知识建构的过程,忽视了对知识建构中所生产的知识的情境性、进化性和社会性的关注。后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的境域化、类型化、价值化、综合化和批判性[12],认为知识是学习者根据个人认知能力、兴趣爱好进行选择和建构的结果,知识具有情境性、社会性和多样性等特点[13]。虽然已有研究认同协同知识建构中知识的动态发展性,但对于知识动态发展过程的揭示、知识在不同阶段的关系及进化表征,均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知识转型的当下,需要以后现代知识观的视角审视知识建构过程中知识所展示出的情境性、进化性和社会性等新特征。
同时,已有研究强调知识建构的过程、步骤或指导原则,关注点以知识网络为主线,忽视了交互过程中所建立的社会性连接以及基于连接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建构主义和维果斯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发生在真实情境中,是学习者构建个人知识意义的过程,其关注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社会交互和学习共同体对个人知识意义建构所起的关键作用[14]。联通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建立连接、形成网络的过程[15],网络节点之间的连接越强,信息在网络节点之间流动就越顺畅,知道如何、从哪里找到所需要的知识变得日益重要[16]。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需要从联通主义学习观的视角探讨知识建构的模型及过程分析方法,关注知识建构过程中基于社会性交互建立的有意义连接。
三、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设计
借鉴后现代知识观和联通主义学习观的核心思想,本研究提出的连接式知识建构具有以下四个核心特征:(1)强调知识的情境性,认为知识是与具体学习情境相关联的,主张对所建构的知识进行公共知识与情境知识的区分;(2)强调知识的进化性,认为知识会从知识内容本身、知识与知识之间关联、知识与学习资源之间关联、知识与学习者之间关联四个方向实现动态进化,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所建构的学习资源、知识、学习者之间的连接关系;(3)强调知识的社会性,将参与知识建构过程的学习者主体视作一种可以提升知识与知识、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通达性的社会性知识,主张将学习者主体与知识客体之间建立的各种连接与知识客体一样进行同等对待;(4)强调知识的连通性,认为既要关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知识属性维度及基于此形成的知识网络,又要关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社会交互维度及基于此形成的社会网络,还应关注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两者的螺旋促进效应及基于此形成的社会知识网络。
基于上述核心特征,本研究设计了以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为双循环的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如图 3所示,其中,左循环为知识网络环,右循环为社会网络环,箭头表示信息流的转换方向,矩形框表示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建构的中间环节。具体说来,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不仅包括知识社区、学习者、知识、知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网络等基本要素,而且包含了构建知识网络涉及的知识接受、知识内化、知识贡献三个过程环节和构建社会网络涉及的交互连接、认知连接、社会连接三个过程环节,还对建构过程中社会知识网络的进化与情境适应机理进行了表征。
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以知识社区中的知识本体、学习资源和情境本体为基础,充分利用学习资源与知识、情境之间建立的语义关联信息,以学习者作为实施连接建构的主体,最终生成社会知识网络,其结构如图 4所示。社会知识网络作为连接式知识建构的关键载体,融入了学习者、公共知识和情境知识等要素,展示了通过学习者参与知识建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知识连接、学习者与知识之间的认知连接以及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社会连接,其中,社会知识网络节点的数量、节点之间连接的强弱程度(连接线的粗细表示强弱程度)、节点之间连接的更新速率则用作衡量知识社区发展质量水平的标准。
图3 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
图4 社会知识网络结构示意图
(一)知识网络的构建
知识网络是对知识社区中所生产的不同类型知识及其之间逻辑关系的结构化组织。知识社区中的学习者通过参与学习活动进行知识的生产,所生产的知识经过知识社区中不同学习者之间的讨论协商逐步达成原则性共识,并进一步收敛为范围界定清晰、意义指向明确的公共知识,进而沉淀为知识社区中知识本体的某个知识概念或知识概念之间的某个关系,最终以节点或连接的形式纳入社区的整体知识网络之中。对于暂时无法达成原则性共识的知识,将作为情境知识纳入社区的整体知识网络之中。这些情境知识可能被证实进而演化为公共知识,抑或被证伪进而从整体知识网络中淘汰,也可能长时间维持个性情境知识的状态。同时,对于知识网络中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连接强度,则通过对学习者参与的相互讨论协商、投票表决等行为的社会性计算获得,社区成员之间对知识的认可程度一致性越高,连接强度越强。
具体说来,知识网络的构建主要涉及知识接受、知识内化和知识贡献三个层次。其中,知识接受指学习者为开展学习而与知识关联的学习资源产生的互动操作,如学习资源的编辑、批注和评论等;知识内化指学习者为了获得对具有强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问题的深层次理解而投入认知努力并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是一种与学习者内在原有认知结构产生冲突并演化更新的过程;知识贡献是知识创生的过程,是通过集体讨论协商、决策共享等形式与其他学习者之间建立连接并达成一致性共识进而创造出新知识、建立或更新知识连接,并将所构造的新知识接入知识社区整体知识网络的过程。知识网络的构建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和支持,一方面,社会网络为知识贡献提供了高质量的社会化交互支持,能够迅速聚合与当前知识紧密关联的权威知识专家,获取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加快一致性共识达成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为知识网络中知识连接的建立和更新提供了推理支持,利用社会网络中大规模学习者对不同知识的掌握水平差异挖掘生成知识之间新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知识连接,促进知识网络通达性的提升。
知识网络展示了知识社区中知识的存量和增量,刻画了学习者构建的情境知识逐渐外显化为公共知识、知识之间由凌乱无序向自治有序发展的过程,体现了知识的分布式构建和进化发展的理念,其知识要素兼具了现代知识观的客观性与后现代知识观的境域性。同时,知识网络也使得对学习的理解从只关心学习者的知识生产贡献转变为同时关注知识生产和知识之间逻辑连接两方面贡献。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
社会网络是对知识社区中不同类型学习者及其之间连接的结构化组织。知识社区中的学习者不仅借助物化知识学习,围绕某个知识形成的学习者关系网络也可成为学习的社会性知识[17],而社会网络正是对这种社会性知识的结构化表示。社会网络围绕某个相同或相似主题知识,将具有共同学习需求、兴趣或爱好的学习者组织在一起形成学习者共同体网络。
具体说来,社会网络的构建主要涉及交互连接、认知连接和社会连接三个阶段。其中,交互连接指学习者为了学习与所处外部环境发生交互,建立与学习资源的连接的过程;认知连接指基于知识社区中学习资源与知识之间的语义关联,经过社会认知计算,将交互连接转化为学习者对知识的认知层次,从而建立学习者与知识之间不同层次连接的过程;社会连接是指学习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性活动建立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基于知识交互的服务连接,并将参与知识建构活动的新的学习者节点及其建立或更新连接纳入知识社区整体社会网络的过程。其中,作为建立社会连接的关键要素——学习者,只有在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意愿与行为后,才能成为社会网络中具有知识属性的节点。同时,社会网络的构建受到知识网络的影响和支持,一方面,知识网络为社会网络中认知连接的建立提供了高度可信有效的知识关系网络,保障了認知连接建立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知识网络为社会网络中社会连接的建立及更新提供了基于知识逻辑推理的规则支持,利用知识社区中大规模学习者与知识网络中某个知识节点建立认知连接的差异挖掘产生学习者之间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为其建立新的社会连接,促进社会网络通达性的提升。
社会网络展示了知识社区中参与知识贡献学习者的存量和增量,描绘了承载知识的管道网络中节点和关系的创建、重构过程,是对知识建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互动、共享、联通等知识社会性特质的通俗化表达。学习者个体作为社会网络中的独立节点,既是分布式的知识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形态的社会性知识,代表了对某个主题知识的不同观点或诠释视角,具有动态性、可扩展性和社会性等特点。社会网络致力于建立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连接,通过连接汇聚源自不同个体的观点、创意和智慧,促进个体内部认知网络与外部知识网络之间的联结,让学习从单一化的个体认知走向集体互联的分布式认知。
(三)社会知识网络的进化与情境适应
社会知识网络是对知识社区中物化资源—知识与社会性资源—学习者之间智能联通融合网络的结构化组织,是促进知识建构广度和深度双向提升的关键所在。社会知识网络表征了参与知识建构活动的学习者主体与知识客体两类核心要素,并对知识客体做了公共知识和情境知识的划分,展示了学习者主体与知识客体之间所建立的知识连接、社会连接和认知连接。知识社区中每个生成的知识、每个参与知识建构的学习者都是社会知识网络空间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可以与其他节点建立直接或间接连接,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弱由连接两端的节点共同决定。其中,知识连接旨在促进个性物化知识表达,具体表现为相关、前驱、从属、等价、继承等类型的知识关系;社会连接旨在促进群体社会性知识表达,具体表现为同伴、师生、协作等类型的人际关系;认知连接旨在促进人与知识的双向联通,具体表现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类型的认知关系。
在社会知识网络中,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两者之间是双螺旋连接的,网络之间是相互交织的,能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伴随知识建构的不断深入,网络中的节点数量、节点状态和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弱将动态更新,并逐步进化发展形成一系列面向不同学习情境的社会知识网络版本。社会知识网络融合了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展现的是物化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联通,网络内部节点越多、连通程度越高,将产生社会群体智能[19]。同时,作为知识与知识服务载体的社会知识网络,不再是静态固化、千人一面的,而是基于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中的情境属性进行适应性呈现。面对同一知识社区中构建的社会知识网络,处在不同学习情境下的学习者个体将获得符合其当前学习情境的知识网络资源和当前学习情境下可通达、可联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升知识、资源和服务的适切性。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学习充分体现了连接学习的特点,与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学习是一个网络节点联结过程的理念不谋而合,展示出互联网时代的学习就是连通社会知识网络中的物化资源和社会性资源的过程。
以社会知识网络为载体,知识建构从“知识”或“人”的单向网络走向“人”与“知识”互相融合的双向网络,即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两者互联互通、内嵌循环,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建构形态——连接式建构,其核心就是社会知识网络的建构与进化。连接式建构关注所建构知识的进化发展过程、所构建知识的情境属性、所构建知识与构建者之间以及不同构建者之间所建立的动态社会交互以及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旨在通过创造生产、结构组织、变更淘汰等形式建构并发展社会知识网络,动态建立人与知识之间的有意义连接,实现人与知识之间的无缝融通,保障学习需求与知识服务连接的持续适应匹配,最终产生社会群体智能。基于知识网络,学习者不仅能获得个体参与建构贡献的知识,还能清晰了解知识的进化发展脉络,并获得与个体学习情境相符的知识服务。基于社会网络,学习者不但能知晓个体与知识、个体与其他学习者的连接状态,而且能够利用个体与知识的连接找到知识背后的权威专家,并透过网络获得持续更新的社会性人际资源。
四、基于学习元知识社区的连接式知识建构
基于上述模型,笔者团队研发了连接式知识建构的支撑环境——学习元知识社区。学习元知识社区中,学习者通过与学习元进行学习交互实现社区知识的建构、分享和创造,随着学习交互的深入,学习者个体的知识逐渐外化为社区的公共知识,学习者个体之间碎片零散、无序开放的知识也逐渐演化为具有群体共识的知识网络[18]。同时,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知识之间会逐渐形成一个交往频繁的社会认知网络,每个学习者和知识都是该网络空间的一个节点,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知识之间可以建立学习连接,知识节点的学习状态、学习者与学习者和学习者与知识节点之间的连接状态将随着知识建构过程的开展而不断更新[19]。
为了检验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的可行性,笔者团队利用学习元知识社区,在“教育技术新发展”课程中开展了长达六年的探索[20]。课程实施过程中,以连接式知识建构为设计理念,通过师生间协同参与阅读、协同设计和学习微课程、协同完成学习活动等知识建构任务,建立起学术著作内容知识之间、学术著作内容知识与参与课程学习的师生之间、参与课程学习的师生之间的意义连接,生成基于知识内部逻辑和知识认知水平的社会知识网络。
(一)可进化的课程知识图谱,促进课程背后所关联知识之间的知识连接
知识图谱是某个学科领域的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常用于形式化表征该领域的知识及其结构。知识图谱作为学习内容背后的知识框架,是建立學习内容与学科知识之间关联的重要纽带,也是保障学习内容进化质量的关键。在课程实施之前,由课程教师创立课程的知识图谱骨架。随后,允许课程学习者在学习期间协同参与课程知识图谱的补全和关系更新,即学习者可以对课程单元主题内容进行知识或关联的贡献。经过多轮群体讨论协商并获得大多数学习者认同的知识或知识关系贡献,将融合汇聚为群体共识,并纳入课程知识图谱中,如图 5所示。课程知识图谱一方面展示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个体认知发展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展示了学习者群体在同一知识上进行情境化、社会化协商和意义建构的过程。
图5 支持群体知识进化的课程知识图谱
(二)表征知识结构和认知状态的学习认知地图,促进人与知识的认知连接
学习认知地图具有表征学习者知识结构和认知状态,向学习者提供适应性学习资源、学习路径和人际网络等功能[21]。学习元知识社区中,学习认知地图是通过在课程知识图谱上叠加学习者的全学习过程信息构建的,其中,节点的颜色代表学习者的认知状态水平,节点之间的连接状态代表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基于课程构建中产生的创建微课、设计微课活动、参与微课活动、协同编辑微课内容及活动、批注和评论微课内容等过程性数据,参照微课学习评价方案,学习元知识社区将完成每位学习者对课程知识的认知状态及其结构水平的计算评估和可视化表征,生成学习认知地图。围绕学习认知地图中某个主题知识,通过计算不同学习者之间的学习认知地图相似度,学习者可以查找在该主题知识上与自己学习步调相当的同伴,并建立获得知识的通道,从而拓宽知识获取范围并提升知识认知深度。如图 6所示,越靠近中心的学习同伴表明其与当前学习者在课程知识“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的学习步调越一致,通过查看学习认知地图、加为好友、进入空间等方式建立联系,加深与知识之间的认知连接。
图6 基于学习认知地图拓展人与知识的认知连接
(三)基于情境感知的适应性服务,促进社会知识网络中人与人的社会连接
情境感知适应服务主要感知学习者的学习情境和学习需求,为学习者聚合适应性的学习支持服务,从而构建起服务与人之间的动态连接。在此过程中,学习者与学习元知识社区进行交互时,嵌入学习元知识社区的情境感知适应模块将利用传感器对学习者的信息进行检测和分析处理,根据聚合模型推荐基于社会知识网络的学习支持服务要素,如学习活动、学习工具、内容资源等。利用协同构建的微课程以及学习者与微课程交互生成的过程数据,计算推理微课程知识之间的关联强度、学习者对微课程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深度,建立微课程知识、学习者之间的两两连接,生成面向课程社群的社会知识网络。社会知识网络是课程所有师生共同参与知识构建的结果,是当下与课程相关的所有知识、学习者和学习资源等学习支持服务的集合,每位学习者所获得的只是社会知识网络中适合其当前学习情境和学习需求的部分学习支持服务要素,通过这些服务要素促进学习者与服务要素背后提供者之间的社会连接。
五、结 语
学习是通过社会对话实现认知网络连接与共享的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利用物化资源以及社会性的学习交互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本研究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时代下知识所具有的新特征,在总结知识建构相关模型的基础上,以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为核心,设计了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并以学习元知识社区为依托开展了实践探索,为新形势下知识建构的研究探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SAWYER R K.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M].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SCARDAMALIA M, BEREITER C. A brief history of knowledge building[J]. Canadian journal of learning & technology,2010,36(1):1-16.
[3] BROWN A L, CAMPIONE J C. Communities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or a context by any other name[J]. Contributions to human development, 1990, 21:108-126.
[4] LIPMAN M. Philosophy goes to school[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SCARDAMALIA M, BEREITER C. Computer support for knowledge-building communities[J].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 1994, 3(3):265-283.
[6] GUNAWARDENA C N, LOWE C M A, ANDERSON T.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a global online deb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1997, 17(4):397-431.
[7] BROWN A, CAMPIONE J. Guided discovery in a community of learners[M]// MCGILLY K. Classroom Lessons: Integrating Cognitive Theory and Classroom Practi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229-270.
[8] STAHL G. A Model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Building[C]//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Mahwah, NJ: Erlbaum, 2000:70-77.
[9] SCARDAMALIA M, BEREITER C. Knowledge Building[M]// GUTHRIE J W.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2003.
[10] SCARDAMALIA M. Collective cognitiv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M]// SMITH B. Liberal education in a knowledge society.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67-98.
[11] CHEN B D, HONG H Y. Schools as knowledge-building organizations: thirty years of design research[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16, 51(2):266-288.
[12] 石中英,尚志遠.后现代知识状况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J].教育探索,1999(2):3-5.
[13] 潘新民,张薇薇.必须走出后现代知识观——试论科学知识教育的作用与价值[J].教育学报,2006(4):18-21,96.
[14] ANDERSON T, DRON J. Three generations of distance education pedagogy[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2011, 12(3):80-97.
[15] SIEMENS G. Connectivism: learning as network-creation[EB/OL]. [2020-09-07]. http://masters.donntu.org/2010/fknt/lozovoi/library/article4.htm.
[16] SIEMENS G. Connectivism: 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learning, 2005, 2(1): 3-10.
[17] 余胜泉,陈敏.泛在学习资源建设的特征与趋势——以学习元资源模型为例[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1(6):14-22.
[18] 余胜泉,段金菊,崔京菁.基于学习元的双螺旋深度学习模型[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7(6):37-47,56.
[19] 余胜泉,陈敏.基于学习元平台的微课设计[J].开放教育研究,2014(1):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