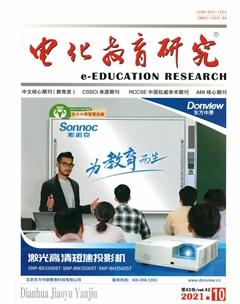命题符号理论中知识表征思想的发生学追问
付文星 刘月 李艺
[摘 要] 命题符号理论以命题作为知识表征的基本单位,但对命题之“从何而来、如何而来”尚未厘清。研究聚焦构成命题的奠基元素,基于知识发生的视角看知识表征,对既有理论的表征机理展开发生学追问;通过回溯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知识何以可能”问题的思想成就,尝试自先验条件开始把握命题的发生发展机理,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对既有命题表征问题给出新的诠释;进一步阐述对于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等部门科学以及知识表征工作的启发和建议。
[关键词] 命题符号理论; 知识表征; 发生学; 发生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付文星(1997—),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E-mail:870889303@qq.com。
一、引 言
知识表征作为若干部门科学中的重要问题,自兴起至今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所谓知识表征,顾名思义,是关于知识如何表示的研究,认知心理学家把信息在人脑中呈现和记载的方式统称为知识的表征[1]。较为经典的表征理论是命题符号理论,该理论属于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的代表性理论,其思想内核是:认知的构成单位是命题,然后基于命题形成命题网络,随着对命题的不同操作或操作次数的增加,命题网络不断更新,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能力也会增强[2]。命题符号理论下的知识表征问题,又以认知心理学基于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分类思想开展的工作为代表,本文亦是以此为例对命题符号的表征机理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进一步追问。
认知心理学直接将命题作为知识表征的基本单位,对命题“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的问题并无深入思考,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命题总是由概念等元素组成的,若命题作为知识表征的基本单位,“概念”与“命题”是何关系?也即我们是如何从“概念”得到“命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组成命题的最初元素那里开始追问,即将问题概括到被认知心理学作为最小知识表征单位的命题是“从何而来”并“如何而来”上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发生学视角,所秉持的态度是从知识的发生看知识表征,由此或许能够更好地逼近问题的真相。
问题发生在认知心理学,但在既有认知心理学研究成就内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本文尝试向上游的哲学思考进行追溯以寻求可能的答案。“知识何以可能”是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话题,其专注于对知识发生过程的考量;且哲学认识论发展源远流长,从朴素的认识论思想的提出到最终明确以先验主体性问题为其基本旨归,对认识发生问题的考察已经比较成熟。由此,本文沿着认识论的发展脉络探寻有关命题及其发生机理的思想成就,在完善理论的同时,也希望借此为指向实用的知识表征技术的发展提供指导。
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命题表征思想及其
背后的逻辑危机
(一)命题表征思想简述
认知心理学将广义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称前者指向描述外部世界“是什么”的静态知识,后者指向“怎么做”的动态知识。陈述性知识的表征方式包括命题、命题网络和图式,其中,命题被视为知识表征的基本单位,认为只有命题才使得判断的真伪有了意义[3]。此外,学界对命题的结构与构成也有些思考:一个命题由一种关系和一组论题构成,关系一般通过动词、副词和形容词表达,有时也用其他关联词如介词表达;论题一般指概念,由名词和代词表达[3-4]。例如,“蚂蚁吃了果酱”这个句子中的论题是“蚂蚁”和“果酱”,关系为“吃”。但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以上解释对命题“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的发生过程的探讨远远不够。
再来看程序性知识。认知心理学认为,“怎么做”包括动作序列和语言规则两种类型:动作序列即主体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一系列运算或操作以达成初始意图;语言规则又称语法规则,即组织概念进行语言表达的规则[3]。程序性知识主要通过产生式规则和产生式系统进行表征,产生式由触发条件和相应“动作”组成,触发条件是由“如果”开头的一套短句,“动作”是由“那么”开头的一套短句。若干个产生式规则层层嵌套、相互关联形成产生式系统,则可以支撑主体完成综合性和复杂性更高的活动。以上分析可见,产生式实质仍是基于命题发展而来的扩展形式,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由此也说明认知心理学界关于知识表征的基本态度为命题是思考表征问题的基点,是表征知识的基本单位。基于以上思路,安德森(John Robert Anderson)等人构建的ACT-R模型模拟了人脑的部分信息加工过程[5],积极之处是与实践经验的贴合以及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为此类知识划分及其表征机理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支持,但不足之处是依然深陷缺乏发生学思考的困境之中。
(二)“发生”缺失导致的逻辑困顿
仔细分析,其发生机理缺失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更多的危机。首先,于命题表征理论而言,命题即是知识,以“命题”表征知识,即以“知识”表征知识,实际上陷入了自我循环。其次,看似将论题从整个命题中剥离出来、剩余成分一并归为“关系”的做法并无不妥,实则却坠入逻辑混乱的困局。例如,“关系”的构成中动词、副词聚焦于“怎么做”,强调“过程性”,而形容词则侧重表达“是什么”,趋向“状态性”,贸然将其一并归为组织联结概念的“关系”,说理依据不清。再次,仅就陈述性知识的表征而言,作为基本单位的命题在形成中就涉及了规则的成分,或者说命题所表征的不仅仅是陈述性知识,其中还混杂着程序性知识。仍以“蚂蚁吃了果酱”为例,其中“吃”即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3]。
进一步看,命题并不简单等于句子,而是指一个判断句的语义[3],一个命题可以转换成多种句子形式进行表达,学界强调知识表征所针对的是命题而非句子。这种认识于既有表征思想体系中看来并无不妥,但当我们针对此处知识表征思想进行发生学追问时,便可发现其粗疏之处。立于发生的视角,知识发生当下所形成的必定是具体的句子,是真情实境下认知主体所形成的即时即刻的认识。例如,“蚂蚁吃了果酱”这个判断句即是当下情境真实的认识“发生”,而对若干种针对相同事实的不同发生形式的综合性概括(剥离情境、形容和修饰手法等抽取出句子最内核的意义)才是命题。即如“蚂蚁吃了果酱”和“果酱被蚂蚁吃了”通常被视为具有相同的语义,也因此被归类为同一命题。至此我们发现,认知心理学从“命题”开始谈知识表征,实际上是借“命题”将知识表征与知识发生隔绝开来,人为地在自己可能通向真相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障碍。当然不可否认,于认知心理学等部门科学而言,解决问题是其终极追求,对于知识表征的研究似乎是先预设了某种“知识图景”的存在,而后寻找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對其进行复现,这种思路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不能接受的是,其发生信念的迷失加之“问题主义”的驱使,既有的表征思路就如此“实用主义”地直接指向了认识发生的结果,即将命题作为基本单位,也就因此错过了窥探其发生机理的机会。
哲学认识论层面对于“知识何以可能”问题的思考强调认识发生的当下,致力于从先验条件开始把握知识发生的内在机理,尤其康德后续的继承者——皮亚杰和胡塞尔更是将发生学思想贯彻其认识论思考的始终。对其思想内核进行追溯和梳理,理应能够帮助廓清命题之“从何而来”及“如何而来”的问题,并启发发生学视角下知识表征的相关思考。
三、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发生
自笛卡尔将“我”确立为认识论基点后,康德便聚焦知识得以形成的先验条件,提出先验范畴思想[6],主张主体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所获得的感觉经验为“杂多”,须经由先验知性范畴的综合才成为知识。所谓“范畴”,在康德而言为概念范畴,也即空概念,范畴作为知性认识形式,为人类所共有,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才得以可能[7]。康德的认识论成就毋庸置疑,但其思想本身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性,譬如作为认识形式的先验范畴的“先验性”便引起了后人的质疑,皮亚杰便是其中之一。
(一)皮亚杰“两个范畴说”中的知识发生
1. 康德的忠实追随者——皮亚杰
谈及皮亚杰,第一印象是作为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者,蜚声心理学界,由此也以心理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殊不知在这一光芒背后还是一位被世人所忽视的极具情怀的哲学家。皮亚杰十分欣赏康德的先验范畴思想,但他对于康德所言先验范畴之绝对先验也即先天提出异议,他认为,这种存在于人头脑中的认识形式只能是逻辑上先验,即“先于经验”而并非先天,范畴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发生发展而来的。如此,皮亚杰在引入发生学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了康德思想中逻辑在先的成分,并基于此展开了关于范畴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8]。
2. “两个范畴说”的发生学内涵解读
在皮亚杰的理论体系中,活动论被誉为“理论之根”,若想要揭开范畴理论之谜以窥探知识发生机理,这必定是第一把钥匙。皮亚杰通过观察发现,“活动”(动作)是儿童认识世界的开端[9],一切认识都发源于动作,进而指出,“从感知运动水平往后发展,主客体与日俱增的分化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主体的活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的协调”[9]。前者最终被归为“逻辑数学范畴”,后者被归为“物理范畴”[10]。物理范畴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性范畴”[11],为主体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所获得的感觉经验提供内容或者状态意义上的规定性,逻辑数学范畴起源于主体的运算,经由主体内部协调反省抽象而成,为认识发生提供过程规则意义上的规定性。简单来说,认识的发生是两个范畴相互作用共同“运动”的结果,是一个内外部双向建构的过程,其中,逻辑数学范畴以物理范畴为基础,物理范畴又从属于逻辑数学范畴,逻辑数学范畴始终支配和制约着物理范畴,二者相伴而生、共同发生发展,并以此推动知识的发生发展[12]。“两个范畴说”是皮亚杰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康德先验范畴思想的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厘清知识发生机理。需要说明,皮亚杰的范畴思想继承自康德,故其所言物理范畴必然包含着概念范畴的部分,主要作用在于将感觉经验概念化,为简化讨论,本文对于物理范畴中概念范畴之外的成分暂不予关注。本文中,我们将物理范畴对应概念,将逻辑数学范畴对应规则(如语法规则),便可以尝试揭开命题“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的谜底:在发生的意义上,概念和规则作为知识发生的先在(先验)条件,前者为知识发生提供状态层面的规定性,后者为知识发生提供过程规则层面的规定性,二者的共同“运动”最终使知识(实则为句子、判断)得以发生。
仅以皮亚杰的思想对知识发生机理进行单方面解读或可能被指责为自说自话,较为周全的方法是继续追溯认识论的发展轨迹,为既有关于知识发生的思想内核寻求逻辑旁证,以增强结论的信服力。
(二)胡塞尔思想体系中的知识发生
同为康德认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胡塞尔和皮亚杰分别致力于不同的方向,皮亚杰仅聚焦于康德范畴思想的研究和发展,而胡塞尔则是开辟了一条追求“知识何以发生”真理的崭新逻辑进路——现象学,基于此也初步完成了先验认识论哲学及相应知识学框架的系统搭建。为更好地厘清胡塞尔对于“知识何以可能”问题的思考,我们通过聚焦两个问题进行梳理:其一,胡塞尔的认识论思想是如何体现“发生”的;其二,胡塞尔认为知识(判断)是诉诸什么方式得以实现的,或者说知识发生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1. “时间流”中的发生
首先,胡塞尔对于认识论研究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即是引入了时间性分析,认为范畴形式的运作必须建立在时间之上。“如果我围着一棵橡树转,想去获得对它的更彻底的表象,那么橡树的各个侧面并不作为分离的碎片而呈现自身,而是作为综合地整体化的环节被感知。这个综合化的过程在其本性上就是时间性的。”[13]胡塞尔将其视为“构成任何对象的形式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皮亚杰通过两个范畴的相互作用、协调运作体现其思想的“发生性”,胡塞尔则是通过时间性分析的引入凸显了其认识论思想中的发生。其次,胡塞尔就现象说现象,认为现象是实事显现自身的方式,我们可以直接知觉到现象,也就可以直接在过程中与本质“相遇”。那么现象学认为我们是诉诸什么方式把握本质的呢?胡塞尔聚焦到了“直观”,最终,在时间流中借由直观完成了对知识发生机理的洞察。
2. 直观思想的内涵解读及其内在机理分析
胡塞尔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将直观概念纳入系统的“意向性”思考之中,认为“直观”是一种“需要得到充实的意向”,并且原则上也具有“达到真正的充实成就的能力”[14]。意向性是贯穿現象学始终的重要概念,也是我们打开直观谜题的一把钥匙。意向性首先指意识的对象——指向性,现象学认为,我们的意识总是朝向某物的意识[13],例如,我看到一张纸,思念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热爱所爱的,害怕所害怕的,无论意识活动的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我们拥有的每一个意识经验都是意向性的,这种意向是心灵所认知的意向,由此,认识所得,也即意向对象,就是意识本身的意义构造。那么,知识是如何发生的呢?胡塞尔认为,“当对象正如我所意向的那样被直观的给予,我的信念得到辩护,并且是真的,于是我就拥有了知识”[13],也就是说,知识的适当位置在直观那里。进一步追问,胡塞尔是如何诉诸直观解释判断发生的?实际上,他扬弃了康德直观概念的局限性,在丰富“直观”内涵的基础上明确了一种更为本源的直观方式——本质直观。本质直观所强调的是认识发生的当下对对象本质特征的洞见,这是一种绝然的明察,正如倪梁康所言,“所谓的明察是一个判断意识,在这个意识中有一个事态作为一个本质普遍性的特殊化而被意识到,而这个判断本身涉及普遍之物的绝然性”[14]。在胡塞尔眼中,“范畴直观所‘感知的即是那些根据范畴含义因素而在综合性的行为进行中构造出自身的‘事态”[14],也就是说,范畴直观作为奠基条件,支持并统一于本质直观。本质直观的最终结果以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13],例如,“这是一个玻璃的杯子”,即是一次判断,一次本质直观。
于胡塞尔而言,直观建立于时间之上,时间性的“综合化”过程是知识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且仅在时间的延展中才能对知识的本质予以更好的把握。作为先验认识论的共同推进者,除了对发生思想的坚持,皮亚杰和胡塞尔两人对于知识发生内在机理的认识也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胡塞尔所言本质直观,其过程的展开需要逻辑规则和概念的共同参与。例如,在形成“这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的判断时,主体不仅需要认识“梧桐树”,还需要具有将“一棵”“高大”与“梧桐树”联系起来作出判断的意识,具有这种意识的前提就是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相关的运演规则。这种运演规则与概念有所不同,其是规定认识发生即本质洞察过程的东西,把控着概念的关联和运转。若将概念视为形成判断所需的一种奠基元素,那么,逻辑规则就是另外一种奠基性成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确认皮亚杰“两个范畴说”的思想内核及其关系理路。
至此,我们基于对康德、皮亚杰和胡塞尔关于“知识何以可能”问题的思想要义梳理,形成了关于知识发生机理的较为清晰的认识,为后续基于发生学视角重识命题表征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发生学视角带来的启发与思考
(一)命题与命题表征思想重识
通过对认识论发展轨迹中关键人物的思想进行梳理,我们认识到:知识是主体内部先验的认识形式包括物理范畴和逻辑数学范畴对外部杂多经验进行统整的结果。也认识到,文章之初所言“命题”之“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的提问应该调整为“(判断)句子”是“从何而来、如何而来”。认知心理学既有的静止固定的命题表征方式致使知识表征理论的发展陷入困境,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基于发生学视角,我们所窥探到的则是一幅自先验条件开始逐渐成长起来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动态性知识图景,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句子或知识的发生历程。以此为背景重新考量命题表征问题,可以对既有的表征思想形成新的认识。
若是尝试将哲学认识论的认识成就与认知心理学既有思考相连结,完整的命题表征思想应该顺序解释为:概念和规则作为知识发生所必需的奠基元素逻辑在先,二者相互作用、共同运动促使句子(判断)发生;一次(句子)判断即是一次知识的发生,命题则是指向同一事件的若干种(句子的)可能形式发生的概括性归类;命题相互联结形成命题网络,命题网络可视为不同类型判断的结构性关联。如此,将哲学认识论之知识发生思想与认知心理学既有的知识表征思想连结起来并适当予以修正,得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系。需要修正的细节如前所述,概念和规则的内涵并不简单等同于学界既有的“论题和关系”,依据皮亚杰“两个范畴说”,趋向状态表达的成分应被归为概念一类,侧重过程运演的成分应被归为规则一类,如此,便可以对两类奠基条件的构成予以更具学理性的划分。例如,动词、副词、介词等规定运演过程的理应属于规则一类,而名词、代词、形容词等强调状态的则应属于概念一类。
(二)之于知识表征工作的启发
基于已有的理论积淀,我们对知识的发生机理形成了较为透彻的认识,由此启发了发生学视角下关于知识表征工作的相关思考。句子形成的先验条件包括概念和规则两种形式,在发生的意义上,此处所言概念和规则形式都不是“知识”,而是知识发生所必需的奠基元素,于发生学视域下的知识表征而言,需要构建两大表征体系——概念体系和规则体系,通过两大体系相互作用组合生成判断还原知识发生过程。这种知识表征思路一方面可以脱离“以知识表征知识”的逻辑困境;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知识发生的内在机制,并赋予知识表征以更为丰富的内涵。
具体的表征设计大致如下:概念体系可以用表征概念的节点和表征概念间关联关系的边来表示,若干个概念相互联结组成概念网络,概念网络之上形成类,基于类继续抽象形成领域,层层延伸,不断扩展。伴随着主体的学习活动,网络结构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包括节点和边的增加、边的调整和巩固[15]。规则体系用于把控概念的运转,是一系列逻辑规则的集合,关于规则形式的发生发展以及不同规则间的关联关系在皮亚杰的“可闭合结构”思想[16]中还有更为细致的解释。规则体系可以设想为一棵逻辑规则树(非线性数据结构),树上的每个节点都是一个完整的规则结构。两大表征体系本身作为知识发生的先验条件,概念与规则一并运行形成判断,即为知识的发生,如此,句子“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的问题便可以得到回答。
(三)之于部门科学发展的启发
于认知心理学而言,发生学思想指导下的知识表征理路丰富了既有的命题表征理论,为“命题”之于表征赋予了新的意义;于语言学而言,认识论视角下知识发生发展机制的厘清有助于我们从发生的视角观察语言的成长历程,深化对语义和语法在范畴意义上的认识;于教育学而言,对知识发生过程性的考量也势必会为我们带来关于“知识”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启发教育相关问题的思考。顺便反观当下人工智能领域颇为流行的知识图谱,已有的图谱普遍以表征“概念以及概念间关系”为核心,其表征方式虽与认知心理学关于命题符号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也是一种类似命题的知识表示思路,例如,一般见到关于“国家知识”的图谱中,某国家和其人口数之间的联结实则是由運演规则实现的,即一个命题关系。也就是说,此类表征方式也依旧存在文章伊始所提及的类似命题表征理论的局限和不足。作为特例,Google提出,知识图谱的初衷是为了优化搜索引擎的返回结果,增强检索的准确性,现有的表征技术的确能够满足原始需求,所以其表征方式的学理性并没有得到相应说明。如若按照发生学思想指导下所得到的表征思路,构建两个作为先验条件的表征体系,由两个体系各自提供元素组合生成检索结果,一方面更符合知识发生机理,另一方面由于表征思路的变化以及表征内涵的丰富,必定会为推动相关应用技术的发展带来契机。
五、结 语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必须严格遵守“向真”[17]的逻辑准则,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本文组织和展开的逻辑主轴是演绎,在明确学界既有理论局限以及问题趋向之后,诉诸哲学认识论的思想成就,主要以皮亚杰“两个范畴说”为主,以胡塞尔“本质直观”思想为辅,梳理知识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以此作为“演绎”的理论前提,重识学界既有的命题表征思想,进一步揭示其对部门科学发展以及知识表征工作推进的启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思想对于指导知识表征相关研究而言显现出巨大的潜力,仅以本文作为开端,其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更多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1] 皮连生.一种关于知识的新观点[J].湖南教育,1995(1):14-15.
[2] 王瑞明,莫雷,李莹.知识表征的新观点——知觉符号理论[J].心理科学,2005(3):738-740.
[3] J·R·安德森.现代认知心理学[M].杨清,张述祖,等译.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30-286.
[4] 皮連生.教育心理学[M].3版.李伯黍,燕国材,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9.
[5] 唐广智,胡裕靖,周新民,高阳.ACT-R认知体系结构的理论与应用[J].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14,8(10):1206-1215.
[6] 冒从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范畴学说述评[J].天津师院学报,1979(2):10-18.
[7] 康德.康德哲学原著选读[M].华特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8] 白倩,冯友梅,沈书生,李艺.重识与重估:皮亚杰发生建构论及其视野中的学习理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3):106-116.
[9]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26.
[10] 熊哲宏.皮亚杰理论与康德先天范畴体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
[11] 熊哲宏.皮亚杰理论与康德先天范畴体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2:65.
[12] 冯友梅,李艺.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批判[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2):63-72.
[13] 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M].李忠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2,11,28,33.
[14]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0,48,44.
[15] 景玉慧,沈书生,李艺.认识论语境下的知识模型讨论[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1):37-44.
[16] 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7] 李艺.谈一篇论文意义上理论研究的逻辑之“真”——兼及“论证”与“议论”的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31(4):2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