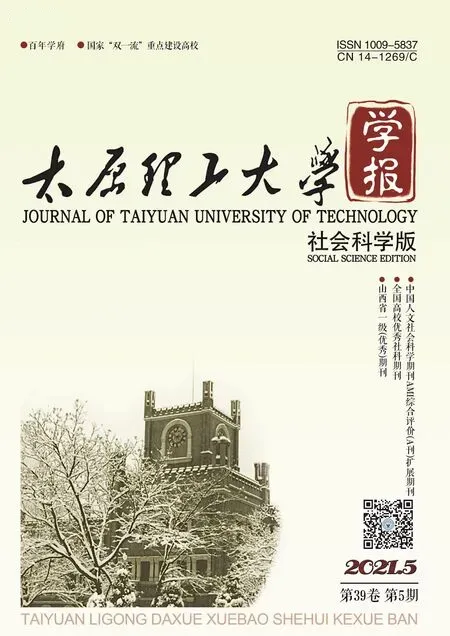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回顾与前瞻
卢厚杰,陈蓉婧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长期以来,地权分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研究的焦点课题。近年来,海内外学者聚焦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问题,收集、整理和出版一系列的近现代山西地区的乡村社会资料,并在运用传统史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基础上,以量化史学为目标,向以基尼系数为分析工具的数理方法进行转变。目前,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硕果累累。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近现代山西的地权分配状况的认识,尤其是土改前地权分配是趋于分散抑或趋于集中,尚未取得一致性意见。这一研究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同学者的研究史料掌握和研究方法运用。为进一步推动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的深化拓展,本文对已有成果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详尽回顾了山西地权分配的研究内容和学术进程,进而归纳影响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演变的历史因素,最后从研究史料的收集使用及研究方法的取舍选择等角度就今后的山西地权分配研究提出了展望。受限于作者的研究积累和学术水平,评述过程中难免存在挂一漏万、不尽准确等问题,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一、土改前山西地权分配的研究
土地改革之前,近代中国乡村地区的土地占有并未受到外在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更多是长期土地交易流转的结果,也代表了近代中国乡村地权分配的“初始状态”。自二十世纪初期,政府、学术团队等均致力深化对当时的地权分配的认识。但是,不同的调查资料、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不同的研究方法等因素,让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过程中共识的达成变得并不容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取得突破和进步,学界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达成共识性认识,即土改之前山西的地权分配相对分散。
(一)二十世纪初土改前山西地权分配研究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发展过程中,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地区,无疑成为近代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诸多问题,引起近代中国政府和社科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近代中国乡村农业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一种生产要素,土地占有状况和利用方式自然是近代农村问题的根本症结之一。针对于此,官方和学者在全国许多地区展开规模不一的土地调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探讨近代山西地权分配状况。
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第五次农商统计表中,详细记录了1914—1916年山西地区的农户数量及田地面积等社会经济信息[1],是考察近代山西土地问题较早的珍贵资料。遗憾的是,此次调查的关注面较为广泛,在调查过程中仅对山西地区的土地利用进行统计,并未对山西的地权分配做出具体描述。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对包括山西在内的全国十七省八百多个县的土地所有状况展开调查。赵冈根据调查资料,量化计算得出山西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与全国地权分配基尼系数0.38相差较小[2]。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又对包括山西省在内的十六省一百六十三县展开为期一年的地权分配研究调查,并于1937年将所调查资料整理出版。在此次调查中,山西被调查人员为6 415户,占有土地244 121.10亩,旱地占比84.9%。统计显示,山西农民每户平均所占土地为34.52亩,平均每人所占土地为7.45亩,此两项指标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该调查认为山西“除部分地方外,尚无十分严重的地权集中问题”[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乡村的中国共产党,着力对农村地区的地权占有问题进行考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共在山西地区的土地调查主要是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走访陕西北部的神府、绥德和晋绥边区的兴县等地,展开为期一年两个月的农村实地考察。调查团对晋西北地区的兴县十四个村的人口数量、劳力占比、役畜分配和土地占有等展开较为详细的调查,认为晋西北地区的乡村土地占有状况由集中趋于分散,“这属于进步的发展”[4]。
国外学者也对山西近代农村土地问题给予关注。1924年,日本学者长野郎对中国农村地权分配进行研究,认为华北农村耕地分配不平均,且小农过多[5]。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学者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描述了民国时期山西土地利用的详细状况,诸如土地耕种、荒地、灌溉等情况[6]。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韩丁参与晋东南潞城县张庄的土地改革,在其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指出,张庄人民在土改前曾受地主、天主教教会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抗战后作为受剥削最严重的贫、雇农阶层,其超过总人口数50.0%的人口只拥有不到25.0%的土地及5.0%的牲口,在新中国成立前55.0%的贫农占有土地24.8%,而4.8%的地主、富农及教会占有土地29.9%[7]。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研究指出,太行山区在抗战前土地集中程度较低,地主与中农较少。1937—1945年,太行农村土地分配中占支配地位的由地主、富农转向中农。抗战结束时,2/3的中农拥有2/3的土地,1/4的贫农拥有约1/7的土地[8],地权分配趋于平均。
(二)改革开放以来土改前山西地权分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珀金斯、马若孟、赵冈、章有义、郭德宏、史志宏、李伯雍、秦晖等人,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展开研究。其中,赵冈[2]和秦晖[9]的基尼系数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此后山西地权分配研究者开始注重基尼系数这一指标的运用。与此同时,研究近现代山西某一地区或村庄的地权分配成为一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
基尼系数计算过程中的技术方法运用,让不同学者对近代山西地权分配产生不同认识。首先,胡英泽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三十四个县(村)农户土地调查资料指出,民国山西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56,土地占用程度较为集中。他又对山西不同地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直观地看出山西南北自然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差异[10]。赵牟云对胡英泽的研究结论和计算方法持有异议,他对晋西北、晋中和晋南地区的多个乡村分别计算户均与人均基尼系数,认为土改前山西农村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为0.34,地权分配在总体上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土地比较分散地分配在各个阶层[11]。此后,胡英泽又对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一书中的相关数据予以重新计算,认为由于赵冈在计算过程中利用的是矩形面积计算方法而不是梯形面积计算方法,使得洛伦兹曲线下的面积S2超出洛伦兹曲线,根据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分子计算偏低造成基尼系数偏低,产生较大误差[12]。
晋绥边区的土地占有分配状况颇受学者关注。近十余年来,岳谦厚团队对张闻天1942年兴县调查报告进行数据整理,利用相对占比而非基尼系数进行研究分析,指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山西兴县的小农经济社会有着“中农化”的特点,许多村庄的土地占有明显“中农化”倾向,中农数量及占有土地数量都占绝对优势。关于地权分配,岳氏认为山西兴县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土地占有关系,地权分配在不同阶层间是不均衡的,但人地矛盾又不如其他地区尖锐[13]。王志芳在对晋绥边区四县十四个自然村土地占有情况分析中指出,战前土地分配不均,9.7%的地主富农占有50.2%的土地,而人数将近50.0%的贫农仅占有13.8%的土地。在战争期间,边区政府在农村开展减租运动,使得战后地、富农阶级在户数和土地占有率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贫雇农一跃成为土地增加比例和土地占有比例方面“双高”阶级[14],因此战后地权分配呈现出分散趋势。
近现代山西单个村庄的地权分配研究集中于对吕梁、忻州等地村庄的考察。刘润民对抗战前后吕梁山区的临南枣圪垯村和临县西林家坪的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两村地主土地占有数量均在20.0%左右,地主和富农并非临县地区主要的土地占有者,土地占有较分散[15]。薛剑文分析晋南地区卓村土改前的土地占有资料,得出卓村以家户为单位的基尼系数为0.54[16],他认为晋南的土地集中度虽然低于同一时期全国土地集中度,但是晋南地区存在大量的无地户、少地户等,地权分配较不均衡。董秋伶对定襄县阎家庄土改前的地权分配进行研究,以户为单位所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54,以人为单位计算所得为0.46,表明阎家庄地权分配较为集中。同时,土改前阎家庄的无地户和少地户较多,而大地主较少,故地权分配又存在相对分散的特点,对地权分配的影响因素,董秋伶强调了分家析产与土地买卖两个重要推动力[17]。
要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土改前山西地权分配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关于地权分配是否集中仍然存在争议。不同学者研究的区域不同,占有的资料不同,所以可能造成不同的结论,且诸位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不同、技术工具的采用都可能产生大相径庭的结论。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如何选出代表性的地区及如何通过研究方法的完善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是亟须攻克的难题。
二、 土改后山西地权分配:两极化抑或分散化
民主革命时期,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成为山西境内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共的主要行政区域之一,山西也是最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之一。山西土改措施的成效如何,土改之后的地权占有状况如何,历年来引起诸多学者关注与探讨。目前,学界争议的关键点在于山西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土地占有是趋于两极化还是趋于分散化。
“两极化”是指土地改革之后,近现代山西农村出现了两大新群体——新富农与新贫雇农,使得农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张闻天在晋陕调查后指出,新富农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中农变为更富裕的中农,一部分农民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需要”[18]。王先明认为,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乡村社会的剥削制度,在起点上为农民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生活条件,但即使起点相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参与要素的差异,也会形成结果的不平均[19],新富农阶层的出现充分预示了土改后乡村结构两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这一阶级分化现象,党内外人士开始担忧山西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在这一背景下,1950年革命老区武乡、长治地委及1952年忻县地委等地区开展农村调查并提交报告[20-22]。这三份针对不同地区的考察报告向中央展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老区和新区在土改之后,农村土地、房屋等的买卖,导致了农村新的阶级分化,土地再次出现集中的苗头。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正是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出现新的贫富分化现象,促使党中央和国家迅速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不过,关于这一结论性认识,新近研究成果也提出不同意见[23]。
“分散化”是学界对于土改后山西地权分配趋势的整体认知。王瑞芳认为,土改结束后贫雇农上升至中农阶层,新中农阶级的壮大使农村社会结构由“下大上小”的“宝塔形”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长治老区的调查报告反映的恰是新中农的崛起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而非两极分化[24]。高沽、辛逸认为,合作化的倡导者在政治因素驱动下夸大了长治地区土地买卖及两极分化现象。他们收集地方性资料,结合田野访谈,对长治老区调查报告重新解读,发现武乡县六个村庄出卖土地数量较少,农户出卖土地比例不足全部耕地的1%,且土改后长治农村的生产生活形势向好,并未因土地买卖导致严重两极分化,也未威胁本地区社会稳定,从而亟须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25]。随后,胡英泽对山西永济吴村土改前至高级社时期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统计分析,发现土改前吴村地权分配以家户为单位与以人口为单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2和0.36,所代表的含义分别为分配不均与分配相对合理;经过土地改革,两个基尼系数指标分别为0.27和0.23,分配趋于平均;高级社前两个基尼系数指标分别为0.27和0.21,表明地权分配进一步趋于平均[26]。张晓玲对山西两个乡的个案及二十个乡的平均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山西阳高县、兴县及二十乡总平均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基尼系数数值在0.20左右,并未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张晓玲认为农业合作化迅速开展的原因并不是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而是为了配合工业化的发展[23]。
要之,山西土改后是否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学界目前已有一定的研究结果。但是从土改后地权分配分散程度的纵向变化来看,山西省内不同区域的变化存在差别。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对某一区域的研究应尽力搜寻其历史资料,拉长纵向研究的时间线,从土改到高级社的较长时段的研究,更有助于向我们展现及还原当地土地改革运动的原貌。
三、影响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的相关因素
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发展态势,或趋于集中,或趋于分散。造成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变动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地权分配的两个相关变量为家户数或人口数及土地面积,因此笔者将从影响土地面积及影响家户数(人口数)两方面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梳理考察。
自然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山西地权分配的变动。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农民,脚下的土地往往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噬。如兴县黑峪口土地面临黄河泛滥带来的严重威胁,黄河水灾曾经吞掉村庄的水地2 000亩[27]。1942年左右,河水冲荡使得平地所剩无几。战后,黄河曾推掉富农平地二十二垧、水地七垧,使得富农平地的增加受到限制且水地减少,因此黄河泛滥使得土地占有集中程度被削弱[28]。此外,旱灾、饥荒等自然灾害使得农民为了活命而不得不进行土地出卖或出典,这类灾害不仅引起地权转移,还可能引起人口及户数的变化。
分家析产使得地权关系趋于分散乃是学界共识。分家析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户数的增加,在分家的过程中,土地重新分配,各家户占有的土地规模变小,地权占有趋于分散[2]。岳谦厚对兴县十村抗战前后各阶级土地占有进行详细分析,指出任家湾战前战后每户农家所占有的土地减少是由于家庭单位的缩小即分家所引起的[28]。董秋伶在研究阎家庄时,提出影响地权分配的两个主要因素之一是分家析产,且土改前分家析产的影响要强于土改后及高级社时期。土改前,分家析产多存在于地主及富农阶级,贫农雇农“无家可分”。随着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贫农、中农“有了分家的基础”,因此土改后的分家现象更多,分家带来的地权分配趋于分散的影响更为明显[17]。
土地买卖作为市场调节生产要素配置的表现形式,使得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不断发生变动。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山西农民土地买卖是否频繁,土地买卖如何影响地权分配,学界仍存在不同认识。国外学者在对近代山西农村调查时指出,土地是山西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农民决不肯为了要取得投机或经商的资本,或者想变动一下处境而出售他们祖传下来的土地”,往往是为了偿还债务被迫出卖土地[29]。从张闻天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过去地主富农的买地使得土地有兼并的可能,而自1941年起土地买卖现象增多,为无地户和少地户带来获得土地的机会,中贫农的买地行为促进了土地的分散[4]。岳谦厚对保德县段家沟村抗战时期土地买卖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出卖土地较少,仅因娶妻、赌博等情况负债而出卖土地。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地价跌落,也遏制了土地买卖的发生。与此同时,段家沟村地权分配与晋西北大部分地区不同,地权较为集中,且土地质量方面各个阶级占有悬殊[30]。王志芳指出,抗战前后晋绥边区的土地转移方式以买卖为多,1940—1944年期间地主阶级卖出土地最多,土地流向了中贫雇农阶级。在交易方式上,地主、富农土地出典较多,中贫农土地卖出比例较高。土地出典、买卖等转移方式的发生,使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的地权分配趋于分散[14]。另有学者对土地买卖影响地权分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成为土地买卖的负反馈机制之一,若仅存在单一的土地买卖交易形式,将很容易造成地权集中,而典、活卖等交易形式会降低地权转移的发生[31]。
土地政策对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的影响,较之分家析产和土地买卖对农户地权转移活动影响更大。1940年,晋西北边区政府颁布《减租减息政策》,“静悄悄的革命”使得地主、富农在收入锐减与支出剧增的双重压力下,纷纷出卖、出典土地。例如,黑峪口四户地主在战后发生身份变动的原因皆有减租减息政策的影响[28]。1946年,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土地数量和产量两种标准抽肥补瘦,在数量上使得地权分配趋于平均,在土地质量上也尽量达到合理分配[7]。岳谦厚指出战争影响及中共减租减息、公粮政策的实施使山西农村土地呈现“均化”现象,这种土地转移表面上似乎是通过自由买卖实现的,其实却带有外加的强制因素,即张闻天所说的“迫”(对地主之“迫”)[13]。因此,在研究土地买卖对近代山西地权分配影响时,应深入分析是否有土地政策这一更深层次的因素发生作用。
除此之外,在中共阶级政策的干预下,阶级成分变化亦会引起土地占有数量的变化。董佳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中,经中共划分阶级后,兴县黑峪口富农的山地和平地占有数量都有所增加,这一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于阶级成分变化所引起的地权转移。与此同时,黑峪口中农的山地占有数量出现增加,首要原因也是阶级成分的改变所引起的地权分配变化[32]。
要之,以上诸项因素均对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产生直接影响。更需说明的是,诸项影响因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比如,土地买卖容易使得地权集中,但是分家析产又使得地权趋于分散。再如,土地政策使得农村形成“纺锤型”的社会结构,土地向中间阶层集中,同时也影响着土改后的农村分家和土地买卖。因此,从量化史学的角度着眼,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以上几类因素进行量化,研究哪一方面因素将在地权分配变动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
四、关于基尼系数的讨论
基尼系数最早用于研究收入分配,随着赵冈使用基尼系数计算地权分配情况,推动了学界运用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的均等程度。学者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标准为,0.2以下表示地权分配绝对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分配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差距悬殊,分配非常不平均。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于基尼系数方法的使用在不断完善,但对于地权分配的研究结论存在争议,绝大部分也是由于在计算基尼系数的过程中存在差异,目前尚无统一的计算标准。
(一)按户均还是人均计算
随着对地权分配研究的深入,学者在计算过程中发现户均占有耕地和人均占有耕地在计算基尼系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别。赵牟云在其研究中发现,按户计算的土地基尼系数与按人口计算的基尼系数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受家庭规模的影响,且按户计算夸大了地权分配的不均等。之后,胡英泽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对两种基尼系数都进行计算。随着学界的研究不断深入,几乎已认可人口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较为准确。
笔者在对张闻天调查团对兴县十村调查资料进行计算的过程中(表1),除使用拟合洛伦兹曲线计算的战前花园沟村及战后唐家吉村,还有不拟合洛伦兹曲线计算的战前花园沟村这三处外(1)以人口为单位计算基尼系数大于以户口为单位所计算的基尼系数的原因在于阶级内家庭人口数量的差别,见隋福民、韩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定十一个村地权分配的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59页。如战前花园沟富农家庭人口数远少于贫雇农家庭人口数,富农家庭平均人口数为2人,贫民家庭平均人口数为6人。而柳叶村与花园沟不同的原因正是地主富农平均每户人口数量大于贫雇农阶级,且差距较大。,其余数据都可证明用人均占有耕地计算基尼系数与户均占有耕地所得出的基尼系数相比较低。因此,在史料充分的前提下可将两种基尼系数都进行计算,避免引起争议。

表1 兴县十村战前战后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统计
(二)是否拟合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的计算通常和洛伦兹曲线有关,在众多学者研究中,是否拟合洛伦兹曲线是造成分歧的原因之一。胡英泽与秦晖利用相同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所得结果却有所不同,因而对秦晖的“关中模式”[33]提出疑问。刘志在之后的研究中对两人的计算过程进行推导,发现胡英泽对洛伦兹曲线进行了拟合,而秦晖没有拟合洛伦兹曲线,这是造成两人结论不同的最大因素。刘志提出,在分组较多的情况下,采用折线法计算的面积可以更为接近洛伦兹曲线,然而分组多少也要结合实际[34]。如上表所示,对于洛伦兹曲线的拟合与否,对地权分配结论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战前十村采用拟合洛伦兹曲线计算以人口为单位的基尼系数为0.43,地权分配差距较大,而采用折线法所得为0.38,地权分配相对合理。赵牟云提到山西战前地权分配存在“总体分散、部分集中”的特点[11],倘若采用不拟合洛伦兹曲线的计算方法,这一结论可能将变更为“总体集中,部分分散”。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否进行拟合,数据表明抗战后兴县十村的地权分配朝着分散的趋势发展,这与岳谦厚等学者的分析结论一致。因此,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往往囿于史料,在研究过程中方法的使用需在考虑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方法的选择,包括是否拟合、是否分组、分组多少等情况。
(三)数据处理标准的不同
在研究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问题上,学界对与土地有关的数据处理标准尚有分歧,理应成为未来深入探索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使用二手资料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容易产生误差,需结合其他材料深入研究还原其真实情况。
对无地户的考虑或将是研究山西地权分配的重要内容。对无地户的研究,刘志提出根据无地外来户、移民户的比例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此外对无地或少地工商户,因其对土地分配不均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无影响,所得出地权分配较为集中的结论可能有所失当,故须将其剔除[35]。胡英泽研究山西贯家堡土地占有分户资料发现,村中存在24.9%的无地户使得土地占有集中程度较高[10]。王先明对二十世纪山西乡村雇工进行调查,在四十四例调查中近75.0%的长工皆有土地,并不是无地户[36]。因此,刘志指出,因公田、一田二主及外来户等因素的影响,可能造成所统计的无地户数据偏高。胡英泽、章有义等人在研究过程中高估了无地户的数量,进而高估了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在剔除相关因素的影响后,修正基尼系数的计算,将会发现地权分配集中程度下降[35]。
对租佃制度的考虑会影响地权分配的数据处理。在分析影响地权分配的相关因素时,龙登高、何国卿表明在土改前北方农村前10.0%的富有阶层土地占有比例低于30.0%,如果考虑田面权、永佃权及公田等因素影响,此比例将会进一步降低[31]。关于一田二主、田面权与田底权等概念把握,曹树基先生在其著作中已有精彩论述,且曹树基及其学生等人与刘志的学术讨论中更能有助于学者对该问题的理解[37-39]。田面权及田底权更多是从租佃角度来考察土地占有情况。从史建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自耕农、租佃制与地权分配存在相关关系,在其研究中将自耕农分为富裕自耕农、一般自耕农及贫苦自耕农,表明自民国以来华北平原上自耕农的比重在不断增高[40]。由于近代以来山西自耕农比重较高已为学界普遍认知,故一田二主因素对于山西地权分配的影响较小,然在分析过程中将租佃情况与土地占有情况结合分析更能说明地权分配问题。
五、结语
在近些年的山西地权分配研究中,主要争议有三:一为土改前土地是否集中,二为土改后土地发展趋势如何,三为利用基尼系数测算地权分配时,如何结合已有史料实际进行精确可靠的研究。三个争议问题能否达成共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史料的丰富和研究方法的完善。
近年来,关于山西近现代农村地权分配史料不断问世,尤其是集体化时代的乡村文献数量庞大,这为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提供难得的机会,也带来一定的挑战,因为史料的时间主线拉长带来处理难度的提升。正如曹树基先生所说,新一代的历史学家缺乏将1949年以前的历史与1949年后的历史打通的能力[41]。
与此同时,作为处理地权分配方面的纷繁数据的重要工具,基尼系数的计算迟迟未能建立达成共识的标准,致使研究人员难以获得研究“利器”。希望在未来的近现代山西地权分配研究中,学者通过寻求新的可靠的史料,针对某一地区辅以田野调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合理运用基尼系数,以研究山西农村的地权分配,在较长时段的纵向变化过程中了解土改前后地权分配变化,探究土地改革对于农民生产生活和生产要素配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