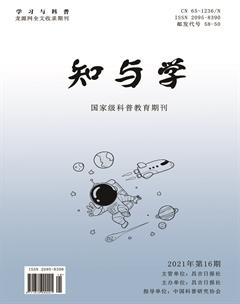略论先秦时期诗教的发生与发展
程诺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从先秦时期诗乐舞一体的诗歌开始,这一点贯穿着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始终。诗教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通过诗歌进行教育,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诗教;先秦;乐教;礼乐
1.从乐教中产生
诗歌的初始形态是祭祀仪式中的一种表演形式,因其歌乐舞一体的综合形态可以断定:此时的诗是一种“声诗”。在那个时期,舞、乐的重要性是超过诗的,那么其教化功能自然是以“声教”或者说以“乐教”为主。这些诗歌在内容上以歌功颂德和记录本部族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在远古时代巫术盛行和图腾崇拜的社会背景下,乐教因此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作用。且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推断,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成熟,可以想见乐教在产生之初就与礼制一起,发挥着沟通人神,统一思想,强化秩序,整合社会的重要作用。
诗教自诞生之初就一直从属于乐教,是乐教的一个分支。直到秦汉以降,音乐的教化功能逐渐消失,诗歌得以独立出来才成为教化的主体,可以说诗教就是从乐教这一母体中脱胎出来的。
2.以《诗》教为主体
“诗教”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于此处详细地分析了“六艺”之教的优缺点以及其所能达到的教育效果,其中《诗》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达到“温柔敦厚而不愚”之教化效果。但诗教与《诗》教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诗”并不等于《诗》。《诗经》中的诗篇并非创作于同一时期,这些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作品展现了诗歌由诗乐舞一体的综合形态向纯文学形态转化的过程。《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时诗、乐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分化,诗的独立功能开始显现。陈世骧先生指出,在《诗经》文本中,直接使用过“诗”字的篇目共有三篇,分别是《崧高》《卷阿》《巷伯》,通过分析,陈先生认为“作者自己在末后加重说他这一个篇章是‘诗’,特为明示或暗示着一种自觉的意识,标出诗之为语言的特有品质,虽然照早已流行着的风尚,这些篇章照例是歌唱的,但此时觉到了诗的要素在其语言性。有和歌唱的音乐性分开来说的可能与必要。”[1]陈先生的观点恰与《尚书·尧典》中所提及的诗乐分化的现象相互印证。可见在先秦时期,诗歌虽然仍是诗乐舞的综合艺术形式,但其中已经孕育着相互分离的趋势。
《诗经》最初的编纂目的与后世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诗集不同,其编纂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从文学角度上做文本的记录和保存,《诗经》的形成更多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其中的雅、颂部分更是周代礼乐文化兴盛的表现,是周代礼乐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周代社会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统治者将其作为礼乐教化的范本,所以礼乐教育又称为“诗教”,最终形成了以《诗》教为主体的一整套礼乐教育系统。
3.最终演进为言教
周代高度发达的礼乐文化孕育出了成熟的礼乐教育。此时的诗歌虽然仍是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诗乐舞各自的发展以及某些政治原因,诗乐舞的分离自西周时期开始逐渐展现,诗教开始脱离音乐呈现出以语言为主的教化特点。
根据《礼记·保傅》的记载,周代的教育更加细化,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分为五类,由不同的官员负责:“周五学,中曰辟雍,环之以水;水南为成均,水北为上庠,水东为东序,水西为瞽宗。”其中成均是学乐的专门场所,由大司乐主持。《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周代音乐教育的具体内容,其中包含乐德、乐语、乐舞三个部分。乐语的具体内容又分为“兴、道、讽、诵、言、语”六部分,类似于六种语言文字技巧。由此可以推测,诗与乐在传授过程中或已出现了分开教授的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大环境加速了诗、乐的分离,此时的音乐的主要职责是娱人,只有极少一部分音乐还保留着教化的作用。诗成为了礼乐教化的主力军。促成这一切的直接动因或是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外交活动。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此处的“诵”可理解为《周礼》中记载的“乐语”之一,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可见“诵”包含着“背诵”和“吟咏”两个意思。而“专对”一词可解释为“擅自应对”或“独立应对”。春秋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要遵守朝聘制度,《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中记载:“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仪礼·聘礼》中讲:“辞无常,孙而说。”郑玄注曰:“孙,顺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辞,辞必顺且说。”刘宝楠先生认为,使者是因为接受过良好的《诗》教,所以其外交辞令可以达到“孙而说”的水平。基于当时以《诗》作为外交辞令的历史事实,外交使臣一定要精于《诗经》,并恰当地引用《诗经》中的语句来进行外交活动。故此时《诗》教的内容,主要是以学习《诗》中的语言技巧和创作手法为主。虽然当时诗乐结合使用的情况依然存在,但在外交活动中,《诗经》都是在脱离音乐的情况下使用的,外交使臣们引用与自己论点相符或对自己论证有利的部分诗句组織外交辞令,这种“断章取义”的用诗方式在当时应用的十分广泛,这与贵族教育中重视言辞的倾向是高度一致的。傅道彬认为“春秋时代经历的从武化向文化、从世族到士族的转型,一个重要倾向是人们普遍的文言意识和言语能力,一个注重诗书礼乐修养追求‘建言修辞’的士人集团走向历史舞台。”[2]士人的崛起为诗歌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士人群体的推动下,诗歌以语言的形式开始承担“言志”的功能,而音乐则逐渐朝着娱乐化和世俗化发展,乐教开始向着言教转变。
参考文献:
[1]陈世骧《中国诗之原始观念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 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