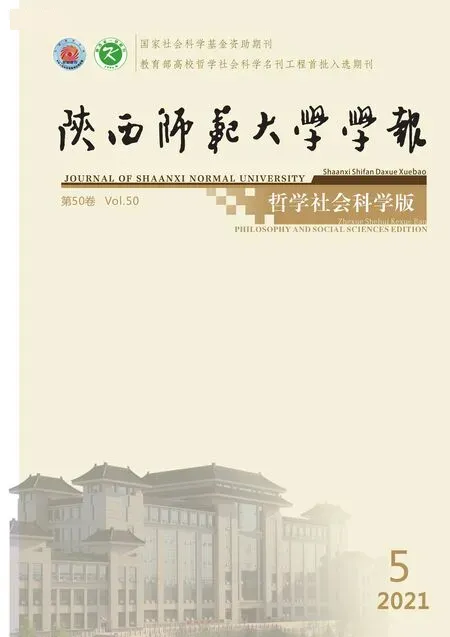从农业资源配置看全面抗战时期的陕西植棉业
石 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主要产棉区为冀、苏、鄂、豫、鲁、陕、晋7省,棉产重心位于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陕西植棉业在一些有利条件推动下渐趋兴盛[1],棉田面积和棉花产量迅速增加,1937年时,陕西棉田面积482万市亩(1)民国时期度量衡不统一,文献和统计资料中的单位也往往有所不同,“市制”与“旧制”并存。其换算关系约为:1旧亩=0.922市亩=614平方米,1旧担=1.19市担=119市斤,1旧斤=1.19市斤。,产量106万市担,而河北棉田面积1 385万市亩,产量267万市担,江苏棉田面积1 182万市亩,产量233万市担,湖北棉田面积794万市亩,产量151万市担。当年,陕西棉田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总数的约8%,位居全国第6位,[2]1-7成为全国主要产棉省份之一,然而陕西并非头等棉区,因为陕西棉花无论是在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在影响力方面,与江苏、河北、湖北等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然而,全面抗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战前形成的植棉业分布格局,各产棉大省或沦陷敌手或成为战区,植棉业遭到重创。陕西植棉业虽然也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但战争的直接破坏作用相对较轻,两相对比之下,“陕西省棉产之重要性,已因其他各省棉区之沦陷,而跃占第一位”[3]264,战争客观上使陕西成为战时大后方唯一重要且保存完整的产棉区,“朝野上下遂对陕西棉区寄托了无限的期望,军需民用靠它,战后收复区的良种供应也指望它,成了唯一的衣被源泉,复兴棉业的根据地”[4],肩负着为后方军民提供棉花的战略重任,陕西植棉业在这个时期也因此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特别重视。
然而,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陕西植棉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对全面抗战时期少有涉及,现有研究成果多强调陕西植棉业因为战争所呈现出的停滞和衰退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个时期陕西植棉业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在良种引进、植棉管理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对陕西植棉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地位缺乏准确的定位和应有的重视。
农业生产离不开各种农业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经济资源,前者是指农业生产可以利用的自然环境要素,如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等,后者是指直接或间接对农业生产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农业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农业技术装备和其他生产要素,包括农具、种子、交通、资金、管理等。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在地域空间上和时间上得到合理布局与利用,从而实现农业资源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时期,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尤其显得突出。本文主要从科技、资金、管理等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角度对全面抗战时期的陕西植棉业进行考察,深入探讨陕西何以成为“大后方罕见的棉产盛区”,并分析战时陕西植棉业的发展成效与影响,希望能够丰富对战时陕西植棉业的认识,加强对战时植棉业问题的研究。
一、 科技资源配置: 棉产改进与植棉技术的改良
全面抗战初期,成立于1934年的陕西棉产改进所(2)1933年10月国民政府成立了棉业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负责对全国植棉业进行大规模改进。1934年4月棉统会与陕西省建设厅合作成立陕西棉产改进所,作为负责陕西棉产改进的专业机构。(简称“陕棉所”)是负责本省棉产改进工作的主要机构。1938年10月,陕西省政府将“陕棉所”、林务局等六机关合并为陕西省农业改进所(简称“陕农所”),作为领导陕西农业的主要行政和技术机构,此后陕西的棉产改进工作即由“陕农所”主持。战时陕西在棉产改进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推广优良棉种
战时陕西推广的优良棉种,主要是斯字棉和德字棉。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征集国内外棉种进行区域试验,发现了原产美国的斯字棉和德字棉两个优良品种,其亩产量及织维品质均较当时种植的其他品种为佳。在随后的试验中进一步发现四号斯字棉表现最佳,具有很多显著优点,如成熟早、产量高、织维长,其他棉种无一能与其相媲美。1936年棉统会从美国购进四号斯字棉和德字棉种进行繁殖,1937年开始全国推广。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良种推广计划在多省严重受挫,而陕西成为参与良种试验和推广的省份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如“陕棉所”泾阳棉场自1934年起,参与进行斯字棉和德字棉区域试验。1936年棉统会将从美国购买的四号斯字棉种分配给“陕棉所”1万磅,在泾阳、高陵两地繁殖1 550旧亩。又将从美国购买的七一九号德字棉种分配陕西8 000磅,在大荔、朝邑一带繁殖660旧亩。这是斯字棉和德字棉在陕西推广的开端。[5]86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棉花滞销,棉价暴跌,农民植棉兴趣下降,而且政府提倡种植粮食作物,限制棉花种植,优良棉种的推广事业受到严重威胁。“陕棉所”认为,“斯字德字两棉种,已经耗费相当之金钱时间与人力,公认为本省最有希望之棉种,确有维持纯良之必要”,如果不继续集中收购保存棉农手中的优良棉种,“则本省棉产改进工作,倒退四年,全功尽弃”,因此提议继续筹款,由政府从棉农手里收买良种继续推广。[6]在“陕棉所”的坚持下,优良棉种的推广工作得以延续不辍。“陕农所”成立后仍将斯字棉和德字棉推广列为中心工作,进行大规模推广。
战时陕西斯字棉和德字棉的推广面积与产量逐年递增。如表1所示,面积从1937年的19 071旧亩增至1945年的1 719 506旧亩,增长了90倍;产量从1937年的5 361市担增至1945年的462 321市担,增长了86倍。其中四号斯字棉因优势明显,是战时推广的最重要的棉种,成效也最为显著,从1937年的1万余旧亩增至1945年的163万余旧亩,增长了126倍。经过数年推广,斯字棉遍布关中各县,“东起潼关,西至宝鸡,南自华山之麓,北至龙门之阳,皆为斯字棉之分布区域,关中人民视为与泾惠渠同样之瑰宝”[7]。陕西斯字棉“推广之顺利而迅速,不特为民国以来棉业史上空前之举,即吾国作物改良史上亦无与伦比”[8]。

表1 1936—1945年陕西优良棉种推广面积与皮棉产量统计表
(二) 防治棉花病虫害
棉花生长极易受到病虫害影响,如果只进行良种推广而不设法防治病虫害,则推广成效难免事倍功半。陕西棉花虫害较多,尤以蚜虫、红铃虫为害最烈。如据调查,1937年棉花红铃虫被害率为16.8%,1938年为20.6%,1939年为45.6%。这对棉花的产量品质和棉农的经济收入都造成了严重影响。[9]因此,战时陕西在推广优良棉种的同时,对于病虫害防治颇为注重,重点进行了棉蚜虫和红铃虫的防治。
棉蚜虫的防治,主要是由改进机关指导各地农民利用烟草水、皂荚棉油乳剂等方法进行。改进机关先在棉区设立棉蚜防治表证示范区,以事实换取农民对防治技术的信任,然后再做大规模推广,使防治方法普遍使用,并使农民养成自动防治的习惯。在棉蚜防治期间,“陕农所”饬令各县附设机关全体动员进行防治,还通过举行治蚜运动宣传周进行治蚜方法表演,对民众进行训练。[10]69红铃虫主要用捕杀法进行防治,“陕农所”用收买及缴纳两种方式动员农民、学生等参与防治。“陕农所”制定了捕缴红铃虫奖惩办法,设立了示范区,进行工作竞赛,并编印红铃虫活页教材转发各小学,寓宣传于教育,以普及红铃虫防治知识,增强学童等捕捉兴趣。陕西省政府饬令各县政府转令各乡保甲长及棉户,按亩缴纳幼虫半斤,各指导人员轮流到各村巡回督导及登记验收红铃虫。[9]
战时陕西棉花病虫害防治工作所需的技术、人员和经费,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除了“陕农所”的经费和技术人员外,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提供了防治经费补助,中央农业实验所每年均派技术人员来陕协助防治。陕西棉花病虫害防治颇具成效,如棉蚜方面,1938年防治棉田1.3万余旧亩,估计增加农民收入8.3万余元;1939年防治棉田8.4万旧亩,估计约增加农民收入121万余元;1940年防治棉田增至33万余旧亩,估计约增加农民收入1 118万余元。[11]红铃虫收缴,1939年为2 636旧斤,1940年和1941年超过了28万旧斤。[12]239
(三) 开展棉作试验研究
植棉业的发展对于各种植棉技术依赖性较强,因而需要通过进行棉作试验掌握各棉种的特性,从而给棉花栽培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全面抗战爆发前,“陕棉所”已经开始进行多项棉作试验。全面抗战时期,“陕农所”泾阳农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和金陵大学西北农场等科研机构继续在陕西进行各项棉作试验,包括棉花品种比较试验、灌溉试验、肥料施用方法试验、棉田土壤管理试验、绿肥轮栽试验等多个方面。这些试验研究工作对于植棉之重要问题,如肥料、灌溉、播期、距离、土壤、管理、轮栽等,无不包括在内,且其中若干试验历经数年已有具体结论,为棉花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在泾惠渠灌区进行的棉田灌溉试验发现,农民因缺乏用水知识,棉田灌溉存在很多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争相用水,过度灌溉,反而使棉花生长受到消极影响,枝条生长过高导致秃而不实。试验找到了棉花的最佳灌溉期、灌溉次数及灌溉量,掌握了棉田灌溉的一些规律,如棉花生长期间需水最殷;灌水过多不但不能增加产量,反而会延迟成熟时间,增加霜后黄花百分率,减低产品收益;棉田灌溉之适期较次数之多寡更为重要。[13]此外,泾阳农场的试验发现,凡灌溉次数少的棉田,提早于始花时灌溉,西北农场的试验发现,灌溉的同时加入氮肥,都能使灌溉取得更为良好的效果。这些灌溉规律的掌握,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益和棉花产量。
近代中国棉产改进过程中,曾先后引进十多个优良棉种,但在繁殖推广前多未经驯化,而是盲目散发给棉农种植,之后又未能对棉农进行技术指导,因此推广效果不佳,很多优良棉种严重退化。战前陕西的棉产改进也曾陷入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恶性循环,战时陕西植棉业则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粗放做法,科学技术在植棉业发展中发挥着指导作用。战时陕西各项棉田作业,大体上依照泾阳农场及西北农场的“试验结论及示范,尤以灌溉地为然”[14]。在传统社会,农业技术改进一般都是由农民在经验基础上自发进行的,而“现代的技术,刚好相反,包括有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农业问题的含义,而且,一般并非由农民本人,而是由有训练的专家作出的”[15]45。战时陕西植棉业正是受益于一批训练有素的棉业专家,他们进行的大量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为棉花种植提供了科技资源,这是植棉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 资金资源配置: 棉业贷款与棉花生产资金
农业生产离不开资金支持,尤其是棉花种植成本较高,投资较大,在棉花生产过程中,棉农购买种子、肥料、农具、病虫防治药剂等各种物资,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资金接济。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棉作改良机构在棉种改进方面已有所成就,培育出一些优良棉种,但却难以大量推广,缺乏资金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试验工作的结果停留在暖房里,如何将这些改进结果推广到农民手里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答……贫农即使想种植改良的种子,也没有能力做,他们没有财力。这就是30年代在农业方面一般存在、在农业金融方面尤其存在的卡脖子的问题。”[16]140陕西农民在种植棉花时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缺乏资金,自1929年遭受严重旱灾之后,“农民经济,整个破产,一般棉农,即有植棉信念,多因资金缺乏,恒难达到目的”[17]。
全面抗战爆发前陕西农村金融事业已有所发展,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在陕西办理农业贷款,棉业贷款是其中主要部分,对于促进植棉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商业银行的农贷大都停办,棉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42年大后方棉荒加剧,国民政府提倡棉花增产,棉贷随之恢复开展,希望通过国家银行的贷款支持,调动农民植棉积极性,从而促进棉花生产。陕西棉贷工作遂重新启动,并成为战时农贷的重点。[18]
1942年之后,陕西棉贷由“陕农所”与中国农民银行会同办理,资金由农民银行统一发放。战时棉贷分为生产贷款、运销贷款和推广贷款三大类,其中以生产贷款为主。1943年农民银行核定陕西棉花生产贷款6 000万元,利用合作社及农会组织,在关中、陕南24县,按水地每旧亩100元,旱地每旧亩50元的标准贷放,共计贷款合作社与农会180个,贷款棉田92万余旧亩,实际贷出生产贷款5 248万余元。[5]266时任“陕农所”所长李国桢曾言:“国库以若此庞大资金运用于农村者,为数亦不多见,由本年棉花增产资金贷款之情形观之,亦可见各方对陕棉增产工作之重视。”[19]
1944年国民政府对于陕棉增产工作更为重视,扩大陕西棉花贷款规模,核定贷款总额为4亿元。当年农民银行陕西棉花生产贷款实际贷放区域增至31县,贷款合作社与农会共计275个,贷款标准为水地每旧亩200元,旱地每旧亩100元,共计贷款棉田190余万旧亩,实际贷款逾3.4亿元。1945年陕西棉花生产贷款核定资金16亿元。为了避免贷款过于分散,并为便于推广指导及节约人力财力起见,农民银行将陕西的棉贷区域进行缩小和集中,并偏重于水地植棉,以提高贷款的增产效益。[20]当年,陕西棉花生产贷款区域为20县,合作社及农会共158个,贷款标准为水地每旧亩1 000元,旱地每旧亩500元,贷款棉田181万余旧亩,实际贷款13.8亿余元。[5]251
全面抗战时期,历年棉花生产贷款不仅数额较多,在农贷总额中占比最高,而且利率较低,因此受到棉农欢迎。“棉农依赖棉贷,许多地方已成为习惯……检讨棉贷的功用,确实帮助棉农甚大,帮助增产甚多。”[21]国民政府通过农民银行给予了陕西植棉业大量资金支持,在推动棉花增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1942年棉贷停顿期间,陕西棉田总面积和总产量逐年锐减。1942年后,随着棉花生产贷款的大规模增加,棉农获得资金调剂,棉田面积和产量止跌回升。战时陕西棉花生产贷款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贷款成效大打折扣,但棉贷仍为棉花生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金资源,是当时陕西植棉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 管理资源配置: 棉种管理区制度与植棉管理
棉花是一种非常易于杂交的农作物,天然杂交率常在30%以上,如果管理不善,将不同棉种混种一地,则不出三五年良种势必会退化变劣,因此推广优良棉种必须严格管理。近代中国植棉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就是农民植棉往往自由耕种,优劣混杂,而且收花之后,棉农自由出售,商贩掺杂作伪,使棉籽更为混杂低劣,良种优越性丧失殆尽。很多地方的优良棉种推而不广,成效不彰,缺乏有效管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一) 棉种管理区制度
在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植棉业发展中,政府力量开始积极介入,进行管理和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推行棉种管理区制度。所谓棉种管理区制度,就是棉产改进机关在政府或法律的授权下,划定一定区域作为棉种管理区,规定在该区域内只能种植一个优良品种,并由改进机关及政府有关机构对管理区内棉花的播种、收获、轧花直至出售产品全过程,及其从业人员,如棉农、轧花厂、棉商等,进行严格管理。通过集中种植和统一推广,以保持棉种纯度并源源不断地供给棉农,持续发挥增产作用,从而达到棉产改进的效果。棉种管理区制度被视为“改良棉作最新最有效之方法”[22]。
中国的棉种管理区制度最早于1937年由河南省棉产改进所实施,陕西的棉种管理区制度也始行于1937年。当时,“陕棉所”计划大量推广斯字棉和德字棉,但良种数量有限,如任其自由推广,日久必致散漫变劣,故为保持棉种纯度及增加推广效率起见,“陕棉所”拟订了《陕西省棉种管理区暂行办法》,由陕西省政府于1937年4月通过。该办法规定: (1) 本省为谋棉种之纯良,以维持其原有之产量,并为良种之大量供给,以应本省推广植棉之需要起见,特设棉种管理区。管理区设立办事处办理区内一切事务。(2) 管理区内棉农每年皆须一律领种“陕棉所”规定之优良纯洁棉籽,不得种植其他棉种,如另种其他棉种者须立即铲除。管理区棉农对于棉作之栽培、选种、病虫害之防除等方法,应切实接受管理区办事处技术人员之指导。(3) 管理区内棉农所需优良棉种,由办事处借给或由棉农价领。棉花收获后棉农需按照借一斤还一斤半的比例偿还棉籽,其余全部棉籽应按照市价售让给办事处。管理区内棉农不得自行留种,由本区年年供给优良棉种,区内所产棉籽依次向外推广。区内棉籽由办事处统筹支配,非经核准棉籽不得输入或输出。(4) 管理区内设置轧花厂,由“陕棉所”派员管理。区内所产籽花,非在区内轧花后不得运出区外。区内农户因轧取自产棉花而设置的轧花厂,须向办事处登记。棉商在管理区内收花,应以皮花为限。违反规定者将处以罚金。[23]为加强对轧花车的管理,防止因轧花导致棉籽混乱,“陕棉所”还制定了《陕西省各棉种管理处轧花车登记指导办法》,要求凡在棉种管理区内的轧花车必须加以登记,并在轧花时期严禁偷轧退化洋棉,否则由地方行政当局予以处罚。[24]可见,棉种管理区内的棉花种植、棉籽运输和轧花等,均须接受严格管理。
(二) 棉种管理区制度的实施
1937年春开始推广斯字棉时,“陕棉所”即以棉种管理区的方式在泾阳县集中推广,棉种管理区制度初步推行。1937年七八月份,“陕棉所”分别在泾惠、洛惠两棉区与当地县政府合办棉种管理区两处。泾惠棉种管理区为斯字棉繁殖推广的根据地,以泾阳棉场为中心,包括村庄21个,棉田万余旧亩。洛惠棉种管理区为德字棉繁殖推广的根据地,以大荔棉场为中心,包括村庄10个,棉田5 500旧亩。[5]87此后根据推广需要,棉种管理区不断增设。棉种管理区的范围逐年扩大,到1940年时斯字棉管理区已有503个村庄,16万旧亩棉田。[8]截至1941年已设立了泾惠区、洛惠区、渭南、兴平、长安、宝鸡、朝邑、韩城等斯字棉管理区,以及在陕南城固设立的德字棉管理区。
棉产改进机关与地方政府合作,在管理区大力宣传棉花纯种观念。如1938年“陕棉所”和渭南县政府在换发良种的布告中规定:棉农种植德字棉后,就不许再种当地的土种,免得好坏混杂在一起,将来好种子反而变成坏种子了;在“陕棉所”规定区域之内,农民如种植土种,县政府立刻就要派警力前来铲除;棉花收获后棉农得到的所有棉籽,要按照当地的市价售与“陕棉所”,不准自己处理,免得好种散失;领种的农友要接受“陕棉所”职员的指导。[25]“陕农所”成立后继续严格推行棉种管理区制度。每当棉花成熟季节,“陕农所”都会发布命令或告示,加强对区内良种的管理。为避免良种散失及混杂起见,泾阳农场经常派员赴管理区及油坊和城镇各轧花棚户巡查,严禁代轧籽棉及棉籽偷漏,并禁止油坊收买良种榨油。为预防种植杂棉,避免良种混杂,泾阳农场时常派员向农民宣传设立管理区之意义,泾阳县政府也训令各保甲长转嘱农民勿植杂棉,否则立即铲除。此项工作自棉花播种时起,一直在不断进行检查。对于所发现的杂棉,由县政府派员监督铲除。[26]
各棉种管理区通过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在棉种保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棉种管理区逐年扩大,棉种供给充足且仍保持相当高的纯度,可向周边地区大量推广。如推广斯字棉成绩最为显著的泾阳县,至1940年时全县已经普遍种植斯字棉,面积达23万余旧亩,是全国唯一的棉花纯种普及县。[27]120当时,正在陕西协助指导斯字棉推广工作的棉业专家冯泽芳赞赏道:“吾人巡视泾阳县之农田中,见到处皆是斯字棉,生长整齐可爱,实创吾国仅有之全县普及棉花纯种之纪录。此吾人于叙述棉种管理区时,不能不特予表扬者也”[8]。棉业专家孙恩麟也曾指出,“地方纯种制度,以陕西省最为成功”[28]。
棉种管理区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严格管理以避免农民各行其是导致棉种混杂,并保证优良棉种能够科学有序、源源不断地向各地推广,发挥良种供给根据地之功能。这种积极监管而非消极放任的管理方式,为以前推广植棉所未有。从陕西优良棉种的推广效果来看,这一制度的目的很好地实现了,植棉管理水平较前有了显著提高。这种新的管理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是战时陕西植棉业取得进步的重要保障。
四、 战时陕西植棉业的发展成效与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棉纺织工业停顿和交通阻塞,陕棉外运困难,销路锐减,棉价大跌,棉农被迫少种或不种棉花,因而1938—1942年陕西棉田总面积和棉花总产量持续下降。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在棉产改进机关及各方面的努力下,在上述各项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战时陕西植棉业仍取得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一) 棉花亩产量增加,品质大幅提高
就陕棉单位面积产量而言,1928—1937年间年每市亩平均产量为24.89市斤[2]13,同期全国棉花年每市亩平均产量为29.16市斤[2]15,较全国低4.27市斤。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不仅较战前有显著增长,而且这一时期除1942年和1944年因受灾影响外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棉花年每市亩平均产量提高至30.74市斤,较1928—1937年间的24.89市斤,每市亩约增产5.85市斤,增产23.5%,而同期全国棉花年每市亩平均产量下降为24.94市斤,陕西足足高出全国5.80市斤。

图1 1937—1945年陕西棉花平均亩产量与全国棉花平均亩产量对比示意图
战时陕西棉花亩产量的提高,以各水利灌溉区域最为显著。因灌溉区棉花水分能及时供应,故亩产量常超过旱地两倍以上。关中灌溉棉田亩产皮花100旧斤颇为常见,最多者可达一百四五十旧斤,亩产量之高“不仅为国内所罕见,即世界最著名高产量之埃及亦不能与之比拟”[29]。各灌区棉花亩产量增加之成效,以泾惠渠灌区最具代表性。据统计,1938—1945年,泾惠渠灌区棉花年平均亩产量为65.5市斤,不仅高于该区战前的年平均亩产量,而且远高于战时全省的年平均亩产量。[30]尤其是1939年,泾惠渠灌区皮棉平均亩产量约100市斤,最高达150市斤,“其产量之丰,不仅为国内所未有,抑且为世界所罕见。较之旱地,每亩只能收获二三十斤者,直不可同日语矣”[31]19。
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棉田总面积和棉花总产量均严重下降,但总产量降幅明显小于总面积降幅,如表2所示。以1937年为基准,1938年棉田面积较1937年下降了近22%,而皮棉产量下降了不到2%。1939年棉田面积较1937年下降了42%,而皮棉产量下降了不到10%。直到1945年时棉田面积相当于1937年的39.15%,而皮棉产量则相当于1937年的48.53%。除1944年外,战时陕西皮棉总产量的下降幅度一直小于棉田面积的降幅。正是由于棉花亩产量有所提高,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面积减少对总产量造成的损失。

表2 1937—1945年陕西棉花种植面积与皮棉产量统计表
就棉花品质而言,全面抗战前我国棉花品质随着优良美棉的大量种植而日渐提高,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省的棉产改进工作中断,良种推广半途而废,很多地方甚至重新种植本应淘汰的中棉。这主要是因为美棉适于机器纺织,而中棉则适于手工纺织,战时厂用减少,各地所产皮棉多供当地手纺使用,美棉在土法弹纺上反不如中棉易于处理,故农民乐于种植中棉。美棉面积和产额大量减少,棉花品质也随之退步,多年来以推广优良美棉为目标的棉产改进事业可谓前功尽弃。然而,“唯一的例外是陕西省”[32]43。战时陕西由于大量推广斯字棉和德字棉,到1945年时优良棉种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到全省棉田总面积和总产量的90%以上。陕西省的棉田面积和皮棉产额中,美棉所占比例在全国名列第一,远超其他各省。[33]1-9优良棉种的普遍种植,使陕棉品质和战前相比有了显著提高。如据调查,1936年时,陕棉织维长度中1英寸以下者占到了98%,1英寸及以上者仅2%。而到1940年时,织维长度中1英寸及以上者占到了33%,可见长绒棉比例大幅上升。[34]陕棉因品质优良,“色泽长度更见优美,深为厂家所乐用”[35]。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陕棉所”确定的战时棉产改进的目标是“求质的改良与单位产量之增加,不求棉田量的扩充”[36]。从陕西植棉业发展的结果来看,这一目标得到实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战时陕棉总面积与总产量出现了严重下降,但并非所有区域都在下降,水利工程灌溉区域的棉花面积和产量就不减反增。据统计,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黑惠渠等各渠灌区棉田面积从1937年的30万市亩,增加至1945年的近40万市亩,在全省棉田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从6%上升到21%。灌区棉花产量从1937年的约18万市担,增至1945年的26万余市担,在全省棉花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从17%上升到50%,占全省棉花总产量的一半多,成为陕棉的主产区。[37]这反映出战时陕西棉花种植在向水利等资源条件较好的区域集中,而这些地区植棉的产出效益更大。
(二) 植棉业带动了棉产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全面抗战前棉业已经与陕西尤其是关中农村经济形成了密切关系,棉花的生产、运输、加工、贸易等带动了区域农工商业的发展,关中农村经济中“棉花经济”的色彩非常鲜明。战时棉花种植面积虽然大幅减少,但仍是关中农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是农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农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渭南、泾阳等县农民而言,棉花是他们种植的主要作物,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每个农民除了栽种一些仅够果腹的小麦与杂粮以外,其余都是栽种棉花,故每个棉农开支的一切费用,也需仰仗棉花。如完粮纳税,称盐打油,购买农具,耕牛,以及庆吊酬酌,都是靠卖棉花来维持,就是治产盖房,积财千万的财主,也无一不是在棉花上打主意”,农村经济“完全建筑在棉花上面”[38]。据调查,20世纪40年代时陕西植棉农家人口达300余万,约占全省人口的1/3。[39]植棉业与陕西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战时推广种植的优良棉种,量丰质优,售价较高,能够给棉农带来更多经济利益。而且,植棉业发展带动了轧花、打包等相关事业的进步,关中一些产棉区农村市场出现繁荣景象。如泾惠渠灌区每年棉花收获时期,各地棉商纷纷前来采购,“故泾惠渠灌区,每届十月以后,沿途车马络绎不绝”[40]6。灌区棉花大多运到泾阳、三原、高陵及永乐店出售。泾阳县位于灌区核心,是陕西最著名的棉产区,也是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战前即执陕西市场之牛耳,抗战后河北江苏等产棉区沦陷,该地尤为后方仅有之棉花市场,亦为国内有数之原始市场”[41]。1942年陇海铁路支线咸同铁路建成后,该县东部的永乐店镇因位于咸同铁路中点,交通便利,灌区棉花外运以永乐店最为适中,因而很快成为关中新兴棉花集散中心,当地工商业也随之走向繁荣。永乐店作为一个乡村小集市,全市商铺百余家,花店占20余家,“当皮棉上市时,花车辂辂,由四乡群集于此,乡民麇集,百业繁荣,及至棉季一过,则市面萧条,商铺门可罗雀,此乃棉业影响商民经济之明证”[42]。当地还设立有棉花打包厂,全县所产棉花大都集中于此打包,再运往咸阳转往宝鸡等地。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纷纷在永乐店设立分支机构,各大纱厂在此收购棉花,“年来市面日趋繁荣”[43]。在棉业经济带动下,永乐店一跃而成为该县商业重镇,“有工厂,银行,商号,花行……一切均在蓬勃之发展中”[44]。
(三) 陕西为战时大后方棉花供给发挥了关键作用
战时陕西棉田总面积和总产量虽较战前大幅减少,但1938—1945年年平均棉田面积仍有225万市亩,8年皮棉总产量约40万市担,年平均产量约67万市担。即使1942年陕西棉产最少的一年,其产量仍占到了陕、豫、湘、鄂、川5省产量的31%。[45]战时国民政府曾在后方各省积极推动棉花种植和增产,但陕西棉产始终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产量曾占全国后方棉产总额之半。品质之佳,亦为各省所称誉”[46]。
陕西棉花生产不仅保障了陕西军民和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而且为后方其他各省提供了大量棉花。战时四川、云南、鄂西、豫西等地虽然也产棉花,但数量有限,自给尚感不足,而且多是品质较低的中棉,无法满足纱厂需求。陕西棉产则自给有余,遂大量销往以四川为主的后方各省,成为“后方棉产之主要供给来源”[47]。陕棉织维较长,尤为适宜机纺,故为后方各纱厂所仰赖,被视为“战后西南西北机纺原棉的唯一来源”[48]。1940年宜昌沦陷后鄂棉来源断绝,“后方厂用原棉,几全仰给陕西”[49]。1942之前陕棉每年约有30万市担外销,约占年产量的近一半。1942年之后国民政府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1942—1944年3年间政府共收购陕棉111万余市担。[5]303国民政府控制了90%以上的陕西棉花,同时在政府所征购的棉花总量中陕棉也占到了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所能够控制的棉花资源的主要来源。陕棉的重要性得到了政府、纱厂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如时人所言:“陕西的棉花,产量最多,品质最好,抗战中军用民用的棉花,多取给于此”[50]。陕西棉花“在抗战期间对于军需民用贡献最大”[51]。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植棉史和陕西植棉史上一个艰难而又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战时陕西植棉业发展中,关中地区的土壤、气候为棉花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抗战前后进行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为棉花生长提供了充分的水资源。战时的棉业科技、优良品种、生产资金和新的管理制度,为植棉业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资源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与匹配,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也提高了棉花生产力。而且,相较于一般粮食作物种植而言,植棉业对于科技、资金等资源的要求更高,要想提高棉花生产力,仅靠知识水平有限、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民是难以办到的。在战时陕西植棉业发展中,以“陕农所”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是农业资源能够实现优化配置的主导力量。“陕农所”不仅积极推广优良棉种,进行棉作试验,而且与地方政府、水利机关、国家银行等相关机构合作,为植棉业提供所需资源,并将优良棉种、生产资金等向关中平原,尤其是向水利条件较好的新型灌区进行倾斜。正如全面抗战时期在陕西主持棉产改进工作的棉业专家所言:关中地区植棉业“可谓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惠条件于一炉,故目前关中棉产所以对后方供(贡)献如是之大,实非偶然”[52]。通过农业资源的供给与优化配置,战时陕西实现了棉花品种的更新换代,优良棉种的推广使棉花亩产量与品质均较战前显著提高,尤其是斯字棉成为了陕棉增产的主力军。因此,战时陕棉总面积和总产量虽较战前大幅下降,但在大后方仍保持较大规模和领先地位,故被视为“大后方罕见的棉产盛区”[53]和“后方最重要之棉区”[54]188,在后方棉花生产与供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衰退与发展并存,是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植棉业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