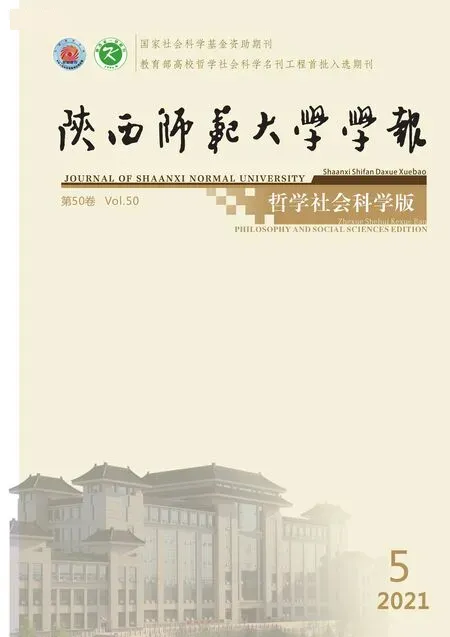学会融入世界:适应未来生存的教育
[澳]阿弗里卡·泰勒, [加]维罗妮卡·帕西尼—凯奇巴, [澳]明迪·布莱瑟, [美]伊维塔·西洛瓦
(堪培拉大学 创意与文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 堪培拉 2601; 韦仕敦大学 教育学院,加拿大 安大略 N6A 3k7;埃迪斯科文大学 教育学院,澳大利亚 珀斯 602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全球教育高级研究中心,美国 菲尼克斯 852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研究和展望(Education Research and Foresight,ERF)工作论文集推出了关于全球教育的批判性政策分析和评论文章,(1)本文作为背景资料,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协助起草将于2021年出版的未来教育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未对其进行编辑。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场。本文可引用以下参考文献:共同世界研究集体,2020,《学会融入世界:适应未来生存的教育》。本文被委托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教育报告,预计2021年出版。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遭受着全球和地方、公有和私有之间边界模糊不清的困扰。工作论文集中的文章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教育、学习和知识进行了概念的澄清和分析,并为教育政策分析师、研究人员、倡导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方案。[1]1-13
一、 适应未来生存的教育
如果人类不能在这场生态危机中生存下来,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没有想象和找到新的方法与地球共存……我们将以一种不同的人类模式前进,或者根本不前进。[2]
我们生活在一个从全新世(Holocene)到人类世(2)Anthropocene,其字面意思所说的“人类时代”,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并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可能是由18世纪末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开始,这与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于1782年改良蒸汽机的时间相吻合。据《自然》杂志2019年5月21日报道,权威科研小组“人类世工作小组”投票决定,认可地球已进入新地质时代——人类世。发生划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地理/生物圈系统,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危机,威胁着我们已知的地球上的未来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3)生态危机威胁地球和人类生命的其他文献,可参见:P. J. Crutzen,Geology of Mankind.Nature, 2002,Vol.415;W. Steffen, P. Crutzen,J.R. Mcneill,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2007,Vol.8。随着我们的碳排放使地球变暖,我们面临着洪水、干旱和火灾加剧的气候变化。[3]随着我们持续砍伐森林、破坏栖息地并减少生物多样性,我们加速了物种大规模迁移和灭绝的发生,并为持续、毁灭性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创造了条件。[4]因为没有想要纠正导致人类世的根本原因(the root causes of the Anthropocene)的意愿,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悲惨的后果。与万普德(V.Plumwood)的观点一样,[2]我们认为,这首先表明我们未能想象出与地球共存的其他方式。
教育与人类世的危机和未来我们无法想象的替代方案直接相关。尽管人类将努力促进教育作为实现可持续生存的关键,但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继续将劳动力供给作为经济增长的优先考虑因素,从而忽略了环境的可持续性。依据笛卡尔的二元论构建的课程体系和教育,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身边的世界并对之采取行动而无须受到惩罚。[5]1-10现实是,世界上“受过教育”的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然而生态系统却最接近崩溃的边缘。这一事实清楚地提醒我们,更多类似的教育只会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4)受过教育的人类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其他文献,可参见:O. David,Hope is an Imperative: The Essential.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2011,p.238;H. Komatsu,J. Rappleye,I. Silova,“Will Education Post-2015 Move Us Towar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in A. Wulff(Eds.),Grading Goal Four.Leiden:Brill Sense,2020,pp.297-321;J. Rappleye,H. Komatsu ,Towa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a Finite Future.Comparative Education, 2020,Vol.2;I. Silova,J. Rappleye,E. Auld,“Beyond the Western Horizon: Rethinking Education, Values, and Policy Transfer”,in G. Fan,P.S. Popkewitz(Eds.),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Zurich: Springer,2020,pp.3-29。面对我们自己造成的多重生存威胁,一切照旧已不再是一种选择。现在是时候应对挑战,并从根本上重构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角色,以便从根本上重新构想和认识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为此,我们提出从现在到2050年以后7项富有远见的教育宣言。这些宣言基于3个前提。第一,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性是一体的。我们是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我们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正在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第二,任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而继续将人类与世界其他部分分离的企图即使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结局都是妄想和徒劳的。第三,教育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关于人类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这需要一个彻底的模式转变:从了解世界以便采取行动到学会融入并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未来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实现这一转变的能力。
二、 2050年教育愿景宣言
(一) 到2050年,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评估和重新调整教育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保留了教育曾经具有的人文主义使命的最佳方面——促进正义,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人类或社会框架之外。
教育的新使命是通过教会我们在受损的星球上怀有敬畏之心且负责任地生活,(5)教育新使命的其他文献,可参见:A. L. Tsing,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2-9;A. L. Tsing, N. Bubandt,E. Gan,A. Swanson(Eds.),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and Monsters of the Anthropocen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7,pp.1-4;A. L. Tsing,“When the Things We Study Respond to Each Other: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Material’”,in P. G. Harvey, Krohn-Hanson, K. G. Nustad(Eds.),Anthropos and the Material.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pp.221-243。以及学会如何通过共同生存[6]1-20来促进生态公平。伴随着生态公平的重构,我们将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教育的人文主义知识传统。我们需要警觉以人为本的思维和行动模式,积极抵制人类例外论的假定,拒绝人类统治地球的危险主张。
随着21世纪的徐徐展开,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剥削、生产和消费不但不可持续,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地球地缘生物圈系统的稳定。相信教育能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已经式微。[7]不可否认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已经被以人类进步为幌子的、短视的、对永久经济增长的痴迷所取代。为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主义项目已经被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议题所左右。
如果联合国(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未能在2030年之前实现时,我们终将承认,它最核心的人文主义认识论无法解决威胁地球生命的一连串生态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通过重申和延续以人为本的认识论和例外论的设想,已使教育自身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6)教育成为问题的相关论述,可参见:A. I. Silova, H. Komatsu, J. Rappleye,Facing the Climate Change Catastrophe: Education as Solution or Cause? Worlds of Education.https:∥www.norrag.org/facing-the-climate-change-catastrophe-education-as-solution-or-cause-by-iveta-silova-hikaru-komatsu-and-jeremy-rappleye/(2018.Accessed 19 June, 2020);H. Komatsu, J. Rappleye,Reimagining Modern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Modern Japanes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ECNU Review of Education,2020,Vol.1。到2050年,我们必须抛弃笛卡尔的二元论,因为这种二元论构建了坚定不移的人文主义信念,即我们的最高理性和有意识的排他性迫使我们与所生活的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分离,并凌驾于此之上。[8]1-30我们也将排斥与之相关的信念,即人类可以无休止地对世界其他组成部分采取行动而不受惩罚——要么利用其资源,要么随心所欲地“改进”其资源。总之,我们将打破欧美国家倡行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桎梏。
为了巩固超越人类的正义观念,并实现教育的新使命,即学会如何与地球共存,[6]1-19我们将寻求生态和谐的替代方案,承认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实体和力量的共同作用和相互依赖。我们将接受西方学者针对在人类世传播的人文主义缺陷的批判,(7)人文主义缺陷批评的相关论述,可参见:K. Gibson,D. B. Rose, R. Fincher(Eds.),Manifesto for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New York: Punctum Books,2015,pp.10-20;D. Haraway,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pp.1-6;B. Latour,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New York: Polity Press,2018,pp.3-8;I. Stengers,Another Science is Possible: A Manifesto for Slow Science.New York: Polity Press,2017,pp.1-8。并将放弃支持“一个世界”框架的欧洲—西方认识论,(8)卡勒等学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可参见:J. Law,What’s Wrong With a One-World World? Distink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15,Vol.1;S. Carney, J. Rapleye, I. Silova,Between Faith and Science: World Cultur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12,Vol.3。虽然这种认识论推动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在寻找“超越西方视野”的过程中,[9]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多元化”框架中。(9)“多元化”框架的更多论述,可参见:A. Escobar,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9;A. Kothari, A. Salleh, A. Escobar, F. Demaria, A. Acosta(Eds.),Pluriverse: A Post-Development Dictiona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pp.4-15;W. Mignolo,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pp.5-30。这些框架与“南方认识论”(10)“南方认识论”的专题研究,可参见:B. Santos,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2014,pp.1-10;R. Connell,Southern Theory.Sydney: Allen and Unwin,2007,pp.1-50。和其他非西方思想传统有关。这些思想传统假定,存在着无限的人类世界和超越人类的世界,这些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而且从根本上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承认,在基于土地的土著关系本体论中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方面,因为土著的认知方式和他们与土地及其所有生物的互惠关系的共生模式为可持续生存提供了古老的蓝图。(11)土著的可持续生存的智慧的相关论述,可参见:M. K. Turer,Iwenhe Tyerrtye: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boriginal Person.Alice Springs: IAD Press,2010,pp.1-6;D. B. Rose,Dingo Makes Us Human: Life and Land in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Cultur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0;D. B. Rose,Country of the Heart: An Indigenous Australian Homeland.Canberra: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2011,pp.1-7;L. Legrange,“The Notion of Ubuntu and the(Post) Humanist Condition”,in J. P. Mitchell(Eds.),Indigenous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 Routledge,2018,pp.40-60;K. Tallbear,Care Taking Relations not American Dreaming.Kalfou: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Relational Ethnic Studies, 2019,Vol.1。
通过学习和教授多元化原则——包括认知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土著关系本体论的智慧以及人类以外世界的生命——我们将扩展正义这一概念,教育实践也将具有无限的包容性。
(二) 到2050年,我们会完全认识到人类是植根于生态系统之中的。我们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生态的产物。我们将消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在生态意识基础上牢固地建立所有的课程体系和教育。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了这样的错觉,即我们在自治的人类社会中生活和学习,这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我们所研究的“自然”生态群落。我们很难完全理解自己是生态圈内的人。起初,它更多的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或部分被认可的观点。在21世纪早期,一些人文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关注科学家的警告,即人类过高的碳排放水平正在引发全球生态系统趋向崩溃,并最终对人类造成威胁。[10]但我们仍然坚信人类智慧能够“解决”或至少“控制”这些问题,就好像我们还有一只脚踏在这些生态系统之外。这一点从长达10年的围绕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人类适应环境还是减缓环境被破坏和恶化的进程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得到了证明。重申诸如生态系统要为人类福祉“服务”[11]1-5等概念表明,健康生态系统对维持人类生命至关重要的全新认识未能说明我们是这些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能停止自我分离,摆脱这样一种生态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给人类提供服务和帮助人类维持生命,因此人类产生了可以“控制”生态系统的双重错觉。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差异仍然是一个难以祛除的障碍,它阻碍了对我们是生态人的认知,[12]1-3也阻碍了我们去全面揭示生态灾难。尽管联合国(2015年)坚持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三大支柱,即经济、文化和环境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以及平衡的,但它们在学科分界上仍然被区别对待。[7]自2015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社会公平有关的目标始终优先于环境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教育主要与社会科学有关,大多数教育者把重点放在人类发展目标上,认为这些目标对纠正集中出现在南半球以及生活在北半球的土著人民和其他边缘民族人民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至关重要,并认为环境目标主要通过科学和技术课程来解决,同时把促进技术修复和优化治理工作作为最终解决办法。
但历史表明这些都是错误的分离和选择。很明显,到2030年,过度发达的北半球开发“被殖民的土地”(colonized lands)和民族的历史模式将会更加根深蒂固。社会不平等差距扩大,环境目标远未实现。此外,那些在南半球生态足迹最少、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负有最少责任的人,却不幸地受到了最不利的影响。如果未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促使人们对隐性的二元论进行批判性地重新评价,因为这些二元论持续阻碍了相互关联且密不可分的人类和环境目标的实现。
当我们最终意识到人类命运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元素和力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时,我们终于接受了生存和学习是生态人的一个方面的观念。[13]在消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界限的同时,我们开始怀着浓厚的生态意识去实践教育。
(三) 到2050年,我们那时已经停止使用教育作为传播人类例外论的一种工具。我们教导人们学会理解能动性是相互关联、集中分布和超越人类的。
由于我们打破了现代学校教育中人类中心论的前提,我们就不再推崇人类例外论及这种理论中最基本的、人类专属的理性和意识能动性的笛卡尔逻辑。这一逻辑使我们认为人类世的等级制关系和“人对自然”的剥削关系是合理的。现代教育系统地践行了人类例外论,将教师和学生定位为能动的、无所不知的主体,将“外面”的世界定位为有待研究和了解的无生命物体。因为教育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曾在人类例外论逻辑支配下接受教育,导致我们仍然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世界不只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随意研究和行动。[14]1-15我们很难跳出人类例外论的逻辑,即通过想出更聪明、更伟大、更美好的“人类拯救”方案来盲目修复我们造成的生态危机。[15]
尽管人类例外论和(新)自由个人主义已被主流教育吸收,但它们从未被普遍接受,它们对于土著和非洲的宇宙论以及神圣而古老的土地论来说非常可恶,(12)人类例外论和(新)自由个人主义对土著、宇宙论、土地论的负效应的相关论述,可参见:D. B. Rose,Dingo Makes Us Human: Life and Land in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Cultur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S. Styres,“Literacies of Land: Decolonizing Narratives, Storying, and Literature”,in T. L. Smith, E. Tuck, Y. K. Wayne(Eds.),Indigenous and Decolonizing Studies in Education: Mapping the Long View.New York: Routledge,2019,pp.24-37;L. Legrange,Ubuntu, Ukama and the Healing of Nature, Self and Society.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2,Vol.44;K. B. Martin, Mirraboopa,Ways of Knowing, Being and Do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s for Indigenous and Indigenist Research.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2003,Vol.76;K. Tallbear,Dossier: Theorizing Queer Inhumanisms: An Indigenous Reflection on Working Beyond the Human/not Human.GLQ: A Journal and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015,Vol.2-3。也与南美地区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和环保运动相对立,(13)人类例外论和(新)自由个人主义与多样性、环保运动相对立的更多论述,可参见:Eduardo Batalha Viveiros De Castro,Exchanging Perspecti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s Into Subjects in Amerindian Ontologies.Common Knowledge, 2004,Vol.3;A. Escobar,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15;W. Mignolo,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pp.5-10。与亚洲哲学传统相违背。(14)亚洲哲学传统与人类例外论和(新)自由个人主义的对立的论述,可参见:A. Abe,“From Symbiosis (Kyosei) to the Ontology of ‘Arising Both From Oneself and From Another’ (Gusho)”,in J. B. Callicott, J. Mcrae(Eds.),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New York: SUNY Press,2014,pp.315-336;G. Zhao,Two Notions of Transcendence: Confucian Man and the Modern Subject.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09,Vol.3;A. Sevilla,Education and Empty Relationality: Thoughts on Education and Kyoto School of Philosophy.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5,Vol.4;H. Komatsu, J. Rappleye,Reimagining Modern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Modern Japanes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ECNU Review of Education,2020,Vol.1。
人类例外论的笛卡尔主义基础也遭到了来自内部的强力批评。自20世纪末以来,逐渐与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大批西方哲学家和理论家开始质疑人类处于最高层的等级制度。他们用类似于“组合”或“网络”的扁平化本体取代了这些等级结构,这种本体由多样化的、具有分布式能动性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组成。(15)扁平化本体的相关论述,可参见:G. Deleuze, F. Guattari, A. B. Massumi(Eds.and Trans),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London: Continuum,1987,pp.1-7;B. C. Latou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2;B. Latour,The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B.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0。他们一起制造了自然/文化“大鸿沟”,[16]1-11使人类、动物和机器之间的分类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给我们呈现出“半机械人”和“自然文化”的混合概念。(16)半机械人的相关论述,可参见:D. A. Haraway,Cyborg Manifesto,Socialist Review, 1985,Vol.80;D.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s.Feminist Studies, 1988,Vol.3。他们揭示了断言人类“主宰自然”的结构二元论只不过是对从属的他人的否认,而后者的能动性也被否认。(17)主宰自然和生态危机的相关论述,可参见:C. Merchant,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New York: Routledge,1996,pp.1-6;V. Plumwood,Feminism and Mastery of Nature.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3,pp.2-10;V. Plumwood,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2,pp.1-5。他们强调所有生命的共生(18)生命共生的更多论述可参见:D. Haraway,“Otherworldly Conversations, Terran Topics,Local Terms”,in S. Alaimo, S. Hekman(Eds.),Material Feminism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7-187;D. Haraway,When Species Mee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p.1-15。以及各种物质之间活跃且能动的相互作用。(19)物质能动作用的相关论述,可参见:J. Bennett,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8;K. Barad,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K. Barad,“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in S. Alaimo, S. Hekman(Eds.),Material Feminism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pp.120-154;S. Alaimo, S. Hekman,Material Feminism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15。总之,他们认为能动性不是人类“独有”和“独立行使”的属性,而是人类和非人类关系及其附属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21世纪初,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加深了人类对能动性是共同的、超越人类的以及相互关联的理解。(20)教育研究作用的更多论述,可参见:C. A. Bowers,Educating for an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Culture: Rethinking Moral Education,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Other Moral Orthodoxies.New York:SUNY Press,1995,pp.1-4;N. Snaza, J. A. Weaver(Eds.),Posthumanis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New York: Routledge,2015,pp.5-13;C. Taylor, C. Hughes(Eds.).Posthuman Research Practices in Education.Houndmills, Basingstoke &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6,pp.1-7;J. Ringrose, K. Warfield, S. Zarabadi(Eds.),Feminist Posthumanisms, New Materialisms and Educati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18,pp.3-9;L. Legrange,“The Notion of Ubuntu and the (Post) Humanist Condition”,in J. P. Mitchell(Eds.),Indigenous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 Routledge,2018,pp.40-60;J. P. Mitchell(Eds.),Indigenous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 Routledge,2018,pp.2-12;T. L. Smith, E. Tuck, Y. K. Wayne(Eds.).Indigenous and Decolonizing Studies in Education: Mapping the Long View.New York: Routledge,2019,pp.1-15;Y. Waghid, P. Smeyers,Reconsidering Ubuntu: On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a Particular Ethic of Care.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2,Vol.2;Y. Waghid,Afric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Reconsidered: On Being Human.New York: Routledge,2014,pp.10-30;W. Zhao,Historicizing Tianrenheyi as Correlative Cosmology for Rethinking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Beyond.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8,Vol.11;K. Takayma,Engaging With the More Than Human and Decolonial Turns in the Land of Shinto Cosmologies: “Negative”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Practice.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2020 ,Vol.1。然而这些超越人类的关于能动性的概念调整在教育政策和学校教育的日常实践中要慢得多。直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人类世的影响真正开始显现,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利用地球的变革力量,因为我们人类无法独自完成保护环境的任务。为此,我们开始了一项重大工作,即依照能动性是超越人类的、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这些特点,从根本上调整我们的课程体系和教育系统,做到不去依靠人类的智慧和技术最终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学会如何将我们的角色转变成为地球上众多生命的执行者、创造者和塑造者之一。
(四) 到2050年,我们那时已经抛弃了教育的人类发展框架。我们将不再拥护个人主义,而是更加注重培养集体主义品质和轻松友好、善解人意的人际关系和超越人类的关系。
主导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人类发展框架是帝国主义按照西方进步和发展的目的论观念“使世界现代化”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关于“进步”的规范性概念被用作普遍化的标准来衡量“发展的”个人、文化、国家这一有缺陷的观念。[17]1-10
在教育领域,发展逻辑最初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儿童研究运动中形成的。该运动呼吁全世界对儿童进行科学的观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心理学成为主导学科,并形成了对“儿童”的普遍理解,产生了若干规范的儿童发展阶段。在这个总体化的学科范畴中,“个体儿童”被认为是在这些阶段中不断改变并从世界中分离和抽象出来的。
到20世纪末,“儿童中心学习”(child-centred learning)已经成为一种广受好评的发展主义观念,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幼儿期和小学课程从儿童的需求和兴趣开始,照顾到每个儿童独特的性格特点。教育促进并支持个体儿童学习者成为自主性强、善于自我调节、充满理性和能动性的学习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儿童或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借鉴了看似“进步的”西方价值观,如民主和个人自由。(21)基于学生中心的学习的相关论述,可参见:G. S. Cannella,Deconstruct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ocial Justice and Revolution.New York: Peter Lang,1997,pp.1-20;R. Jeremy, K. Hikaru, I. Silova,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nd Sustainability: Solution or Problem.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21,Vol.1。几十年来,国际发展机构经常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最佳做法”加以推广,并在很多情况下取代甚至有时完全淘汰其他的教育实践。
随着人类世的影响在21世纪20年代开始显现,教育却并没有让年轻的学习者为他们面临的岌岌可危的生态未来做好准备,因而我们需要一种与20世纪倡导的、已经过时的、崇尚个人主义的人类发展观截然不同的新框架。同时,可持续发展教育也被质疑,因为很明显,所有的“发展”议程都被石炭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和关注点彻底占满。
从2018年开始,一场日益壮大的学生运动吸引了世界各地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宣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一场生态灾难,并要求政府和国家领导人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他们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问题本身。为了未来的生存,学生们呼吁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教育者开始倾听并动员人们给予支持。[18]
在学生的坚持下,我们必须持续地将教育从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双重逻辑中脱离出来,使其回归到生态生存的逻辑中。由于认识到人类以及超越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在人类世中难以分辨,[5]1-30我们将根据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原则重新调整教育,使所有人和物都成为地球生态群落的一部分。
自我的个人主义文化已经成为过去式。当务之急是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品质。[19]1-22目前,教育实践的特点是对“他者”开放,无论是其他人类、物种、土地、祖先,还是机器人或机器。这些开放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令人愉悦和可以修正的观念,即“迎接惊喜、怀抱希望、建立联系、包容共存,并关心新事物”。[20]8
(五) 到2050年,我们将在一个世界里生活和学习。我们的教育不再把“外面的”的世界定位为我们了解的对象。学会融入世界既是一种情境实践,也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教育合作。
教授和学会在一个被破坏的地球上负责任且有尊严地生活是一个全新的使命。这个使命要求我们挑战教育中最基本的主客体分离“二元论” 。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主客体分离的观点一直没有受到挑战。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会(理性的)人类主体了解(外在的)世界。世界被视为是人类研究的对象,人类作为认知主体一直在研究外在世界。在新的使命中,教育者根本不可能继续利用和复制主客体分离的模式。教育者将按照全新的生态意识行事,将人类重新定位为生态内部人,成为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些最早的教育倡议来自幼儿教育领域,超越了从外部了解世界的既定做法。来自共同世界研究集体(22)共同世界研究集体(Commonworlds.net)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人员网络,研究我们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为了共同世界研究集体的利益,这场关于教育未来的讨论由以下作者共同发起: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Affrica Taylor (Affrica.Taylor@canberra.edu.au);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Iveta Silova (Iveta.Silova@asu.edu);加拿大韦仕敦大学的Veronica Pacini-Ketchabaw (vpacinik@uwo.ca);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的Mindy Blaise (m.blaise@ecu.edu.au)。的教育者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21]即学龄前儿童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西方教育的主客体分离和人文主义的假定,他们还没有与世界其他部分相脱离。通过观察幼儿与共同世界中的非人类之间的教育关系,这些教育者开始尝试融入世界、共同合作、超越人类学习的可能性。(23)儿童与人类世的相关论述,可参见:A. Taylor, V. Pacini-Ketchabaw,The Common Worlds of Children and Animals: Relational Ethics for Entangled Lives.New York:Routledge,2018,pp.1-10;V. Pacini-Ketchabaw, A. Taylor, M. Blaise,“Decentring the Human in Multispecies Ethnographies”,in C. Taylor,C. Hughes(Eds.),Posthuman Research Practices in Education.Houndmills, Basingstoke &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6,pp.5-17;M. Blaise, C. Hamm, J. Iorio,Modest Witness(ing) and Lively Sto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Matters of Concern in Early Childhood.Pedagogy, Culture, and Society,2017,Vol.1;A. Taylor,“Countering the Conceits of the Anthropocene: Scaling Down and Researching With Minor Players”,in P. Kraftp, A. Taylor, V. Pacini-Ketchabaw(Eds.),Childhood Studies in the Anthropocene.Discours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Special Issue),2019,Vol.41。
随后,比较教育、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教育者也在努力超越主客体分离的模式,并开始重构学习任务。通过专注于把世界固有的关系作为内在的教学理论,承认教和学不是人类的专属活动,并通过调动人类的好奇心去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终将完成从了解世界到融入世界的伟大变革。
这也意味着我们将采用“情境化”的教学实践,拒绝“超越的承诺”,[22]因为这种承诺只存在于我们所了解的世界。通过情境教育,我们坚持融入受损的地球以及和所有居住者一起了解地球面临的“麻烦”。[6]1-16我们以人类属于世界一部分的视角、怀着具象化的愿景以及在认识到我们并非无罪的前提下来发言和思考。[22]学会融入世界使我们能够与所面临的矛盾和危险和睦共处,并对令人不安和充满暴力的因素作出反应,诸如人为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和许多物种的灭绝。教育者和学生都将意识到,我们的行为都事出有因。我们知道要对身边人和我们共同居住的环境负责。
最重要的也许是,人类还没有失去希望。情境教育的主张已经成为对“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坚持。[22]很长时间以来,人类已经从自以为是地推进了西方“全民教育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23]向致力于将情境学习作为一种手段去构建更宜居的世界转变了。我们正满怀热情地与居住在同一个世界的物种一起共同学习,并将其作为重建世界的新模式。
(六) 到2050年,我们重新赋予了教育的世界政治职责。这个职责远远超越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的普遍性和人本位主张。
教育者将完全拥护世界主义,承认多元性,或承认许多不同世界的共存。我们将逐渐放弃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被广泛接受的具有人道主义意味的“教科文组织通用语言”,也将摒弃最近对于“新人文主义”的重申。此种人道主义使命不仅未能实现世界和平,而且还揭示了“解放人类的人道主义观点”根本不足以界定地球上的所有居住者。[24]457世界主义的教育方法不是从多个角度揭示单一的世界,而是既承认相互联系的世界的多样性,也承认我们包含在由不同知识、实践和技术构成的多物种生态中。在“世界主义”一词中,“世界”是指“由多样、不同的世界构成的未知,以及它们最终能够实现的联系,而不是企图实现终极、普世的和平”。[25]995
世界主义原则使我们能对“归属”的含义进行更为广泛的定义,它包含了全人类以及一切生物和非生物——因此包含了超越人类的世界。这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和实践来自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不仅打破了普适性原则,而且使我们能够继续通过人类网络和超人类行为者来完成集体组装共同世界的任务。[26]1-10观察、融入和关注成为世界主义教育模式的关键,因为共同的世界不会先于它们的联系而存在,而是需要在人类和人类之外的事物存在之后“慢慢形成”。[24]457世界主义教育实践是“世俗化”“与世界一起”或“融入世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4)融入世界的教育实践的更多研究,可参见:D. Haraway,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p.40-50;D. Haraway,The Harawa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4,pp.1-16;D. Haraway,When Species Mee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p.20-40。
虽然这种新型教育具有深层次的联系,但它并不依赖于一个单纯的关系概念。相反,它关注的是与极度不平衡和不可调和的差异共存的伦理与政治,在这些跨越性别、种族、阶级、物种、机器和物质的“超越的边界”和“强大而禁忌的融合”中认识我们的盟友。[27]这种学习需要一种横向思考,即“对人类在其他生物中的不同构成和不同定位所扮演的角色负责任的同时抵制人类例外论”。[28]136几十年后,当我们学会与动物、物质和机器相融合时,我们同时也就忘记了如何“做人——西方标志的化身”。[27]教育空间由此转变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多元宇宙”[28]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个宇宙中,所有人和物都可以在创造多元宇宙的过程中做出贡献。
到2050年,世界主义实践将广泛渗透到教育、文化和政治等领域中,以至于联合国成员国不再满足于“只有人类……是俱乐部唯一可接受的成员”。[24]257在2050年9月20日举行联合国大会后,几届会议都将致力于全面审核联合国以人为本的逻辑局限性,并将探讨推翻联合国的人类中心逻辑和改变世界主义的狭隘忠诚所必需的哲学和组织变革的紧迫性。经过激烈讨论,委员会将以联合国的名义一致决定用“自然文化”取代“国家”,[29]这标志着全面接受将世界性原则作为在受损的地球上使万物尽可能和谐生存和消亡的实践和艺术。
(七) 到2050年,我们会优先考虑在这个受损的地球上施行集体修复伦理,以达成未来生存的教育目标。
我们将围绕地球的未来生存对教育进行彻底的重新构想和调整。我们将重新定位教育在共同世界中的实践功能,因为我们不再将社会教育和环境教育区别对待,也不再将教育作为一种专属于人类的活动。致力于在受损的地球上寻求代际和物种公平的激励下,[5]1-15我们将教育的目标从人道主义转变为生态正义。与所有这些转变相一致的是,我们将采用一种全新的道德模式,即一种集体的、超越人类并且具有修复作用的道德模式。这些新愿景和伦理将使“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旧观念彻底成为过去式。
到21世纪2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战略是失败的。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巴黎协定宣告失败,由学生发动的持续已久的全球气候抗议行动以及国际地层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ICS)关于人类世的官方声明[30]都使人们无法否认这一明显事实,即任何形式的石炭纪经济发展都阻碍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即使是那些提倡可持续发展教育却不把可持续发展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的教育项目也仍然将自然与文化分离开来。那些基于环境管理原则的项目仍然将人类作为环境的“守护者”和“保护者”[31]而将其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同样,有关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绿色一代(202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以及凭借人类智慧找到技术解决方案来最终“拯救”地球的假设,也是基于人类例外论的错觉。这类项目和愿景并不能应对新时代的关键挑战,即实现并维持稳固的生态图景。在这种图景中,我们将自己完全重新置身于环境中,并与环境永不分离。[32]1-5
通过放弃人类拯救环境的宏大幻想,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更适中的目标上,即协同致力于人类和超越人类的繁荣,并集体修复受损的共享世界,哪怕只是部分修复。我们终将吸取教训,若要实现生态公正,必须考虑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包括考虑他们的所有特性。(25)共享世界的更多研究,可参考:D. B. Rose,Wild Dog Dreaming: Love and Extinction.Charlottesville, V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1,pp.20-40;D. T. Van,The Wake of Crows: Living and Dying in Shared World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pp.1-15。当认识到我们在寻求生态公正的过程中与地球其他物种相互关联这一价值之后,我们就会站在一种新的伦理立场上,即从根本上否定人类具有主宰和控制地球的优势。这种伦理立场将对联合国产生深远影响。联合国一旦接受了它的“自然文化”新名称和世界主义原则后,就会关注世界内在联系的持续性,并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破坏中共同修复什么样的世界?很明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融合的过程中找到,因为我们都在集体重组世界。[6]1-18
三、 学会融入世界
在我们富有远见的宣言中,预测到2050年,围绕人类世的生存,将会对教育进行彻底调整。我们将专注于未来生存,因为我们知道生态灾难是人为的,这个事实正在迅速颠覆人们对人类进步和发展的盲目信仰,教育无论以何种形式维持这些危险的假设都将落空。这些假设主要包括:教育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人类能够学会更好地治理环境,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宝贵资源;教育可以培养人类的智慧,人类可以开发新技术去解决我们造成的环境灾难并拯救地球。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人类世不仅预示着会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而且也证实了人类和自然历史、命运及未来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把人类世作为一个长鸣的警钟。[32]1-9教育能够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主张只不过是基于人类虚拟分离和人类例外论妄想主宰地球的危险神话。[8]10-25人类世对教育者的召唤和学生对紧急气候行动的恳求是相似的。如果教育者和学生想要拥有未来,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未来生存的愿景从根本上与人文教育进行决裂(无论新旧)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转变:从倡导人文主义到践行生态意识;从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到努力实现生态公正;从将人类理解为社会人到将人类理解为生态人;从维护人类的专属权到承认人与万物之间存在主观能动的相互关系;从鼓励个人发展到培养集体主义品质;从把教、学看作人类独有的活动到把世界的内在联系理解为教、学固有的联系;从教学生(作为主体)了解世界(作为客体)到学会融入我们共同的世界;从假设普适性的立场和标准到考虑多元化视角;从倡导人类的世界主义到理解超越人类的世界性;从培养人类的环境管理能力到参与超越人类的集体修复伦理;从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控制或拯救世界到学会如何融入世界。
我们确信,要实现这些转变的最大挑战,是将教育从构建人文主义知识传统和教育的笛卡尔二元论中分离出来,即从诸如精神和身体、自然和文化、主体和客体等分离出来,确保我们永远只能从安全而有利的外部了解世界。这些二元论强调外部世界“就在某个地方”,与我们分离,被动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管理”。换句话说,这些二元论将我们与生态存在感和归属感分离开来,阻碍了我们需要生存下去的生态意识的形成。
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让人类放弃崇高的自我幻想并回到“现实”中来。[33]1-10在充分意识到人类是地球上许多相互依赖的生物、实体和力量之一后,就应该坚决并彻底地以共同世界为基础重新将我们塑造为地球生物。只有基于这些超越人类的共同基础,我们才能揭示在超越了使人类最先陷入混乱的以人为本的自负和短见之后,教育意味着什么。只有在这些共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地球上所有的物种一起汲取未来在地球生存迫切需要相互协作和相互修复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学会融入这个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将永远对它充满感激。
四、 余 论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世界中,《教育研究和展望工作论文集》为有关教育与发展的全球辩论做出了贡献。它们为政策分析人员、学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广泛的服务。该系列文件还提供了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教育未来倡议》框架内关键问题的见解。
这些文件带有作者的名字,应据实引用。这些文件中表达的观点只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观点,也不代表其代表的政府的观点。
[本文由冯用军、何芳、刘凤翻译,具体分工是:刘凤,北京联合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初译);何芳,北京联合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教授(二译);冯用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三译及定稿,通讯译者);江婕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玛丽卢富尔顿师范学院博士生(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