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地方知识与实践:三个民族志案例的比较研究
陈 晋
当代中国民间司法中,在地方层面,有关法的知识与实践,常常与当地的宗教信仰、仪式行动、政治体制等纠缠不清;进一步地,人们对公平正义等问题的实际认知、判断与解决方式,不仅指向当地道德和伦理秩序的生成过程,也指向外部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阿拉伯语中的“哈克”(haqq)、梵语中的“达摩”(dharma)、马来西亚诸语言中的“阿达特”(adat)这些地方术语,其实更接近西方的“正确”(Recht,droit)而非“法律”(Gesetz,loi)概念。(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4~246页。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法律的定义是“通过一个社会组织集团的力量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体制”。(2)[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654页。然而通过长时段的田野调查与细腻的民族志研究,人类学家发现,现实中的法不仅意味着自上而下、抽象的外在规则,更对应千差万别的文化观念和相应的行为模式。
本文基于对三个民族志案例(纳人、阿赞德人、阿除瓦人)的介绍与比较,试图呈现有关法的地方知识与实践在形式上的丰富性,并且探索其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在空间分布上,研究案例分别涉及我国西南地区、中部非洲和南美亚马逊流域;在时间序列上,相关的调查依次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希望展现人类学对法的重要议题(如诉讼、审判、复仇、战争)的长期关切,以及相应的研究视角(如巫术、神谕、魔法、萨满教、仪式)的发展变化。
一、仪式与诉讼
纳人目前分布在四川省木里县、盐源县,以及云南省中甸县(现更名为香格里拉市)、宁蒗县等地,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过着以耕种、畜牧为主的农业生活。长期以来,纳人社会独特的亲属制度和性生活方式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乃至公众的注意。当地的基础亲属和经济单位被称为“支系”(纳语称“lhe”),纯粹由母系血亲组成。传统上,纳人实行男性在夜间走访(sésé)女性的性生活制度。(3)Cai Hua,Une société sans père ni mari.Les Na de Chin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7,pp.93~180.
纳人社会中存在两类处理宗教事务的专家:藏传佛教系统下的喇嘛,以及“达巴”(daba),两者在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喇嘛的生活起居,基本上围绕寺院发生,在纳人家户主持仪式时,他们依赖藏语写成的佛教经典来完成工作。达巴则是高度个人化的职业,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经书,在仪式中唱诵凭心记忆的复杂祷词(相传为古老的纳语),为同胞祈求福祉、祛除病灾。在纳人眼中,达巴熟知支系和氏族(sizi)的家谱、各种神话传说和传统文化,因此普遍受到尊敬。
2003~2017年期间,我在川滇交界的多个纳人村落进行了累计20多个月的田野调查,试图理解达巴仪式实践与当地社会文化的关系。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与多名达巴和当地人合作,记录、解释和分析不同的仪式案例;长时间追随多位达巴师父,系统地学习其唱诵的内容;作为达巴的助手,在实地参与仪式的过程中不断观察、验证和复习学到的知识。在考察过程中,以及随后的材料整理阶段,我逐渐发现,达巴的仪式知识及其实践方式,对于理解纳人社会如何运作有着关键的意义。
在1956年以前,纳人社会长期为土司所统治。在纳语中,这些统治者及其阶级被称之为“sipi”。土司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了维持边疆稳定而推行的地方治理制度,指由朝廷任命和认可的地方社会首领,管理所在地的内政事务。土司的职位常常是世袭的、固定的,跟中央指派的、四处调动的“流官”相对。纳人地区的土司统治历史,可追溯至元代。明代中央政府沿袭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在纳人社会内部,以土司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宗教制度长期存在,并由此形成包括贵族(sipi)、平民(dzékra)、奴隶(er)等阶级的社会结构。(4)Cai Hua,Une société sans père ni mari.Les Na de Chin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7,pp.40~50.
纳语中的“dhudzo”指“诉讼”。在历史上,百姓之间如果有了冲突,需要到辖管土司面前陈诉、解决,履行一套“上衙门”的程序。跟土司制度一样,这一诉讼制度在纳人地区实施了数百年时间。当地人至今采用这一说法来指称现代司法活动。
关于土司诉讼的细节,《木里县志》中有如下描述:
解放前木里百姓的诉讼,须向衙门里大小官员和各级头人呈送叩头银子……官越大,所呈叩头银子越多,直到最后呈送叩头银子(通常为数两至十数两)与土司,始得向土司哭诉状情……凡人命大案,在衙门最底层天井中设立公堂……人犯过堂取跪审方式。案情稍轻的在衙门二楼设堂……凡审犯官则在衙门三楼设堂……只有极少数的重大案件才有大喇嘛(土司)亲自审理。(5)木里藏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木里藏族自治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0~671页。
在目前可观察到的达巴仪式行为中,“木卡布“(mukrabu)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纳人传统的诉讼生活。该仪式通常以氏族为单位举行,由达巴主持,目的是将各种污秽从纳人家中驱除出去。举行时间在农历年尾或葬礼的最后一天,持续时间通常为十多个小时。根据不同场合,“木卡布”仪式可分为两种:一种称“挖肥木卡布”(kraiguamukrabu),举行时间在每年农历十一月,伴随每年一次、将牲畜棚圈中积累的肥料运到园地的积肥行为,目的是净化家屋、迎接农历新年;另一种称“死人木卡布”(hingshimukrabu),举行时间在葬礼的最后一天,目的是在送出棺柩后,祛除家中的各种不洁,特别是大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员所产生的闲言碎语、矛盾冲突,从而保证后续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两者的程序稍有不同,但关键步骤一致。
在“木卡布”仪式中,达巴驱逐的污秽以各种形象出现,它们被统一称作“恶灵”(tsi、tsikrua或tsikruami)。纳人的恶灵种类繁多,每种都有特定的来源、形态和脾气性格。其中代表“流言”的“木卡”(mukra)是达巴在仪式中重点驱赶的恶灵,这也是“木卡布”仪式名称的由来(“bu”指“仪式”)。在当地的汉语方言中,“mukrabu”也被翻译为“打口嘴”,其中的“口嘴”即对应“流言”,“打”则对应“驱赶”。(6)在口语中,纳人常以“打”(la)指代对恶灵的“驱逐”(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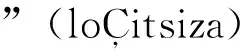
为了和无处不在的恶灵作斗争,达巴在“木卡布”仪式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胜利:首先,他清洁仪式现场、确保仪式效果不受到污物的干扰;继而,他邀请山神和自己的保护神降临,并请求他们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协助自己、加强法力;接下来,达巴开始逐一跟恶灵对话,这包括教育其基本的行事道理、诉说恶灵的诞生来源、展示力量恐吓恶灵、讲述神话史诗等等。漫长的对话过程结束后,达巴要求恶灵离开。他先是送出礼物,然后令其起身,最终将之送出至室外。恶灵在达巴的指挥下被纳人押送上路,翻越重重山头,一直赶到世界的尽头。在这一切完成之后,达巴将恶灵回程的路封死,确保它们不再回来。在“木卡布”仪式末尾,达巴向各个方向投出木箭、石头等武器,打击分散于四面八方的恶灵。他同时念诵经文,祈求该支系来年不会卷入任何的诉讼案件中。在一切完成之后,达巴烧香感谢神灵的帮助,并庆祝仪式的成功。(7)对木卡布仪式过程的详细分析见陈 晋《唱诵、仪式行动与仪式过程:以纳人达巴的“木卡布”仪式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支系、氏族乃至村庄之间的口角、摩擦、争吵,极易引发纠纷与冲突。流言、辱骂等行为,往往直接引发民间的诉讼案件。在这一意义上,达巴在“木卡布”仪式中面对的正是纳人社会中持续存在的问题。通过在仪式中驱逐恶灵,达巴将各种可能引起社会冲突的因素象征性地排除出支系,从而避免了诉讼的产生。仪式化的复杂操作和安排,为纳人可能面临的道德和法律风险提供了解决方案。
二、巫术、神谕和魔法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以其对苏丹南部努尔人(Nuer)和相邻阿赞德人(Azande,为Zande的复数形式)的考察而闻名于世。首次出版于1937年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Witchcraft,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基于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26~1930年期间的三次田野调查写成。
阿赞德人是生活在中部非洲的民族。他们居住在热带稀树草原上的树林或热带雨林的边缘,靠耕耘土地、捕杀动物、采集野果等经济活动为生,在手工艺品制作方面亦有高超的技能。赞德地区分布有许多由贵族统治的王国,王国又划分为省,各省长官通过在各个地区的代理人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
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巫术、神谕、魔法等貌似神秘的现象,实际上构成理解赞德社会生活的钥匙。这些观念和实践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深入到了当地人的思想和日常行动中,从而体现出社会功能的一致性:
我们在观察他们日常经济和社会行为的时候,惊奇地发现神谕、魔法和其他的仪式表演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很大部分……民族学家并不需要刻意寻找神秘概念和仪式实践,他们从日常的各种典礼、争吵、司法案例以及其他社会情景中,就能获得有关神秘概念和仪式行为的信息。(8)[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6页。
在赞德文化中,巫术——即赞德语中的“曼古”(mangu)——是巫师体内一种器官性和遗传性的物质。它可以通过尸体解剖的方式取出,也可以从父母的一方遗传给与之同性别的所有孩子。尽管具有物质基础,巫术的功能却是精神性的:在施放巫术时,巫师总是隔着一段距离把其“射”在受害人的身上,后者身体器官的精神部分便被前者巫术的精神部分所掠夺,并且被带回给巫师。随后,巫师伙同其同伴将果实——受害者器官的灵魂——吞噬下去,造成受害人生病、死亡或者遭遇不幸等各种后果。
阿赞德人认为,巫术源自人们心中常常燃起的仇恨、嫉妒、贪婪等强烈的反社会情绪。这意味着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巫师,而且巫术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施放。事实上,阿赞德人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提及巫术,它被认为是人们可能遇到的一切不幸事件的根源:不论是人生病、死亡、农作物歉收、发生意外,乃至走路时不小心踢到木桩,当地人都将之解释为“被巫师施放的巫术所害”。不过巫术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危险和不幸本身,它起到的作用,更多地是将原来就存在的危险和不幸在特定情境下,跟特定的受害者联系起来。正如路上的木桩本来就在那里,是巫术使人一时看不见它、踢到它,从而脚趾受伤。因此,阿赞德人把巫术称为“第二支矛”(umbaga),以表明它不是迫使人们限于危难的直接因素。例如当某人被大象伤害致死时,阿赞德人说大象是第一支矛,巫术是第二支矛,两者共同杀死了这个人。
由于巫术是一种公然存在的冒犯行为,阿赞德人被迫采取种种抗击手段,以抵御和限制巫术。其中,请教神谕是最为常见的办法。阿赞德人把神谕比作欧洲人的纸张和书本,认为它能起到指导人类趋利避害的作用。毒药神谕即当地人口中的“本吉”(benge),是赞德社会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受信任的一种神谕。其实施的方式为:要提问的人先给鸡喂食一种毒性植物研磨制成的粉末,随即以神谕为提问对象,说出自己的问题;根据鸡吞食毒药后的症状,特别是其生死,人们就能获知神谕给出的答案。
赞德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活动(婚姻、经济生产、司法、仪式,乃至重大的个人事务)均要通过毒药神谕的批准才得以进行。尤其在赞德法律程序中,每个人都要使用毒药神谕:“要了解赞德法律程序,必须清楚地知道毒药神谕是如何操作的。我们知道现在的法律程序在原则上必须有证据、法官、陪审团和证人,而过去毒药神谕单独承担了这些角色的绝大部分内容。”(9)[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7页。
有两类案件涉及使用毒药神谕:巫术案和通奸案。其中巫术案等同于谋杀案,因为在阿赞德人看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死亡,所有类型的死亡都是被巫术谋杀的结果。这构成赞德法律程序的基本出发点。与此同时,只有当巫师真正地杀死人时,人们才能在法庭上对之采取法律措施,否则将无法通过司法程序索要任何赔偿。在处理巫术案件时,被巫术杀死的受害人亲属,把可能施放该巫术的巫师名字告诉亲王,亲王则把这些名字放在自己的神谕前进行确认。根据毒药神谕的结果,亲王便可裁定被害人亲属是否可以向巫师复仇或者是索要赔偿。
至于通奸案,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怀疑妻子有奸情的丈夫当场发现情夫的几率非常小,他向亲王提交的唯一确切证据,通常也是通过毒药神谕所获得的。丈夫虽也可以在亲王面前强调其他证据,但原则上他有了神谕的判断便不再需要其他依据。从被指控者的角度,神谕测试同样得到拥护,因为赞德妻子常常在丈夫的逼问和暴力下说出无辜男子的名字,以保护自己的真正情夫,这时无辜者只有通过神谕的裁定才能洗刷罪名。即便妻子本身清白,她也只有通过神谕的结果才能捍卫自己的忠贞。
有趣的是,阿赞德人认为,通奸和巫术行为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正如巫师暗地里派出其灵魂迫害他人那样,通奸者悄悄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来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两种行为都难以被察觉,却又都在社会中频繁地发生,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打击和限制它们,人们需要借助毒药神谕来揭示其存在。
总之,毒药神谕体现出了赞德社会中的法律原则,以及当地人如何认定司法证据的问题。对此,埃文斯-普里查德写道:
我们这些不相信毒药神谕的人会认为我们建立的法庭才是公平的,因为它只认可我们认为是证据的证据……而阿赞德人则认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仅和案件本身真正有关的证据才是证据这一观点,也不能够接受掌管司法的亲王舍弃信仰、照搬欧洲人的法律原则,因为这些法律原则根本不符合赞德习俗。(10)[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8页。
关于阿赞德人在亲王面前使用毒药神谕、完成法律程序的具体过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亲王有两位正式的操作者来监管他的毒药神谕。他们大概工作1个月,然后回家和妻儿团聚,其位置有人取代。这些人负责监督毒药的准备工作,把亲王咨询的问题放在神谕前面,最后把神谕的答复告诉亲王。操作者们必须完全可靠,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亲王神谕的威望及法律的纯净。如果他们违背了禁忌,无辜的人就会被判有罪、有罪的人被判无罪,亲王的权威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反过来,如果神谕裁定某人会死,后来那人果然死了,则神谕的真实性和操作者的德行之高都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在赞德地区,神谕的判决得到了国王政权的全力支持,而国王自己的神谕判决就是案件的最终判决。历史上,偶尔有些案件要经过省区长官的神谕判决,然后再放到国王神谕面前,而后者可能宣布前者给出的判断是错误的。此外,如果有人的神谕指控涉及惩罚和赔偿,而案件又没有得到国王的神谕批准,那么这个人终究将不能执行其指控。所以在阿赞德人的法律纠纷中,毒药神谕的权力就是国王的权力,两者实质上合二为一。
最后,请教毒药神谕所使用的问答体系并不复杂,通常包括两次毒药测试,两次测试的结果必须相反,神谕的答案才有效。如果在第一次测试中鸡死了,那么用于第二次测试的鸡必须活下来;如果第一次测试的鸡活了下来,那么用于第二次测试的鸡必须死。一般来说,神谕在第一次测试中杀死鸡、在第二次测试中让鸡活下来,意味着给出了肯定回答;反之则意味着神谕给出了否定回答。
当毒药神谕给出有效的结论时,阿赞德人便将鸡的翅膀砍下,后者成为神谕给出判决的有效凭证,可用于在别人(包括亲王和巫师)面前出示。
为了抗击无所不在的巫术以及巫师,阿赞德人诉诸于神谕,以避开危险、揭发巫师的真实身份。进一步地,为了惩治巫师,他们使用魔药、施放魔法(ngua),使之不能如愿冒犯他人,或者遭到惩罚。在众多的赞德魔法中,涉及死亡的复仇魔法最具破坏性。如前所述,赞德文化中的死亡都跟巫术有关;为了替死者报仇,阿赞德人有时会使用复仇魔法来杀死凶手。在此情况下,复仇魔法被公认为是一种“好的魔法”,能准确地找到并杀死凶手。人们会说它“判决公正”(pe zunga),相当于表扬它“主持正义”,如同他们赞美赞德国王的公正判决一样。
综合所述,可以看到赞德文化中的法律问题,实际上同时涉及巫术、神谕和魔法三种体系。三者彼此联结,如同埃文斯-普里查德说的“三角形的三个边”那样,共同推动阿赞德人司法判决程序的展开。(11)[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98页。在赞德社会的死亡案件中,巫术信仰使之成为一场隐蔽的谋杀,从而牵涉到可能的凶手;请教神谕则可以锁定凶手、揭露其身份,以便展开复仇;最后,实施魔法可达到复仇的目的,完成判决。
三、萨满的复仇
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文化,是现代人类学长期的研究热点。分布于亚马孙河流域的众多族群,更是欧美学者所青睐的田野调查对象。其中,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出版于1993年的《黄昏之矛:上亚马孙地区日伐赫人的关系》(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 Relations jivaros, Haute-Amazonie)是一部特殊的作品。与作者之前的民族志相比,(12)See Philippe Descola,La nature domestique.Symbolisme et praxis dans l’écologie des Achuar,Paris: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1986.《黄昏之矛》基于德斯科拉于1976至1978年对阿除瓦人(Achuar)的调查,混合了丰富的个人体验,带有自传性质。用德斯科拉自己的话说,写作本书是为了向公众展示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搜集信息、对材料展开分析、并最终获取知识的过程。(13)Philippe Descola,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 Relations jivaros,Haute-Amazonie,Paris:éditions Plon,collection Terre humaine,1993,pp.443~444.因此,该书可看作是向其老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享誉世界的传奇作品《忧郁的热带》的某种致敬。
阿除瓦人居于亚马孙盆地西北部帕斯塔萨河(Pastaza)流域的茂林深处,属于日伐赫人(Jivaro)的4个分支之一,另外3支分别是舒阿人(Shuar)、阿瓜忽那人(Aguaruna)和环比萨人(Huambisa)。其中,舒阿人和阿瓜忽那人相对为外界所知,特别是舒阿社会的“猎头”以及将猎来的头颅制作为干缩物的风俗。阿除瓦人的人口比舒阿人和阿瓜忽那人更少,不到5千人。他们的经济活动以种植和渔猎为主。
和赞德社会相比,阿除瓦人的社会组织可谓松散。他们的家户容纳一夫多妻式的父系核心家庭,有时也包括若干关系亲近的亲属成员。家户之间保持相对的距离,每家都有自己的住处、花园等,在经济上也保持独立运作。每个阿除瓦部族由十几个家户组成,部族内很少爆发矛盾冲突。跟部族和家户内的宁静状态相比,阿除瓦部族之间乃至阿除瓦人和其他族群之间,则长期处于战斗和激烈冲突的局面中。
阿除瓦语中的“么色”(meset)一词可翻译为“复仇”。作者将其解释为:“正常情况下互为亲戚、说同一种方言、互相了解对方,乃至于偶尔互相拜访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恶化。”(14)Philippe Descola,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Relations jivaros,Haute-Amazonie,Paris: éditions Plon,collection Terre humaine,1993,p.349.笔者自译,下同。阿除瓦人部族间的复仇冲突,通常在血亲和姻亲之间展开,其触发点包括妻子不堪忍受坏脾气的丈夫而离开,寡妇不顾兄死弟及的传统而另结新欢等等。复仇发生时,阿除瓦社会爆发大规模的喋血战斗,因为敌对的双方又会再呼吁自己的婚姻联盟加入战斗,从而使得复仇牵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和族群间的冲突相比,阿除瓦人谈论他们和舒阿人等其他邻近族群之间的战争时,使用的词汇包括“一场杀戮”(maniakmu)、“一次举矛”(nanki jukimiau)等等。这类敌对是永恒的,跟复仇时存在调解机制、可能暂时停战不同。阿除瓦人强调在针对邻近族群的战争中,不存在任何消除敌意或是通过赔偿而休战的办法,这便意味着这类敌人无法成为哪怕是暂时的盟友。
阿除瓦人的族群或部族冲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触发或强化的因素总是和“萨满攻击”(tunchi)有关。萨满教是阿除瓦文化中的核心元素。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迈克尔·哈尔奈(Michael Harner)对舒阿人开展田野调查,随后出版了《日伐赫人》(The Jivaros)、《萨满之路》(The Way of the Shaman)等著作,引发公众对亚马孙印第安人萨满文化的强烈兴趣。但是在德斯科拉看来,哈尔奈的宣传反而阻碍了对日伐赫社会的正确理解,“因为缺乏对日伐赫语言的掌握,以及缺乏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哈尔奈)出版的著作更多地是一部信息汇编,而不是真正的人类学分析……他甚至没有展示出舒阿社会如何运转的基本原则”。(15)Philippe Descola,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Relations jivaros,Haute-Amazonie,Paris:éditions Plon,collection Terre humaine,1993,p.29.
在《黄昏之矛》中,德斯科拉记述了一次具体的萨满治疗过程,以呈现阿除瓦人的萨满信仰及其实践特色。敦奇(Tunki)是一位阿除瓦语中的“uwishin”(萨满)。有一天,他的朋友、表兄弟卫随(Wisui)前来找他,声称自己的肝部疼痛不已。不久前,他梦到过一些小鸟飞来啄食他的胸膛,并且穿过肋部进入其身体。这让卫随确信,疼痛实际上来自某个敌对萨满的攻击。于是,敦奇接受了卫随带来的烟草以及专用的致幻剂“那达慕”(natem),开始为其治疗。
在服用了致幻剂和吸食了大量烟草后,敦奇挥动起乐弓,使其发出嗡嗡的响声。伴随着这种单一、重复的节奏,他慢慢吟唱起歌曲(anent)。其歌词节选如下:
我,我,我,我使我的镖刺入/我,我,我,我身处和谐之中/我使我的Iwianch精灵显现/我使他们穿越标枪的屏障/我使他们跨过箭的墙/我让他们立即出发/我给他们让出道路/就以这种方式,我吹,我,我,我/投出我吹的镖/吞没一切,渗透一切/……/Tsunki,Tsunki,我的精灵,我召唤你/给我猛烈地开出一条道路,我吹,我吹/……/如同河卷走它的岸堤,我用我的波涛淹没一切,到处泛滥/尽管此处我静止不动/……/虽然镖嵌入得很深,我吹着,还是一下子把它给拔出来/一边开路前进,我一边吸引这你体内聚集的所有外来之物/……/在你痛苦的头颅中,在你疼痛的头颅中/你的痛深嵌,我将它狠狠拔出/使你完全恢复,我唱啊唱,我吹啊吹。(16)Philippe Descola,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Relations jivaros,Haute-Amazonie,Paris: éditions Plon,collection Terre humaine,1993,pp.350~351.
敦奇的歌唱中出现了大量的萨满文化元素。首先,在致幻剂、烟草和单一旋律的多重作用下,萨满进入所谓的“恍神”状态;在该状态下,他得以实现“灵魂的旅行”,包括进入患者的身体、去往邻近的地区等等。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和灵魂旅行方式,在许多社会中都有所体现,被认为是萨满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17)See Mircea Eliade,Le chamanisme et les techniques archaïques de l’extase,Paris:Payot,1951.
其次,敦奇在歌唱过程中一再强调自己如何“拔除”卫随体内的飞镖,这里涉及阿除瓦人对萨满特殊能力的认识。阿除瓦萨满的体内存储着普通人看不见的“魔法飞镖”(tsentsak);当意欲伤害某人时,他们便施放这些飞镖,能够隔着很远的距离刺中对方,给其带来伤害。在本案例中,为了治愈卫随,敦奇需要找出敌方萨满刺入其体内的所有飞镖,将其一一拔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敌人的飞镖顺利脱离患者身体,萨满同时需要施放自己的魔法飞镖,以达到“引诱”敌方飞镖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敦奇在歌曲中不断重复“我吹”和“我吸”:在现实操作中,敦奇对着卫随的背部吹出大量烟雾,代表他吹出自己的魔法飞镖,使之进入卫随的体内,随后吸出敌方的飞镖。成功将敌人飞镖拔除后,萨满还将它们纳入自己的飞镖库,日后可以再施放。
最后,敦奇需要召唤他的附属精灵前来帮忙。这些精灵在阿除瓦语中被称作“pasuk”,它们服从于萨满的命令,多数不为普通人察知。敦奇在歌唱中提到了两类附属精灵,Iwianch和Tsunki。前者为人形、颜色深暗,萨满常用它来指代自己掌握的魔法飞镖库;后者生活在水下,形态、行为如同男子,它被认为是萨满魔法力量的来源及其效力的保证。(18)萨满与附属精灵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是人类学的经典议题。代表研究可参见Roberte Hamayon,La chasse à l’ame.Esquisse d’une théorie du chamanisme sibérien,Société d’ethnologie,1990.
通过治疗,以及通过对患者及其亲属的询问,敦奇最终获知了卫随体内飞镖的来源:它们是所谓“箭毒型”飞镖(cucare),施放者是淳处卡(Chunchukia),不久前被卫随的同盟军帕昆(Pakunt)杀害的萨满玛舒(Mashu)的儿子。由于卫随的居住地较远,不在敦奇的保护范围下,淳处卡便选取了他作为攻击对象。现在,通过敦奇的治疗,这一迫害过程昭然若揭:
魔法飞镖和射出飞镖的人之间由很长的银线相连,便于后者远距离控制飞镖,这一联系只有萨满在服用了“那达慕”之后才能看见,——它们如阳光下的蛛网般散发着七彩的光彩。通过跟随着这些银线,以及同时辨别敌方所派出的、保护这些线的附属精灵们,有经验的萨满基本上能够察知侵犯者究竟是谁。(19)Philippe Descola,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Relations jivaros,Haute-Amazonie,Paris: éditions Plon,collection Terre humaine,1993,p.362.
阿除瓦人的萨满教既是维系社会关系不可缺少的基石,也为复仇、战争等冲突行动提供了合法性。这类行动中有一群特殊的人,即所谓的“大人物”(juunt),他们有着突出的个人能力和魅力,可以指挥军团进行战斗。如果说日常的阿除瓦社会处于一种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那么在战时,阿初瓦人则完全以大人物为核心,在宗派性的团结下思考和行动。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事务的重要决定者和战争首领,大人物们普遍拥有更大的花园和房屋,同时也是杰出的猎手。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强,擅长与其他部族、族群对话,以及对公众喊话。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亲属同盟网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大人物倾向于选择来自不同家庭的妻子,嫁出自己的姐妹,并竭力和自己的血亲和姻亲亲属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阿除瓦萨满常常和大人物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具体手段包括交换姐妹、结成亲家,以各自不同的能力(萨满以自己的魔法能力,大人物则是以自己的军事战略能力)来保护双方。
总之,阿除瓦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处理着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的关系。在部族、族群之间高度紧张、常年征战不休的背景下,萨满提供了针对具体个人同时又难以被察觉的高超手段,打击敌人和捍卫自己的社区。大人物则以个人化和宗派化的组织方式,将社会冲突进一步落实为军事打击。透过这些现象,德斯科拉观察到阿除瓦人独特的个人主义哲学:
在阿除瓦人中间,不仅难以见到一种可以高于个人利益的群体性理念,更缺乏实现这样一种理念的威权人物。作为其基础的,无疑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个人主义,它实现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可以说,阿除瓦人把社会哲学中的最高价值放在了实现个人命运上,他们并不关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阿除瓦社区,忘记了过去、也不关心未来,他们驾驭亲属关系以实现即时的利益,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威望。对于那些期待从他人处得到更多的人,阿除瓦人将很快地抛弃他们。(20)Philippe Descola,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Relations jivaros,Haute-Amazonie,Paris:éditions Plon,collection Terre humaine,1993,pp.322~323.
四、结 论
在各自的时空背景下,上述案例展现了当地人如何处理与法相关的问题。在纳人社会,以“木卡布”为代表的仪式化诉讼(或“诉讼化仪式”)与土司统治下的司法诉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仪式专家,达巴既是社会问题的诉说者,也是实际的施动者(agent):借助复杂的口头和肢体表演,他将流言、争吵、辱骂等引发冲突的因素从家户中一步步地排除出去;人、神、精灵三者间的互动构成“木卡布”仪式行动的核心,其背后是精密的知识体系,例如达巴详细讲述每种恶灵的来源和危害,以及人类如何借助神的力量驱赶恶灵,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21)亦可参见陈 晋《多种实践与多重关系:纳人达巴的“古布”仪式》,《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驱邪仪式反映出纳人对传统诉讼体系的模拟(mimicking):在象征层面,达巴在神面前对恶灵的训斥、教育和恐吓,以及最后押送恶灵上路,无一不令人联想起纳人口中的“上衙门”程序。而在社会学意义上,“木卡布”实质上逆转了土司治下的权力关系,即当地人从被统治的一方转变为统治者,从诉讼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诉讼的主动组织者和实施者。这种转变的手段和结果是双向的,既包括法的道德化(moralization),也包括道德的法律化(legislation)。后者意味着地方社会与外部区域、国家甚至制度化宗教力量(如藏传佛教)之间的联合。
阿赞德人对巫术的倚重源自他们对人性的洞察,当地语言中的“曼古”远非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是事物表象下的深层因果联系(causality)。神谕审判进一步将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如谋杀和通奸)的根源,落实在具体的个体和家庭关系上,从而为“魔法反噬”提供充足的理由。在此意义上,赞德文化中孜孜不倦运作的催化剂,实质上是某种常人难以捕捉的或然逻辑,这一逻辑只有借助现实中的政治和司法结构才得以揭示,因为“毒药神谕的权力就是国王的权力”。正因为此,阿赞德人有关法的知识和实践并非绝对的“地方”,而是深深地嵌入宏观的权力网络之中。
在阿除瓦社会,萨满与大人物的联手复仇体现了“个人主义社会”的特征。萨满在治疗仪式中的唱诵实践,形象地描绘了具身化(embodied)个体问题的社会根源,即来自部落内部或外部的“魔法飞镖”,其重点显然在于飞镖尾部所系的、普通人难以察觉的银线。疾病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所导致的,还包括源自深刻的集体裂痕,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才能解决。频繁地举行战争,既需要大人物们杰出的个人能力,更有赖于长期费心建立的亲属关系网络(萨满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此意义上,阿除瓦人的复仇,指向的是某种“超社会结构”,体现为面向当地但不局限于当地的知识和实践体系。
纳人、阿赞德人和阿除瓦人的案例,显然与现代社会的诉讼、审判和执法过程大相径庭。研究者们对道德、政治、军事等相关议题的整合分析,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法的理解,也体现了人类学传统上的整体性(holistic)视角。在全球化趋势下,法律和宗教、现代与传统、国家与社会等矛盾之间的张力正在愈来愈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以致“关于地方性知识和法律多元的概念在学术论著成为时髦的术语,风靡一时”。(22)张世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陷阱》,《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8日。然而,社会文化现象的多样性不能成为人类学或其他任何学科废除比较研究的理由,亦不构成认识论的禁锢或“概念陷阱”。(23)蔡 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的对话》,《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恰恰相反,民族志研究为批判地思考西方语境下的“正当”“律法”等原则提供了大量可能。
我们可以从上述案例中总结和归纳出以下规律:首先,有关法的知识与当地的道德秩序密不可分,人们对规则的认识亦是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伦理化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因此,“法律”和“正确”难以二分。其次,法的地方实践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一基础并不仅仅是地方的,而是区域或国家的,嵌入了宏观的权力网络。最后,仪式(驱邪、神谕或治疗)提供了某种契机,促使当地人运用具体的知识和实践手段去落实和解决潜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