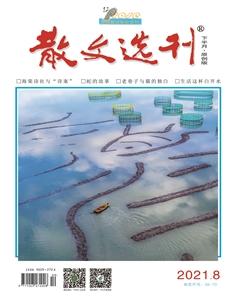堂二哥
向墅平
我常称他“二哥”,比我大20 岁,省去“堂”字,以显亲近感。他十七八岁时就离开老家,到数十公里外的万县城里(今万州)闯荡,在城里开起旅社、酒楼,被当时的新闻媒体赞为“第一批农民企业家”!
“后来,他咋落魄了?”我曾探问过一些知底的长者。“嗐,他人是能干,就喜欢结交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包括一些江湖上的狐朋狗友,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挣的钱,大都花在那些事上了……”这是他们的回答,语气里,满是惋惜,还有几分不屑。“不过,有钱的时候,人还挺义气,也因此在社会上,颇有些人缘。”有人补充道。
据说,他在外跑江湖,还到处以替人办事为名,骗人钱财,渐渐臭名远播。在略谙人事后,我果真亲自目睹过几回,有人闹到他家找他家人要钱的情景。
堂二哥与我发生交集,源于我的一次次升学。
由于我后天坐姿不正,身体发生了一定形变,落下点儿残疾;尽管我从小学开始,学业成绩就一直优异,但总担心这会不利于升学。“弟娃只管好好念书,到时我自有办法。”一次,我家杀年猪,堂二哥刚好路过我家门口,被请进屋一起吃饭时,他一边就着肉块下酒,一边拍着胸脯对我们全家人说,“毕竟,咱们都是亲亲一大家人嘛。”本着对堂二哥“神通广大”的信任,我们全家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也放下了思想包袱,用心念书。我在村小念书,目标是升入区重点中学念初中。那年,我参加全区统考,得了高分。但,还是不放心身体上的问题,怕被拒收(当年的农村人,不懂相关政策)。堂二哥挺身而出,去学校走了一转。果真,我顺利地升了学。不过,我家还是付出了代价:从原本拮据的家庭经济里,抠出一些钱,买了一套烟酒,交给了堂二哥去“打通门道”。至于他如何处置了那套烟酒,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关心的,只是结果。
初中升学考试结束,我报考的是中专。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县农业学校;第二志愿县卫生学校。我的分数,两所学校都够。按录取顺序,我稳上第一志愿学校,何况还有个熟人在那学校招生处上班。“农村娃就是想‘鲤鱼跳龙(农)门,咋还去农校呢?我去卫校找人,把你录了。”堂二哥对我说。
我们相信他的神通,主动给农校的那个熟人打了招呼,不要录取我。接下来,我们一家子就只等堂二哥后面的佳音了。
不久,堂二哥捎回了令我们失望的结果:卫校领导说,上面对所有大中专学校加强了整治,他不敢轻易越线,录取我这个第二志愿!
不过,略作安慰的是,依靠堂二哥的关系,我被转录到县重点中学念高中。
我再度憋一口气,发奋念完三年高中。可惜考场失利,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最终,由“调招志愿”,被当地电大录取。开始,我不肯去读,因为电大毕业不包分配。“你先把书读了,二哥到时替你想办法。”我从他笃定的目光里,看到了希望。
我念的是外贸英语专业。毕业时,学校实行“双向择业”。家人对我的就业满含忧虑,因我的身体带点残疾,怕被一般单位拒绝,何况,又是外贸专业。我们自然把堂二哥,当作唯一可靠的“救命稻草”。起初,堂二哥让我家买了几回烟酒,说是拿去疏通门道。后来有一天,堂二哥一脸笑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信誓旦旦地说:“我去给那单位说好了,只是——”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只是开口要三千块钱。”我瞥见,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恍惚。
三千块钱,对于那时的我家而言是笔大数目。在我们把好不容易凑好的钱交给堂二哥前,院子里人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他哦,听说他在外面骗了好些人。”但,我们最终下赌注一般,把钱悉数交给了堂二哥。一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来,毕竟我们彼此是堂亲,料他不会骗我们的!
此后,我就在家安心等候佳音。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却迟迟不见那纸通知书到达。我在酷暑天听着屋外那树上知了声声的鸣叫,心里觉着特别烦躁。“八成是被他拿去挥霍了,你们被骗了。”很快,院子里就传开来这种猜测。我们终于也沉不住气了,就试着问他咋回事,可他只是闪烁其词,并无明确回答。
我们更疑心那笔钱的不正当下落处。于是,父亲亲自出面,带着我和堂二哥一道,去城里核实情况。永远记得,在热浪扑面的大街头,堂二哥背着手,若有所思地走在前面,我们父子跟在后面。我心底涌起阵阵浪涛:我的命运,难道就真的掌握在前面那个城府幽深的中年男人手里吗?他究竟要把我的人生之舟引向何方……
堂二哥没有把我們引向他承诺过的那家进出口公司,到最后我都没有进那里去看过一眼。他一直背着手,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像一个神秘莫测的引路人。直到他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迎面相逢,才听到他开口说话。
原来,老者是堂二哥当年开餐馆时结交的一位某部门干部,现已退休在家。后来,通过他的关系,我在县教委谋得了一个教书的名额。尽管我从来没想过要教书,况且要被分配到一所远离家乡的偏僻山村学校,可父亲一席话让我定了心:“孩子,认命吧,有份正式工作就不错了,总比爸和土地打交道强,至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我走向了命运安排给我的那个地方。
我后来在城里安了家,妻子贤惠,儿子争气,一家子过得幸福无比。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和堂二哥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偶尔在城里街上,远远望见堂二哥:头发也渐渐白了,脊背也略有佝偻,走起路来,也有些滞缓,再不复当年那个江湖气浓厚的“二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