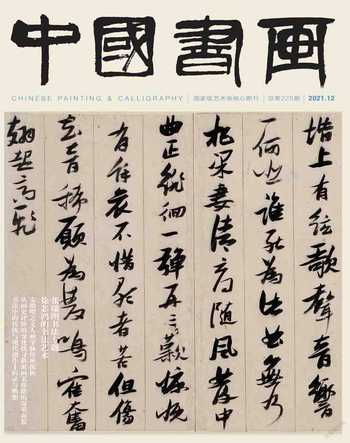墨妙好手,还是狂态邪学?
赵琰哲



在明代前期的绘画史中,浙派是继院体之重要的艺术流派,也是明代产生的首个地方画派。戴进所开创的“浙派”与吴伟所开创的作为浙派分支的“江夏派”在明代初期艺坛声名甚著,追随者众多。张路作为学习吴伟画风的浙派后学,一方面笼罩在戴进、吴伟的盛名之下,另一方面处于吴门文人画风逐渐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中。因其职业画家的身份与风格放逸的笔墨,使其在画史上更多地背负了“狂态邪学”的恶名。但在“日就狐禅”“衣钵尘土”的画史评价之外,张路是否还存在其他面貌?我们不妨通过考察画史记载来一窥究竟。
一、墨妙好手:16世纪中期之前有关张路的记载与评价
《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浙派画家张路的基本信息:“张路,字天驰,号平山,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生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工画山水、人物。”〔1〕遗憾的是,书中所汇集的史料并没有收集与张路同时期之人的著述记载,也没有涉及当时人对张路人品及画艺的评价。但这并不表示与张路同时期之人没有对其进行评述。恰恰相反,如果检索资料,会发现在张路主要活动的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上半期,有多位文人士大夫甚至明室宗室都与张路有交往,并在其诗文著述中对张路的清高人品与卓绝画艺多有提及。
张路曾为早其两年出生的文人官僚杭淮〔2〕图绘《梧凤图》。画中以梧桐比喻君王,以凤凰比喻文士。画成之后,杭淮作诗一首—《酬张平山梧凤图》,在诗中赞扬了张路的画艺精妙:张子墨妙今所无,寒天写赠高冈图。梧桐萋萋凤哕哕,海天红日升渠渠。凤兮联翩五彩色,梧桐霄汉双撑扶。眼前焕烂见此物,吾恐草堂非所居。忆昔周时大雅歌,梧桐比君凤比士。君道昭兮臣德彰,明良相须实相倚。只今遭逢圣明朝,子之意匠无乃尔。下阶舞蹈日月光,吾为作歌谢张子。〔3〕
生年略晚于张路的明“前七子”之一李梦阳〔4〕,曾买绢请张路为其兄长作画,用以祝寿:“复闻张生善山水,买绢请扫青嵯峨。”李梦阳在祝寿歌中不仅赞扬张路为“大梁好手”,还描述出张路作画的神态—“当堂掉臂扫丹墨,倏忽老面开生色”。从李梦阳的叙述中,颇能见出张路运笔急速、酣畅淋漓的作画风格。此画绘成之后悬挂于墙壁之上,前来观看的人都赞赏不已,称其形神皆备〔5〕。
张路与李梦阳两人不仅仅是作画与求画的主顾关系,更是当时齐名的“祥符三绝”。《河南通志》称张路“工画人物,独绝一时”。张路的画与李梦阳的文章、左国玑的书法,并称“三绝”〔6〕。
除杭淮、李梦阳之外,与张路同时或稍晚的多位官居高位的文人都与张路有所往来,一方面称赞其画艺之高,另一方面褒扬其不为权势财物所动的清傲之品(详见表1)。如陆深〔7〕称张路:“当今好手张平山,写出巉岩水墨间。”薛惠〔8〕称:“奈何绝艺多自惜,未许千金换真迹。高士飞扬不易驯,贵人造请空无益。”王慎中〔9〕称:“安知尺幅上,墨妙能使然。”
对张路的生平、性情、人品、画艺等方面描述得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朱安所写的千字有余的《张平山先生》传记。这篇传记首先描述了张路异于常人的相貌:“奇姿英发,隽迈绝伦,身躯短小,而双瞳炯然。”之后说明其自小便有经世之志,文章出众,“属文隽永,为时辈所宗”,同时性格清傲,以“清介持身,忠义自许”。后因屡举不第,于是“弃置旧学,专精画理”。张路的习画之路从模仿名家名迹开始,“始仿王谔之缜细”,“后喜吴伟之豪迈”,而后自成一家,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俱入神品。以膺例入太学后,名动京师,甚至得到时任兵部尚书李钺〔10〕的青睐,一时之间公卿贵戚皆以张路之画为珍宝。传记称张路作画之前先要“默坐构思,神会意到”,而后“扬袂而起落笔,如造化之生物而无穷也”。张路隐居林泉之后,“布袍芒履,逍遥物外,未尝以尘事婴怀”,“平生不乐造请,足迹不至公门”。曾有监司想要借权势之威命张路作画,张路却始终回避不应。传记中称若想要求画,倘是“韵人佳士,无不应之。有以货财至者,必却之”。传记中还引用了张路自己对于作画的态度:“画乃士君子游戏翰墨耳,岂可以货取哉。
朱安是受封于开封的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五世孙,也是一位理学家。他与张路关系甚密,其女儿嫁予张路的小儿子张柯为妻,二人为儿女亲家。同时,朱安又与张路“居止接近,气味颇同”,“常与先生评品画理至于夜分”。在张路去世后,因为担心其画名与德行日久而被湮没,故而为其作传。
从朱安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张路不仅自身具有很高的诗文修养,与当朝文人、明代宗室交往密切,而且认为作画乃“士君子游戏翰墨”,并不为金钱权势所拘束,其观点与做派更加接近于文人情趣,并非后来画史所认为的为时势所趋的职业画匠。
曾为张路画册作序的文人赵完璧〔12〕也持有相近的看法。赵完璧与张路相识于其画名大振之前,认为其“器识温雅,胸次洒有奇趣,不多饮酒,赋诗鸣琴,志役物外”。后来张路入太学,“珍于公卿,名动京师”,“天下莫不脍称张平山”。其画作也成为收藏对象,“有得片纸尺素之遗者,宝藏珍爱,琬琰木难无以易之”。赵完璧还将张路画作比作“无声诗”〔13〕。
在文人官僚與明代室宗室对张路一致褒赞的同时,此时的画史著录对张路的评价亦甚高。这一点从略晚于张路的韩昂所编写的《图绘宝鉴续编》可见一斑:张平山者,名路,字天驰,大梁人,以庠生游太学,然竟不仕,独游情绘事,其人物似吴伟,而山水尤有戴文进风致,一时缙绅咸嘉尚之,得其真迹如拱璧焉。〔14〕由此可见,对张路学问修养及画艺高妙的认同已不仅是当时文人官僚及明代宗室的一致看法,同时也进入了当朝画史的写作之中。
现将这一时期文人文集及画史著述中对张路的记载进行统计列表(见表1),总结出16世纪中期之前有关张路文献记载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时间来说,这些文集著录的著者多出生于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初年,为与张路同时期之人,成书于16世纪前半期。
第二,就身份来说,著者多为文人官僚或明代宗室。他们与张路往来甚密,甚至结为儿女亲家。
第三,就地域来说,与张路同为河南人的李梦阳、陆深、李钺、朱安等人对张路推崇有加,但多位南方文人如杭淮、薛蕙、沈炼、王慎中等人也持褒奖态度。可见,此时南北方文人对张路皆持较高的评价,并无地域之分。
第四,就评价来说,此时的文人多认为张路在自身修养上气质温雅,属文隽永,志役物外;在性格上清介持身,忠义自许;在画艺上游戏翰墨,名动京师,宝藏珍爱者甚多。
二、狂态邪学:16世纪中后期至明末对张路评价的转变
在张路去世之后,画史对他的褒扬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像朱安所担心的那样,张路的画名与德行因日久而被湮没,果真成了现实。
16世纪上半期之后,浙派后学的画风日渐粗放与程式化,对张路的模仿及赝品不断出现。更重要的是随着吴门画派、松江画派逐渐兴起于画坛,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画坛中心转向了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此时的江南文人大量著书立说,树立自身的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并对此前画家进行评判。作为浙派后学的张路,成为江南文人画家与收藏家诘难的对象。张路在画史中的另一种面貌,也在此时逐渐形成。
较早对张路等浙派后学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松江文人何良俊〔15〕,其撰写于嘉靖后期的《四友斋画论》一书中称:“南京之蒋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张平山,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辱吾之几榻也。”书中对浙派后学如蒋嵩、汪肇、郭诩、张路等人的贬斥之意十分明显,甚至说他们的画用来擦桌子都不够格。
稍后,苏州文人王世贞〔16〕开始将张路的画作与“北人”的审美品位联系在一起。《艺苑巵言》中称张路学习吴伟画风,然而却没有学到好处:“传伟法者平山张路最知名,然不能得其秀逸处,仅有遒劲耳。”同时又认为北方人的审美趣味不高,看重真伪混杂的张路之画,连带着吴伟的名声也被拖累:“北人重之,以为至宝,真赝错杂,丑徒实繁,伟亦不免恶道之累矣。”〔17〕詹景凤〔18〕在《詹氏小辨》中将张路的人物画与山水画分开来讨论。詹氏认为张路的人物画“结构停妥,衣褶操插入妙,用笔矫健,而行笔迅捷,亦自雄伟,足当名家”。但话锋一转,又认为张路的山水画画艺不高,“或加一山一石一木,便入浊俗,不足观”〔19〕。
与《詹氏小辨》约成书于同时的高濂〔20〕的《遵生八笺》一书在称赞戴进、吴伟、夏芷、石锐等人画作为“明一代妙品,士夫画家各得其趣”之后,笔锋一转,批判“郑颠仙、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张平山、汪海云,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俱无足取”〔21〕。《遵生八笺》首次将张路等浙派后学称为“徒逞狂态”的“画家邪学”。这句语气极重的负面评论被后来人所延续,成为文人画史中相互承袭、出现极多的一句评语。屠隆撰成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画笺》一书,几乎一字不落地引用了高濂《遵生八笺》中“画家邪学”的看法。到了明末,文震亨的《长物志》、唐志契的《绘事微言》、朱谋垔的《画史会要》等文人著述都采用了大同小异的说法评价张路,称其为“画中邪学”,并且认为这些浙派后学的画作不宜作为收藏品,“其不甚著名者,非所宜蓄”。
明代晚期最有影响力的绘画理论是莫是龙、董其昌等人所提出的“南北宗论”。以纯化文人画为宗旨的“南北宗论”,将自古以来的画家分为南北两派。“南北宗论”崇仰重视笔墨的南宗,贬斥重视形似的北宗,建构起以南宗文人山水画为绘画最高境界的画史叙述模式。这无疑对后世画史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崇南抑北的董其昌眼中,浙派创始人戴进还算得上“国朝画史大家”。比董其昌稍晚并明显受到南北宗论的影响的文士沈颢〔22〕,在其著于天启元年(1621)的《画麈》一书中更加激进地划分南北两宗,勾勒出从李思训、赵幹、赵伯驹、赵伯骕、马远、夏圭到明代戴进、吴伟、张路等人的北宗行家谱系〔23〕:
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气运复相敌也。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出韵幽澹,为文人开山,若荆、关、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兴沈、文,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若赵幹、伯驹、伯骕、马远、夏珪,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24〕
在沈颢笔下,张路连同浙派的代表人物戴进、吴伟一样被归为北宗画派,并称他们“日就狐禅,衣钵尘土”。其后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一书则完全征引《画麈》的观点。
现将16世纪中晚期至明末这一时期有关张路的著述记载列表(见表2),总结出16世纪中后期至明末有关张路评价的特点:
第一,就时间来说,这些文集著录的书写者多出生于16世纪,约比张路晚半个世纪以上,其书多成于16世纪后半期至明末。
第二,就著者的身份和地域来说,这些画史著述无一例外皆出自江南文人手笔,尤其集中于吴门、松江等地。
第三,就评价来说,此时的文人多认为张路在自身修养方面徒逞狂态,俱无足取;在畫艺上用墨虽佳,未脱院体;总体评价都将其归于被贬斥的北宗绘画,认为其人其画日就狐禅,衣钵尘土,属画中邪学。
三、双重张路
尽管在进入清代之后,画史著述又重新出现对张路较为中肯的评价,如徐沁的《明画录》称张路“传吴伟法作人物,虽少秀逸,然颇遒劲可观”〔25〕。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为张路鸣不平,在为张路水墨《明妃出塞图》题诗中云:“似此澹描翻绝世,按图谁复诋平山?”〔26〕王毓贤在其《绘事备考》中亦称张路“少无宦情,以贡入成均非其好也,精于绘事,人物似吴伟,山水似戴文进,当时士大夫咸尊礼之”〔27〕。
不过,16世纪中期直至明末江南文人的画史书写仍旧奠定了后世人们对于张路的认识与理解。经过明末南北宗论的洗涤,诸如张路的浙派画家已经失去了气质温雅、游戏翰墨的一面,仅剩下徒逞狂态、画中邪学的一面。
关于这一点之前学界亦有提及。班宗华(Richard M. Barnhart)曾指出明末大部分江南评论家提及张路时,必然称其为“北方的”张路,仿佛地理上的事实足以解释其绘画创作本身。同时因为他被认为是粗俗的北方人、邪学之流,故将其排除在正统之外。实际上张路生于富庶之家,自小接受良好教育。作为专业的画家他取得巨大的成功,获得极高的声誉,但是生活却相当简朴低调,过着近乎隐士的生活〔28〕。高居翰(James Cahill)把遭到江南文人贬斥的浙派画家如吴伟、张路、郭诩等人归为同一种类型,认为他们在生平及性格上有共通之处:出身不低,才华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因科举不利而被迫做了职业画家,受到有地位有财力的赞助人青睐,可称为“有修养的职业画家”〔29〕。
张路,因其浙派后学的身份,使得其本来所具有气质温雅、游戏翰墨的一面被画史所掩盖。这涉及由身份所导致的效用问题〔30〕,也体现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建构起来的北方与南方、职业与业余之间的对立。
值得庆幸的是,与张路同时期画史文献的存在能够部分还原张路其人,发掘其被文人画史所掩盖的另一面。我们不能否认张路粗率放逸的画风及其职业画家的身份,但也不应回避其气质温雅的修养与游戏翰墨的主张。通过画史叙述及评价的变化,可以更明确体现出浙派画家张路所具有的双重面貌,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其人品与画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