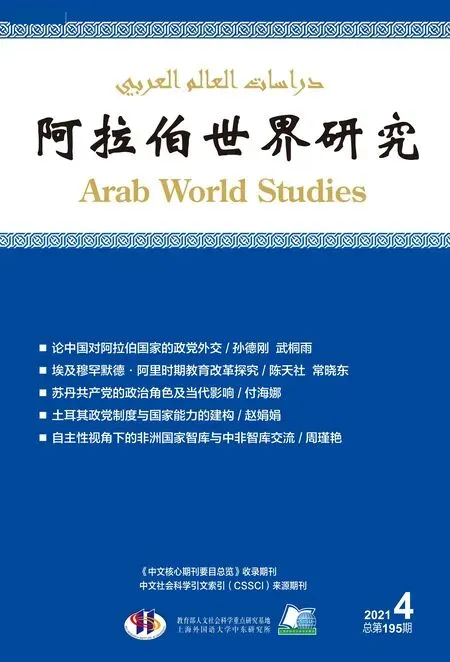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赵娟娟
土耳其是中东第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国内政治发展备受关注。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人民党掌权使国家权力从军队转移至政党手中,土耳其第一部宪法赋予了共和人民党威权统治的政治合法性。1946年,反对党与执政党共同参与议会选举角逐议席,标志着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多党联合政府的频繁更迭和周期性的军事政变成为该时期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正式进入主导党执政的时代,过去文官与军人的二元治理模式转变为文官政府的一元治理模式。
本文试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理论基础,重构国家政治再建构能力的理论框架,同时以土耳其政党体制的发展为研究视角,宏观考察土耳其政党制度的演变,分析政党政治发展对土耳其国家能力建构的重要影响。
一、 国家能力的理论阐释与理论重构
本文对于国家能力理论的关注与再阐释,主要是基于现有国家理论的规范主义研究局限了国家能力研究视角的考虑。在当今政党政治的时代,政党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角,赋予了从政党入手进行国家理论建构的合理性。政党作为土耳其近百年政治发展中的主导者角色,虽因军方多次接管政权而割裂了文官政府一元治理的连续性,但正是这种“割裂性”为从政党政治角度考察土耳其国家能力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一) 国家能力的理论阐释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大行其道时,学界提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将国家能力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其环境中的总体绩效,并列举了提取、规制、分配、符号和响应五类行为。当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而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成功未如约而至时,民主化的回潮呈现出的是政治衰败与政治解体的“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正如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言,世界各国之间最主要的差别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而政府有效统治的程度所取决于的政治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就是维持基本秩序的国家统治能力的体现。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将国家权力分为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两个向度。作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向公民社会渗透,在其统治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就是其所谓的国家能力。因此,曼对于国家权力的划分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之上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后,国家重新回到政治理论的研究视野之中,面对学界“国家中心主义”的复归传统与矫枉过正,乔尔·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从“找回国家”转向“超越找回国家”,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提出了一种国家—社会关系的推陈出新的理论方向。米格代尔通过社会结构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将国家能力划分为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种能力。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社会控制的分布及其集中程度直接影响社会与国家强弱角色的划分,即国家能力的体现。中国政治学学者将国家能力分为专断性国家能力和基础性国家能力。基础性国家能力即国家建设的“基础设施”,具体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以及吸纳和整合能力。其中,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濡化能力是近代国家的基本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是民主国家的基础。国家能力理论兴起后,学界对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愈加丰富。从研究视角来看,有学者将政党纳入国家范畴,以政党—国家能力统摄国家能力建构。有中国学者从“政党能力”出发,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的逻辑,建构了一种“从政党能力到国家能力”的转型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路径。
上述国家能力的理论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路径建构的,并试图将国家能力结构化、普遍化。这种从规范的理论意义上建构国家能力的图谱本身没有问题,但如若具体到某一国家的研究,应考虑国家能力建构主体的差异性。土耳其目前是政党支配下的现代化国家,政党参与了土耳其建国以来的全部过程,政党政治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地位不可小觑。本文通过对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制度的梳理,提出土耳其政党政治深刻影响着国家能力的建构。
(二) 理论重构: 政治再建构能力
政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元素,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被国家和人民所需要。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政治活动的状态,是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它“不仅因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不同而存在差异,且同一政治体制下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也千差万别”。在国家能力的理论中,政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变量,尤其在“政党中心主义”国家或政党支配下的国家。虽然政党能力不等同于国家能力,但政党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对国家能力理论的梳理与分析表明,现有研究更多是在规范意义上建构国家能力的图谱,而在实际政治发展中,政党也是影响国家能力建构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土耳其这个国家,政党是政治场域中的元老,共和国建立之初,凯末尔就将政党作为构建国家政治秩序的主体和推动世俗化与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发党支配下的土耳其更是扩大了政党对国家政治发展的意义,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了土耳其政治权力体系的塑造。在土耳其政党制度的历史演变中,每一次执政党地位的易主、制度类型的转变及军队还政于文官政府的实践,都是对政党进行社会整合与权力重塑即国家政治再建构能力的考验。
政治再建构能力是重要的国家能力之一,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在变革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的政治权力体系重塑。政党作为土耳其政治再建构的主体,在文官政府时期通过自身的有效行为——包括政党社会基础的扩大、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平衡及在军人执政时重塑社会力量等——实现了政治权力体系的重塑。因此,研究土耳其国家能力的建构需从政党这一角色入手,对土耳其政党政治的研究不仅要围绕政党本身,还要超越政党使其纳入国家的范畴,以政党政治的发展推动政党能力的建设和国家政治再建构能力的塑造。
作为一种国家能力的政治再建构能力,在土耳其政治场域中主要体现为,政党作为承载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政治权力体系的重塑和对社会力量的整合、吸纳与平衡,以推动现代国家的建设。但政党对国家的建构也必须契合国家的实际需要,执政党的政治能力要嵌构于国家能力的整体逻辑。这是因为,执政党可以是超越性的,但国家是现实性的;执政党的这种超越性及其限度,必须从当代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土耳其政党政治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中,如果说政党的存在是土耳其共和国的“配置性资源”,那么强大的政党或推动国家能力建构的政党政治则是共和国的“权威性资源”。
二、 土耳其政党制度的演变
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7月24日随着《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
)的签署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同年8月,“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成立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人民党,其在担任共和国总统的同时,也担任该党主席。同年11月,人民党易名为共和人民党。1924年土耳其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权力,标志着具有双重身份的凯末尔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政党的成立则使土耳其与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封建制度彻底划清界限,推动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一) 一党专政时期
1920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创立的大国民议会,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是国家唯一的权力机构。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总理由总统任命,总理在获得总统授权后可从议会中遴选出组成内阁的议员。1923年凯末尔建立共和人民党,开启了土耳其政党政治的进程。1924年,土耳其第一部成文宪法的颁布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自此,凯末尔以共和国总统、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三位一体”模式使土耳其进入一党专政时代。可以说,凯末尔克里斯玛式的威权使总统取代了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


(二) 多党制的发展与成熟
多党制初期,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是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党,两党拥有由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原则构成的共同政治基础。共和人民党作为共和国元老,拥有庞大的政治势力与群众基础,但因1949年难以扭转国内经济颓势而饱受批评,反对该党的群体转而成为支持民主党的重要力量。因此,在1950年由选民直选的议会大选中,民主党以83.8%得票率的绝对优势成为执政党,实现了土耳其首次由执政党向在野党的权力交接。从1946年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到1950年议会选举的民主化,短短四年,土耳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在发展中国家堪称绝无仅有。
共和人民党“三位一体”政治模式的消失及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本应使土耳其政党政治愈加民主化,但随着共和人民党在大选中落败,其几乎将所有的权力和支持者都移交给了民主党,这使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几次议会选举中均取得多数席位。极高支持率使民主党挤压了共和人民党和其他政党的力量,并开始出现专制倾向。民主党政府取缔政治集会和工会联盟、颁布禁止不同政党组成竞选联盟的法令等,导致军人世俗力量的不满。正如亨廷顿所说:“在个人独裁下变得高度政治化的军方、中低级的官员通常具有成熟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对失去的权力和地位愤愤不平,并感到来自新民主政治中活跃的或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常从事各种政治活动,旨在推翻新的民主政权或迫使其领导成员或政策发生变化。最具戏剧性的政治活动就是军事政变或政变企图。”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取缔了民主党的统治,组建临时军政府。自此,土耳其国内第一次由文官政治转向军人政治,军人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民主党的独裁统治引发了1960年军方的政治干预,致使土耳其政党政治逐渐脆弱化。1960年至1980年的二十年间,军方三次干预政治接管政权,分割着政党的文官统治,联合政府与短命内阁是这一时期土耳其政治的主要特征。1961年,军人政府颁布新宪法,为多元政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参与角逐议席的政党数量增加,但都不足以单独组阁,这使土耳其政党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特征。1965年,正义党在议会大选中胜出,并成为联合政府的主角。但随着民主参与的扩大,土耳其政党中陆续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激进组织,使政治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1971年3月12日,军方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迫使正义党政府倒台。此次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土耳其民主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在这二十年间,土耳其政坛呈现出联合政府与军政府交替执政的局面。内阁更换达18次之多。政党组合频繁变化,弱化了政党体制,削弱了政府合法性,使政局愈加不稳。1980年9月军方在政治暴力的泛滥下再次推翻民选政府,接管国家政权,并废除1961年宪法,以整饬社会秩序为名通过立法进行政党重组。可以说,此次政变“是土耳其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缩’,军方的行为并没有真正破坏土耳其民主化进程,而是土耳其民主发展过程中一次缓解矛盾的行动”。1983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举行土耳其议会选举,唯一一个非军方背景的祖国党赢得议会选举,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执政权再次回到文官手中。

繁荣党被迫取缔后,以埃尔多安(Recep Eayyip Erdogan)和居尔(Abdullah Gül)为首的支持者创建了美德党,并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15.4%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但军方同样以其宗教色彩浓厚为由,对美德党扣上反世俗罪名并将其取缔。2002年上台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就是繁荣党和美德党,为避免重蹈两党被取缔的覆辙,正发党努力淡化宗教背景,调整意识形态,塑造伊斯兰教与世俗民主化相结合的新话语体系,将自身定义为保守的民主政党。正发党通过官方声明将其政治立场概括为“中间偏右”,将意识形态概括为“温和的、保守的”。在持续执政的20年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逐步确立了绝对的主导党地位。尤其是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开始排斥甚至清洗异已力量,并通过修宪将土耳其的政治体制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一党独大的执政优势呈现出威权政治的回潮。
三、 2002年前土耳其的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其发展的主轴,高效的政党体系是其运行的重要依托。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源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而渗透到东方国家。政党作为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推动现代政治模式的构建,对土耳其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党是民主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普遍现象,政党体制直接反映出政治制度能力。在土耳其政治发展中,政治再建构是国家的政治功能之一,它不仅解构着现存政治权威,且重构了新的政治权力体系与社会资源。
(一) 一党制时期
土耳其共和国是凯末尔通过世俗化改革而完成的民族国家建构。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虽结束了传统统治,完成了政权在现代化意义上的转移,但帝国传统势力并未完全丧失在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其对新政权的冲击使凯末尔政权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关于土耳其国家发展问题,议员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凯末尔于1920年组织召开的大国民议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混合体,议员具有公务员、工程师、商人、部落酋长、农民等不同背景。这些背景各异的群体围绕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严重分歧。议会共有437人,其中主张废除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的激进变革者有197名,继续维持帝国君主立宪制的保守派和自由人士有118名,其余122名持中立态度。其次,凯末尔为最大限度降低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在共和国制度和文化中的影响,通过推行激进的世俗化改革来接纳西方文明、压制伊斯兰文化,但这与根深蒂固的历史宗教传统是不相容的。最后,凯末尔时期土耳其的统治精英主要由军队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成员组成,难以向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这使得凯末尔统治集团不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因此,凯末尔主义未能彻底改造土耳其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和消除伊斯兰框架,以引进新的土耳其民族概念,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叛乱、1930年的梅内曼叛乱以及1933年布尔萨叛乱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凯末尔主义者推动的乡村结构性变革的失败。建立在文官、军人、碎片化地方精英联合间接统治基础上的凯末尔统治,对社会的渗透极为有限,因此,“只有消除民众对伊斯兰教的精神倚赖,才可以为新的权力结构奠定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奥斯曼帝国割裂、削弱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和融入“西方文明”的世俗化改革,最终变成激进的文明转型。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权力塑造,经历了从伊斯兰教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到打击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并进行权力重构的转变。全面掌握国家权力,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世俗化改革的终极目的。凯末尔通过建立共和人民党作为推行世俗化的工具,重新整合国家与社会势力。一方面,凯末尔消除宗教精英的权力基础。1923年第二届大国民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共和人民党党员,世俗化改革要求政治精英必须具有世俗性特性,因此从1920年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到1946年,议会中宗教精英的比例从17%急剧下降至“大国民议会中没有一位宗教人员”。另一方面,凯末尔通过建立民间组织和乡村研究所向基层深化世俗化观念。1931年,凯末尔建立了从属于共和人民党的两个民间组织——“人民之家”和“人民园地”。这两个民间组织在全国各地分别设有4,322个和479个分支机构,主要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多个领域输出凯末尔主义,推动世俗化改革,影响民众的观念。
凯末尔在执政期间集总统、党主席和军队领袖权力于一身,议会、政党和军队的权力身份和阶级支持构成了一党专政的基本条件。军人推动建立的共和国,使得政党只是国家治理的表面工具。正如贝尔克·埃森(Berk Esen)教授所言:“土耳其是通过武力强制的方式脱胎于奥斯曼传统帝国的废墟之上的,并非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结果。”凯末尔时期以军事暴力为后盾的一党专权,虽然具有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但相较于传统帝国则缺乏向下渗透的机制。激进的改革所引起的传统伊斯兰社会价值体系的强烈反抗与乡村结构性变革的失败,使土耳其长期形成一种以城市和农村为基础的精英与大众的“中心—边缘”结构。凯末尔西化政策仅作用到中心的精英阶层,由此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逐渐疏离进一步导致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因此,建国初期的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专断性弱国家”。但也正是“专断性”赋予了凯末尔一党专政的合理性以及政党制度对世俗化改革的推动作用。
此外,土耳其一党制时期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即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伊诺努。如前所述,伊诺努掌权初期虽然沿袭了凯末尔政权的威权统治,但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已出现松动。1939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推动执政党内部的改革,将政党与政府机构相分离,并在议会内部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由执政党议员组成的“独立集团”,监督政府和议会,以显示国家制度的民主性。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对民主的需要构成了伊诺努的执政理性,发展民主政治成为政党体制下重塑政治权力体系的指导目标,推动着政党制度的转变。如果说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塑造了一批世俗化的政治精英,那么伊诺努则沿袭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促进了民众的政治参与。
(二) 多党制时期
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土耳其政党制度经历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演变。1946年,除执政党共和人民党参加议会大选外,民主党以在野党的身份角逐议会席位,这使得土耳其的政党制度开始向多党制过渡。1960年军事政变后联合政府和短命内阁的出现,使土耳其正式步入了多党制时代。
1950年的议会选举是土耳其现代化的重要分水岭。作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象征,民主党通过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挑战共和人民党的执政党地位。成为执政党以后,民主党通过取缔和打击共和人民党建立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等重要的民间组织,削弱共和人民党作为反对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以巩固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使政治精英的社会背景也发生重要变化。凯末尔时期主要由军队和国家官僚机构成员构成的统治精英被另一批以律师和商人为主体的专业技术精英组成的新精英群体所替代。新精英群体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地方性网络,他们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在立法和行政上取代了原有的国家官员。因此,向多党制的过渡也意味着世俗精英对权力垄断的结束,民主政治得到发展,议会成为精英群体博弈的核心舞台。同时,土耳其政治制度也通过给予几乎所有成年公民参与全国性政治决策的权利,以公开竞争的方式选举执政党,此举使参与政党政治的群体愈加广泛,政党组织的吸纳力更强。亨廷顿认为,政党作为建立强大政府的组织基础,实行有效统治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在于政党的质量。土耳其的多党联合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党力量弱小使政府难以在增加政党数量和扩大社会基础所形成的民主化基础之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因此,政党不但没有发挥国家与社会间的桥梁作用,还造成了社会分裂与动荡。当政党无力应对乱政危机时,军方作为失序的文官政府的纠正者,代表国家的利益稳定局势,重新构建新的权力框架。
凯末尔时期政党对社会整合的失败,表明共和人民党没有建立起与广大民众的联系,政党渗透社会的能力极为有限。民主化进程开启后,政党政治首次实现执政党向在野党的权力移交,但最终也因民主党的独裁统治而使土耳其陷入军方与文官政府的持续对抗。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土耳其处于温和多党制和极化多党制时期,军队对议会的影响较大。对土耳其来说,军队就像国家的守护者,发动的政变也是建立在政党无力整合国家的前提之上。因此,军事政变总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缔文官政府,并进行国家建设。军方控制政府后,通过制定新宪法承认军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作为参与国家事务的制度性渠道,修改总统职权、限制政党活动以防止文官独裁。但就军方自身而言,在军政府时期军方始终面临一个理论性困境,即军队通过暴力手段快速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有效的短暂性与恪守凯末尔主义和维护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使军队难以替代政党进行长久的国家与制度建设;就文官治理而言,政党政治一直是土耳其政治建构与政治发展的主流形式,政党所具有的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提供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最终,军队只能还权于文官政府。
多党制的政党政治是政治资源的社会整合方式,这一时期政党在推进民主化时已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纳入其中。一方面,军事政变的发生解构着文官政府脆弱的政权体系。作为诸多政治力量整合的结果,军事政变的频发使政府执政效率变得极为低下,政党的脆弱降低了民众对代表政党利益的政治精英的信任,从而影响政党形象的树立。可以说,军事政变对原有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使政党政治受到极大冲击。另一方面,军事政变也带来了国家官僚精英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党重整旗鼓,为政党重新整合社会力量,推动国家能力的建构提供了时间。武装力量相较于文官政治更像是一个莽夫,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却难以在稳定秩序后实行有效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军事政变的二重性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党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在回归文官政府统治后以更好地推动政党对国家能力的建构,实现政治权力体系的重塑。

四、 2002年后土耳其的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
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执政使土耳其成为一个由政党支配的国家。正发党在不断适应政治现实、发挥自身功能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角色。但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并非取决于单个政党,而是取决于政党体制运行的有效性,因此“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就依赖于特定的政党体制”。正发党在近20年的执政中塑造了土耳其的主导党体制,也通过其所具有的“主导性”意义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再建构。
(一) 正发党支配国家
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执政使土耳其自此告别了军人与文官政府交替执政的格局,在政党主导国家发展的政治体制下,土耳其进入了一党独大的政治统治新阶段。正发党的主导性意义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导党属于政党多元主义的范畴,政党政治允许主导党以外的其他小党存在,并且在法律意义上能够与主导党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但在这个竞争性政治体制中,轮流执政并不会发生,因为同一个政党总能长期赢得议席的绝对多数。布隆代尔(Jean Blondel)认为,主导性政党必须是最大的且至少两倍于第二大政党,并能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40%以上选票的政党;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认为,主导性政党须连续三次获得议席的绝对多数,且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的议席数量差要超过10%。根据这一标准,正发党的主导性集中体现为土耳其政治中以及全体选民眼中和观念中所谓的“选举霸权”。在2002年、2007年、2011年、2015年的第二次议会选举、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正发党以绝对多数的议席数量赢得大选,建立和巩固了其一党独大的支配性地位。
其次,在与军人政治权力的较量上,正发党扭转了以往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轮流执政的局势。一是正发党通过修宪限制军队在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例如,军队法官不再担任国安委法官;增加国安委的文官政府代表;国安委会议由每月一开改为两月一开等,都为军队通过国安委参与政治事务或给政府施压增加了难度。二是正发党通过推行与军人秉持的现代化策略相契合的加入欧盟政策,软化军方政治态度。三是正发党通过对“埃尔盖内孔”案件的调查以及对“大锤”政变阴谋的揭露,清洗了国家和军队中的亲政变力量,使军队自此走下神坛。文官政府对军方政治职能和对操控政权权力的淡化,重塑了新时期的政军关系,使正发党在二者博弈中,逐渐占据支配性地位。
最后,在政党间的力量对比上,无论是与正发党结成“人民联盟”的民族行动党,还是正发党的反对派人民共和党,都受到正发党权力优势的影响。就共和人民党而言,作为土耳其历史最悠久的党派,在政党政治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民主化后因党内精英阶层的社会基础与民主发展的要义相悖而逐渐失去影响力,甚至进入“封禁期”。该党目前是土耳其国内第一大反对党。第二大反对党民族行动党虽然响应了执政党修改政治体制的号召使修宪顺利通过,并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与正发党结成“人民联盟”获得议席,但其政治力量始终难以与正发党等量齐观。正发党主导体制下的支配性力量使其具有形塑国家政治议程和对土耳其政权体系进行再建构的能力。
(二) 正发党的政治再建构
2002年以来,在正发党的治理下,土耳其政治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国家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党制下的军政府与文官政府交替主导国家政局的二元治理体系就此结束,土耳其正式进入了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的时代。正发党近20年的执政实践表明,正发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中心—边缘”力量的弥合与平衡以及对政治权力体系的重塑。
1. 平衡世俗与宗教力量
历史地看,土耳其现代化建设始终建立在世俗化改革基础之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的世俗主义所伴随的政治极化,实质上是强化世俗力量对宗教力量的控制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内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创建的民族秩序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正式崛起。伊斯兰政党利用多党制政治体制的民主性吸纳了更多的社会边缘性群体,多党制下的社会碎片化促使国家有意对宗教进行战略性吸纳。土耳其历史上既存的城市和农村间的社会差距与文化鸿沟所造成的世俗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发达与否的差异等,在伊斯兰政治化后扩大了政党的执政基础。可以说,从世俗的民主化中产生的伊斯兰却实现了反世俗化。2002年,正发党选择了摒弃意识形态标签,采取“保守民主”原则进行国家建构和政治制度的建设。
在世俗与宗教意义上的中心—边缘方面,共和人民党、军队、高等司法机构等代表世俗力量,正发党则是边缘力量的主要代表。正发党的上台本身就推动了边缘力量向中心的靠近。边缘力量发出政治声音,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中心力量的某些优势。世俗政治精英与伊斯兰政治精英的长期博弈,使土耳其走上了以世俗国家底色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土耳其模式”。正发党主要通过“宗教教育”推动中心与边缘力量的弥合,如废除关于《古兰经》等宗教课程的限制规定、重新开放伊玛目·哈蒂普高中、允许代表伊斯兰主义的新社会变革力量在大学求学等。此外,埃尔多安对“世俗主义”的重新定义也淡化了世俗主义的尖锐性和伊斯兰主义的威胁性,“国家不应按照宗教法度构建,且应该尊重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并平等对待不同的宗教信仰,……世俗主义是土耳其的基础性原则”。因此,随着正发党边缘性群体的崛起,世俗与宗教力量在民主、自由等观念上逐渐出现重合之处。正发党最初摒弃宗教意识形态的标签不代表将彻底切断与保守民族观念运动的联系,其明显的伊斯兰色彩也不意味着土耳其世俗化国家底色将彻底改变。
在正发党时代,军方与文官政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安委的职责变迁上。“埃尔多安相继通过修宪和制定法律的形式修改国安委的成员构成,增加副总理和司法部部长的常委资格,废除体制内的军方委员会,扩大非军方人员的参会比例。取消国安委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最终决定权,而只是负责协调相关部长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分歧……同时部长委员会对国安委提出的建议也不必‘优先考虑’,废除国安委秘书长由现役军事将领担任的规定,废除秘书长可进入文官政府机构并对国安委所提出的建议进行监督的规定等。”最终国安委总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且其中文官政府的官员大比例提升,国安委从之前的决策机构下降为咨询机构。土耳其政治的“去军事化”加速了国安委的平民化,加之2007年军事政变阴谋的暴露改变了土耳其军方作为国家政治秩序坚定护卫者的形象,对军人干政涉案人员的审判削弱了军方势力的影响,这使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2. 弥合国家与社会的分裂
正发党上台后不仅将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且打造了一个疏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作为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根基所形成的一张广泛且深入的网络,是由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想、“人民联盟”和“民族联盟”两大政治联盟,以及政治排斥关系、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划分及其所形成的政党与社会组织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作为界定国家—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其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基础。在新时期,政党承担起国家的政治主导角色,正发党的政党自主性与政党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
现代国家必须在社会之中建构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凯末尔时期,土耳其社会结构就存在明显的中心—边缘力量的分野。正发党上台后,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有了显著变化。土耳其国家与社会的分裂结构建立在世俗群体与伊斯兰宗教的关系之上,军队、反对派和司法界代表了土耳其社会阶层的中心力量,在共和国一直是有权势的精英阶层,而正发党更多代表了广大农民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边缘力量。在正发党的执政时代,原本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力量格局被改变,军方世俗力量被极大削弱,更多的市民阶级开始进入政治场域。
20世纪50年代民主化开始后,土耳其政党的社会基础持续扩大。1983年,土耳其恢复文官统治,“经济设计师”厄扎尔提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承诺要建立一个自由定价、由市场确定资金投放的制度。随着经济模式的变革,大量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私营企业取代了国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传统地位。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公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土耳其国内一批新兴伊斯兰主义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是创新经济模式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所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战略催生出一大批生活充裕的中产阶级,这些边缘力量不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直到正发党将这种社会资本转化为政治权力,通过一种持久存在的权威反对世俗精英力量和官僚体制。以世俗精英为中心的政治威权国家向由边缘力量掌权的转变,是消弭国家与社会分裂的体现,也是弥合中心—边缘鸿沟的重要路径。
3. 正发党的权力重塑
土耳其现行宪法是在1982年宪法的基础上多次修订而成的。该宪法规定,土耳其坚持世俗主义、共和主义、平民主义、改革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民族意识至上、分权制、政教分离、以人为本等重要原则。宪法历经多次修改,尤其是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和2017年宪法在国家性质和权力来源、政党政治、公民权力与义务、军方权威和司法体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改动。
第一,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曾任正发党主席与内阁总理,由于正发党党章规定,党员担任某一职务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届,因此已经在2003年、2007年和2011年连任的埃尔多安为了继续执政,推动土耳其的2017年宪法改革,通过全民公决从宪法上赋予总统实权,将土耳其政治体制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2018年,埃尔多安赢得总统选举,这赋予了埃尔多安重塑政治权力构架的合法性。政治体制变革后,总理职位被废除,总统拥有直接任命副总统与内阁高官的权力,这使得埃尔多安拥有绝对的国家领导权。
第二,2017年宪法修正案中将1982年宪法规定的“当选总统后必须脱离原属党籍”修改为“总统可保留与政党的关系”。2017年埃尔多安重新当选正发党领袖,这不仅提高了正发党的政治地位,也增强了埃尔多安对政党的控制。政党间的斗争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土耳其政局。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重新界定了议会的职能,加之于总统直选方式的确立,议会失去了监督和弹劾总统的权力。2017年推动的宪法修正案废除了议会审查内阁和政府部长工作的职能,并且正发党掌控议会使议会无法对兼任政党领袖的埃尔多安进行权力的有效制约。
第四,在军事机制设计层面,军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参谋部直接向总统汇报,将军方置于总统的控制之下,削弱了国家政治层面最大的不稳定因素。2017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在改变土耳其政治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最具合法性的修宪方式扩大总统权力,是土耳其自1982年来修宪范围最广、修改幅度最大且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修正案。
在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发展史上,五次军事政变的发生表明了边缘向中心进行力量转移和社会动员的短暂性失败。中心力量的官僚阶层和世俗政府对基层社会动员的歧视,促使边缘群体寻求更多的机会进行政治冲击。正发党在选举胜利后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弱化军队作用、重塑国家官僚机构、通过政党政治竞争挤压世俗力量的政治生存空间,都表明保守边缘力量的增强和对世俗中心力量的削弱。正发党支配下的土耳其,政治社会的形成与中心—边缘力量的弥合坚实了政党在土耳其的主导地位。
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是基于国家能力理论和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中的实践与经验依据而提出的。正发党通过政治再建构不仅使“中心—边缘”力量得以弥合与平衡,政治权力体系也得到重塑。可以说,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推动国家能力的建构,政治再建构能力是对土耳其政党制度演变和政党对国家能力建构的历史性分析的回应。如果说政党制度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那么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则是对国家能力在长久的政治发展中的考验。
五、 余论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发展推动着国家能力的建构。共和国的建立是土耳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军队塑造的土耳其虽然在凯末尔时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威权国家,但在规范政治制度上却是政党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承担了建构任务。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更替不仅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定位与执政实践同样影响着执政党的政治生命与执政效果。军人主动将政权交还文官政府所透露的军人政治的正义性,为政党重新整合社会力量提供了契机。可以说,多党制时期的政党整合能力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军人主动成就基础之上的。正发党支配下的土耳其的国家能力更多体现在政党的能力上,原有的社会分裂开始趋向于中心—边缘力量间的弥合与平衡。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正发党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主义背景充斥着世俗化的国家底色;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政治社会的形塑使正发党在社会中建构了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在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之间,政党通过削弱军方权威重塑权力体系,使军队走下神坛。
鉴于2007年土耳其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选举改为全民直选、埃尔多安在2014年赢得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直选使土耳其进入半总统制,伴随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民众对政治强人的迫切要求,2018年正发党实现了政治体制由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土耳其政治体制的改革,对该国政党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在总统与政党关系上,2017年宪法修正了1982年宪法对总统须脱离原属党籍的限定,总统不再受政党中立的限制,可以有政党隶属,这为埃尔多安重回正发党并加强对正发党的控制提供了政治机会。在总统与议会关系上,2018年6月举行的土耳其总统和议会“二合一”选举,使掌握实权的总理一职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总统与总理相互牵制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为过去。在政党政治层面上,2018年议会选举中所形成的以结盟为基础的政党对抗将继续在议会中上演,以正发党为代表的执政党和以共和人民党为代表的在野党都将面临内部危机和外部重组的情势。
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其一党独大的执政优势与土耳其总统制的结合使土耳其政党政治和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面临新的考验。基于正发党与伊斯兰教的关联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实现对政坛的主导其实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和威权政治的回潮,这使得政治发展呈现出倒退的趋势。但就正发党的伊斯兰属性而言,一方面正发党主导性地位的确立并非源自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体现于近年来土耳其议会选举所呈现的政治区域图景中。例如,原本属于伊斯兰力量传统势力范围的东南地区成为世俗政党共和人民党支持者的阵营,而曾积极支持凯末尔主义的西部地区如今却成为正发党的强大后盾。另一方面,正发党主导下的政党政治是教俗权力的分离状态,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相比,正发党并非实行真正的神权统治,给正发党赋予宗教政党标签的是领导人的伊斯兰倾向与社会基础的伊斯兰属性,埃尔多安擅长利用宗教话语与宗教体系争取选民支持。
此外,对于土耳其在长期奉行西方化道路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叙利亚危机暴露出的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罅隙,使得埃尔多安必须重新思考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问题。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推手,正发党在将宗教作为获取选票实现政治统治的方式中,要处理好世俗与宗教力量的整合问题,以避免被宗教反噬。对土耳其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走上世俗化与宗教化的中庸之路。总统制的确立以及总统与政党领袖身份的重合,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正发党权力的巩固,也使正发党主导下的政党政治持续面临世俗化的冲击和对伊斯兰主义回归的质疑,其中暗含政治治理危机。新政治体制下的埃尔多安时代的国家治理将是政党治理的时代,在总统制的政治发展道路上,政党政治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多元化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且推动着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