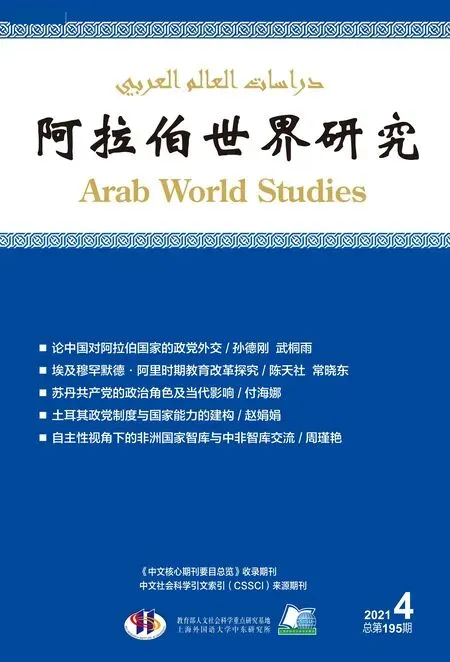自主性视角下的非洲国家智库与中非智库交流*
周瑾艳
由于殖民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独立后非洲国家治理问题的长期存在,非洲思想、非洲声音在国际舞台长期缺位或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非洲自身的发展战略长期由西方的智库所主导,这制约了非洲本土方案的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快速且持续崛起,政治和学术精英们迫切希望改变本土力量在非洲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和依附性。随着知识生产自主性意识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逐步意识到,保证国家不断获得、扩充其自主性存在与能力的自由,是国家的根本目标追求和最根本的外交目标。然而,与非洲国家智库迅猛发展的现实不相称的是,中国学界对非洲国家智库的系统研究较为薄弱,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中非合作中的智库角色、中非智库交流以及智库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构建等作用,但对非洲国家智库的发展与变革背后的大国博弈则鲜有涉及。
智库是践行以思想外交、文化外交、人民外交为基础的人文外交的重要依托和途径。随着中非交往的日益广泛和深入,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影响力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的非洲国家智库已经成为推动中非民间交往、增信释疑的纽带。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非洲国家智库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有助于了解非洲官方和民间的声音,为中国对非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二是剖析非洲国家智库的资金来源、运行特点、影响机制及其背后的域外力量博弈,有助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非智库交流;三是探析非洲国家智库的自主性困境及原因,有助于更好地推动非洲智库的机制建设,助力非洲国家智库自主开展对中国和中非议题的研究,促进中非关系国际话语的多样化和理性化。
本文在梳理非洲国家智库历史变迁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非洲国家智库的分类、研究取向和运行特点进行分析,并尝试辨析非洲国家智库发展背后的西方力量,探索非洲国家智库与非洲国家政府和政党政治的互动,指出其面临的自主性困境和挑战,并据此提出破解困境之路及其对中非智库交流的启示。
一、 非洲国家智库发展的历史沿革
非洲国家智库初创于19世纪末殖民地时期。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不断探索发展道路,努力提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量本土智库应运而生,成为非洲知识精英凝聚集体认知、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非洲国家智库可划分为初创期、勃兴期、调整期和转型期四个发展阶段。
(一) 初创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 服务于殖民宗主国利益
非洲大陆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末遭受了长达70余年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时期,非洲的本土知识精英在政策制定上几乎没有发言权。而法国、英国等殖民宗主国牢牢控制非洲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主导权,没有支持非洲本土知识分子成长的意愿。当时,零星设立的智库主要是为了辅助殖民当局管理当地事务。
殖民当局将非洲大陆纳入殖民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使之作为商品原料的供应地。由此,如何扩大经济作物出口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宗主国利益,便成为殖民当局的迫切任务。在此背景下,英国在西非创办了农业和畜牧业研究机构。1893年,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设立植物研究站。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该国其他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植物研究站和实验农场网络,其重点是提升出口经济作物的种植水平及产出效能。实际上,对于非洲本土民众来说,粮食作物的产能对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更为重要。但殖民地政府更关切自身利益,由其主导建立的智库研究工作聚焦于为种植园经济提供智力支持,对改善本土民众种植的粮食作物兴趣不大。
当然,殖民当局为维系其统治的可持续性,也要加强对非洲国家国情、区情、社情的研究。1950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创立了西非社会和经济研究所(West Africa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其主要职能是通过研究了解当地民众情况,帮助其殖民统治的平稳发展。
(二) 勃兴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助力独立初期的非洲国家发展
1957年加纳脱离英国独立,1958年几内亚脱离法国独立,这对整个非洲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至1969年,除葡语非洲国家外,大多数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努力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一方面,非洲国家对殖民时期建立的研究机构进行了重组,同时调整研究机构的定位,服务于促进非洲国家自身增长和发展的总体目标。例如,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1960年10月独立后,立即解散了西非社会和经济研究所,转而在伊巴丹大学成立了尼日利亚社会和经济研究所(Nigerian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NISER)。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政府着手建立新的智库,政府型智库由此应运而生。众多非洲国家的财政部、教育部和农业部等政府部门开始建立服务于政府及部门决策的研究和咨询类智库。例如,博茨瓦纳教育部建立了规划统计和研究机构,赞比亚的财政和规划部、加纳的财政和经济规划部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部门。1961年,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旨在为尼日利亚在国际事务中的发展方向提供决策参考。而在农业领域,殖民者建立的区域性商品农业研究机构纷纷转变为国有农业研究机构。
除政府型智库外,非洲大陆还涌现出区域型、网络型智库,其中最著名的是1973年成立于塞内加尔达喀尔的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该机构本身并不参与具体议题的研究,其主要功能是推动和促进学术交流、传播研究结果、提供研究资助,以及支持非洲智库的研究和能力建设,重在发挥智库服务的平台与桥梁作用。创立于1958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UNECA)是非洲第一个区域性、国际性的智库。联合国非经委在20世纪60年代聚焦于非洲当时的发展要务,基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规划数据,研究了农业、工业、交通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情况,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以期增强非洲国家的发展能力。
(三) 调整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受制于西方援助
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在国际石油危机及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深陷经济危机。迫于摆脱经济危机、解决发展资金严重匮乏等问题,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外部援助,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在经济领域实施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在得到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必须接受西方政治民主化价值观,这对非洲国家智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在非洲强制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导致非洲国家普遍缩减政府开支。受限于政府和教育机构等公共部门的改革,非洲本土智库由此难以再从本国政府获得持续充足的研究资金,部分政府智库规模缩减乃至被迫关闭,非洲本土智库和学者在政府决策和政策分析体系中的声音日渐式微。以农业为例,结构调整计划极大地冲击了非洲国家原有的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推广体系,导致非洲国家在外来势力的干预下无法完善和发展本土的农业生产体系。
第二,受西方援助支持的非洲国家“独立”智库大量涌现,国际援助机构及其智库对非洲国家政府的政策影响力日益增大等原因,非洲本土智库和学者被进一步边缘化。作为对非援助的附加条件,西方援助国和机构一般会要求在受援国决策中发挥实质性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援助国派遣了超过8万名外籍顾问在4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工作。外国援助官员成为非洲政府决策咨询的事实主体,“总统府和中央银行的部分技术官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们开始共同制定经济政策”。
第三,非洲国家智库聚焦政治及经济自由化相关议题,包括贸易自由化、“良治”及减贫等西方语境下的“非洲问题”。成立于1975年的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Free Market Foundation of South Africa,FMF)主要研究南非如何参与多哈谈判。而随着贫困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国际发展领域,1994年成立的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POA)主要致力于研究如何摆脱贫困以及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转型,其主要资助方是加拿大的“智库计划”(Think Tank Initiative, TTI)。随着环境、气候变化等议题不断出现,非洲国家智库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非洲国家智库的研究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沦为西方援助国在非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助推器。西方援助国在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时,通过附加政治、经济条件对非洲国家智库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向这些智库提出监督非洲受援国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等要求。
(四) 转型期(21世纪以来): 自主探索意识增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非洲国家致力于自主探索的发展道路,非洲国家智库自主设置议题,在国际舞台发声的意识逐步提升。
第一,提振政府型智库,重视智库在国家规划和决策中的作用,自主创立更好地服务于本国政府的智库。例如,在埃塞俄比亚,1999年成立的埃塞俄比亚发展研究所(Ethiopi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EDRI)和2007年成立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IPSS, Addis Ababa University)致力于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在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政府出资创办智库或向智库提供研究资金的情形虽然仅发生在非洲部分国家,但改变了非洲国家智库以往由西方出资的传统,有利于智库更好地发挥资政议政、政策解读、民意通达的作用。
第二,非洲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纷纷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非洲国家的政治家通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推动非洲本土知识的生产,促进非洲与外部的交流,培养非洲青年领袖。例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成立的塔博·姆贝基基金会(Thabo Mbeki Foundation, TMF)以促进“非洲复兴”为己任,除学术研究外,还通过实施“非洲领导力培训项目”培养非洲精英青年。曼德拉发展研究所(Mandela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MINDS)则由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遗孀格拉萨女士担任董事会主席。这是一家秉持泛非主义、面向整个非洲的知名智库,不仅为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提供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还十分关注非洲国家青年领袖的培训。
第三,非洲国家智库自主出资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参加研讨会。例如,安哥拉前总统1996年成立了多斯桑托斯基金会(Eduardo Dos Santos Foundation, FESA),该基金会每年自主出资召开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非洲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学者研讨非洲大陆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和战略。
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发展的自主意识逐渐提升。它们希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自主制定国家经济和政治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智库在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性受到部分非洲国家的认可,非洲国家政府和政治家自主创立的智库不断增加。非洲国家智库在议题设置方面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尽管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语境的影响下,环境、气候变化、良治等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关心的议题已经被纳入非洲国家智库的关注视野,但农业发展、工业化、经济社会转型等聚焦非洲自身发展需求的议题依然受到重视。
二、 非洲国家智库的定位与发展现状
近年来,非洲国家智库发展方兴未艾。通过对非洲国家智库的类型、特点及政策影响机制的梳理,以及结合案例对非洲国家智库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个层面的主要运行特点加以介绍,可以管窥非洲国家智库的总体状况和影响机制。
(一) 非洲国家智库的规模与类型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写的《2019全球智库报告》,全球共有8,248家智库。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智库612家智库,北非地区的智库数量为87家(约占全球智库总数的1%),整个非洲地区拥有智库699家(约占全球智库总数的8.4%)。
从研究领域和议题的角度来看,非洲国家智库可分为综合型智库和专业型智库。例如,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HSRC)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是类似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综合型研究智库。南非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ISS)则专门研究跨国犯罪、移民、海事安全与发展、维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以及应对冲突和治理等安全议题;肯尼亚非洲技术研究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Technology Studies, ACTS)专门研究非洲能源和技术。它们均属专业型智库。
此外,非洲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区域型、次区域型智库和网络型智库。例如,1999年成立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是一家覆盖全非洲的民间独立调查研究机构,在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民主、治理、经济状况和相关问题的民意调查。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研究所(Rift Valley Institute, RVI),以苏丹和南苏丹、非洲之角、东非、大湖区域作为研究重点。成立于1985年的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er, SARDC)是一家区域知识资源中心,致力于加强区域政策研究,跟踪研究南部非洲地区诸多发展议题,并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开展合作。
区域型、网络型智库是非洲地区独有的特色,这主要是源于泛非主义及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基于遭受殖民侵略共同的历史遭遇和争取独立的斗争目标,非洲各族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对于非洲大陆的认同超过了对殖民地国家的认同,泛非主义思潮有力地推动了非洲一体化进程。非洲区域一体化是非洲政治家和知识精英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一方面,非洲50多个国家的国情虽各不相同,却面临共同的发展掣肘;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深知单个国家的力量有限,唯有发出共同的非洲声音,才能提高非洲大陆的整体国际地位。因此,区域型、次区域型和网络型智库也是对这种发展诉求的回应。
从智库的定位和资金来源上看,非洲国家智库可分为政府型智库、大学型智库和民间智库。政府型智库指由政府直接设立或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政策咨询的研究机构,例如埃塞俄比亚对外关系战略研究所(Ethiopian Foreign Rel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EFRSSI)。该所原名为埃塞俄比亚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Ethiopi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EIIPD),原隶属于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现隶属于埃塞和平部,直接为埃塞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高校智库主要指附属于高校的研究机构,它们注重基础问题研究,例如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ISR)。民间智库指独立于政府的智库,但其经济来源一般为西方援助或私营部门,例如2008年在尼日利亚阿布贾成立的非洲经济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in Africa, CESA),其资助全部来自加拿大的“智库计划”。
(二) 非洲国家智库的研究取向
非洲国家智库在其宣介的使命和愿景中,大多将自身定位为沟通研究与政策的桥梁。它们主要承担四大职能:对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对策研究;建言献策、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传播知识、舆论引导和公众;培训非洲精英、建立人才网络。在现实运行中,智库的功能与研究取向与非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与欧美知名智库热衷于研究战略和外交事务不同,非洲国家智库主要关注本国和非洲地区的发展议题,如经济转型、发展政策、公共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事务等。以南部非洲的174家智库为例(见表1),除南非外,几乎所有国家的智库都聚焦国内发展议题。津巴布韦的智库主要关注农业和土地、货币和债务等对该国发展至关重要的议题。赞比亚的智库聚焦贸易与投资、交通与运输、公共财政等议题。埃塞俄比亚发展研究所注重工业化、产业园的研究,并参与埃塞政府“增长与转型”计划、工业园区规划的起草。非洲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博茨瓦纳发展政策分析研究所(Botswana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BIDPA)于1995年由博茨瓦纳政府建立,受政府委托,负责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中期评估,并通过发布年度报告、政策简报、工作论文、专著、期刊、新闻简报等研究成果影响政策制定。

表1 南部非洲国家的智库
(三) 非洲国家智库的影响力
非洲国家智库重视与非洲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的互动,影响区域层面的政策制定。以“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African Capacity Building Foundation, ACBF)为例,该基金会创建于1991年,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加纳首都阿克拉均设有办公室,其影响力分别辐射南部、东部、西部及中部非洲。基金会的愿景是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资金、技术和知识支持,提升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基金会类似于非洲国家智库的孵化机构,以“种子资金”的形式培育智库,20多年间已先后资助了25个非洲国家的39家智库。博茨瓦纳发展政策分析研究所等受益于该基金会的智库,就是在其支持下逐渐成长为非洲国家的知名智库以及非洲区域政策网络的重要参与主体。
在2014年8月首届美非峰会前夕,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委托其支持的6个非洲国家智库编写各自所在的次区域组织的美非关系立场文件,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研讨会,广泛听取官员、学者、民间组织的意见,最后形成共同的非洲立场文件,呈送非盟委员会并在美非峰会上发布。这一案例展示了非洲国家智库如何通过智库网络建设逐步建立对区域政策决策的影响力。
非洲国家智库除聚焦影响非洲自身发展的议题外,还开始关注区域和国际事务,致力于提升国际影响力。智库在非洲各国的分布基本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体量和战略地位一致。由于财力、人力的限制,非洲国家智库大多仅在本国首都设总部,很少有实力在其他国家设立分部或代表处,大多数智库缺乏对国际事务的研究。但近年来,随着非洲经济的增长,非洲议题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非洲区域大国愈加注重区域和国际事务的研究,逐步利用智库塑造国际影响力。
一方面,非洲国家智库召开高级别的区域会议,打造智库品牌。塔纳论坛(Tana Forum)由埃塞俄比亚已故前总理梅莱斯于2012年倡议发起,是非洲每年一度的高级别会议,类似于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非洲版。非洲领导人和利益攸关方汇聚一堂,共同探讨非洲安全问题及非洲主导的解决途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虽只是高校智库,但作为塔纳论坛的秘书处所在机构全程参与论坛的举办。该研究所作为主办方,赋予了塔纳论坛二轨外交的特色。论坛在非洲独有的猴面包树下举行会议,为小组讨论、会场的互动和双边会谈提供了非正式空间,成为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正式会议外颇具影响力的政策沟通平台。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智库积极参与全球议题讨论和设置,提高国际影响力。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的顶级非洲智库,其研究议题涵盖外交政策、经济外交、发展、治理、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六大领域,尤其关注非洲与世界的关系、中非关系、和平与安全以及南非的外交政策。2017年,德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沿用中国将非洲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议题的做法,发起“二十国集团非洲智库峰会”。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成为由二十国集团国家和非洲国家智库组成的非洲常设小组的联合主席,持续通过智库峰会这一平台影响二十国集团对非洲议题的讨论。2018年,阿根廷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作为常设小组成员提交了政策简报,并向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建议。作为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中唯一的非洲国家,南非通过智库参与国际议题设置,为非洲国家发声,提高了智库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大多数国家政府虽意识到智库在决策过程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囿于自身实力,无法给予智库有力的经济和政策支持。因此,颇具影响力的非洲智库尚属少数,大部分非洲智库尚缺乏政策、社会及国际影响力。
三、 非洲国家智库面临的自主性挑战
非洲国家智库自2014年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召开首届峰会以来,至今共举办了六届。峰会的创立既凸显智库在非洲日益重要的作用,也是对智库发展面临挑战的回应。非洲国家智库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及对非洲发展的作用一直是峰会关注的重点。首届非洲智库峰会的主题为“智库与非洲转型”,峰会执行秘书曾指出,受到自主性不足的影响,不少非洲国家智库可能会关闭或陷入严重危机。非洲国家智库的发展始终困扰于自主性问题。
(一) 严重依赖西方资金援助
非洲国家智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及对西方援助的依赖性。目前,非洲国家智库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国际援助。以安全领域的非洲国家智库为例,80%的资金来源于欧洲国家。例如,泛非智库“非洲晴雨表”财政资助(第七轮)来自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莫·易卜拉欣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和“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等机构。该智库此前的西方资助方包括:英国国际发展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莫·易卜拉欣基金会、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世界银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透明国际”、丹麦外交部、丹麦国际开发署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又如,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除非洲30多个国家的政府,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丹麦、芬兰等域外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际援助,资助形式主要包括三种:对机构的援助、项目援助(一般为长期项目)以及更为灵活的委托研究(一般为短期项目)。其主要资助方是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丹麦外交部和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等。
非洲国家智库过于依赖西方援助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国家通过对援助的形式、作用、路径进一步反思,未将智库援助列入未来对非援助的重点,非洲国家智库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其次,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智库的援助大多采用项目援助,而不是预算援助的形式,这导致非洲国家智库的整体架构脆弱、人力资源建设后劲不足。以项目制聘用的智库研究人员在项目结束后离开智库,造成智库人员流失,研究缺乏传承,“有库无智”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意识到非洲国家智库长期受到资金和组织能力方面的制约,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的“智库计划”(Think Tank Initiative, TTI)通过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相结合的方式,增强非洲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整体实力。“智库计划”是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在2008年提出的,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提供资金帮助推动实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英国国际发展部、挪威发展合作署(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orad)等也一直对该项目提供资金。然而,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发展援助严重受限。“智库计划”于2019年终止。2020年6月,英国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宣布合并则是另一例证。由此可见,发展援助对非洲智库在长期资金和机制建设方面的支持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 深受西方思想影响
随着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日益激烈,非洲在世界相对边缘的地位得到改善,非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遗憾的是,非洲本土尚未成为非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非洲学者在非洲知识的生产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和依赖地位。西方在非洲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独立后对非洲价值观领域的渗透、西方媒体和话语权在非洲的强势地位等,都影响到了非洲国家智库的思想。
西方思想对非洲国家智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聘请西方学者在非洲国家智库任职或担任领导。例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奥尔登(Chris Alden)同时兼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是欧洲人,特别是在2016年中心领导更替后其中国研究大多引用西方观点,并中断与中方合作单位学者的互访协议。第二,一些在欧美留学的非洲知识精英毕业后留在欧美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与非洲问题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接近了西方与非洲思想界的联系。例如,当代非洲著名思想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同时兼任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第三,西方通过赋予非洲国家智库相对自由的空间,潜移默化地将西方偏好的议题嵌入非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通过西方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引导,“民主”“良治”“发展有效性”“人的安全”等西方概念不断出现在智库的研究成果中,逐渐成为非洲精英广泛接受的价值观。
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洲智库的公信力。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于2020年发起“高级研究政策对话”项目,旨在鼓励非洲政府和机构更紧密地与当地学术机构合作,而不是向域外国家进行政策咨询。塞内加尔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认为,非洲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目前有倚重外国思想的倾向,非洲政府应更多地依靠非洲本土的知识生产和政策咨询。通过“高级研究政策对话”项目,塞内加尔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希望非洲本土高校和智库能够发挥更多的政策影响力。然而,这项以“代表非洲,为非洲发声”为宗旨的政策对话项目的资助方仍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折射出非洲知识生产的困境,即发展自主性与资金依赖的矛盾。
除资金可持续性的挑战外,非洲国家智库还面临能力建设和专业性方面的挑战。例如,非洲国家智库对农业、工业化、基础设施等非洲重点领域和行业缺乏真正深入的专业研究,对第四代工业革命等非洲发展面临的新时代议题的研究关注度较低。此外,由于西方智库和援助机构能够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和科研环境,非洲本土智库还面临人才流失的现实挑战。
(三) 对本国决策的影响力较弱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智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建言献策、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但非洲国家智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仍然较弱,这主要是由于非洲自身的政党政治和决策模式导致,也与外部依赖性造成的非洲国家智库的自我矛盾定位相关。
第一,非洲国家智库的影响力受政党政治和政局变迁影响较大。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目前实行多党制,但政党政治并不成熟,大多数政党仍惯于以民族和地域因素动员选民。非洲的族群政治导致政党大多代表族群和宗教派别的利益,智库在非洲政治生活中不被重视。非洲很少有政党注重用政策纲领去争取民众支持和用智力支持来改善其政策制订和执行,政党宣言大多缺乏严谨的论证和分析。在政党政治稳定、执政党长期执政或政党竞争有序进行的非洲国家,智库与政府的互动则较为密切,智库在本国决策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在政党力量碎片化型的国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由于任期无法得到保障,考虑问题往往趋向于短视,对国家发展缺乏长远思考,也无能力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长远规划。因此,它们对智库等知识支持的力量不够重视,也少有互动。一旦政局发生动荡,智库研究的持续性和政策影响力将会受到波及。
第二,非洲国家智库与政府的政策决策互动模式多为单向委托,缺乏互动。西方智库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往往作为决策源头,扮演决策倡议和舆论引导的角色,美国的决策过程一般是智库→媒体→国会→政府→政策出台。日本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发现政策课题并制定研究项目、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提出建议、政策普及、政策评估等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但非洲国家智库大多是政府委托项目的受托方,按照政府需求完成政策评估和执行,智库很少能够自行设置议题,也很难依循发现问题→形成研究→方案提交→政策决策的路径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第三,由于对西方援助资金的依赖性,非洲国家智库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不以援助方的需求和偏好为导向,难免忽视或偏离非洲发展自身的需求。以博茨瓦纳发展政策分析研究所为例,研究所虽由博茨瓦纳政府部分出资自主创立,但为了迎合西方援助方对智库“独立性”的要求,不得不将自身定位为“政府创立的独立智库”。
第四,非洲国家智库与政府的人员互动呈现“单向旋转门”的特点。即非洲领导人卸任后常常组建智库或去智库任职,而从非洲国家智库、大学进入非洲政府决策层的情况则很少见。埃塞俄比亚智库对话、研究与合作中心(Centre for Dialogue,Research and Cooperation, CDRC)创始人阿布迪塔·德里布萨(Abdeta Dribssa)博士曾在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任职多年;尼日利亚经济峰会小组(Nigerian Economic Summit Group, NESG)负责人劳耶·贾约拉(Laoye Jaiyeola)曾在尼日利亚央行工作了15年。近年来,非洲国家智库专家开始为政府提供座谈、项目研究等政策咨询服务,但智库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决策层的案例极少。
四、 中非智库交流的现状与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智库自主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随着新兴经济体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这些智库在合作伙伴和研究议题上“向东看”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非洲国家智库开始努力拓展西方之外的合作交流伙伴;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智库的研究除了继续关注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等西方关心的议题,还逐渐兴起了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中非智库交流逐渐向机制化、专业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一) 非洲国家智库开始关注中国议题,非中智库交流增多
随着中非合作在经贸领域的迅猛发展,中非智库合作与学者交流日益重要。中国也为非洲国家智库拓展多元合作伙伴、摆脱自主性困境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非智库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有别于西方通过资金援助和人员设置影响非洲议题塑造、建构西方话语体系的做法。
过去,非洲国家智库中鲜有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项目,而由中国、非洲单独或联合设立的更少。非洲国家智库对中国及中非关系的研究主要受到西方援助资金的支持。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是为数不多的长期追踪中非合作的非洲国家智库,其中非项目资助方主要是瑞典国际发展署。纳米比亚公共政策研究所在2019年发布的首份关于中纳关系的报告是受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委托完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中心或中非研究中心依托非洲大学或非洲孔子学院成立,例如非洲政策研究所(Africa Policy Institute, API)2013年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2007年成立南部非洲中非关系研究所,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依托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拉各斯大学中尼发展研究所2018年依托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的推动下,塞内加尔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所、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与中国智库建立“一对一”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研究机构交流的机制化和常态化,提升了中非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水平,深化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中非合作的贡献与挑战、中国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等议题逐渐进入非洲国家智库的视野。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智库论坛成为中非民间交流的机制化平台,每年在中国和非洲轮流举办,每届论坛邀请中国政府部门、主要涉非非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非洲国家相关组织、机构等参会,就中非如何维护与拓展共同利益、非洲2063愿景、中非产能合作与非洲工业化、中非减贫发展、改革开放和中非关系、中非合作论坛等主题进行研讨,以此促进中非思想界的交流对话。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继续将智库交流作为中非人文合作的重要支柱,决定继续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智库论坛”,成立专门机构支持中非学术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鼓励论坛和相关机构开展联合研究,为中非合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双方在中非智库论坛框架下建立了中非智库合作网络,继续实施“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鼓励双方智库拓展合作,中方每年邀请200名非洲学者访华。2019年4月,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同非洲国家智库开展了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经验、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等前沿课题进行了深度合作与研究。研究院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非洲学者来中国讲学,派遣中国学者赴非洲国家智库开展学术交流。中国非洲研究院还连续三年期间资助50项中非共同研究课题,课题将由中国学者和非洲大学或智库学者联合申请和执行。
(二) 加强中非智库合作的政策建议
非洲国家智库自主性困境的出路在于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和非洲自身的能力建设,非洲国家智库的自主意识提升则为中非智库交流提供了契机。中非智库交流应成为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的增长点,中国应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加强中非人文交流,巩固中非智库论坛机制建设,加强对非洲国家智库的智力支持,尤其是推动非洲国家智库的机制和能力建设,提高非洲国家智库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
中非智库交流不应仅限于举办研讨会,而应向非洲国家智库建设提供一定的物质和资金支持,用于购买电脑、办公室设备,支持人力资源建设。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无偿援助中,可设立专款用于支持非洲国家智库建设,在非洲国家智库内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项目。另一方面,鼓励中国在非企业资助非洲国家智库,开展行业研究。这也有助于中资企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局势,从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中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非洲国家智库的能力建设,具体包括:招聘非洲学者在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工作,长期聘用常驻中国的非洲学者,设立非洲访问学者计划,招聘非洲实习生等;针对中非关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联合研究;资助非洲国家智库开展学术研究和出版研究成果。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设立“非洲国家智库青年学者培训项目”,公开招募对中国和中非研究感兴趣的非洲国家智库青年学者;通过对非洲国家智库青年学者进行在华培训,向非洲青年学者讲授中国发展经验,交流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鼓励中非学者设立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培训结束后继续支持研究课题;每年举办一届类似的培训班,建立非洲国家智库青年学者数据库,定期邀请培训班校友来中国交流;邀请非洲国家智库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调研;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支持非洲国家智库学者到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开展田野调研,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与世界互动学习的经验等。
由于非洲国家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较弱,中非智库交流应着重提高非洲国家智库的研究和建言能力,并鼓励非洲国家智库对中国问题和中非关系开展客观扎实的研究。具体举措包括:其一,支持中非智库联合举办研讨会,传播非洲学者的观点;资助非洲学者在非洲演讲和出版学术成果,提高在非洲当地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资助非洲学者参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洲研究年会,提高非洲国家智库在世界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其二,通过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传播非洲国家智库的研究成果。中非学者可在非洲主流媒体联合开设阐述中非关系的专栏,既要对“债务陷阱”“白象工程”等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进行阐释,又要主动设置议题,展示中非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三,建立非洲国家智库数据库,系统梳理非洲国家智库的类型、运行特点及其有影响力的智库学者。
中非智库交流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帮助非洲国家智库通过系统研究对中国和中非合作形成客观真实的评价,从而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另一方面,通过在平等基础上对非洲国家智库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助力非洲国家智库提升自主能力,走出自主性困境。
五、 结语
非洲国家智库的发展沿革、运行特点凸显了非洲知识生产面临的自主性困境。纵观非洲国家智库的发展历程,从受殖民宗主国主导的智库初创期到非洲大陆独立初期非洲政府主导的智库热潮,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依附性智库的涌现,无不体现出非洲国家智库发展与西方的经济援助与思想影响之间的密切联系。非洲国家智库的外部依赖性造成的智库自我矛盾定位,非洲各国自身的政党政治和决策模式导致非洲国家智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仍然较弱。在现实运行中,非洲国家智库的功能与研究取向与非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总体上大部分智库以研究国内发展议题为主,少部分智库开始参与非洲区域的政策制定,并通过国际平台积极参与非洲相关议题的设置。尽管非洲国家智库的自主发展意识提升,但组织建设和研究能力仍有不足,而长期资助非洲国家智库的传统西方援助国纷纷收缩发展援助战略和资金,非洲国家智库面临资金和能力的双重自主性困境。这为中非智库交流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日益意识到非洲国家智库和中非智库交流的重要性,已通过中非智库论坛等平台推动中非智库交流的机制化和专业化。未来中国应着重从机制建设、能力建设和研究能力三方面帮助非洲国家智库的自主发展。对非洲来说,非洲国家智库自主性的增强有助于为非洲政府提供更为有效的本土解决方案,促进非洲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非洲方案对全球事务的贡献;对中国来说,非洲国家智库自主性的增强有利于非洲自主开展对中国和中非议题的研究,推动国际学界、媒体塑造更为多元化和理性化的中非关系国际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