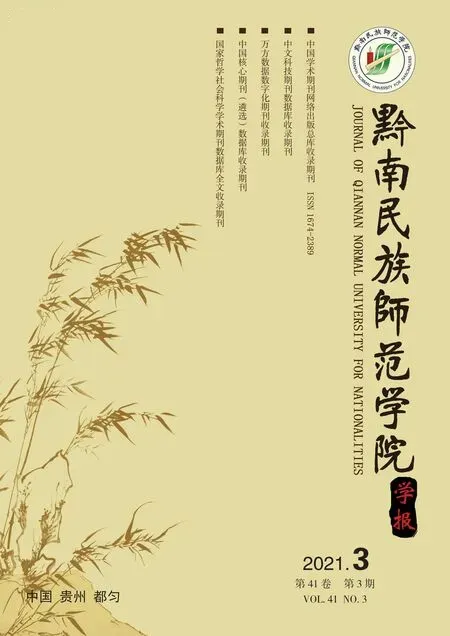雍乾时期贵州“新辟苗疆”科举政策探析
吴晓芳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
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开辟苗疆和改土归流二者关系上,李世愉先生指出:“开辟苗疆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一大特点”。[1]清政府开辟苗疆同改土归流一样,是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治理体系的重要措施,在开辟以黔东南为主要区域的苗疆后,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以实现苗疆稳定。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已有较多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李世愉先生对苗疆开辟过程与善后措施较为系统的介绍和阐述,为研究“新辟苗疆”区域专题的深度考察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2]。张中奎教授对苗疆治理研究更为详尽,并以“苗疆六厅”为研究对象,从“王化进程”的视角来考察清朝的治理得失,是对清代苗疆治理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3]。以上两位学者在著述中,皆注意到苗疆开办学校对于该地区善后的作用,对于苗疆科举问题有所讨论不过并未深入,近年来亦有一些专门讨论“新辟苗疆”科举问题的文章出现,如有学者着重讨论了清代黔东南“苗疆”科举考试变革与变通的原因[4],还有学者在对“苗疆六厅”的教育发展动因等问题的分析中,对苗疆科举推行取得的成效作了介绍[5]。以上成果推动了“新辟苗疆”科举政策的研究,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基础,然而在相关政策的推行与调整方面讨论涉及较少,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清代贵州“新辟苗疆”科举政策推行,对该地区社会稳定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而从民族地区治理角度考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特别是雍乾时期相关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深入探讨,本文拟对其政策背景、推行进程与效果评价等方面做一番梳理与讨论。
一、以科举行“教化”之讨论
雍正四年(1726年)春,此前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时任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的鄂尔泰,认为西南地区土司等地方势力影响清朝的大一统局面,于是奏请改土归流并提出一套宏观策略与具体的措施。雍正接受鄂尔泰建议并命其主持推行相关事宜,随后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展开大规模改土归流。在此次改土归流的各省中,贵州是较为特殊的一个,因在改土归流前的贵州除流官和土司辖区之外,在黔东南地区还有大片的苗疆“生界”需要“开辟”,且须解决“开辟”后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
鄂尔泰在《云贵事宜疏》中,对改土归流前云南和贵州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两地土司与苗民之间的不同关系。他认为云南土司多为豪强,所属苗民皆听其指使,而“贵州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若不及时对“苗患”进行“清理”,即使处理了土司,“亦不过急则治其标,本病未除,恐终难宁帖”。[6]鄂尔泰之所以认为“苗患”能否解决直接影响到贵州改土归流效果,主要是因为贵州苗疆面积较大,且苗疆相较于土司管辖地区,与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较少,因而苗民对中央王朝与儒家文化缺少认同,更加难以治理。对此,时任贵州巡抚何世璂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上奏中称“生界”地区的苗民“向无管辖,不隶版图,不供赋役,几同化外”,故对于这一地区苗民需要加强“教化”,从而“使犷悍顽野之辈,尽化为服教奉法之民”。[7]可见,在当时主政贵州的官员眼中,苗疆的“外化”主要表现在“政”与“教”两个方面:其中“政”的方面,虽然以往这些地区“不隶版图,不供赋役”,但清政府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完成苗疆与内地政治上的一体化阻力相对较小;而“教”的方面,由于“生界”苗民与官方存在语言、文字不通以及思想观念差异等文化上隔阂,解决起来要困难的多。因此,他们认为“开辟”苗疆和“教化”苗民,对贵州改土归流所欲达到的稳定地方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除地方官员外,雍正对于黔东南“新辟苗疆”苗民的“教化”问题也十分重视。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在收到鄂尔泰已经将“古州荡平”的上奏后,雍正作了大段的朱批,称“古州等处生苗,自古未归王化,其人愚悍性成,罔知法度……朕怙冒万方,岂忍令此苗蛮独在教化之外”。[8]雍正这段话能够充分反映出他对“生苗”的认知和对“教化”的重视,他认为生苗因为久未“王化”,所以才表现出“愚悍”和“罔知法度”的习性,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的。当然,对于“新辟苗疆”的苗民“教化”任务的艰巨性雍正也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选择“能办理此事之人”也非常慎重,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他在鄂尔泰所器重的黔省官员石礼哈和张广泗之间选择了后者。雍正认为张广泗“才具优长,周详慎密”能够委以重任,从而能够完成使苗疆“沾被朝廷之声教”的任务,而石礼哈则因在他任上表现出“恃才自用,俱欠和平”“每以不知为知,举止乖张”[9]等问题而被革职,也证明了雍正选择张广泗是较为明智的。当然,张广泗也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在处理苗疆事务上表现出了勤勉与务实的态度,并给出了一套颇具实效和远见的治理方案。
张广泗在由黎平知府升任贵州巡抚后,经过一番调查,向雍正提出了通过“兴学校,行科举”来对“新辟苗疆”行教化的方针。张广泗在“复查上下两游新辟各地”后,于雍正八年(1730年)上《设立苗疆义学疏》,其中介绍了“新辟苗疆”苗民基本情况,并提出了设立义学的建议。张广泗指出,“新辟苗疆”地区苗民种类不一,在上游附近的安顺、镇宁地区为“仲苗”,下游附近的都匀、镇远等地区为“黑苗”,靠近黎平一边之古州为“洞苗”,这些地区的苗民都是中央王朝教化所未及的。“新辟苗疆”延绵千里,人口也有数十万,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后应当培养苗民之中天资聪慧者,教之以忠顺之道及礼义,这样不久便可起到改变地方落后风气以趋同于内地的效果,“是所设立义学,课诲新附苗人子弟,实为振励安疆要务”。[10]张广泗在上疏中不仅提出苗民应当启蒙教育,而且提请“特设苗籍取进之例”,即给苗民提供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的机会,具体做法是“每届岁科,于各府州县有苗童者,取进生员一二名不等,以示奖拨”[10],张广泗的请求得到了雍正的批准。
除张广泗外,其他一些贵州地方官员也奏请在苗疆地区开设义学并得到了批准。雍正八年(1730年)“户部议覆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遵旨酌定乌蒙总兵刘其元条奏苗疆事宜:苗俗向无学校,应于各属四乡适中之所设义学,以广化导。”[11]同年,雍正批准贵州“新辟苗疆”地区设立义学鼓励苗民接受教育,随后在“新辟苗疆”中的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等六厅陆续建立了义学,如古州车寨义学、都江厅义学、清江城乡义学、八寨城乡义学、大小丹江义学、台拱厅城义学等,使得义学开始在各厅普及,为日后科举政策在当地的推行打下了基础。
通过以上介绍可知,“新辟苗疆”对苗民需采取教化的必要性上,雍正与主政贵州的张广泗等君臣之间是有共识的,张广泗对雍正提出教化苗民的方针给出了具体方案,即以科举行“教化”。在清代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学校是育才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入仕做官则是培养人才的目标[12]。清廷在开辟苗疆后,通过将当地苗民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之中,让苗民可以进入学校继而参加科考获得向上晋升的机会,这样对于民族地方稳定与发展来说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措施。
二、科举政策在“新辟苗疆”的推行与调整
清政府在“开辟”贵州苗疆之前的康熙时期,已允许湖广和贵州苗民中的熟苗参加科举,为雍正时期贵州“苗疆六厅”科举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清代最早在苗疆地区推行科举的是湖南,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政府对湘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开辟湘西苗疆之后,湖南学政潘宗洛奏称:“熟苗归化愿改入汉里,即应许以民籍应试……使汉苗无殊,则熟化为民,生化为熟,可为楚南久安长治之策”。[13]康熙批准后实行,但要求参加考试的必须是“熟苗”子弟,且要加入“民籍”,即试图通科举制度促进苗民“化生为熟”继而“化熟为民”。黔东南苗疆在开辟时间上虽然晚于湘西苗疆,但清政府在两地“开辟”之后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类似的,即如何在运用强硬的政治与军事手段实现快速稳定“新辟苗疆”之外,通过柔性的“教化”苗民的方式来实现地方的长久安定,故科举在湘西苗疆推行取得成效后,也自然成了黔东南苗疆“久安长治之策”。
湖南开启了允许苗民子弟参科举考试的先例后,不久贵州地方官员也奏请实行。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贵州巡抚于准上《苗民火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疏》,称如今贵州苗民已经开始输粮贡赋,并且与汉民相邻而居,彼此之间有贸易等往来,并不是原本不通声教之“生苗”可比的。所以应该将土司族属和苗民之中聪慧者入学,“一体科举、一体康贡、以观上国威仪,傅其渐观礼教。”康熙于当年议准:“贵州苗民,照湖广例,即以民籍应试。进额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别”。[14]以此为标志,贵州苗民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不过仍然需要像湖广地区一样只能以“民籍”应试,这一境况到雍正继位不久后得以改变。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考虑到苗民文化基础较差的情况,对贵州苗民子弟参加科举政策又进行了调整,规定“贵州苗童应试,准于各府、州、县定额外,加取一名苗童生”。[15]从此苗民子弟不但不必加入“民籍”而以“苗籍”参加科考,且得到了额外的童生名额,对于提高苗民子弟参加科举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苗童”还仅限于“熟苗”子弟,“生苗”参加科举考试是在黔东南苗疆“开辟”之后。前文提到雍正八年(1730年)张广泗在《设立苗疆义学疏》中提出在黔东南“新辟苗疆”开设义学、给予苗童生员名额等建议被雍正采纳后,科举政策得以在“生苗”地区推行继而推广。新辟苗疆科举的得以顺利推行,除了张广泗的提议和雍正的政策批准之外,也离不开贵州地方官员的支持,特别是贵州学政晏斯盛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晏斯盛,字虞际,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人,他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江西乡试中获第一名,次年又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才能出众得到雍正赏识,雍正九年(1731年)督贵州学政。晏斯盛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向朝廷奏请:“黎平府之古州,虽未设学,而苗民繁庶,颇知向学,请择其文理明顺者量取一二名,附入府学苗童之后,以示鼓励”。[11]在收到奏请后,朝廷批准“新疆六厅”中的古州厅按照开泰、天柱两县此前增设苗童考取之例,选择苗童附入府学童之后,晏斯盛作为学政直接推动了科举政策的在古州厅率先实施,以此开新辟苗疆科举之先例。
纵观雍正朝对贵州苗疆推行科举的态度,始终是较为积极的,而之后的乾隆虽在继位之初也延续了苗疆地区科举政策上的优待,但仅十余年后政策便开始转向保守。乾隆四年(1739年)议准:“凡贵州归化未久之苗,有能读书赴考者,准其与新童报名应试,照加取额进。地方官不得因其祖籍苗民,仍以新童送试。汉童亦不得以既定有苗额阻抑”。[16]此时的乾隆还是延续了雍正对“苗疆六厅”苗民实行以扩征科举入学资格名额的优待政策,既是考虑到苗民文教薄弱,以此保障公平,也是为了激励苗民向学,意在将久为化外之地的“新辟苗疆”尽快“王化”,实现内地边疆一体化。然而,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对贵州苗民子弟的科举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取消了对苗民子弟科举优惠政策,实行汉苗一体合考,这一转变背后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有学者指出,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开始全面转向,主要标志就是在这一年乾隆驳回了湖南巡抚开泰在湘西苗疆“建学延师,设法奖励”的奏请,并提出对待苗民等少数民族“宜使其不知书”,并将这一旨意传达给西南各省督抚[17]。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才有了之后贵州对苗民科举政策的调整。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任贵州布政使的温福为了迎合乾隆的旨意,上奏称“苗地遍立社学,并择内地社师训教,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将奸诈百出。请密饬地方官,将新疆各社学之社师已满三年者,徐行裁汰;未满三年者,亦以训迪无成,渐次停撒,则从学苗童,不禁自止。交请岁、科现两试,仍准苗童一体应考,但不必另设额数,则苗卷自难入彀,亦可不禁自退”。[18]纵观温福认为苗民学习知识后“将奸诈百出”,未必就能认定清政府所规定的“贵州各属苗民岁、科两试,仍与汉童一体合考,不必分立新童加额取进。学臣亦不得以粗浅之苗卷,滥行录取”。[14]意在愚民便于驾驭,但“汉苗一体应考”这一科举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清政府认为对苗民的“化导”取得阶段性突破,是对“新辟苗疆”地区文教治理成效的一种自我认可。当然,除此之外随着“新辟苗疆”地区苗民文教水平的提高,苗疆地区与王朝腹地差别的缩小,以及苗疆科考中存在的“冒籍”问题难以根除等问题,也是乾隆取消苗生科举优惠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分析。
通过对以上讨论可知,清政府在贵州“新辟苗疆”推行科举并非偶然,乃是湖南和贵州其他“熟苗”地区先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对之前政策的一种延续,也是在西南地区“治苗”整体策略的体现。雍正对贵州“新辟苗疆”科举政策进行调整,开始允许“生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并予以专门的名额,这是清政府随着形式变化采取因地制宜的调整,促使科举政策更好的推广与执行,也基本达到了以“教化”来稳定地方之目的。乾隆在延续了雍正的苗疆科举政策十六年后开始发生改变实行“汉苗一体应考”。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爆发了规模较大的“乙卯苗变”对苗疆地区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影响,清政府继而在民族政策方面做出新的调整,而“汉苗一体”的科举政策随民族政策也做出调试。乾隆晚年和此后的嘉庆、道光等皇帝在苗疆治理上不断吸取经验,意识到对苗疆文教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
三、“新辟苗疆”科举政策成效评析
科举制度产生之初是一种选官制度,本与教育无关,但由于封建政府要选拔、培养符合自己需要的人才,需以封建伦理去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从学习的内容上去引导他们,因此“科举制度创立不久,便与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成了教育的根本导向”。[12]清政府在“新辟苗疆”推行科举制度亦是如此,允许苗民子弟入学然后给予参加科考的名额是作为一个整体政策出台的,其目的是对原本长期处于“外化”的苗民能够“陶以文教,消其悍顽”,从而有利于对苗疆治理。从客观效果来看,科举制度的推行也较好推动了苗疆文化教育发展,增进了苗民对于中央王朝的认同,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冒籍”等问题影响了实际效果。
清政府在贵州“新辟苗疆”地区推行科举制,推动了义学和书院在苗疆的发展,从而提高了苗民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雍正年间,黔东南苗疆各地共设有义学67所之多,“苗疆六厅”也是全部都有开设,其中八寨(今丹寨)1所、丹江(今剑河)1所、台拱(今台江)1所、都江(今三都)1所、清江(今雷山)3所,古州(今榕江)10所[19]。在义学中苗民子弟通过学习《圣谕广训》和儒家经典,逐渐与内地“声教相通”,据嘉庆年间任古州厅厅事林溥所做《古州杂记》记载:“苗人素不识字,无文卷……今则附郭苗民悉敦弦诵,数年来入庠者接踵而起,且举孝廉一人”。[20]义学对于文化水平的提高与苗疆风气的改善由此可见一斑。
在清代学校教育体系中,义学重在普及文化,而书院则更加注重与科举考试的衔接,通常是义学发展有一定基础之后书院才能更好的培养人才。这样形成了义学与书院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苗疆六厅”下属的苗疆书院便是在义学创立并得到推广后,陆续成立。如古州厅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建立榕城书院、光绪三年(1877年)建龙冈书院,八寨厅同治十二年建(1873年)龙泉书院,丹江厅光绪九年(1883年)设鸡窗书院,台拱厅咸丰六年(1856年)设三台书院、拱辰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年)设莲花书院,丹江厅光绪二年(1876年)设丹阳书院。通过以上列举可见,书院已经在道光时期开始逐渐在“苗疆六厅”普及,反映出苗疆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书院在清代到教育中的作用被认为是“辅学校所不及”,由于招生质量优秀,在学生数量形成规模效应后,许多地方书院的教育成就超过了儒学。
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导向作用,清代书院的课试程序、活动安排和章程等的制定,也尽量与科举接轨,因此苗疆书院的设立对于苗族子弟适应科举考试,起到推动作用。学额的分配是反映地方参加科考学生水平的重要指标,“苗疆六厅”的学额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离不开这些地区中各学校的贡献。下面通过对道光年间“苗疆六厅”的部分学额学制的大致统计,可对此有较为直观的认识:

表1 贵州苗疆六厅学额学制
苗疆书院的设立,除当时对于开启民智、推动苗疆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之外,清末新政之初,这些书院又逐步改为大、中、小学堂,成为近代教育发展的基础。
科举制在新辟苗疆的推行,除了能促进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传承民族文化以及促进与其他区域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之外,对于苗民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经过雍、乾、嘉三朝的发展,至道光时期的苗疆在文化水平与民族关系上,已经与开辟之初有着天壤之别。雍正之前清朝官员对八寨等地区的苗民印象是“不知读书为何事”,而到了道光时期黎平府的情况是“岁科考试,府学额入二十五名内,例取苗生十三名,是以读书识字之苗民,各寨俱有,其间客民之居住苗寨者,又较别地为多”。[21]这里描述的黎平府苗民与苗寨的情况,既反映出在学校与科举推行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苗民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也反映出由于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各民族间交往与融合也得以加强。与此同时,苗民通过对儒学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学习,有利于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进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清政府在“新辟苗疆”开设科举和建立学校,特别是给予苗民子弟专门名额的优待政策,其目的是鼓励苗民向学,提高苗民文化水平,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汉人占用苗民考试名额,即“冒籍”的不良现象。在贵州科举考试中推行增加“苗额”政策之初,就有防范汉民冒充苗民的考试规定,雍正十年六月贵州学政晏斯盛就在上奏中提到:“苗童应试,加取一名。请用汉廪生同苗生联名保结,苗童五名互结,以杜汉童冒占。其苗童名目改为新童,苗卷改为新卷”。[11]虽然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但是根据时任贵州布政使的邓善燮描述:“向来考试,苗学多因人不敷取额,遂为汉人篡籍获售,苗人百不得一”。[22]为了解决冒籍问题,同时也为了保护久居苗地的以及“苗化”的汉民,乾隆三年(1738年)议准:“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无籍可归,而入籍之年,又定例相符者方准收考;实有原籍可归,将此等考生拨回原籍考试。无知之徒,聚众攻击者,仗六十,徒一年”。[23]在出台加强惩治“冒籍”措施后,该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也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决定取消“苗额”的原因之一。
科举名额的分配,实质上是清政府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教育权益分配的制度化,也是清政府在推行国家化、一体化中的文化政策,同时表现出因地制宜的多元性。针对贵州苗疆出现的“冒籍”问题,乾隆采用取消“苗额”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虽然这样可以彻底杜绝了汉民占用“苗额”的现象,但这种损害苗民的教育权益的做法也使得苗民子弟通过科举上升的通道变窄。这样“一刀切”的政策虽然强化了苗疆的国家化与一体化,但也忽视了民族地区的多元性,为日后的苗疆稳定埋下了隐患。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雍正时期开始在“新辟苗疆”推行科举政策,是清朝对于苗疆治理政策的一贯体现,具体表现出在推行的地域上“先湖南后贵州”,适用的对象上“先熟苗后生苗”的特点,即在推行地域和适用的少数民族人口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可以说贵州“新辟苗疆”科举制的推行也是一种必然。当然,针对贵州苗疆具体的情况,清政府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也对科举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来看,科举制政策在“新辟苗疆”的推行大致是成功的,它促进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学在该地区的传播,加强了苗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联系,而科举考试所采用的统一的考试内容,有利于苗民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心理素质和价值追求。虽然在实行过程中存在苗民子弟专门名额较少和“冒籍”的等权益受损的问题,但伴随着科举推行而产生义学和书院使得当地文教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最后,从历史对现实的启示来看,清政府通过文教作为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久稳定的政策,即通过推行科举和学校教育增进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在当今仍然具有价值,至于如何保障给予少数民族学子考试的优惠政策更加合理和真正落实,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同样是今天需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