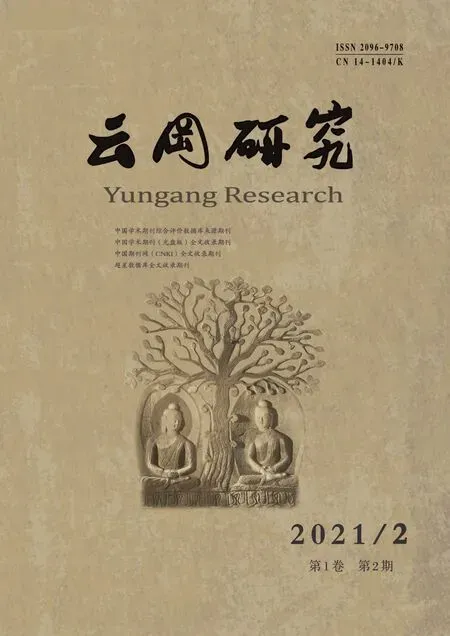云冈、龙门石窟屋形龛溯源试论稿
张善庆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佛教艺术从古代印度东传中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工匠根据自身的认知与审美重塑佛教艺术。屋形龛和阙形龛的出现就属于典型案例。河西石窟一改古代印度盝形龛,以汉地双阙为蓝本,创造出阙形龛。这种龛形成为兜率天宫所特有的标志,构成了“补处菩萨+双阙”的组合。云冈石窟则引进了殿堂,并由此创造了屋形帷幕龛这种新样式。(图1)梁思成先生指出,云冈石窟浮雕屋顶都是四注式,没有歇山、硬山和悬山等等;龙门古阳洞则有作歇山式的小龛。[1](P57)在云冈石窟,屋形龛被大量运用到洞窟内部壁面和石窟外壁立面的装饰,形式多样,所包含的内容也异常丰富。[2]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屋型龛也传播到龙门石窟,在形制上,虽有继承,但更有发展,包含歇山顶和庑殿顶。[3](P177-178)由于屋形龛中的尊像并不限于菩萨,还包括诸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故事等等,(图2)在此笔者简称“佛/菩萨+殿堂”组合。

图1 云冈石窟第11窟屋形龛(采自《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图2 云冈石窟第9窟屋形龛(采自《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耐人寻味的是,阙形龛只出现在河西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和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在中原石窟却无迹可寻;屋形龛盛行于云冈、龙门等石窟,其影响则没有波及河西石窟。两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组并行不悖的平行线。在分析中国北朝弥勒信仰时,王静芬先生也曾提出过弥勒造像龛形在敦煌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的不同。[4](P302-304)[5]问题是,内地工匠在重新塑造佛龛的时候,为什么会把殿堂建筑引入石窟?屋形龛的源头在哪里?对此,日本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先生曾经指出,屋形龛来自楣形龛(即盝形龛——笔者注),楣形龛是平顶的屋顶,常常连同角柱表现出来,代替这种梯形龛则用了中国的瓦屋顶。[6]据此,屋形龛的出现似乎是因为它和盝形龛在外形上的相似性。王洁、赵声良先生更将两种龛形的差异追溯到文化差异,认为:“建筑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阙是作为一种识别尊卑,向人示威的礼仪性建筑存在的。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大力倡导佛教而兴建了云冈石窟,采用汉式建筑的屋形作为佛龛,却没有采用阙形,说明在对传统建筑的理解上与长期以来深受儒学浸淫的敦煌有着一定的差异。”[7]这一论点颇具启发性。
宿白先生曾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详解云冈石窟开凿前后北魏政权强制性聚集人力和物力的情况,全面展现云冈石窟艺术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中西交通等历史信息。[8](P176-197)后学就是在这一大作的引导下所做的一点尝试性探讨。拙稿《河西石窟阙形龛溯源刍议》[9]曾对河西石窟阙形龛造型进行溯源研究,本文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殿堂或者说图像中的殿堂为什么会被汉地工匠单独甄选出来雕刻在佛教洞窟中?“佛/菩萨+殿堂”或者“西王母+殿堂”对于中原社会而言是否具有特殊的意涵?
一、汉晋墓葬“西王母+殿堂/楼阁”遗存
在中国石窟寺营建史上,云冈石窟尚属于初期阶段。在此之前,屋形龛虽然也出现在单体佛教造像上,但从现存遗迹来看,除了颇具争议的魏文朗造像碑,似乎屈指可数。①陕西耀县碑林博物馆所藏魏文朗造像碑雕刻屋形龛,内刻尊像,碑左侧面上层龛内为一铺三身像,主尊两侧各有一身胁侍。但是本文暂时不把该碑放入讨论之列。学术界一直对其纪年题记“始□元年”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是“始光元年”,代表文章有李凇:《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考补》(《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9-452页);Dorothy C.Wong.Chinese Steles: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缪哲:《魏文朗造像碑考释》(《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1期,2006年,第1-50页);李改、李文军:《关于魏文朗佛道造像碑纪年的考释》(《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46-48页)。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碑是6世纪初的作品,代表论著是石松日奈子:《关于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魏文朗造像碑”的年代——始光元年年代新论》(刘永增译,《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筱原典生译,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胡文和:《陕西北魏道(佛)教造像碑、石类型和形象造型探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第76页)等等。此外,至今我们尚未发现更多的同一时期的屋形龛方面的考古资料,魏文朗造像碑便成为“孤证”。该碑阳面和阴面主龛并不是屋形龛,而是龙首龛梁的圆拱形龛或者券形龛,屋形龛的特色不突出。如果追根溯源,除了早期佛教造像以外,我们拟以汉晋墓葬西王母图像为中心。至于个中原因,笔者已经在拙稿《河西石窟阙形龛溯源刍议》[9]中详细论证,为保持本文的完整性,再次说明,并作补充。
其一,北魏在扩张过程中数量庞大的技术工巧被汇集到平城,从而完成云冈皇家石窟的开凿。对此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已做详论。[8](P178)能够在巨大的山体岩石上开窟造像,在造像前构建大型的殿前建筑的“伎巧”大概有两个来源,一是给活在世上的人修造房子的工匠,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在已经基本荡然无存,再者就是给死去的人构筑地下墓室的工匠,我们通过考古资料还能领略他们高超的技艺。古代传统伎巧讲求师徒或者家族手手相传,在风格上表现出很强的保守性,尤其是墓葬文化更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墓葬艺术图像要素往往具有较长的生命力。从统计的结果来看,许多迁徙人口的原籍是两汉画像石非常发达的地区,而且从这一时期造像碑的雕刻风格看,它们和汉画之间存在无法剪断的联系。因此北魏历次入迁平城的人口特别是汉代画像石发达地区的人口尤其值得关注。
其二,西王母图像是连接早期佛教图像和汉地传统艺术的纽带。在佛教传入之后,佛教造像和西王母图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互动关系。当时人们对佛陀和传统的仙人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模糊。这种模糊性恰恰成为连接佛教艺术和传统工艺的纽带,是内地工匠改造佛教艺术的开始。根据王苏琦先生的研究,早期佛教图像实践发生在既有西王母实践的区域内;和西王母图像相似,它多出于丧葬情境,结合其时空分布规律推测,它很可能是沿着西王母既有仪轨而进入这个情境的;在图像志方面两者存在互相借用标志性特征和共享相似图像结构的情况。[10]
其三,学界研究也证明,汉晋时期以西王母图像为代表的图像系统对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敦煌莫高窟以第249窟为代表的龙车凤辇图、启门图就可以上溯到汉画,特别是升天图。[11](P1-24)[12][13]他们两者之间不仅仅是图像要素和艺术设计风格存在继承性,而且所表达的意涵也有共通性。学界已有的个案研究再次揭示汉画与佛教石窟、西王母图像和佛教尊像之间的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关联。
因此早期佛教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西王母图像传入的。其影响是汉地工匠也往往会依照西王母造型,进行佛教艺术创作。那么西王母图像中的建筑样式,比如楼阁、殿堂乃至双阙,也就有可能被照搬到佛教建筑艺术当中。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以西王母图像为中心的考古材料。对此李凇先生对西王母图像地域时代特征、载体材质、图像志等方面已做深入剖析论证。[14]拙文也是在此大作的引导下展开的。
在墓葬美术中,最为常见的西王母形象是,戴胜,危坐于龙虎座或者悬圃上,搭配图像主要是玉兔、三青鸟、九尾狐和昆仑山等等;发展到东汉,东王公方才与西王母图像搭配对称出现。通览全国汉代画像石和壁画墓,直接和建筑有紧密联系的西王母图像相对集中,并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主要为两种类型。一类和双阙结合,另一类和殿堂楼阁结合,具体情况如下。
A型“西王母+殿堂/楼阁”模式。这类资料主要是画像石,另有一例为北魏壁画。按照图像内容,尚可分为两类。①在此类图像资料中,部分汉画人物是西王母还是女墓主人,我们无法确定。这批资料同样包含殿堂和楼阁两种建筑样式。对于神仙图像配置的随意情形,张欣提出“同一组图像先后被配置于三种位置,他们是世俗化了的西王母、东王公形象,还是升仙后的墓主夫妇形象?人与神仙的界限在此模糊了。”(张欣:《规制与变异——陕北汉代画像石综述》,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研究》(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
Ⅰ类 “西王母+殿堂”模式
1.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汉代画像石。左格刻画一小型殿堂,左右两边设有立柱,上设栌斗。殿檐下饰有连弧形垂帐纹。中有一人端坐在几后,发冠奇特,此人应为西王母②原报告认为此图像乃是东王公,信立祥先生(《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李凇先生(《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订正为西王母。,殿堂外面左右各有树一棵,下部立鸟首、马首、蛇身等神祇和一人。[15]时代为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图3)

图3 山东微山岛画像石(采自《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调查报告》)
2.山东微山县微山岛M20G2石椁东侧板画像石。西王母头上戴胜,凭几危坐于殿堂之内,堂外左侧玉兔捣药。殿堂前面有鸡首、马首、蛇身、鱼身神祇。[16](图26)(图4)

图4 山东微山县微山岛M20G2(采自《山东微山县微山湖汉代墓葬》)
3.陕西绥德四十里铺墓门右立柱。从上往下第一格,殿堂中,一人正在朝拜戴胜妇人。③学界一说认为是朝见图(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183),一说认为是西王母(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图5)

图5 陕西绥德汉代画像石(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
Ⅱ类 “西王母+楼阁”模式
这类资料主要集中于鲁南和苏北,部分来自陕西。
1.江苏沛县栖山汉墓3号中棺东壁画像石第一组。[17](P111,图6、图7)
2.山东微山县微山岛M20G1石椁东侧板画像石。(图6)[16](图24)

图6 江苏沛县栖山汉墓三号中棺(采自《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3.山东微山县微山岛M20G4石椁东侧板画像石。[16](图30)
4.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石椁画像。[18](P69,图20)
5.陕西米脂县党家沟门楣石。①对于这两身图像,学界释读不一。李凇先生认为是西王母和东王公。(详见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第163页)《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则认为是升仙羽化的男女墓主人。(详见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图25)
6.陕西米脂县官庄东汉画像石。(图7)②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编著:《米脂官庄画像石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报告称“疑是墓主人生前景象”。(吴兰、学勇:《陕西米脂县官庄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7年第11期,第999页)

图7 陕西米脂县官庄东汉画像石(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
B型“西王母+双阙”模式。这类资料丰富,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如果按照载体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类。
Ⅰ类 画像石
西王母图像集中在石棺,代表有泸州1号汉代石棺[19](图版158)、乐山肖坝石棺(图8)[19](图版67)、简阳县鬼头山3号崖墓石棺。[19](图版98)

图8 乐山肖坝石棺汉画像(采自《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
Ⅱ类 铜牌
代表是重庆市巫山县9件鎏金铜牌。[20]
Ⅲ类 摇钱树
西王母造像或在树干,或在树座。代表是成都钱币学会所藏摇钱树[21]、绵阳河边东汉崖墓摇钱树座白M2:4(图9)。[22]

图9 绵阳河边东汉崖墓摇钱树底座(采自《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
殿堂、楼阁乃至双阙都是汉画中出现的、和西王母图像结合的建筑形式,它们似乎成为了仙人世界的代表符号。“西王母+双阙”模式的出现和四川为中心画像石分布区所特有的天门观念相关,[23][24](P27-34)在此不赘。“西王母+楼阁”和“西王母+殿堂”模式出现在山东、江苏和陕北,也许是由于两地之间的联系所致。据李凇先生研究,诸多案例表明陕北、晋西北画像石与鲁南、苏北地区关系紧密,这和陕北籍官员任职外地、外地官员移民陕北有关,同时与山东地区画像石传统和西王母信仰强大的辐射力有关。[14](P170-172)“西王母+楼阁”也许源自汉人的神仙观念。《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公孙卿曾进言:“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25](卷12《孝武纪》,P478)A型Ⅱ类,西王母东王公全部置身于楼阁之中。至于“西王母+殿堂”,笔者下文详论。
三、“西王母+殿堂”和“佛/菩萨+屋形龛”
根据上文所述,汉画中的西王母图像资料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显示出强烈地域性,特色显著;另一方面它们和中原地区、河西地区石窟寺中的屋形龛、阙形龛相对应。具体而言,以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和山西陕西北部为中心的地带,同中原云冈、龙门石窟毗邻,汉画“西王母+殿堂”模式和石窟寺“佛/菩萨+屋形龛”模式相类。以四川为中心的汉画集中地和河西石窟相毗邻,“西王母+双阙”模式和“补处菩萨+阙形龛”雷同。这似乎不是出于一种偶然。这两种构图模式可能分别就是阙形龛和屋形龛各自的源头。那么屋形龛和汉画中的殿堂有怎样的联系?“西王母+殿堂”和“佛像+屋形龛”这两种构图又有怎样相通之处?前者是否有进入佛窟的契机?
(一)阙形龛溯源探讨所提供的借鉴
拙稿《河西石窟阙形龛溯源刍议》[9]认为,河西石窟“补处菩萨+阙形龛”模式的创意来源可能是汉晋三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西王母+双阙”模式。当时蜀地是联系河西和江南的重要交通枢纽,经行这里的政府使节乃至高僧商贾络绎不绝。他们活动或者经行的地区也多是汉代画像石发达和天门思想兴盛的区域,这为“西王母+双阙”的北传提供了条件;“补处菩萨+阙形龛”(图10)和“西王母+双阙”(图11)不仅构图模式雷同,图像意涵也相通,都是表现人们所向往的死后的往生空间,表达了对极乐,对永生的向往。无独有偶,在早期的几铺净土变中,双阙又被拿来表示净土世界的入口;另外从考古资料上看,河西地区虽然也有天门观念,并创造了照墙天门造型艺术,但是和“补处菩萨+阙形龛”尚有一点距离,四川模式的传入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补处菩萨+阙形龛”提供了摹本。

图10 敦煌莫高窟第275窟补处菩萨和阙形龛(采自《敦煌学大词典》)

图11 重庆巫山县鎏金铜牌西王母与双阙图像(采自《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
如果拙稿观点成立,那么接踵而至的一个问题是,集中在山东江苏等地的另外一种构图模式是否会催生屋形龛。因此,阙形龛的溯源讨论一定意义上可以为屋型龛蓝本研究提供对比性借鉴。
(二)“ 西王母+殿堂”和“佛像/菩萨+屋形龛”构图模式的对比考察
山东微山县微山岛画像石中的殿堂是一庑顶建筑,阳刻简瓦,檐下有垂障纹,大殿有两个立柱,上部设有栌斗。由于汉画的面积比较小,不能够精雕,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魏文朗造像碑屋形龛省略了立柱和垂障,而只是一个简单的殿堂屋顶。云冈石窟中的屋形龛形制前文已经简述。它吸收了微山汉画中的庑顶殿堂,把斗拱、人字叉手和阑干一一细化,并增加了金翅鸟、素面三角形等装饰。再者,微山汉画殿堂中的主像,体型大于其他仙人。她凭几而坐,正面危坐在殿堂中央,两侧为胁侍,其构图模式类似于佛教造像中一铺一佛二菩萨的对称性构图。云冈石窟“佛像/菩萨+屋形龛”模式多具有这种特点。例如,第10窟前室东壁就有大型屋形龛。交脚佛坐在殿堂的中央位置明间中,胁侍菩萨位于两梢间,交脚佛和两个站立的胁侍菩萨的高度相当。可见这种图像的结构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西王母+殿堂”模式影响较远。在此本文引用一个典型案例——固原北魏漆棺。报告称墓葬年代为北魏太和十年(486年)左右;棺盖正中上方有两座悬垂帷幔的单层庑殿顶房屋,鸱尾翘起,二层阑额间有一斗三升和人字斗拱,柱呈黄色,帷幔下垂;左侧屋内榻上坐着男子,盘腿袖手,头戴黑色高冠,左右各有一无冠女侍立;右侧屋内女子,屋内设置和人物服饰等与左类似。左屋左侧有墨书榜题“东王父”三字,右屋左侧也有榜题,但已经残缺;屋顶正中各有一只金翅鸟,展翅欲飞。(图12)[26](P8-9)这条材料弥足珍贵,因为根据笔者涉猎,三国两晋北朝初期,西王母图像几乎是空白,更遑论西王母与建筑相结合的图像了。北魏漆棺画和汉代画像石遥相呼应,展示出墓葬绘画艺术虽然历经百年社会动荡但未曾中断。

图12 西王母东王公图像摹本(改制自《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相比之下,云冈石窟“佛像/菩萨+屋形龛”和汉代画像石“西王母+殿堂”非常相似,而且和固原北魏漆棺画中“西王母+殿堂”如出一辙。
首先,常见的殿堂形制是:顶部为庑顶,鸱尾突出,瓦脊高耸,中央立有金翅鸟,也多饰有素面三角形;檐下为斗拱,多为一斗三升,中间刻有人字叉手;椽子、简瓦和帷幕都被极被精巧地刻镂出来;有些立柱把殿堂分为三间,主像置身于明间,胁侍菩萨在两梢间;主像同胁侍菩萨共处在明间的情况也有;有些佛龛还有台阶和勾栏,并装饰了忍冬等纹样。屋形帷幕龛是由它演化出的新样式,其下立柱多被省略,颇似一个华盖。由于瓦屋顶长度不一,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便于表现复杂的故事情节,例如佛教故事,也能容纳更多的尊像,例如七佛。龙门石窟屋型龛则沿袭了云冈屋型龛的内容题材。对此,王恒先生对石窟中的瓦顶建筑进行了分类归纳,并就其产生的影响作了探讨;另外就屋形龛和科林斯浮柱在表现佛教造像中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27]张华先生则对第9和第10窟中包括屋形龛在内的6种建筑形式进行介绍,根据具体形象的不同,将屋形龛分为4类进行论述。[28]
其次,主尊全部为偶像式构图。①关于偶像型和情节型构图的概念,请参见[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9-150页。上述鲁南和苏北的“西王母+殿堂”图像中,西王母全部为正面,而不是四分之三侧面。侍从分列于两侧。整体来看,主尊造像形体大于侍从,从而形成主大从小的模式。这和云冈石窟“佛像/菩萨+屋形龛”非常接近。屋形龛和佛教故事画的组合暂且不论,“佛像/菩萨+屋形龛”模式中,诸佛与菩萨呈现完全的正面,形体较大,左右胁侍围绕在两侧,形体较小。整个构图几乎就是固原北魏漆棺西王母图像组合的翻版。
(三)两汉佛道观念的混同与图像模式的借用
作为异域文化,在传播初期佛教主要依附中原社会传统的黄老道术发展起来,所以东汉汉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29](卷7《孝桓帝纪》,P320)楚王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29](卷42《楚王英传》,P1430)以至于《老子化胡经》编纂流通。当时一批高僧在讲经说法的同时,还兼通占卜医术、阴阳神咒。[30](P31-34)[31](P126)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开始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竭力从黄老道术的影子中走出来。
佛教初传时期的这种态势,在图像中也有所反映,仙佛并存。温玉成先生称之为“仙佛模式”。[31](P159-170)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就曾在两汉墓葬和祠堂等地上建筑中发现多例佛陀与西王母、东王公以及老子等等被同等或者混同对待的案例。拓跋氏迁都平城之前的故都是盛乐,其附近的和林格尔墓葬“猞猁”、“仙人骑白象”等题材和西王母、东王公一样各自占据墓顶的一坡。[33][34][35](P26)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东西两面是东王公西王母,南北两面上部各存有一身佛像,温玉成先生将北面的一尊考定为弥勒。[32](P164)另外,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中,老子图像和坐佛、立佛、涅槃图以及舍身饲虎图混杂在一起。在川渝地区,佛像还代替了西王母,出现在摇钱树、崖墓的门楣上。因此,王苏琦先生认为,早期佛教图像主要出现在原有的西王母图像集中的地区,并沿着西王母的图像仪轨出现在丧葬情境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佛像和西王母图像还存在标志性特征共享的现象。[10]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此时的佛教依附于黄老道术,内地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佛教,其结果就是当人们创作佛像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先前对待神仙的“礼遇”转移到佛像身上。这样汉画中“西王母+殿堂”模式就为佛教艺术“佛像/菩萨+屋形龛”模式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四)汉画发达地区人口迁移与汉画传统的续写
汉代画像石“西王母+殿堂”模式图像资料主要出现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陕西东北部、山西西北部,这是汉代画像石两个重要的分布区域。[36](P13-21)在拓跋氏统一北中国的过程中,就曾经从这些汉代画像石发达的地区掳掠过大量人口,其中就包括能工巧匠。正是鲜卑族统一北中国前后这种连续持续不断的人力的集聚成就了云冈石窟如此辉煌的艺术魅力。[8](P176-179)
太延元年(435年)拓跋焘“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37](卷4上《世祖纪上》,P84)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37](卷4下《世祖纪下》,P100)如果说太延元年条记载没有说明移民的行业,那么从太平真君七年条记载看,移民的“工巧”身份则非常明确,而且具有一定规模。颇富争议的魏文朗造像碑所在地耀县距离西安不到100公里。如若其年代确定为始光元年(424年),它比云冈石窟早40年,但是已经开始利用屋形龛。[38][39]它的时代如此之早,也就更能接近画像石发达的时代。较之其它画像石发达地区,耀县与画像石第五分区中心洛阳以及第三分区陕西山西空间距离接近,与后者(A型Ⅰ类3)地理上更加接近。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这三者之间便可联系起来了。
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徙西河离石五千余家于京师。”[37](卷4下《世祖纪下》,P102)山西省离石自上个世纪不断有画像石出土,[40][41][42]与它一河之隔的陕西米脂同属一个画像石分区。这两地的画像石风格是一致的。主要因为,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北方匈奴的侵扰,上郡和西河郡的治所分别从陕西山西长城沿线一带迁到夏阳和离石。所以山西离石的作品基本是东汉晚期的,是陕北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装饰多集中在门楣上;门楣上都是出行图;门柱上部多是坐在悬圃上的西王母和东王公,或者是牛头和鸡首人身的形象,下部是门吏和玄武或博山炉;整个门饰的周围刻有云气纹或忍冬纹。因此虽然没有山西离石的资料,但是B型3却能看到它的影子。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37](卷4下《世祖纪下》,P100)正平元年(451年),淮南降民五万余家被安置在京师附近。[37](卷4下《世祖纪下》,P105)皇兴三年(469年)青齐望族也被迁徙。[37](卷6《显祖纪》,P129)这时候山东南部微山湖地区和江苏北部徐州地区已经被囊括在它的统治范围内。上述的A型I和Ⅱ就在此列。关于青齐地区伎巧对平城的影响,宿白先生有详尽深入的探讨。[8](P190)《水经注》记载,太和七年(483年)皇信堂建造,其“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贤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辨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43](卷13《㶟水》,P1143-1144)设计者就是青徐营户。“古圣忠贤烈士”历史人物,也是汉画的一个重要题材,主要是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的道德观。画像旁边往往配有题记以示分别。以武梁祠为例,三皇五帝、忠臣贤后、烈女义士等图像刊刻其中,正所谓“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贤烈士之容,刊题其侧”。可见北魏的许多重要工程也沿袭了传统手法。
“西王母+殿堂”的构图模式很有可能就是随着一股又一股的移民浪潮进入京师。这些移民按照规定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魏书》记载,拓跋焘下诏:“……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37](卷4下《世祖纪下》,P97)这就限制了工匠向其他阶层流动的自由,客观上汉画传统得以续写,传统观念也得以体现在佛教艺术之中。
结语
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屋形龛和敦煌莫高窟的阙形龛一样,是古人对佛教艺术的一次改造,殿堂和双阙的出现拥有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从上面的论述看来,屋形龛不同于莫高窟的“借用”。敦煌莫高窟阙形龛代表兜率天宫;四川“西王母+双阙”反映了蜀人的天门观念,所以两者有一个相通之处,它们都代表人们所向往的往生空间,弥勒和西王母、东王公是这个空间的教主。但是云冈龙门的屋形龛则不然。佛像之所以被放置在原来仙人所使用的殿堂内,是因为时人对“仙”和“佛”认识上的模糊,对“佛”的概念也是笼统的,所以屋形龛没有往生空间的味道,更不是兜率天宫补处菩萨的专用龛形,而是包含了诸佛、菩萨、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等等。
本文主要对屋形龛进入佛窟的过程做了简要的推论。不过,画像石墓在三国之后就已经走向了没落,本文只是搜集到在此之前的资料。由此到武州山的开凿,中间存在很大的空档,其中的变化情况不是很明了,有待进一步调查。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5年夏,原题为《敦煌莫高窟阙形龛溯源——兼论云冈龙门屋形龛》,后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也经历了若干次修改,终因篇幅过长,最后一分为二。修改稿《河西石窟阙形龛溯源刍议》后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云冈龙门石窟屋形龛溯源试论稿》则迟迟未刊。今蒙《云冈研究》厚爱,笔者特此奉上,在此也谨对长期以来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师友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