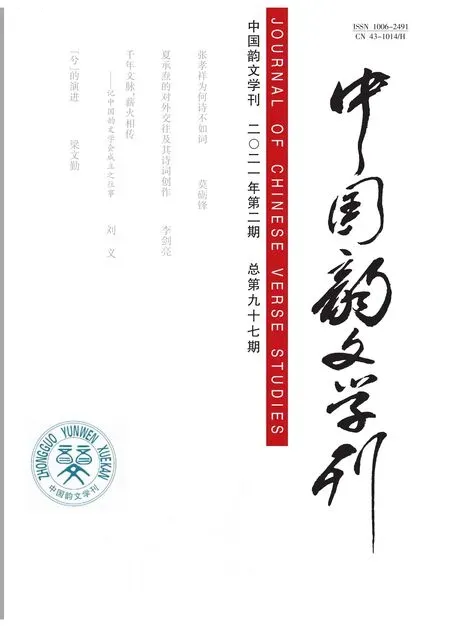先秦两汉“歌”、“诗”及“歌诗”的概念移嬗
——“概念”视域下诗源辨体的理论践行
刘士义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前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体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其实质就是一部中国古代诗体嬗变史。中国古诗体系涉及诗本体及其诸多衍生体,诸如歌诗、乐府、歌行、近体等文体皆可视为因诗体概念移嬗而产生之变体。迄今,在诗歌发展史研究领域,学界多将诗体及其衍生体视为独立的文体学现象,对于诸者之间的“本体与现象”、“歌”与“诗”及“歌诗”等关系研究则相对薄弱。然而,“诗”之概念本自人为,而后又因“诗”理论发展而产生概念移嬗,进而出现“诗”体衍变。以此论之,诗之本体与变体之关系在于“诗”本体的品质转移与“诗”概念范围的移嬗所致,两者相互作用,从而完成“本体与现象”“理论与事实”的“诗”体实践活动。因此,探讨诗体嬗变就必须以名与实、概念与本体为认知基础,寻找诗体嬗变的内外促发因素,从而揭橥诗体嬗变的本质规律。
对于概念与本体及其范畴的认识,先贤古哲已有洞彻之分析,荀子曾言:“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诗”概念之产生乃先民利用政治工具改造社会政治的实践产物,“诗”体源自“诗”理论的社会实践,而“诗”体则是“诗”概念理论形成后指导社会实践之产物,所以“诗”概念与“诗”体之关系的实质是“实践(讽谏性的政治需求)—认识(“诗”概念)—实践(“诗”体)—认识(“诗”本体及变体)”的认知过程。诗体嬗变之动因源于政治、文化、教育等外在社会元素与“诗”体概念之内在因质的合力促成。时下学界对诗体及其变体的研究多流于现象层次的探析,而对诗体嬗变的内外促发因质并未进行过多的阐释,且将“诗”“歌”等而视之,实乃以今世静态之视角掩盖了“歌”“诗”“歌诗”诸体的嬗变及分合过程。
一 “歌”与“诗”的概念纠缠
在社会认知领域,概念体系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总结,人类的认知维度及广域是由无数层级的概念及其定义构成的。人类通过对概念及定义的不断修正与更替,从而实现认知层次的进步与跨越。一个成熟概念的形成及定义过程牵连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其不仅涉及概念形成的社会环境以及语源实践与意义等问题,亦与人类的求知欲与认知视野有着密切的联系。概念所秉持的认知视阈与实践意义使其持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功利性。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于揭橥“诗”概念与诗体嬗变之事实,并探赜“诗”本体与其衍生体的渊源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出诗体发展的理论框架。
一部诗学发展史其实质就是“诗”现象及“诗”概念的交替作用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语源概念,“诗”概念的出现有其必然的诱导因素与外设环境。在探讨“诗”体嬗变时,必然会提及其先导事实,即“歌”体的嬗变状况。在先秦著作中,“歌”“诗”两体具有颇为复杂的概念纠缠关系,其拥有各自的概念体系,但其功能涵域却有着巨量的重叠空间。通识而论,后世因“诗”“歌”二体而产生的“诗”体概念包括两汉之“歌诗”、魏晋之“乐府”、南朝之“歌行”与唐代之近体等。除此之外,两宋之词体、元代之散曲与明清之民歌亦以“乐府”命世,此亦可视为“诗”体概念移嬗之结果。
作为一个成熟的语源概念,“诗”“歌”“歌诗”诸体的定义、命名及发展与社会认知的强力助推有着密切联系。宗周时期,新晋“诗”体对传统“歌”体概念场域的侵食及相融,实质上反映了政治势力改革传统语源概念进而实现政治诉求的强大操控能力。“歌”“诗”以及因其而产生的“歌诗”等概念体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陶染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歌”体概念是一种通行于社会各群体的自由文化概念,而“诗”体则带有强烈的时代性,这一点使我们在探讨“诗”概念及其衍生体时显得尤为关键。自“诗”体概念形成后,在周代至秦朝的历史维度里,“歌”与“诗”是两个并行的文化概念,虽然时有交集,然而大体仍延续各自的概念体系前行。只不过,由于“诗”体与政治及礼乐文化的密切结合而产生较大的概念体系嬗变。因此,探讨“诗”体内部嬗变的关键就表现为对不同时期影响“诗”体概念移嬗原因的探究上。
对于“歌”“诗”二体的起源及渊源关系,历代治经者多陈陈相因,将其溯及《尚书》与《诗·大序》。然而,作为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概念体系,“歌”与“诗”都有其各自的文化溯源与成因。荀子有言“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即以为证。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概念,“歌”体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的人类发声,其形成乃社会语言的自然促发。其过程是先有语言便利之成形,然后才据之而约定为通俗的语源概念。在人类原始语言的形成期,大量的人类行为与认知对象被逐步定义并形诸概念,人类的思维逻辑并据之以形成。
以语源学而论,原始的“动—名”词定义与其中心义项所涉指的行为动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动—名”词特指中国古汉语中兼具名词与动词或形容词等多种词性的兼类词汇。在古汉语中,词性的分类并不明显,其语言逻辑仍然遵循以义项为中心的组织状态,而义项则依赖于定义及概念而存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以名词性为中心的词汇其本质仍然是定义与概念的结合体。在上古语源词汇中,兼名词与动词属性的词汇定义过程有两种形态:其一,以名词性概念为中心,进而延伸出动词性的实践意义,如甲骨文中“老”本义为老人,后逐渐产生“年龄增长”的动词意义;其二,以动作定义为中心而生发出名词性概念,如甲骨文中“歌”本义指开口之动作,进而形诸名词性概念,即先形成与具体动作或行为相对应的语音词汇,然后再孳乳出与此动作相对应的名词性概念。

那么,当“歌”之语音与义项逐步实现“动—名”词转化时,“歌”概念亦伴随“歌”现象的定义而渐趋形成。“歌”概念的定义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即具有一定的音律节奏并附着特定情感及意义的语音行为。它突出了“歌”体概念的两个充要因质——音律节奏与情感意义。原始“歌”概念的执施范畴则表现为表达一定情感意义的徒歌行为。《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四音”即是明证。孔甲、禹、整甲、有娀氏诸事,后世称其为四方徒歌之滥觞。与之相应,“歌”概念的功能场域集中于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表现,并未上升至政治及文化等层面。
随着时代发展,受政治及文化之影响,“歌”的概念体系逐渐拓展至礼乐祭歌与庙堂讽谏等领域。降及礼乐时代,由于祭祀与娱乐文化的普及,“歌”体概念逐步拓展至与器乐旋律相关的音乐系统。敬天祭祖的宗教乐词体系逐步成为“歌”体的基本功能领域。《尚书·尧典》所载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训语,即是“歌”体功能场域拓展的明证。与此同时,“歌”的功能场域亦实现了个体情感抒发向群体性的政治讽谏功用拓展。《尚书》所传载的舜与皋陶唱和之《赓歌》、五子规谏太康之《五子之歌》等,均可视为“歌”体概念体系的整体拓展。
总而言之,“歌”之概念形成于人类的自然用语习惯,乃是因“动—名”词性的过渡而形诸定义的过程。“歌”体概念本初为具有一定的音律节奏并附着特定情感及意义的语言行为。乐律发明后,最初的“歌”概念体系发生了整体拓展与移嬗。首先是“歌”概念由附着情感的徒歌拓展为合乐演唱的乐词系统;其次,“歌”体的功能场域由抒发个体情感的语音行为拓展至具有祭祀仪礼性质与政治讽谏功用的实用性文体。由此可推断,时至尧舜禹汤时代,“歌”体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化概念。与其相较,“诗”体概念的定义及其体系的形成则远为后出。“诗”体概念亦因牵涉过多的政治、文化、传播等因素而呈现与“歌”体迥异的替嬗过程。
二 “诗”概念及现象的几个问题
与自然形诸体系的“歌”概念不同,“诗”概念本身即是一个成熟的语源概念,并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品质。“诗”概念之形成乃是先民刻意为之的造语行为。相较于“歌”体现象所体现出的集体潜意识,“诗”体之出现带有周部族群体的初始认知与功能欲求,并浸染此时代的意识形态,亦不排除周部族在征服商王朝并建立自己统治体系时所标新立异的胜者塑造。显而易见,周初之“诗”概念与孔子时代的成熟“诗”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异。周初贵族所用之“诗”乃是一种政治性的讽谏文体,与相近时期之《风》《雅》《颂》等功能文献有较大的指称重叠。降及春秋,孔子所指之“诗”概念则是一个涵盖《风》《雅》《颂》三种不同文本体系的“诗文类”。从周初的文体特指到春秋时期的文类泛称,再到孔子删定的《诗》文本,实质上反映了“诗”概念及其现象移嬗的一个发展过程。
从概念衍生及嬗变角度而论,“诗”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诗”概念、“诗”现象、《诗》辑本与《诗三百》等滋生体系,甚至因后世“寺”系文字之音义转换亦产生诸多衍生概念。有鉴于此,对“诗”概念及其现象的历史性梳理及辨析,就成为“诗”学认知的重要场域。诗学研究离不开“诗”概念定义等核心问题,其包括“诗”体溯源、“诗”体定义与“诗”体功能等方面。从文字及音义角度而论,“诗”本义为“持”,后又因“借音异义”的造语行为而兼具“法令规范”义,并由引申为“讽谏,劝谏”等义项。《尚书·金滕》载:“公(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如果《尚书》所载乃是即时实录的话,那么基本上反映了“诗”体概念的初始状态,即“诗”之初始概念是“讽谏君王性质的语言或文本”,其使用范畴为“君臣之间有关政治的庙堂规谏”,而“讽谏性质的施政内容与君主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则是其直接应用。如此一来,凡是符合此概念品质的语言及文本均属“诗”体内容,由此亦促成第一批“诗”文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批“诗”文献是因“诗”之功用而形诸文本,所以这种“诗”文本是开放性质的,凡符合此“诗”概念体系的语言载体均可视为“诗”文本,这一点与后世的《诗》文献或《诗三百》辑本概念有着实质差别。
“诗”初始概念之应用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即政治性、讽谏性与臣君性。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原始“诗”概念的基本品质,由此可得出,“诗”实是因政治与文学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文化现象。“诗”概念直接引发了后世两大“诗”学现象。其一,因形塑礼乐文化而采集的地方音乐系统——《邦风》。降及春秋,《邦风》因其礼乐文化及政治意图而被施加“讽谏”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可以从“风”至“讽”之语源概念的衍生过程中体现出来。因“风”而“讽”的语源衍生关系,与由“寺”至“诗”的嬗变过程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其二,以歌谣谚语为主体、用于讽谏君王的邦国采歌传统。“采歌以干政治”是西周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采歌的执施者为王官与地方执事,而讽谏的主体则为邦国执政者。其中不乏部分作品流入王廷而被当作周王治事的重要依据。此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体系被后世统一编辑于“邦风”系统中,从而造成概念及体例上的分裂,后世诗论中有关“风体正变”之论题亦因此而产生。除此之外,此亦造成后世《诗·国风》中出现“周南”“召南”与其他邦风不同的《诗》编辑现象。
“诗”概念的第一次移嬗与周王朝的礼乐文献整理活动密切相关,是在具体礼乐仪式文本编辑活动中出现的衍生概念。西周初至东周中叶,因周王廷对王朝礼乐文化的系统整理而出现了礼乐仪式文本的系统结集。这种礼乐仪式曲辞及其用乐方式以文本的形式被系统地保存下来,从而为后世《诗》辑本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在礼乐仪式系统的整理过程中,执政者不仅继承了周初祭祖祀神的“颂”乐体系,亦拓展了庙堂礼乐的“雅”乐体系,更重要的是逐步吸收了“邦风”系统的音乐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各自独立的“颂”“雅”“风”被统一整合至仪式乐“歌”体系中,其文本亦全部音乐化,开创了“诗—乐”的系统融合,由此亦造成“诗”之使用范畴的巨大迁移,从而为传统“诗”概念移嬗奠定了事实基础。
西周礼乐仪式文本的结集引发了“诗”概念的整体移嬗,而“乐教”体系的建立与邦国政治的实际执施则将“诗”概念的定型进一步向前推动。当西周礼乐文化仪式逐渐严密且系统化时,周王廷的权力威信与统治力亦逐渐增强,王廷与诸侯之间的朝贡交流借之得以延续。政治的强势与传统宗主国的威信为礼乐文化输出提供了源源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礼乐文化输出成为王廷对诸侯加强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周王廷的礼乐文化输出政策是建立在周代乐教体系之上的礼仪规范及秩序输出。这种仪式与规范有效地维系了周王朝统治的等级、尊亲与秩序。《周礼·春官》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国之子弟”即为各诸侯国公卿大夫之子弟,其作为诸侯邦国未来的执政者,在西周王廷接受系统的礼乐文化教育后,便有意识地将这种礼乐文化实施于邦国政治之中。
在西周王廷所输出的礼乐文化中,适用于诸侯邦国的礼乐为“雅”乐与“邦风”,主要应用于诸侯礼乐及邦国聘问用辞。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把“雅”乐与“邦风”应用于本国政治及外交场合。在《左传》与《国语》中,“邦风”与“雅”系歌乐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聘问歌咏功能,而其中“邦风”的地位尤其重要,而“风”本兼“讽”义,而“讽”又为“诗”之特质,如此一来,“诗”之概念便逐渐覆盖了“雅”“颂”固有的概念体系。郑玄《诗谱》曰“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正是言此。伴随着“雅”“颂”文本在邦国聘问传统下不断地被“断章取义”“借诗言志”,“诗”便由与“雅”“颂”平行的概念体系而过渡至统一的“诗”文类概念。“风”与“诗”本是相对等的文体概念,但后世逐渐以“诗”来总括“风”“雅”“颂”,其原因亦是因“诗”与“讽”及“风”的概念嬗移而形成的。
当然,此时的“诗”仍然是一个文类性质的概念,它把因礼乐文化功用而形诸一体的“风”“雅”“颂”统一在这个宽泛的概念体系下,从而为《诗》文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由概念性的“诗文类”过渡到文献《诗》文本,其过程与“诗”文本编辑密不可分。《诗》文本是伴随着复杂的“诗”体概念开阖与“风”“雅”“颂”概念的嬗移而逐步推进的。这个过程可以在《左传》《国语》中以“诗”的衍生概念来代替“雅”“颂”初始概念的使用情况中得以佐证。迄今,由于材料所限,尚不能对“诗文类”过渡到“《诗》文本”的内在进程及具体时间做出准确的推断,但可以断定的是至少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宽泛概念性质的、以“诗”命名的《诗》文献出现,并且由于《诗》文本的辗转传抄以及诸侯邦国的礼乐文化自建活动,而出现了诸多版本的《诗》文本辑录。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可以推断在“诗文类”的概念体系下所存在的庞大《诗》文本数量与复杂体系,这个推断亦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事实依据。
以认识论衡之,由“诗文类”向“《诗》文本”概念的实质转型,直到孔子对《诗》文本的最终整理才得以实现。孔子的贡献在于对散存于诸侯邦国的《诗》文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工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个过程的实绩是《诗三百》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诗》定本而被整理出来,并且实现了由“诗文类”概念向《诗三百》文本的最终合流。孔子所整理之《诗三百》,是对流行于各诸侯国之《诗》文献的总结性整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诗》文本及其所代表的礼乐文化趋于崩溃,孔子之实绩在于以一己之力保存并维系了以《诗》为中心的礼乐文化。此后,孔儒学派便以孔子整理之《诗三百》立教于世,并区别于传统鲁学之《诗》学系统。降及两汉,儒学独尊,随着孔门儒学的发扬光大,《诗三百》最终成为《诗》文本的最终定本,而《诗》亦成为《诗三百》的专属概念而丧失了其原始的文献意义。
概而言之,“诗”概念与“诗”文本编辑是解决诗学研究的两个关键。“诗”概念的逐次嬗移与“诗”文本及《诗》辑本的递修整理,加之两者累积形成的认知堆砌,更加重了先秦诗学研究的困难维度。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规律的切入就变得非常必要。据此,结合《诗》辑本的历史编辑状况,并通过重点探赜“诗”本质及其概念移嬗的过程,从而对“风”“雅”“颂”与“诗”的概念合流、不同时期之《诗》文本与逸诗、孔子删诗与《诗三百》、《邦风》与《国风》等问题便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三 两汉“歌诗”的嬗变
作为两汉乐府实绩的主要艺术形式——“歌诗”,在诗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对“歌诗”之语源定义及概念嬗移等研究仍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乐府研究者多将“歌诗”简单地概括为“可以歌唱的诗”,并视之为一种成熟的“诗”体衍生概念。然而,这种粗放的定义方式不但忽略了“歌诗”形成的语源条件,亦遮蔽了“歌诗”发展的内外背景。如果仅以“歌唱”与“诗”两个要素来衡定“歌诗”内核的话,那么于认识逻辑亦多有抵牾。首先,“歌”概念本质即为具有一定音乐旋律且表达特定情感的人类发声,且乐府作品中亦多有以“歌”命名者,如果仅以“可以歌唱”而言,为何不径以“歌”来指代其体?其次,《诗经》在西汉的礼乐应用已臻鼎盛,如果强调乐府作品对“诗”体的直承性质,为何不径用“诗”或《诗》来指称?再次,“歌诗”概念的大量运用出现于东汉,“歌诗”概念主要表现了东汉人之意识,以东汉之概念来解释西汉之事实,岂不有以今律古之嫌?
究其实质,在于忽略了两汉“歌诗”嬗变的内外环境及其促发规律。作为一个在东汉频繁使用的语源概念,“歌诗”是东汉人对西汉乐府机构及其作品认识的总结性概念。东汉的“歌诗”文体秉承着西汉文体事实与东汉概念认知的二维品质。如果要洞察“歌诗”的本质及其嬗变过程,就必须联系西汉乐府建构的内外境况与“歌诗”形成的语源环境,不仅如此,亦须探赜东汉文人对西汉乐府及其“歌诗”作品的文学审视。总而言之,东汉“歌诗”之概念及其所指称两汉“歌诗”之事实均与其时代之政治及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又以东汉儒学的经今古文论争最为关键。
汉制初造,皇室搜求百家典籍以兴学术,儒、道、名、法、阴阳、纵横诸家皆为政府所用,其中又以道、法、儒为重,从而形成自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文化复兴。在此背景下,各种学说相互吸收与融合,孔门儒学亦逐渐吸收法家、阴阳、道家等思想,进一步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嬗变。降及武帝朝,在董仲舒等儒士的鼓吹下,儒学独尊并逐步形成了儒学与政治互为依存的共生关系,从而又反向促发了儒学体系的自我完善。儒家知识体系中的“诗”“礼”学说,完善了宗庙祭祀与朝堂宴飨的礼仪规范,并进一步刺激了词乐体系的蓬勃发展,礼乐与歌词实现了更加紧密的结合。然而,传统儒学中的《诗》《礼》仪制及庙堂用乐根本无法满足武帝朝对礼乐的巨大需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礼乐机构的职能拓展便成了重中之重。
西汉时期,承接礼乐职责的音乐机构有内外廷之分,外廷属太常管辖,主掌宗庙祭祀、廷宴礼乐等职;内廷属乐府,供内廷皇室歌舞享乐之用。宗庙祭祀、封禅仪范等国之大事本应以太常为中心而展开,然而武帝却故意避开外廷太常而刻意拓展内廷乐府的职责。《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这则材料向我们提供了与武帝朝乐府相关的重要信息:定郊祀之礼、采诗夜诵、赵代秦楚之讴、任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等造诗赋、作十九章之歌等内容。很明显,武帝有意混融了太常与乐府的职属范围以扩大内廷乐府的辖制。因为相比于受儒学仪制限制的外廷礼乐机构,内廷是武帝最直接也最容易控制的音乐机构,所以武帝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内廷之乐府来实现外廷礼乐之掌控。
武帝拓展乐府机构的直接目的有两个。其一,为了满足皇室对世俗音乐的享乐需求。原因很明显,“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与武帝及皇室关系最为密切。以武帝直系亲族为例,文、景、武诸帝均为楚人后裔,且文、景二帝起于代郡,文帝皇后窦漪房生于赵地,而武帝生于秦地,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采歌之实质正在于此;其二,建立统一的文化意识形态,以粉饰汉帝国的辉煌盛世。对于诗体嬗变来说,武帝造兴乐府对传统的诗礼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其意义在于赋予了娱乐“歌”体进入宫廷的正当借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娱乐性质的“歌”体逐渐被施以政治意义而具有与“诗”体并肩的文化地位。这种强烈的政治附会性促使“歌”体与先秦本已存在的“采风”制度相结合,逐步被形塑为“采诗观政”事实。这种累世堆积而成的认识过程夹杂着政治、文化、学术、教育等诸多因素。
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质是建立皇权统治之下的帝国文化统一,然而传统鲁地儒学的局限性使其根本无法承担这种重任。“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鲁地儒学所持承的传统礼乐文化,根本满足不了武帝的真正需求。武帝想要建立一个“大一统”旗帜下的文化盛世,而孔儒学派的“礼乐文化”学说则极大地满足了武帝的这种雄心壮志。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这则事实凸显了孔儒学派与鲁地儒学的博弈事实。公孙弘乃经今文学派的代表,徐偃则更倾向于传统鲁地儒学。在这场论争中,公孙弘与方士顺应了武帝的自我膨胀意识,而徐偃与周霸则坚守鲁地儒学、循持古义而不知变通。最终公孙弘的胜利巩固了皇权对孔儒学派的强力支持,亦预示了皇权对儒学实际掌控时代的到来。
伴随着武帝对儒学体系的强力掌控,乐府职能亦得到了极大扩充,从而进一步实现了乐府对外廷礼乐职属的侵蚀。“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武帝以名马为契机而随意制定宗庙祭礼乐歌,颇可说明因内府职能扩展而导致的内外廷矛盾冲突。如果联及武帝朝对儒学的掌控与李延年任协律都尉两则事实,那么问题的实质便昭然若揭。武帝扩大内廷俗乐机构职属之实质,就是利用内廷对外廷的礼乐职能侵蚀来实现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的意图。
武帝朝的文化一统建设直接促发了汉帝国文学的兴盛,骚、赋、歌(乐府乐“歌”体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乐府职能扩张至外廷庙堂礼祭等职责时,“歌”体亦实现了与传统“诗”体之政治地位的分庭抗礼。大量的乐府“歌”体作品被施以礼乐并赋予政治性职能,刘邦所作《大风歌》《鸿鹄歌》皆协之声律而被于宗庙,以及武帝时所创作之“十九章之歌”等皆可佐证此文体嬗变之事实。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之“歌诗”中,除了上述歌曲被施于宗庙礼祭仪式外,其他作品均未实施于宗庙礼仪。考虑到“诗”体及《诗三百》在西汉时期的巨大政治影响力,这些与政治关系不密切的“歌”体作品不可能存在被“礼乐化”的可能,更毋庸谈及“诗”化的条件了。因此可推断在“歌诗”概念下遮掩了不同含义体系的内在冲突,而这一冲突的调和则直到东汉经今古文的融合才得以实现。
西汉武帝时,孔门儒学与皇权执政形成了稳定的依附关系。武帝对孔儒学派的强力支持实现了“歌”体政治化与“诗”体世俗化的双向推毂。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歌”体得以世俗音乐身份进入庙堂礼乐,而“诗”体亦实现了文人参与的开放性状态。与之相应,《诗》学呈现出经今古文合注的文化现象,郑玄在《六艺论》中言:“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而《毛诗》《尚书》等经典的今古文合注,直接影响了“诗”“歌”与“歌诗”体的后概念时代的定义方式。
东汉以降,阐释儒典往往采用经今古文合注的方式,班固《艺文志》将“诗言志,歌咏言”解为“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即为明证。由此推知,“诗”“歌”至班固时期已作为平行文体概念来进行解释了。这种解释颇具古文经学特点,与《毛诗序》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及《诗谱序》中“诗之道放于此”不谋而合。这种释诂方式成为后世阐释“诗”“歌”两体的基本思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对“诗”之解释正是东汉经今古文合注方式的有力证据: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
可以推知,东汉经今古文学的释诂合流从学术上弥合了西汉时期因经学政治化而产生的诗与歌的文体分野。东汉时期,《诗》《书》等经典的文化互释为“歌诗”体的学术化定型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西汉武帝时期因乐府扩造而产生的“歌诗”体系在学术上得以正式巩固与确立。东汉“歌诗”体在学术领域的确立,不仅解放了西汉时期因经学政治化而产生的诗体束缚,亦为汉代诗体的文体开阖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在此背景下,乐府乐“歌”体系才得以在南北朝正式成为“诗”学之一体。
小结
由此观之,“歌”体源于上古人类对音乐、语言、情感、认知等现象的综合及抽象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约定俗成的自然概念。“诗”之初始概念则源于人类因政治实践而形成的讽谏性文体,政治性是其本质品质。降及后世,因“诗”之讽谏功能逐步被施以礼乐化与仪式化,从而促进“风”“雅”“颂”之合流,与此相应,“诗”概念亦逐步完成向“诗”文本的过渡。从早期的《诗》辑本至孔子之《诗三百》,实质上反映了“诗”概念移嬗与《诗》文献整理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诗学认知更新。
从具有开放性质的“歌”体概念到人为定义的“诗”体概念,两种文体呈现出相互交叉却又各自独立的发展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西汉武帝朝的乐府扩造活动而发生改观。儒学诗、礼、乐强力结合的学术传统伴随着武帝朝俗乐对传统雅乐的侵蚀,两者综合作用而促发了“歌诗”体之出现。“歌诗”的出现打开了传统“诗”体封闭性的政治品质,而呈现出开放的文体状态。降及东汉,经今古文释诂合流,“诗言志”“歌永言”的互释在学术上确立了“歌”“诗”二体的文体地位,“歌诗”之概念亦至此而确立。
传统“诗”体的政治因素与礼乐因素是“诗”体概念的核心品质,后世“诗”体开阖均与其有密切关系。两汉歌诗是先秦“诗”体在新时代的替嬗,自此歌诗所秉持的音乐特性与讽谏功能成为后世“诗”体开阖的一大关键。加之以“诗言志”“歌永言”的文化释诂,后世“诗”体逐步完成了“诗”“歌”两体的文化合流,就此亦实现了传统“诗”体的政治性功用向个人“言志”的功能嬗变。以此为鹄的,重新审视“歌”“诗”“歌诗”体的概念形成,以及因“诗”体概念开阖而累代产生的“诗”体衍生品,诸如歌诗、歌行、拟乐府、新乐府,甚至词、曲、民歌等文体,都得到一种达观而通彻的系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