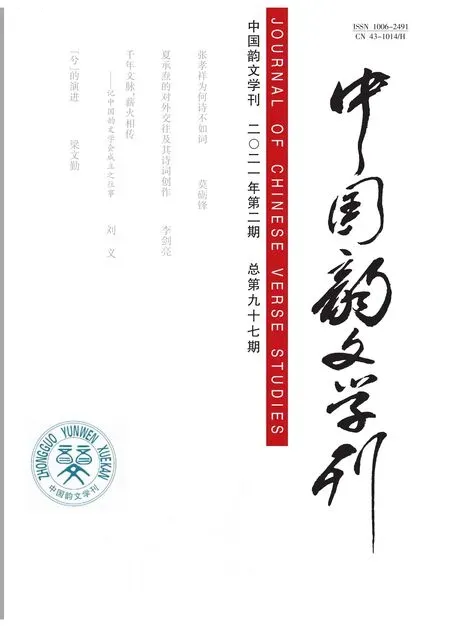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诗经·周南·兔罝》之“兔”字释疑
李延欣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4)
《诗经·周南·兔罝》诗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郑笺云:“罝兔之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则是贤人众多。”历代学者对于“后妃之化”及“贤人众多”的说法提出众多质疑,而将诗旨的关键放在“赳赳武夫”上,注意到诗歌对猎人武夫的赞美。以赞美武夫为基础,又生发出两种引申内涵,一是认为此诗表达了贤才未得重用之意,二是认为此诗应指《墨子·尚贤》中所说“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一类任用贤能之事。综而观之,现有的诸种解释存在两个侧重点,一是强调武夫体能才能之健,二是强调武夫身处鄙陋之位。从第一个侧重点出发,则不免使人对“捕兔”和“赳赳”之间颇具滑稽的落差产生怀疑。为了更好地突出武夫形象之威武雄壮,使诗意更加连贯,有学者提出“於菟”说,认为“兔”应为老虎而非兔子,如袁行霈在《诗经国风新注》中认为“惟捕虎方见猎人之勇武也”。《兔罝》一诗中的“兔”究竟是指老虎还是兔子呢?如何理解“兔罝”在全诗中的作用?“兔”字的含义不仅关系到诗句解释,还跟诗旨相关联,因此笔者想通过梳理文字学材料,并结合对先秦两汉田猎方式的考察,尝试解答这一疑惑。
一 “於菟”说的依据及疑点
将“兔”释作“於菟”,最早见于宋代王质《诗总闻》。王质注意到《诗经》文本存在“兔”和“菟”两种写法,认为“菟”即老虎,还提及捕虎之器具和方式:
闻字曰:陆氏作“菟,又作兔”,今皆用菟。於菟、虎也。言取虎之具不一,用阱、用矢、用绳,见杜氏。所谓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今荆峡间或用此,未见用罝者,今从现字。
不过,王质自己对这个解释未有足够信心,他以当时荆峡地区未见用罝网捕虎为由,转而默认“兔”是兔子,在总括诗意时加以阐释:
总闻曰:西北地平旷,多用鹰犬取兔;东南山深阻,多用罝。东南自商至周,常为中国之患,当文王之时,江汉虽定,然淮夷未甚尽服,当是此地有睹物兴感者,寻诗可见。

接着,闻一多对王质提到的捕虎不用罝网之疑惑做出回应:“古者猎兽,无不先用网罗遮遏,以防其遁逸,然后射杀或生缚之。《汉书·扬雄传·长杨赋序》曰‘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是其明证。”又引《孔丛子·连丛篇》中的《谏格虎赋》来说明捕虎用罝之状。
虽然有字音和捕虎用网的证据,但仍然只是验证了“菟”释作“虎”的可能性,而无法认定它就是指老虎这种动物。于是闻一多又从情理上加以解释,认为“赳赳武夫”既然能当“公侯干城”之任,其人必为乌获、贲育之流,诗人见其在林中张罝捕虎,而生起钦慕之情,所以发此歌咏,如果只是寻常猎人,则难与“赳赳武夫”匹配。最后,闻一多又以《诗经》之“驺虞”、《尚书》之“柷敔”、《淮南子》之“敦圄”皆形似虎,而合音近“菟”为据,证明“《召南》之诗称虎曰‘驺虞’,犹《周南》之诗称虎为曰‘菟’,盖皆是楚语欤?”闻一多的论证紧系字音,兼及捕猎方式和情理推敲,考虑不可谓不周全。但细究起来,也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再者,在王质之前还未有人专门解释《兔罝》中的“兔”字,假如其真如闻一多所言,则说明楚地方言直接用“菟”指称虎至少在宋以前是某种共识,那么为何王质、闻一多及其后的学者均未能举出“於菟”省称为“菟”而指虎的文献例证,只能根据字音和“於”字功能作推测?这似乎也并不符合语言的流传常理。有人也援引楚地方言的证据认为《楚辞》中“顾菟在腹”的“顾菟”指老虎,但此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并非用《诗经》和《楚辞》互相印证就能简单带过,因而“於菟”究竟能否简称为“菟”仍需存疑。
闻一多怀疑古本即作“菟”,是从结论反推的,还需要有更明确的文献依据。此外,闻一多提及捕虎也用罝网,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王质的困惑,但也需要更细致的辨析。
二 从“兔”到“菟”:字义的回归与歧义的产生

《诗经》的唐代写本见于敦煌文献,S.1722和S.3951均载有《兔罝》一诗的内容。在S.1722文件里,诗中的兔字作“菟”,而在S.3951中则写作“兔”,可知唐代亦有两种写法。此外,P.2529中载有《兔爰》一诗,写作“菟”,而《兔爰》一诗中的“兔”指兔子是可以确定的,这就说明唐代存在“菟”“兔”混用均指代兔子的现象。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写为“菟罝”,释文曰“菟又作兔,他故反”,也可知陆德明当时能见到这两种异文,而同书中《兔爰》的“兔”则仍然写作“兔”。虽然王质说当时流传的文本都写作“菟”,但事实上宋代仍有大量刊本、抄本中的《兔罝》一诗是写作“兔”字,而且宋代学者也未将其视为一个问题。宋本《毛诗诂训传》写作“兔罝”。北宋蔡卞《毛诗名物解》有“兔”一条,在介绍兔子相关传说及形象时引用并解释了《兔罝》一诗:“盖椓木之丁丁,以有所闻;施于中逵,以有所见。施于中林,则无所闻、无所见于是焉,肃肃则好德之至也,故诗以此为德。”南宋刘叔刚刻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的《兔罝》诗文写作“兔”。南宋魏了翁《毛诗要义》作“兔”。宋抄本《群经音辨》引用“肃肃兔罝”时也写作“兔”。王质由“兔”联想到“於菟”,在当时未能引起注意,一方面固然跟《诗总闻》的传播状况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也因为这一说法确实难为时人所接受。

战国楚地的出土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有力的材料。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版本《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的本子,其中《兔罝》一首中的“兔”字的字形即为“兔”(见图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部分,也有“兔罝”二字(释文为“兔虘”),字形也为“兔”(见图2)。就目前的材料看来,古本《兔罝》中的“兔”应为“兔”而不是“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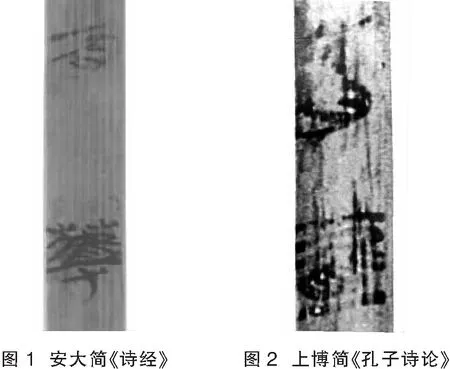
那么,何以《兔罝》原先的“兔”字会增出一个“菟”的写法呢?正如段玉裁所言,“菟”应为“兔”的俗字,李富荪《诗经异文释》也认为“盖本作兔,又加艸,俗字”。根据张涌泉的研究,俗字主要流行于民间通俗文书,在抄本和刻本中都有可能存在。敦煌文献中存在大量俗字,其中一类可列为增旁俗字,即在原有字体上增加一个偏旁,例如增加草旁的字有“葇”“苽”等。增加偏旁的目的之一是强化表意的功能,“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批评的‘飞鸟即须安鸟,水族便应着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屮’,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菟”也属于这类情况,“兔”字增加表示草类生物的偏旁就形成俗字“菟”,它更加突出了兔子是草类动物的意涵。

三 从捕猎方式看“兔罝”的确指与泛指
《诗经》中有不少田猎诗,展现了猎手敏捷的动作和矫健的身姿,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对于勇猛、智慧、雄壮等品格的追求,比如《召南·驺虞》赞美猎人的高超技艺,《齐风·还》提及猎人的收获,《齐风·卢令》称许猎人的美好形象等等。《郑风·大叔于田》更是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写了规模宏大的狩猎场面:
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叔在捕猎过程中,需要驾驭马车,点燃烈火,使用弓箭,可谓装备齐全。诗中最能体现叔之勇猛的莫过于“袒裼暴虎”。这首诗是直接刻画猎人形象的典型,相较之下,《兔罝》一诗显得更加节制,只是有椓木、施网两个简单动作。
孔臧《谏格虎赋》叙述的捕虎场景也并不轻松:“戴星入野,列火求踪。见虎自来,乃往寻从。张罝网,罗刃锋,驱槛车,听鼓钟。猛虎颠遽,奔走西东。”捕虎虽然可以用网,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驱车持刃进行动态追捕。除了围猎和追捕外,还有一种相对静态的捕捉野生动物的方式,就是王质提到的“枝撑已在脚”。《中庸》有“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朱熹释“擭”为“机槛”,有学者认为就是在土坑中插上树枝形成的一个简易捕猎机关,野兽掉入后会陷在其中无法自拔,这和王质所说的很相似。
捕捉兔子的方式则比较特别。兔子跑得较快,所以有借助鹰犬来捕捉的方法。也有用网设置屏障的方式,这种网捕还可以用于鸟禽类动物。《王风·兔爰》写“雉离于罗”“雉离于罦”“雉离于罿”,和“有兔爰爰”并举,马瑞辰云:“据《齐语》‘田猎毕弋’,韦注‘毕弋,掩雉兔之网也’,是古者掩雉兔之网可以同用。”“雉兔”也有合称,比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有“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其中的“雉兔者”就是指与王公贵族相对的民。兔子在先秦时期是较为常见的动物,捕兔之人也不必有特殊身份,平民百姓皆可为之。用木桩和罝网制作捕兔之器,放设于道路中间(“中逵”)和树林中间(“中林”),以捕捉误入的野兔,应是普通打猎者就可以做的事情。比较两种动物的捕猎方式以及《兔罝》诗中涉及的捕猎步骤,“兔罝”更接近捕兔之网,而非捕虎之网。
扬雄在《长杨赋》中描绘了在山林间大型围猎的场景:“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椓巀嶭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罝,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帅军踤阹,锡戎获胡。搤熊罴,拖豪猪,木拥枪累,以为储胥,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这场围猎需要众人合作,取木材于巀嶭,将整个南山包围起来,用千乘万骑的阵势捕猎,因而是穷览极观。此种声势浩大的行为,非一般人所能完成,和《兔罝》中的简易设网不是一个级别。然而,从椓木桩、围成罝网的步骤看,两者又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认为是同一种捕猎思路,只不过范围和规模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兔罝》中所赞美的武夫和《长杨赋》中的武夫其实是一类人,他们都有能力为统治者猎取野兽,进而保家卫国。《长杨赋》在讽谏时采取了正面赞扬的手法,提及帝王田猎本来具有居安思危的目的;西周时期的狩猎也与政治、军事紧密联系,集体围猎既有军事演练的性质,又有选拔人才的功能。《兔罝》的武夫也正是这样的贤能之人。
朱熹认为《兔爰》诗中的“兔”比喻小人,而“雉”比喻君子:“言张罗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脱,而雉以耿介,反离于罗。以比小人致乱,而以巧计幸免;君子无辜,而以忠直受祸也。”马瑞辰也说:“狡兔以喻小人;雉,耿介之鸟,以喻君子。‘有兔爰爰’以喻小人之放纵,‘雉离于罗’以喻君子之获罪。”从兔子的这个隐喻义来看《兔罝》一诗,似乎也可以将“兔罝”看作是捕捉小人的比喻。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狡兔”的原本含义应为“迅疾的兔子”,而释为“狡猾”并赋予其小人形象应是汉代之后的事情。较早的《毛传》只是说《兔爰》“言为政有缓有急,用心之不均”,并没有提及小人和君子之对比,或许可以印证这一点。笔者认为,《兔罝》中的“兔罝”应当是捕兔之网,但并不一定就要把捕猎对象坐实为“兔子”,毕竟兔网中也可能落入其他动物;也不必然要将“兔”理解为小人之喻。“兔罝”很可能只是一种泛指,作为一首诗的起兴,比喻武夫拥有守卫、辅佐公侯的才能。无论是将“兔”理解为老虎,或者是将“兔”理解为拥有小人之喻的兔子,以及将捕兔之人理解为鄙陋之人的一类阐释,其出发点都是认为“兔罝”有确指,只能捕捉某一种动物。而如果我们放弃对这种动物究竟是什么的执念,或许可以对诗意有更为通达的理解。
四 《兔罝》诗旨与《周南》诗序谱系
《兔罝》从字面意义上很难看出与后妃的关联,因而后世之人只能围绕“贤人众多”的角度来揭示或反驳诗序的论说。或将“肃肃”当作武夫猎人的恭敬之态,用“慎独”的眼光赞许武夫,认为即便是从事捕兔这样鄙贱之事的武夫也有自我约束力,从而可以见出“贤人众多”;或将“肃肃”和“椓之丁丁”都看作是对布置兔网这一行为的描述,认为诗歌赞颂了这位武夫的体格,由此延伸,认为这位武夫是已被重用或未被重用的贤能之材,影射出王风之化或王风不行。不论是在肯定武夫的内在修养基础上而将“兔罝”理解为捕兔之网,还是在肯定武夫的外在体貌基础上而将“兔罝”理解为捕虎之网,这些解释都遵循着共同的思维模式,即认为作为“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的“赳赳武夫”,就是前文“兔罝”的制作者、一系列动作的发出者,而把整首诗当成一个武夫捕猎场景的呈现。它们就好比是共享了同一幅武夫结网的底图,然后从不同维度加以描述,以求其生动可感,并且又在思想的层面加以不同的阐释,最终为底图堆叠出多向度、多层次的意义表述。
这种用场景化思维来阅读《兔罝》的方式颇近于《大叔于田》的读法,因而产生了对叙事准确性的追问以及对人物塑造连贯性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用《桃夭》一诗的读法来释读《兔罝》,则会发现其实诗歌的重点并不在于刻画某个人物。“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对出嫁女子的赞美和对美好婚姻的烘托。类似的以物起兴手法在《诗经》中多有使用,所借之物与诗歌歌咏主题相关,但未必与主要人物或事件真实同现,有时只是为了突出主旨、人物或事件而选取关联之物来起头,《兔罝》一诗中“肃肃兔罝”三句也是如此。朱熹解“肃肃”为“整饬貌”,明言“兴也”,正和“赳赳武夫”在句式上形成对应。《诗经》中同样用形容性叠词加名词来起兴的,还有“关关雎鸠”“采采卷耳”“采采芣苢”“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等等,都是由主人公而联想到的情境,并不一定就是诗人亲眼所见的完整场景。同理,“兔罝”的整饬貌和椓之有声,“兔罝”在中逵,“兔罝”在中林,都喻示着“赳赳武夫”的才能,并且正好与“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和“公侯腹心”相对应,而不是对武夫捕猎场面的描述。
如果以捕猎场面的叙述为立论基础,把这名武夫的行为作为诗歌的重点,自然是很难理解诗序所说的“后妃之化”,因为这样一幅底图与“后妃”确实没有什么关联。但如果把诗歌三章的首句都看成是后二句的兴喻,那么施设兔罝的人是谁、兔罝捕捉的动物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赳赳武夫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也不要紧,诗歌的重点在于赞颂武夫的才能。
《周南》有八首诗的小序提及后妃:《关雎》是“后妃之德”,《葛覃》是“后妃之本”,《卷耳》是“后妃之志”,《樛木》是“后妃逮下”,《螽斯》是“后妃子孙众多”,《桃夭》是“后妃之所致”,《兔罝》是“后妃之化”,《芣苢》是“后妃之美”。至于未提及后妃的《汉广》《汝坟》《麟之趾》三首小序也涉及道德之广布,与前面几首有所呼应。不难看出,《周南》拥有一个关于“后妃”的诗序谱系,诗序中透露出对后妃品行的赞扬,或者说是立标准。虽然每首诗诗序中具体所用的词不同,但其蕴含的美德基础是共通的,因此整组诗歌可以互相发明。其中《卷耳》一诗的小序曰:“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尽管对于后妃进贤的要求有汉儒过度构建之嫌,但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邦国能有贤才辅佐,与后妃之美德、婚配之中正美好密切相关。
我们不妨把《兔罝》的“后妃之化”放回《周南》的诗序谱系中理解:公侯有忠诚得力的武夫作守卫,也可以反映出后妃和婚配的美好。此外,《周南》本身又具备王室乐歌属性和仪式功用,更提醒我们不能将《兔罝》视为单纯的颂扬英雄之诗,而应结合其形式特征和应用场景来理解诗歌最初的创作目的,把握诗歌的本义。从这些结构性的角度回观诗歌文本,也就不必再拘泥于“兔”的兔与虎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