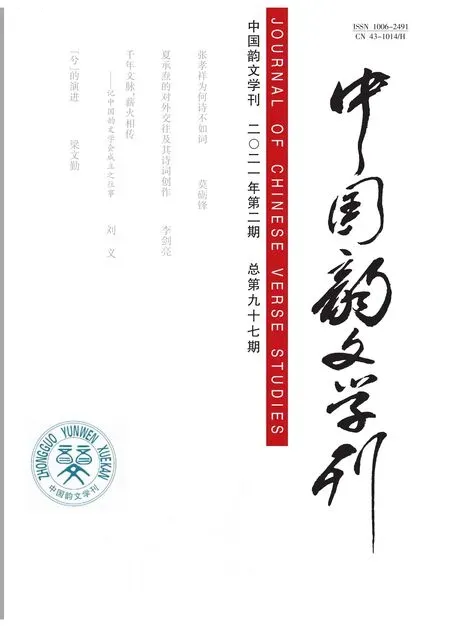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兮”的演进
梁文勤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楚辞研究所,江苏 南通 226010)
“兮”在先秦多见于诗歌,《诗经》中凡324处;至于楚辞,屈原的作品除《天问》外,篇篇用“兮”,“兮”成为楚辞的文体标识。诸子散文中也偶见“兮”,不过依然和韵文有关。如《老子》中共有27处“兮”,《荀子·赋》中共计4处“兮”:“从句子的规整,排偶的运用,以及押韵这些特征来看,至少应该承认它(《老子》)在形式上与诗歌是相近的。尤其是使用‘兮’字的那些句子,这个特点更为明显。”《荀子·赋》也同样是押韵的文体。由此可见,“兮”与韵文文体关联密切。我们在此着重探讨的是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后来的汉语诗歌,“兮”的功能发生了何种变化,并尝试依凭等值关系构拟“兮”的演化轨迹。
一 《诗经》“兮”的分布
“兮”在《诗经》中的分布相当丰富多样:以诗行为单位,有分布在句中的,也有分布在句末的。以诗歌中的章节为单位,有句句用“兮”的,也有间隔用“兮”的。间隔用“兮”又分几种情况:单句句末用“兮”,偶句句末用“兮”,或者一章中仅某句用“兮”,或者一章中仅某句不用“兮”。各自举例如下:
1.句中用“兮”:
父兮
生我,母兮
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小雅·蓼莪》)
萚兮
萚兮,风其吹女。叔兮
伯兮,倡予和女。(《郑风·萚兮》)
2.句末用“兮”:
猗嗟昌兮
,颀而长兮
。抑若扬兮
,美目扬兮
。巧趋跄兮
,射则臧兮
。(《齐风·猗嗟》)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魏风·伐檀》)
3.句末句中同时用“兮”:
瑟兮
僴兮
,赫兮
咺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卫风·淇奥》)
伯兮
朅兮
,邦之桀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卫风·伯兮》)
4.句句用“兮”: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
。劳心悄兮
。(《陈风·月出》)
于嗟阔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邶风·击鼓》)
5.单句句末用“兮”:
彼采葛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卫风·采葛》)
于嗟鸠兮
!无食桑葚。于嗟女兮
!无与士耽。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卫风·氓》)
6.偶句句末用“兮”: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兮
。(《郑风·溱洧》)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郑风·野有蔓草》)
7.仅首句用“兮”:
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郑风·将仲子》)
8.仅末句用“兮”: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周南·麟之趾》)
9.仅中间某句用“兮”: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
,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邶风·日月》)
10.仅末句不用“兮”: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
,无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
旄丘之葛兮
,何诞之节兮
。叔兮伯兮
,何多日也?(《谷风·旄丘》)
11.仅第二句不用“兮”:
东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履我即兮
。(《齐风·东方之日》)
12.仅第三句不用“兮”:
彼狡童兮
,不与我言兮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郑风·狡童》)
挑兮达兮
,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郑风·子衿》)
稍做枚举,我们就列出了《诗经》“兮”分布的12种情况。《诗经》“兮”分布之多样,由此可见。《诗经》最初源于民间,抒情写意纯任自然,与之相应,“兮”字的分布灵活多样:“《诗经》是主要源于非文人的鲜活语言的而经文人整理的民歌(《雅》《颂》最初也是口头的诗歌形式),‘兮’是鲜活口头语言吐辞纳气及节律自然需要的自然音节,随口而出。因为自然,所以与‘兮’有关的句式并不工整。”
“兮”具备何种性质,它的分布可以如此灵活多样?《说文解字》:“兮,语所稽也。象气越亏也。”段玉裁注:“稽部曰:‘留止也,语于此少驻也。’”刘勰《文心雕龙》:“(兮)乃语助余声。”刘知几《史通》:“夫人机枢之发,亹亹不穷,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可见,“兮”为语助词,“语助余声”或“余音足句”是其特点。当代学人郭建勋在研究楚辞的过程中,曾详细论述“兮”字有声无义的特点,“兮”的泛声性质无须赘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兮”:这是一个语助词,附着在线性位置靠前的词句之后;这些词句借助“兮”字之余声,形成语音的绵延舒展。
那么,“兮”这个余声有什么功能呢?《诗经》中,“兮”的位置固然灵活多样,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句中和句末。分布在句中或句末的“兮”,主体功能一致,而有细微差异。举例如下: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小雅·蓼莪》)
→改写为:父生我,母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魏风·十亩之间》)
→改写为:十亩之间,桑者闲闲,行与子还。
语助词“兮”不具有实际的词汇意义,所以我们去掉这个“兮”,仍然语义完足。从语音层面看,前一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有了这个“兮”,每个诗行都是四个音节,诗行整齐匀称,“兮”具有补足音节的功能。后一例中,“兮”分布在句末,由于“兮”在语音上具有“气分而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特点,“十亩之间兮”与“十亩之间”相比,语音悠扬,抒情意味大大增强。以语音的延长强化抒情意味,这也是“兮”的普遍功能。回看前一个用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当我们还原语言的有声性,我们就能鲜明地感受到:正是这个“兮”赋予了诗行强烈的咏叹意味。所以,有声无义的“兮”,或在句中补足音节,或在句末形成语音延宕;无论出现在何种位置,它都极大地强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这也应该是先秦时代“兮”字广泛应用于诗歌的根本原因。
二 楚辞“兮”的发展
与分布“并不工整”的《诗经》“兮”相比,楚辞“兮”的分布相当工整。在我们统计的楚辞篇目中,共计965处“兮”,具体分布如下:

表1 楚辞中的“兮”字统计
根据表1统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与《诗经》相比,楚辞中的“兮”有两个特点:
一是数量庞大。不妨以《诗经》为参照。《诗经》305篇共计29645字,“兮”共计出现了324次,《诗经》“兮”的出现频次是324∶29645,即1.09%。楚辞中,《离骚》《九章》《九歌》《九辩》《天问》这些篇目,共计11576字,“兮”字出现了965次,出现频次为965∶11576,即8.34%。两相对比,不论是“兮”的绝对数量(324—965);还是出现频次(1.09%—8.34%),楚辞都远高于《诗经》。
二是分布规整。我们在《诗经》中,仅不完全统计,就归纳出“兮”的12种分布情况,可见在《诗经》中,“兮”字的分布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楚辞则不然。尽管楚辞中“兮”高频次出现,“兮”的分布基本就是三种类型:(1)《橘颂》型,“兮”字用于偶句句末;(2)《离骚》型,“兮”字用于单句句末;(3)《九歌》型,“兮”字用于句腰。楚辞用“兮”的方式大多是纵贯全篇的,一首诗看了开头,确认了“兮”的位置,那么在接下来的诗行中“兮”字必然在同样的位置如约而至。
这两个分布特点,意味着从《诗经》到《楚辞》,“兮”在补足音节、造成语音延宕之外,衍生出非常重要的新的功能:
首先,三种分布位置上的“兮”成为诗行节奏的建立者。诗歌首先以其韵律特征区别于其他文体;节奏是韵律的核心要素。分布规整的“兮”或者句句出现,或者间隔出现,一律纵贯到底。不论是哪种情况,“兮”的规整分布意味着:在鸿篇巨制的诗篇当中,在大体一致的语音间隔当中,具有语音延宕特征的“兮”纵贯全篇,此呼彼应,诗行的节奏由此诞生。节奏是诗歌的生命:“它的有规律的均匀的起伏,仿佛大海的波浪,人身的脉搏,第一个节拍出现之后就会预期着第二个节拍的出现,这预期之感具有一种极为自然的魅力。这预期之感使得下一个诗行的出现,仿佛是在跳板上,欲罢不能。”
其次,句腰“兮”不仅贡献了诗行的节奏,同时也维护和稳固了汉语诗歌的半逗律。“事实上中国诗歌形式从来都遵守着一条规律,那就是让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似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的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楚辞诗行加长,句腰“兮”作为显性标记,标记了诗行半逗的位置。如:“石濑兮
浅浅,飞龙兮
翩翩”,“悲莫悲兮
生别离,乐莫乐兮
新相知”。“兮”是一组对句中语音最绵长的一个音节,当我们还原语言的有声性,这个“兮”字就水到渠成地突显为一个诗行中语音停歇延宕的位置。由于“兮”字前后的音节数量大体相当,它就成为二分诗行的节奏点。如果所有诗行都在句中的位置、借助“兮”发生语音延宕,二分节奏就成为诗篇的节奏。我们在《九歌》各篇中看到的情形就是如此。以“兮”为标记建立诗行节奏,是与楚辞诗行的加长互为因果的。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郑樵《通志·乐略》)《诗经》时代是汉民族的童年期,总体氛围显得质朴而悠缓,“故发诸咏歌,其声和以平,其思深以长”(杨维桢《杨维桢集》)。“和以平”的内在情绪与平正优婉的四言相得益彰,故《诗经》以四言为主;既然四言为主,诗行节奏自然二分,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诗经》之后,诗坛沉寂了将近三百年;其间,时代震荡变异、散文风格日趋铺张扬厉。“《诗经》所代表的来自农村的从容朴素的作风,已必须由一种激荡纷繁紧张尖锐的表现所代替。”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当屈原登上诗坛引吭高歌时,惊艳了世人:“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言甚长”,不仅是篇幅的长,还有句式的长。楚辞诗行加长,较为表层的原因来自语言层面的变化:“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先秦晚期,应该是汉语复音词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复音词涌入诗行,与原有的单音节词交错使用,必然导致诗行的增长。其次是文化传统的影响。“楚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的确比北方远为浓厚地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原始的自发产生的自由精神表现得更强烈。”“从楚辞到《山海经》……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楚文化中那种自由的精神、炽烈的情感,在屈原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至屈子始以一己之性灵情志,与世相见”,“杂用长短,一以辞气之缓急为衡,而绝去约束”。滔滔不绝,又“杂用长短”,这使得楚辞与散文相当靠近。如何在散文的波澜里获得诗歌的形式?“兮”正是密钥所在:“兮”字以其语音延宕的特质规整分布于诗行、纵贯全篇,诗化了散句,确立了诗歌的节奏。“《楚辞》是文人的作品,首先是书面语言,呈现程式化的语句和表达方式,创作时可以从容铺成排比……因为句式的既定,所以‘兮’字在这种句式中的作用,实际上不是与语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种内容需要的结构先有直接联系,而是纯粹在辞句形式上起着延长辞气、节奏韵律、呼应前后、规整篇章的作用。”
三 句腰“兮”的演进
汉语诗歌自《诗经》发端,经由楚辞到达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五七言诗歌便渐至成熟。既然句腰“兮”对于构建节奏如此重要,在汉语诗歌臻于完善的过程中它又何以淡出直至完全隐没了呢? 我们尝试着对“兮”的演化轨迹做一个勾勒。
1.句腰“X”到句腰“兮”
根据表1,句腰“兮”在我们统计到的965个楚辞“兮”中,所占比例约(297/965)为30.78%。那么,还有大约70%的诗行是如何构建诗行节奏的呢?
音节数量不多的诗行,多数情况下不用句腰。如: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九章·橘颂》)
低回夷犹,宿北姑兮。
(《九章·抽思》)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九章·涉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九章·怀沙》)
音节数量在四音节以上的诗行,多采用句腰标识诗行中最大的顿逗,但是不限于句腰“兮”。举例如下:
悲莫悲兮
生别离,乐莫乐兮
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与天地兮
比寿 , 与日月兮
齐光。(《九章·涉江》)
倚结軨兮
长太息,涕潺湲兮
下沾轼。(《九辨》)
惟草木之
零落兮,恐美人之
迟暮。(《离骚》)
羿淫游以
佚畋兮,又好射夫
封狐。(《离骚》)
路曼曼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离骚》)
显而易见,句腰“兮”和句末“兮”不会共现。一个音节相对较多的诗行,如果以“兮”为句腰,一般是句句用、连续用,如这里所举《九歌》的前三个用例;如果单句句末用“兮”,则会在句腰处安置其他虚词,这样可以避免单一而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如这里所举后三例中的“之、其、以、夫、而”等等。句腰位置上分布“兮”或其他虚词,频率非常高:《离骚》中372句,340个句腰虚词;《九歌》253句,一律采用“兮”作句腰;《九章》644句,489个句腰虚词;《九辨》中266句,212个句腰虚词。
普通虚词和“兮”都可以分布在句腰位置上,说明它们具有等值关系。“之、其、以、夫、而”等虚词一般具有语法功能,也正是根据它们的语法功能把它们分布归类为连词、介词等类别;“兮”是典型的语助词,不具备明显的语法意义,其主要功能在于语音层面。二者等值,说明在楚辞语境中,句腰虚词“X”偏离了它们在散文语体中的一般用法。确实,我们在楚辞中可以看到如下几类语料:
其一,句腰“X”有不承担句法功能的用例。以“其”为例:
日月忽其
不淹兮,春与秋其
代序。(《离骚》)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
然否。(《惜往日》)
第一个“其”位于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第二个“其”位于主谓之间,第三个“其”位于动宾之间。这些句法成分之间没有语法空位,从语法层面说虚词“其”是冗余的存在,不承担任何句法功能。“其”在此处显然不是以其句法功能出现在诗行中的。
其二,句腰“兮”有承担句法功能的用例。如: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
瑶之圃。(《九章·涉江》)
悲莫悲兮
生别离,乐莫乐兮
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搴汀洲兮
杜若,将以遗兮远者。(《九歌·湘夫人》)
这里第一个加点“兮”引入地点,相当于介词“于”;第二、第三个“兮”引入比较对象,相当于介词“于”;第四个加点“兮”表示隶属关系,相当于结构助词“之”。一个典型的语助词,可以承担不同的语法功能、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不能不引人深思。
其三,句腰“兮”和句腰“X”有分布完全相同的用例。如:
步余马于
兰皋兮(《离骚》)——步余马兮
山皋(《九章·涉江》)
载云旗之
委蛇(《离骚》) ——载云旗兮
委蛇(《九歌·东君》)
九疑缤其
并迎(《离骚》)——九嶷缤兮
并迎(《九歌·湘夫人》)
聊逍遥以
相羊(《离骚》)——聊逍遥兮
容与。(《九歌·湘夫人》)
以上例句中,左列加点虚词和右列的“兮”,分布完全一致。这组例证更加一目了然,句腰位置上的虚词“X”和句腰“兮”确实具有等值关系。
句法和语音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在这两个层面发生等值关系,显然有个方向性问题:是句法向语音靠拢,还是语音向句法靠拢?我们认为是句法向语音靠拢。在诗歌文体中,韵律的实现具有优先性;节奏又是构建诗歌韵律的第一要素。这些虚词出现在句腰位置上,它们跟“兮”同质,都是以自身的语音延宕标记诗行的节奏。此处所举第一组用例中,“其”从句法层面看是冗余的,它是作为语音实体存在于诗行中。第二组用例中,不同句法功能由同一个“兮”兼任;第三组用例中,功能不同的虚词对应同一个“兮”。它们都充分表明:不同虚词的不同句法功能在这里被弱化,它们的语音功能被强化、甚至被整齐划一为专职的语助词“兮”。因此,等值的方向性应表述为:从句腰“X”到句腰“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说《九歌》是楚辞中诗化程度最高的一组诗歌,是诗歌迈进中的一种姿态。
2.从句腰“兮”到句中顿歇
从各个不同的句腰虚词演进为专职的语助词“兮”,借助“兮”的语音延宕标记诗行节奏;继续向前,楚辞中这个具有语音实体的“兮”在后来的汉语诗歌中,演化成了没有语音实体的句中顿歇。
“(兮)在后世的演进中朝逆向的两极发生变化:其一是单纯充当泛声、表示语音持续的‘兮’字逐渐弱化,以致最终完全消失;其二是具有文法意义的‘兮’字渐次被其他的虚字所代替,并最终强化为实词。”“兮”是否会强化为实词需要另行论述;“兮”弱化以至消失、演化为一个零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我们可以推导出句腰“兮”和句中顿歇具有等值关系。上文提及:为避免单一,楚辞诗行中,如果句腰用“兮”,句末则不再用“兮”。但其实诗行末端依然存在节奏标识,这个节奏标识就是零形式的语音顿歇。以《离骚》和《九歌》为例,二者标识句中节奏和句末节奏的情况大体如下:
《离骚》 —— 《九歌》
句中节奏: 句腰虚词 “兮”
句末节奏: “兮” 顿歇
句腰虚词“X”和句腰“兮”构成等值关系,句末“兮”和句末顿歇构成等值关系。 “兮”和顿歇的这种等值关系可以发生在句末,也应该可以发生在句中;因此,句腰“兮”的进一步发展就是零形式的句中顿歇。于是,整个演进过程构拟如下:
句腰虚词“X”→句腰“兮”→句中顿歇
其二,“兮”和停顿的等值,并演化为零形式的顿歇,我们可以在后来的骚体赋中找到旁证。在历时层面,我们看到楚辞中大量使用句腰“兮”;汉代以后的诗歌里,“兮”字踪影难寻:这不足以成为“兮”演化为零形式的证明。那我们不妨看看楚辞的近亲,骚体赋。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比较典型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差异正在于“兮”字的有无。贾谊《服鸟鸟赋》,《史记》的引录有“兮”,《汉书》的征引中无“兮”。第二个例证是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有用“兮”字的情况,也有不同“兮”字的情况。以曹植为例。他的《九咏》:“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这里句句用“兮”。但是,他的《九愁赋》,如“眷浮云以太息,顾攀登而无阶。匪徇荣而愉乐,信旧都之可怀。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词”,一律不用“兮”。“随着语言骈偶化的进程,当骚体句式,尤其是句腰虚字的六字句成为骚体的主要句式后,因外在规整与内在节奏的一致,‘兮’字主要功能即调整节奏于规整诗行作用的减弱以及音乐与可歌背景的淡去,势必反映在作家的实际创作中,也就是说,骚体‘兮’字一部分失去,是作家创作时的主动放弃。”汉语一音一节,易于形成整齐对称的格局,一旦不需要借助显性标识提示诗行节奏,“兮”字很容易弱化以至完全消失。
汉语诗歌的节奏支点是停延。在汉语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兮”自汉代起逐步淡出了诗歌的疆域,但其实正是通过“兮”的奠基,才有了后来五言诗的“上二下三”、七言诗的“上四下三”。五七言诗歌虽然没有句腰“兮”,但在诗行大体居中的位置会通过顿歇的方式二分诗行节奏。这里,“兮”作为一个语音实体隐没了,但是它所确立的以语音停延标识节奏的方式流传了下来;只是标识物从有形式演化为无形式。从有到无,也是一种进步:“寂之于音,或为先声,或为遗响,当声之无,有声之用。……虽‘希声’而蕴响酝响,是谓‘大音’。”“当声之无,有声之用”,是标识诗行节的最高境界。
四 楚辞“兮”对汉语诗歌的贡献
楚辞句腰“兮”二分诗行节奏、并逐步演化为零形式的顿歇,直接奠基了汉语诗歌的音顿节奏体系。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点,以不同语言为材质的诗歌也必然各成体系。“拉丁和希腊诗依靠音量对比的原则;……汉语诗依靠数目、响应和声调对比的原则。……仔细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特别是它的动力特点,就能知道它发展过哪样的诗。要是历史曾经跟它的心理开过玩笑,我们也知道它本该发展哪样的诗,将来会发展哪样的诗。”西语诗歌以轻重音的音量对比为原则,是典型的音步节奏体系,音步的边界与词义的边界可以错落。汉语诗歌以音节数目为基准,借助诗行中的停顿构成音顿节奏体系。
音顿节奏的基本特点是:“(1)实体化音顿。顿歇是节奏支点,故音顿必须与词边界吻合,不允许程式化虚拟。(2)长度不固定。等长的诗句,音顿的长度不一定相同。如同是十音诗就有‘五五逗’、‘四六逗’和‘六四逗’的可能,属于哪一种,得因句而定。(3)具有层次性。根据停延的大小,音顿有多个层次。”
汉语诗歌是二分式的音顿节奏。“古典诗歌从四言发展至五言、七言,虽然字数不等,但是一句之内由两大节奏音组构成,则是句式的共同特征。”不过《诗经》的二分与后世汉语诗歌的二分并不相同:《诗经》多四言,因此多数诗行,不论语音节奏层面还是句法语义层面,都只有一个层次。随着语言的发展、表意的繁复,《诗经》的简短朴素已经一去不返,诗句的长度加长,由四言而五言六言七言等等。长度增加,即使只是一个音节的增加,都意味着诗行的语音层次、句法层次可能不再单一。如: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行行重行行》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这里,《诗经》所举用例在语音语义层面都只有一个层次。古诗十九首不同:只增加了一个字,语音层面就多出一个音步,层次必然增加;句法层面,第一个层次为主谓结构,其后谓语部分又有动宾。于是问题来了:在加长的诗行中如何继续保持二分的节奏模式?句法层次增加,如何确保“音顿边界”与“词边界”吻合一致?楚辞进行了意义非凡的尝试。
首先,楚辞借助句腰虚词维护了汉语诗歌节奏二分的韵律模式。诗行加长,二分诗行的节奏支点安放在何处?楚辞把以“兮”为代表的虚词规整地嵌入长短参差的诗句中,借助句腰虚词语音停延的特点,在诗行大体居中的位置形成顿歇,从而实现对诗行节奏的二分。把句腰虚词记作X,我们在楚辞中统计到的韵律模式主要有三种:“三X二”式,“二X二”式,“三X三”式。不论诗行有多长、包含了多少数量的音节,句腰虚词X必然是诗行中语音停延最长的音节,同时句腰虚词前后音节大体相当。于是,不论诗行其他位置是否有顿歇,句腰虚词位置成为诗行最大的顿歇,诗行节奏于此二分没有分歧。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前一句中语音层面就一个层次,后一句中“洞庭/波兮”还可以续分;不论前后,都必然在“兮”处实现首层二分诗行节奏。
其次,楚辞为汉语诗歌中多层二分提供了范例。诗句加长而继续保留节奏二分的格局,很容易出现节奏的续分,而语音层面的续分又往往同时伴随着句法语义层面的二分。由于汉语中单音节音步和双音节音步并存,续分在语音层面怎么分都能认同;因此继续二分以语义为凭据。这样就很容易实现“音顿边界”与“词边界”吻合一致。楚辞诗行中“三X二”式最为普遍,《离骚》372句,其中“三X二”式共计255句。在这个节奏模式中,句腰后面的双音节音步不用再分;句腰前面的三音节音组则会发生续分;至于这个“三”续分为“一二”还是“二一”,是依据语义确定的。如:“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楚辞诗句加长,突破节奏层面或表意层面的单一层次,这为汉语诗歌表意的复杂化、精密化提供了途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楚辞为汉语诗歌建立音顿节奏体系提供了声音的模型。停延是汉语诗歌的节奏支点,楚辞以虚词为句腰,正是充分利用了它们在语音上具有延宕的特点。此处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汉语实词的数量远多于虚词,实词中满足语音延宕特质的语词一定数量庞大,何以弃实词不用而以虚词为用?这是因为诗行中的顿歇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顿歇不可能单独存在, 它必须附着在音组的末一音上;它实际上是音的一种变化过程,是声音消失,或者变弱成为一点尾音,由此而与下一音组显出界限。在此意义上它成了诗的节奏点。”虚词没有实际语义,才有可能实现对音步或音组的“附着”。楚辞以句腰虚词标识诗行节奏点,确立了汉语诗律的一个重要特色:用拖音表示顿歇。再进一步,语音实体消失,句腰“兮”就演化为零形式的句中停顿。显性的形式确实消失了,但是那个句腰的位置、那个以顿歇标记节奏点的方式始终都在,汉语诗歌的音顿体系因此遗响不绝:“古音会变化、消失,但节奏不会消失,一直遗传到今天。”
“诗歌是只以语言为唯一构筑材料的艺术品种,除了靠语言本身创造构成诗体的形式标志,别无他路。而语言本身是语义和语音二元化的人工信息,语义必须以语音为物质载体,所以,又只有语音才是创造诗体形式标志有可感性的物质材料。”楚辞时代早已远去,我们甚至也无法亲切感知唐人的歌吟。但是在母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面对唐诗宋词,不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会采用同样的节奏、声韵铿锵地诵读,足见诗歌对于语音的倚重。汉语诗歌的韵律节奏自《诗经》、楚辞奠基,此后一直长养在我们的血脉里,代代相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