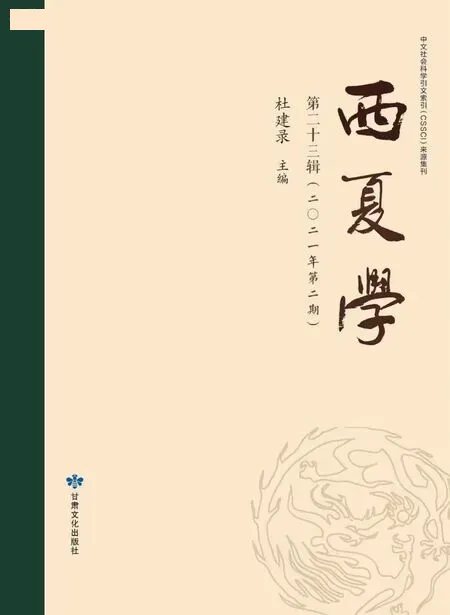政治的隐喻:榆林窟第39窟主室题材布局内涵探析
刘人铭
前言
归义军覆灭后,沙州回鹘接替归义军在敦煌进行了短暂统治,并于敦煌石窟营建上颇有建树。沙州回鹘新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这种新因素在沙州回鹘洞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榆林窟第39 窟是沙州回鹘洞窟代表窟之一,其不但传达了新时期的民众信仰,而且弥补了沙州回鹘史料少的缺憾,为研究沙州回鹘艺术提供了“标型物”,对探讨敦煌石窟营建史有重要意义。多年以来,只有沈雁①沈雁:《回鹘服饰文化研究》,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沙武田:《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220—221 页。在谈及回鹘服饰,以及刘玉权②刘玉权:《沙州回鹘石窟艺术》,载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216—227 页。、松井太③[日]松井太著,刘宏梅译:《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劄记(二)》,《吐鲁番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17—119 页。等学者在言及沙州回鹘洞窟营建时对第39 窟略有涉及,近日学者马莉对第39 窟定光佛授记(儒童本生)图像中胁侍的考证将第39 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④马莉:《榆林39 窟“儒童本生”中的菩萨及持“拂”天王身份考——兼论其“合并叙述”的构图形式及内涵》,《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0 年第4 期,第89—94 页。。但是第39 窟图像粉本来源、图像组合思想的表达、图像与历史背景的关联等基本且核心的问题依然未得到很好的回答,而我们发现这些问题都能以第39 窟定光佛授记这一新图像为线索一一解开。故本文通过对佛教文献、佛教图像的基本爬梳,从定光佛授记图像透视到第39 窟主室图像乃至整个洞窟图像的组合设计,尝试对第39 窟主室图像组合思想及营建目的等问题进行回答,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深入的讨论,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一、第39窟洞窟题材内容与空间布局概况
第39 窟位于榆林窟西崖左段,形制为中心柱窟,整窟由前甬道、前室、甬道、主室构成,初建于唐,沙州回鹘时期整窟重修。前甬道顶绘凉州瑞像一身(图1),两壁绘供养人像,女像绘于北侧,有4 身尼人像、9 身回鹘装女像及13 身汉装女像。男像绘于南侧,有1 身僧人像、21 身回鹘装男像,前两身男像十分高大且跟有侍从(图2)。现存供养人题记汉文11 条,回鹘文4 条,汉文题记和回鹘文题记分别可见于《安西榆林窟》《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①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263—266 页。[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著:《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017 年,第130—133 页。等资料。前室绘说法图、药师、菩萨和化佛。前室南、北间各设一像台,像台上保存清代塑像。前室顶、南、北壁绘说法图各一铺,东壁门南、北绘菩萨各四身,西壁门南、北绘药师佛各一铺,西壁门上绘15身化佛,化佛榜题清晰可见②榜题此前并未刊布,本人于2020 年1 月考察期间对其进行了摘录,详情参见附表。。甬道顶绘说法图,南、北壁绘千手观音各一铺。

附表 第39 窟西壁门上化佛榜题录文

图1
主室绘三种题材,定光佛授记、三身佛、十六罗汉。东壁门南、北绘定光佛授记各一铺,此图为单幅画形式,定光佛立于画面中央,菩萨弟子侍立左右,儒童于定光佛侧旁布发于地(图3)。南、北壁东侧绘三身佛各一铺,三身佛皆为倚坐,呈品字形排列,图中除三身佛外无其他天众人物及装饰性图案,此三身佛的身份与尊格学界还未有明确观点(图4)。南、北壁西侧及西壁绘十六罗汉,现今西壁罗汉像残缺脱落,北壁残存二身,南壁残存三身(图5)。十六罗汉形象相似于高僧像,呈现出世态之相,可能依张玄本而绘。主室中心柱四面为清代重塑塑像。

图3

图4

图5
第39 窟整窟左、右壁题材相同,布局对称(图6),尤其是在主室采用了新的图像题材定光佛授记及三身佛,这种组合不见于前代洞窟,那么这一组合有何内涵?我们可以尝试从新题材定光佛授记入手进行分析。

图6

图2-1

图2-2
二、从图像流变与粉本来源看定光佛授记本生图像之特殊性
第39 窟是敦煌唯一一个绘制单行本定光佛授记图像的洞窟①莫高窟第61 窟曾绘制屏风画式佛传故事,其中定光佛授记(儒童本生)作为佛传内容的一部分出现。敦煌单行本定光佛授记图像只出现在榆林窟第39 窟,且敦煌石窟中仅此一例。,此定光佛授记图像不仅是敦煌石窟中的新题材,也是沙州回鹘时期敦煌石窟营建的一种“复古”现象。定光佛授记故事发生在那揭国城,讲述了释迦佛过去为儒童菩萨,以花和身体布施定光佛,而得定光佛授记成佛的故事②《修行本起经》是最早记录此故事的经典,后译的《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普曜经》《增一阿含经》《佛本行经》《大智度论》等经典中都记载了此故事,不同经典对故事的叙述有所差别,主要在于“授记腾空”与“以发蹈地”二者的先后顺序。。定光佛授记图像是定光佛授记本生故事的图像化,定光佛授记图像起源于犍陀罗地区,“犍陀罗式定光佛授记的图像后来成为各地区效仿的标准”③朱天舒:《克孜尔第123 窟主室两侧壁画新探》,《敦煌研究》2015 年第3 期,第3 页。,最完整的图像包括买花、献花抛花、以发铺地、授记腾空四个故事情节(图7)。《高僧传》中“(罽宾人)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④[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中华书局,1992 年,第107 页。的记载为定光佛授记图像传入中国提供了时间下限即南朝宋时期,从出土实物来看,现今出土最早且最集中的时间是北魏时期⑤参见赵雨昆:《云冈的儒童本生及阿输迦施土信仰模式》,《佛教文化》2004 年第5 期,第74 页。李静杰:《北朝时期定光佛授记本生图像的两种造型》,载《艺术学》第23 期,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2007 年,第75—116 页。,图像与犍陀罗地区基本一致,只是情节选取有所侧重。南北朝“发端于小乘佛教美术的本生、因缘、佛传图像,在中原北方佛教美术中被借用,成为表述大乘佛教思想的因子”①李静杰:《北朝隋代佛教图像反映的经典思想》,《民族艺术》2008 年第2 期,第97 页。,隋唐时期随着大乘佛教中更为方便的净土法门的发展,佛传、本生等强调累世修行的图像被摒弃,南北朝之后中原及河西地区很少使用包括定光佛授记在内的本生故事作为造像题材了。

图7
定光佛授记图像在敦煌石窟中的再现与回归,与第39 窟题材组合的思想表达,以及敦煌地区的时代背景密切关联。1030 年左右沙州回鹘开始统治瓜沙地区②刘人铭:《莫高窟第310 窟回鹘供养人画像阐释——兼论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318—334 页。,由于与高昌回鹘同源之故,在图像艺术上受到高昌回鹘的影响,流行于高昌回鹘的依据《佛本行集经》绘制的誓愿画成为了第39 窟定光佛授记图像的粉本来源(图8)。

图8
比对沙州回鹘、高昌回鹘的定光佛授记图像,可以发现其有几处共同点:其一,二者都是单幅画,构图上皆以立佛为中心,胁侍围绕,儒童布发于侧旁。其二,定光佛袈裟覆肩右绕且佛衣下摆呈两侧散开式,菩萨着喇叭式裤且帔帛呈“S”环状垂下。其三,执拂尘金刚及双手外展执花菩萨是二图中的共同人物,敦煌本地没有执拂尘的金刚像,但是高昌回鹘壁画中却十分多见,马莉先生考证执拂尘人物为“帝释天”①马莉:《榆林39 窟“儒童本生”中的菩萨及持“拂”天王身份考——兼论其“合并叙述”的构图形式及内涵》,《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0 年第4 期,第89—94 页。。
从图像对比中可以发现,敦煌定光佛授记图像中有“授记腾空”情节,即“菩萨以双手合十,跪在一放光的圆环里”,而高昌回鹘出土的定光佛授记图像皆无此情节。“授记腾空”在南北朝依犍陀罗粉本绘制的定光佛授记图像中是重要组成部分,此处的“授记腾空”图像与南北朝时期乃至犍陀罗地区的造像一致,应该是借鉴了前代图像(图9),刘玉权先生认为此为化生,显然是不正确的②刘玉权:《沙州回鹘石窟艺术》,载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218 页。。是故,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第39窟定光佛授记图像粉本虽然源于高昌回鹘,但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而是以高昌回鹘本为蓝本,还参考了南北朝时期的本子,图像中“授记腾空”因素的加入,应该是基于整个洞窟营建思想表达的需要。

图9
三、定光佛授记图像中的“授记腾空”与主室三身佛身份之关联
第39 窟主室的三身佛是整窟中唯一没有明确身份的图像,敦煌研究院的内容总录中笼统称之为三身佛。第39 窟定光佛授记图像在高昌粉本基础上加入前代图像因素“授记腾空”,是为了契合整个主室主题,那么从整个主室题材选取与设计思想来看,三身佛与“授记腾空”情节这二者应该是有关联的,可以以此为切点对三身佛身份进行考证。
不同于儒童“以发铺地”情节强调的是佛教中的自身布施,“授记腾空”情节则强调的是佛教中的付法传承。画工在高昌粉本上特意加入这一情节,其意欲强调付法传承的佛教主题,而这恰对主室中未定名的三佛身份进行了暗示。定光佛授记讲述的是过去佛定光佛付法于现在佛释迦佛,那么循此逻辑,按照付法顺序,三佛主题则应该与未来佛弥勒有关。若以此推测三佛的弥勒身份还稍显臆断的话,那么主室的罗汉像再作证据之补充,以证其为弥勒身份应是大体不差。十六罗汉是主室中除定光佛授记、三身佛之外的唯一题材,绘制于南、北壁西侧及西壁整壁。罗汉信仰起源于印度,在唐代玄奘翻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简称《法住记》)前,罗汉仅仅限于观念,“迄至玄奘译出《法注记》后,十六罗汉的功德神通和特殊身份方始界定,成为我国民间罗汉信仰的真正典据”③沈柏村:《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青海社会科学》1997 年第3 期,第87 页。,“可以说我国历史悠久的罗汉信仰基本上是从《法住记》付嘱十六罗汉起始,尔后发展盛行的”④沈柏村:《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青海社会科学》1997 年第3 期,第87 页。。在《法住记》中载:
佛薄伽梵般涅盘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我受教勅护持正法,及与天人作诸饶益,法藏已没有缘已周今辞灭度,说是语已一时俱入无余涅盘。先定愿力火起焚身,如灯焰灭骸骨无遗,时窣堵波便陷入地。……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具如弥勒成佛经说。弥勒如来成正觉已,为声闻众三会说法令出生死得证涅槃。①[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大正藏》第49 册,第12—14 页。

图10-1

图10-2
为罗汉在佛教中的功能作了说明,即释迦灭度后护持正法等待弥勒降临。《法住记》中对弥勒世界做了详细描绘,并且明确提到即《弥勒成佛经》所绘世界,而《弥勒成佛经》的主体内容是弥勒三次说法,即弥勒三会,主室三倚坐佛应该就是表现的是弥勒三会。弥勒三会在初唐已经进入敦煌壁画,是弥勒经变最为主要的部分,其他如婚嫁图、一种七收、剃度图等都是在以三会为主体的构图中而增加的次要因素。梳理敦煌壁画中的弥勒三会图像,几乎为三身倚坐弥勒成品字形的模式(图10),与此处的坐姿与排列相同。
由此观之,主室定光佛授记、十六罗汉、三身佛三种题材关系密切,定光佛授记中“授记腾空”情节对付法传承的强调,以及十六罗汉护世待弥勒降生的作用最终将三身佛的身份指向了弥勒,也由此确定了三身佛内容实则是弥勒三会的简化。
四、主室题材组合所蕴含的“转轮王”的政治意涵
敦煌的佛教对大部分僧俗而言,是为大众服务的民俗佛教,敦煌石窟的壁画题材和内容都是为社会服务的,敦煌石窟是“社会化的佛教场所”①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192 页。。第39 窟作为敦煌石窟中唯一一个绘制单行本定光佛授记图像的洞窟,其不见于前代石窟中,除粉本与审美之故,更是其所具有的转轮王的政治蕴意使节度使身份的归义军统治者所忌讳。“燃灯佛授记(定光佛授记)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居于极为特殊的地位,带有明确的宗教和政治意涵。其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在印度本土罕见,却在中国中古政治和信仰世界里成为一个重要的信仰主题和政治理念。”②孙英刚:《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历史研究》2019 年第6 期,第30 页。定光佛授记与政治的关联在于经典中对儒童转轮王身份的赋予,经典中记载:“菩萨承事定光,至于泥曰……毕天之寿,下生人间,作转轮圣王飞行皇帝……如是上作天帝,下为圣主”③[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 册,第473 页。。定光佛授记所蕴含的转轮王的政治概念于佛教传入后对中古君主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君主观念主要植根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强调统治者‘顺乎天而应乎人’”④孙英刚:《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历史研究》2019 年第6 期,第34 页。,佛教传入后,“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加上了‘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⑤孙英刚:《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历史研究》2019 年第6 期,第34 页。。在中古民众意识中,“转轮王”是“君主”的代名词,是“君权神授”的象征。在政治实践上,北齐高洋、唐代武则天等统治者都曾经通过塑造自身转轮王的身份以示自己天命的合法性。
第39 窟主室中采用的三种题材则完成了在佛教表象下转轮王身份的建构,定光佛授记图像是对儒童转轮王身份的强调,而相呼应的是弥勒三会中对转轮王国家的叙述,在《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中记载弥勒下生而三次说法的国家其君主则为转轮王,经典记载“其国尔时,有转轮王,名曰蠰佉,有四种兵,不以威武治四天下”⑥[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第14 册,第424 页。,转轮王所在国土国泰民安、四时顺节、清净庄严、强盛无有怖扰、人民安居乐业①[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第14 册,第424 页。。
因此,敦煌石窟的属性是综合性的,不仅具有宗教内涵,更具有世俗功能,敦煌石窟壁画的内容和形式要服从于功德主的实际需要,“赞助者的营建意图通过工匠之手得以实现”②张利明、张敏:《肃南上石坝河石窟第3 窟壁画研究》,《敦煌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89 页。。第39窟的功德主通过选择具有政治蕴涵的佛教图像表达了“转轮王”的身份诉求,使得洞窟在宗教内涵之外更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五、主室转轮王身份地强调对功德主身份的启示
第39 窟主室布局严密、题材独特、思想突出且明确,不但反映出功德主的功德观念,同时也传达出功德主的身份信息。政治色彩如此浓郁、如此强调转轮王身份的洞窟,功德主大抵是沙州回鹘统治者才能与洞窟强调的转轮王身份相契合。第39 窟中位于南壁的第1、2 身男像比其他供养人像更加高大并且冠式也不同于其他供养人像,可知身份等级应该比其他供养人高,从排列规律看二者中又以第1 身为尊。第1 身男像榜题为回鹘文,具体内容是“松井太先生对其释读为“宰相阁下的真实影像正在此处,祝愿他获得上天宠爱,从此变得幸福”③[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著:《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017 年,第130 页。,而“sаngun”“”词语皆为官职,分别为“将军”“宰相”之意,故此榜题可理解为“宰相将军阁下的真实影像正在此处,祝愿他获得上天宠爱,从此变得幸福”。松井太先生在其注语中论述到“”为11 世纪左右统辖沙州的“沙州将军”,其可能为圣彼得堡所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2kr17 中的西州回鹘同名宰相“必里哥(伯克)”④[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著:《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017 年,第131 页。。虽然,松井太先生对于“”西州回鹘属性的推测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是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此回鹘文榜题主人公为“”的讯息。若对此窟功德主为沙州回鹘统治者的推测不误的话,这里的“”可能应该就是汉文史料所载唯一可查的沙州回鹘统治者——沙州镇国王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1041)夏,四月,……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⑤[宋]李焘撰,[清]黄以周等辑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仁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1191—1192 页。
根据《宋史》“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①[元]脱脱撰:《宋史》卷四九〇《外国六》,中华书局,1977 年,第14114 页。的记载,可知文中称唐甥的沙州镇国王子为回鹘人。这里的沙州镇国王子在之后不久称可汗,《宋会要辑稿》载:
(1041)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亭可汗奉表贡玉、乳香、硵砂、名马。②[清]徐松撰:《宋会要辑稿》第一九九册《番夷七》,中华书局,1957 年,第7852 页。
(1042)庆历二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贡。③[清]徐松撰:《宋会要辑稿》第一九八册《番夷五》,中华书局,1957 年,第7768 页。
李正宇先生已经论据充分地论述了沙州镇国王子与沙州北亭可汗实为一人④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载《1990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年,第149—174 页。,在此不再赘述。沙州回鹘取代归义军的时间于1030 年左右,在1041 年贡宋材料中沙州回鹘统治者以沙州镇国王子名义贡宋,此次贡宋后被宋朝封授可汗,此后汉文史料中才出现可汗称号,是故,回鹘文题记中未出现可汗名号类词语也属正常。正是如此,我们有了断代依据,此窟的时代应该在沙州回鹘统治者被封授可汗之前,即1041 年之前。
论述至此,也应该对第39 窟其他供养人像有所说明。第39 窟是沙州回鹘洞窟中供养人数量最多的洞窟,从题记中看还有“石、安、王”等敦煌大族姓氏、“都头”官职⑤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263—266 页。、“可敦殿下”称呼⑥[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著:《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017 年,第131 页。,可见这些供养像并不是沙州镇国王子的家族成员,十分有可能是沙州镇国王子夫妇及其僚属家庭。通过在敦煌石窟中绘制统治者及其僚属供养像以达到宣示地位和巩固统治的目的,滥觞于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苦心营建莫高窟第98 窟并绘制曹氏归义军文武官员实则是其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⑦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241 页。,而第39 窟的营建目的相似于第98 窟,即拉拢当地僧俗大众及宣誓统治地位合法性。在供养人像上方绘制的凉州瑞像也揭露了这一目的,《续高僧传》载“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⑧[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六《魏文成沙门释慧达传》,中华书局,2014 年,第981 页。,一般认为凉州瑞像“通过像首的完整与否,预示王朝与佛法的兴衰”⑨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407 页。。巫鸿先生提到凉州瑞像是一尊具有极强意义的佛像,它的形象得完整和受尊崇就意味着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安居乐业①[美]巫鸿:《敦煌323 窟与道宣》,载巫鸿著,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三联出版社,2016 年,第425 页。。
综上所述,第39 窟主室如此强调转轮王身份和国家统一、人民安乐,使得其与沙州回鹘统治者产生了联系,此窟极大可能为沙州回鹘统治者沙州镇国王子所营建,供养人群像为沙州镇国王子夫妇及其僚属家庭、敦煌大族家庭,其目的是拉拢当地僧俗与地方大族,彰显自身统治合法性,维护沙州回鹘统治。
六、结论与余论
榆林窟第39 窟是沙州回鹘洞窟中十分特殊且重要的洞窟,从第39 窟改造本定光佛授记图像入手,可以以点带面地对第39 窟主室壁画组合进行解读,发现了主室壁画隐藏在佛教主题中的“转轮王”的政治意涵,而 “转轮王”在政治中的独特内涵,将功德主的身份指向了沙州回鹘统治者,即文献中的沙州镇国王子,也就是沙州北亭可汗。
此外,还需要对前室的图像布局作一说明。甬道与前室的题材分别为说法图、化佛、千手观音、药师、菩萨题材。前室西壁的化佛与南、北壁的说法图共同构建了十方佛的空间概念,并配合甬道的千手千眼观音共同完成“灭罪”的宗教功能,《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载“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佛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②[唐]不空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大正藏》第20 册,第 116 页。应该是此设计的典据。前室东壁的8 身菩萨与西壁药师配合起到接引之功能③[唐]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载“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菩萨,乘神通来,示其道路,即于彼界种种杂色众宝华中,自然化生。”。总体看来前室主要强调灭罪的佛教主题,这一主题可能反映了政权更迭之下统治者借助佛教洗涤罪恶的心理状态。
因此,可以看出前室和主室的落脚点是不同的,前室更注重佛教功能,主室更强调政治功能。与敦煌多数洞窟单纯以追求佛教功能的功德目的不同,由于第39 窟功德主身份的特殊性与营建目的的多重性,其欲在宗教表象下去完成一个政治主题的表达,使得此窟具有宗教的一面,更有世俗的一面,所以主室和前室的设计并不能用一个连贯的宗教思想去解读,这是由功德主的身份、营建目的等因素所决定的,看似矛盾而又有理可循,因为整个洞窟在佛教内涵之外更突出对政治主题的建构。
(附记:在本文撰写过程中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西北工业大学石建刚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李志军博士提出诸多建议,兰州大学车涓涓博士对本文的回鹘文进行了再次释读,四川大学吕瑞东博士及复旦大学乔天博士为本文绘制线图,敦煌研究院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宋子贞所长提供了考察榆林第39 窟的机会,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