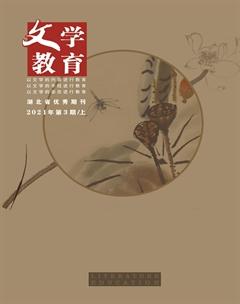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被掩埋的巨人》
吴奇
内容摘要: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运用各种奇异元素,对撒克逊入侵不列颠的历史进行拟写,以“遗忘”为叙事背景,继续着眼于他所关注的“记忆”主题。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分析不同空间中人物在集体信仰和自我目标间的不可协调性,从空间层面探究石黑一雄试图展现人类生存困境中普遍存在之矛盾的意图。通过小说中各种叙述视角的转换,作家深入洞悉不同人物的抉择与命运,表达了对集体信仰和使命感的质疑,并以开放式结尾的方式探讨真正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被掩埋的巨人》 空间理论 个体与集体 悖论
当代“英国移民三雄”之一的小说家石黑一雄于2015年发表的作品《被掩埋的巨人》以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为叙事背景,加以各种奇异元素,继续探讨他在创作过中一直关注的主题。与之前不同的是,《被掩埋的巨人》成功将人们的视线引向5、6世纪的不列颠岛,而不仅仅停留在某一国家的层面上[1]。这种书写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单一民族的权威历史话语,又使得石黑一雄惯用的“遗忘叙事[2]”手法更加普世。
石黑一雄依托“迷雾”,设置了多个寓意丰富的场景空间,它们充斥着各行其是但又互有交集的人物。寻求记忆却又惧怕过去的埃克索夫妇;英勇无畏却又充满困惑的维斯坦;守护母龙却又不被理解的高文;他们时刻存在于记忆与遗忘、个体与集体、信仰与道德的两难困境中,为所谓的“终极理想”而牺牲自我。某些空间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如罗马时代的宅子、神秘的森林、巨人冢等。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了空间的“三元组合概念”: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3]420,它们分别与小说的地理、精神和社会空间对应。
一.地理空间:权威话语与个体道德的悖论
根据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理论,地理空间通常指代物质化的空间,包括自然景观、城市景观等。与认为空间是一种容器的观念不同,列斐伏尔认為空间不仅起着容器的作用,其容器本身也具有意义,并且影响着其中的物体。地理空间对应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三元组合概念”中的“空间实践”。它指空间性的生产,围绕生产和再生产,与空间中的各种因素紧密相连[3]420。
在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往往存在超越自身的隐喻意义,而这些意义又与文本中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通过对多方面的隐喻,空间相对于文本整体而言的作用得以实现。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存在多个具有隐喻意义的地理空间,作者通过对远古时代地理空间和其中人物的描写,欲表达一种长存于人类社会的悖论。
1.修道院
社会空间实践与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空间实践在征服与使用社会空间之时,将其缓慢地与确确实实地生产出来。某一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通过对其空间的解谜才展现出来的[4]99。在《被掩埋的巨人》中,那座修道院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谜,而正是这些在遗忘背景下的谜团催生出地理空间中的各种矛盾。
修道院本是僧侣们静心修行之处,但却出现了象征灾祸的鸟类——乌鸦、黑鸫、林鸽,环绕屋顶的现象。一些僧侣更是对这些鸟恨之入骨——新来的僧侣拿着一个草袋子,这时他伸手进去,掏出一块石头,朝鸟群中扔去。“魔鬼!该死的魔鬼,魔鬼,魔鬼!”[5]129一位僧侣如此憎恨鸟群,一方面可以从僧侣们自我赎罪的方法中得知,另一方面更与在权力话语下个体行为准则密切相关。用于接受所谓“严酷考验”的笼子是僧侣们的赎罪媒介,但隐藏的却是集体对个人无形的控制。僧侣们轮流到那个笼子里去,让野鸟啄食身体,最终因凶残的鸟类而受伤或死亡。
僧侣出于对死亡的恐惧,真心忏悔之人在见证他人的死亡时就变得唯唯诺诺,这就导致了他们内心的矛盾。有些僧侣不理解这种自杀式赎罪行为背后意识与权力的关系,把这种无奈的心理外化到不详之物上。用以摧残身体的笼子可以看作是以院长为首的一派以肉体修行抵消罪过的僧侣对其余僧侣在道德行为规范上的压制。主张修行的僧侣逐渐由理性的赎罪转变为自我虐待的狂热,而直面真相的僧侣则逐渐由虐待的狂热转变为理性的赎罪。但由于院长的势力占据优势,理性之人便成了“小众群体”,想要为自我发声,却不得不服从集体。这种个体与集体在道德行为上的矛盾体现出修道院这一地理空间内部因素的不稳定性。
修道院的前身为撒克逊人防御外敌的要塞,且它的功能远不止御敌——对那些无法复仇的人来说,这就是提前享受复仇之乐[5]142。空间不仅是权威统治下的一台控制机器,也是没有特权之人的防御工具[6]。撒克逊人从对和平条约的坚信,到被亚瑟王背叛后遭到屠杀,这给族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仇恨。亚瑟王则为了独裁,利用迷雾美化统治。空间实践包括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特定的地点和空间设置[6]。这一切都可归结为通过对外部群体的压迫进而满足权力的欲望,所以这座要塞象征着撒克逊人对独裁统治的反抗。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与仇恨之下,撒克逊人开始变得享受复仇之乐,由此可以看出强权统治下群体情感的扭曲正是通过特殊空间的生产体现出的。
2.撒克逊村庄
由于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体现出某一种意义,每个由地点和物体所组成的团体都有一个中心,因此房屋、城市或整个世界都是如此[7154。但中心并非一直起着领导作用,它可利用自身权威的特点,在特定情形下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统治。小说中的村庄和部落体现空间中充斥的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冲突。在记忆模糊的背景下,融洽共处的人们实则被笼罩在权威话语的统治之下。
由于受到食人魔的侵扰,村民对一切外来事物都显得极其排斥。他们将食人魔作为一种负面的集体记忆而采取了适当的遗忘策略,所以一些人会因个人记忆而痛苦。当作为族长的不列颠人责备围堵埃克索夫妇的撒克逊人擅离职守时,他们虽神情沮丧,但仍略有疑惑。村民对异族族长表现出隐晦的疑惑感,这一现象表明撒克逊人在背负集体记忆的情况下对权威话语的内在抵制。这种抵制使他们质疑自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与“心照不宣”的统治产生矛盾,进而在村庄这一空间内部形成个人与集体的悖论。
当埃德温被维斯坦救回后,村民们的态度出现了反转。同样地,他们对待其他人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遗忘策略。这种策略看似能使族人暂时忘却折磨,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但也容易被权威所利用。食人魔代表某种潜在危险,它们造成的创伤形成了负面记忆。在短暂狂热后,村民的反应变得极为冷漠:这里头有种谨慎的沉默,近乎冷漠……钦佩与感激逐渐变成了其他情感[5]66……村民们并没有给予埃德温应有的关怀,而是想要杀死他,因为他们认为他会感染他人。害怕受伤害的人排斥、驱赶受伤的个体,目的是为了避免负面记忆入侵日常生活。同族人没有做到对集体记忆的共同承担与反思,而只是一味责怪真正需要关怀的人,这使得集权话语更容易依托遗忘渗透进集体道德规范中。
二.精神空间:守护和平与觉醒正义的悖论
人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等内化的空间即是精神空间。它是一种表象性的空间,通常与个人的知识与认知有联系,可以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潜意识行为得以显现。精神空间对应列斐伏尔“三元组合概念”中的“空间的再现(或空间表征)”。它指被概念化的空间,与生产关系以及这关系设定的秩序相连,从而控制一切书写的和言说的世界,进而控制空间知识的生产[3]420。
在文学作品中,精神空间构成了个体独有的、稳定的或者变化的特征。人物的内心想法和周围环境是影响精神空间的重要因素。在《被掩埋的巨人》中,骑士高文和武士维斯坦均存在丰富且变化着的内心活动。由于各自不同的使命,他们在如何对待遗忘的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异。通过对主要人物精神空间向度的分析,可以探究依托遗忘背景的权威统治对个体伦理道德的深远影响。
1.高文的浮想
索亚称第二空间为一个乌托邦的主要空间:艺术家和诗人的创造性想象,在此可谓如鱼得水[3]420。小说中最具乌托邦式想象色彩的人物就是骑士高文,他前后进行了两次浮想,将内心想法与读者娓娓道来。这些不外露的想法使得高文有别于英雄史诗中忠诚勇敢的圆桌骑士形象,纵然盲目服从权威,但也更接近现实中的人。
一群寡妇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高文的第一次浮想中,指责他未尽到职责,从而导致她们与丈夫相隔两岸。高文面对侮辱显得愤慨却又无力反驳。他无法隐藏内心的惊恐,因为高文的良知还未被权力话语完全压制。发生抵抗时,骑士时刻被拷问着:是否该以个人价值为代价换来民族使命;是否该以自由为代价承担生存的悲剧。高文从一位渴望向撒克逊人复仇的姑娘身上洞见了战争的残酷,开始对使命产生怀疑,并萌发了常人之爱。当面对埃克索的质问时,纵使显得振振有词,但被害者的骷髅却时刻提醒着高文该行为的后果。这也验证了在民族信仰以文化氛围、时代语境、社会责任等方式控制个体行为时,个体内心情感常常也会处在被扼制与压抑的痛苦之中[8]132。
“她有多么虚弱,难道埃克索阁下看不出来吗……难道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丢下这对拉着羊的老夫妻不管?”[5]264高文在第二次浮想的一系列反问足以看出他无法自拔的使命感不能完全磨灭他尚存的正义感。亚瑟王是高文自我辩护的主要来源,但小说通过历史隐喻解构了其英雄形象。在小说中,亚瑟王变得善于运用权力的铁腕达到专制。正是这种单一族群利益为先的权威统治,使为国家服务的人在集体制约与个人发展间痛苦徘徊,而高文则毅然选择了前者。选择终究是无比困难的,个人总在权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2.维斯坦屠龙后的困惑
空间的表象与生产关系还有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联系在一起,从而也与知识,与符号,与符码还有种种的“台前的”关系联系在一起[7]33。维斯坦虽然逃脱了被杀的命运,但却无法摆脱种族之间被强加的“秩序”,在自我身份的矛盾与复仇的使命间飘忽不定。虽然撒克逊人在小说中为屠杀的受害者,但小说中并未提及撒克逊人也是侵略者的事实,维斯坦的使命即是美化以暴制暴的战争。
维斯坦幼年时就被不列颠人带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战斗方式,成为了一名武士。在帮助同族人对付食人魔时,维斯坦被武士的职责所支配,虽然内在蛰伏着复仇的火种,但此时理性的一面占据优势。在拆穿僧人暗地里饲养母龙的事实后,火种被点燃,复仇的欲望淹没了理性的意识,个体职责和集体使命产生矛盾。最后在维斯坦屠龙之后,他显得垂头丧气,一点儿凯旋的模样也没有[5]304。维斯坦会引以为乐,因为在他看来那是正当的复仇。
维斯坦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因为他不仅是一名撒克逊武士,更是一名与敌人一起生活过的武士。多重身份使得维斯坦在蒙蔽自我完成使命时进退两难。在讲述与布雷纳斯的恩怨时,维斯坦显露出对不列颠人的厌恶:像兄弟一样去爱不列颠人,是一件耻辱的事情[5]223。在屠龙之后,维斯坦吐露了内心的想法:“等着我的是公正与复仇……现在时候快到了,我发现自己心里却颤抖起来……这只能是因为我在你们当中呆得太久了。[5]304”维斯坦明白其君主借复仇所要实施的侵占策略,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完成使命,因为维斯坦明白这种集体使命感与个体情感是互相排斥的。在强制的民族使命中,他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换来了悲壮的价值。
三.社会空间:安于和平与抵抗遗忘的悖论
作为空间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社会空间可以分为实体空间和非实体空间。实体空间包括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非实体空间内含文化、经济、阶级、性别等因素的多样化。社会与空间之间不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还是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社会空间对应列斐伏尔“三元组合概念”中的“再现的空间(或表征性空间)”。它指既有别于前两类空间同时又将它们包含其中的空间[3]420。
社会空间中“地点(或位置)”的概念和自然空间中的不相同,因为它们不是简单地并置在一起的:它们可能是插入、组合、叠加的,有时甚至可能发生冲突[7]88。小說描绘了一幅人人在遗忘的末端追求记忆的图景,但这些人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他们种族不同、价值观不同、终极理想不同等,并由此在记忆与遗忘的碰撞中产生了个体与集体间的种种矛盾。
1.社会地标中的权力运作
在列斐伏尔看来,除了作为一种生产的工具,它(社会空间)还是一种控制的工具,因而也是统治和权力的工具[6]……小说开篇就给出了社会空间中隐含的权力运作关系:“罗马人留下来的大道,那时候大多已经损毁,或者长满杂草野树,没入了荒野。[5]3”埃克索夫妇的避雨之处是罗马时代一幢辉煌的宅子,如今成了残垣断壁的景象。没落暗示权力的争夺所引发的战争终将摧毁一切,而战争就是复仇轮回的起点。维斯坦就是一个被复仇冲昏头脑的正义之士,他要求小男孩定要向不列颠人复仇。即使如此,他仍依稀记得从前埃克索所带来的两族人的和平,这种矛盾是对历史上复仇循环的隐喻。
荒地上生长的树林正巧处于巨人冢之前,这个位置排布象征着小说社会空间中和平表象下的权力作用。树林中被冰冻住而没入水中的食人魔就如普通人一般淹没在集体权力中,无法左右其命运。与所想不同,巨人冢不是“纪念一场胜利或一位国王[5]273”,只是为了掩饰母龙的藏身之处。在杀死母龙后,出现了“汹涌的血液先在脑袋两侧分流过,随后脑袋便浮了起来[5]303……”的景象,这也隐喻了不列颠和撒克逊之间即将爆发的冲突。虽说维斯坦执行了复仇之举,但他的君主依旧会像亚瑟王一样遵循着专制统治,也会通过某种手段掩埋屠杀的记忆,从而激起又新一轮的复仇。所以复仇带来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为争夺权力所导致的复仇轮回。
2.迷雾下的抵抗意识
《空间的生产》中有提及社会空间对利用者的反抗:这个空间也部分地摆脱了那些想利用它的人的掌控。那个造就了这种空间的社会和政治(国家)力量现在试图完全掌控它,但并没有完全做到[6]……在这个空间中,少年被设定为一群不受迷雾影响,始终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更为讽刺的是,不像“这些村民就从没想过要去回想往事——哪怕是刚刚过去的事情[5]7”,小说中涉及的少年似乎都没有忘记过去,他们反抗权威的统治。典型的代表就是小女孩玛塔和小男孩埃德温,他们都反映出权力下个体与集体需求的矛盾。
据埃克索回忆,玛塔在某天疑似失踪后,村民们开始四处搜寻。但两名牧羊人的归来“打断”了村民们不久前的记忆,众人开始为一只金鹰起争执,而把小女孩抛之脑后。只有埃克索一人隐约记得:“人们仍在争论着金鹰的事情,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他拼命集中精力,才能抓住小玛塔这个念头。[5]10”而玛塔心知肚明地表示:“……他们没有想我……他们可不是为我吵。[5]11”就连其母亲也只是在发现她后斥责了她一番,就又加入到争论中去。一个人云亦云的传闻就能令一群人为琐事起争执,人们在集体遗忘之下呈现出一种原始文明社会的状态——只关心自我生存,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9]105。
埃德温想要救出被不列颠人带走的母亲,于是产生了幻想,而频繁的幻想正是对遗忘最好的反抗。在谷仓中时,强烈的思念使他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她通过让埃德温像骡子一样转马车轮,暗示他历经磨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后,就将她找回。这是小男孩渴望追寻记忆时的自我激励,而母亲的形象就是这一渴望的象征。这种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强烈,变成了一种萦绕耳边的“呼喊”。随着埃德温的思念越发强烈,他开始谎称自己能察觉母龙的气息,以达到拯救母亲的目的。隐藏在幻想下的是意识中对“权威政治”的抵抗,这种意识推动着任何对社会空间内部统治力量“不满”的人摆脱它的控制。
四.结论
从整体来看,石黑一雄利用三重空间重读那些创伤的历史,以陌生的叙事加之弥漫于空间中的“遗忘”气息来揭示人类生存境遇中普遍存在的悖论,即个人一味顺从集体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无法实现独立个体的终极理想。石黑一雄通过对历史的拟写,对集体信仰和使命感提出质疑,反思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个体期望与集体使命的矛盾,并试图以“集体失忆”的方式获得救赎。模糊的结尾给读者留有充分的余地,引导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如何做到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王岚.历史的隐喻——论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1):8-14.
[2]邓颖玲.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遗忘叙事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1):1-7.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节译)[J].刘怀玉,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94-110.
[5]石黑一雄著.被掩埋的巨人.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6]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节译[J].晓默,译.建筑师,2005(5):51-60.
[7]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USA:Blackwell,1991.
[8]韩伟.《被掩埋的巨人》:民族信仰与个体道德的悖谬[J].河北学刊,2019(4):131-138.
[9]韩伟,胡亚蓉.记憶的责任与忘却的冲动——对《被掩埋的巨人》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语教学,2018(6):106-111.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