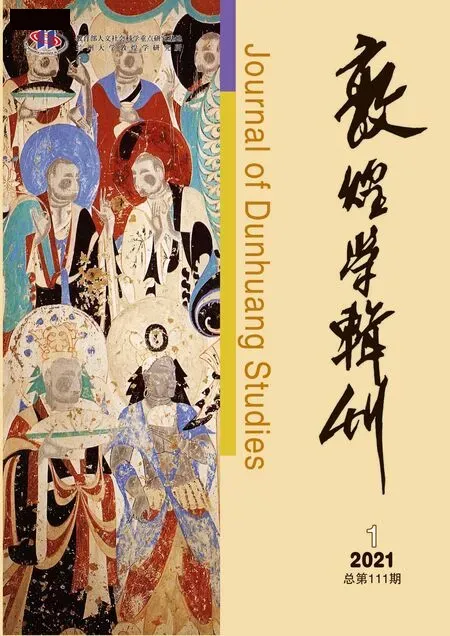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观念体现、视觉呈现与情感表达
杜星星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富丽、绚烂”,其“赋彩、渲染技巧发展到了高度纯熟的境地”(1)段文杰《佛在敦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5页。。近年来,学界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进行分期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其风格特征,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例如,常书鸿先生认为初唐色彩“古朴拙劣”,盛唐色彩“金碧辉煌”,但整体而言又呈现出“富丽”的特征(2)常书鸿《敦煌艺术的特点·敦煌艺展目录》,《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艺术卷》(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60页。;段文杰先生认为唐前期色彩“绚丽夺目”,后期则 “清新淡雅”“浑厚温润”(3)段文杰《略论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第4页。。另外,也有学者从用色、材质、观念等方面对唐代敦煌壁画色彩进行分析。如王履祥从唐代敦煌壁画的用色切入,发现从唐前期开始壁画色彩中的红、绿、青、黄等色逐渐增多,而唐后期因经济衰弱,用色单调,主要以青、绿两色为主色(4)王履祥《略谈敦煌的图案艺术》,《艺术生活》1954年第4期,第47-50页。;王进玉等人对唐后期壁画主要用色的原因进行考证,发现与当地制取及出售的矿物质有关(5)王进玉、王进聪《敦煌石窟铜绿颜料的应用与来源》,《敦煌研究》2002年第4期,第23-28页。;周大正对画面中的色彩构成进行分析,认为壁画的色彩的美感来自于对形式美的追求(6)周大正《敦煌壁画色彩结构分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95-100页。;王乃惠认为敦煌壁画的色彩体现了古人不同的审美思想和文化观念(7)陈乃惠《敦煌壁画“色彩之美”与“装饰之道”的融合》,《美术》2017年第11期,第136-137页。。还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的用色,认为色彩的理论根基来源于传统哲学(8)李栋良《探源溯流 五色弥新 ——2020年中国传统色彩学学术年会综述》,《美术观察》2020年第12期,第29-31页。。如彭德认为古人的“尚色”观会影响艺术创作的用色;冯时以传统阴阳观为基础,认为颜色的应用决定于“方色”(9)李栋良《探源溯流 五色弥新——2020年中国传统色彩学学术年会综述》,第29-31页。。这些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对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宏观把握,也加深了我们对敦煌壁画用色技术的微观认知。
不难看出,这些研究多运用西方建构的“色彩构成”理论体系来展开。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唐代敦煌壁画色彩方面的论题,还有较大的开掘空间。近年来,中国传统色彩理论研究逐渐深入,为立足本土,以“颜色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性和内涵”(10)[英]汪涛著,郅晓娜译《颜色与祭祀 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页。为基础,进行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体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我们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方光谱理论解读中国传统色彩有了重新的认知。我们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西传统色彩观念的视域中,运用文本解读、图像分析等方法对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从观念体现、视觉效果、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客观呈现不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色彩观。
一、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观念体现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马克思《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卷,第2页。,人们通过宗教来慰藉心灵。恩格斯也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1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对于这种“超人间力量形式”,也可以借助色彩来把握。色彩作为视觉感知中最易被把握的对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蕴含着不同的观念。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中的观念,是印度佛教文化的色彩观与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等不同色彩观念的折射与体现。
(一)对印度宗教用色观的发展
敦煌壁画的色彩虽受印度佛教用色的影响,却不同于印度佛教以“味”“情”为主的色彩美学观。如印度《舞论》规定色彩“分别隶属于某种‘情’和‘味’,诸如:绿色代表艳情、白色代表滑稽、灰色代表悲悯、红色代表暴戾、橙色代表英勇、黑色代表恐怖、蓝色代表厌恶、黄色代表奇异”(13)王镛《印度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0页。。另外,在印度佛教美术鼎盛时期的笈多时代,绘画所运用的青、绿、红、黄、白等色虽在敦煌壁画的用色中有所延续,但观念截然不同。就唐代而言,前期社会稳定,文化多元,经济繁荣,国家的自信与包容影响着敦煌壁画的色彩表达,壁画绚烂多彩,颜色满壁飞舞。壁画中的用色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银朱、朱磦、赭石、土红、石黄、藤黄、靛青、蛤粉、白土、金箔、墨等数十种”(14)段文杰《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整体以暖色调为主,色彩对比强烈。此外,在用色过程中画工还根据颜色品质的高低,将色彩绘制于不同位置:如将上品的、鲜红的朱砂色(马牙)应用于“主佛、菩萨、主要人物的嘴唇和面部”(15)王进玉、王进聪《中国古代朱砂的应用之调查》,《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9年第1期,第40-45页。。同时,将中国传统“五正色、五间色”理念对应于壁画设色当中,体现以人伦为基础的尊卑礼仪等级关系。在技法上,通过五色相生、间色杂多以寻求画面色彩的和谐关系(16)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及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2018年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图1 第57窟 说法图(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5·敦煌初唐》)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具体来看,唐代第57窟《说法图》的色彩,主要运用了矿物质颜料和人工颜料,颜色有蓝、棕、绿、白、红、金等色。画面中主尊佛结迦盘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身着朱砂及石绿相间的袈裟,头部发髻为石青色,佛身为赭石色系,色彩由深到浅依次减弱。头光以平涂法,配以蓝、棕、绿、红方形小色块环绕头部,在赭石及黑色头光之间有七尊金色小佛嵌于其中。主尊佛头顶华盖,华盖由黑、红边饰组合而成,华盖下部饰有青色琉璃宝珠。佛的两侧各有年长、年少两弟子,年少弟子身着白色僧服,衣襟以棕色相衬,手拖蓝色钵盂。年老弟子手持棕色净瓶,身着白色僧服,衣襟衬以深绿色,并以赭石色线勾勒衣纹结构。除此之外,还有数众菩萨,整体面相丰满,头戴宝冠,体态婀娜。主尊佛左侧菩萨面容以白色晕染描绘,头戴金冠,璎珞、项圈、臂钏、腕钏均以沥粉堆金。菩萨穿红色长裙,腰间搭以红色、蓝色腰裙并配以绿色腰带。头光以蓝、红、绿、蓝色相互交错而成。主尊佛右侧为大势至菩萨,菩萨身着红绿双色络腋,肩上披着石青色半透披帛。整体来看,色彩丰富、华丽,体现着唐前期社会的繁荣与自信(图1)。
唐前期壁画已经完成了从神性世界向人性化世界的转变(17)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 以壁画艺术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壁画色彩表达既是佛教色彩观的体现,又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唐代第57窟《说法图》局部《菩萨》来看,菩萨面部、身体均以白色罩染完成,画面层次丰富,肤色通透、气质温婉,菩萨符号已由“男性”转为“女性”形象,并展现了当时社会妇女的审美标准,是标准的“美人菩萨”(图2)。从《齐民要术》可知,当时妇女为美将米粉与胡粉混合进行面部化妆,配以“S”形身段,显得婀娜多姿,楚楚动人。然而,从象征性出发,白色更多体现菩萨的庄严、菩提、清静之心。因此,以白色对应菩萨形象,不仅是美的装饰,更是佛教文化色彩观对“菩萨”符号的特指。另将蓝色运用于主尊佛的头部,以体现佛的至高无上及“色相如天”的语词含义,同理,“佛头青”即是佛的特指。此外,头光中蓝、棕、绿、红等色不仅是头光的具象表达,更是光明之光、智慧之光的象征。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不仅具有装饰性或色相的称谓性,更多是被意向化的色彩。

图2 第57窟 菩萨(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5·敦煌初唐》)
此外,壁画色彩也是佛教经卷中色彩观念的体现。如《觉林菩萨偈》所载:
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彼心恒无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知。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 。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18)澄观撰,于德隆点校《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689-691页。。
画工通过作画来修行,并将画中的“五彩色”与佛教的“五心”教义相结合,达到内心与修行合一的无上境界。
由此可见,唐代敦煌壁画的用色相较于印度佛教,削弱了单色的观念体现,更多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在用色过程中,以多色彩结合或并置的方式来体现国家的自信以及人物社会地位的高低关系。同时,画工通过色彩的表现来达到修行的目的,以世俗之色来营造宗教之色。因而,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在传播的过程中,色彩也因文化语境不同被赋予了新的观念。
(二)儒家文化用色观的影响
唐后期敦煌壁画色彩具有端庄儒雅、和谐中庸之气(19)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及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2018年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17页。,体现了儒家文化观念的渗透和显现。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主要运用于佛像画、青绿山水、供养人、经变画等壁画之中。画面虽有“皇家贵族气派”(20)王文娟《论儒之理学与心学和中国绘画的内在关联》,《美术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2-107页。,但整体简淡、素雅。此时对石青、石绿的广泛运用与本地开采及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为画面色调的营造提供了物质资源(图3)。同时,唐代敦煌由盛转衰到几次易主,使得人们对大唐故国的怀念也成为壁画色彩呈现简淡、忧伤的关键所在。如唐代第323窟《远山归帆图》为青绿山水画。山、水为画面主要构成元素,从设色来看,山施以黑色,水为石绿色。山、水借助于三段式的构图方法营造于画面之中。利用没骨画法,将山峰以黑色分染、绿水以平涂罩染。近景现已模糊不清,对照段文杰先生的临摹作品《舟渡——迎佛图》,可知左侧近景处为黑色平面并置山峰,右侧以“平远”之法体现由前到后错落有致的四座黑色山峰,形状大小各异,山峰黑色均以不同的渐变方式由浓到淡。中景处有一黑色孤帆向堤岸挺进,船上分别点缀有着白、红二衣之人。两横向短墨堤岸,一前一后置于左侧,右侧堤岸横画墨线以百里之迥呼应于左侧。远景处从近山到远山具有“迷远”之势,山峰墨色有浓有淡,区别于近景,山峰在晕染过程中由黑色逐渐变为绿色。画面整体层次分明、云雾缭绕,远处山峰悄然消失于虚境之中。将水墨写意与石绿罩染、分染相结合,体现了儒家平和、内敛的精神意蕴。青水、墨山的空间营造整体给人以简淡、素雅的人生意境。结合山体三角点状的黑色(实)与湖面若隐若现绿(虚),有大实大虚之势(图4)。

图3 第323窟 远山归帆图(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5·(采自《敦煌壁画集》)

图4 第323窟 舟渡—迎佛图之一部(段文杰临摹)敦煌初唐》)
在唐代敦煌壁画中此种技法独具特色,并与同时期中原流行的青绿山水画互为影响。对于信众而言,现实生活中山的色彩并非黑色,画工将山的形态、色彩抽象提炼概括成黑色及三角形的母题的形式并平面叠加于画面之中,以与中国传统山水绘画的范式相统一,即黑色三角即为山,绿色平铺无需波纹便为水的“虚实”“留白”观。从可感知的黑、绿色到观念色的山与水,其背后体现的是儒家文化对敦煌壁画色彩观的渗透。儒家的色彩观以“素”“和谐、纯净、清朗”等气质来体现“平和、内敛”的情感(21)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及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第17页。,在唐后期敦煌壁画以青绿设色为特点,即是“正德正色的合礼之色彩,文质兼备的合度之色彩、绘事后素”(22)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及其对中国绘画的影响》,第17页。等文化观念的综合显现,也是退去浮华归本真的生命状态。
有学者认为以青绿设色的样式与印度佛教绘画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不可否认,唐代敦煌壁画与印度佛教绘画在用色的一致性上的确有传承性,但从唐代敦煌壁画青绿山水的设色特点来看,更是儒家文化观念的体现。史苇湘先生曾明确指出,“敦煌的壁画并不是边境艺术”,从现有文献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画家、画稿曾经不断地支配着莫高窟艺术的制作”(23)史苇湘《敦煌历史与敦煌莫高窟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竞争、交流及学习普遍存在于士大夫、民间画工及各民族画家之中(24)马化龙《莫高窟220窟〈维摩诘经变〉与长安画风初探》,《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艺术卷》(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儒家文化在敦煌壁画色彩观念中的渗入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与其说青绿设色的技法来源于印度,还不如说,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传播,思路便要发生改变,并要在本地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回应现实存在的问题(2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7页。,实现本土化的转变。
(三)道家文化用色观的影响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是以充盈之景来体现虚空之境。充盈与虚空是相对的概念,将其对应于壁画中,是构图、用色的饱满与画面视觉感知对信众的内心孤寂追求的无声回应。《庄子》中说,“厉风济则众窍为虚”,画面中的色彩太过丰富,反而给人以目盲之感。将道家的哲学观融入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中,在用色上虽感繁花似锦、琳琅满目,但在心理联觉反映上却是静穆与孤寂之境。可以看出,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是以技体道、以道来安顿生活。
如唐代第329窟《乘象入胎图》,画面五色杂呈,热闹非凡,描绘了佛陀在诞生前,菩萨乘坐六牙白象,在音乐声中飘然而来的场景。白象为人工颜料所绘,因时代久远,空气氧化,由原来的白色变为深棕色;乘龙仙人面容变为褐色,并身着红、绿相间服饰在前引导;菩萨身边有两位天人侍立,天人除氧化而成的黑色之外,主要以绿、红、蓝色点缀;菩萨头光绘有蓝、红、白色,光感强烈;左上角有四身飞天凌空而降,分别以花、音乐供养,在颜色、形体的衬托下具有强烈的舞动之美;另外,天空大面积弥漫着彩色流云与各色的鲜花,动感强烈,以“气”贯穿始终,体现了六朝宗炳所谓“万趣融其神思”的美学观。整体来看,色彩充盈、场面宏大、绚闹纷杂,使画面 “充实”而饱满,展现的是信众对佛国世界美景之向往。画工通过壁画中多种色相的混杂,以节奏、韵律等形式来表达 “充实”之实景(图5)。

图5 第329窟 西壁龛顶 乘象入胎图
但是,通过联觉感应,阅画者则体会到“充实”之景背后的“虚空”之境。只有达到内心的放空与无欲之境,才能脱离苦海达到彼岸佛国。因而,从视觉体现上虽以佛国世界的曼妙佛音、流云撒花、仙人飞舞来呈现,但在抵达之前,必须“化实景为虚境”(26)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0页。,以此来修心、修行、修性,以色彩达象征,直至高不可见、深不可测的心灵世界,以达到人生的“空灵”(27)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5页。,以及“无”“一”“玄”(2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页。之人生境界。此外,在道家看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作为修行者如若被世间红、黄、蓝、白、黑等色所迷惑,内心将难以抵达光明之境。画面虽然繁缛灵动,佛音缭绕,但五音、五色是让人静穆的内在本质,是道家文化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回归静穆之道,虚空之道,抵达信众心灵的重要途径。
二、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视觉呈现
“颜色是人类视觉最主要的内容,也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呈现给我们的重要维度。”(29)李海燕《光与色 从笛卡尔到梅洛—庞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在敦煌壁画中色彩的大面积运用,以达到“观者悦情”的宗教目的及审美效果。因而,从视觉呈现出发是继观念体现之后对色彩成因的进一步体认。它有异于西方光谱色的“视觉色彩”,也有异于歌德的“生理颜色、物理颜色和化学颜色”(30)李海燕《光与色 从笛卡尔到梅洛—庞蒂》,第71页。。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以“物理颜色”和“化学颜色”为基础,将信众的“生理颜色”与视觉感知相结合去澄清色彩的本质。对于视觉感知虽无相应的色彩理论,但在佛教经卷中有相似的“光”思维来对应,如“此是诸佛世尊常法,社如校时,口中便有五色光出,青、黄、白、黑、赤”(31)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36,《大正藏》第2册,第750页。。《大智度论》卷四十七云:“光明有二种,一者色光,二者智慧光。”(32)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藏》第25册,1988年,第58页。可见,佛教认为“色光”与智慧光、心光有关。大自然的造物离不开光,人类要摆脱苦难,达到彼岸更需要光明的指引。因而,画工通过色彩对光的视觉表达来体现信众对光明的内心向往。在唐代特殊的文化环境下,统治者与画工通过光思维以实现政治目的,表达信众的精神渴求。
(一)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中的光思维
“宗教运用光创造了人类永恒与幸福的心灵空间,把光速变成了通往宇宙或生命再生的桥梁。”(33)黄木村《色彩再生论全方位色彩运用与创新设计理念》,第24页。光虽然与色彩是不同的视觉现象,但二者密不可分,共同引导人类创造不同的精神文明。在唐代敦煌壁画中有大量图像资料通过色彩来表达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色彩来表达具象的光或火焰,二是通过掌握矿物质颜料的物质属性,根据色与色“同时对比”产生光的视错觉来体现光感。两种方式都是画工长期“处在丰富的生存空间中所积累而形成的色彩思维”(34)黄木村《色彩再生论全方位色彩运用与创新设计理念》,第25页。,将其应运于壁画创作之中,以表达信众对“生命之光”的渴望与追求。
唐代敦煌壁画中对光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可以通过具体图像来把握。
第一,仍以唐代第329窟《乘象入胎图》为例,在画面的左下角用红、蓝、绿色填涂火焰纹来表达光的形态,此为光的具象表达。通过光的真实描绘与信众在现实生活中对光的经验产生相同心理。同时,在盛唐第148窟的《倚坐弥勒佛》(图6)及晚唐第12窟的《倚坐弥勒佛》中将“色光、身光、外光”(35)芮传明《现代学术精品精读 中国民间宗教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7页。以绿、红、蓝、黑色来表达,也为光的真实再现(图7)。信众在黑暗无光的洞窟中得到画工思维之光的心理引导,产生光的情感共鸣,使具象的光从信众内心发生转换进而变为心光、光明之光、生命之光。可以看出,画工是借用经验之光到思维之“光”的创作转化过程来引导信众的心理体验。
第二,画工通过掌握颜料的物质属性来体现难以把握的心理之光。敦煌壁画主要用到的颜料有矿物质色、人工颜色和植物颜色(36)常书鸿《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第36-39页。。除少量植物颜料及易变色的人工颜料外,大量的矿物质颜料以及合理的色彩对比也是让壁画闪烁发光的原因之一,昏暗的洞窟在烛光的照射下矿物质颜料更具光明性。从唐代壁画来看,主要用到的颜色有石青、石绿,都为矿物质颜料。凡单独使用矿物质颜料,其呈色都比较明亮,且具有发光的视错觉。作为蓝色、绿色的对比色,橙色、红色(朱磦)也有一定的使用。据文献记载和现有壁画颜料分析,“敦煌彩绘艺术中大都用朱砂作为红色颜料”(37)王进玉、王喆《敦煌石窟艺术中铅白颜料应用与变色问题的研究》,第249页。,或用“红色的铅丹加白垩或其他白色矿物质颜料调成浓淡不同的红色”(38)王进玉、王喆《敦煌石窟艺术中铅白颜料应用与变色问题的研究》,第249页。。基于此,画工在长期的绘制过程中,利用颜料的矿物质属性,结合“光思维”和“同时对比”,在昏暗的洞窟中给信众营造光明的视觉心理暗示。

图6 第148窟 南壁 倚坐弥勒佛 图7 第12窟 南壁 倚坐弥勒佛
(二)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中的环境思维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呈现“是运用环境的色彩图形或合乎大众需要的空间色彩及共享安全的生活环境”(39)黄木村《色彩再生论全方位色彩运用与创新设计理念》,第127页。而形成的。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统治者通过善、爱的观念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壁画中的色彩环境思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如唐朝天台宗大师湛然(711-782年)在“众生皆有佛性”的基础上,提出“无情有性”之说,认为不仅众生有佛性,一草一木有佛性,世间万物皆有佛性。唐朝孟安排在《道教义枢》卷八《道性义》中亦云:“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40)《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册,第832页。。统治者通过佛道的戒杀生、禁贡献笼养鸟兽,提倡放生,崇尚节俭得善报等思想,影响人们去放生、斋戒。唐高祖、唐玄宗、武则天等分别诏令在佛、道斋戒之日断屠,皇帝生辰禁屠等。不难看出,在整个唐代社会环境中统治阶级都在营造善的、博爱的氛围,为人们的衣、食、起、居、习俗等方面营造良好的生存氛围,信众长期在这种环境思维的引导下,对万物的爱的同理心感触已形成契合度较高的色彩思维。
在莫高窟第202窟南壁的《弥勒经变》中,壁画以现实社会生活为依据,给信众营造“庄稼“一种七收,树上生衣,伸手可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41)王进玉《敦煌壁画中农作图实地调查》,《农业考古》1985年第7期,第139页。等理想家园。从局部《树上生衣》来看,树、衣服包括绿色草地,在佛国世界祥和的环境中也具有了佛性,并以没骨施彩的形式表达出来。树以石绿寥寥数笔勾勒而成,树枝分别挂有的三件红色长衣。依据佛经所讲,众生只要信仰佛法,都可以成佛。此处的树、草以及衣服并非画面上所呈现的一棵树或三件衣服,树、衣服都具有了佛性、彩性,而是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树及各种款式、色彩的华丽服饰的抽象物。画工通过色彩思维引领信众从视觉色彩创造生理色彩,让信众切实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从而去爱自然万物、爱国爱家。可见,色彩结合叙事情节刺激信众产生向善的心境,进而引导他们规范生活,故环境色彩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统治者的管理工具(图8)。

图8 图9
在中唐第205窟西壁《弥勒经变农作物》中,可以看到画面所描绘的场景来自现实生活,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视觉经验上也合乎大众对环境空间色彩观的认知。画面中收获的粮食为金黄色,捆扎于田间,整齐排列为三行;一着赭石色衣服的农夫正扬起连枷准备打场;收获的田地用土黄色绘制,与路边的绿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画面前方有红、绿两头牛正在耕作。整体来看,粮食的赭黄、田地的土黄、草地的绿色,都被信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意向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色彩。整幅画面洋溢着收获的色彩,应归功于画工对环境色彩的提炼与概括,色彩被信众所意向的同时,也达到了统治者运用环境思维的目的(图9)。
(三)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中的宗教思维
宗教思维与环境思维密切关联。工匠在创造信仰空间的同时,让信众“在庄重的色彩环境中产生信仰的力量”(42)黄木村《色彩再生论全方位色彩运用与创新设计理念》,第128页。。对于宗教特性的解释,迪尔凯姆认为,“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43)[法]迪尔凯姆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8页。。弗雷泽认为,“宗教是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讨好和信奉”(44)曹颖《从世俗化到宗教市场——论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转换》,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9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有着与其相适应的信仰、感情及仪式和组织。由此,宗教是庄重的、神秘的、超人的、有感情的,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难以被把握的,但信众的确通过宗教思维可获得神通与救赎。色彩作为宗教思维的桥梁,其功能不言而喻。宗教思维下的色彩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在原始社会时期,红色作为法器以赤铁矿粉或血液为鬼神沟通的中介物,具有巫术的寓意。从殷商到西周,用色彩体现尊卑等级(45)肖世梦《中国色彩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9页。。对于唐代敦煌壁画而言,色彩在昏暗的洞窟中,是信众与佛、菩萨沟通的媒介。从内色彩来看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以宗教人物为元素或以“五色”理论来设色,信众在特殊的色彩环境中既具亲切感又有陌生性。宗教思维给信众以心理暗示的同时,也启迪壁画艺术的创作。
如在中唐第44窟《千佛》的色彩表达中,将石绿、石青、赭石、朱砂、鹅黄、白色等交替描绘于佛的袈裟、头光、身光中,色与色的相互交映,给人以佛光普照,法相庄严的视觉感知,同时具有“超脱的宗教氛围”(46)李海磊《4-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壁画色彩技术与应用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90页。。若将以上色彩变换成其它任意色系的色彩,或提高色彩的明度,势必削弱宗教氛围的神秘性、庄严性。此外,假设将此幅壁画脱离于洞窟昏暗的环境空间,放置于现代或明亮的空间氛围中,也将失去色彩的神秘意味。由此可以看出,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色彩、特定的受众群体,都是宗教思维不可缺失的条件(图10)。
另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色彩观念也迎合了中国宗教的思维模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在不断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在色彩的运用上也出现了极大的适应性改变,如对“五色”体系的应用,就是突出的例证。早在先秦文献中,“五色——青、赤、黄、白、黑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而且广义的五色和狭义的五色往往混在一起,使神秘的五色更加扑朔迷离,难以理解”(47)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唐代敦煌壁画中,对 “青、绿、黑、白、朱五色,间用少许金银”(48)李其琼《敦煌唐代壁画技法试探》,《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篇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的运用与中国传统五色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初唐第244窟《说法图》中,主尊佛的袈裟用大面积的朱砂来渲染,明丽而鲜亮。在佛教中朱色袈裟最为尊贵,用朱砂绘饰,符合中国信众的审美认知。因此相似的色彩认知,在特殊的空间环境中才能给信众以认可和安全感。因而,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宗教思维只有在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的基础上才能够被信众所接纳(图11)。

图10 第44窟 千佛 图11 第244窟 说法图
在唐代,宗教是普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个人、社会乃至国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宗教对唐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统治者利用画工之手,借助不同的色彩思维模式,在安抚信众、巩固统治的同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特色鲜明的壁画作品。
三、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情感表达
宗教壁画是信众情感的寄托点和宣泄口,画工通过色彩将信众遮蔽的情感转换为可感、可知的语言形式,是信众内在生命追求的显现。色彩作为特殊的符号,在唐代敦煌壁画中并非画工的“主观情感”表达,画工个人的“主观情感”在壁画中常常是被遮蔽的。敦煌壁画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客观情感”,“是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亦即各具体情感的抽象物”(49)Susanne K.L,anger.Philosophy in a Neww Ke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41.,是将信众的情感对象化,是对信众普遍情感的抽象与提炼。色彩是情感表达的媒介,其所表现的也正是情感的本质。
(一)唐代敦煌壁画色彩是生命的体现
“生命形式是同人类情感的普遍形式相近的概念”(50)朱立元等《现代外国美学教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58页。。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色彩是信众生命情感的投射,色彩具有生命性、流动性及融合性。同时,壁画中的色彩是生命的显现,是画工对信众普遍内在生命的关照,信众也常常通过色彩来体认自我。唐前期社会稳定,富足,壁画色彩彰显着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包容,以及信众对生命的热情和由内而外的自信与乐观,因而壁画色彩丰富、绚烂、舞动。唐后期,吐蕃入侵,社会动乱,随着张议潮对敦煌的收复,壁画中对故国大唐怀念的种种情绪流露在石青、石绿为主的冷色调中,宁静而内敛,更多的是内心隐秘情绪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唐后期壁画中绿色的大量应用,象征着“希望和永生”(51)[法]米歇尔·帕斯图罗著,张文敬译《色彩列传·绿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2页。,是表达“生命欲望的‘生命体征’”(52)[美]W.J.T.米歇尔著,陈永国、高焓译《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9页。。信众在进入黑暗洞窟的一刹那,情感得以宣泄,生命之情得以流淌。总之,唐前期敦煌壁画色彩体现着生命的活力、自信及积极向上的流动力,唐后期敦煌壁画的色彩体现着信众对生命的笃定与渴望以及繁华之后内在生命的沉寂与反思。
壁画中色彩的方向性是生命的动态流动。仍以唐代第329窟《乘象入胎图》为例。色彩本身是静止不动的,但将其蕴含于曲线形体之中,色与色之间便产生了强烈的方向性及流动性。在壁画中以乘坐六牙白象的菩萨为中心,天空中的飞天、菩萨、乘龙仙人、流云、鲜花如“旋玑玉衡”般环绕着乘象菩萨“天道左旋”(5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133页。。整幅画面流淌着气韵、流动着生命。若没有对天、地、人的顺“道”而行的感悟,画面将是杂乱无序的,更不会出现繁缛中蕴藏顺时针旋转的秩序性。此种秩序性,也引导着信众的视线在有序流动,“它们看上去就好像是那生命湍流中最为突出的浪峰。因此,它们的基本形式也就是生命的形式,它们的产生与消失也就是生命的成长与死亡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形式”(54)[美]苏珊·朗格著,藤守尧译《艺术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3页。。生命在流动,色彩也在流动,二者彼此相融(图12)。

图12 第329窟 西壁龛顶 乘象入胎图
另外,画工借助情感共鸣将壁画中的色彩与信众联系在一起,这在歌德看来是“生命动态的流动”(55)[英]孙孝华、多萝西·孙著,白路译《色彩心理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7页。,是“心理的运动知觉”(56)包玉姣《艺术:一种生命的形式——苏珊·朗格艺术生命形式理论研究及其对艺术教育的启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6页。在视觉感知空间当中的营造。结合整个唐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变化,可以深切体会到生命的存在、成长、繁荣与没落,这是一个完整的流动的过程。壁画中的色彩将信众生命中遮蔽的情感通过可知、可感的色彩符号投射出来。色彩的生命即是信众的生命,它流动不息,共感共知。
(二)唐代敦煌壁画色彩的自由性表达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遵循“随类赋彩”的用色规律。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有“随类赋彩”(5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年,第3页。的说法。所谓“类”,就壁画而言,是在同一文化语境中对相同或相似的壁画内容进行归类。唐代作为敦煌壁画的全盛时期,凿窟数量众多,壁画内容丰富,藻井图、佛像画、佛教史迹画、经变画等各具特色,但整体设色井然有序。在佛像画中,根据主尊佛、菩萨的不同地位,将主色、辅色、点缀色依次按照面积大小进行分配。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遵循了以上的赋彩规律,壁画的色彩才给人以自由放松的状态。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具有概括性、平面性。在设色过程中除去了繁缛的细节,将形体用色彩的方式概括于平面当中。正如宗炳所说:“且夫昆仑山之大,曈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方寸之内。”(58)俞建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583页。通过对色彩的提炼与概括,舍去画面中不必要的小细节,才能达到“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自由状态,以及对色彩表达过程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笔笔生发”的效果。另外,从受众来看,方可对画工在创作过程中身形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感同身受。
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具有“象征性”。对颜色的分类和象征“在古代中国的天人交感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59)[英]汪涛著,郅晓娜译《颜色与祭祀 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98页。。如果将“五方”“五行”对应“五色”,色彩依次为青、赤、黄、白、黑,依据不同的文化语境,色彩的表达也不尽相同,如“黄色”在西汉、曹魏、北魏具有“土”德之意,从唐代开始则变为至尊之色,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正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载:“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6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2页。不难看出,唐代对黄色的运用与分类已非常细致,并影响于敦煌壁画的设色当中。唐代敦煌壁画中底色一改前期的土红底,有大量的黄土底出现,同时在人物的配饰上也大量运用金色,以金代替黄色,体现黄色的至尊之色。如上文《说法图》局部《菩萨》,将金色运用于菩萨的头饰当中象征佛教的神圣与光明。
总之,作为敦煌壁画全盛时期的唐代敦煌壁画,其色彩的观念体现、视觉呈现与情感表达等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观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再发展。从唐前期到唐后期所呈现色彩的相异之处,更多体现了色彩象征性的变化及文化内涵的多元化发展。画工、信众、统治者作为敦煌壁画的共同参与者,在笃定营造宗教信仰空间的同时,各自得到了生命的体验和自由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