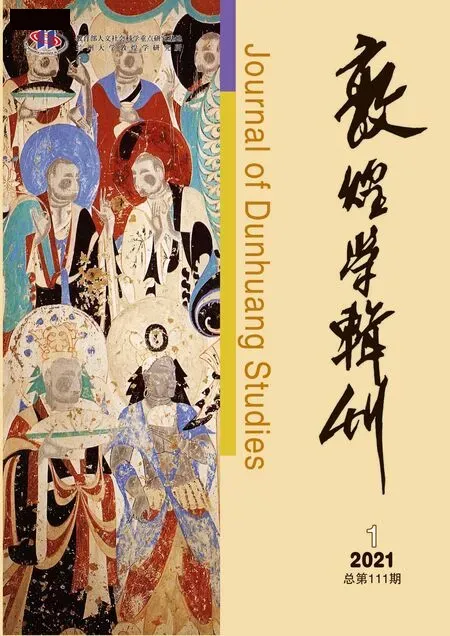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与唐代焉耆交通研究
党 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位于新疆尉犁县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属于从罗布泊沿孔雀河通往焉耆的烽燧群,普遍被认为是汉晋时期所设。(1)黄文弼 《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吐尔逊·艾沙 《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羊毅勇 《从考古资料看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等。新近考古发现认为,该烽燧始建于唐代,(2)张迎春 《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大量文书、木牍等》,《新疆日报》2019年11月23日;张海峰《烽火边声壮士行——唐烽燧遗址考古还原千年前戍边生活》,《新疆日报》2020年11月13日;王瑟《1200多年前唐代将士如何戍边》,《光明日报》2021年2月22日等。是唐代继续使用“大碛路”的体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书中出现了大量与焉耆相关的交通路线及军防建置的名称,如“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交通线路,(3)比如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苏累铺等军事机构,也有铁门关、于术守捉、西夷僻守捉、西州、于阗、安西都护府等地名。是唐代焉耆四通八达交通路网的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于唐代焉耆道路交通多侧重于连接西州与龟兹的东西交通,而对于“大碛路”及焉耆南北交通的关注不够。(4)目前关于焉耆交通体系的相关研究主要如:王子今 《焉耆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唐都学刊》2018年第1期;郑炳林《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并的大碛路:兼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毕波 《粟特人在焉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裴成国 《论5-8世纪吐鲁番与焉耆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李行力、孙雪峰《焉耆历史沿革考述》,《西域研究》1998年3期;张宜婷《从安西四镇之焉耆镇看唐朝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和经营》,《昆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等等。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及出土文书为研究唐代焉耆交通提供了实物资料,以此可更为深入地分析焉耆在天山廊道和塔里木盆地的交通状况。
一、唐“大碛路”史籍阙载的原因
“大碛路”,又称白龙堆道,即汉通西域时的“北道”,汉晋时期,从敦煌到西域多循此道。该道从敦煌出发,沿古代疏勒河向西,到楼兰,此后,从罗布泊沿着孔雀河河道到焉耆。(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魏略》中对该道有明确的记载:“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并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6)[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59页。这条道路横穿库木塔格沙漠,路程最短,但沿途仅有楼兰绿洲可提供补给,导致出现了楼兰国因供应汉使不堪繁重赋役而截杀汉使的情况。(7)[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6页。
在官方记载中,“大碛路”在隋末废弃。“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08-6209页。,由此因焉耆要求唐朝重开大碛路而引起了高昌和焉耆的战争。贞观六年(632),焉耆遣使唐朝,《资治通鉴》载:“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六年”,第6209页。焉耆欲重新开通“大碛路”,遭到高昌的攻击,成为唐朝发兵平高昌的导火索。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平高昌之役,侯君集特意“遣使与相闻,突骑支喜,引兵佐唐”(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9页。。而且,在贞观九年(635)时,唐朝平定吐谷浑,收复了被吐谷浑占领的鄯善、且末一带,控制了青海道,从青海道进入塔里木盆地也成为丝绸之路较为便捷的通道。
因此,从中原进入西域,北可经伊吾、高昌,南可取青海道,“大碛路”逐渐失去了进出塔里木盆地的交通枢纽地位,此后,“大碛路”阙载于史籍。
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与唐代“大碛路”
位于孔雀河沿岸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发掘,使得唐代“大碛路”重现于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烽燧不是魏晋时期的建筑,而是唐朝时期所建,这说明唐朝不仅没有放弃“大碛路”,而且还在继续使用并进行建设,使其继续发挥交通职能。
1.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基本情况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今新疆尉犁县古勒巴克乡兴地村西偏南57公里处的荒漠中,东距营盘古城47公里,距楼兰古城233公里。目前考古发掘显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始建于唐代,称为“沙堆烽”,是焉耆镇守军下辖一处游奕所驻地,填补了史籍对于唐代“大碛路”记载的空白。
根据考古工作者胡兴军的记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包括烽燧本体、居址等设施,目前已清理出房屋、土埂、木栅栏、踏步各一处,灰堆五处。烽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东、北两侧因风蚀坍塌严重,南侧有土坯垒筑的护坡,烽燧在使用时期至少加固过三次;在烽燧南侧沙堆下呈南北向排列分布着一道木栅栏,似为牲畜圈墙,反映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将士的日常戍守情况。(11)王瑟《1200多年前唐代将士如何戍边》,《光明日报》2021年2月22日。
至2020年底,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共出土各类遗物1368件(组),其中有纸文书、木简861件,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以及各级军事机构正常运行的情形;烽铺之间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令,并对该地实施了有效管理,如文书中出现的“开元六年榆林镇下各烽远藩探候宜急书入报牒”“十七日第一牌送沙堆”(12)胡兴军、索琼 《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纸文书、木牍700余件,初步推断为唐代焉耆镇下设军事设施》,《中国考古网》2021年1月7日。的记载。这些多元化军事机构的设置,是唐代焉耆镇守军戍卫孔雀河流域交通路线的具体展现。
2.唐朝重开“大碛路”的背景
唐朝自贞观九年开通“大碛路”后,(13)李宗俊《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第128-139页。对焉耆南部的交通极为重视。根据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出土的钱币、含有“武周新字”的文书简牍以及碳十四标本的测试,该烽燧的建造时间至少不会晚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破四镇、以三万汉兵驻守西域的时间。
第一,应对吐蕃威胁
吐蕃对西域的威胁,唐朝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王小甫先生认为,唐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从讨龟兹到平阿史那贺鲁置四镇,全部精力都在对付西突厥,并没有认识到吐蕃兴起的严重性。(14)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第95-104页。
唐太宗在贞观六年允诺焉耆重开“大碛路”主要是出于联合焉耆共抗高昌的战略考量,而此后吐蕃征服吐谷浑时就开始染指塔里木,龙朔二年(662)苏海政的海道行军为史载吐蕃与唐军在西域的首次交集,苏海政因“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而撤兵(15)[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二年,第6447页。;龙朔三年(663),吐蕃灭吐谷浑,尽有其地,青海道成为吐蕃进入塔里木的交通要道。且正值吐蕃攻灭吐谷浑时,唐朝却在尽全力攻伐高句丽,体现了唐朝对吐蕃缺乏应有的警惕。
但吐蕃对于塔里木的入侵渐趋猛烈,总章元年(668),吐蕃经阿尔金山“于且末国建造堡垒”(16)王尧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藏学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陆离 《论萨毗地区的吐蕃势力及其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认为ji ma gol是大非川,吐蕃不可能于668年就进入西域,且在新疆米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中且末被称为cer cen。,并大举进攻西域,到咸亨元年(670)“于且末国击唐军多人”,与于阗联兵攻破龟兹拨换城,“陷四镇”。在与唐朝争夺四镇的过程中,吐蕃在阿尔金山一带频繁出没,增加了焉耆南部的防御压力,因此唐朝逐渐意识到“大碛路”的重要性,可与焉耆形成南北策应,以免腹背受敌。
长寿元年(692),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但吐蕃勾结西突厥势力,“首领勃论赞与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与孝杰战冷泉”(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079页。;延载元年(694),“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勃论赞刃、突厥可汗俀子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俟斤等万余人”,“冷泉”在焉耆东南,(18)“冷泉,在焉耆东南,唐武后长寿末,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及四镇与冷泉,又破之于大岭谷,或曰破西突厥于冷泉也。”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5《陕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65页。这说明,吐蕃在碎叶一带作战失败后,很可能与阿史那俀子相互勾结南下沿塔里木河直至焉耆东南一带,王孝杰在此与吐蕃交战,这一带也是吐蕃进入塔里木行军的路线之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书中有关于“麻泽贼路”的记载,这里的“贼”或指吐蕃或者吐谷浑,《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有“迂曲近贼”的记载,“贼”指的正是当时与唐关系紧张的吐蕃和役属于吐蕃的吐谷浑人,且该文书撰成于武周长寿元年(19)李宗俊 《〈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3-59页;李宗俊 《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第128-139页。,因此,也不难看出唐朝以“大碛路”作为防御吐蕃的目的。
开元七年(719)唐朝以焉耆备四镇的规划,也是对吐蕃势力防控的战略考量。根据《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及至羊年(719)……征集“羊同”与“玛儿”之青壮兵丁,埃·芒夏木达则布征集大藏之王田土地贡赋”“及至猴年(720)……默啜(可汗)之使者前来致礼……征集大藏之王田全部土地贡赋……攻陷唐之索格松城……”(20)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吐蕃与后突厥默啜合兵威逼河西的举动也引起了唐朝的重视,以焉耆备四镇的战略选择强化了对“大碛路”的防御;同时,以焉耆备四镇也阻止了吐蕃取阿尔金山道与突骑施苏禄的联兵。(21)[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63页。景龙二年(708),《旧唐书·郭元振传》载:“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2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第4365页。开元十五年(727),吐蕃与突骑施联合入侵塔里木,吐蕃正是采用了经图伦碛东南北上进入焉耆的路线(23)王小甫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155页。。因此,以“大碛路”为主建立抵御吐蕃的防线是焉耆镇守军军防职能的重要体现。
第二,唐朝开通并重建“大碛路”是西域形势所迫
“大碛路”连接罗布泊地区与塔里木盆地,P.2695《沙州图经》载:“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西度计戍河。”(24)图版及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6页。“大碛路”成为与银山道并行的交通要道,体现出唐朝对焉耆交通体系的高度重视。
孔雀河沿线是“大碛路”交通的主体部分。《晋书·焉耆传》载:“其地南至尉犁,北与乌孙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2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7《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2页。焉耆地处山间盆地,铁门关是其西南部的唯一出口,孔雀河经铁门关,迂回流向东南注入罗布泊,且少有支流,使得孔雀河流域成为从东南部进入焉耆的唯一路径,因此,焉耆在掌控并完善进出焉耆的交通路线时,有必要重新开通“大碛路”,并重建焉耆南部的交通体系,将“大碛路”与铁门关一带充分结合起来,形成焉耆南部的防御圈。
早在汉代时,孔雀河尾闾楼兰地区的重要交通地位就得到中原王朝的充分重视和经营,一度成为屯田要地,东汉班勇欲屯田楼兰时指出:“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2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8页。如此,中原驻军可进可退,攻守自如,充分反映出这条路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又有敦煌索励“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27)[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卷2《河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页。是当时引塔里木河水灌溉楼兰屯田的体现,皆为唐朝经营“大碛路”奠定了基础。
从楼兰古城过营盘遗址溯孔雀河而上,可到达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朝设置在孔雀河沿线的防御工事之一。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遗址中出土了包含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遗迹各类园艺作物、马、牛、羊、驴、骆驼等动物标本,显示出唐朝军队曾在此屯田的迹象。(28)王瑟 《1200多年前唐代将士如何戍边》,《光明日报》2021年2月22日。
此外,分布在孔雀河沿岸的烽燧又有兴地山口烽燧、脱西克烽燧、卡勒塔烽燧、沙鲁瓦克烽燧、萨其该烽燧、孙基烽燧、亚克仑烽燧、苏盖提烽燧、库木什烽燧、阿克吾尔地克烽燧等军防工事,可与罗布泊以南的石城镇、播仙镇等形成拱卫之势。因此,唐朝开通“大碛路”,为强化对焉耆的管理、进一步经营天山南麓绿洲诸国奠定了交通路线基础。
3.“大碛路”与“墨山国之路”
“墨山国之路”是唐代“大碛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山国故址似为今营盘古城遗址,(29)黄文弼 《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同氏著、黄烈编 《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7页。楼兰文书中将其称为“山城”(30)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8页。,“墨山国之路”即为从楼兰经营盘遗址、兴地山谷进入库鲁克塔格山,过辛格尔绿洲、梧桐沟,至吐鲁番盆地柳中的道路,(31)罗新《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3-509页。民国时期称为“吐鲁番歧路”。是连接罗布泊、渠犁与吐鲁番盆地之间的纽带。沿“大碛路”从焉耆沿孔雀河至营盘后,可与“墨山国之路”相接,成为焉耆连接吐鲁番盆地的交通要道。
汉代墨山国就与焉耆来往密切,《汉书·西域传》载:“(山国)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榖于焉耆、危须。”(32)[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1页。墨山城在鄯善与焉耆之间的交通线上,“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33)[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2页。,北道从楼兰古城向西北方向去往车师前国,“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34)[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5-3876页。,而从扜泥城抵山国经由焉耆前往交河城,里程将多出四百七十里(35)余太山 《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14-20页。,这说明从焉耆经山国至吐鲁番盆地的道路自汉时便畅通,为交通要道。
唐代“墨山国之路”仍在频繁使用,是大碛路的辅助道路。《通典》“交河郡”载:“南至三百五十里,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36)[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47“交河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557页。“荒山”即为库鲁克塔格山,(37)罗新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5卷,第508页。这条路正是从焉耆经“大碛路”至营盘取“墨山国之路”的必经之地。
斯坦因曾在此发现了一个东西400英里、南北200英里的辛格尔绿洲,“这是山中唯一的田园,土地经过灌溉,生产出粮食,卖给来往于吐鲁番、罗布间那条直路上的客商”(38)巫新华 《斯坦因》,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且“辛格尔是一个较小但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库鲁克塔格山西部的一个绿洲地区,在此有数条分道可以通向塔里木盆地的下部、故楼兰和焉耆地区”(39)[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页。但是,在该文中斯坦因误将辛格尔绿洲视为山国所在地。,斯坦因所发现的道路,就是墨山国之路的一部分。
唐代墨山国故地应是西州下辖的一处屯戍要地,斯坦因曾在营盘遗址获取《唐右廂第二队上应请官牛数状》文书,录文如下:
1 右廂第二队 状上
2 合当队应请官牛数□五头
(后缺)(40)陈国灿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6页。
由文书中出现的“官牛”“西州”等内容,结合斯坦因发现的其他诸如《唐纳钱抄》《书札残片》《纸片》等唐代文书,(41)陈国灿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第477-479页。林梅村认为出土于古墓的编号Y.Ⅲ.03号文书(《唐右廂第二队上应请官牛数状》)可能为唐代文书,其他三件文书相当残碎,可能为魏晋文书,见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97页。可以认为,营盘遗址在唐代仍然发挥着保障“大碛路”“墨山国之路”交通沿线的作用,进一步反映出焉耆经库鲁克塔格山与西州之间交通防御的严密布局。
此外,根据目前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文书,如《唐残文书为入大城报西州裴司马等事》《开元六年(718)榆林镇下各烽远藩探候宜急书入报牒》等,以及新发现的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苏累铺等未见于史籍的军事机构的记载,(42)胡兴军、索琼 《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纸文书、木牍700余件,初步推断为唐代焉耆镇下设军事设施》,《中国考古网》2021年1月7日。其具体地点暂不能确切考证,但仍可透露出焉耆经“墨山国之路”与西州交通体系的紧密联系,补充并强化了西州与塔里木的交通路线。
三、焉耆在西域东西交通的地位
唐代“大碛路”的继续使用,也启发了我们对焉耆东西交通的重新认知。实际上,焉耆在唐代的天山廊道中,不仅是从西州通龟兹的枢纽,南下驰援于阗、石城的要道,而且是进出天山廊道内部的重要通道,由此可以通过开都河而上从天山内部进入北部轮台、弓月,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和战略枢纽。
1.焉耆通西州的交通
唐代从焉耆前往西州多取“银山道”,《西州图经》载:“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卤。”(43)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5页。唐朝在沿途设置了守捉、馆驿保障交通畅通,《新唐书·地理志》载:
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磐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44)[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40《地理志》,第1046页。
这条道路是唐代连接西州与焉耆镇守军的官道。《唐神龙元年(705)天山县录申上西州兵曹为长行马在路致死事》文书载:“州糟长行马一匹,赤、敦,右得马夫令狐嘉宝辞称:‘被差逐上件马送使主何思敬乘往乌耆,却回。’其马瘦弱乏困,行至县西卅里头碛内转困,牵不前进,遂即致死……”(45)陈国灿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256页。此为天山县呈报西州至焉耆后返回的长行马在银山碛一带死亡的牒文,反映出这一条道路为唐朝频繁使用的情形。又如阿斯塔纳出土的纸棺文书,记载了唐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753-755)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所见驿馆名称有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舍、柳中、罗护、赤亭等(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第51页。,其中卷之第(一六)件某馆牒中,于十一月十八日记载:
127 同日封大夫乘帖马卌二匹……
128 同日郡坊帖马卌五匹送封大夫到吕光迴……(47)朱雷 《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碛西北庭行》,收入《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封常清一行人经过的“吕光”即吕光馆,属于安西四镇节度使的管辖范围。
此外,根据目前焉耆东部的遗存分布来看,焉耆镇守军东部布防了大量镇戍、烽燧保障焉耆东道的安全畅通,以博格达沁古城为中心,分布着阿克墩烽燧、四十里大墩烽燧、曲惠古城、西地古城、红蝶谷戍堡、黑圪垯城址、硝尔墩遗址等,(48)张安福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2-130页。部分遗址内出土了石磨、陶罐等遗物,有的遗址区域内灌溉渠道纵横,是唐代在此屯田以保障交通安全的重要见证。同时,根据这些遗址分布可以发现,焉耆在东西交通路线中也存在着南北的勾连,如从红蝶谷戍堡向北可到达阿拉沟,即唐代鸜鹆镇所在地,位于西州进入天山内部廊道的山口,也是西州连接焉耆的天山内部捷径,体现出唐朝对焉耆镇守军交通路线的严密布局。
2.焉耆通龟兹的交通
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新出土的文书中,也出现了“铁门关”“于术守捉”“西夷僻守捉”“安西都护府”等地名,(49)王瑟 《1200多年前唐代将士如何戍边》,《光明日报》2021年2月22日。是唐代焉耆镇守军与安西都护府之间密切往来的重要见证,是焉耆西道交通布局的体现。《新唐书·地理志》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50)[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第1151页。这些关口、镇戍、守捉皆为保障焉耆西向交通的军事设施,维护焉耆的交通枢纽作用。
从焉耆西出铁门关,进入今轮台县,为安西都护府辖境,汉代乌垒国所在地。其中“于术守捉”位于焉耆镇守军至安西都护府的大道上,其遗址为今玉孜干古城,黄文弼称其为“夏渴兰旦古城”,又说为尉犁国之都城,是焉耆西道重要的屯戍基地;又有“榆林守捉城”,即今阿克墩城堡,位于轮台县东约75公里的野云沟,考古工作人员曾在阿克墩古城采集有陶器和铜器以及“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5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轮台县文教局 《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第10-11页。;“龙泉守捉城”即轮台县策大雅乡西约26公里的阳霞乡博斯坦村的龙泉遗址,今遗址不存,唐代为重要的屯戍区域。
“东夷僻守捉”为轮台县阳霞乡西南30公里的恰库木排来克戍堡,古城地表曾发现有夹砂红陶片,五铢钱币,铜制饰品和陶器残件(52)张平 《有关唐安西乌垒州等地望考》,《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西夷僻守捉”即今拉依苏戍堡遗址,汉代时,这里曾是龟兹与乌累两国分界处的关城,唐代的乌垒关,包括汉代烽燧、唐代烽燧以及城堡遗址三部分,戍堡内出土了铁刀、弓箭等兵器外,还出土了铁犁铧、铁镢头、铁镰刀等农具,大量的石磨谷物加工用具、陶罐、纺轮等生活用具(53)张平 《有关唐安西乌垒州等地望考》。,戍堡四周有明显的水利渠道遗址,是唐代屯田保障交通的重要基地;“赤岸守捉”可能为却勒阿瓦提烽戍,位于库车县牙哈镇却勒阿瓦提村东约7公里的盐碱荒漠中,是焉耆西道最靠近安西都护府的防御镇戍,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以上六个守捉在焉耆镇守军与安西都护府之间依次排开,保障了焉耆通龟兹的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沿途遗存的阔纳协海尔古城、喀拉亚烽燧、廷木墩烽燧、喀拉墩烽燧、阿孜甘古城等,(54)包括依斯塔那戍堡、吾孜塔木戍堡、克日西戍堡、脱盖塔木烽火台、丘甫吐尔烽火台、博斯坦托格拉克烽火台、麻扎巴格烽火台等,参见张安福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0-308页。都体现了该条道路的昔日繁华。及至清代,这条道路依然发挥着连通东西的作用,根据诸守捉方位的判断,从焉耆至安西都护府的道路与清代的驿路基本一致,(55)孟凡人 《北庭和高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629页;王启明 《天山廊道:清代天山道路交通与驿传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4页。足见这条路线在天山南麓交通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要发挥作用,也需要社会主义民主过程各环节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关系就决定了各民主党派既不等同于党委政府,也不完全是对民意的机械反映。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不仅仅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只起到桥梁、纽带、联系群众的作用,而且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催化剂,起着“化合作用”,是民主过程。虽然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政治结构中的议会制度,但各民主党派具有批评监督、协商、表达整合等政治功能,也遵循民主运行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民主的运行也正是基于民主党派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才得以实现。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具有政治功能,民主党派才不同于政治协商中的一般社会界别,而称作“政治界”。
四、焉耆的南北交通
焉耆不仅东西交通发达,而且南北交通尤其是从焉耆进出天山内部廊道(56)天山廊道,是指依托天山山体的东西道路、跨越山体的南北道路或者以山间盆地、河流为依托的东西和南北交错的道路。天山廊道内部道路,是指依托天山内部的山间盆地、河流、湖泊等为依托的经行山间内部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汉唐时期早已出现,但多是游牧民族所利用,即使在唐代时期,也主要是阿史那舍尔、契苾何力等带领军队攻伐龟兹等战争中经行该条道路,而中原军队极少使用,相对缺乏记载。直到清代控制了天山廊道后,才被时人所认知,徐松在《西域水道记》载:这条道路从东部的哈密可以一直行进到伊宁。地当西域东西之中。东达阿拉癸山,西接伊犁空格斯河源。“准部未靖时,自哈密至伊犁者,恒取道于兹。”([清]徐松撰,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5页。)相关“天山廊道”的内容,见张安福《天山廊道军镇遗存与唐代西域边防》,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绪论”部分。的道路也较为重要,但是目前学界对其鲜有研究。焉耆地处山间盆地,其地以北溯乌拉斯台河沿“庭焉道”(57)孟凡人 《丝绸之路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经轮台可与北庭取得联系,溯开都河则可进入尤尔都斯盆地,这里是游牧势力进出天山的隘口。如果控扼天山内部廊道,西北可到达弓月城和碎叶,南部以“大碛路”为依托,沿用孔雀河沿线防御带,则可将阿尔金山北麓的石城镇、播仙镇等与焉耆镇守军的防御体系连接起来,使得焉耆成为天山廊道交通的十字路口。
1.通往天山内部廊道的道路
天山内部廊道为史籍所不载,最早为天山以北的游牧部族占据并广泛使用。自汉以来中原军队进入西域的路线则较少使用天山内部廊道。唐朝经营西域时,以天山南北的军防布局为战略依托,因此天山内部廊道成为焉耆交通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焉耆北部的“庭焉道”是天山内部廊道的东段部分,是指从庭州西南经轮台到焉耆的道路,具体路线为从今北庭故城西南经乌拉泊古城,南越胜利达坂经巴仑台至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庭焉道”最初为西突厥诸部频繁使用,连接西突厥南、北庭的交通要道,《旧唐书·突厥传》载“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58)[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卷194《突厥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7页。。隋时,在天山南北两路有北道和中道,裴矩《西域图记》所载“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59)[唐]魏徵等 《隋书》卷67《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1580页。,唐初西行求法的玄奘,最初选择从北道“取可汗浮图过”(60)[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8页。,即裴矩所载的“北道”,很可能就是从今巴里坤至乌鲁木齐一带,再向南翻越天山达坂进入尤尔都斯盆地西突厥可汗庭,从天山内部西出伊塞克湖前往中亚的道路,(61)芮传明《〈西域图记〉中的“北道”考》,《铁道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庭焉道”正是其必经之路。
第一,防御处月、处密部落的交通道路
在唐朝势力未进入西域之前,天山以北诸部落就通过天山峡谷道路侵扰绿洲诸国,其中分布在今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的西突厥处月、处密部落,(62)[日]松田寿男,陈俊谋泽《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8页;又岑仲勉认为,处月处密相互位置为南北而不是东西而言,处月部在额林哈毕尔噶之南,即今沙湾、乌苏一带,处密在今塔城县东南,额尔齐斯河之西南(岑仲勉 《处月处密所在部地考》,《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1页)与高昌、焉耆交集频繁。《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贞观)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6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01-5302页。西突厥处月、处密部落出兵进攻焉耆的道路有两条:一条可经白水涧道至高昌,两军会合经银山道出击焉耆;二为自轮台地区沿乌鲁木齐河谷而上即沿“庭焉道”直达焉耆北境,高昌军队自银山道出,两军对焉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从处月、处密部落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64)从阿拉沟口进出天山内部廊道是处月、处密部落入侵西州的行军路线之一,可参见刘安志 《读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其相关文书》,《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58-67页。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发动昆丘道行军伐龟兹,天山北麓的处月、处密部落为其主要目标之一。(65)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第315页。时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及副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清河郡公杨弘礼等分南北两道讨伐龟兹,充分利用了“庭焉道”的交通优势。时阿史那社尔出兵天山北麓,“既破西蕃处月、处密,乃进师趋其北境,出其不意。西突厥所署(属)焉耆王弃城而遁,社尔遣轻骑擒之,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而走。社尔进屯碛石,去其都城三百里……”(66)[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72页。阿史那社尔的进军路线应为自庭州沿碎叶道向西破西突厥处月、处密部,而后在今乌鲁木齐一带越天山胜利达坂经巴仑台南下直达焉耆,即“趋其北境”,并向西追击擒焉耆王,屯龟兹以东三百里处。
天山内部廊道也是唐朝三次讨伐阿史那贺鲁重要的行军路线,“庭焉道”在这三次战役“弓月道行军”“葱山道行军”和“伊丽道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弓月道行军。永徽元年(650),阿史那贺鲁起兵叛唐,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次年,“诏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6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二年”,第6387页。。唐军在攻伐阿史那贺鲁时,追随阿史那贺鲁的处月部首领朱邪孤注率兵驻守牢山(新疆阿拉沟)(68)吴玉贵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0-341页;又,松田寿男将“牢山”比定为博格达山,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01页。,挡住了唐军前往伊犁河追击阿史那贺鲁的通道,而处月部南下阿拉沟最便捷的行军路线无疑是“庭焉道”,即翻越胜利达坂至乌拉斯台,向东便可到达阿拉沟。根据史料的记载,永徽三年(652)正月,契苾何力追击朱邪孤注五百里将其擒杀,途中俘虏了处密部落的时健俟斤、合支贺等渠帅六十余人,斩首五千余级。因此,朱邪孤注被斩杀的地方应为处月以西的某个地方,(69)[日]松田寿男,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01页。或为处密所在地即今玛纳斯,由此可以推测,契苾何力追击朱邪孤注的路线应为从阿拉沟口西向到达焉耆北部,取“庭焉道”到达天山以北,再西行经处密部落,这是朱邪孤注遁逃最有可能选择的道路,也是其部落较为熟知的路线之一。
葱山道行军。永徽六年(655),唐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伊州都督苏海政等,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程知节“与哥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7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元年,第6413页。榆慕谷具体位置不可考,大概为今自奇台县至吉木萨尔一带,可以发现,程知节自天山以北出兵,击败了葛逻禄、处月二部,率兵到达鹰娑川,即开都河上游地区。而此次行军没有提及位于玛纳斯一带的处密部,可以推测,程知节并未沿天山北路继续西行,很有可能取“庭焉道”转而南下进军鹰娑川,即从今乌鲁木齐翻越天山进入焉耆北部巴仑台一带,而后溯开都河西行,进入尤尔都斯盆地,挺进西突厥的腹心,遭遇了游牧在尤尔都斯盆地的鼠尼施部落两万余骑的攻击,但被苏定方击破。唐灭阿史那贺鲁后,以活动于尤尔都斯的西突厥鼠尼施处半部置鹰娑都督府,唐朝的充分重视更促进了天山内部廊道交通的发展。
伊丽道行军。显庆二年(657),唐朝开始了对阿史那贺鲁的第三次讨伐。苏定方任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出北道,“自金山之北,指处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嫩独禄以众万余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进至突骑施部”(7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第2778页。;南道为流沙道安抚大使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以及阿史那步真的行军。苏定方率军“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7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突厥传》,第6062页。,且根据史料的记载,可以认为,伊丽道行军的南道流沙道行军很有可能是从西州出发,且根据第一次弓月道行军时被朱邪孤注扼守阿拉沟口而无法前行的战略教训,阿史那弥射行军很可能正是从阿拉沟口进入天山,西行达乌拉斯台,继而沿“庭焉道”达到乌鲁木齐,逐次击破处月、处密部落,再西行至双河,即今博乐市达勒特古城与苏定方会合。伊丽道行军在唐朝征伐阿史那贺鲁、统治西域的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连通天山南北的“庭焉道”则在此次行军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输送和战略联防的作用。
第三,对抗突骑施的军事防线
公元7世纪末,逐渐强盛的突骑施成为西天山最大的隐患,连接西天山、扼守天山内部廊道隘口的焉耆成为防御突骑施部落南下的重要屏障。景龙二年(708),同时兼领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伊西节度使的阿史那献以焉耆作为对抗突骑施的战略基地,这里向北可经轮台连接北庭,西向连接安西都护府,交通极为便捷。开元三年(715),阿史那献任定远道行军大总管,“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五月,壬辰,敕汤嘉惠等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远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7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译《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三年”,第6829页。体现出唐朝对焉耆连接北庭、安西形成掎角之势的战略布防,在抗击默啜的战斗中,唐朝充分利用焉耆的地理交通优势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开元七年,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7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西域传》,第6230页。。十姓可汗阿史那献请居碎叶,汤嘉惠请以焉耆备四镇,阿史那献势力的转移涉及西域形势使得焉耆镇发生了变动,阿史那献居碎叶,对于突骑施、大食甚至后突厥的西侵都有着重大震慑作用。汤嘉惠以焉耆备四镇,正是出于对焉耆交通发达,可策应安西、北庭的考量。
总体来讲,在唐朝数次针对天山以北诸游牧部落的用兵过程中,“庭焉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朝先后在从焉耆进入天山腹部的道路沿途设置了大量防御工事来保障内部廊道的安全。根据目前的遗址分布来看,如科克苏门遗址、哈尔莫墩城址、肖霍尔城址、墩墩尔城址、灰日克古城、协比乃尔布呼古城、查汗通古东西烽火台以及哈布其哈沟口遗址等,都是扼守从天山南下进出焉耆的交通隘口的军事防御建置。
“庭焉道”稳定的交通体系一直沿用至安史之乱后,时河西路断,从西域通往中原需借“回鹘道”,唐代高僧悟空从天竺返回时,“次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延留三月。从此又发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洎贞元五年(789)己巳之岁九月十三日,与本道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75)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悟空一行人正是取“庭焉道”翻越天山,由庭州借道回鹘前往中原。
2.与焉耆南部地区的联动
焉耆与塔里木南部地区的联动,实际上是与唐朝在南道最大的绿洲设置的于阗镇守军取得联系,于阗的地位仅次于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76)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第56-64页。。这条道路从焉耆取“大碛路”,进入罗布泊地区,“……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脩(循)城也。又西(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77)[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43《地理七》,第1151页。这条纵贯南北的道路将焉耆与于阗连接起来,在塔里木盆地东缘形成对安西四镇的防御圈。
然则值得重视的是,塔里木东南与青海道接壤,也是吐蕃经阿尔金山进入塔里木的主线,而唐朝以焉耆联动于阗所形成的交通防线,见证了唐蕃在此地反复争夺的历史,客观上反映了从焉耆到于阗交通的重要性。
其中,萨毗城是吐蕃在塔里木南道的经营重点和交通要地。《寿昌县地境》载:“萨毗城,在镇城东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置筑,近萨毗城泽险,恒有吐蓍土谷贼往来。”(78)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2页。《沙州图经》亦载:“(前缺)其城康艳典造,近萨毗泽□六十里,山险,恒有吐蕃吐(后缺)”(79)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3页。萨毗泽即今若羌县阿牙克库木湖,地置进出阿尔金山的交通孔道,这也是吐蕃、吐谷浑由柴达木盆地进入若羌之后避开石城镇直取萨毗城并由此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捷径。米兰出土的M.I.xxviii.0036文书载:
由论·措热和论·塔热在季冬月之……日盖印发出。信使(Ring-lugs)和力夫董真(Vdong-phreng)和突古(Vdor-dgu,或许同于Dor-dgu……),护卫……必须紧跟一批流放犯,即上部牧区部落的穆杰波和信使部落的彭·拉古,除了萨毗之小罗布(Tshal-byivi Nob-chungu)以外,此二人可以到任何地方,甚至远到瓜州、姑臧等地……(80)[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4页。
吐蕃对“萨毗”向外的交通路线极为重视,可以看出,信使二人所走的路线横贯小罗布到瓜州,他们即使放弃沿着沙漠边缘途经鄯善的道路,也有山路可供选择。这里地处唐朝设置的焉耆—于阗交通防线以外,是唐代塔里木以安西四镇为中心的严密的交通布局中东南部唯一的缺口,是吐蕃进入塔里木的通道,吐蕃一度在此屯田布兵,最终发展成为与唐朝争夺塔里木的前方基地。
综上,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书体现了唐代“大碛路”的畅通情况,客观上反映了焉耆在安西四镇交通中的枢纽作用。焉耆不仅连接西州与龟兹,而且对于北部经乌拉斯台河进入天山内部廊道连接轮台、北庭、尤尔都斯盆地的道路也极为重视,使得焉耆也成为天山南北军防的交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