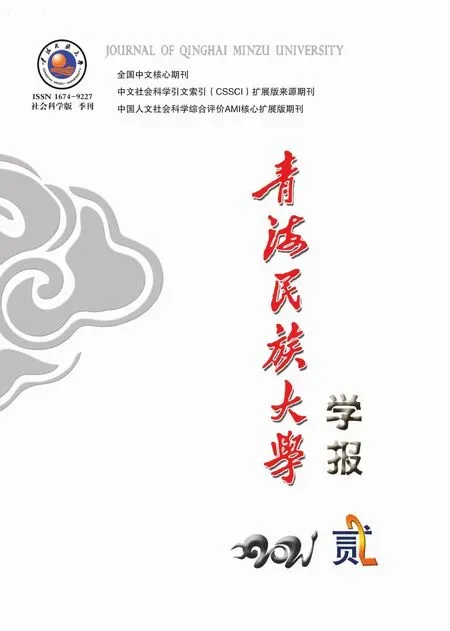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与反思
——基于内蒙古牧区田野调查的研究
武 宁 王 娅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将其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定义,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目前公共文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公共管理领域,更侧重供给模式、服务标准、服务效能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公共文化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例如教育、科技、卫生、法律等,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柔性”的特征,在实践过程中受具体环境以及服务对象影响较大。因此,加强公共文化制度运行科学化水平,要提高公共文化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反思能力,结合本土历史文化传统、民间组织运行状况,对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人们的“实践智慧”进行把握。
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均等化的要求,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短板。目前牧区的公共文化制度安排,与城市及农村地区相差不大,基本上是依靠“三馆一站”(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综合文化站)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然而,牧区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活方式有其特殊性,这造成了无差别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同牧区生活实践之间的冲突,由此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现带来挑战。正如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所言,即便在法律和市场经济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方社会,正式规则也只是对人们社会选择施加约束很小的一部分,而社会文化传统中包括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习惯等非正式约束对行动者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1]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组织的制度形式和组织程序是并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行动者(rational-actor)模 式 的 独 立 变 量(independent variable),需要从文化与认知层面给与解释。[2]笔者通过对内蒙古锡林郭勒、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等多个盟、市的田野调查发现,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遇到的困境反而创造了一个契机,使刚性的制度设计与本土社会文化相调适;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一些“权宜之计”,可以为我们改进当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为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
二、公共文化服务困境与牧区社会的实践逻辑
根据对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的调查,公共文化活动主办方多是基层文化站、文化室。演出主体分为两类,一是政府通过补贴规定“送文化下乡”任务的艺术团体,如旗县乌兰牧骑;二是当地的业余文艺团队或文艺爱好者。牧民主动参与度不高,活动主办方也缺乏主动性。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基层公共文化部门疲于应对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如做好台账应付考核和检查,搞好宣传工作,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及牧民的需求的考虑反在其次。这使得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缺乏沟通,导致一厢情愿的服务。例如内蒙古某旗文化馆,上级单位规定一年几百场的电影放映任务,但因该地位于戈壁地带,沙尘暴多发,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放映。嘎查(行政村)有定居点,但真正长期在此居住的往往仅有少数几户人。放映队不得不逐户联系牧民,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动用个人关系,央求牧民“给面子”观看放映。再如“草原书屋”,设在嘎查文化室,而多数牧民居住地离嘎查近则十几里,远则几十里,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文化室借书。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发展,年轻一代牧民受教育水平提高,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品位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目前大多数文艺表演内容和表现形式雷同,鲜有反映牧民当前社会生活的内容,难以吸引牧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关注。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市场化,基层牧区缺乏区位优势,牧区公共文化资源匮乏、人才流失严重,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难以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与地方社会实践存在脱节的现象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牧区十分普遍。一些研究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和提供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地方文化理解缺乏“整体性”和“动态性”的视角,将地方文化本质化、符号化。这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地方文化被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分割,导致文化发展丧失活力和可持续性;[3]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与当地社会需求产生错位,无法满足百姓需求,同时造成大量资源浪费[4],等等。
将制度的表层设计与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当中的实践倾向相割裂,就会把“标准化”等同于“同质化”,将“均等化”理解为“平均化”,造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这一谬误在于“把人们为解释实践而构成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5]也就是说用制度的框架捕捉、切割现实的社会行为。布迪厄在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许多本地概念在实际使用中的模糊性,而实践逻辑既包含一致性和规则性,又具有模糊性和无规则性。[6]基层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牧区,在社会生活实践的空间与时间维度上,以及参与者的身份构成上,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给制度化规则的实际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时间的模糊性
牧民的生活时间是由生态时间决定的,生态时间包括季节变迁、草的长势、水资源的情况,而草原的季节变化、气候变化、水草的状况,都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如接牛犊一般在2-5月份,但有时可以晚至6月份。8月份是打草的季节,但具体时间要根据草的长势而定。牧业生产的特点也决定了牧民的作息时间是弹性的,如春天是接羊羔的季节,母羊随时都可能下羔,这时牧民就得不分昼夜地看守。牧民一天的时间安排有一定的节律,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早晨6点起来,把骆驼赶出去,回来以后拣驼粪到10点钟。这时候骆驼陆续回来就开始饮骆驼。骆驼不是集中来的,一会儿来一个,一回儿来一个,我就一直守着。现在都是抽水机,不用像过去一样用水车推,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压水,省事多了。中午喝点奶茶,下午四五点羊回来了,又得饮羊。饮完羊,把羊关进圈里,就回家做饭。有时候羊圈需要清理,有点空就削削鼻棍,抽水机、电动机坏了,也得自己修理,没有闲的时间。(阿拉善右旗牧民乌恩巴雅尔访谈)
在牧民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的节假日或工作日,用牧民的话说,“你放假了,牛羊不放假”。所谓的休闲时光,往往是在放牧羊群,饮马、饮骆驼间歇时刻放歌一曲,与路过的牧民闲聊。牧民的社会生活往往有多重时间组成的节律,例如根据农作物、牲畜生长计算的生产循环时间,有通过个人生死及家庭生活再现的人生时间,以及仪式中用物物交换表现的交换时间等等。[7]在蒙古族牧区,遵循日历时间的制度安排与建立在自然韵律之上的生产、生活时间必然产生冲突,在紧凑而多变的日常生活中很难为文化生活开辟专门的时间。
(二)空间的模糊性
“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北方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需要牧民不断地迁徙才能保持草原生态的平衡。历史上,北方草原牧场长期以来是公有开放的,蒙古族牧民活动的范围非常广阔。牧民传统的游牧有三季牧场、四季牧场。而在20世纪20年代,游牧的距离远到外蒙古、俄罗斯等地。集体化时代当地牧民仍然进行营地化的通场移牧,根据地形、植被、水源和气候条件,把放牧地分成几个地段,按季节通入或倒出。近年来,长距离游牧和四季转场虽几近消失,但大部分牧民仍根据地形差异和草场长势在自家牧场不同地点设置冬营盘和夏营盘,根据季节变化选择放牧地点。
城市中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布局,有城市规划的科学理论依据可循,但牧区的空间安排有其特定的逻辑,牧民生产生活的流动性使得草原空间很难按照固定标准划分为条条块块。[8]他们灵活地与周边环境发生互动。例如在阿拉善右旗,当地修路取土的土坑,因降雨的累积形成一个水潭,被一位牧民当作饮骆驼的水槽加以利用。这种因势利导,灵活运用环境的做法在牧区非常普遍。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苏木政府所在地,只有在地方干部选举、政策宣传时才能将牧民聚集起来。四子王旗靠近中蒙边境的脑木更苏木,南北纵贯一百多公里,许多牧民从家到苏木政府,都要驱车一个小时左右。因此,地理位置上的行政中心无法成为文化中心。在为牧民提供文化娱乐和集会社交方面,牧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很难发挥和城市相同的作用。
(三)个体身份的模糊性
受到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蒙古族牧民居住一般都很分散,与外界联系相对较少。传统牧区社会分工不够明显,大多自给自足,在生产生活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便一些具有专业技艺的人,如鞣皮匠、木匠、铁匠、阉畜手、兽医等等,依然不能完全脱离放牧而生存。虽然在家庭中男女老幼有基本的内部分工,但由于畜牧业突发情况多,有些季节性劳动需要家人相互协助才能完成。相应的,牧民对身份的认知,受专业分工和行政等级的影响较不明显。牧民往往承担着多重身份,他们既是放牧者,同时也可能是兽医、皮匠、裁缝、蒙古包建筑师、长调民歌歌手,有时在祭敖包、祭骆驼等活动中还要担当喇嘛的角色。这种分工的不明确和角色的多样性使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身份对牧民进行标识。当地的干部,如嘎查长、支部书记,往往也拥有草场并经营畜牧业。
模糊的身份定位使得文化活动与文化产品的价值很难用专业的标准加以衡量。阿拉善右旗一位叫孟和吉日格勒的牧民,以放牧为生,禁牧后他被安置在苏木所在地定居,平时承揽一些小型的建筑工程。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作家与民间学者,不定期举办诗歌会并一直从事阿拉善骆驼文化的研究。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图书馆,牧民自费出版的图书和民歌专辑就有180多种,内容涉及民族风情、蒙医蒙药等多个领域。当地盟委宣传部的干部解释说:“在今天的草原上,牧民自费出书和录制民歌专辑已不甚新奇,互赠自己的著作和专辑是牧民们礼尚往来的流行时尚。”牧民在公共服务需求及其表达方式上有其特殊性,[9]写诗、出书对牧民来说并非专业性的文字工作或者有意识的附庸风雅,并不看作是“打破常规”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延续。
由此可见,在蒙古族牧区,歌舞、文学等现象并不能够简单地划归到外在的“文化”领域,而是“嵌入”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对同一文化现象的官方与民间表述往往具有二重性。[10]与此同时,我们在文化供给与需求主体之间,很难划分出明确的界限。形式上无差别的公共文化服务,在不同接受主体的感知当中,其价值差异非常明显,这给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带来挑战。
三、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成功案例
牧区生活实践的特质,使得我们参照公共文化一般的定义和逻辑对当地文化活动进行解释时遇到了困难。目前公共文化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适应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在牧区动态、模糊的社会环境中难以有效运作。当然,笔者通过在牧区的田野调查也发现一些成功案例,并借此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作的有效机制。
(一)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1957年诞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当时自治区的文化部门经过认真调查,认为:“鉴于牧区、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和居民点极其分散的种种特点,要使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建队之初,队伍中几乎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例如报幕员兼歌手、舞蹈演员兼乐器演奏员。他们同时还辅导培训农牧区文艺骨干, 向牧民宣政策、法规、卫生常识、养畜知识和致富经验。在演出前后,他们还分别担当图片展览讲解员、售书员、业余文艺辅导员、摄影员、播音员、理发员等。一位老乌兰牧骑队员回忆说:
“我们当时边演边走,遇到定居点或者放牧点就停下来,来不及搭帐篷,就在风沙中化妆,没有电灯就点汽灯。台上演完,又到蒙古包内为不能出门的老弱病残演出。”
参加或运用民族民间固有的集会、节日开展文化活动,是乌兰牧骑采用的又一经常性的活动形式。根据牧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在各个季节里,都有一些固定的节日和集会,如那达慕、奈日、敖包会等。乌兰牧骑在这些活动中不但要送上自己的演出,还要辅导牧民进行演出,组织牧民业余团队。在20世纪50-60年代,乌兰牧骑的足迹已经遍及内蒙古牧区。原科右前旗乌兰牧骑队员金玉鸽回忆道:
“1965年8月,我参加了科右前旗的乌兰牧骑,加入乌兰牧骑后的第三天,我就随队下乡了。当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经常是坐马车或勒勒车。到达一个演出地点,卸车后分头为当地农牧民服务:打扫院子、打水、理发、办图书展览……紧接着就投入到晚间演出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无论条件好坏,观众多少,我们都得努力把一场节目演下来。1965年10 月,我被选派到呼伦贝尔盟卫生学校参加东四盟乌兰牧骑卫生员培训班。从那以后,我又增加了一个身份,成了一名业余赤脚医生和接生员。”
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乌兰牧骑队员把自己深度融合在牧民的生活中。扎鲁特旗乌兰牧骑老队员回忆,每到一地, 队员们都分散住在牧民家里, 一进门便放下携带的物品, 打扫院子、挑水、挖菜、做饭、圈牲畜、挤牛奶, 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在参加集体劳动方面, 他们采取了到地边、下牧场, 边劳动边演出的办法。由于深度融入牧民生活中,他们的编创、表演高度贴近牧民生活,文化工作者与牧民在创作灵感和文化生活之间实现了互惠。同时,这也使得一个由官方建构出来的基层组织在其并不久远的历史过程中沉淀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受人才市场化和牧区人口空心化的影响,让今天的乌兰牧骑像过去一样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已不大现实,但其适应牧区社会的“综合服务”理念仍应得以保留。乌兰牧骑依然可在法治、医疗、政策推广、社会服务等方面作为官方与民间社会衔接的纽带发挥重要作用。
(二)乌审旗“文化独贵龙”
“文化独贵龙”是以文化户、民间艺人、文化能人为主体,群众自发建立、自我管理、广泛参与、自娱自乐的组织。[11]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随着地方经济的繁荣,牧民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便凸显出来。当地一批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艺术特长的牧民以自己的居住地为中心,自发地组织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吸引周边的牧户参加,有的是以马头琴、长调为特色,有的是以蒙古服饰制作为特色,还有的牧民自办图书室。当地的政府文化部门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认为这是一支有活力的文化力量,决定将其纳入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建构中。
乌审旗历史上曾发生过影响深远的“独贵龙”运动,“独贵龙”在蒙古语中是很多圆圈的意思,历史上的“独贵龙”是蒙古族人民发起的一种反封建斗争形式。参加者围成圆圈,商讨各项问题,最终通过决议上报政府,其呈文签名也呈圆圈形。而星罗棋布的牧民文化户也恰如一个个文化圈子。于是政府文化部门就以“文化独贵龙”这个有地方特色的称谓为这些文化牧户命名。这种形式也与民间文化共同参与、平等交流的精神较为契合。
2006年,乌审旗启动了“文化独贵龙”建设工作,按照地方文化部门的设想是“以文化户、民间艺人、文化能人为主体,以带动农牧民开展文体活动,提高农牧民综合素质为主要任务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间组织。”在现有的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独贵龙这个民间文化组织,牧区公共文化服务半径得到了延伸。为激励和扶持文化独贵龙,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制定出台了文化独贵龙建设标准和扶持办法,按照每个文化独贵龙的种类、规模、活动次数和影响力,每年给予一定的补贴。
文化户作为一种民间公共文化组织,在牧区以及农村地区并不稀奇。但以“独贵龙”命名,却能够传达出一种基层社会自组织的特性。这恰与当下“社会治理”的理念有某种契合,①使得一个在汉语语境中有着丰富内涵的政治术语在蒙古族牧区获得了承载的媒介。“独贵龙”的命名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有意或无意策划的“产品”(“文化独贵龙”命名时社会治理概念在官方与学术界尚未普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地方历史文化自我呈现的必然结果。
(三)额济纳旗民间文艺协会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各种民间文化协会非常活跃,基层文化单位通过与民间协会合作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目前额济纳旗注册的文化类协会有12个,同时还存在众多的社区小型协会。当地文化馆为这一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搭建平台,提供业务的规范、指导和经济上的扶持。
另一方面,通过民间协会开展公共文化活动也是形势所迫。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站归属于乡镇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站的人员编制归属苏木政府,由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安排,而地方文化馆对此无法插手。文化站曾经由文广局管理,但归属综合服务中心以后,苏木的文化站站长往往是挂名的,主要人员实际上由苏木的司机、兽医等人员构成。这些人员在文化工作方面缺乏专业性,工作事务与文化服务关联性不大。因此,对文化馆来说,面向乡镇苏木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针对这一情况,文化馆面向乡镇苏木以下开展活动,主要依靠民间协会。协会当中人员众多,参与积极主动。开展活动时,可与文化馆相互配合。文化馆先把活动通知下发给协会,协会又把通知转发给每一个会员,很快就能行动起来。为了照顾到全旗各个苏木镇,文化馆有意引导协会在各个苏木、乡镇发展会员,特别是一些骨干会员。
从2015年开始,额济纳旗文化局每年拿出一定款项,对文化协会进行补贴,尽管补贴金额有限,但调动了协会积极性。文化馆作为业务指导单位,有了这项补贴,就有资格对协会提出一些要求。协会参加文化馆组织的活动,文化馆派出业务人员对其进行全程辅导,还为他们的演出免费提供服装。文化馆要求每个协会每年至少要参加三次全旗性的文化活动。旗政府根据年底的考核情况发放这笔补贴。协会给会员下发通知,对报送作品提出要求,征集作品。征集到作品以后交给文化馆,文化馆负责筛选、冲洗制作,提供展出场地,组织评比等等。民间文化协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原本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采取的权宜之计,基层文化管理者却抓住这一机会,由直接的管理与服务转变为间接的发现、引导与扶持,反而激发了牧民文化参与的热情与创造力。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公共文化服务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按照牧民的实际需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第二,不局限于专业分工,一专多能,提供综合性服务;第三,官方和民间力量良性互动,在刚性的制度设计与多变的社会实践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它们突破了政府公共文化供给的刚性思维,打破了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界限、引导基层社会以自组织的方式填充制度与实践之间的模糊地带。
从形式上看,这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源于对制度的变通与调整,也有一以贯之的文化脉络。乌兰牧骑的流动服务实际上继承了过去草原上如哈扎布等民间艺术家的流浪艺人精神;“独贵龙”是乌审旗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而额济纳旗的文化协会则是长期活跃在草原上的民间力量。这些成功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式在实践中与牧区社会不断磨合:乌兰牧骑作为一个官方建立的文化工作队,融入牧区社会,却没有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文化独贵龙”和民间协会在基层文化馆的指导下不断制度化,却依然保留活力与创造力。而与地方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制度安排很难发挥实际作用。如图1所示,合乎实践理性的制度,不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设计,而是上下互构、当下需求与文化传统耦合的结果。在上述成功的案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策略展开探索。

图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践当中的上下互构示意图
四、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策略
基层社会组织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脉络,它们“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总是‘合情合理’的”。[12]牧区文化组织(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一些社会组织)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其制度上的模糊性以及实践当中的灵活性。这表现在正反两方面:为满足民众现实需求,基层工作人员需要在不逾越身份与制度边界的同时能够“有组织地即兴发挥”;[13]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看似制度化的行为,却很难用固定的条文加以规范,这些行为是介于制度与习俗之间,内化于基层干部、文化工作者以及普通牧民之中的某种“性情倾向”。[14]这些行为的过程和意义具有动态特征,但并非难以捕捉。如何把握牧区社会运行脉络,将这一模糊地带纳入制度运行的范围之内,是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有效供给的关键所在。
(一)流动服务
因牧民生活实际,阵地设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流动服务是必然的替代选择。白维军在其研究中提到了以“草原110”和流动科技馆为代表的流动性公共服务,[15]类似的模式可以延伸到公共文化领域。当然,流动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上文的案例已经说明,基层电影放映队虽然也具有流动性,但其形式上的流动性与牧区生活节律并不合拍。流动并非机械性地跨区域执行任务,而是像候鸟一样随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变化而迁移。流动服务的理念与设计想要在牧区真正落实,需要基层文化工作者熟稔地方社会生活的时空脉络,一些节日庆典、仪式活动,如那达慕、祭敖包等都可以作为参照。如文化工作者自身在牧区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婚礼、寿宴等偶发事件则会为流动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因此,在牧区公共文化人才培养与选拔的过程中,除了提高专业技能之外,更应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多元主体支持[16]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流动性的动力。
(二)数字服务
数字服务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已有所实践。[17]考虑到内蒙古全区互联网只能覆盖大部分城镇,偏远的牧区无法覆盖,基层牧民无法享受数字文化服务,内蒙古一些地区开始尝试“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设计者在原有文化共享工程网络设施和服务的基础上,在乡镇、苏木设一级“数字加油站”,在村、嘎查设二级“数字加油站”,在游牧点设移动便携式“加油站”,为偏远地区的牧民提供全天候的数字文化服务。牧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把他们对数字资源的需求通过“辅导员”“加油员”“专管员”一层层集中报送到自治区分中心,分中心根据牧民的“订阅”,安排资源直接通过网络传输给需要的人。类似“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的公共文化服务,其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数字服务的形式还需要有合适的内容给予支撑。但无论其未来发展如何,数字平台本身就可以为文化工作者与基层牧民的交流提供便利,而两者之间高度的互动性与社会网络的重合性正是上文提到的有效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成功原因之一。
(三)综合性服务
由于牧区居住地分散、交通不便,单一的服务不但不能满足牧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且成本过高。普通牧民在繁忙的牧业生产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欣赏一些文艺表演,近乎奢侈。对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来说,单一化服务的吸引力不够,起不到应有的效益,推行起来也困难重重。因此,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性与多样性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例如,结合牧民生活实际的农牧业科技知识普及、政策咨询、法律咨询、文艺活动的辅导、电脑与卫星天线修理等等。这种方式满足了牧民多方面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主体可以借助公共文化平台落实政策及开展项目。一方面可以使牧区公共文化建设从多方获取资源,同时也减少了公共文化软硬件设施投入产生的“沉没成本”。
(四)适合牧区特点的社会参与机制
牧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而且需要牧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在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不仅要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建设牧民参与文化活动的平台和载体,通过一种参与机制的建立,调动起牧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一些相关研究也指出,公共文化参与者来去自由,人数不固定,时间有弹性,单纯依靠全职工作人员的服务会很不经济,因此调动志愿者一类的民间力量是较好的途径。[18]上文提到的“文化独贵龙”,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延伸,上接文化站、文化室,下衔文化户;弥补文化站服务距离不足,文化户实力单薄、能力有限等问题;调动各方力量、连接不同功能,从而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额济纳旗通过协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也充分调动了民间力量,激发了牧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也在制度规范与实践的灵活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公共文化制度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制度本身各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还要看这种制度在特定时空当中运行的节律,也就是说它如何被当地人“身体力行”。正如传统牧民与其牧养牲畜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样,制度、规范以及民间组织的实践在牧区往往以一种动态的、模糊的形式呈现。内蒙古牧区面临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在公共服务需求及其表达方式上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既注重“公共”性,也不能偏废“文化”性,在把握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能力。
注释:
①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转型社会:公共服务与治理机制”论坛中提出,检验社会治理的“成色”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多元主体(治理的起点),二是自愿合作(治理的过程),三是各得其所(治理的结果)。“文化独贵龙”无论字面含义还是组织方式都体现出“社会治理”在这三个层面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