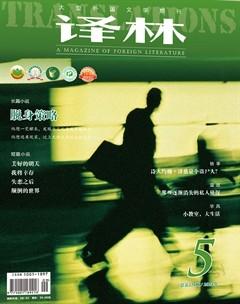颠倒的世界
〔英国〕赫·欧·贝茨

奥利弗·斯特拉顿小姐初次套上两只不同颜色的长袜——一只棕色带绿,另一只锈红色——纯系偶然,因为当时她是在冬天朦胧晨光中仓促着装。但等到天色亮到能看清物体时,她才蓦然发现,这双颜色不一的长筒袜醒目甚至抢眼到何等离奇的地步。它们或能成为一个理由,她想,促使男人越发频繁、仔细,或许赏识有加地打量自己的两条腿。她的腿不太好看,但凡能多做点什么令其改观,心里便觉得好受些。
她的脸酷似一块相当粗糙的淡黄色法兰绒布料,毫无姿色。灰色的眼睛阴森森的,仿佛下面多了两块瘀斑。为此她戴了副烟熏玫瑰红的浅色眼镜。她的黑发也很粗糙,有可能微微泛灰,若非定期染色的话。
有了关于长筒袜的发现之后,她每天早晨上班都穿着两只颜色各异的长筒袜。她有时选择蓝色和绿色,有时选择红色与黄色,一次是紫色和棕色。有一回,她甚至别出心裁地一边穿绿袜红鞋,另一边穿红袜绿鞋;另一回,一个遍地黑色雪泥的早晨,她套着一双奇异的、高到腿肚的皮靴,一只白一只黑,手套也是一黑一白,只是与皮靴形成黑与白及白与黑的反向搭配。
尽管使出了这些招数,却似乎从未如其所愿,让男人对她的两条腿稍加注视。她的腿继续制造一种既不雅观又难撩人的表象。男人在街上只是打她身旁走过,仿佛她是某个另类的女人。此种情形持续了几周,直到一个阴雨苦寒的早晨,她赶火车迟了一步,发现二等座已满,只得改乘头等座。
车厢里仅有的另一名乘客,是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子,她即刻察觉到他也是仓促着装。他那条蓝领带,一半掖在衬衫领子里,一半露在外面。这唤起了她内心一种渐渐增长的强烈愿望,不仅要对他告知实情,还得站起身替他理好领带,使之符合自己的意愿。
随着这种情绪的滋长,她不停地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复又放下,一只套着蓝袜的膝盖露出几分钟,而后一只绿色的膝盖露出一阵,与此同时,她始终试图读她的《泰晤士报》,却发现无法集中心思,遂将报纸放在身边的座位上。
大约过了一分钟,这男人咳了声,俯身向前,客客气气地说:“可否借你的《泰晤士报》一读?我没买到报纸。”
“噢!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你真是太好了。”
斯特拉顿小姐礼貌地笑了笑,将《泰晤士报》递过去。就在男人拿起报纸开始阅读前的一瞬间,她又瞥了一眼对方衣领下鼓起的蓝领带,觉得自己知道,保准知道,此人尚未成家。没有哪个女人,她断定,会让一个男人衣领和领带如此凌乱地走出家门。
她脑中转悠着这个念头,掂量自己是否敢于提及这条领带如何反常,同时望着窗外,注视着冬天灰黑萧索的景象掠过眼前,注视着乌云堆积的天空下一片片浸透雨水的田野。
等到她将视线重新转向男人时,面临的景象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起初她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亲眼所见。接着,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次拖长的瞥视后,她才确信自己没在做梦。
男人正在上下颠倒着读《泰晤士报》。
“领带嘛,”她暗忖,“我能理解。那不过是准备出门之时出了个小小的纰漏。跟我的袜子一样。谁都可能做出那样的事。但是倒着读报——绝不可能事出偶然。那绝不可能。”
她立即感到时间的紧迫,她必须对这种离奇的事态做点什么,于是倏地探身往前说:“哦!对不起。”
“唔?”
“我希望——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在倒着读《泰晤士报》。”
“没错,我知道。”
斯特拉顿小姐张大了嘴坐着,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没错,我知道。我喜欢这样读报。”
“你当真——你是说——可那不是挺麻烦的吗?”
“一点也不。我好多年都是这样做的。”
“可这不很费劲吗?顺着读岂不方便些?”
“这样读起来更有乐趣。再说我也习惯了。”他脸上掠过一丝羞涩的微笑,一种她认为很像松鼠的神态。“我打小就一直这样做。我特别迷恋代码之类的东西。你知道男孩子都怎么做——把一个个单词颠来倒去,省略字母,用X代表某个元音,Y代表另一个元音。我开始倒着写句子,当然这只不过是倒着阅读的第一步。”
斯特拉顿小姐再度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自己试试看。”男人把《泰晤士报》举到她面前,“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不过是集中精力的事。”
“噢!我想我不可能——”
“试试看。”
忽然斯特拉顿小姐意识到男人已坐在自己身边,他俩共同拿着上下颠倒的《泰晤士报》。
“試着读读标题。这一条。”
斯特拉顿小姐盯着报纸足有半分钟,两眼在烟熏玫瑰红的镜片后细细寻觅,像是初次尝试阅读的孩子。
“我根本弄不清它的头绪。它看上去像是俄文。”
“噢!它很好懂。它说美国在越南又损失了几架直升机。据报道越共伤亡惨重。”
“噢!是这样。我现在看出来了。我准是蠢极了。”
“一点也不,只是需要训练罢了。”男人继而发出短促的三声笑,斯特拉顿小姐觉得特别悦耳动听。她感到这笑声很有一股孩子气。“特别滑稽的是,你连续多年一直上下颠倒着阅读,一旦开始按正常顺序阅读,就会有种特别古怪的感觉。”
“是的,我估计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这完全是角度的问题。说到底,这世界本身恰恰是上下颠倒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斯特拉顿小姐也笑了,说她的确这么认为。
“知道吧,”他忽然继续说,“不过你第一个让我注意到自己在颠倒顺序阅读。每年都有几百号人在火车上看见我这样读报,但没人对我提过一个字。我猜他们要么是羞于提及,要么就是认为我疯了。你认为我疯了吗?”
“噢!一点也不。一点也不。”
“这不过是角度倒转的问题——”
“你能这样读数字吗?”
“哦!读数字,是的。我能从后往前相加等等——它是一种心算练习,知道吧。一项挑战。”
火车缓速行驶了五六分钟。男人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挂在一根细细的金链条上的怀表,瞅着它。
“早料到了。又是晚点。真是讨厌透顶,这条线。上星期每天我们都晚点十来分钟。”
“晚班火车更糟。”
“我知道。你乘的哪班车?六点十分的吗?”
是的。她总是乘六点十分的班车,斯特拉顿小姐说。其实她平素无一例外地乘五点二十的车。
“我寻思我以前从没跟你照过面,对吧?”他飞快地往下瞟了眼斯特拉顿小姐的两条腿,一如既往地裹着反常的长筒袜,一只绿色的,一只蓝色的。“只要遇见过,我保准想得起来。”
斯特拉顿小姐感到自己微微涨红了脸,一时无言以对。
“我通常乘五点二十的车,”他说,“可是情况完全乱了套。一场糟糕的喧闹茶会。”
“我想,我通常乘坐二等车,所以你没见过我。”
“啊!有可能,有可能。”
他又朝斯特拉顿小姐的长筒袜斜睨了一眼。在他看来,长筒袜一事之反常,实不亚于斯特拉顿小姐发现他上下颠倒着读《泰晤士报》。一个女人为什么穿着一双不配对的袜子去上班呢?太奇怪了。你尽可认为她疯了。
“我总是中途在马路对面的黑啤酒吧下车,在那儿喝杯雪利,”他说,“我让自个儿有那么一点闲暇。它有助于身心松弛。你大概不会介意,我想,今晚跟我共饮一杯吧?”
斯特拉顿小姐委实不知究竟是什么促使她即刻作答,她忽然说她真的不知道,此事完全取决于她的朋友。
“哦!我知道。”
斯特拉顿小姐当即编造出什么朋友,纯系情急慌乱的缘故,她此刻发现如何摆脱这位朋友反倒成了一道棘手难题。
“好吧,改到哪天晚上。顺便说一下,我叫弗莱彻。”
“你真是太好了,弗莱彻先生。我想我可以打个电话给朋友。”
“噢!可以吗?那太好了。这地方的雪利味道好极了。当然,你也可以喝点别的。一杯勃艮第葡萄酒。他们还有论杯卖的香槟。”
他说这番话的当儿,斯特拉顿小姐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估摸,”她说,“你不会哪次倒拿着杯子喝酒吧?”
“是个好主意。”弗莱彻先生说着,同样莫名其妙地忍不住笑出了声。
那天傍晚,在六点十分的火车上,斯特拉顿小姐闯进头等车厢的角落,面对弗莱彻先生,不禁涨红了脸,直喘粗气。他们此前得一路跑来赶上火车,手拿两大杯雪利——俗称雪利大杯,弗莱彻先生告诉她——她为此偶尔咯咯傻笑两声,一边还在努力平定喘息。
“唔,这事真够急的,”弗莱彻先生说,“不过,要是我们没赶上车,不就有理由再喝一大杯了?”
“嗨!那种大杯雪利,准有三杯的量。”
等到自己也终于呼吸匀畅了,弗莱彻先生瞄了一眼斯特拉顿小姐的两条腿,却发现另一种更有趣的意外之物在那儿候着他。午餐时分,在一阵放任无羁的仓促行动中,斯特拉顿小姐为自己配置了几只新长筒袜,此时两腿上套着的一只是鲜艳的紫莓玫瑰红,一只是柔和的紫罗兰色。它们反差很大,却搭配得当,她想。
弗莱彻先生被迫也这么想,只是过于害羞,既不敢朝它们多看几秒,也不敢如实说出心里的想法。
他的确想聊点别的什么,然而直到他将自己的晚报又读了半个钟头,才终于有胆量这么做。
“你可知道这个地方,泼兰德宅邸?”他说,“他们已经将它改建成几座公寓了。”
“不知道。”斯特拉顿小姐说,她认为自己不知道。
“它曾经是古老的布拉德菲尔德宅邸。宽大的维多利亚建筑,在维多利亚公园里。我搞到其中的一套公寓。哦!只是很小的一套。在顶楼。原来是一间仆人的储藏室,我想。”
“莫不是带有巨大熟铁门的那种地方?”
“正是。春天里美丽极了。林荫大道两侧排列着一棵棵酸橙树,树下成百万朵乌头花儿盛开。早在二月份,全是金黄色的。”
“乌头是什么?我对花卉的了解怕是少得可怜哪。”
弗莱彻先生解释乌头是什么,说明自己对它有多喜欢。在他看来,不知何故,乌头花多少代表了希腊格调。它们把春色带入寒冬,他说。斯特拉顿小姐听着他说这番话,心头怦然一动,觉得他的声音带有某种紧迫而又温柔、迷惘的腔调。
“你明天乘火车吗?”他终于说道。
“噢!每天都乘,”斯特拉顿小姐又禁不住咯咯笑了两声,“总是在慌慌张张地赶路。”
“我会留意你的。或许我们还能再品味一杯雪利葡萄酒呢。”
品味一词蕴含的某种意味,立即使火车車厢里原本沉闷的气氛平添了一抹亮色。这个词儿还带有些许暧昧和暖意:一种情分,几乎使斯特拉顿小姐开口就弗莱彻先生的领带说点什么,因为这条领带显然整天始终半藏衣领内,半露衣领外。然而她只是瞅着领带,一副迷惘的神态。俄顷,弗莱彻先生说:“假如我明天早晨见不到你,我们能不能现在说好傍晚五点半碰面?除非你得见你的朋友。”
哦!她可没觉得明天非见自己的朋友不可,斯特拉顿小姐说。弗莱彻先生以为她的朋友是个男人呢,她眼下多了这种印象,心头好不烦恼。
“噢!那好。”弗莱彻先生朝她羞涩地笑了笑,接着又说一切多么令人愉快,与她相逢啦,雪利酒啦,所有的事情。
斯特拉顿小姐说她也很愉快,及至终于回到家里,早早上了床,上下倒拿着她的报纸读了许久,这一做法耗神费力,致使她过后难以入睡。
翌晨弗莱彻先生走上火车时,手拿一小束花,裹在薄纸里的十五或二十朵黄色的乌头。斯特拉顿小姐见了惊讶不已,不曾想如此纤美的花儿,带有如此的希腊格调,正像弗莱彻先生声称的那样,能在冬季最黑暗的时刻展露清新冷艳的芳容,于是她起初一整天、继而本周余下的几天,都将其置于自己的写字台上,养在一只蓝色的平底塑料小杯里。
每次仔细端详它们,她都依稀看见弗莱彻先生的领带,上面的领结,那天早晨,在他左耳的什么部位。
打那以后,他俩开始每天傍晚在酒吧见面,恪守教规般地重复着品雪利葡萄酒的程序。同样,斯特拉顿小姐每晚到家以后,上下颠倒着读她的报纸,由此感受到一阵奇特而暧昧的激动,仿佛弗莱彻先生与她同床共寝似的。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持久不辍,若非斯特拉顿小姐一天傍晚碰巧说了句:“哦!我现在不见我的朋友了——我——呃,我们还是别提了吧。”
弗莱彻先生似乎认为这话终于让他免除了这种或那种义务,经过几分钟明显的凝神思索,说道:
“我一直想知道你是否愿意什么时候来瞧瞧我的小地方。它很普通,但——”
“哦!我挺乐意。”
“你不能借着什么小小的由头来吃午饭吗?那就礼拜天。”
斯特拉顿小姐说她将绝对乐意,旋即琢磨她该穿什么。一连几天她继续琢磨,最后拿定了主意,既然弗莱彻先生住在一栋维多利亚豪宅的寓所里,她的着装打扮最好与其相称。结果,她给自己买了套新礼服,淡绿色的两件套亚麻布礼服,穿在身上显得特别清爽,甚至有些高雅。她还决定破例一次,放弃颜色不同的长筒袜,改穿一双普普通通的肉红色尼龙袜。
“麻烦的是没有电梯。但愿你爬上楼梯不会累坏了。”
斯特拉顿小姐爬上最后四段逼仄陡峭的楼梯,心里惴惴不安,终于发现自己在打量这个被弗莱彻先生称为他的小地方的乱糟糟的斗室。一只煤气炉上堆着一摞书,一张无靠背长沙发上卧着三只白猫,一辆脚踏车上悬挂着几串山毛榉叶,一台旧式脚踏的缝纫机上,搁着餐盘、酒杯和几瓶调味番茄酱,一碗香蕉蛋奶沙司,一只没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一张书桌上胡乱堆放着许多报纸,有的报纸上面压着几盆番红花,有的压着几罐鱼酱,甚至有一处压着吃了一半的一条小葡萄干面包卷:整间屋子在她眼里像是来自某个疯狂的梦境。她还分明嗅到一股污浊的气味,搁馊了的鱼,混杂着呛鼻的尘烟,来自许久未扫的地板与久未打开的窗户。
“我这地方怕是有点紧巴巴的呢。”弗莱彻先生说。
斯特拉顿小姐对这话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只是不觉为弗莱彻先生感到哀怜而沮丧,他那身打扮同样吻合他这小地方简陋杂乱的环境。他的衣裳,一件仿佛在走气啤酒和车轴油溶液中浸过的圆领运动衫,一条松松垮垮的大号马粪色运动裤,使她簇新的淡绿色礼服顿时显得多余,她此刻几乎为穿它而羞臊。
弗莱彻先生将雪利酒倒进一对有疵点的漱口杯时,斯特拉顿小姐只能揣测他接下来能提供怎样的午餐。弗莱彻先生很快向她告以实情:
“我倒是凑合做了一道鸽肉牛肉饼。这菜我通常做得挺拿手。哪晓得我只顾去公园寻找报春花,煤气灶上的火头留得太高,结果给烧焦了。你大概不介意沙丁鱼吧?沙丁鱼和葡萄酒应当是绝佳的搭配。”
紧紧卡在煤气灶和书桌之间的是一张矮沙发,弗莱彻先生赶紧从沙发上拿走一篮芜菁甘蓝,一台便携式收音机,两只空雪利酒瓶,一只狩猎袋,一盒唱片,为他和斯特拉顿小姐腾出坐的地方。
“这是今年首开的报春花。今年开得很早。我特别想摘一些放到午餐桌上。”
报春花搁在一只蛋杯里。斯特拉顿小姐心底里复又泛起几许哀怜,把花贴近自己的面庞,嗅着柔嫩花瓣的清香。
“我一向认为,你从报春花的清香中得到了整个春天,”弗莱彻先生说,“它带着你重新历经你既往生命中所有的春天。”
弗莱彻先生类似的话语总是深深地打动着她,恍若弗莱彻先生抚摩了她的手,或是脸凑过来紧贴她的面颊。这类话语蕴蓄着一种无法容忍、难以捉摸的暧昧情分。
弗莱彻先生在倒酒和饮酒的间隙站起身,切下厚厚的几片褐面包和黄油。斯特拉顿小姐仍在忖度她尚未瞧见任何痕迹的午餐桌,见状忍不住问她可否顺便搭把手。
“我一般在缝纫机上用餐,”弗莱彻先生说,“机头往里一收便是一面平顶,大约适合两个人坐。”
“要不要我稍微整理一下?”
“哦!你愿意?那可太好了。”
斯特拉顿小姐格外仔细地整理午餐桌。她看到油渍斑驳的平纹白桌布上有几个洞眼,遂用胡椒瓶、盐瓶、餐盘和香蕉蛋奶沙司碗逐一将其遮盖。在她忙碌的同时,弗莱彻先生打开沙丁鱼罐头,说:“我相信沙丁鱼一定味道好。它们可是有了年头。你知道沙丁鱼存放越久味道越香吗,就像葡萄酒?”
斯特拉顿小姐说不知道,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自己并不怎么喜欢沙丁鱼,尽管这话她碍于情面说不出口,只顾思索弗莱彻先生是否允许她做个水煮荷包蛋,或是煎一张蛋饼,或是别的什么。
第三杯雪利酒落肚,她壮起胆子,终于决定提出这一建议。这将是世上最容易办到的事情。他喜欢什么呢?水煮荷包蛋还是蛋饼?
“我喜欢蛋饼,说真格的。”
很好,斯特拉顿小姐说,那她就煎蛋饼。她颇为自己的蛋饼而骄傲。弗莱彻先生可有什么给蛋饼调味的佐料啊?奶酪或是火腿,或是别的什么?
“我在什么地方搁了一罐蘑菇。”弗莱彻先生说,旋即在他的小地方乱糟糟的杂物中搜寻起来,最后从书桌里的几个猫食罐头中,找到混杂其间的那个蘑菇罐头。
“我知道正是这一罐,因为它上面没有标牌。”
斯特拉顿小姐想起猫食顿时反胃想吐,满心指望正是这罐。结果的确如此,于是她开始煎蛋饼。蛋饼做得真好,弗莱彻先生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夸赞,一副特有的羞涩而热情的腔调。
午餐后,弗莱彻先生坐在沙发上倒着读星期日的报纸。其间他一抬眼,瞧见斯特拉顿小姐也在倒着读她的报纸,说道:
“我看你渐渐习惯这样读了。它真的没那么难,对吧?”
是的,斯特拉顿小姐说,不难,随后觑见弗莱彻先生在端详她的膝蓋,她的裙子已经撩到膝盖上方几英寸。她希望这足以表明弗莱彻先生正对她的两条腿产生一种更强烈、更暧昧的兴趣,最终他大概会招呼她和自己一起坐在沙发上吧。然而这类事情到底没有发生。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还是什么都没发生。弗莱彻先生始终和善、礼貌、体贴、细致,急于讨她的欢心。他在火车上带给斯特拉顿小姐一束束芬芳的紫罗兰,一次还携来一捧樱草花和一盆白色的仙客来,让她放在写字桌上,后来又适时地送上一捧玫瑰。晚上他俩共饮雪利酒。星期天她为他烧午饭,身处逼仄的环境,缝纫机、三只猫儿、到处散落的报纸,以及浓烈呛鼻的鱼腥味充斥其间。
但她最盼望的东西却没有丝毫迹象。她盼望弗莱彻先生做出某个并非纯属友谊的动作:触碰她的膝盖,把脸贴着她的脸,做个温存的姿态,甚至爱情的姿态。每到夜里,独自躺在床上,她甚至怀着疯狂的意念,相信弗莱彻先生哪天会在一时冲动之下亲吻她,甚至狂热地搂住她。沉浸在这些情绪之中时,她总是乐意乖乖地顺从对方。
可是到了仲夏时节,什么也没发生;有些绝望的斯特拉顿小姐,终于决定为此做点什么。
她决定重新介绍自己的朋友。
她的朋友,按照她的推测,兴许能在弗莱彻先生心目中勾起一种对她本人的更浓厚的兴趣,甚或嫉妒。
“喏,我真怕今晚不能跟你见面呢。你瞧,我的朋友——”
奇怪的是,她日益增多的拒绝,对弗莱彻先生产生了一种与她的希望和意图截然相反的效果。弗莱彻先生不仅没有一点留意、激情甚或嫉妒,一次次痛苦地遭拒,反而使他变得越发沮丧,越发紧紧地把自己封闭起来。终于,七月一个湿热的星期天,两人吵了一架。
出人意料地持续了一段时日的好天气,促使弗莱彻先生提议在公园野餐。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长长的林荫道上,两旁的酸橙树鲜花盛开:一个香气飘溢的广阔仙境,尽显夏日的芳华。
弗莱彻先生建议一点钟开始野餐,但斯特拉顿小姐两点过后才到。弗莱彻先生对此发了一点牢骚,为她可能遭遇什么不测略显急躁,她说:“噢,我刚才接到我朋友的电话——我不太可能不聊聊——”
除了存心迟到以外,斯特拉顿小姐还给自己添置了一条新的夏裙:一条淡黄色的短袖府绸连衣裙,颈部故意开口很低。她这样做,盖因偶读一文受到的启发。一家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探讨了女性用以吸引男性的种种由来已久的方式之成因。通过裸露腿部吸引异性的方式使用相对较晚,女人的腿部始终被裹得严严实实,直到现代才发生变化;而另一方面女性的胸部则是长期袒露的。
她和弗莱彻先生坐在一株古老而巨大的酸橙树的树荫里,共进野餐,吃着火腿、绿叶蔬菜沙拉、奶酪、番茄,最后是奶油草莓,佐以一瓶阿尔萨斯白葡萄酒。空气中散发着酸橙花馥郁而又奇异的香气。酒也染上了几许花香,甘爽的味道与周遭的香气融为一体。
吃完奶油草莓,斯特拉顿小姐仰卧在草地上,两条腿漫不经心地裸露着,胸部的轮廓曲线依稀可见。她不时发出饱食之余放纵的一声叹息,嗅进酸橙花的香气之际伴有一种声音,表达一阵如梦似幻的狂喜。弗莱彻先生唯一的反应是上下颠倒着看报纸。
“你必须看报纸吗?”
“是啊,我总是在看。你有报纸而不看,还有什么意思哩。”
“这么好的天气,你居然只想把脑瓜埋进许许多多的股票期货或什么名堂里。”
“哦,抱歉。当然如果这让你反感——”
“我可没说这让我反感。我说这么好的天气,你能做的只是变成一只书虫——一只报纸虫——或类似什么虫。”
“我想我不介意虫这个词儿。你到底怎么啦?”“我一点也没怎么样,照你爱用的说法。”
“你让我大吃一惊。我可从没听见你这样说话啊。”
斯特拉顿小姐面色阴冷毅然不语地躺了几分钟。而后,她蓦地吐出急迫的轻轻一声:“我的上帝!”
“请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弗莱彻先生问道。
“噢!读你讨厌的报纸去吧!”
“说真的。”
斯特拉顿小姐沉默而乏力地仰望天空,目光透过她头顶上方宽展的绿叶花簇的华盖的缝隙。整个天宇只能看见星星点点的渺小碎片,犹如一只蔚蓝色杯子摔得四散飞溅的玻璃碴。
“你指望我做什么呢?”弗莱彻先生说。
“做什么?喏,你可以欣赏我的新连衣裙,比方说。或者注意它也成啊。”
“我已经注意到它了。我喜欢它。”“喜欢它!我的朋友可是为了它如痴如狂呢。”“我是否可以说,你宁愿和你的朋友待在一起?”
“我可没说这话。我只是说——啊!不说也罢。”
他俩默然无语地又待了半个多小时。有一回,斯特拉顿小姐仿佛被午后的暑热熏蒸得透不过气来,进一步松开连衣裙的领扣,用手帕擦拭裸露微凸的汗津津的脖颈和胸口。
挨到最后,弗莱彻先生以一种平淡的、几近病态的单调声音说道:
“我们好像浪费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们!”斯特拉顿小姐再也忍不住了,霍地立起身来,“我们,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把我包括进去,像他们说的那样。”
“噢!我亲爱的,我從没想过我们会到这个地步。”
“别用‘我亲爱的称呼我!”
斯特拉顿小姐已经拔腿走开了,令弗莱彻先生惊愕不已。
“你到底要去哪儿?”
“去哪儿?你以为我会去哪儿?我要去见我的朋友。注意这个词。朋友——朋友!”
斯特拉顿小姐高昂着头,顶着火辣辣的七月骄阳,怒气冲冲地走出公园。
自此以后的将近两个月,她再也没在火车上遇到弗莱彻先生。她晚上有时去酒吧消磨时间,也不曾见过他的身影。她一口一口地抿着雪利,巴望他能奇迹般地忽然出现在她眼前。
终于,她实在憋不住了,径自前往弗莱彻先生的公寓,他的小地方。她爬上长长的一段段楼梯,一遍遍地敲门,摁门铃,没有得到一声回应。她随后走下楼梯时,下面人家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对她说:“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找弗莱彻先生。”
“噢!弗莱彻先生如今不住这儿了。”
“不住这儿?”
“他在伦敦租了一间公寓,说他发现每天乘火车旅行太疲劳了。”
“你不知道地址吗?”
“不知道。他的离去实在太突然了。我们全都认为他一副病态。这些楼梯实在让他吃不消。你时常听见他拼命喘息的声音。哮喘病的声音。”
“他有哮喘病?”
“噢!可怜。有一两回我以为他就要死了。我的确不好意思说,我每天都看讣告栏——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我知道,可是我不想错过消息。”
斯特拉顿小姐也开始看讣告栏了。几乎过了一年之后她从报上看到,弗莱彻先生——一向倒着读报,只能借助一些简单的物体,诸如乌头、一捧报春花、一杯雪利或一两枝玫瑰向她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弗莱彻先生——去世了。
斯特拉顿小姐现已嫁为人妇,丈夫名叫劳林森,他开了一家商店,经营油漆、乳胶等化工材料的批发。他们所住的别墅由一家装潢公司提供巨细无遗、完美无缺的装修服务,花园也做了景观美化,使之具有一种讲究专业与条理的修整如新的氛围,没有瑕疵却也没有生气。
劳林森是一个恪守习惯的人,每天清晨六点半起身,以便完成一套宗教仪式般的严苛程序,包括修胡髭,抹发油,面部涂上须后水,刷牙,修剪光洁有如贝壳的指甲,好在钟敲九点之际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中午他在办公室里用餐,每晚九时到家,发现一如从前的斯特拉顿小姐在玩单人纸牌游戏,或编织衣物,或读书,或看电视,等着吃晚餐。每当他离家在外,无论多远,他的办公室都会一天两次打电话给他,不厌其详地报告当日的各项数据、订单和事务。在外用餐时,他研读而非浏览菜单,同样细致而敏锐地注视每一道菜肴,仿佛它像圣经箴言一般神圣。
在斯特拉顿小姐看来,他的行为举止同样严苛、准确,毫无瑕疵,井井有条。他自以为她拥有所能希冀的一切。她如今什么都不缺。
有时,在这个安全而有序的世界当中,斯特拉顿小姐会想起弗莱彻先生,想起一些小东西,诸如他的乌头,他的报春花,他的雪利。有时,当她独处或劳林森不在看她之际,她又开始倒着读她的报纸。
只有在那时,世界在她眼里才是正常的,她才能在观察它的时候生出更有益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