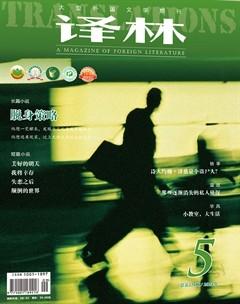译者的丈夫
〔美国〕玛丽·戈登

我从没和芭芭拉谈论过我的第一段婚姻,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是在我遇见她很久之前的事,而且那段婚姻很短暂,我没想到会和我现在的婚姻有任何交集。
我的前妻叫布兰达。学生时代,她离开伯明翰,来美国进行一年的交换学习。在那一年里,我们相遇了,然后很快就结了婚。布兰达虽然有语言天赋,但对学习并不上心。她是那种爱咯咯傻笑的女孩。像她这样的英国女孩在六十年代末的美国是很受欢迎的,那时披头士乐队和其他英国的东西也很流行。当时,人们认为有着雪白肌肤和健壮小腿的金发姑娘就是好姑娘。多喝了一两杯的陌生人友好地在她们屁股上拍一下,她们也不会介意,也不会把事情往坏处想。布兰达就是这种天性善良的好姑娘。
但布兰达还是离开了我,投向了一个滑雪教练的怀抱。这个滑雪教练是我雇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指导,布兰达却觉得雇用教练这件事就是个天大的笑话。随时可能摔断腿,然后在医院里度过整个假期的人应该是她,因为她压根没滑过雪。这个教练叫汉斯,是个奥地利人。他和布兰达一直用德语交流,而我又不懂德语,不知道他们在谈些啥。
我猜在布兰达眼里我太过古板。她经常说:“迪基,你太严肃了。”过去,只有布兰达叫我迪基,其他人都叫我迪克。现在,大家都叫我理查德。不过布兰达说她就喜欢我严肃的样子,但我觉得她没多久就厌倦了我。我母亲曾提醒说布兰达太轻浮。我遇见布兰达是因为我想进印第安纳大学系统学习比较文学,我必须精通法语和西班牙语,而她刚好是一名西班牙语家教。我跟她结婚后,因为要准备各种考试,我没法每天晚上陪她一起去镇上玩。我并不怪她爱上了汉斯,但下意识地会把博士资格考试的失败归咎于她的离开。好吧,事实是竞争太激烈,许多人没有通过考试。我最后只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有一次,我谈起这件事,芭芭拉说我的语气太悲伤了,好像我快要死了一样。不过这个学位还是帮我找到了好工作。我在纽约一所顶尖的预备学校教法语和西班牙语,这所学校在所有英语国家里数一数二。
在这所学校,我遇见了芭芭拉。她儿子西班牙语考试不及格,我尽心尽力辅导他,提高了他的成绩。芭芭拉比她儿子内森还要感激我。说实话内森不是个好学生,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父母都很有学问。芭芭拉的前夫是著名的神经学家,而喜爱文学的人都知道芭芭拉的名字。
遇到芭芭拉后的十五年里,我都没听说过布兰达的消息。和芭芭拉相处三年后,我与她喜结连理,到现在我们结婚十二年了。当我用“喜结连理”这个词时,芭芭拉总是嘲笑我是她认识的人里唯一的一个老古董。有时,她会戏称我为“郎君”。
芭芭拉经常开我的玩笑,但我一点不介意,甚至乐在其中。她的朋友也会和她一起开我的玩笑,有时说的话还很粗俗,这时我就会让她们适可而止。我认为她的朋友觉得我不谙世事,但如果她们知道我和芭芭拉在床上的翻云覆雨,肯定会大吃一惊。如果她们知道我在搬进芭芭拉的复式公寓前,曾和许多学生的妈妈在我单身公寓的折叠床上睡过,肯定也会震惊不已。
芭芭拉的小说被翻译成几种语言,我过去常看法语版和西班牙语版,惊讶地发现里面有很多错误。为了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我会一一列出错误,发送给译者。但后来芭芭拉劝我别这样做,称他们一个字都不会改,只会让她看上去有强迫症。我反驳强迫症和准确是两码事。芭芭拉说我应该休息,说她想好了如何消耗我的精力。说完,她把我拉上床。
因此,直到在马德里,我才看了她新作的西班牙语版。当布兰达的名字映入眼帘时,我如遭雷击。
我的前妻是我第二任妻子小说的译者,这种极小概率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我从没想过这种巧合,否则我肯定会把关于布兰达的事告诉给芭芭拉。我更没想过布兰达有这么高的水平,能够翻译芭芭拉的小说。要知道她仅为了一个滑雪教练就抛弃了我,而芭芭拉的作品绝对是一流的。我突然注意到我两任妻子的名字都有两个音节,并且都是以b开头、以a结尾,但这个发现没什么大不了。
布兰达没写信告诉芭芭拉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想这是件好事,但也有可能是她不知道我是芭芭拉的丈夫。芭芭拉认为放太多个人信息显得俗套,所以书皮上只写了“芭芭拉·汉诺威,现居纽约”,根本没提我的名字。
布兰达翻译芭芭拉的新作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但书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不过,如果她翻译过芭芭拉的其他小说,那句话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况且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布兰达可能根本没注意到。
芭芭拉喜欢听我讲我的情史,但那不是要挑起她的情欲。她擅长描写人类行为,她把我的情史说成是她的“小说素材”。这就像我和一个医生结婚,生病了要把病情告诉给医生一样。
布兰达做爱时有个怪癖,她只喜欢上位。这不算什么,怪就怪在她兴奋的时候会唱一首童谣,看上去傻傻的。“骑上小公马,去往班伯里,去看美人骑白马,”她越唱越激动,“美人满手戴戒指,脚趾挂铃铛。”唱到“走到哪儿音乐跟到哪儿”时,她会达到高潮。不得不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芭芭拉正好在布兰达翻译的那本小说里用了这首童谣。故事的主要人物没有说出来,它只是穿插在主人公的一段风流韵事里,而那段经历只用了两页纸就结束了,所以根本不起眼。我告诉芭芭拉这首童谣时,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
我曾向西班牙出版商建议采访芭芭拉时不用让翻译来,因为我精通西班牙语并且非常了解我的妻子。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不,不,汉诺威先生,您可以休息下,也可以参观下这座美丽的城市。”我说过自己从未到过马德里,那些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能再收回。
本该和布兰达见面的那天,我撒谎自己生病了。芭芭拉习惯了我在旅游的时候胃疼,对我这个谎言她没有多想。
我们住在西贝莉广场的丽兹酒店,通过房间的窗户可以俯瞰普拉多博物馆。天知道住在这里一晚上要花多少钱!坐在长榻上,我喝完了四瓶格兰菲迪,接着喝第五瓶。
就这样度过一个小时后,我看见芭芭拉来到了露天广场,向酒店大门走来。看来她按西班牙传统享用了一顿漫长的午餐。
天哪,芭芭拉似乎不是独自一人,她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那个人就是布兰达。我清楚地看见她们走在广场的梧桐树下。她们手挽着手,另一只手摆动着,手上的黑色小包很相像。
我突然如释重负,感觉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我早就不记得她们身高相同。她们的发色也很像。芭芭拉把头发染成了铂金色,布兰达可能还是天然金发,毕竟我俩已经三十年没见过面了。
她们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
她们在放声大笑。现在,她们走到了遮阳篷下,我的视线被挡住,只能猜测她们在等电梯了,很快就会出现在房间里。
我穿着得体的休闲装——布克兄弟的卡奇裤、黄色的鳄鱼牌衬衫、流苏装饰的巴利平底鞋——布兰达肯定会吃惊。最后一次同她见面时,我穿的是救世军制服,瘦得像根稻草。现在,我和芭芭拉一周在健身房锻炼三次,身体很棒。
我想象自己潇洒地面对她们。我会模仿汉弗莱·鲍嘉的声音说:“世界上有那么多酒馆,你偏偏走进了这一家。”布兰达肯定会笑。
现在,芭芭拉打开了房门。
闭上眼,我听见她们仍在笑。
芭芭拉唤我:“亲爱的理查德。”布兰达则叫道:“迪基宝贝。”
她们都感到不可思议,一直在说:“真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们去外面吃饭,她们要我请客,但这有点难办,因为出版商已经承担了芭芭拉的所有花销,不过当时我认为自己最好保持沉默。
布兰达向服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的丈夫”,服务员看起来很困惑,但还是点头微笑。我认为她们香槟喝多了。当然,我不是抱怨她们,事实上,我对当时的情形感到十分庆幸。
她俩中的一人会时不时地唱起“骑上小公马”,接着两人都哈哈大笑。她们一见如故,而我整晚都插不上话。
当然,我也没那么多话要说。
(刘杰: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郵编:411105)